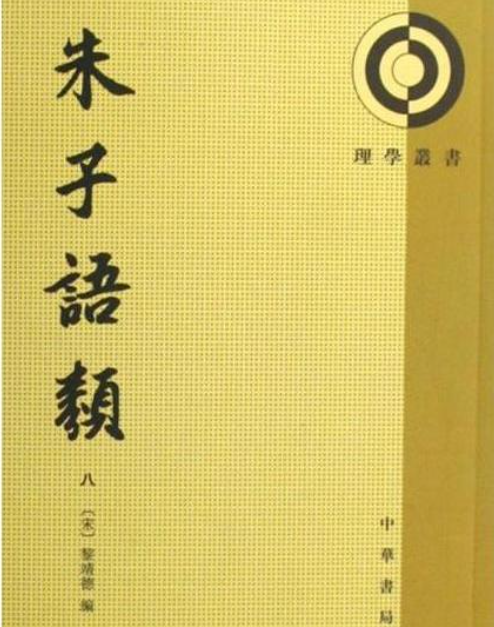易八
咸
「否泰咸恒损益既济未济,此八卦首尾皆是一义。如咸皆是感动之义之类。咸内卦艮,止也,何以皆说动?」曰:「艮虽是止,然咸有交感之义,都是要动,所以都说动。卦体虽是动,然才动便不吉。动之所以不吉者,以内卦属艮也。」
咸就人身取象,看来便也是有些取象说。咸上一画如人口,中三画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阳画有头之象,中二阴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辅」,于五爻言之。内卦以下亦有足象。砺。
问:「本义以为柔上刚下,乃自旅来。旅之六五,上而为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为咸之九五,此谓『柔上刚下』,与程传不同。」先生问:「所以不同,何也?」铢曰:「易中自有卦变耳。」曰:「须知程子说有不通处,必着如卦变说,方见得下落。此等处,当录出看。」
「山上有泽,咸」,当如伊川说,水润土燥,有受之义。又曰:「上若不虚,如何受得?」又曰:「上兑下艮,兑上缺,有泽口之象;兑下二阳画,有泽底之象;艮上一画阳,有土之象;下二阴画中虚,便是渗水之象。」砺。
问:「『君子以虚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择合而受之。』以量,莫是要着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随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虚了。」又问:「『贞吉悔亡』,易传云:『贞者,虚中无我之谓』;本义云:『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如『贞』字作『正而固』,仔细玩索,自有滋味。若晓得正而固,则虚中无我亦在里面。」又问:「『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莫是此感彼应,憧憧是添一个心否?」曰:「往来固是感应。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来应。如正其义,便欲谋其利;明其道,便欲计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时,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这便是憧憧底病。」
厚之问「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曰:「往来自不妨,天地间自是往来不绝。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德明录云:「如暑往寒来,日往月来,皆是常理。只着个『憧憧』字,便闹了。」又问:「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来顺应』,便不是『朋从尔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这一段,旧看易惑人,近来看得节目极分明。」
往来是感应合当底,憧憧是私。感应自是当有,只是不当私感应耳。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圣人未尝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这便是私了。感应自有个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义理,却不可不思。
问:「咸传之九四,说虚心贞一处,全似敬。」曰:「盖尝有语曰:『敬,心之贞也。』」
易传言感应之理,咸九四尽矣。
问:「伊川解屈伸往来一段,以屈伸为感应。屈伸之与感应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则感伸,伸则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观之:出则必入,出感入也;入则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则有应,应复为感,所感复有应。』屈伸非感应而何?」洽。
或问易传说感应之理,曰:「如日往则感得那月来,月往则感得那日来;寒往则感得那暑来,暑往则感得那寒来。一感一应,一往一来,其理无穷。感应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应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动皆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则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则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周易传『有感必有应』,是如何?」曰:「凡在天地间,无非感应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且如雨旸,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个旸出来;旸不成只管旸,旸已是应处,又感得雨来。是『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寒暑昼夜,无非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晓,须着起来;一日运动,向晦亦须常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来,一语一默,皆是感应。中人之性,半善半恶,有善则有恶。古今天下,一盛必有一衰。圣人在上,兢兢业业,必日保治。及到衰废,自是整顿不起;终不成一向如此,必有兴起时唐贞观之治,可谓甚盛。至中间武后出来作坏一番,自恁地塌塌底去。至五代,衰微极矣!国之纪纲,国之人才,举无一足恃。一旦圣人勃兴,转动一世,天地为之豁开!仁宗时,天下称太平,眼虽不得见,想见是太平。然当时灾异亦数有之,所以驯至后来之变,亦是感应之常如此。」又问:「感应之理,于学者工夫有用处否?」曰:「此理无乎不在,如何学者用不得?『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这道理。研精义理于内,所以致用于外;利用安身于外,所以崇德于内。横渠此处说得更好:『「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此几句亲切,正学者用功处。」
林一之问「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曰:「如风来是感,树动便是应;树拽又是感,下面物动又是应。如昼极必感得夜来,夜极又便感得昼来。」曰:「感便有善恶否?」曰:「自是有善恶。」曰:「何谓『心无私主,则有感皆通』?」曰:「心无私主,不是溟涬没理会,也只是公。善则好之,恶则恶之;善则赏之,恶则刑之,此是圣人至神之化。心无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则遍天下皆寒,热则遍天下皆热,便是『有感皆通』。」曰:「心无私主最难。」曰:「只是克去己私,便心无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应,不相契者则不应。如好读书人,见读书便爱;不好读书人,见书便不爱。」
器之问程子说感通之理。曰:「如昼而夜,夜而复昼,循环不穷。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木之问:「所谓『天下之理,无独必有对』,便是这话否?」曰:「便是。天下事那件无对来?阴与阳对,动与静对,一物便与一理对。君可谓尊矣,便与民为对。人说碁盘中间一路无对,某说道,便与许多路为对。」因举「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与屈伸消长之说。邵氏击壤集云:「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因说:「易咸感处,伊川说得未备。往来,自还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静为主,则吉而悔亡。至于憧憧则私为主,而思虑之所及者朋从,所不及者不朋从矣。是以事未至则迎之,事已过则将之,全掉脱不下。今人皆病于无公平之心,所以事物之来,少有私意杂焉,则陷于所偏重矣。」
赵致道问感通之理。曰:「感,是事来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处之意。」
问:「程子说『感应』,在学者日用言之,则如何?」曰:「只因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与应。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应。如王文正公平生俭约,家无姬妾。自东封后,真宗以太平宜共享,令直省官为买妾,公不乐。有沈伦家鬻银器花篮火筒之属,公嚬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后姬妾既具,乃复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银器而用之。此买妾底便是感,买银器底便是应。」
系辞解咸九四,据爻义看,上文说「贞吉悔亡」,「贞」字甚重。程子谓:「圣人感天下,如雨旸寒暑,无不通,无不应者,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贞矣,则吉而悔亡。盖天下本无二理,果同归矣,何患乎殊涂!果一致矣,何患乎百虑!所以重言「何思何虑」也。如日月寒暑之往来,皆是自然感应如此。日不往则月不来,月不往则日不来,寒暑亦然。往来只是一般往来,但憧憧之往来者,患得患失,既要感这个,又要感那个,便自憧憧忙乱,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昼必有夜,设使长长为昼而不夜,则何以息?夜而不昼,安得有此光明?春气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无秋冬,则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无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来之理,所以必待迭相为用,而后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个感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为应也。春夏是一个大感,秋冬则必应之,而秋冬又为春夏之感。以细言之,则春为夏之感,夏则应春而又为秋之感;秋为冬之感,冬则应秋而又为春之感,所以不穷也。尺蠖不屈,则不可以伸;龙蛇不蛰,则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伸往来感应必然之理。夫子因「往来」两字,说得许多大。又推以言学,所以内外交相养,亦只是此理而已。横渠曰:「事豫吾内,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养吾内。」此下学所当致力处。过此以上,则不容计功。所谓「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至,非思勉所及,此则圣人事矣。
或说「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云:「一往一来,皆感应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则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应,所谓『朋从尔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问:「『往来』,是心中憧憧然往来,犹言往来于怀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安得为心中之往来?伊川说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来,感应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问:「是憧憧于往来之间否?」曰:「亦非也。这个只是对那日往则月来底说。那个是自然之往来,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来。『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底心,不能顺自然之理,犹言『助长』、『正心』,与计获相似。方往时,又便要来;方来时,又便要往,只是一个忙。」又曰:「方做去时是往,后面来底是来。如人耕种,下种是往,少间禾生是来。」问:「『憧憧往来』,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应。自然往来,如王者,我感之也,无心而感;其应我也,无心而应,周遍公溥,无所私系。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问:「此以私而感;恐彼之应者非以私而应,只是应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应。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间被我之惠者则以我为恩,不被我之惠者则不以我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驱失前禽。』去者不以为恩,获者不以为怨,如此方是公正无私心。」又问:「『天下何思何虑』?人固不能无思虑,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虑,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应之理,本不消思虑。空费思量,空费计较,空费安排,都是枉了,无益于事,只顺其自然而已。」因问:「某人在位,当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翕,受敷施』。每广坐中见有这边人,即加敬与语,其它皆不顾;以至差遣之属,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祸也。」曰:「这事便是难说。今只是以成败论人,不知当日事势有难处者。若论大势,则九分九厘,须还时或其人见识之深浅,力量之广狭,病却在此。以此而论,却不是。前辈有云:『牢笼之事,吾不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说一般话,或虑其人不好,他日或为吾患,遂委曲牢笼之,此却是憧憧往来之心。与人说话,或偶然与这人话未终,因而不暇及其它,如何逐人面分问劳他得!李文靖为相,严毅端重,每见人不交一谈。或有谏之者,公曰:『吾见豪俊跅弛之士,其议论尚不足以起发人意。今所谓通家子弟,每见我,语言进退之间,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识见,而足与语,徒乱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害为贤相,岂必人人皆与之语耶?宰相只是一个进贤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辈尝言:『做宰相只要办一片心,办一双眼。心公则能进贤退不肖,眼明则能识得那个是贤,那个是不肖。』此两言说尽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贤,其所恶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个知得,更何用牢笼!且天下之大,人才之众,可人人牢笼之耶?」或问:「如一样小人,涉历既多,又未有过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将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间此等小人自然退听,不容他出来也。今之为相者,朝夕疲精神于应接书简之间,更何暇理会国事!世俗之论,遂以此为相业。然只是牢笼人住在那里,今日一见,明日一请,或住半年、周岁,或住数月,必不得已而后与之。其人亦以为宰相之顾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贤愚同滞,举世以为当然。有一人焉,略欲分别善恶,杜绝干请,分诸阙于部中,己得以免应接之烦,稍留心国事,则人争非之矣!且以当日所用之才观之,固未能皆贤,然比之今日为如何?今日之谤议者,皆昔之遭摈弃之人也。其论固何足信!此下逸两句。若牢笼得一人,则所谓小人者,岂止此一人!与一人,则千百皆怨矣。且吾欲牢笼之,能保其终不畔己否?已往之事,可以鉴矣。如公之言,却是憧憧往来之心也。其人之失处,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真知贤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洁,岂可弃之耶?」曰:「公欲取贤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祸哉?今世之人,见识一例低矮,所论皆卑。某尝说,须是尽吐泻出那肚里许多鏖糟恶浊底见识,方略有进处。譬如人病伤寒,在上则吐,在下则泻,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诸公多有为持平之说者,如何?」曰:「所谓近时恶浊之论此是也,不成议!论某尝说,此所谓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僩问:「胡文定说,元佑某人建议,欲为调停之说者云:『但能内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体天理人欲者也。此语亦似持平之论,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论。然小人亦有数般样,若一样可用底,也须用。或有事势危急,翻转后,其祸不测。或只得隐忍,权以济一时之急耳,然终非常法也。明道当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诸公用熙丰执政之人,与之共事,令变熙丰之法。或他日事翻,则其罪不独在我。他正是要使术,然亦拙谋。谚所谓『掩目捕雀』,我却不见雀,不知雀却看见我。你欲以此术制他,不知他之术更高你在。所以后来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卒至帘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吃剑得!』便至如此,无可平之理,尽是拙谋。某尝说,今世之士,所谓巧者,是大拙,无有能以巧而济者,都是枉了,空费心力。只有一个公平正大行将去,其济不济,天也。古人间有如此用术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此,决定无益。张子房号为有意智者,以今观之,可谓甚疏。如劝帝与项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胜。」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个『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它费心费力,用智用数,牢笼计较,都不济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见百官,皆以班见。国忌拈香归来,回班以见。宰相见时有刻数,不知过几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风拦断。也是省事,拦截了几多干请私曲底事。某旧见陈魏公汤进之为相时,那时犹无甚人相见,每见不过五六人,十数人,他也随官之崇卑做两番请。今则不胜其多,为宰相者每日只了得应接,更无心理会国事。如此者谓之有相业有精神。秦会之也是会做,严毅尊重,不妄发一谈。其答人书,只是数字。今宰相答人书,[戋刂]地委曲详尽,人皆翕然称之。只是不曾见已前事,只见后来习俗,遂以为例。其有不然者,便群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项云:『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请以奏牍闻于朝廷,某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喻,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则可以通书简,分付吏人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理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此皆前辈做处。」又曰:「伊川云:『[犬旬]俗雷同,不唤做「随时」;惟严毅特立,乃「随时」也。』而今人见识低,只是[犬旬]流俗之论,流俗之论便以为是,是可叹也!公们只是见那向时不得差遣底人说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见得难。且如有两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为贤,一人为不肖。若自家执政,定不肯舍其贤而举其不肖,定是举其贤而舍其不肖。若举此一人,则彼一人怨,必矣,如何尽要他说好得!只怕自家自认不破,贤者却以为不肖,不肖者却以为贤,如此则乖。若认得定,何害?又有一样人底,半间不界,可进可退,自家却以此为贤,以彼为不肖,此尤难认,便是难。」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举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
问:「咸之九五传曰:『感非其所见而说者。』此是任贞一之理则如此?」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是其心量该遍,故周流如此,是此义也。」
恒
恒是个一条物事,彻头彻尾,不是寻常字。古字作「●」,其说象一只船两头靠岸,可见彻头彻尾。值。
履之问:「常非一定之谓,『一定则不能恒矣』。」曰:「物理之始终变易,所以为恒而不穷。然所谓不易者,亦须有以变通,乃能不穷。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亲亲,然所谓『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则又有变焉。惟其如此,所以为恒。论其体则终是恒。然体之常,所以为用之变;用之变,乃所以为体之恒。」
恒,非一定之谓,故昼则必夜,夜而复昼;寒则必暑,暑而复寒,若一定,则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今日道合便从,明日不合则去。又如孟子辞齐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馈,皆随时变易,故可以为常也。
能常而后能变,能常而不已,所以能变;及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说变而后能常,非是。
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这个只是说久。
物各有个情。有个人在此,决定是有那羞恶、恻隐、是非、辞让之情。性只是个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灭,然而头面却只一般。长长恁地,这便是「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之义。「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叔重说:「『浚恒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程氏所谓『守常而不能度势』之意。」曰:「未见有不安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
问:「『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谓常其柔顺之德,固贞矣。然此妇人之道,非夫子之义。盖妇人从一而终,以顺为正,夫子则制义者也。若从妇道,则凶。」曰:「固是如此。然须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贞』之象,占者若妇人则吉,夫子则凶。大底看易,须是晓得象占分明。所谓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视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为妇人,又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为吉凶耳。又如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于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虽正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则无羞吝。
遯
问:「遯卦『遯』字,虽是逃隐,大抵亦取远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辽绝,象之以君子远小人,则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绝之义,须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渐远者愈善也。」曰:「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学履。
问:「『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说能遯便亨。下更说『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阴方微,为他刚当位而应,所以能知时而遯,是能『与时行』。不然,便是与时背也。」砺。
问:「『小利贞,浸而长也』,是见其浸长,故设戒令其贞正,且以宽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此与否初、二两爻义相似。」同。
问:「『小利贞』,以彖辞『小利贞,浸而长也』之语观之,则小当为阴柔小人。如「小往大来」、「小过」、「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则亨,小人则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长之故,而浸迫于阳也。此与程传『遯者,阴之始长,君子知微,故当深戒。而圣人之意未遽已,故有「与时行,小利贞」之教』之意不同。」曰:「若如程传所云,则于『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之下,当云『止而健,阴进而长,故小利贞』。今但言『小利贞,浸而长也』,而不言阴进而长,则小指『阴小』之『小』可知。况当遯去之时,事势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说虽善,而有不通矣。」又问:「『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当晦处静俟耳。此意如何?」曰:程传作『不可往』,谓不可去也。言『遯已后矣,不可往,往则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为无梨』。某窃以为不然。遯而在后,尾也。既已危矣,岂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辞看,尤分明。」先生又言:「『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说,吐活反。九四:『君子吉,小人否。』否,方九反。」
伊川说「小利贞」云,尚可以有为。阴已浸长,如何可以有为?所说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杀了董卓,谢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时节,不是浸长之时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为在下位有为之兆者,则可以去。大臣任国安危,君在与在,君亡与亡,如何去!又曰:「王允不合要尽杀梁州兵,所以致败。」砺。
「遯尾厉」,到这时节去不迭了,所以危厉,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贤人君子有这般底多。
问:「『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对,更不可与相接。若臣妾,是终日在自家脚手头,若无以系之,则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今学者平日只在灯窗下习读,不曾应接世变;一旦读此,皆看不得。某旧时也如此,即管读得不相入,所以常说易难读。」砺。
问:「九五『嘉遯』,以阳刚中正,渐向遯极,故为嘉美。未是极处,故戒以贞正则吉。」曰:「是如此。便是『刚当位而应』处,是去得恰好时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见小人不嫌,却与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贞正。」砺。
大壮
问:「大壮『大者正』与『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阳,下『正大』是说理。」曰:「亦缘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说此。」学履。
大壮「利贞」,利于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则天地之情不过于此。
问:「『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伊川云云,其义是否?」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须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严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决,济得甚事!」
或问:「伊川『自胜者为强』之说如何?」曰:「雷在天上,是甚威严!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则威严果决以去其恶,而必于为善。若半上落下,则不济事,何以为君子。须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礼。」
此卦如「九二贞吉」,只是自守而不进;九四「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却是有可进之象,此卦爻之好者。盖以阳居阴,不极其刚,而前遇二阴,有藩决之象,所以为进,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阳隔之,不得进也。又曰:「『丧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汉食货志『疆埸』之『埸』正作『易』。盖后面有『丧羊于易』,亦同此义。今本义所注,只是从前所说如此,只且仍旧耳。上六取喻甚巧,盖壮终动极,无可去处,如羝羊之角挂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艰则吉』者,毕竟有可进之理,但必艰始吉耳。」
问:「大壮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对九二,处非其位;九四对上九,本非相应,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壮便是过了,纔过便不好。如睽卦之类,却是。易之取爻,多为占者而言。占法取变爻,便是到此处变了。所以困卦虽是不好,然其间利用祭祀之属,却好。」问:「此正与『群龙无首』、『利水贞』一般。」曰:「然。却是变了,故如此。」
此卦多说羊,羊是兑之属。季通说,这个是夹住底兑卦,两画当一画。
晋
「康侯」,似说「宁侯」相似。「用锡马」之「用」,只是个虚字,说他得这个物事。
「昼日」,是那上卦离也。昼日为之是此意。
问:「初六『晋如、摧如』,象也;『贞吉』,占辞。」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两句。恐『贞吉』说不明,故又晓之。」又问:「『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盖周礼有享先妣之礼。」又问「众允悔亡」。曰:「『众允』,象也;『悔亡』,占也。」又问:「『晋其角,维用伐邑』,本义作『伐其私邑』,程传以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传多不肯说实事,皆以为取喻。伐邑,如堕费、堕郈之类是也。大抵今人说易,多是见易中有此一语,便以为通体事当如此。不知当其时节地头,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说,则易之说有穷矣!又如『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晓耳。」
「晋六三,如何见得为众所信处?既不中正,众方不信。虽能信之,又安能『悔亡』?」曰:「晋之时,二阴皆欲上进,三处地较近,故二阴从之以进。」问:「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当有悔。以其得众,故悔可亡。」
问:「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为:『六以柔居尊位,本当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顺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顺附,当推诚委任,尽众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复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则吉而无不利。』此说是否?」曰:「便是伊川说得太深。据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则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说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复恤其失得!如此,则荡然无复是非,而天下之事乱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乱者,亦将不恤之乎?虽以尧舜之圣,皋夔益稷之贤,犹云『屡省乃成』,如何说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则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为!岂有此理!且彼所为既失矣,为上者如何不恤得?圣人无此等说话。圣人所说卦爻,只是略略说以为人当着此爻,则大势已好,虽有所失得,亦不必虑而自无所不利也。圣人说得甚浅,伊川说得太深;圣人所说短,伊川解得长。」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发解做官,这个却必不得,只得尽其所当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相似。」
「失得勿恤」,此说失也不须问他,得也不须问他,自是好,犹言「胜负兵家之常」云尔。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
「晋上九,刚进之极,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刚,故可伐邑。若不刚,则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于小;若伐国,则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之类。『维用伐邑』,则不可用之于大可知。虽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厉,乃可以吉而无咎。过刚而能危厉,则不至于过刚矣。」
看伯丰与庐陵问答内晋卦伐邑说,曰:「晋上九『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难,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贞吝』之义,诸义只云贞固守此则吝,不应于此独云于正道为吝也。」
明夷
明夷,未是说闇之主,只是说明而被伤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说闇。君子出门庭,言君子去闇尚远,可以得其本心而远去。文王箕子大概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顺」,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艰」,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艰难底气象。爻说「贞」而不言「艰」者,盖言箕子,则艰可见,不必更言之。
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则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则晦得没理会了。故外晦而内必明,乃好。学履。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义。」曰:「初爻所伤地远,故虽伤而尚能飞。」问:「初爻比二爻,似二爻伤得浅,初爻伤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飞,但垂翼耳。」
问明夷。曰:「下三爻皆说明夷是明而见伤者。六四爻,说者却以为奸邪之臣先蛊惑其君心,而后肆行于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说。六四之与上六既非正应,又不相比。又况下三爻皆说明夷是好底,何独比爻却作不好说?故某于此爻之义未详。但以意观之,六四居暗地尚浅,犹可以得意而远去,故虽入于幽隐之处,犹能『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也』,故小象曰:『获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则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国』,而不免『后入于地』,则是始于伤人之明,而终于自伤以坠其命矣。吕原明以为唐明皇可以当之,盖言始明而终暗也。」
家人
问:「家人彖辞,不尽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象者,但只因彖传而言耳。大抵彖传取义最精。象中所取,却恐有假合处。」
问「风自火出」。曰:「谓如一炉火,必有气冲上去,便是『风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内及外之意。」学履录云:「是火中有风,如一堆火在此,气自熏蒸上出。」
「王假有家」,言到这里,方且得许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个家。
问「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谓有三德者,则夙夜浚明于其家;有六德者,则亮采于其邦。『有』是虚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或问:「易传云,正家之道在于『正伦理,笃恩义』。今欲正伦理,则有伤恩义;欲笃恩义,又有乖于伦理;如何?」曰:「须是于正伦理处笃恩义,笃恩义而不失伦理,方可。」柄。
睽
睽,皆言始异终同之理。
问「君子以同而异」。曰:「此是取两象合体为同,而其性各异,在人则是『和而不同』之意。盖其趋则同,而所以为同则异。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趋不同,而其归则一。彖辞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异』。在人则出处语默虽不同,而同归于理;讲论文字为说不同,而同于求合义理;立朝论事所见不同,而同于忠君。本义所谓『二卦合体』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异也。『以同而异』语意与『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读易到精熟后,颠倒说来皆合;不然,则是死说耳。」又问:「睽卦无正应,而同德相应者何?」曰:「无正应,所以为睽,当睽之时,当合者既离,其离者却合也。」
问:「『君子以同而异』,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这处又就人事之异上说。盖君子有同处,有异处,如所谓『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处说,不必深去求他。此处伊川说得甚好。」学履。
过举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异」,解曰:「不能大同者,乱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独异者,随俗习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尔。」「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择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专以求富贵为事,惑乱此心,则异矣。如士人应科举,则同也;不曲学以阿世,则异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
马是行底物,初间行不得,后来却行得。大率睽之诸爻都如此,多说先异而后同。
问:「睽『见恶人』,其义何取?」曰:「以其当睽之时,故须见恶人,乃能无咎。」
「天」,合作「而」,剃须也。篆文「天」作「●」,「而」作「●」。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载鬼一车」等语所以差异者,为他这般事是差异底事,所以却把世间差异底明之。世间自有这般差异底事。
蹇
「蹇,利西南」,是说坤卦分晓。但不知从何插入这坤卦来,此须是个变例。圣人到这里,看见得有个做坤底道理。大率阳卦多自阴来,阴卦多自阳来。震是坤第一画变,坎是第二画变,艮是第三画变。易之取象,不曾确定了他。
蹇无坤体,只取坎中爻变,如沈存中论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谓地也。据卦体艮下坎上,无坤,而繇辞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变,变则为坤矣。沈存中论五姓,自古无之,后人既如此呼唤,即便有义可推。
潘谦之书曰:「蹇与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泽无水,困。」是尽干燥,处困之极,事无可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则犹可进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艰阻,然犹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岂可以困为比?只观「泽无水,困」,与「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学履。
问:「往蹇来誉」。曰:「『来往』二字,唯程传言『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说得极好。今人或谓六四『往蹇来连』,是来就三;九三『往蹇来反』,是来就二;上六『往蹇来硕』,是来就五,亦说得通。但初六『来誉』,则位居最下,无可来之地,其说不得通矣。故不若程传好,只是不往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进。故不进则为来。诸爻皆不言吉,盖未离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来硕,吉』,却是蹇极有可济之理。既是不往,惟守于蹇,则必得见九五之大人与共济,蹇而有硕大之功矣。」
问:「蹇九五,何故为『大蹇』?」曰:「五是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须人主当之。」砺。
问:「大蹇朋来」之义。曰:「处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为『大蹇』,所谓『遗大投艰于朕身』。人君当此,则须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济也。」学履。
解
先生举「无所往,其来复吉」。程传以为「天下之难已解,而安平无事,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复先代明王之治」。「夫祸乱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复三代之规模,却只便休了!两汉以来,人主还有理会正心、诚意否?须得人主如穷阎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讲明义理,以此应天下之务,用天下之才,方见次第。」因言:「神庙,大有为之主,励精治道,事事要理会过,是时却有许多人才。若专用明道为大臣,当大段有可观。明道天资高,又加以学,诚意感格,声色不动,而事至立断。当时用人参差如此,亦是气数舛逆。」
「天地解而雷雨作。」阴阳之气闭结之极,忽然迸散出做这雷雨。只管闭结了,若不解散,如何会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极也。雷便是如今一个爆杖。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负且乘」,圣人到这里,又见得有个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于此发出这个道理来。
问「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与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虽阴位而才则阳,与初六阴柔则为有间,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阳刚之朋类至而相信矣。」
「射隼于高墉」,圣人说易,大概是如此,不似今人说底。向来钦夫书与林艾轩云:「圣人说易,却则恁地。」此却似说得易了。
损
「二簋」与「簋贰」字不同,可见其义亦不同。
「惩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问:「『惩忿、窒欲』,忿怒易发难制,故曰『惩』,惩是戒于后。欲之起则甚微,渐渐到炽处,故曰『窒』,窒谓塞于初。古人说『情窦』,窦是罅隙,须是塞其罅隙。」曰:「惩也不专是戒于后,若是怒时,也须去惩治他始得。所谓惩者,惩于今而戒于后耳。窒亦非是真有个孔穴去塞了,但遏绝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观山之象以惩忿,观泽之象以窒欲。欲如污泽然,其中秽浊解污染人,须当填塞了。如风之迅速以迁善,如雷之奋发以改」广云:「观山之象以惩忿,是如何?」曰:「人怒时,自是恁突兀起来。故孙权曰:『令人气涌如山!』」
问:「『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曰:「伊川将来相牵合说,某不晓。看来人自有迁善时节,自有改过时节,不必只是一件事。某看来,只是惩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迁善如风之迅,改过如雷之烈。」又曰:「圣人取象,亦只是个大约彷佛意思如此。若纔着言语穷他,便有说不去时。如后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几句,也添不去。」
「酌损之」,在损之初下,犹可以斟酌也。
问:「损卦三阳皆能益阴,而二与上二爻,则曰:『弗损,益之。』初则曰:『酌损之。』何邪?」曰:「这一爻难解,只得用伊川说。」又云:「易解得处少,难解处多,今且恁地说去。到那占时,又自别消详有应处,难立为定说也。」学履。
「三人行,损一人」,三阳损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阳上去换得一阴来。」
「或益之十朋之龟」为句。
「得臣无家」,犹言化家为国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则可见其大。
问:「损卦下三爻皆损己益人,四五两爻是损己从人,上爻有为人上之象,不待损己而自有以益人。」曰:「下三爻无损己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极处,去不得,自是损了。四爻『损其疾』,只是损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无损己从人底意。」砺。
益
问:「『木道乃行』,程传以为『木』字本『益』字之误,如何?」曰:「看来只是『木』字。涣卦说『乘木有功』,中孚说『乘木舟虚』,以此见得只是『木』字。」又问「或击之」。曰:「『或』字,众无定主之辞,言非但一人击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辞。此处亦可疑,且阙之。」
「木道乃行」,不须改「木」字为「益」字,只「木」字亦得。见一朋友说,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干为金」,易卦之金也;兑之金,五行之金也。「巽为木」,是卦中取象。震为木,乃东方属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维故也。
「某昨日思『风雷,益,君子以迁善、改过』。迁善如风之速,改过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迁善,便是改过否?」曰;「不然,『迁善』字轻,『改过』字重。迁善如惨淡之物,要使之白;改过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迁善者,但见是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迁之。儒用录云:「只消当下迁过就他底。」若改过,须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说蒙与蛊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泽,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儒用同。
问「迁善、改过」。曰:「风是一个急底物,见人之善,己所不及,迁之如风之急;雷是一个勇决底物,己有过,便断然改之,如雷之勇,决不容有些子迟缓!」赐。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盖有事则吉,而理则过差者,是之谓吉而有咎。
「享于帝吉」是「祭则受福」底道理。
「益之,用凶事」,犹书言「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
伊川说易亦有不分晓处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说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当时未见有这守令,恐难以此说。某谓「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难,必以危言鲠论恐动其君而益之。虽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于君者也。
「中行」与「依」,见不得是指谁。
「利用迁国」,程昌寓守寿春,虏人来,占得此爻,迁来鼎州。后平杨么有功。方子录云「守蔡州」。
益损二卦说龟,一在二,一在五,是颠倒说去。未济与既济说「伐,鬼方」,亦然。不知如何。未济,看来只阳爻便好,阴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如何。盖六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济之才,又当未济之极,可以济矣。却云不吉,更不可晓。学蒙。
「大抵损益二卦,诸爻皆互换。损好,益却不好。如损六五却成益六二。损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夬
用之说夬卦云:「圣人于阴消阳长之时亦如此戒惧,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说,自是无时不戒慎恐惧,不是到这时方戒惧。不成说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扬于王庭,孚号有厉。」若合开口处,便虽有剑从自家头上落,也须着说。但使功罪各当,是非显白,于吾何慊!
夬卦中「号」字,皆当作「户羔反」。唯「孚号」,古来作去声,看来亦只当作平声。
「壮于前趾」,与大壮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壮,只争一画。
王子献卜,遇夬之九二,曰「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吉。卜者告之曰:「必夜有惊恐,后有兵权。」未几果夜遇寇,旋得洪帅。
问九三「壮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见于面目,至于遇雨而为所濡湿,虽为众阳所愠,然志在决阴,必能终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盖九三虽与上六为应,而实以刚居刚,有能决之象;故『壮于頄』则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于董卓,温峤之于王敦是也。」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今人以为阳不能无阴,中国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尽去。今观『刚长乃终』之言,则圣人岂不欲小人之尽去耶?但所以决之者自有道耳。」又问:「夬卦辞言『孚号』,九二言『惕号』,上九言『无号』,取象之义如何?」曰:「卦有兑体,『兑为口』,故多言『号』也。」又问:「以五阳决一阴,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势,而卦辞则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壮于前趾』,则『往不胜』;九二『惕号』,则『有戎勿恤』;『壮于頄』则凶,『牵羊』则『悔亡』,『中行无咎』。岂去小人之道,须先自治而严厉戒惧,不可安肆耶?」曰:「观上六一爻,则小人势穷,无号有凶之时,而君子去之之道,犹当如此严谨,自做手脚,盖不可以其势衰而安意自肆也,其为戒深矣!」
九三「壮于頄」,看来旧文本义自顺,不知程氏何故欲易之。「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颜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间与其徒曰:「吾辈何为服此?」归而借兵伐之,正类此也。卦中与复卦六四有「独」字。此卦诸爻皆欲去阴,独此一爻与六为应,也是恶模样。砺。
伊川改九三爻次序,看来不必改。
这几卦都说那臀,不可晓。
「牵羊悔亡」,其说得于许慎之。
苋、陆是两物。苋者,马齿苋;陆者,章陆,一名商陆,皆感阴气多之物。药中用商陆治水肿,其子红。渊录云:「其物难干。」学履。
「中行无咎」,言人能刚决自胜其私,合乎中行,则得无咎。无咎,但能「补过」而已,未是极至处。这是说那微茫间有些个意思断未得,释氏所谓「流注想」,荀子所谓「偷则自行」,便是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将去那里去。爻虽无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辞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之类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则无咎,不然则有咎。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虽正而意潜有所系吝,荀子所谓「偷则自行」,佛家所谓「流注不断」,皆意不诚之本也。
姤
不是说阴渐长为「女壮」,乃是一阴遇五阳。
大率姤是一个女遇五阳,是个不正当底,如「人尽夫也」之事。圣人去这里,又看见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来。
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刚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盖「天地相遇」,又是别取一义。「刚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谓亦以九二言,非也。
问:「『姤之时义大矣哉!』本义云:『几微之际,圣人所谨。』与伊川之说不同,何也?」曰:「上面说『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时节,而不好之渐已生于微矣,故当谨于此。」学履。
「金柅」,或以为止车物,或以为丝羇,不可晓。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鱼象。或说:「『离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鱼便在里面了。」不知是不是。此条未详。
「包无鱼」,又去这里见得个君民底道理。阳在上为君,阴在下为民。
「有陨自天」,言能回造化,则阳气复自天而陨,复生上来,都换了这时
萃
大率人之精神萃于己,祖考之精神萃于庙。
「顺天命」,说道理时,彷佛如伊川说,也去得,只是文势不如此。他是说丰萃之时,若不「用大牲」,则便是那「以天下俭其亲」相似。也有此理,这时节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这彖辞散漫说,说了「王假有庙」,又说「利见大人」,又说「用大牲,吉」。大率是圣人观象,节节地看见许多道理,看到这里见有这个象,便说出这一句来;又看见那个象,又说出那一个理来。然而观象,则今不可得见是如何地观矣。
问「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故当预为之备。又泽本当在地中,今却上出于地上,则是水盛长,有溃决奔突之忧,故取象如此。」
不知如何地说个「一握」底句出来。
「孚乃利用禴」说,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圣人说个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说祭。升卦同。
问:「九五『萃有位』。以阳刚居中正,当萃之时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则虽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当修其『元永贞』之德,而后『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庙』,是祖考精神聚于庙。又为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后可以至于庙而承祖考。今人择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
问:「九五一爻亦似甚好,而反云『未光也』,是如何?」曰:「见不得。读易,似这样且恁地解去,若强说,便至凿了。」学履。
升
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个南,如看命人「虚拱」底说话。砺。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木之生也,无日不长;一日不长,则木死矣!人之学也,一日不可已;不日而已,则心必死矣!
「『地中生木,升。』汪丈尝云:『曾考究得树木之生,日日滋长;若一日不长,便将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学者之于学,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须日日要进,若一日不进便退。近日学者才相疏,便都休了。」
问:「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义,不知升何取义?」曰:「人积其诚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义。」又曰:「六五『贞吉升阶』,与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贞,悔亡』,皆谓有其位必当有其德,若无其德,则萃虽有位而人不信,虽有升阶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元德问「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享』字。古文无『享』字。所谓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干,元亨利贞』,屯之『元亨利贞』,只一般。圣人借此四字论干之德,本非四件事也。」
「亨于岐山」与「亨于西山」,只是说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