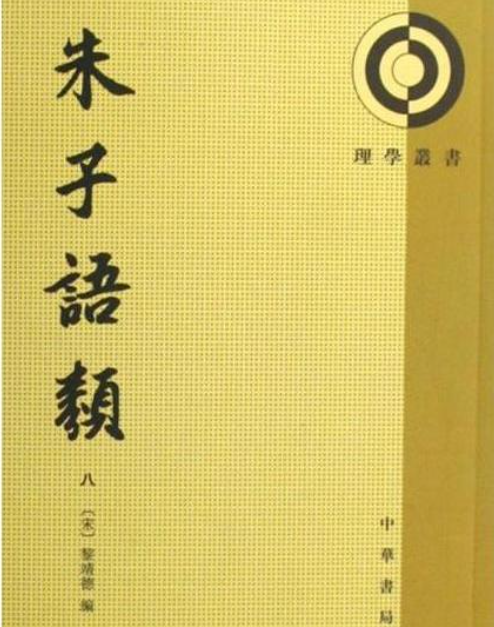易七
噬嗑
彖辞中「刚柔分」以下,都掉了「颐中有物」,只说「利用狱」。爻亦各自取义,不说噬颐中之物。
张元德问:「易中言『刚柔分』两处。一是噬嗑,一是此颇难解。」曰:「据某所见,只是一卦三阴三阳谓之『刚柔分』。」洽录云:「分,犹均也。」曰:「易中三阴三阳卦多,独于此言之,何也?」曰:「偶于此言之,其它卦别有义。」洽录云:「『刚柔分』,语意与『日夜分』同。」又问:「复卦『刚反』作一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复亨』,下云『动而以顺行』,是解『先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辞解得易极分明,子细寻索,尽有条理。」洽同。
问:「诸卦象皆顺说,独『雷电噬嗑』倒说,何耶?」曰:「先儒皆以为倒写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雷电噬嗑』与雷电丰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动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这法在此,未见犯底人,留待异时而用,故云:『明罚敕法』。丰威在上,明在下,是用这法时,须是明见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动于上,必有过错也,故云『折狱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说极好。」学履。
「噬肤灭鼻。」肤,腹腴拖泥处;灭,浸没也。谓因噬肤而没其鼻于器中也。「噬干胏,得金矢」,荆公已尝引周礼「钧金」之说。按:「噬肤灭鼻」之说,与本义不同。
问:「九四『利艰贞』,六五『贞厉』,皆有艰难正固危惧之意,故皆为戒占者之辞。」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为敌,不是易事。故虽是时、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须以艰难正固处之。至于六三『噬腊肉遇毒』,则是所噬者坚韧难合。六三以阴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当治者,但难治耳。治之虽小吝,终无咎也。」
问:「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狱讼要钧金束矢之意如何?」曰:「不见得。想是词讼时,便令他纳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妄来。」又问:「如此则不问曲直,一例出此,则实有冤枉者亦惧而不敢诉矣。」曰:「这个须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别有所在。」如剂石之类。学履。
贲
伊川说:「乾坤变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画了,旋变去,这话难说。伊川说两仪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画,须是都画了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刚柔、来往、上下。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刚柔相错』四字。」恐有之,方与下文相似,且得分晓。砺。
问:「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狱』,本义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狱是明之大者,此专是就象取义。伊川说此,则又就贲饰上说。不知二说可相备否?」曰:「『明庶政』是就离上说。无折狱是就艮上说。离明在内,艮止在外,则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狱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义。明在内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说,则意味长。若悬空说道理,虽说得去,亦不甚亲切也。」学履。
「『山下有火,贲』,内明外止。虽然内明,是个止杀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狱。此与旅相似而相反,贲内明外止,旅外明内止,其象不同如此。」问:「苟明见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难于折狱?」曰:「是他自有个象如此。遇着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狱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须待囚讯鞠勘,录问结证而后了底。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周礼秋官亦有此数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狱未是而决之,是所谓『敢折狱』也;若狱已具而留之不决,是所谓『留狱』也。『不留狱』者,谓囚讯结证已毕,而即决之也。」
问「明庶政,无敢折狱」。曰:「此与旅卦都说刑狱事,但争艮与离之在内外,故其说相反。止在外,明在内,故明政而不敢折狱;止在内,明在外,故明谨用刑而不敢留狱。」又曰:「[分鹿]言之:如今州县治狱,禁勘审覆,自有许多节次,过乎此而不决,便是留狱;不及乎此而决,便是敢于折狱。尚书要囚至于旬时,他须有许多时日。此一段与周礼秋官同意。」砺。
六四「白马翰如」,言此爻无所贲饰,其马亦白也,言无饰之象如此。学履。
问「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曰:「此两句只是当来卦辞,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这个道理。」或曰:「『贲于丘园』,安定作『敦本』说。」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戋戋」为盛多之貌。曰:「非也。『戋戋』者,浅小之意。凡『浅』字、『笺』字皆从『戋』。」或问:「浅小是俭之义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终吉。』吝者虽不好看,然终却吉。」
问:「『贲于丘园』,是在艮体,故安止于丘园,而不复有外贲之象。」曰:「虽是止体,亦是上比于九,渐渐到极处。若一向贲饰去,亦自不好,须是收敛方得。」问:「敦本务实,莫是反朴还淳之义否?」曰:「贲取贲饰之义,他今却来贲田园为农圃之事。当贲之时,似若鄙吝。然俭约终得吉,吉则有喜,故象云『有喜』也。」砺。
问「贲于丘园」。曰:「当贲饰华盛之时,而安于丘园朴陋之事,其道虽可吝,而终则有吉也。」问:「『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终吉,所以有喜。」又问「白贲无咎」。曰:「贲饰之事太盛,则有咎。所以处太盛之终,则归于白贲,势当然也。」
「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是个务农尚俭。「戋戋」是狭小不足之意。以字义考之,从「水」则为「浅」,从「贝」则为「贱」,从「金」则为钱。如所谓「束帛戋戋」,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俭,便似吝啬。如卫文公汉文帝虽是吝,却终吉,此在贲卦有反本之义。到上九便「白贲」,和束帛之类都没了。
「贲于丘园」是个务实底。学履作「务农尚本之义」。「束帛戋戋」是贲得不甚大,所以说「吝」。两句是两意。
问:「伊川解『贲于丘园』,指上九而言,看来似好。盖贲三阴皆受贲于阳,不应此又独异,而作敦本务实说也。」曰:「如何丘园便能贲人?『束帛戋戋』,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艰曲说不出。这八字只平白在这里,若如所说,则曲折多,意思远。旧说指上九作高尚隐于丘园之贤,而用束帛之礼聘召之。若不用某说,则此说似近。他将丘园作上九之象,『束帛戋戋』作裁剪纷裂之象,则与象意大故相远也。」学履。
问:「六五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实,故有『贲于丘园』之象。然阴性吝啬,故有『束帛戋戋』之象。戋戋,浅小貌。人而如此,虽可羞吝,然礼奢宁俭,故得终吉。此与程传指丘园为上九者如何?」曰:「旧说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贤。但若如此说,则与『吝终吉』文义不协。今程传所指亦然。盖『戋戋』自是浅小之意,如从『水』则为『浅』,从『人』则为『俴』,从『贝』则为贱,皆浅小意。程传作剪裁,已是迂回;又说丘园,更觉牵强。如本义所说,却似与『吝终吉』文义稍协。」又问:「『白贲无咎,上得志也』,何谓『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饰,而有自然之文,便自优游自得也。」铢曰:「如本义说六五、上九两爻,却是贲极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渐,故曰『丘园』,又曰『束帛戋戋』。至上九『白贲』,则反本而复于无饰矣,盖皆贲极之象也。」
伊川此卦传大有牵强处。「束帛」解作「剪裁」,恐无此理。且如今将「束帛」之说教人解,人决不思量从剪裁上去。
「白贲无咎」,据「刚上文柔」,是不当说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说一义。
剥
问:「『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于礼义而不迁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于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则其位亦安而不摇,犹所谓『本固邦宁』也。」
问:「剥之初与二『蔑贞凶』,是以阴蔑阳,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阳与君子当之则凶为复,阴与小人亦自为凶?」曰:「自古小人灭害君子,终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说阳与君子之凶也。」砺。
或问:「『硕果不食』,伊川谓『阳无可尽之理,剥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变于上则生于下,乃剥复相因之理。毕竟须经由坤,坤卦纯阴无阳;如此阳有断灭也,何以能生于复?」曰:「凡阴阳之生,一爻当一月,须是满三十日,方满得那腔子,做得一画成。今坤卦非是无阳,阳始生甚微,未满那腔子,做一画未成。非是坤卦纯阴,便无阳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奥事,但伊川当时解不曾分明道与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小人剥庐」,是说阴到这里时,把他这些阳都剥了。此是自剥其庐舍,无安身己处。众小人托这一君子为芘覆,若更剥了,是自剥其庐舍,便不成剥了。
「旧见二十家叔说,怀,字公立。『庐』,如周礼『秦无庐』之『庐』,音『庐』,盖戟柄也。谓小人自剥削其戟柄,仅留其铁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说,方见得小象『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问:「『变化』二字,旧见本义云:『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夜来听得说此二字,乃谓『化是渐化,变是顿变』,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难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谓之变』,则化又是渐。盖化如正月一日,渐渐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则是正月变为二月矣。然变则又化,是化长而变短。此等字,须当通看乃好。」
复
问:「剥一阳尽而为坤。程云:『阳未尝尽也。』」曰:「剥之一阳未尽时,不曾生;纔尽于上,这些子便生于下了。」
问:「一阳复于下,是前日既退之阳已消尽,而今别生否?」曰:「前日既退之阳已消尽,此又是别生。伊川谓『阳无可尽之理,剥于上则生于下,无闲可容息』,说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则剥九月,坤十月,复十一月。剥一阳尚存,复一阳已生。坤纯阴,阳气阙了三十日,安得谓之无尽?」曰:「恐是一月三十日,虽到二十九日,阳亦未尽否?」曰:「只有一夜,亦是尽,安得谓之无尽?尝细推之,这一阳不是忽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气象。上面剥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剥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积累到那复处,方成一阳。坤初六,便是阳已萌了。」
问伊川所说剥卦。曰:「公说关要处未甚分明。他上纔消,下便生。且如复卦是一阳,有三十分,他便从三十日头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二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时也如此。只伊川说欠得几句说渐消渐长之意。」直卿问:「『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阳方生?」贺孙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阳,不是一阳方生。」曰:「冬至方是结算那一阳,冬至以后又渐生成二阳,过一月却成临卦。坤卦之下,初阳已生矣。」
「为嫌于无阳也。」自观至剥,三十日剥方尽。自剥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阳渐长,至冬至,方是一阳,第二阳方从此生。阴剥,每日剥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剥得尽;阳长,每日长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长得成一阳。阴剥时,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渐渐剥,全一日方剥得三十分之一。阳长之渐,亦如此长。直卿举「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阳。子之半后,第二阳方生。阳无可尽之理,这个才剥尽,阳当下便生,不曾断续。伊川说这处未分晓,似欠两句在中间,方说得阴剥阳生不相离处。」虞复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见阴剥阳生,逐旋如此。阴不会一上剥,阳不会一上长也。」
「剥上九一画分为三十分,一日剥一分,至九月尽,方尽。然剥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积三十分而成一画,但其始未着耳。至十一月,则此画已成,此所谓『阳未尝尽』也。」道夫问:「阴亦然。今以夬干姤推之,亦可见矣。但所谓『圣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刘履之说,蔡季通以为不然。某以为分明是如此。但圣人所以不言者,这便是一个参赞裁成之道。盖抑阴而进阳,长善而消恶,用君子而退小人,这便可见此理自是恁地。虽尧舜之世,岂无小人!但有圣人压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为耳,岂能使之无邪!」刘履之曰:「蔡季通尝言:『阴不可以抗阳,犹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谓「阴亦然,圣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为然也。』」
问:「十月何以为阳月?」先生因诘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于易传虽发其端,然终说得不透彻。」诸生答皆不合,复请问。先生曰:「剥尽为坤,复则一阳生也。复之一阳,不是顿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积来。且一月三十日,以复之一阳分作三十分,从小雪后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趱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阳始成也。以此便见得天地无休息处。」
义刚曰:「十月为阳月,不应一月无阳。一阳是生于此月,但未成体耳。」曰:「十月阴极,则下已阳生。谓如六阳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为三十小段,从十月积起,至冬至积成一爻。不成一阳是陡顿生,亦须以分毫积起。且如天运流行,本无一息间断,岂解一月无阳!且如木之黄落时,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后旧叶方落。若论变时,天地无时不变。如楞严经第二卷首段所载,非惟一岁有变,月亦有之;非惟月有变,日亦有之;非惟日有变,时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说亦是。」
问:「坤为十月。阳气剥于上,必生于下,则此十月阳气已生,但微而未成体,至十一月一阳之体方具否?」曰:「然。凡物变之渐,不惟月变日变,而时亦有变,但人不觉尔。十一月不能顿成一阳之体,须是十月生起云云。」学履。
味道举十月无阳。曰:「十月坤卦皆纯阴。自交过十月节气,固是纯阴,然潜阳在地下,已旋生起来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细以时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阳生时,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画阳。这一画是卦中六分之一,全在地下;二画又较在上面则个;至三阳,则全在地上矣。四阳、五阳、六阳,则又层层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时便顿然生得一画,所以庄子之徒说道:『造化密移,畴觉之哉?』」又曰:「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盖见此理。阴阳消长亦然。如包胎时十月具,方成个儿子。」贺孙录见下。
「阳无骤生之理,如冬至前一月中气是小雪,阳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几日,须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一画。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复了,大抵剥尽处便生。庄子云:『造化密移,畴觉之哉?』这语自说得好。又如列子亦谓:『运转无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凡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亦不觉其成,不觉其亏。盖阴阳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植问:「不顿进,是渐生;不顿亏,是渐消。阴阳之气皆然否?」曰:「是。」
问:「十月是坤卦,阳已尽乎?」曰:「阴阳皆不尽。至此则微微一线路过,因而复发耳。」
「七日」,只取七义。犹「八月有凶」,只取八义。
问「朋来无咎」。曰:「复卦一阳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阳有刚长之道,自一阳始生而渐长,砺录云:「毕竟是阳长,将次并进。」以至于极,则有朋来之道而无咎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消长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处阴之极,乱者复治,往者复还,凶者复吉,危者复安,天地自然之运也。」问「六二『休复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为仁人之体,六二爻能下之,谓附下于仁者。学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亲之,资其善以自益,则力不劳而学美矣,故曰『休复吉』。上六『迷复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这是个极不好底爻,故其终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数中自有个数如此,故圣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则其凶甚矣!」
问:「复卦『刚反』当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复亨』。下云『动而以顺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辞解得易极分明,子细寻索,尽有条理。」
圣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到这里微茫发动了,最可以见生气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见。天只有个春夏秋冬,人只有个仁义礼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说四端犹四体,阙一不可。人若无此四者,便不足为人矣。心是一个运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无别物,只此体验可见。
问:「『复其见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尝息,但到坤时藏伏在此,至复乃见其动之端否?」曰:「不是如此。这个只是就阴阳动静,阖辟消长处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发以至渐渐发过,消尽为灰。其消之未尽处,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尽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个不如那新生底鲜好,故指那接头再生者言之,则可以见天地之心亲切。如云『利贞者性情也』。一元之气,亨通发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尽发见在品物上,但丛杂难看;及到利贞时,万物悉已收敛,那时只有个天地之心,丹青着见,故云『利贞者性情也』,正与『复其见天地之心』相似。康节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盖万物生时,此心非不见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丛杂,无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难见。若会看者,能于此观之,则所见无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复时万物皆未生,只有一个天地之心昭然着见在这里,所以易看也。」
问:「天地之心,虽静未尝不流行,何为必于复乃见?」曰:「三阳之时,万物蕃新,只见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见。惟是一阳初复,万物未生,冷冷静静;而一阳既动,生物之心闯然而见,虽在积阴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于复见天地之心也。」铢曰:「邵子所谓『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稀』,正谓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别下注脚矣。」又问:「『天心无改移』谓何?」曰:「年年岁岁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问:「纯坤之月,可谓至静。然昨日之静,所以养成今日之动;故一阳之复,乃是纯阴养得出来。在人,则主静而后善端始复;在天地之化,则是终则有始,贞则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义。大象所谓『至日闭关』者,正是于已动之后,要以安静养之。盖一阳初复,阳气甚微,劳动他不得,故当安静以养微阳。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静以养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说,却是倒了。」
「复见天地心。」动之端,静中动,方见生物心。寻常吐露见于万物者,尽是天地心。只是冬尽时,物已成性,又动而将发生,此乃可见处。
问「复见天地之心」之义。曰:「十月纯阴为坤卦,而阳未尝无也。以阴阳之气言之,则有消有息;以阴阳之理言之,则无消息之间。学者体认此理,则识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间断也。」
问「复见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运行不息者,做个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于春,长于夏,至秋万物咸遂,如收敛结实,是渐欲离其本之时也。及其成,则物之成实者各具生理,所谓『硕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继其生,而物之归根复命,犹自若也。如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斯可见矣。」又问:「既言『心性』,则『天命之谓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运用是心。」
「天地生物之心,未尝须臾停。然当气候肃杀草木摇落之时,此心何以见?」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见,故必到复而后始可见。」
天地之心未尝无,但静则人不得而见尔。
伊川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盖谓天地以生生为德,自「元亨利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静而复,乃未发之体;动而通焉,则已发之用。一阳来复,其始生甚微,固若静矣。然其实动之机,其势日长,而万物莫不资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发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是而可见也。若其静而未发,则此之心体虽无所不在,然却有未发见处。此程子所以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亦举用以该其体尔。
问:「『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窃谓十月纯坤,不为无阳。天地生物之心未尝间息,但未动耳,因动而生物之心始可见。」曰:「十月阳气收敛,一时关闭得尽。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尝息,但无端倪可见。惟一阳动,则生意始发露出,乃始可见端绪也。言动之头绪于此处起,于此处方见得天地之心也。」因问:「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时,而所谓中节之体已各完具,但未发则寂然而已,不可见也。特因事感动,而恻隐、羞恶之端始觉因事发露出来,非因动而渐有此也。」曰:「是。」
问:「程子言:『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动处如何见得?」曰:「这处便见得阳气发生,其端已兆于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从这里发去。事物间亦可见,只是这里见得较亲切。」郑兄举王辅嗣说「寂然至无,乃见天地心」。曰:「他说『无』,是胡说!若静处说无,不知下面一画作甚么?」寓问:「动见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静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这处在天地则为阴阳,在人则为善恶。『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不善处便是阴,善处便属阳。上五阴下一阳,是当沉迷蔽锢之时,忽然一夕省觉,便是阳动处。齐宣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可谓极矣,及其不忍觳觫,即见善端之萌。肯从这里做去,三王事业何患不到!」
居甫问「复见天地之心」。曰:「复未见造化,而造化之心于此可见。」某问:「静亦是心,而心未见?」曰:「固是。但又须静中含动意始得。」曰:「王弼说此,似把静作无。」曰:「渠是添一重说话,下自是一阳,如何说无?上五阴亦不可说无。说无便死了,无复生成之意,如何见其心?且如人身上,一阳善也,五阴恶也;一阳君子也,五阴小人也。只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且看一阳对五阴,是恶五而善一。纔复,则本性复明,非天心而何!」与上条同闻。
问:「复以动见天地之心,而主静观复者又何谓?」曰:「复固是动,主静是所以养其动,动只是这静所养底。一阳动,便是纯坤月养来。」曰:「此是养之于未动之前否?」曰:「此不可分前后,但今日所积底,便为明日之动;明日所积底,便为后日之动,只管恁地去。『观复』是老氏语,儒家不说。老氏爱说动静。『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谓万物有归根时,吾只观他复处。」
问:「程子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动乃心之发处,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须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静,震是动。十月纯坤,当贞之时,万物收敛,寂无踪迹,到此一阳复生便是动。然不直下『动』字,却云『动之端』,端又从此起。虽动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动处。凡发生万物,都从这里起,岂不是天地之心!康节诗云:『冬至子之半,大雪,子之初冬至,子之中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羲!』可谓振古豪杰!」
问「冬至子之半」。曰:「康节此诗最好,某于本义亦载此诗。盖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时冬至,盖夜半以前,一半已属子时,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数每从这处起,略不差移,此所以为天心。然当是时,一阳方动,万物未生,未有声臭气味之可闻可见,所谓『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也。」
汉卿问「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曰:「此在贞、元之间,才见孺子入井,未做出恻隐之心时」因言:「康节之学,不似濂溪二程。康节爱说个循环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说得活。如『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康节无此说。」广录见下。
问:「康节所谓『一阳初动后,万物未生时』,这个时节,莫是程子所谓『有善无恶,有是无非,有吉无凶』之时否?」先生良久曰:「也是如此。是那怵惕恻隐方动而未发于外之时。」正淳云:「此正康节所谓『一动一静之间』也。」曰:「然。某尝谓康节之学与周子程子所说小有不同。康节于那阴阳相接处看得分晓,故多举此处为说;不似周子说『无极而太极』,与『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说,则康节所说在其中矣。康节是指贞、元之间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说得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贺孙录别出。
汉卿问:「『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人心观之,便是善恶之端,感物而动处。」曰:「此是欲动未动之间,如怵惕恻隐于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恻隐而未成怵惕恻隐之时。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节常要就中间说。『子之半』则是未成子,方离于亥而为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说,常要说阴阳之间,动静之间,便与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只是体用动静,互换无极。康节便只要说循环,便须指消息动静之间,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
天地之心,动后方见;圣人之心,应事接物方见。「出入」、「朋来」,只做人说,觉不劳攘。
论「复见天地之心」。「程子曰:『圣人无复,故未尝见其心。』且尧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圣人之心周流运行,何往而不可见?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发育,犹是显著。此独曰『圣人无复,未尝见其心』者,只为是说复卦。系辞曰:『复小而辨于物。』盖复卦是一阳方生于群阴之下,如幽暗中一点白,便是「小而辨」也。圣人赞易而曰:『复见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复卦可以见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于复卦忽见一阳来复,故即此而赞之尔。论此者当知有动静之心,有善恶之心,各随事而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因发动而见其恻隐之心;未有孺子将入井之时,此心未动,只静而已。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及其复也,然后本然之善心可见。圣人之心纯于善而已,所以谓『未尝见其心』者,只是言不见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谓幽暗中一点白者而已。但此等语话,只可就此一路看去;纔转入别处,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
问:「『圣人无复,未尝见其心。』天地之气,有消长进退,故有复;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复。」曰:「固是。」又问:「『鼓舞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地则任其自然,圣人赞化育,则不能无忧。」曰:「圣人也安得无忧?但圣人之忧忧得恰好,不过忧耳。」
举「圣人无复,故不见其心」一节,语学者曰:「圣人天地心,无时不见。此是圣人因赞易而言一阳来复,于此见天地之心尤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点明。」
国秀问:「旧见蔡元思说,先生说复卦处:『静极而动,圣人之复;恶极而善,常人之复。』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静极而动底时节,圣人则不复有恶极而善之复矣。」
上云「见天地之心」,以动静言也;下云「未尝见圣人之心」,以善恶言也。
复虽一阳方生,然而与众阴不相乱。如人之善端方萌,虽小而不为众恶所遏底意思相似。学履。饶录作:「虽小而众恶却遏他不得。」
问:「『一阳复』,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处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处;以恶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复。如睡到忽然醒觉处,亦是复气象。又如人之沉滞,道不得行,到极处,忽小亨;道虽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复。这道理千变万化,随所在无不浑沦。」
敬子问:「今寂然至静在此,若一念之动,此便是复否?」曰:「恁地说不尽。复有两样,有善恶之复,有动静之复,两样复自不相须,须各看得分晓。终日营营,与万物并驰,忽然有恻隐、是非、羞恶之心发见,此善恶为阴阳也。若寂然至静之中,有一念之动,此动静为阴阳也。二者各不同,须推教子细。」
「伊川与濂溪说『复』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说得『复』字就归处说,伊川就动处说。」曰:「然。濂溪就坤上说,就回来处说。如云『利贞者诚之复』,『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皆是就归来处说。伊川却正就动处说。如『元亨利贞』,濂溪就『利贞』上说『复』字,伊川就『元』字头说『复』字。以周易卦爻之义推之,则伊川之说为正。然濂溪伊川之说,道理只一般,非有所异,只是所指地头不同。以复卦言之,下面一画便是动处。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动,如何说静得?雷在地中,复』云云。看来伊川说得较好。王弼之说与濂溪同。」
问:「『阳始生甚微,安静而后能长。』故复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人于迷途之复,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须庄敬持养,然后能大。不然,复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强而仕者,前面许多年亦且养其善端。若一下便出来与事物羇了,岂不坏事!」
「阳气始生甚微,必安静而后能长。」问曰:「此是静而后能动之理,如何?如人之天理亦甚微,须是无私欲挠之,则顺发出来。」曰:「且如此看。」又问:「『安静』二字,还有分别否?」曰:「作一字看。」
叔重问:「『先生以至日闭关』,程传谓阳之始生至微,当安静以养之,恐是十月纯坤之卦,阳已养于至静之中,至是方成体尔。」曰:「非也。养于既复之后。」又问「复见天地之心」。曰:「要说得『见』字亲切,盖此时天地之间无物可见天地之心。只有一阳初生,净净洁洁,见得天地之心在此。若见三阳发生万物之后,则天地之心散在万物,则不能见得如此端的。」
掩身事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斋戒,处必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至、夏闭关息商旅,所以养阳气也。绝彼柔道牵。所以绝阴易姤之初六『系于金柅』是也。
问:「『无祗悔』,『祗』字何训?」曰:「书中『祗』字,只有这『祗』字使得来别。看来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训『多』为『祗』者,如『多见其不知量也』,『多,祗也』。『祗』与『只』同。」
先生举易传语「惟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曰:「这般说话好简当。」
问:「上六『迷复』,至下『十年不克征』,如何?」曰:「过而能改,则亦可以进善。迷而不复,自是无说,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三年』、『十年』、『三岁』,皆是有个象,方说。若三岁犹是有个期限,到十年,便是无说了。」砺。
无妄
无妄本是「无望」。这是没理会时节,忽然如此得来面前,朱英所谓「无望之福」是也。桑树中箭,柳树出汁。
「史记,『无妄』作『无望』。」问:「若以为『无望』,即是愿望之『望』,非诚妄之『妄』。」曰:「有所愿望,即是妄。但『望』字说得浅,『妄』字说得深。」
「刚自外来」,说卦变;「动而健」,说卦德;「刚中而应」,说卦体;「大亨以正」,说「元亨利贞」。自文王以来说做希望之「望」。这事只得倚阁在这里,难为断杀他。
伊川易传似不是本意。「刚自外来」,是所以做造无妄;「动而健」,是有卦后说底。
「往」字说得不同。
问:「『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则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于正理,如贤智者过之。他其心岂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岂有邪心者!」
因论易传「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则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门人为臣」事为证。先生曰:「如鬻拳强谏之类是也。」或云:「王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称荆公『无奸邪,只不晓事』。看来荆公亦有邪心夹杂,他却将周礼来卖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向见何一之有一小论,称荆公所以办得尽行许多事,缘李文靖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尽皆报罢,积得许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来一齐要整顿荆公此意便是庆历范文正公诸人要做事底规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或问:「『物与无妄』,众说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与他一个无妄。」
或说无妄。曰:「卦中未便有许多道理。圣人只是说有许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则有此象。无妄是个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祸。如人方病,忽然勿药而愈,是所谓『无妄』也。据诸爻名义,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说归『无妄』。人之卜筮,如决杯珓,如此则吉,如此则凶,杯珓又何尝有许多道理!如程子之说,说得道理尽好,尽开阔;只是不如此,未有许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虽云祸福之来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于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为之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则有眚矣。眚即灾也。」问:「伊川言『灾自外来,眚自内作,是否?」曰:「看来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灾,是祸偶然生于彼者;眚,是过误致然。书曰『眚灾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过误而赦之也。」
问「『不耕获,不菑畬』,伊川说爻辞与小象却不同,如何?」曰:「便是晓不得。爻下说『不耕而获』,到小象又却说耕而不必求获,都不相应。某所以不敢如此说。他爻辞分明说道『不耕获』了,自是有一样时节都不须得作为。」又曰:「看来无妄合是『无望』之义,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之灾』,『无妄之疾』,都是没巴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须是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则『行有眚』,『眚』即与『灾』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是,他那里便有灾来。」问:「『眚』与『灾』如何分?」曰:「也只一般。尚书云『眚灾肆赦』,春秋『肆大眚』,眚似是过误,灾便直自是外来。」又曰:「此不可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说,见有此象,便有此义,少间自有一时筑着磕着。如今人问杯珓,杯珓上岂曾有道理!自是有许多吉凶。」砺。
「不耕获」一句,伊川作三意说:不耕而获,耕而不获,耕而不必获。看来只是也不耕,也不获,只见成领会他物事。
问「不耕获,不菑畬」。曰:「言不耕不获,不菑不畬,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未尝略起私意以作为,唯因时顺理而已。程传作『不耕而获,不菑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势牵强,恐不如此。」又问「无妄之灾」。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头不正,故有『无妄之灾』,言无故而有灾也。如行人牵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诘之扰,此正『无妄之灾』之象。」又问:「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听其自尔,久则自定,所以『勿药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圣人因象示戒。」又问:「史记作『无望』,谓无所期望而有得,疑有『不耕获,不菑畬』之意。」曰:「此出史记春申君传,正说李园事。正是说无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灾』、『无妄之疾』。亦见得古人相传,尚识得当时此意也。」
「『不耕获,不菑畬』,如易传所解,则当言『不耕而获,不菑而畬』方可。又如云『极言无妄之义』,是要去义理上说,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占吉凶之辞,至彖象方说义理。六二在无妄之时,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获,不菑畬』,是四字都不做,谓虽事事都不动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记『无妄』作『无望』,是此意。六三便是『无望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何与邑人事?而『邑人之灾』。如谚曰:『闭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是也。此是占辞。如『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若庶人占得此爻,只是利去见大人也。然吉凶以正胜,有虽得凶而不可避者,纵贫贱穷困死亡,却无悔吝。故横渠云『不可避凶趋吉,一以正胜』,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须是自己『直方大』,方与爻辞相应,便『不习无不利』。若不直方大,却反凶也。」必大录此下云:「如春秋时,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一段,说得极好。盖南蒯所占虽得吉爻,然所为却不黄裳,即是大凶。」
问「不耕获,不菑畬,未富」之义。曰:「此有不可晓。然既不耕获,不菑畬,自是未富。只是圣人说占得此爻,虽是未富,但『利有攸往』耳。虽是占爻,然义理亦包在其中。易传中说『未』字,多费辞。」
大畜
「能止健」,都不说健而止,见得是艮来止这干。
「笃实」便有「辉光」,艮止便能笃实。
「九三一爻,不为所畜,而欲进与上九合志同进,俱为畜极而通之时,故有『良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达无碍,只是滔滔去。九三过刚锐进,故戒以艰贞闲习。盖初、二两爻皆为所畜,独九三一爻自进耳。」子善问:「九六为正应,皆阴皆阳则为无应,独畜卦不尔,何也?」曰:「阳遇阴,则为阴所畜。九三与上九皆阳,皆欲上进,故但以同类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某作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只大纲依文王本义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辞中发之。且如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刚上尚贤等处,乃孔子发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则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见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顿耳。」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进,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进。然四能止之于初,故为力易。五则阳已进而止之则难,但以柔居尊,得其机会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说,衍一「何」字,亦不可知。砺。
颐
颐,须是正则吉。何以观其正不正?盖「观颐」是观其养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实」是又观其养身是正不正,未说到养人处。「观其所养」,亦只是说君子之所养,养浩然之气模样。
「自养」则如爵禄下至于饮食之类,是说「自求口实」。
问:「『观颐,观其所养』,作所养之道;『观其自养』,作所以养生之术。」曰:「所养之道,如学圣贤之道则为正,黄老申商则为非,凡见于修身行义,皆是也。所养之术,则饮食起居皆是也。」又问:「伊川把『观其所养』作观人之养,如何?」曰:「这两句是解『养正则吉』。所养之道与养生之术正,则吉;不正,则不吉。如何是观人之养!不晓程说是如何。」学履。
「颐卦最难看。」铢问:「本义言『「观颐」谓观其所养之道,「自求口实」谓观其所养之术』,与程传以『观颐』为所以养人之道,『求口实』谓所以自养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传似胜。盖下体三爻皆是自养,上体三爻皆是养人。不能自求所养,而求人以养己则凶,故上三爻皆凶;求于人以养其下,虽不免于颠拂,毕竟皆好,故下三爻皆吉。」又问:「『虎视眈眈』,本义以为『下而专也』。盖『赖其养以施于下』,必有下专之诚,方能无咎。程传作欲立威严,恐未必然。」曰:「颐卦难看,正谓此等。且『虎视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晓耳。」铢曰:「音辩载马氏云:『眈眈,虎下视貌。』则当为『下而专』矣。」曰:「然。」又问:「『其欲逐逐』,如何?」曰:「求养于下以养人,必当继继求之,不厌乎数,然后可以养人而不穷。不然,则所以养人者必无继矣。以四而赖养于初,亦是颠倒。但是求养以养人,所以虽颠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贞吉』,犹洪范『用静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养人,反赖上九之养,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则吉,而涉险阻则不可也。」直卿因云:「颐之六爻,只是『颠拂』二字。求养于下则为颠,求食于上则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颠颐』当为句,『拂经于丘颐』句。『征凶』即其占辞也。六三『拂颐』,虽与上为正应,然毕竟是求于上以养己,所以有『拂颐』之象,故虽正亦凶也。六四『颠颐』,固与初为正应,然是赖初之养以养人,故虽颠亦吉。六五『拂经』,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经』之象;然是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养,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或云:「谚有『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甚好。」曰:「此语,前辈曾用以解颐之象:『慎言语,节饮食。』」
问:「伊川解下三爻养口体,上三爻养德义,如何?」曰:「看来下三爻是资人以为养,上三爻是养人也。六四、六五虽是资初与上之养,其实是他居尊位,藉人以养,而又推以养人,故此三爻似都是养人之事。伊川说亦得,但失之疏也。」学履。义刚录云:「下三爻是资人以养己,养己所以养人也。」
颐六四一爻,理会不得。虽是恁地解,毕竟晓不得如何是「施于下」,又如何是「虎」。砺。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阴柔之才,但守正则吉,故不可以涉患难。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晓。
大过
问:「大过既『栋桡』,不是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辞可见。『栋桡』是以卦体『本末弱』而言,卦体自不好了。却因『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大抵彖传解得卦辞,直是分明。」学履。洽同。
问:「大过小过,先生与伊川之说不同。」曰:「然。伊川此论,正如以反经合道为非相似。殊不知大过自有大过时节,小过自有小过时处大过之时,则当为大过之事;处小过之时,则当为小过之事。如尧舜之禅受,汤武之放伐,此便是大过之事;『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此便是小过之事。只是在事虽是过,然适当其时,便是合当如此做,便是合义。如尧舜之有朱均,岂不能多择贤辅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然道理去不得,须是禅授方合义。汤武岂不能出师以恐吓纣,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须放伐而后已。此所以事虽过,而皆合理也。」
易传大过云:「道无不中,无不常。」圣人有小过,无大过,看来亦不消如此说。圣人既说有「大过」,直是有此事。虽云「大过」,亦是常理,始得。因举晋州蒲事云:「旧常不晓胡文定公意,以问范伯达丈,他亦不晓。后来在都下,见其孙伯逢,问之。渠云:『此处有意思,但是难说出。如左氏分明有「称君无道」之说。厉公虽有罪,但合当废之可也,而栾书中行偃弒之,则不是。然毕竟厉公有罪,故难说,后必有晓此意者。』」赐。
「泽灭木。」泽在下而木在上,今泽水高涨,乃至浸没了木,是为大又曰:「木虽为水浸,而木未尝动,故君子观之而『独立不惧,遯世无闷』。」砺。
小过是收敛入来底,大过是行出来底,如「独立不惧,遯世无闷」是也。
「藉用白茅」,亦有过慎之意。此是大过之初,所以其过尚小在。
问:「大过『栋桡』,是初、上二阴不能胜四阳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刚不中,自不能胜其任,亦有此象。两义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与上六正应,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辅,自是过于刚强,辅他不得。九四『栋隆』,只是隆,便『不桡乎下』。『过涉灭顶』,『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说。易中『无咎』有两义,如『不节之嗟』无咎,王辅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将谁咎?至『出门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谁咎也』。此处恐不然。」又曰:「四阳居中,如何是大过?二阳在中,又如何是小过?这两卦晓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晓得,便也可占。」砺。
大过阳刚过盛,不相对值之义,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了初六是过于畏慎无咎外,九二虽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毕竟是不相当,所以象言「过以相与也」。九四虽吉,而又有他则吝。九五所谓「老妇」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妇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誉」,亦不为全吉。至于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则是事虽凶,而义则无咎也。
「过涉灭顶,凶。」「不可咎也。」东汉诸人不量深浅,至于杀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坎
「水流不盈」,纔是说一坎满便流出去,一坎又满,又流出去。「行险而不失其信」,则是说决定如此。
坎水只是平,不解满,盈是满出来。
六三「险且枕」,只是前后皆是枕,便如枕头之「枕」。砺。
问「来之坎坎」。曰:「经文中迭字如『兢兢业业』之类,是重字。来之自是两字,各有所指,谓下来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进退皆险也。」又问:「六四,旧读『樽酒簋』,句。『贰用缶』,句。本义从之,其说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贰』,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贰,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险之时,刚柔相际,故有但用薄礼,益以诚心,进结自牖之象。」问:「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处,岂险难之时,不容由正以进耶?」曰:「非是不可由正。盖事变不一,势有不容不自牖者。『终无咎』者,始虽不甚好,然于义理无害,故终亦无咎。『无咎者,善补过』之谓也。」又问:「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两股曰纆。』」曰:「据释文如此。」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说文如此。砺。
问「纳约自牖」。曰:「不由户而自牖,以言艰险之时,不可直致也。」
「纳约自牖」,虽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
「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无说处,看来只得作「抵」字解。复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将来必会平。二与五虽是陷于阴中,毕竟是阳会动,陷他不得。如「有孚维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砺。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义。『中未大』者,平则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学履。
离
离便是丽,附着之意。易中多说做丽,也有兼说明处,也有单说明处。明是离之体。丽,是丽着底意思。「离」字,古人多用做丽着说。然而物相离去,也只是这字。「富贵不离其身」,东坡说道剩个「不」字,便是这意。古来自有这般两用底字,如「乱」字又唤做治。
「离」字不合单用。
火中虚暗,则离中之阴也;水中虚明,则坎中之阳也。
问:「离卦是阳包阴,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顺之物。」曰:「然。」砺。
彖辞「重明」,自是五、二两爻为君臣重明之义。大象又自说继世重明之义,不同。同。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丽乎正」,「丽乎中正」,次第说六二分数多。此卦唯这爻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说,只得且说「未详」。本义今无「未详」字。
问「明两作,离。」曰:「若做两明,则是有二个日,不可也,故曰『明两作,离』,只是一个日相继之义。『明两作』,如坎卦『水洊至』,非以『明两』为句也。」「明」字便是指日而言。学履。
「明两作」,犹言「水洊至」。今日明,来日又明。若说两明,却是两个日头!
「明两作,离。」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谓「两作」。盖只是这一个明,两番作,非「明两」,乃「两作」也。
叔重说离卦,问:「『火体阴而用阳』,是如何?」曰:「此言三画卦中阴而外阳者也。坎象为阴,水体阳而用阴,盖三画卦中阳而外阴者也。惟六二一爻,柔丽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虽是柔丽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问「日昃之离」。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乐,则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犹昼之必夜,故君子当观日昃之象以自处。」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临时自不能安耳。」又问「九四『突如其来如』」。曰:「九四以刚迫柔,故有突来之象。『焚』、『死』、『弃』,言无所用也。『离为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来如』与『焚如』,自当属上句。『死如、弃如』,自当做一句。」曰:「说时亦少通,但文势恐不如此。」
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来如」。火之象,则有自焚之义,故曰「焚如,死如,弃如」,言其焚死而弃也。学履。
「焚」、「死」、「弃」,只是说九四阳爻突出来逼拶上爻。「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弃」是死而弃之之意。
「焚如,死如,弃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说。砺。
六五介于两阳之间,忧惧如此,然处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问:「郭冲晦以为离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于得贤,故忧之如此。如『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是否?」曰:「离六五陷于二刚之中,故其忧如此。只为孟子说得此二句,便取以为说,金录云:「恐不是如此,于上下爻不相通。」所以有牵合之病。解释经义,最怕如此。」去伪同。
「有嘉折首」是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