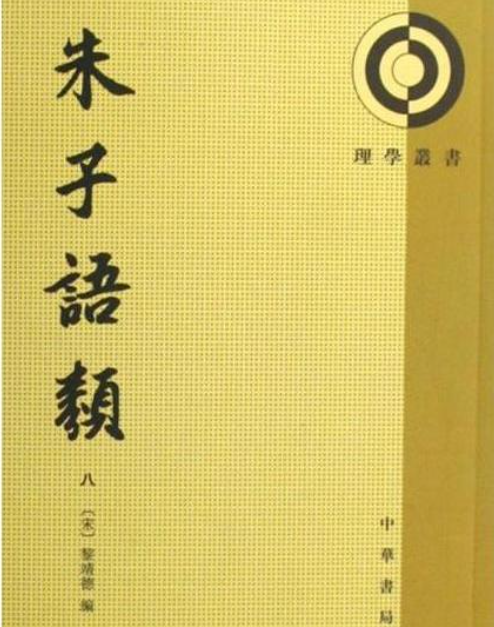大学四或问上
经一章
或问吾子以为大人之学一段
问友仁:「看大学或问如何?」曰:「粗晓其义。」曰:「如何是『收其放心,养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听邪言,目观乱色,口谈不道之言,至于手足动之不以礼,皆是放也。收者,便于邪思妄念处截断不续,至于耳目言动皆然,此乃谓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养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养个德性也。」曰:「看得也好。」友仁。
问:「或问:『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人于已失学后,须如此勉强奋励方得。」曰:「失时而后学,必着如此趱补得前许多欠阙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见没长进,如何要填补前面!」
持敬以补小学之阙。小学且是拘检住身心,到后来『克己复礼』,又是一段事。
问:「大学首云明德,而不曾说主敬,莫是已具于小学?」曰:「固然。自小学不传,伊川却是带补一『敬』字。」
「敬」字是彻头彻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国、平天下,皆不外此。
问或问说敬处。曰:「四句不须分析,只做一句看。」次日,又曰:「夜来说敬,不须只管解说,但整齐严肃便是敬,散乱不收敛便是不敬。四句只行着,皆是敬。」
或问:「大学论敬所引诸说有内外之分。」曰:「不必分内外,都只一般,只恁行着都是敬。」
问:「敬,诸先生之说各不同。然总而行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实只一般。若是敬时,自然『主一无适』,自然『整齐严肃』,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齐严肃』与谢氏尹氏之说又更分晓。」履孙。
或问:「先生说敬处,举伊川主一与整齐严肃之说与谢氏常惺惺之说。就其中看,谢氏尤切当。」曰:「如某所见,伊川说得切当。且如整齐严肃,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无整齐严肃,却要惺惺,恐无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问:「或问举伊川及谢氏尹氏之说,只是一意说敬。」曰:『主一无适』,又说个『整齐严肃』;『整齐严肃』,亦只是『主一无适』意。且自看整齐严肃时如何这里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敛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见。试自体察看,便见。只是要教心下常如此。」因说到放心:「如恻隐、羞恶、是非、辞逊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齐、严肃,便有恻隐、羞恶、是非、辞逊。某看来,四海九州岛,无远无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无一个不放。如小儿子才有智识,此心便放了,这里便要讲学存养。」
光祖问:「『主一无适』与『整齐严肃』不同否?」曰:「如何有两样!只是个敬。极而至于尧舜,也只常常是个敬。若语言不同,自是那时就那事说,自应如此。且如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都说敬;诗也,书也,礼也,亦都说敬。各就那事上说得改头换面。要之,只是个敬。」又曰:「或人问:『出门、使民时是敬,未出门、使民时是如何?』伊川答:『此「俨若思」时也。』要知这两句只是个『毋不敬』。又须要问未出门、使民时是如何。这又何用问,这自可见。如未出门、使民时是这个敬;当出门、使民时也只是这个敬。到得出门、使民了,也只是如此。论语如此样尽有,最不可如此看。」
或问「整齐严肃」与「严威俨恪」之别。曰:「只一般。整齐严肃虽非敬,然所以为敬也。严威俨恪,亦是如此。」
问:「上蔡说:『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说极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齐严肃之说为好。盖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齐严肃,而内不惺惺者。如人一时间外面整齐严肃,便一时惺惺;一时放宽了,便昏怠也。」祖道曰:「此个是须是气清明时,便整齐严肃。昏时便放过了,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气之帅也。』此只当责志。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若能持其志,气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学者为习所夺,气所胜,只可责志。』又曰:『只这个也是私,学者不恁地不得。』此说如何?」曰:「涉于人为,便是私。但学者不如此,如何着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放一句云『不如此不得』也。」
因看涪陵记善录,问:「和靖说敬,就整齐严肃上做;上蔡却云『是惺惺法』,二者如何?」厚之云:「先由和靖之说,方到上蔡地位。」曰:「各有法门:和靖是持守,上蔡却不要如此,常要唤得醒。要之,和靖底是上蔡底。横渠曰:『易曰:「敬以直内。」』伊川云:『主一。』却与和靖同。大抵敬有二:有未发,有已发。所谓『毋不敬』,『事思敬』,是也。」曰:「虽是有二,然但一本,只是见于动静有异,学者须要常流通无间。又如和靖之说固好,但不知集义,又却欠工夫。」曰:「亦是渠才气去不得,只得如此。大抵有体无用,便不浑全。」又问:「南轩说敬,常云:『义已森然于其中。』」曰:「渠好如此说,如仁智动静之类皆然。」
问谢氏惺惺之说。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只此便是敬。今人说敬,却只以『整齐严肃』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烛理不明,虽强把捉,岂得为敬!」又问孟子告子不动心。曰:「孟子是明理合义,告子只是硬把捉。」砥。
或问:「谢氏常惺惺之说,佛氏亦有此语。」曰:「其唤醒此心则同,而其为道则异。吾儒唤醒此心,欲他照管许多道理;佛氏则空唤醒在此,无所作为,其异处在此。」
问:「和靖说:『其心收敛,不容一物。』」曰:「这心都不着一物,便收敛。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当那时直是更不着得些子事,只有个恭敬。』此最亲切。今人若能专一此心,便收敛紧密,都无些子空罅。若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边去,心便成两路。」
问尹氏「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之说。曰:「心主这一事,不为他事所乱,便是不容一物也。」问:「此只是说静时气象否?」曰:「然。」又问:「只静时主敬,便是『必有事』否?」曰:「然。」
此篇所谓在明明德一段
问:「或问说『仁义礼智之性』,添『健顺』字,如何?」曰:「此健顺,只是那阴阳之性。」
问「健顺仁义礼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阴阳五行而言。健,阳也;顺,阴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礼属阳,义智属阴。」问:「『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何以属阴?」曰:「仁何尝属阴!袁机仲正来争辨。他引『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为证。殊不知论仁之定体,则自属阳。至于论君子之学,则又各自就地头说,如何拘文牵引得!今只观天地之化,草木发生,自是条畅洞达,无所窒碍,此便是阳刚之如云:『采薇采薇,薇亦阳止。』『薇亦刚止。』盖薇之生也,挺直而上,此处皆可见。」问:「礼属阳。至乐记,则又以礼属阴,乐属阳。」曰:「固是。若对乐说,则自是如此。盖礼是个限定裁节,粲然有文底物事;乐是和动底物事,自当如此分。如云『礼主其减,乐主其盈』之类,推之可见。」
问:「健顺在四端何属?」曰:「仁与礼属阳,义与智属阴。」问:「小学:『诗、书、礼、乐以造士。』注云:『礼,阴也。』」曰:「此以文明言,彼以节制言。」问:「礼智是束敛底意思,故属阴否?」曰:「然。」或问:「智未见束敛处。」曰:「义犹略有作为,智一知便了,愈是束敛。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也。』纔知得是而爱,非而恶,便交过仁义去了。」
问阴阳五行健顺五常之性。曰:「健是禀得那阳之气,顺是禀得那阴之气,五常是禀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禀得健顺五常之性。且如狗子,会咬人底,便是禀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禀得那顺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禀得刚底;软底弱底,是禀得那顺底。」
问:「或问『气之正且通者为人,气之偏且塞者为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气之聚而后有形,得其清者为人,得其浊者为物。假如大炉镕铁,其好者在一处,其渣滓又在一处。」又问:「气则有清浊,而理则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宝珠。在圣贤,则如置在清水中,其辉光自然发见;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浊水中,须是澄去泥沙,则光方可见。今人所以不见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须要克治也。至如万物亦有此理。天何尝不将此理与他。只为气昏塞,如置宝珠于浊泥中,不复可见。然物类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时者,亦是其中有一线明处。然而不能如人者,只为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饥则噬人之类是也。」
问:「或问云:『于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无清浊之异,故其所赋之质,又有智愚贤不肖之殊。』世间有人聪明通晓,是禀其气之清者矣,然却所为过差,或流而为小人之归者;又有为人贤,而不甚聪明通晓,是如何?」曰:「或问中固已言之,所谓『又有智愚贤不肖之殊』,是也。盖其所赋之质,便有此四样。聪明晓事者,智也而或不贤,便是禀赋中欠了清和温恭之德。又有人极温和而不甚晓事,便是贤而不智。为学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气质令恰好耳。」
舜功问:「序引参天地事,如何?」曰:「初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至下须是见己之所以参化育者。」又问:「此是到处,如何?」曰:「到,大有地步在。但学者须先知其如此,方可以下手。今学者多言待发见处下手,此已迟却。纔思要得善时,便是善。」
问:「或问『自其有生之初』以下是一节;『顾人心禀受之初,又必皆有以得乎阴阳五行之气』以下是一节;『苟于是焉而不值其清明纯粹之会』,这又转一节;下又转入一节物欲去,是否?」曰:「初间说人人同得之理,次又说人人同受之然其间却有撞着不好底气以生者,这便被他拘滞了,要变化却难。」问:「如何是不好底气?」曰:「天地之气,有清有浊。若值得晦暗昏浊底气,这便禀受得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应接事物,逐逐于利欲,故本来明德只管昏塞了。故大学必教人如此用工,到后来却会复得初头浑全底道理。」
林安卿问:「『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其本体已洞然矣。』须是就这些觉处,便致知充扩将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击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觉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这般时节!林先引或问中「至于久而后有觉」之语为比,先生因及此。那个觉,是物格知至了,大彻悟。到恁地时,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觉,一日之间,其发也无时无数,只要人识认得操持充养将去。」又问:「『真知』之『知』与『久而后有觉』之『觉』字,同否?」曰:「大略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个如此,不只是听得人说,便唤做知。觉,则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觉悟,晓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两般心:一个是是底心,一个是不是底心。只是才知得这是个不是底心,只这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将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将这个做主去治那个客,便常守定这个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别讨个心来唤做是底心!如非礼勿视听言动,只才知得这个是非礼底心,此便是礼底心,便莫要视。如人瞌睡,方其睡时,固无所觉。莫教纔醒,便抖擞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已醒了,更别去讨个醒,说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谓『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两个心,不知只是将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元思云:「上蔡所谓『人须是识其真心』,方乍见孺子入井之时,其怵惕、恻隐之心,乃真心也。」曰:「孟子亦是只讨譬喻,就这亲切处说仁之心是如此,欲人易晓。若论此心发见,无时而不发见,不特见孺子之时为然也。若必待见孺子入井之时,怵惕、恻隐之发而后用功,则终身无缘有此等时节也。」元思云:「旧见五峰答彪居仁书,说齐王易牛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然。齐王之良心,想得也常有发见时。只是常时发见时,不曾识得,都放过了。偶然爱牛之心,有言语说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广之也。」又问:「自非物欲昏蔽之极,未有不醒觉者。」曰:「便是物欲昏蔽之极,也无时不醒觉。只是醒觉了,自放过去,不曾存得耳。」
友仁说「明明德」:「此『明德』乃是人本有之物,只为气禀与物欲所蔽而昏。今学问进修,便如磨镜相似。镜本明,被尘垢昏之,用磨擦之工,其明始现。及其现也,乃本然之明耳。」曰:「公说甚善。但此理不比磨镜之法。」先生略抬身,露开两手,如闪出之状,曰:「忽然闪出这光明来,不待磨而后现,但人不自察耳。如孺子将入于井,不拘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便可见。」友仁云:「或问中说『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便是这个道理。」先生颔之,曰:「于大原处不差,正好进修。」友仁。
问:「或问:『所以明而新之者,非可以私意苟且为也。』私意是说着不得人为,苟且是说至善。」曰:「才苟且,如何会到极处!」贺孙举程子义理精微之极。曰:「大抵至善只是极好处,十分端正恰好,无一毫不是处,无一毫不到处。且如事君,必当如舜之所以事尧,而后唤做敬;治民,必当如尧之所以治民,而后唤做仁。不独如此,凡事皆有个极好处。今之人,多是理会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来,唤做好也得,唤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识得到,少刻也会入于老,也会入于佛,也会入于申韩之刑名。止缘初间不理会到十分,少刻便没理会那个是白,那个是皂,那个是酸,那个是咸。故大学必使人从致知直截要理会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间半界,含含糊糊。某与人商量一件事,须是要彻底教尽。若有些子未尽处,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处,须着极力辨别教是。且看孟子,那个事恁地含糊放过!有一字不是,直争到底。这是他见得十分极至,十分透彻,如何不说得?」
问:「或问说明德处云:『所以应乎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其说至善处,又云:『所以见于日用之间者,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则。』二处相类,何以别?」曰:「都一般。至善只是明德极尽处,至纤至悉,无所不尽。」
仁甫问:「以其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说。至善,便如今人说极是。且如说孝:孟子说『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此是不孝。到得会奉养其亲,也似煞强得这个,又须着如曾子之养志,而后为能养。这又似好了,又当如所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不遗父母恶名』,使国人称愿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于尊亲,其次能养。直是到这里,方唤做极是处,方唤做至善处。」
郭德元问:「或问:『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谓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类甚多。自谓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务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于至善者,如前日所论王通便是。卓录云:「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顾乃安于小成,因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论王通之事是也。」看他于己分上亦甚修饬,其论为治本末,亦有条理,甚有志于斯世。只是规模浅狭,不曾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彻。须是无所不用其极,方始是。看古之圣贤别无用心,只这两者是吃紧处:明明德,便欲无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于事事物物上皆是当。正如佛家说,『为此一大事因缘出见于世』,此亦是圣人一大事也。千言万语,只是说这个道理。若还一日不扶持,便倒了。圣人只是常欲扶持这个道理,教他撑天柱地。」
问:「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谓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种人不如此,此便是释、老之学。此个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专独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须当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岂可说我自会了,我自乐之,不与人共!」因说,曾有学佛者王天顺,与陆子静辨论云:「我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脑,皆不爱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岂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陆子静从初亦学佛,尝言:『儒佛差处是义利之间。』某应曰:『此犹是第二着,只它根本处便不是。当初释迦为太子时,出游,见生老病死苦,遂厌恶之,入雪山修行。从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弃之不猛,屏除之不尽。吾儒却不然。盖见得无一物不具此理,无一理可违于物。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从此一差,方有公私、义利之不同。』今学佛者云『识心见性』,不知是识何心,是见何性。」
知止而后有定以下一段
问:「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曰:「定、静、安三项若相似,说出来煞不同。有定,是就事理上说,言知得到时,见事物上各各有个合当底道理。静,只就心上说。」问:「『无所择于地而安』,莫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否?」曰:「这段须看意思接续处。如『能得』上面带个『虑』字,『能虑』上面带个『安』字,『能安』上面带个『静』字,『能静』上面带个『定』字,『有定』上面带个『知止』字,意思都接续。既见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宁静了,看处在那里:在这里也安,在那边也安,在富贵也安,在贫贱也安,在患难也安。不见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区处不得,恁地区处又不得,这如何会有定!才不定,则心下便营营皇皇,心下才恁地,又安顿在那里得!看在何处,只是不安。」
「能虑则随事观理,极深研几。」曰:「到这处又更须审一审。『虑』字看来更重似『思』字。圣人下得言语恁地镇重,恁地重三迭四,不若今人只说一下便了,此圣人所以为圣人。」
安卿问:「『知止是始,能得是终。』或问言:『非有等级之相悬。』何也?」曰:「也不是无等级,中间许多只是小阶级,无那大阶级。如志学至从心,中间许多便是大阶级,步却阔。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学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静、安,皆相类,只是中间细分别恁地。」问:「到能得处是学之大成,抑后面更有工夫?」曰:「在己已尽了,更要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段
问:「或问『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齐家治国说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后,更要去齐家,治国,平天下?」曰:「以修身言之,都已尽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己无所不尽,万物之理亦无所不尽。如至诚惟能尽性,只尽性时万物之理都无不尽了。故尽其性,便尽人之性;尽人之性,便尽物之性。」
蜚卿言:「或问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尧舜之圣,闺门之内,或未尽化,况谓天下之大,能服尧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学『明明德于天下』,只是且说个规模如此。学者须是有如此规模,却是自家本来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泽,如己推而纳之沟中,伊尹也只大概要恁地,又如何使得无一人不被其泽!又如说『比屋可封』,也须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见得自家规模自当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得做不去处,却无可奈何。规模自是着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进。若无规模次第,只管去细碎处走,便入世之计功谋利处去;若有规模而又无细密工夫,又只是一个空规模。外极规模之大,内推至于事事物物处,莫不尽其工夫,此所以为圣贤之学。」
问或问「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无事时,都不见;到得应事接物,便在这里;应事了,又不见:恁地神出鬼没!」又曰:「理是定在这里,心便是运用这理底,须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为善也未肯便与你为善;欲不为恶,也未肯便不与你为恶。知得到了,直是如饥渴之于饮食。而今不读书时,也须收敛身心教在这里,乃程夫子所谓敬也。『整齐严肃』,虽只是恁地,须是下工夫,方见得。」
德元问:「何谓『妙众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或录此下云:「便只是理,才知得。」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或录云:「才知得底,便是自家先有之道理也。只是无知,则道无安顿处。故须知,然后道理有所凑泊也。如夏热冬寒,君仁臣敬,非知,如何知得!」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或录云:「盖知得此理也。」又问:「知与思,于身最切紧。」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
问:「知如何宰物?」曰:「无所知觉,则不足以宰制万物。要宰制他,也须是知觉。」
或问:「『宰万物』,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又问:「孟子集注言:『心者,具众理而应万事。』此言『妙众理而宰万物』,如何?」曰:「『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稳当,『具』字便平稳。」履孙。
郭兄问「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层。如君之所以仁,盖君是个主脑,人民土地皆属它管,它自是用仁爱。试不仁爱看,便行不得。非是说为君了,不得已用仁爱,自是理合如此。试以一家论之:为家长者便用爱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着,极好笑,自那原头来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盖父子本同一气,只是一人之身,分成两个,其恩爱相属,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伦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岂容强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这物时便有个仁,它只知生而已。从他原头下来,自然有个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阴阳,有阴阳,便有此四者。故赋于人物,便有仁义礼智之性。仁属春,属木。且看春间天地发生,蔼然和气,如草木萌芽,初间仅一针许,少间渐渐生长,以至枝叶花实,变化万状,便可见他生生之意。非仁爱,何以如此。缘他本原处有个仁爱温和之理如此,所以发之于用,自然慈祥恻隐。孟子说『恻隐之端』,恻隐又与慈仁不同,恻隐是伤痛之切。盖仁,本只有慈爱,缘见孺子入井,所以伤痛之切。义属金,是天地自然有个清峻刚烈之所以人禀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恶之心。礼智皆然。盖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龟山问一学者:『当见孺子入井时,其心怵惕、恻隐,何故如此?』学者曰:『自然如此。』龟山曰:『岂可只说自然如此了便休?须是知其所自来,则仁不远矣。』龟山此语极好。又或人问龟山曰:『「以先知觉后知」,知、觉如何分?』龟山曰:『知是知此事,觉是觉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觉此理也。」
或问「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曰:「后来看得,且要见得『所当然』是要切处。若果见得不容已处,则自可默会矣。」
治国平天下者诸侯之事一段
问:「南轩谓:『为己者,无所为而然也。』」曰:「只是见得天下事皆我所合当为而为之,非有所因而为之。然所谓天下之事皆我之所当为者,只恁地强信不得。须是学到那田地,经历磨炼多后,方信得」
问为己。曰:「这须要自看,逐日之间,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这便是无所为。且如读书,只道自家合当如此读,合当如此理会身己。才说要人知,便是有所为。如世上人才读书,便安排这个好做时文,此又为人之甚者。」
「『为己者,无所为而然。』无所为,只是见得自家合当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钱谷、笾豆、有司,到当自家理会便理会,不是为别人了理会。如割股、庐墓,一则是不忍其亲之病,一则是不忍其亲之死,这都是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器远问:「子房以家世相韩故,从少年结士,欲为韩报仇,这是有所为否?」曰:「他当初只一心欲为国报仇。只见这是个臣子合当做底事,不是为别人,不是要人知。」
行夫问「为己者无所为而然」。曰:「有所为者,是为人也。这须是见得天下之事实是己所当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后为之,而无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今人吊人之丧,若以为亡者平日与吾善厚,真个可悼,哭之发于中心,此固出于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这便是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强做,此便不是为人也。」道夫曰:「先生所说钱谷、甲兵、割股、庐墓,已甚分明,在人所见如何尔。」又问:「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诚心为之,不求人知,亦庶几。」「今有以此要誉者。」因举一事为问。先生询究,骇愕者久之,乃始正色直辞曰:「只是自家过计了。设使后来如何,自家也未到得如此,天下事惟其直而已。试问乡邻,自家平日是甚么样人!官司推究亦自可见。」行夫曰:「亦着下狱使钱,得个费力去。」曰:「世上那解免得全不沾湿!如先所说,是不安于义理之虑。若安于义理之虑,但见义理之当为,便恁滴水滴冻做去,都无后来许多事。」
传一章
然则其曰克明德一段
问:「『克明德』,『克,能也』。或问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虽训『能』字,然『克』字重于『能』字。『能』字无力,『克』字有力。便见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独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语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训义一般,而声响顿异,便见得有力无力之分,如『克』之与『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类,可见。」
顾諟天之明命一段
问:「『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如何是体?如何是用?」曰:「体与用不相离。且如身是体,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只此一端,体、用便可见。如喜怒哀乐是用,所以喜怒哀乐是体。」淳录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体。」
问:「或问:『常目在之,真若见其「参于前,倚于衡」也,则「成性存存」,而道义出矣。』不知所见者果何物耶?」曰:「此岂有物可见!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与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谓顾諟者,只是心里常常存着此理在。一出言,则言必有当然之则,不可失也;一行事,则事必有当然之则,不可失也。不过如此耳,初岂实有一物可以见其形象耶!」
问:「引『成性存存」,道义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谓之明命,我这里得之于己,谓之明德,只是一个道理。人只要存得这些在这里。才存得在这里,则事君必会忠;事亲必会孝;见孺子,则怵惕之心便发;见穿窬之类,则羞恶之心便发;合恭敬处,便自然会恭敬;合辞逊处,便自然会辞逊。须要常存得此心,则便见得此性发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这些,待做出,那个会合道理!」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问:「『顾諟』一句,或问复以为见『天之未始不为人,而人之未始不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无不善,而其日用之间莫不有当然之则。则,所谓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则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
问「天未始不为人,而人未始不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也。只今说话,天便在这里。顾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灿烂,照在目前。」
传二章
或问盘之有铭一段
德元问:「汤之盘铭,见于何书?」曰:「只见于大学。」又曰:「成汤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来,大段是一个修饬底人,故当时人说他做工夫处亦说得大段地着。如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之类,却是大纲说。到汤,便说『检身若不及』。」文蔚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不迩声色,不殖货利』等语,可见日新之功。」曰:「固是。某于或问中所以特地详载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学者经心耳。」
问:「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从』字意如何?」曰:「从,顺也。敬便竖起,怠便放倒。以理从事,是义;不以理从事,便是欲。这处敬与义,是个体、用,亦犹坤卦说敬、义。」
传三章
复引淇澳之诗一段
「『瑟兮僩兮者,恂栗也』。『僩』字,旧训宽大。某看经子所载,或从『[忄]』、或从『扌』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则方与『瑟』字及下文恂栗之说相合。」曰:「且如『恂』字,郑氏读为『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读庄子,见所谓『木处则惴栗恂惧』,然后知郑氏之音为当。如此等处,某于或问中不及载也。要之,如这般处,须是读得书多,然后方见得。」
问:「切磋琢磨,是学者事,而『盛德至善』,或问乃指圣人言之,何也?」曰:「后面说得来大,非圣人不能。此是连上文『文王于缉熙敬止』说。然圣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处,也须学始得。如孔子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此有甚紧要?圣人却忧者,何故?惟其忧之,所以为圣人。所谓『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学而犹虑其未至,则复讲习讨论以求之,犹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切得一个朴在这里,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于滑泽,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犹虑其未至,则又省察克治以终之,犹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琢,是琢得一个朴在这里,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于精细,这是治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于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正心、诚意,便是道学、自修。『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到这里,睟面盎背,发见于外,便是道学、自修之验也。」道夫云:「所以或问中有始终条理之别也,良为此尔。」曰:「然。」
「『如切如磋』,道学也」,却以为始条理之事;「『如琢如磨』,自修也」,却以为终条理之事,皆是要工夫精密。道学是起头处,自修是成就处。中间工夫,既讲求又复讲求,既克治又复克治,此所谓已精而求其益精,已密而求其益密也。
周问:「切磋是始条理,琢磨是终条理。终条理较密否?」曰:「始终条理都要密,讲贯而益讲贯,修饬而益修饬。」
问:「琢磨后,更有瑟僩赫喧,何故为终条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处,是成就了气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气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