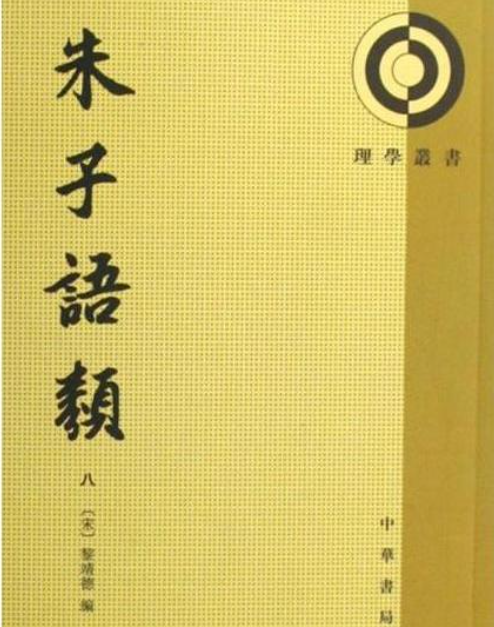大学五或问下
传五章
独其所谓格物致知者一段
先生为道夫读格物说,举遗书「或问学何为而可以有觉」一段,曰:「『能致其知,则思自然明,至于久而后有觉』,是积累之多,自有个觉悟时『勉强学问』,所以致其知也。『闻见博而智益明』,则其效着矣。『学而无觉,则亦何以学为也哉?』此程子晓人至切处。」
问:「致知下面更有节次。程子说知处,只就知上说,如何?」曰:「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
伊川云「知非一概,其为浅深有甚相绝者」云云。曰:「此语说得极分明。至论知之浅深,则从前未有人说到此。」
知,便要知得极。致知,是推致到极处,穷究彻底,真见得决定如此。程子说虎伤人之譬,甚好。如这一个物,四陲四角皆知得尽,前头更无去处,外面更无去处,方始是格到那物极处。
「人各有个知识,须是推致而极其不然,半上落下,终不济事。须是真知。」问:「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养未到,却为私意所夺。」曰:「只为明得不尽。若明得尽,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黄,未能透彻,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谓真知也。」问:「须是涵养到心体无不尽处,方善。不然知之虽至,行之终恐不尽也。」曰:「只为知不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它只知得五分,见识只识到那地位。譬诸穿窬,稍是个人,便不肯做,盖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伤事亦然。」
「致知,是推极吾之知识无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个「尽」字底道理。见得尽,方是真实。如言吃酒解醉,吃饭解饱,毒药解杀人。须是吃酒,方见得解醉人;吃饭,方见得解饱人。不曾吃底,见人说道是解醉解饱,他也道是解醉解饱,只是见得不亲切。见得亲切时,须是如伊川所谓曾经虎伤者一般。卓。
问「进修之术何先者」云云。曰:「物理无穷,故他说得来亦自多端。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专,则所格亦非一端而尽。如曰:『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但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此一项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问,则亦何以得之哉?」
问:「『一理通则万理通』,其说如何?」曰:「伊川尝云:『虽颜子亦未到此。』天下岂有一理通便解万理皆通!也须积累将去。如颜子高明,不过闻一知十,亦是大段聪明了。学问却有渐,无急迫之理。有人尝说,学问只用穷究一个大处,则其它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说,须是逐旋做将去。不成只用穷究一个,其它更不用管,便都理会得。岂有此理!为此说者,将谓是天理,不知却是人欲。」
叔文问:「正心、诚意,莫须操存否?」曰:「也须见得后,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济事。盖谨守则在此,一合眼则便走了。须是格物。盖物格则理明,理明则诚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则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难事,如何尽格得?」曰:「程子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某尝谓,他此语便是真实做工夫来。他也不说格一件后便会通,也不说尽格得天下物理后方始通。只云:『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又曰:「今却不用虑其它,只是个『知至而后意诚』,这一转较难。」
问:「伊川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读书,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会一事,明日理会一事,积习多后,自然通贯。」德功云:「释氏说斫树木,今日斫,明日斫,到树倒时,只一斫便了。」
问:「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执着否?」曰:「人日用间自是不察耳。若体察当格之物,一日之间尽有之。」
穷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穷理者,只是足于已知已达,而不能穷其未知未达,故见得一截,不曾又见得一截,此其所以于理未精也。然仍须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进得一步,右脚又进一步;右脚进得一步,左脚又进,接续不已,自然贯通。
黄毅然问:「程子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说要随事理会。恐精力短,如何?」曰:「也须用理会。不成精力短后,话便信口开,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又问:「无事时见得是如此,临事又做错了,如何?」曰:「只是断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闲时看得道理分晓,则事来时断置自易。格物只是理会未理会得底,不是从头都要理会。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错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会当蹈水火与不当蹈水火,临事时断置教分晓。程子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圣贤说话粹,无可疑者。若后世诸儒之言,唤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里面也有不好处,不好底里面也有好处;有这一事说得是,那一件说得不是;有这一句说得是,那一句说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别。如临事,亦要如此理会那个是,那个不是。若道理明时,自分晓。有一般说,汉唐来都是;有一般说,汉唐来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贾谊说话,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须是要见得他那个议论是,那个议论不是。如此,方唤做格物。如今将一个物事来,是与不是见得不定,便是自家这里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则这样处自通透。」黄自录详,别出。
问:「陆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说。若以为随事讨论,则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则无所不照,其说亦似省力。」曰:「不去随事讨论后,听他胡做,话便信口说,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义刚曰:「平时明知此事不是,临时却做错了,随即又悔。此毕竟是精神短后,照烛不逮。」曰:「只是断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牵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后,只听他牵去。须是知道那里不可去,我不要随他去。」义刚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断制不下,这须是精神强,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错去蹈水火来!若是平时看得分明时,卒然到面前,须解断制。若理会不得时,也须临事时与尽心理会。十分断制不下,则亦无奈何。然亦岂可道晓不得后,但听他!如今有十人,须看他那个好,那个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处得那件是,那件不是。处得是,又有曲折处。而今人读书,全一例说好底,固不是。但取圣人书,而以为后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圣人之言,自是纯粹。但后世人也有说得是底,如汉仲舒之徒。说得是底还他是。然也有不是处,也自可见。须是如此去穷,方是。但所谓格物,也是格未晓底,已自晓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说那难理会底。」
「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其始固须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个事不可欲速,「欲速则不达」,须是慢慢做去。
问:「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曰:「此一段,尤其切要,学者所当深究。」道夫曰:「自一身以至万物之理,则所谓『由中而外,自近而远,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处,是非人力勉强而至者也。」
行夫问:「明道言致知云:『夫人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然有个觉悟处。』」曰:「一身之中是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与夫耳目手足视听言动,皆所当理会。至若万物之荣悴与夫动植小大,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皆所当理会。」又问:「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曰:「公且说,天是如何独高?盖天只是气,非独是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见如此要之,他连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转来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许多渣滓在中间。世间无一个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气之渣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显,自今观之,他是以鬼为幽,以神为显。鬼者,阴也;神者,阳也。气之屈者谓之鬼,气之只管恁地来者谓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这便是那发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长大,故见其显,便是气之伸者。今人谓人之死为鬼,是死后收敛,无形无迹,不可理会,便是那气之屈底。」道夫问:「横渠所谓『二气之良能』,良能便是那会屈伸底否?」曰:「然。」
明道云:「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会得五六十件了,这三四十件虽未理会,也大概是如此。向来某在某处,有讼田者,契数十本,中间一段作伪。自崇宁、政和间,至今不决。将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众契比验,前后所断情伪更不能逃者。穷理亦只是如此。
问:「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曰:「程先生言语气象自活,与众人不同。」
器远问:「格物当穷究万物之理令归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间多了,自然会贯通。如一案有许多器用,逐一理会得,少间便自见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晓未得,又去看一样,看那个未了,又看一样,到后一齐都晓不得。如人读书,初未理会得,却不去究心理会。问他易如何,便说中间说话与书甚处相类。问他书如何,便云与诗甚处相类。一齐都没理会。所以程子说:『所谓穷理者,非欲尽穷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此语最亲切。」
问:「知至若论极尽处,则圣贤亦未可谓之知如孔子不能证夏商之礼,孟子未学诸侯丧礼,与未详周室班爵之制之类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虽未能事事知得,然理会得已极多。万一有插生一件差异底事来,也都识得他破。只是贯通,便不知底亦通将去。某旧来亦如此疑,后来看程子说:『格物非谓欲尽穷天下之物,又非谓只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脱然有悟处。』方理会得。」
问程子格物之说。曰:「须合而观之,所谓『不必尽穷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穷得八九,则其一二虽未穷得,将来凑会,都自见得。又如四旁已穷得,中央虽未穷得,毕竟是在中间了,将来贯通,自能见得。程子谓『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此语最好。若以为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日又一一穷这草木是如何,明日又一一穷这草木是如何,则不胜其繁矣。盖当时也只是逐人告之如此。」
问:「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久,自当脱然有贯通处。』又言:『格物非谓尽穷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二说如何?」曰:「既是教类推,不是穷尽一事便了。且如孝,尽得个孝底道理,故忠可移于君,又须去尽得忠。以至于兄弟、夫妇、朋友,从此推之无不尽穷,始得。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穷得黑,不穷得白,亦不得。且如水虽是冷而湿者,然亦有许多样,只认冷湿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须从近处做去。若幽奥纷拏,却留向后面做。所以先要读书,理会道理。盖先学得在这里,到临时应事接物,撞着便有用处。且如火炉,理会得一角了,又须都理会得三角,又须都理会得上下四边,方是物格。若一处不通,便非物格也。」又曰:「格物不可只理会文义,须实下工夫格将去,始得。」
问:「伊川论致知处云:『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窃谓致之为言,推而致之以至于尽也。于穷不得处正当努力,岂可迁延逃避,别穷一事邪?至于所谓『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类推而通其余矣』。夫专心致志,犹虑其未能尽知,况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难者乎?」曰:「这是言随人之量,非曰迁延逃避也。盖于此处既理会不得,若专一守在这里,却转昏了。须着别穷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问:「程子『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之说,与中庸『弗得弗措』相发明否?」曰:「看来有一样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这个,少间便会担阁了。若谓穷一事不得,便掉了别穷一事,又轻忽了,也不得。程子为见学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说此话。」
仁甫问:「伊川说『若一事穷不得,须别穷一事』,与延平之说如何?」曰:「这说自有一项难穷底事,如造化、礼乐、度数等事,是卒急难晓,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这如何要穷晓得?若使孔子复生,也便未易理会在。须是且就合理会底所在理会。延平说,是穷理之要。若平常遇事,这一件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二件;第二件理会未得,又理会第三件,恁地终身不长进。」
陶安国问:「『千蹊万径,皆可适国。』国,恐是譬理之一源处。不知从一事上便可穷得到一源处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类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间曲折甚多,须是把这个做样子,却从这里推去,始得。且如事亲,固当尽其事之之道,若得于亲时是如何,不得于亲时又当如何。以此而推之于事君,则知得于君时是如何,不得于君时又当如何。推以事长,亦是如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
德元问:「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曰:「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圣人所以『穷理尽性而至于命』,凡世间所有之物,莫不穷极其理,所以处置得物物各得其所,无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无此物,方无此理;既有此物,圣人无有不尽其理者。所谓『惟至诚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者也。』」
行夫问:「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远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众,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这个道理,某不用假借于公,公不用求于某,仲思与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虽各自有一个理,又却同出于一个理尔。如排数器水相似;这盂也是这样水,那盂也是这样水,各各满足,不待求假于外。然打破放里,却也只是个水。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所以谓格得多后自能贯通者,只为是一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濂溪通书只是说这一事。」
或问:『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曰:「一个一般道理,只是一个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窝窟便有大窝窟水,小窝窟便有小窝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随处各别,只是一般水。」
又问「物必有理,皆所当穷」云云。曰:「此处是紧切。学者须当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为幽显,山岳如何而能融结,这方是格物。」
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己。』此说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无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将来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并自知。」
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其实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所以大学说「致知在格物」,又不说「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
程子云:「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只是举其至大与其至细者,言学者之穷理,无一物而在所遗也。至于言「讲明经义,论古今人物及应接事物」,则上所言亦在其中矣。但天地高厚,则资次未到这里,亦未易知尔。
问「致知之要当知至善之所在」云云。曰:「天下之理,偪塞满前,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非物也,若之何而穷之哉!须当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后于物之所在从而察之,则不至于泛滥矣。」
周问:「程子谓『一草一木,皆所当穷』。又谓『恐如大军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何也?」曰:「便是此等语说得好,平正,不向一边去。」
问:「程子谓『如大军游骑无所归』,莫只是要切己看否?」曰:「只要从近去。」士毅。
且穷实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穷天下万物之理,不务切己,即是遗书所谓「游骑无所归」矣。
问:「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当理会,然后方可?」曰:「不必如此。圣人正怕人如此。圣人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圣人恐人走作这心无所归着。故程子云:『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
「或问格物问得太烦」。曰:「若只此联缠说,济得自家甚事。某最怕人如此。人心是个神明不测物事,今合是如何理会?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顿?如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合是如何区处?就切近处,且逐旋理会。程先生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泛然观万物之理,恐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莫急于教人,然且就身上理会。凡纤悉细大,固着逐一理会。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
问:「格物虽是格天下万物之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显,微而至于一草一木之间,物物皆格,然后可也;然而用工之始,伊川所谓『莫若察之吾身者为急』。不知一身之中,当如何用力,莫亦随事而致察否?」曰:「次第亦是如此。但如今且从头做将去。若初学,又如何便去讨天地高深、鬼神幽显得?且如人说一件事,明日得工夫时,也便去做了。逐一件理会去,久之自然贯通。但除了不是当闲底物事,皆当格也。」又曰:「物既格,则知自」履孙。
问「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说当察物理,不可专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于身为尤切,皆是互相发处。」
问「格物穷理,但立诚意以格之」。曰:「立诚意,只是朴实下工夫,与经文『诚意』之说不同。」
问「立诚意以格之」。曰:「此『诚』字说较浅,未说到深处,只是确定徐录作「坚确」。其志,朴实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此意。」
李德之问「立诚意以格之」。曰:「这个诚意,只是要着实用力,所以下『立』字。」
诚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谓立诚意者,只是要着实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须是真个即此一物究极得个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大学盖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则必在于立诚。佐。
问:「中庸言自明而诚,今先生教人以诚格物,何故?」曰:「诚只是一个诚,只争个缓颊。」
问「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敬则此心惺惺。」
伊川谓「学莫先于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师之也;敬,是克一而协之也。
敬则心存,心存,则理具于此而得失可验,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问:「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盖敬则胸次虚明,然后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虽是如此,然亦须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为之蔽,然后胸次方得虚明。只一个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时时提撕着,亦易以昏困。须是提撕,才见有私欲底意思来,便屏去。且谨守着,到得复来,又屏去。时时提撕,私意自当去也。」
问:「春间幸闻格物之论,谓事至物来,便格取一个是非,觉有下手处。」曰:「春间说得亦太迫切。只是伊川说得好。」问:「如何迫切?」曰:「取效太速,相次易生出病。伊川教人只说敬,敬则便自见得一个是非。」
问:「春间所论致知格物,便见得一个是非,工夫有依据。秋间却以为太迫切,何也?」曰:「看来亦有病,侵过了正心、诚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说敬,又所论格物、致知,多是读书讲学,不专如春间所论偏在一边。今若只理会正心、诚意,池录作「四端情性」。却有局促之病;只说致知、格物,池录作「读书讲学」,一作「博穷众理」。又却似泛滥。古人语言自是周浃。若今日学者所谓格物,却无一个端绪,只似寻物去格。如齐宣王因见牛而发不忍之心,此盖端绪也,便就此扩充,直到无一物不被其泽,方是。致与格,只是推致穷格到尽处。凡人各有个见识,不可谓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恶是非之际,亦甚分晓。但不推致充广,故其见识终只如此。须是因此端绪从而穷格之。未见端倪发见之时,且得恭敬涵养;有个端倪发见,直是穷格去。亦不是凿空寻事物去格也。」又曰:「涵养于未发见之先,穷格于已发见之后。」
问:「格物,敬为主,如何?」曰:「敬者,彻上彻下工夫。」
问:「格物,或问论之已详。不必分大小先后,但是以敬为本后,遇在面前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须是从近处格将去。」
问:「程先生所说,格物之要,在以诚敬为主。胡氏说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说得为人切处。古人由小便学来如,『视无诳』,如『洒埽、应对、进退』,皆是少年从小学,教他都是诚敬。今人小学都不曾去学,却欲便从大学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诚不敬,诚是不欺不妄;敬是无怠慢放荡。纔格不到,便弃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谓敬。』此理又深。」又说:「今人所作所为,皆缘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学,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说甚好。非止为读书说,一切之事皆要立志。」椿。
问「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曰:「二者偏废不得。致知须用涵养,涵养必用致知。」
任道弟问:「或问,涵养又在致知之先?」曰:「涵养是合下在先。古人从小以敬涵养,父兄渐渐教之读书,识义理。今若说待涵养了方去理会致知,也无期限。须是两下用工,也着涵养,也着致知。伊川多说敬,敬则此心不放,事事皆从此做去。」因言「此心至灵,细入毫芒纤芥之间,便知便觉,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到那里;下面方来又不知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也到那里。这个神明不测,至虚至灵,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将这个心包了。起居动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动,便是这个物事」。广录云:「或问存养、致知先后。曰:『程先生谓:「存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盖古人才生下儿子,便有存养他底道理。父兄渐渐教他读书,识义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学者先须存养。然存养便当去穷理。若说道,俟我存养得,却去穷理,则无期矣。因言人心至灵,虽千万里之远,千百世之上,一念才发,便到那里。神妙如此,却不去养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转于利欲中,都不知觉!』」
问窦:「看格物之义如何?」曰:「须先涵养清明,然后能格物。」曰:「亦不必专执此说。事到面前,须与他分别去。到得无事,又且持敬。看自家这里敬与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来,便与屏彻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己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顷,便有许多语话,岂不是动。才不语话,便是静。一动一静,循环无已,便就此穷格,无有空阙时,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时亦曾说,未有事时且涵养,到得有事却将此去应物,却成两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笃敬』,只见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蛮貊之邦行矣』,便未须理会。及其久也,只见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为忠信笃敬如何,而忠信笃敬自在里许,方好。」从周录云:「先生问:『如何理会致知、格物?』曰:『涵养主一之义,使心地虚明,物来当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则两截了。』」
又问「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道夫云:「『养知莫过于寡欲』,此句最为紧切。」曰:「便是这话难说,又须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着寡欲,又不得。」
行夫问「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曰:「二者自是个两头说话,本若无相干。但得其道,则交相为养;失其道,则交相为害。」
杨子顺问:「『养知莫过于寡欲』,是既知后,便如此养否?」曰:「此不分先后。未知之前,若不养之,此知如何发得。既知之后,若不养,则又差了。」
「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识而至于尽也。将致知者,必先有以养其知。有以养之,则所见益明,所得益固。欲养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则无纷扰之杂,而知益明矣;无变迁之患,而得益固矣。直卿。
遗书晁氏客语卷中,张思叔记程先生语云「思欲格物,则固已近道」一段甚好,当收入近思录。
问:「畅潜道记一篇,多有不是处,如说格物数段。如云『思欲格物则固已近道』,言皆缓慢。」曰:「它不合作文章,意思亦是,只是走作。」又问:「如云『可以意得,不可以言传』,此乃学佛之下一段云『因物有迁』数语,似得之。」曰:「然。」先生举一段云:「极好。」记夜又问:「它把致知为本,亦未是。」曰:「他便把终始本末作一事了。」
问:「看致知说如何?」曰:「程子说得确实平易,读着意味愈长。」先生曰:「且是教人有下手处。」
问大学致知、格物之曰:「程子与门人言亦不同:或告之读书穷理,或告之就事物上体察。」炎。
先生既为道夫读程子致知说,复曰:「『格物』一章,正大学之头首,宜熟复,将程先生说更逐段研究。大抵程先生说与其门人说,大体不同。不知当时诸公身亲闻之,却因甚恁地差了。」
问:「两日看何书?」对:「看或问『致知』一段,犹未了。」曰:「此是最初下手处,理会得此一章分明,后面便容易。程子于此段节目甚多,皆是因人资质说,故有说向外处,有说向内处。要知学者用功,六分内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难,若六分外面,则尤不可。今有一等人甚明,且于道理亦分晓,却只恁地者,只是向外做工夫。」士毅。广录详。
「致知」一章,此是大学最初下手处。若理会得透彻,后面便容易。故程子此处说得节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资质耳。虽若不同,其实一也。见人之敏者,太去理会外事,则教之使去父慈、子孝处理会,曰:「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若是人专只去里面理会,则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时,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或问程子致知、格物之说不同。曰:「当时答问,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须是合就许多不同处,来看作一意为佳。且如既言『不必尽穷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于一草一木上理会,有甚了期。但其间有『积习多后自当脱然有贯通处』者为切当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旁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盖长短大小,自有准则。如忽然遇一件事来时,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则此方来之事亦有可见者矣。圣贤于难处之事,只以数语尽其曲折,后人皆不能易者,以其于此理素明故也。」又云:「所谓格物者,常人于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穷得来无去处,方是格物。」
问:「伊川说格物、致知许多项,当如何看?」曰:「说得已自分晓。如初间说知觉及诚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后有以行之』,这许多说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间说物物当格,及反之吾身之说,却是指出格物个地头如此。」又云:「此项兼两意,又见节次格处。自『立诚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云:「用诚敬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
问:「程子谓致知节目如何?」曰:「如此理会也未可。须存得此心,却逐节子思索,自然有个觉处,如谚所谓『冷灰里豆爆』。」
问:「二程说格物,谓当从物物上格之,穷极物理之谓也。或谓格物不当从外物上留意,特在吾一身之内,是『有物必有则』之谓,如何?」曰:「外物亦是物。格物当从伊川之说,不可易。洒埽应对中,要见得精义入神处,如何分内外!」
先生问:「公读大学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说不当意。先生曰:「看文字,须看他紧要处。且如大段落,自有个紧要处,正要人看。如作一篇诗,亦自有个紧要处。『格物』一章,前面说许多,便是药料。它自有个炮爦炙[火尃]道理,这药方可合,若不识个炮爦炙[火尃]道理,如何合得药!药方亦为无用。」次日禀云:「夜来蒙举药方为喻,退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问首叙程夫子之说,中间条陈始末,反复甚备,末后又举延平之教。千言万语,只是欲学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穷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穷究,则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谓道理者,即程夫子与先生已说了。试问如何是穷究?先生或问中间一段『求之文字,索之讲论,考之事为,察之念虑』等事,皆是也。既是如此穷究,则仁之爱,义之宜,礼之理,智之通,皆在此矣。推而及于身之所用,则听聪,视明,貌恭,言从。又至于身之所接,则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显,又至草木鸟兽,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先生所谓『众理之精粗无不到』者,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吾心之光明照察无不周』者,全体大用无不明,随所诣而无不尽之谓。书之所谓睿,董子之所谓明,伊川之所谓说虎者之真知,皆是。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
蜚卿问:「诚敬寡欲以立其本,如何?」曰:「但将不诚处看,便见得诚;将不敬处看,便见得敬;将多欲来看,便见得寡欲。」
然则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闻一段
问:「天道流行,发育万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是此性随所生处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极。」问:「此生之道,其实也是仁义礼智信?」曰:「只是一个道理,界破看,以一岁言之,有春夏秋冬;以干言之,有元亨利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昼暮夜。」
问:「或问中谓『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如何?」曰:「『貌曰恭,言曰从』,视明,听聪。」又问:「『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如何?」曰:「事君忠,事亲孝。」
问由中而外,自近而远。曰:「某之意,只是说欲致其知者,须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这个道理是如何。又推之于身,又推之于物,只管一层展开一层,又见得许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这便是一身之则所当然者。曲礼三百,威仪三千,皆是人所合当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圣人安排这物事约束人。如洪范亦曰『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以至于『睿作圣』。夫子亦谓『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
问「上帝降衷」。曰「衷,只是中也。」又曰:「是恰好处。如折衷,是折两者之半而取中之义。」
陶安国问:「『降衷』之『衷』与『受中』之『中』,二字义如何?」曰:「左氏云:『始终而衷举之。』又曰:『衷甲以见。』看此『衷』字义,本是『衷甲以见』之义,为其在里而当中也。然『中』字大概因过不及而立名,如『六艺折衷于夫子』,盖是折两头而取其中之义。后人以衷为善,却说得未亲切。」
德元问:「诗所谓秉彝,书所谓降衷一段,其名虽异,要之皆是一理。」曰:「诚是一理,岂可无分别!且如何谓之降衷?」曰:「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衷』字,看来只是个无过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与你。与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刘子所谓民受天地之中相似;与诗所谓秉彝,张子所谓万物之一原又不同。须各晓其名字训义之所以异,方见其所谓同。一云:「若说降衷便是秉彝,则不可。若说便是万物一原,则又不可。万物一原,自说万物皆出此也。若统论道理,固是一般,圣贤何故说许多名字?」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去声。者,以中为准则而取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则』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个当然之则,故民执之以为常道,所以无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则,盖君有君之则,臣有臣之则:『为人君,止于仁』,君之则也;『为人臣,止于敬』,臣之则也。如耳有耳之则,目有目之则:『视远惟明』,目之则也;『听德惟聪』,耳之则也。『从作乂』,言之则也;『恭作肃』,貌之则也。四肢百骸,万物万事,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子细推之,皆可见。」又曰:「凡看道理,须是细心看他名义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固同此一理,然圣贤所说有许多般样,须是一一通晓分别得出,始得。若只儱侗说了,尽不见他里面好处。如一炉火,四人四面同向此火,火固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若说我只认晓得这是一堆火便了,这便不得,他里面玲珑好处无由见。如『降衷于下民』,这紧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则谓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则谓之性。如云『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则谓之性,而不谓之衷。所以不同,缘各据他来处与所受处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据天之所与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据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绥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发用处,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说得道理如此缜密,处处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某尝说,古之诸圣人亦是为此一大事也。前圣后圣,心心一符,如印记相合,无纤毫不似处。」刘用之曰:「『衷』字是兼心说,如云衷诚,丹衷是也,言天与我以是心也。」曰:「恁地说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处,又有析而言处。须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尽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养其性』。圣贤说话自有分别,何尝如此儱侗不分晓!固有儱侗一统说时,然名义各自不同。心、性之别,如以碗盛水,水须碗乃能盛,然谓碗便是水,则不可。后来横渠说得极精,云:『心统性、情者也。』如『降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施于天之所降而言,不可施于人之所受而言也。」池录作二段。
天降衷者,衷降此。以降言,为命;以受言,为性。
陈问:「刘子所谓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谓太极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处。上帝降衷,亦是恰好处。极不是中,极之为物,只是在中。如这烛台,中央簪处便是极。从这里比到那里,也恰好,不曾加些;从那里比到这里,也恰好,不曾减些。」
问:「天地之中与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盖指大本之中也。此处中庸说得甚分明,他日自考之。」
问:「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发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时中。」曰:「然则天地之中是指道体,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
问:「以其理之一,故于物无不能知;以其禀之异,故于理或不能知。」曰:「气禀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这心要求,便即在这里。缘本来个仁义礼智,人人同有,只被气禀物欲遮了。然这个理未尝亡,才求便得。」又曰:「这个便是难说。唤做难,又不得;唤做易,又不得。唤做易时,如何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后,如何更无一个人与相似?唤做难,又才知觉,这个理又便在这里。这个便须是要子细讲究,须端的知得,做将去自容易。若不知得,虽然恁地把捉在这里,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见了;明朝捉住,后日又不见了。若知得到,许多蔽翳都没了。如气禀物欲一齐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稳稳做到圣人地位。」
问「或问中云,知有未至,是气禀、私欲所累」。曰:「是被这两个阻障了,所以知识不明,见得道理不分晓。圣人所以将格物、致知教学者,只是要教你理会得这个道理,便不错。一事上皆有一个理。当处事时,便思量体认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见理而不见事了。如读圣人言语,读时研穷子细,认得这言语中有一个道理在里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见理而不见圣人言语。不然,只是冥行,都颠倒错乱了。且如汉高帝做事,亦有合理处,如宽仁大度,约法三章,岂不是合理处甚多。有功诸将,嫚骂待他,都无礼数,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爱恶易太子。如此全错,更无些子道理,前后恰似两人,此只是不曾真个见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资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处多,亦无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圣人教学者理会道理,要他真个见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时,把捉教心定,子细体认,逐旋捱将去,不要放积累功夫,日久自然见这道理分晓,便处事不错,此与偶合者天渊不同。」问去私欲、气禀之累。曰:「只得逐旋战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无此理,亦不济得事。须是当事时子细思量,认得道理分明,自然胜得他。次第这边分明了,那边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只穷理为上。」又问:「客气暴怒,害事为多,不知是物欲耶,气禀耶?」曰:「气禀物欲亦自相连着。且如人禀得性急,于事上所欲必急,举此一端,可以类推。」又曰:「气禀、物欲生来便有,要无不得,只逐旋自去理会消磨。大要只是观得理分明,便胜得他。」
问:「『或考之事为之着,或察之念虑之微。』看来关于事为者,不外乎念虑;而入于念虑者,往往皆是事为。此分为二项,意如何?」曰:「固是都相关,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虑方动底。念虑方动,便须辨别那个是正,那个是不正。这只就始末上大约如此说。」问:「只就着与微上看?」曰:「有个显,有个微。」问:「所藉以为从事之实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为精微要妙不可测度者,则在乎真积力久,默识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谓『下学而上达』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饮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处,便是这道理。只就近处行到熟处,见得自有人说,只且据眼前这近处行,便是了,这便成苟简卑下。又有人说,掉了这个,上面自有一个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谩人。圣人便只说『下学上达』,即这个便是道理,别更那有道理。只是这个熟处,自见精微。」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处做得熟,便是尧舜。圣人与庸凡之分,只是个熟与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古之善书者亦造神妙。」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所谓『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寓录云:「春生秋杀,阳开阴闭,趱来趱去,自住不得。」
或问:「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当为者,自不容已。孟子最发明此处。如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处。」
今人未尝看见「当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较量一个好恶尔。如真见得这底是我合当为,则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为臣而必忠,非是谩说如此,盖为臣不可以不忠;为子而必孝,亦非是谩说如此,盖为子不可以不孝也。
问:「或问,物有当然之则,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
或问:「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问:「每常如何看?」广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其事『所当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个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学者但止见一边。如去见人,只见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识得那人。且如为忠,为孝,为仁,为义,但只据眼前理会得个皮肤便休,都不曾理会得那彻心彻髓处。以至于天地间造化,固是阳长则生,阴消则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万事,一事各有一理,须是一一理会教彻。不成只说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万物万事,吾知其为万物万事而已!』明道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观他此语,须知有极至之理,非册子上所能载者。」广曰:「大至于阴阳造化,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所谓太极,则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须是自向里入深去理会。此个道理,才理会到深处,又易得似禅。须是理会到深处,又却不与禅相似,方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门高弟游氏,则分明是投番了。虽上蔡龟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终看他未破;时时去他那下探头探脑,心下也须疑它那下有个好处在。大凡为学,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里来。譬如吃果子一般:先去其皮壳,然后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间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里头别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壳,固不可;若只去其皮壳了,不管里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则无缘到得极至处。大学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谓于事物之理各极其至,穷到尽头。若是里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极其至也。如今人于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会得,而中间核子未破,则所理会得者亦未必皆是,终有未极其至处。」因举五峰之言,曰:「『身亲格之以精其知』,虽于『致』字得向里之意,然却恐遗了外面许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说。须是内外本末,隐显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学。」
问:「『格物』章或问中如何说表里精粗?」曰:「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知其粗不晓其精,皆不可谓之格。故云:『表里精粗,无所不尽。』」
问以类而推之说。曰:「是从已理会得处推将去。如此,便不隔越。若远去寻讨,则不切于己。
问:「或问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则无所不该,而无一物不在,然其用实不外乎人心。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故如此说。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
「或问云:『万物生于天地之间,不能一日而相无,而亦不可相无也。』如何?」曰:「万物生于天地,人如何少得它,亦如何使它无得?意只是如此。」旧夫。
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
或问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说曰:「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而后能知至道。」温公。「必穷物之理同出于一为格物。」吕与叔。『穷理只是寻个是处。』上蔡。「天下之物不可胜穷,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龟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转归已。」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厌不弃,而身亲格之。」五峰。
吕与叔谓:「凡物皆出于一,又格个甚么?」固是出于一,只缘散了,千岐万径。今日穷理,所以要收拾归于一。
吕与叔说许多一了,理自无可得穷,说甚格物!
「穷理是寻个是处,然必以恕为本。」但恕乃求仁之试看穷理如何着得「恕」字?穷理盖是合下工夫,恕则在穷理之后。胡文定载显道语云:「恕则穷理之要。」某理会,安顿此语不得。
上蔡说:「穷理只寻个是处,以恕为本。」穷理自是我不晓这道理,所以要穷,如何说得「恕」字?他当初说「恕」字,大概只是说要推我之心以穷理,便碍理了。龟山说「反身而诚」,却大段好。须是反身,乃见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须见得孝弟,我元有在这里。若能反身,争多少事。他又却说:「万物皆备于我,不须外面求。」此却错了。「身亲格之」,说得「亲」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倩人格!赐。
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说话不曾闻得,或是其心不以为然,故于此说有所不领会耳。谢子寻个是处之说甚好,与吕与叔「必穷万物之理同出于一为格物,知万物同出乎一理为知至」,其所见大段不同。但寻个是处者,须是于其一二分是处,直穷到十分是处,方可。
张元德问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说也。大抵和靖为人淳,故他不听得而出于众人之录者,皆以为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论春秋之传为案,经为断,它亦以为伊川无此言。且以此两句即『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乃杨遵道所录,不应龟山不知。
龟山说:「『只『反身而诚』,便天地万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转归己。见云雷,知经纶;见山下出泉,知果行之类。」惟伊川言「不可只穷一理,亦不能遍穷天下万物之理。」某谓,须有先后缓急,久之亦要穷尽。如正蒙,是尽穷万物之理。
胡文定宛转归己之说,这是隔陌多少!记得一僧徒作一文,有此一语。
问:「观物察己,其说如何?」曰:「其意谓『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势以厚德』。如此,只是一死法。」
问:「物物致察与物物而格何别?」曰:「文定所谓物物致察,只求之于外。如所谓『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势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顺也。」道夫曰:「所谓宛转归己,此等言语似失之巧。」曰:「若宛转之说,则是理本非己有,乃强委曲牵合,使入来尔。许多说,只有上蔡所谓『穷理只是寻个是处』为得之。」道夫曰:「龟山『反身而诚』之说,只是摸空说了。」曰:「都无一个着实处。」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则圣贤都易做了!」又问:「他既如此说,其下工夫时亦须有个窒碍。」曰:「也无做处。如龟山于天下事极明得,如言治道与官府政事,至纤至细处,亦晓得。到这里却恁说,次第他把来做两截看了!」
知言要「身亲格之」。天下万事,如何尽得!龟山「『反身而诚』,则万物在我矣」。太快。伊川云:「非是一理上穷得,亦非是尽要穷。穷之久,当有觉处。」此乃是。
格物以身,伊川有此一说。然大都说非一。五峰既出于一偏而守之,亦必有一切之效,然不曾熟看伊川之意也。
五峰说「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者,这段语本说得极精。然却有病者,只说得向里来,不曾说得外面,所以语意颇伤急迫。盖致知本是广大,须用说得表里内外周遍兼该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语极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气象。他便要就这里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须是宽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贯。他言语只说得里面一边极精,遗了外面一边,所以其规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久自然贯通。」此言该内外,宽缓不迫,有涵泳从容之意,所谓「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载」也。
黄问「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得事。虽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无主,悠悠终日,亦只是虚言。立志必须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则常存于事物之中,令此敬与事物皆不相违。言也须敬,动也须敬,坐也须敬,顷刻去他不得。」
问:「『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须当立志,不可谓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又问「敬行乎事物之内」。曰:「这个便是细密处,事事要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这事物之上。看是甚么,都不能夺得他,又不恁地细细碎碎,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诸公多说甚大志,开口便要说圣说贤,说天说地,傲睨万物,目视霄汉,更不肯下人。」问:「如此,则『居敬以持其志』都无了。」曰:「岂复有此!据他才说甚敬,便坏了那个。」又曰:「五峰说得这数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时工夫,却是格物已前事。而今却须恁地。」
伊川只云:「渐渐格去,积累多自有贯通处。」说得常宽。五峰之说虽多,然似乎责效太速,所以传言其急迫。
问:「先生旧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体;新改本却削去,只说理,何也?」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检束此心,使无纷扰之病,即此理存也。苟惟不然,岂得为理哉!」问:「先生说格物,引五峰复斋记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云云,以为不免有急迫意思,何也?」曰:「五峰只说立志居敬,至于格物,却不说。其言语自是深险,而无显然明白气象,非急迫而何!」问:「思量义理,易得有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是欢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狭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立着心,不牵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义理,但见有好意思了。」问:「所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当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问:「致知自粗而推至于精,自近而推至于远。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间甚事?」曰:「自『无穿窬之心』,推之至于『以不言餂』之类;自『无欲害人之心』,推之举天下皆在所爱。至如一饭以奉亲,至于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
先生问:「大学看得如何?」曰:「大纲只是明明德,而着力在格物上。」曰:「着力处大段在这里,更熟看,要见血脉相贯穿。程子格物几处,更子细玩味,说更不可易。某当初亦未晓得。如吕,如谢,如尹杨诸公说,都见好。后来都段段录出,排在那里,句句将来比对,逐字称停过,方见得程子说扑不破。诸公说,挨着便成粉碎了!」问:「胡氏说,何谓太迫?」曰:「说得来局蹙,不恁地宽舒,如将绳索絣在这里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说,便宽舒。他说『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个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处,方是可精,此是说格物以前底事。后面所说,又是格物以后底事。中间正好用工曲折处,都不曾说,便是局蹙了。」
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己,亦恐见有错处,不可执一。伊川说得甚详:或读书,或处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诸己,或即人事。复曰:「于人事上推测,自有至当处。」如杨谢游尹诸公,非不见伊川,毕竟说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说传闻不如亲见。看得如此时,又却传闻未必不如亲见。盖当时一问一对,只说得一件话。而今却斗合平日对问讲论作一处,所以分明好看。浩。
这个道理,自孔孟既没,便无人理会得。只有韩文公曾说来,又只说到正心、诚意,而遗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广其说,工夫精密,无复遗憾。然程子既没,诸门人说得便差,都说从别处去,与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晓得程子之说耳。只有五峰说得精,其病犹如此。亦缘当时诸公所闻于程子者语意不全,或只闻一时之语,或只闻得一边,所以其说多差。后来却是集诸家语录,凑起众说,此段工夫方始浑全。则当时门人亲炙者未为全幸,生于先生之后者未为不幸。盖得见诸家记录全书,得以详考,所以其法毕备。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说得稍好。」
诸公致知、格物之说,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门款。于此既差,则他可知矣。
问:「延平谓:『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极。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别穷一事,久之自当有洒然处。』与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语不同,如何?」曰:「这话不如伊川说『今日明日』恁地急。卓录但云:「伊川说得较快。」这说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会教烂熟离析,不待擘开,自然分解。久之自当有洒然处,自是见得快活。某常说道,天下事无他,只是个熟与不熟。若只一时恁地约摸得,都不与自家相干,久后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间被人取将去,又济自家甚事!」卓同。
李尧卿问:「延平言穷理工夫,先生以为不若伊川规模之大,条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穷此一事,必待其融释脱落,然后别穷一事;设若此事未穷,遂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穷此事未得且别穷』之言为大否?」曰:「程子之言诚善。穷一事未透,又便别穷一事,亦不得。彼谓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执此说,容易改换却,致工夫不专一也。」
廷老问:「李先生以为为学之初,凡遇一事,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此说如何?」曰:「为学之初,只得如此。且如杨之为我,墨氏之兼爱,颜子居陋巷,禹稷之三过其门而不入。禹稷则似乎墨氏之兼爱;颜子当天下如此坏乱时节,却自箪瓢陋巷,则似乎杨氏之为我。然也须知道圣贤也有处与他相似,其实却不如此,中间有多少商量。举此一端,即便可见。」
传六章
因说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尽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时,大故郎当。若论自欺细处:且如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当为,也勉强去做,只是心里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为不善,心里也知得不当为而不为,虽是不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恶恶不『如恶恶臭』。便做九分九厘九毫要为善,只那一毫不要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实矣。或问中说得极分晓。」
问:「或问『诚意』章末,旧引程子自慊之说,今何除之?」曰:「此言说得亦」
先之问:「『诚意』章或问云:『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其原盖出于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则其气自直,便自日长,以至于充塞天地。虽是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不怕!」
传七章
陈问:「或问云:『此心之体,寂然不动,如镜之空,如衡之平,何不得其正之有!』此是言其体之正。又:『心之应物,皆出于至公,而无不正矣。』此又是言其用之正。所谓心正者,是兼体、用言之否?」曰:「不可。只道体正,应物未必便正。此心之体,如衡之平。所谓正,又在那下。衡平在这里,随物而应,无不正。」又云:「『如衡之平』下,少几个字:『感物而发无不正。』」
问:「正心必先诚意。而或问有云:『必先持志、守气以正其心。』何也?」曰:「此只是就心上说。思虑不放肆,便是持志;动作不放肆,便是守守气是『无暴其气』,只是不放肆。」
锺唐杰问:「或问云:『意既诚矣,而心犹有动焉,然后可以责其不正而复乎正。』意之既诚,何为心犹有动?」曰:「意虽已诚,而此心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动。到这里,犹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工夫。且意未诚时,譬犹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诚而心犹动,譬犹人之犯公罪也,亦甚有间矣。」
「或问『意既诚矣,而心犹有动焉,然后可以责其不正而复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诚时,只是一个虚伪无实之人,更问甚心之正与不正!唯是意已诚实,然后方可见得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有偏重处,即便随而正之也。」
问「意既诚矣」一段。曰:「不诚是虚伪无实之人,更理会甚正!正如水浑,分甚清浊。不虚伪无实,是个好人了,这里方择得正不正做事。如水清了,只是微动。故忿懥四者,已是好人底事。事至不免为气动,则不免差了。」因举左氏传云:「『正曲为直,正直为正。』曲是体段不直,既为整直,只消安排教端正,故云正直。」士毅。过录云:「先生因子洪问意诚矣,而心犹有动之意,而曰:『如「正直为正,正曲为直」两句,「正曲为直」,如出成界方,已直矣;「正直为正」,则如安顿界方,得是当处。』」
传九章
问:「赤子之心是已发。大学或问云『人之初生,固纯一而未发』,何也?」曰:「赤子之心虽是已发,然也有未发时。如饥便啼,渴便叫,恁地而已,不似大人恁地劳攘。赤子之心亦涵两头意。程子向来只指一边言之。」
问:「仁让言家,贪戾言人,或问以为『善必积而后成,恶虽小而可惧』,发明此意,深足以警人当为善而去恶矣。然所引书云:『德罔小,不德罔大。』则疑下一句正合本文,而上一句不或反乎?」曰:「『尔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小也,则庶乎『万邦惟庆』。正与大学相合。」
或问:「先吏部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曰:「这是说寻常人,若自家有诸己,又何必求诸人;无诸己,又何必非诸人。如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攻其恶,毋攻人之恶』。至于大学之说,是有天下国家者,势不可以不责他。然又须自家有诸己,然后可以求人之善;无诸己,然后可以非人之恶。」
范公「恕己之心恕人」这一句自好。只是圣人说恕,不曾如是倒说了。不若横渠说「以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则是见他人不善,我亦当无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计度之心,此乃恕也。于己,不当下「恕」字。
范公「以恕己之心恕人」,此句未善。若曰「以爱己之心爱人」,方无病。盖恕是个推出去底,今收入来做恕己,便成忽略了。
蜚卿问:「大学或问,近世名卿谓,『以恕己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何?」曰:「这便是自家本领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领上正了,却从此推出去。如『己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处,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己欲达』,也不是邪枉得达,到得达人处,便也不要由邪枉而达。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当了,阿附权势,讨得些官职富贵去做了,便见别人阿附讨得富贵底,便欲以所以恕己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说出去,不可说入来;只可以接物,不可以处己。盖自家身上元着不得个『恕』字,只『恕己』两字便不是了。」问:「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说处,也未见他邪正之所在。若说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这却着不得。若说道偶忙不及写书,切望情恕,这却无害,盖自家有忙底时」
问:「大学或问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说为不然矣,而复录其语于小学者,何也?」曰:「小学所取宽。若欲修润其语,当曰『以爱己之心爱人』,可也。」
传十章
问:「或问以所占之地言之,则随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后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处亦可见:如『并坐不横肱』,恐妨碍左边人,又妨碍右边人。如此,则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于右,以右之心交于左。如『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前人之开,所以待后之来,自家亦当依他恁地开;前人之阖,恐后人有妨所议,自家亦当依他恁地阖,此是不以后来而变乎前之意。如后面更有人来,则吾不当尽阖了门,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后之意。如此,则前后处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于后,以后之心从于前。」问:「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亲,便也要使人皆得事亲;我敬长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长慈幼。此章上面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见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尽其心。若我之事其亲,备四海九州岛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冻饿,藜藿糟糠不给;我之敬长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离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后及中央做七个人看,便自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