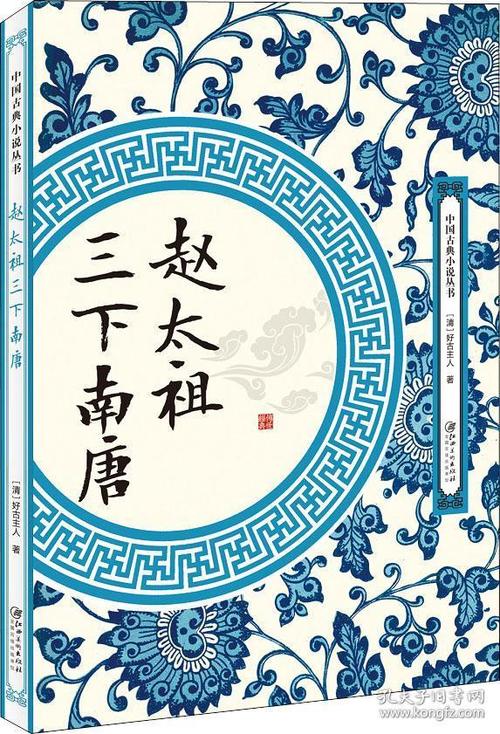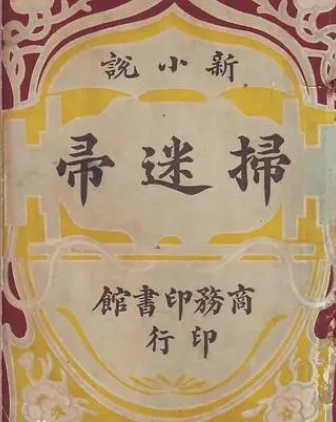月下红绳系一丝,牵成连理玉交枝。
怪他祗绾姻缘事,不为人间绾别离。
匹马如龙走浙江,任教折翼要成双。
关山看得如门阈,似此情魔未易降。
上回书中,说到秦白凤奉了叔父绳之之命,连夜到镇江避涡去了。他从八里铺起程,要走竹西亭,过瓜州镇,渡过长江,才到得镇江。一路上还有些耽搁,说书的且把他按下,等他到了镇江再说他不迟。
如今先说寇四爷,这天暴跳如雷,一定要拿刀去寻杀秦白凤,被寇四娘再三按住,四爷迄自怒骂不了。阿男起先听得,也有点心慌,躲着不敢出来,后来听得父亲怒骂不了,自己仗着父亲钟爱,便按着羞耻,老着脸皮,捱了出来。走到父亲跟前,意思要想伸诉两句,谁知见了父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掩着面啼哭。四娘见阿男啼哭,不觉也抽抽咽咽的哭起来。寇四爷见此情形,也就不骂了,狠狠的叹了一口气,在竹榻上一躺。
四娘哭够多时,方才止住了抽咽,叫一声:“我儿,你……”只说出一个“你”字,便又哭起来。阿男更是哭个不住。寇四爷忽然冷笑一声道:“你们干得好事,这是哭得了结的?”阿男听说,便哭哭啼啼的走到四爷跟前,双膝跪下。四爷忽的一下坐起来道:“这算是了却你的事?”阿男转身对四娘哭道:“母亲,请你替孩儿做个主罢。”说着,便膝行而前。四娘迎上一步,双手把他搀起,搂在怀里,不知不觉的便大哭起来。寇四爷跳一跳脚道:“你们干下这些好事,还要在这里哭。我看你们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可能哭得了结?”说罢,站起来往外就走。吓得寇四娘撇下了阿男,上前一把拖住四爷道:“官人,你往那里去?”四爷道:“你们怄的我还不够?还要我在这里听你们哭热闹呢。”四娘道:“不是这等说,人命关大的事,官人,你不要出去闯祸啊!”四爷道:“许你们丢丑,就不许我闯祸?”四娘听说,越发扯住不放。四爷没法,依旧坐下。三个人六目相看,默默无言。阿男只是低头弄带;四娘一手支颐,靠在梳妆台畔;四爷手捻着两根新留的髭须,在那里默默的出神。
歇了半天,四娘叹一口气道:“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上去,不如将错就错,成就了这件事罢。”四爷听了,并不言语。又歇了半晌,四娘再说一遍,四爷恨恨的道:“随你们去搅罢,我不管这件事。”说罢叹口气,扬长自去。阿男倒在母亲床上二睡了半天,四娘仍是默默无言。这一天的晚饭,母女两个都个曾好好的吃。
阿男一早便到自己房里去睡了。心中忐忐忑忑,翻来覆去,如何睡得着?到了二更时分,依旧换了结束,开了房门,到白凤那里,意思欲商量一个善后办法。到了那里,只见窗里面漆黑,暗想今天为何睡得这般早?轻轻弹了两下,不见答应,不觉大生疑惑。要想撬窗进去,又怕到别有事故。转身到耳房外面一听,只听得里面鼾声大作,心中迄自疑惑不定。又蹩到正房门前,无意中用手轻轻一推,谁知那门便开了,不觉心中一惊。一步跨了进去,走到房门外再轻轻一推,却也是虚掩的,便想跨步人内。忽然转念一想:我和他往来了两个月,向来他是留灯等我的,何以今天忽然如此?莫非这边也闹穿了,把他调开,另外换个人在这里?我且不可造次。想定了,在身边摸出闷香火种,点了一枝,轻轻吹了一口气,把香烟送进去。歇了半响,才挨身进去,把火种吹起了火苗,举向床上一照,不觉吃了一惊,原来帐褥俱无,只剩一张空榻。呆了半晌,回身向书桌上一照,只见笔墨等东西都没了,案头摆着几本书,是白凤天天看的,也不见了。暗想:这件事莫非两家同时发作?这边把他挪到那里去了?为甚昨天晚上还不曾提起半句呢?呆呆的站了一会,不觉扑簌簌的落下泪来。想起昨天晚上,还是有说有笑,相亲相爱的何等有趣,今天晚上变了这个情形。况且我白天里受了多少气,满意晚上到这里来伸诉伸诉,谁知跑一个空。还不知他是到那里去的?字条儿也不给我留一个。想罢了,又拿火种在桌上地下照了一遍,意思要想白凤有个字条儿留下,谁知影儿也没有一点。只得回身出去,轻轻的依旧反手掩上了两重门,飞身上屋,蹿到绳之住房院子里落下。向房窗上一望,也是漆黑的。走近去侧耳一听,也是声息全无。闷闷的站了一会,只得仍旧回去。
可怜他这一夜真个是彻夜无眠:心中想到事情弄穿了,不知如何结果?又是忧愁。凭空的一个意中情人不见了,又是疑虑。满心的委屈没有伸诉的去处,又是苦恼。心里头有了这三件事,来来往往,不知不觉的便又哭起来。眼睁睁看到天色微明,便坐了起来,在那里出神。也不知坐到甚么时候,四娘过来了,看见他一个人坐着动也不动,那眼泪和断线珍珠般落个不住,却没有哭声,也并不抽咽。四娘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我儿,你这是傻甚么。”阿男猛的一下惊醒了,回过头来,见是母亲,便搭讪着道:“不做甚么?”一面拉过检妆,对镜梳洗。四娘坐在旁边看他,一面说道:“孩儿,你这件事,我也不来追究你是怎样弄成功的。昨天晚上我对你父亲说了个舌敝唇焦,劝他就把你说给秦家,一则是将错就错,二来是家丑不出外传,好容易说得你父亲答应了。你今天好好的出去,不要还是哭哭啼啼的,反要激得他动怒。你快梳洗好了,我们一同吃早饭;吃了早饭,我便去央李姆姆做媒。孩儿,你看可好?”阿男只管低头不答,半晌才道:“孩儿吃不下早饭。”四娘道:“孩儿,你不要会错了意。这件事原是你的不是,我只为止有你一个,从小儿是千依百顺的,所以不来责怪你,反来迁就你,并且代你向父亲跟前讨了人情,做娘的自问不过如此了。你再是使脾气,啼哭不吃饭,拿自己的身子去怄气,那我可不管了。昨天晚上已经没有好好的吃饭了,今天早饭又说不吃,你究竞饿得了几顿?”阿男也不言语,默默的梳洗过了,四娘便拉了他出去吃早饭。阿男勉强吃了两口,便自回房,尽力去想他的心事。
四娘便到李姆姆家去,托他做媒。李姆姆道:“四娘好眼力,秦家二官和你们姑娘,真是天生成地配就的一对好夫妻,我便去和你们说合。”四娘道:“大凡亲事,总是男家求女家的,姆姆过去,总求说得好看些。”姆姆道:“四娘放心,我自然说得两面好看。”四娘大喜,千拜托万拜托的去了。
李姆姆送过四娘,便换过一件青布外衫,蹩到秦家去。绳之娘子迎着笑道:“姆姆,今天是甚么风把你吹来了?”李姆姆道:“一向少来和相公、娘于请安。”恰好绳之也在家里,便接口道:“好说、好说,姆姆这么大年纪了,如何敢当?”李姆姆道:“像我叫做老不死,留几根骨头累人。”绳之娘于道:“姆姆说那里话,此刻孙子也长大了,应该要亨福了,不知几时娶孙媳妇,请我们吃喜酒?”李姆姆道:“嗳唷唷,茶饭也不曾弄得周全,还谈这个呢。到是你们二官长大了,大相公又没有第二个。要早点打算和他成家?”。不知可曾定下人家?”绳之道:“早呢,今年才十七岁。”李姆姆道:“不知一向可曾提过亲事?”绳之娘子说道:“提……”只说出这一个“提”字,绳之便抢着道:“没有呢。”李姆姆道:“不知可要提亲?如果要提,我来做个媒人,赚两个媒人钱用用。”绳之道:“不知是甚等人家?想来姆姆的眼力定然不错,就怕我这个顽侄没有福气罢了。”李姆姆道:“我前天到寇四娘家去,看见他家那姑娘,生得十分齐整,和你们二官正是一对,我问起来,知道他还没有人家呢!”绳之道:“好是好极了,只是我这个顽侄,找是不理他的了。前两天他犯了家法,我把他赶了出去,不许他回来。此刻不知他到那里去了?”李姆姆道:“暧呀呀,这是那里说起!他小孩子家犯的甚么大事,怎么便赶了出去,叫他到那里去投奔?”绳之恨恨的说道:“他是我的侄儿子,我念在先兄一脉,才赴了他,放他一条生路;如果是我自己生的儿子,我早就是一刀了。”李姆姆道:“暖唷唷!阿弥陀佛!说说也罪过。他到底甚么事激恼了相公?”绳之道:“无非是些无耻下流的事,还说他做甚么!姆姆难得过来,请在这里吃了中饭去。”说罢,自出去了。
原来绳之看见李姆姆进来,不多几句说话,便提到白凤亲事上去,便有点疑心是寇家打发来的,后来听他提到寇家,所以就顺口撒个大谎,免得他再来乱琐。秦、寇两家,历代乡邻,一家有个男孩子,一家有个女孩子,都生得十分秀气,一向岂有没个联婚的意思?便是绳之娘子,也曾向丈夫提及。绳之总嫌他是个走江湖的女子,一则怕名声不好听,二则怕他的脾气举动,怕有不妥之处,所以一向搁起不提。今番又干出这件事来,闹得八里铺无人不知,如果将错就错成了亲,这个先奸后娶的名气,是终身赖不掉的。绳之虽是乡下人家,却还读过两句书,守着点廉耻,不像那个讲究自由结婚的人,只管实行了交际,然后举行那个甚么文明之礼,不以为奇的。
闲话少提。且说绳之娘子也是个极聪明伶俐的人,听得丈夫这番话,早就会意了。绳之出去之后,李姆姆不住的念佛,又问:“到底为甚事赶出去的?”绳之娘于道:“我也不知道为的甚么事?那天无端的叫了进来,骂了一顿,便撵出去了。我问过他两三回,他也不说。”李姆姆道:“可怜!可怜!他一个小孩子家,身边又不见得有钱,叫他投奔到那里去呢?”绳之娘子道:“想来他也没有投奔之处。只有邵伯镇有个远房姑夫在那边,常常都有信来问起他,或者他到姑夫那边去,也未可知。”诸公,这一个谎又是绳之娘子玲珑的去处。他因为昨天听见寇四爷要杀白凤,白凤昨天晚上走了,今天就有个李姆姆来做媒,这里头不免有点可疑,恐怕是来打听白凤往那里去了,要去追杀,所以白凤明明往南走镇江,他偏说是往北走邵伯镇,以免他追着的意思。这也表过不提。
李姆姆看见做媒不成,虽然绳之娘子留他吃饭,也觉得没甚意思,搭讪着谈了几句,便辞了出来,径到寇四娘家去回覆,把绳之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四踉听了,也觉得顿然一呆。却不料阿男掩在屏风后头,听得白凤被他叔父撵走了,由不得如万箭攒心一般,三步二步,从后面绕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掩面痛哭。恐怕被人听见,又不敢放声。偏偏那李姆姆又坐在堂屋里唠叨不断,寇四娘偏又留他吃中饭,叫人到房里招呼阿男。阿男推说身于不快,没有出去应酬。李姆姆吃过饭,又唠叨了半天才走。四娘送过李姆姆,便来看阿男,见他哭得泪人儿一般,两只眼睛肿得有桃核般大。诸公!若是差不多的人家,女儿干下这等事,他父母知道了,正不知怎样惩治呢。不比得阿男,他父母半生,只有他一个,从小儿当掌上明珠般看大的,一旦他做下这等事,他母亲四娘虽有点怪他,却又舍不得拿他怎样,反要设法成全他的事情。所以四娘到他房里,看见他哭得那副情形,便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叹一口气道:“暖!这是那一辈子造下来的孽!”坐了一会,才低低的对阿男说道:“儿呀。这不是哭的事情。找想秦家对李姆姆说的话,未必是真的,他家两房只有这一子,任是犯了弥天大罪,何至于把他撵出大门,只怕是你爹爹昨天疯了般要拿刀杀人,不知是谁透了风声给他们,他们恐怕认真弄出事情,把他藏到别处,是说不定的。等我消停两大,打听真实了,再托人去说,不怕他不答应。他认真不答应时,我也会翻转脸面,要他赔还我的黄花闺女,看他担得住担不住!”四娘一番半似有理半似无理的话,说得阿男住了啼哭。
四娘又安慰了一会,方才出来,把李姆姆做媒回覆的话,告诉了四爷。四爷心中卡疑半信。后来慢慢采访,知道这件事是在秦家干出来的,是被秦家佃工窥见。传扬出来的。因此知道这件事是自己女儿去就人家的。那恨白凤的心也就淡了。自从李姆姆去做过媒之后,又传出来,说绳之把侄儿撵走了,因此外间谣言,又说是秦绳之硬气,侄儿犯了事,便把他赶了出去,不像寇家仍旧把没廉耻的女儿养在家里。四爷听了这种说话,如何忍耐得住?回到家去,便没事寻事的拍桌于打板凳乱骂,夫妻两个也相骂过几回。阿男明知是为了自己的事,默不敢言。天天受这种哑气,心中又是思念白凤,不觉又恹恹的病起来。
一个人做事,真个是不能走差半步,若是走差了半步,便处处都有人指摘的了。阿男生出病来,未免又要延医吃药,外面人知道了。又纷纷议论起来,说他生的是相思病。四爷耳朵里终日不得干净,心中更觉烦恼,便不顾女儿生病不生病,即日要带了妻女,依旧去走他的江湖,意思是要离开八里铺,免听这些闲话,并且决定这一回出去,一定在外面拣个女婿,就在外面嫁了女儿。定了主意,便要即日起程。四娘再三拦挡不住,阿男也只得挣扎上路。一路向山东大路前去。他夫妻母女三人。这一去又不免冲州过府,我说书的这张嘴,却没闲工夫去跟着他涉水登山。且把他们停顿一停顿,掉转舌锋,再把秦白凤提一提。
秦白凤带了一肩行李,袖了叔父书信,连夜动身。到了瓜州,换了渡江船只,渡过镇江,一路上问讯前去。问到了仁大布店,把行李停放在店门首,亲自走到店里,将书信投递。恰好何仁舫在家里,未曾到店,由何彩章、何彩华兄弟两个招呼,将行李先搬到店里。一面打发小伙计回家,招呼何仁舫,顺便将绳之的信带去。仁舫见了绳之的信,知道白凤已到,连忙亲自到店里来。白凤上前叩见。仁舫便问绳之的好,白凤说过托庇。仁舫道:“令叔来信,意思要叫贤侄在小店这边学生意,不知府上耕种的事,怎生放得下?”白凤道:“家叔因为小侄株守在家,难图长进。先父故后,又已经废读,舍下田地不多,家叔一个人也还照应得过来,所以叫小侄到这边伺候老伯,看有甚么相当的事情,可以学习学习。”仁肪道:“小店里生意本不甚大,事情也不多,既然令叔托到,贤侄不嫌委屈,先在小店里住下,随意帮帮忙,以后再说罢。”白凤连忙谢过。
这天因为白凤初到,仁舫叫另外备了两样小莱,请他吃饭;又叫了一壶酒,仁舫自己也在店里陪着。吃酒中间,仁航和他谈些生意经络,白凤是聪明人,自然容易领略。彩章、彩华两个,虽然一向在店里经营贸易,却还没有撇下书本,便和白凤谈些学问。他三个未必就是学问渊博,配说到“讲学”两个字,但是在商务农田中人,能略讲文学的,要算他三个是工力悉敌的了。仁舫在旁听了,自觉得欢喜。况且白凤相貌又生得十分清秀,举止亦甚为娴雅,更觉可爱。当时饭罢,便叫在店里打扫开一间当街楼面。指给白凤居住。从此白凤就在仁大布号里住下。
彩华把往来书信一事,交给他去办。日间书信无多,白凤便学着算法看银色等事。仁舫察看得他十分勤谨,通信到八里铺时,便请绳之来镇江商量亲事。绳之直等到七月初旬,新稻登场之后,方才有暇来到镇江,与仁舫相见。此时亢之没了”,绳之是白凤胞叔,将来要做主婚的,亲事一层,不便当面自己说。由何仁舫另外请了媒人,两边传话。这爱亲做亲的媒人,自然不费甚么唇舌。两边传过了庚帖,议定了行聘礼物,便择日传红。绳之在客边,没甚亲友,并且住在客栈里,诸事从简。仁舫那边,不免有一班亲友前来道贺,热闹了一天。
只有秦白凤闷在心头,却说不出,想起与阿男山盟海誓,何等深情?自从这件事闹了出来,正不知他在父母跟前受尽了多少委屈,此时他在家里,又不知如何想我?今日我逼于叔父做主,定了何家亲事,将来总有相见之日,不知怎样对得住他?又想起以前幽期密约时,何等恩情,此时独居小楼,日间门前市廛热闹,还容易过去,到了夜阑人静时,便不免万虑纷集。况且这种心事不便告诉别人,自从定了亲之后,和彩章、彩华已定了郎舅名分,这等事更不能提得半个字。因此郁在心里,不得舒发,遂不觉恹恹成病,茶饭懒沾。何仁航父子那里得知他的就里,只说他病了,便替他延医调治。医生说他郁闷所致。仁舫以为他一向在乡间田里游行惯的,此时关闭在店里,所以成了郁闷。就叫彩章、彩华两个,轮着带他去逛金山、焦山、甘露寺等处,替他解闷。虽然略略好些,终久不能复元。他这一病,不知病到何时方好,说书的又不能尽着替病人写照,只好把他暂时放在床上,再掉舌锋,先说别处去了。
且说寇阿男委委屈屈的带着病,踉父母出门去了。此时暑气正盛,寇四爷恼怒之下,不顾死活,只催着赶路。先还由水路先到扬州,打算等阿男病好了起旱。谁知到得扬州,阿男的病仍无起色,便一路仍由水路径到清江浦去。阿男在船上将息了两天,略见精神。寇四爷便叫渡过黄河,到王家营去,就在王家营起旱,要取泰山一路行去。谁知走了两天,到了宿迁县,阿男又重新病倒。这天才落了店,他便浑身上下热得如火炭一般,涕唾全无,吓得寇四娘忙向店家打听,请医生来诊病。医生说是受了暑,开了一剂清凉解暑的方子,吃下去绝无效验。四娘便埋怨四爷:“都是你逼他走旱路,受了暑热。”四爷还是一肚子没好气,并不理会。亏得四娘百般调治,才把烧热退了。但是依然不茶不饭,每日子午两时手心脚心仍然是烧的。形容日见消瘦,唇青面白,只剩得两颊排红。到了夜来,便是梦魂颠倒,呓语模糊。寇四娘明知他的病情,争奈不便和四爷说得,只好暗中设词开解阿男。阿男虽是个女孩子家,却是走过江湖,见多识广,会打主意的人。暗想:我只管病在这里,终不是个了局。不如将息好了,设法寻着了他,再图终身之计。想定了主意,便天天打算寻着了白凤之后,如何偕隐,如何过活,如何温存,越想越快活,那个病就慢慢的好了。
时候也到了七月下旬,天气也渐渐凉快了。寇四爷又整理起程。阿男跨了自己家养的乌孙血汗黄缥马,一路上按辔徐行。第一站到了红花埠,第二站过了李家庄,这李家在已是山东沂州府、剡城县所属,第三站到了丰城。这一路都是平阳大路,再往前去,便是山路了。这天到了丰城,落了客店,吃过晚饭,寇四爷交代早睡,明天要起早赶路。当吃饭时,喝了两杯酒,一早便睡了。他意思仍是明日一早起来,要赶早上路。谁知睡到明日起来时,已是日高三丈了,看看四娘,仍是瞢腾大睡,连忙把他推醒。四娘坐起来,揉揉眼睛道:“呀!这是甚么时候了?”转眼一看,却不见了阿男。又道:“呀!阿男那里去了?”连忙趿鞋下地一看,房门是虚掩的。开了门,叫了店小二来,问道:“我家的姑娘那里去了?”小二笑道:“你老人家关了房门睡觉,谁知道你家姑娘?”四娘大惊,转身人房,只见四爷在那里顿足道:“罢了!罢了!”指着桌上叫四娘道:“你看这是甚么未?”四娘走近一看,却是一撮香灰;便知道阿男夜来烧了闷香,心中更是一急。忽见那店小二走来,说道:“你家姑娘可有了?”四娘道:“没有啊,你可见来?”小二道:“岂但不见你家姑娘,我方才到后槽去,你家那匹牲口也没了。”寇四爷听说,人觉一阵急怒攻心,一口鲜血直喷出来,觉得眼前一阵漆黑,便砉的一声仰跌在地。吓得四娘抱住乱喊,喊了半天,方才醒来。四娘又央人去寻了些童便来,给四爷喝下,略略定了一定。那店主人走来道:“今大早上起来,我店里大门是好好锁着的。怎么连人带马都不见了,莫非飞上天去了?”四爷不住的摇头,身于一歪,便躺在床上,从此气成一病。只可怜四娘又要侍奉丈犬汤药,又要思忆女儿,慢慢的也生起病来了。说书的先尽他两个病人在床上躺躺,却先提一提阿男往那里去了。
原来他早走好了主意。这一夜,等父母睡了,人静的时候,他却拿出一枝闷香点着了,插在桌上。拿了革囊,带了几两银子,与及些干粮带在身边。仍旧扮了男装,结束停当,拿了鞍辔,悄悄开了房门,反手掩上。摸到后槽,把那一匹乌孙血汗黄骡马牵了出来。走到大门前,见已经上了锁,便用一个啄木解锁法,把锁解下,开了大门,牵了马出去,将僵绳拴在一棵树上,把鞍辔一一装好。翻身进了店门,仍旧替他关门上锁,然后腾身上屋,跳在门外。在身边取出早先备下的四张神骏灵符,拴在四个马腿上。这也是他们白莲教相传的道术,无论甚么骡马之类,腿上拴了这个符,跑起来比平日要加四五倍快。譬如这马是日行百里的,拴了符便可以走到四五百里。阿男拴好了符,便腾身上马,加了一鞭,向来路而去。那马发开四蹄,追风逐电般一夜不曾停止。走到天明,已到了黄河边,连忙叫船渡过黄河。走了一天,黄昏时候便到了八里铺,将马匹拴在村外一间都天庙前,自己走到庙内略歇,吃了些干粮。好在这都天庙是一座废庙,庙里没有人的。他等到人静时,便走近村前,腾身上屋,窜到秦绳之家,伏在窗外,要听一个白凤的消息。
此时八月初旬,绳之已从镇江回来。阿男向里一张,只见绳之伏在桌上写信,便潜心静气的等他写完、看过、封好,在信面上写了“祈交白凤舍侄收启”。心中不觉懊悔道:“这仍然是没个着落,如何是好呢?”只见绳之把这封信套在一个大信封内,又封了口,这个信封是写现成的,写的是:“寄镇江西门大街仁大布号何仁舫先生台启。”阿男暗道:“惭愧,今番得着了也!”悄悄的翻身上屋,仍旧窜至村外,跨上黄膘马,打动了一鞭,到了瓜州镇,天还没亮。在马腿上解下了神骏符,就在江边候至天明,叫个渡船,渡过镇江去。在市上买了几件行李,到甘露寺去借一所僧房歇下。安顿了马匹,便出门问讯。到了西门大街,果然有个布店,招牌是“仁大”二字,便不住的在门前来来往往,一则留心体察房屋情形,二则察看店中人物。走了几回,果然看见秦白凤在里面。不觉喜得心痒难搔,巴不得即刻上前相见。无奈耳目众多,不便造次,只得回到寺内,眼巴巴的盼到黄昏,向和尚买了碗斋饭,胡乱吃了,宁心耐性,等到人静时,方才逾垣出去。走到了西门大街仁大布店门首,抬头一望,只见一排四五个楼窗,有两个里面漆黑,有两个还略有灯光。要待上去张一张,却恨窗前没有个立脚之地。好阿男,腾身上屋,将身背贴在房檐边上,用一个悬崖撒手法,身子向后一翻,把双脚挂在檐瓦上,身子倒挂下来。伸手摸着窗槅,轻轻挖开了明瓦片,往里一张:只见两个不相识的人,在那里各睡在一个铺上,隔床谈大。阿男一翻身。仍旧上屋,到那边一个楼窗上面,照样翻下来窥探。只见白凤在那里拿着扇于在床上赶蚊子要睡。阿男轻轻弹了两下,白凤侧耳一听,阿男又弹了两下,白凤便停了扇子,转面过来。阿男轻轻叫道:“哥哥开开窗。”白凤吃了一大惊,走到窗前,把窗扇一推,飕的一声,阿男已蹿了进来。白风见了,又惊,又喜,又害怕。正要说话时,阿男早走过来,把他双手捉住,一翻身背了起来,一脚踏到窗槛上,往下一跳,早已到地。放下白凤,携了手,一直跑到甘露寺,叫白凤在外等着,他却腾身上去,回房取了行李,带了马匹,开了大门,出来拴上神骏符,扶白风上了马,然后自己骑在马鞍后面,加上一鞭,向杭州大路而去。可怜白凤始终犹如做梦一般。正是:
甘向半途抛父母,却从夤夜走夫妻。
未知到了杭州之后,义有甚事?巳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