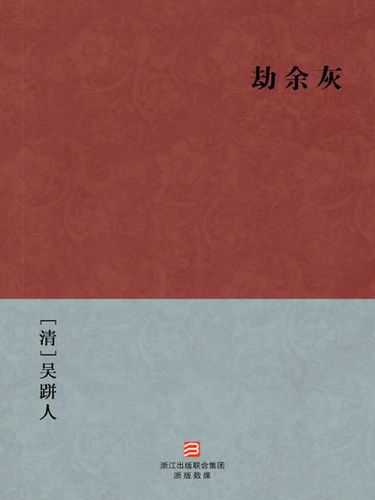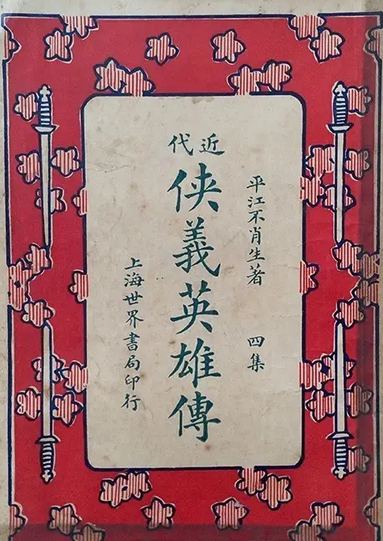且说婉贞悄地投缳自尽,倘使婉贞从此死了,岂不干净。然而婉贞果然从此死了,是历劫已尽,更无余灰了。幸得他命不该绝,方才留下劫余灰这部小说来,以供后人谈助。闲话少提。
且说婉贞上吊,轻轻用脚踢开椅子时,未免訇然有声,早惊动了隔房那妇人。原来那妇人,便是鸨妇阿三姐的媳妇。阿三姐的儿子,每日在花船上,照料各龟奴伺候客人,每至夜深,方才回家。因他得了一个耳聋之病,虽在他旁边放炮,他亦不闻,因此人家起他一个混名,叫做阿聋。娶了这房媳妇之后,人家又因他阿聋的聋字,与龙字同音,便将他的媳妇叫做阿凤,取龙凤相配的意思。起初不过叫着取笑,久而久之,便以假作真,那妇人就以阿凤为名了。且说阿凤当夜闻得訇然一声,便吃了一惊,拿了灯过来,隔门听了一回,不闻声息,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连忙回房,将阿聋推醒,取了钥匙过来开门。及至将锁取下,推了一推,那门屹然不动。便做手势,叫阿聋去撞门。阿聋此时,还是睡眼¥%的,说道:“他关门睡觉,不由他睡去,这半夜三更,又打他做甚么呢。”阿凤恨起来,取过一条板凳,用力去撞了两下,却撞不动。便将板凳交与阿聋,做手势叫他撞。阿聋莫名其妙,只得用死劲撞了二三十下,才把门闩撞断了。二人推门,闯将进去。举火一照,却不见有甚么,便连新买来的姑娘,也不见了。两人不觉吃了一惊。阿凤先拿火向床底下一照,阿聋便去察验窗户、墙壁,却不见一毫动静。两人且惊且疑,道:“总不能遁土去了。”阿凤猛抬头,看见门背后露出一幅衣襟,便失声道:“在这里了。”走近前去,把门掩上,只见婉贞高高挂着,两眼圆睁,舌头已吐了一段在外,头发披散,好不难看。便吓的嗳呀一声,缩退了两步。原来婉贞在门背后上吊,他们毁门而进,恰好把婉贞掩在门后,所以到了此时,方才看见。
此时倒是阿聋有主意,连忙端过椅子,站将起来,一手抱住婉贞,一手先把挂在门头的带子卸下,抱将下来,送到床上,叫阿凤帮着解救,自己却忙到厨下弄开水姜汤,一顿胡乱灌救。也是婉贞寿命未尽,慢慢的回过一口气来,叹了一声“嗳”,便扑簌簌泪如雨下。阿凤便指着脸,一顿大骂,道:“好没良心的贱人,我劝了你多少,你不听我劝倒也罢了,为甚又来和我拼命,要想害我。你这贱人,命犯桃花,落在这里。须知天下容你死,要你好好的把花债还清,那时方许你讨饭捱命呢。”阿聋也咬牙切齿的骂道:“贱人,要寻死,明日告诉了娘,活活的打死你,却不能容得你这般死的舒服。”乱烘烘的吵闹了一会,天色早已大明。阿聋便到外头去了,阿凤还在旁边咕哝。婉贞此时,满心悲苦,无地可诉,只剩得嘤嘤啜泣。
正在十分凄楚烦厌时,忽见阿三姐排闼而入,气冲冲的对准婉贞,劈面两个巴掌,打得耳鸣眼热,打了之后,便一把拖翻在地,自己坐在床上,指手骂道:“贱人,活得不耐烦,要寻死,为甚不早点在家寻死,却到我这里来上吊。我偏不要你死,要磨折你一生一世,看你又奈我何。哼!你想要拿死来讹诈我,吓唬我,你不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里苍梧里的门上大爷,是我的干亲家。衙门里几位师爷,都常在我船上走动。莫说死了你一个贱人,就是多死几个,也没奈我何。”又回头骂阿凤道:“不识羞的婆娘,只知道搂着汉子睡,也不知道看守看守。万一这贱人当真死了,我要在你身上赔还这一个来。”婉贞被打了两下,坐到地下,心中大怒。本要和他大闹起来,拼一个你死我活,因恐怕双拳难敌四手,再吃了眼前亏,只得暂时忍耐。听到阿三姐骂出甚么门上大爷是干亲家的话,不觉心中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来,即刻按住了怒气,忍住了悲苦,呆呆想这个主意的办法。所以以后他们说些甚么,骂些甚么,也听不见了。
阿三姐骂够多时,方才气忿忿的去了,阿凤也跟了出去。两人又在外面唧唧哝哝了一会,阿凤复走了进来,见婉贞仍旧坐在地下,便骂道:“贱人,还不起来,要撒你娘的娇呢。”婉贞此时已定了几分主意,听见他骂,并不倔强,便勉强撑持起来,一步一捱的捱到床上坐下。阿凤还唠唠叨叨的道:“有了钱,那里买不出人来,却买这么一个贱货,还要交给我看管。老虎也有磕睡的时候,叫我那里看守得来。”婉贞道:“你不要埋怨了,我也不想寻死了,你也不必看管了。”阿凤冷笑道:“你便说自在话,我一时看管不到,你又吊死了,我向你的死尸讲理来。”婉贞道:“你不必多疑。昨夜是我一时短见,有累了你。天既然不容我死,方才得你救活,我就再寻死路,也未必死得去的。所以我立定主意,一定不死的了。”阿凤道:“你不死,又怎么?”婉贞道:“我此时想起来,你昨日的话,句句都是好话,我纵千拗万拗,总是拗不过的。所以想到,不如顺从了。一则免了眼前受苦,二则也望后来有个出头之日。想到这里,自然是不愿再寻死路了。”阿凤道:“你的话,可是真的么?”婉贞道:“这是我一心情愿的,为甚么不真。”阿凤喜道:“既然如此,你好好的躺下,先把伤痕养好,待我教你些规矩,包管我婆婆欢喜。”婉贞道:“如此多承指教了。”阿凤道:“你既然到了此地,便是我婆婆的人,你对我婆婆当得叫一声妈妈,就是对我,也得叫一声嫂嫂,还有你哥哥,更不消说了。可惜他是聋的,就是叫他一万声,他也听不见。不过叫我婆婆听着欢喜罢了。你躺下罢,我去弄点伤药,来给你擦上,包你不到几天就好。”说着自出房去了,一会儿,拿了一小瓶油来,要和婉贞擦那皮鞭伤痕。婉贞连忙说道:“油擦在身上,怪腻怪脏的,我不要擦。嫂嫂不要费心,拿了去罢。”阿凤说道:“脏不要紧,好了可以洗的。这东西还可以止痛呢。”婉贞道:“我此刻也不觉痛了,多谢嫂嫂,不要擦罢,我生平第一怕这脏东西。”
看官,你道婉贞是当真嫌脏,不怕痛,不肯擦么?原来他心中此时已定了一个主意,姑且假意顺从,暂作缓兵之计,慢慢再作设施,缓得一时是一时。所以,生怕擦了药油,伤痕好的快,等伤痕好了,那鸨妇少不免要逼着出去应客。因此,只推说怕脏不怕痛罢了。
阿凤听说,果然也不来勉强,再三劝他躺下,又在床前伴着,说了一番闲话,方才出去。一会儿,又捧进一碗粥来,劝婉贞吃。婉贞此时胸中早有了主意,便乐得借来充饥。到了午饭过后,便有许多隔壁邻居的三姑六婆,走过和阿凤大说大笑,又都走到房里和婉贞搭讪。好个婉贞,识得时势,也便拿些不相干闲话,和那一班婆娘去混。过了一会,他们又在外间调开桌椅抹牌,阿凤便来拉婉贞去观局。婉贞也乐得见见天光,舒舒闷气,于是勉强支持着,到外面来坐了一会。
忽然阿三姐走了回来,一眼瞥见婉贞,便嚷道:“怎么就放了这贱人出来?”阿凤笑着道:“他已经千依百顺了,婆婆难道还关着他么?”婉贞便站起来,说道:“昨天前天的事,都是我的不是,妈妈休要怪我。”说此话时,心中想道,我是何等样人,要和这鸨妇说这服低的话,还要叫他妈妈,未免委屈,只是出于无奈,无可如何的,不觉流下泪来。那鸨妇阿三姐也真会变化,听了婉贞此言,登时放出笑
脸来,执着婉贞的手,道:“姑娘,辛苦你了。你跟我来。”说着,拉了婉贞走到一个房里,自己坐在床上,叫婉贞在床前椅子上坐下。先说道:“我昨日手重了,姑娘你可还痛?”说着,拉起婉贞手腕来看,只见纵横错乱的红紫青黑皮鞭痕,便道:“嗳呀!阿凤,你为甚么不和姑娘擦点伤药?”婉贞未及开言,阿凤早抢了进来,道:“我原拿出来要擦的,是姑娘自己说,怕脏不肯擦。”阿三姐道:“姑娘们总是喜欢干净,你去拿来,我亲自给他擦。”婉贞连忙止住道:“妈妈,千万不要,我委实怕他脏,不要擦。况且,昨日妈妈疼我,打得轻,并不怎么痛,过一两日,就好了。”阿凤笑道:“还嫌轻呢,婆婆再打他几下。”阿三姐道:“他依从了我,莫说是打,别人碰他一碰,我还不答应呢。”婉贞道:“本来妈妈是打得轻,若是打得重时,便有十个我,也打死了。”说得阿三姐、阿凤一齐笑了。阿三姐又道:“你既害怕脏,我另外给一个定痛丸你吃。我这定痛丸,是一个跌打名医的家传秘方制成的,无论那里痛,吃了便好。”说着,亲自取了钥匙,开了一个小皮箱,取出一个纸匣来,翻了又翻,道:“是几时把各种丸药都混在一处了?阿凤,你去找那一个识字的,来认一认。”婉贞道:“认甚么,只怕我还看得出。”阿三姐道:“认这蜡壳上的字。我们那里认得。”婉贞道:“我识字,如何认不得?”说时已站起来,走到阿三姐身边,顺手取起一个一看,道:“这是追风苏合丸。”阿三姐道:“好,好,你既然认得,索性给我分开了罢。”
婉贞就接过纸匣,拿那些“跌打丸”,“活络丸”,一种种都分开来。找出了两颗定痛丸,说道:“定痛丸只剩了两颗了。”又看那匣里时,却还有两颗“绝孕丹”,不觉心中暗暗吃惊,原来这些地方,就有这种东西,此等人真是无恶不作的了。忽又转念一想,我是个处女,如何管到这些闲事。想到这里,脸上不觉一红。阿三姐早已觉得,因接过手来道:“这是预备那些倔强丫头们用的,若是我心爱的女儿,我自然要望他多子多孙啊。”说时,用纸一种一种的包开。婉贞再看那匣里时,还有拳头大的一个玻璃瓶,瓶上贴着红纸,写着“打胎散”三个字,心中又是吃惊,却不便说出,只有暗骂龟鸨丧心罢了。阿三姐包好之后,仍旧放在皮箱里面,锁好,单留下一颗定痛丸,交与阿凤道:“你去拿点酒来开了,给姑娘吃。”婉贞接在手里道:“不烦嫂嫂,我自己开了吃罢。”阿凤便到外面取酒去了。
婉贞再看那蜡壳时,果然是定痛丸。捻破蜡壳,拿那颗丸药一闻,多是“乳香”、“没药”的气味,方才放心。阿三姐又说了好些做姑娘的如何快活,遇了个好客人如何开心的话,婉贞只是赔着笑,唯唯诺诺,并不答嘴。一会儿,阿凤取了半杯热酒进来,婉贞把丸药慢慢调开了,一口咽下。阿三姐道:“你好好的将息罢,明天我再来看你。”说着去了。阿凤仍旧引着到外面看抹牌。
光阴易过,又是一天。吃过晚饭,一众三姑六婆方才散去。阿凤却拿了一叠书来,说道:“姑娘,你是识字的,可肯教教我。可怜我拿了这些书,识一个不识一个的,无从唱起。”婉贞接来一看,却是些不相干的小曲唱本,心中猛然一想道:“这老鸨,今天骂了我几句,却触动我打主意的机关,此刻因为知道我识字,是我第二个机会到了,只怕可以借此逃出樊笼,也未可定。”因笑着说道:“嫂嫂既然备了这些书,自然是识字的了,怎么又和我客气起来。”阿凤道:“我委实是识一个不识一个的,才求姑娘教我啊。”婉贞道:“既如此,嫂嫂先自己念起来,有不认得的,我来告诉你。”阿凤果然移近灯下,断断续续的曼声唱起来,每句之中又唱了大半别字,还要想过一会才说得出来。婉贞听了,又是可笑,又是可恼。便随意把他唱错的字,说了几个。阿凤越发欢喜,唱至更深方才住口,便和婉贞同榻睡下。这还是防备他寻死的意思。婉贞明知其意,也不做理会,故意在枕上和他谈些读书识字的话。阿凤问道:“姑娘读过几年书,就识了这许多字?”婉贞道:“我何尝读过书,不过跟着人家学写了两个月字罢了。”阿凤道:“原来姑娘还会写字,不知可肯教我?”婉贞道:“这有甚不肯,嫂嫂如果肯学,我包你不到几天,便会了。”阿凤大喜。
到了明天,果然到隔壁人家去借了一方砚台,一枝破笔来。婉贞看那笔时,已是秃的不成样子的了,因笑道:“砚台还可以将就,这枝笔如何用得,须要去买一枝好的来。还有写字的竹纸,也要买几张来,才好写啊。”阿凤果然去买了几张纸,两枝笔来,道:“这两枝笔,一枝姑娘写给我看,一枝我自己写,可好?”婉贞听了,正中下怀,因随意写了一张,叫他蒙上仿纸,自己去写,他写不成时,婉贞还去把他的手。幸得服定痛丸之后,过了一夜,果然诸痛大减,便乐得借此消遣,一面自己默运绮思,打自己的主意。阿三姐每日来家一转,看见如此,以为婉贞果然顺从了,自是欢喜。不知婉贞是:
要离虎穴龙潭险,费尽三毛七孔心。
不知婉贞打甚主意,有甚妙法,可以出得樊笼,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