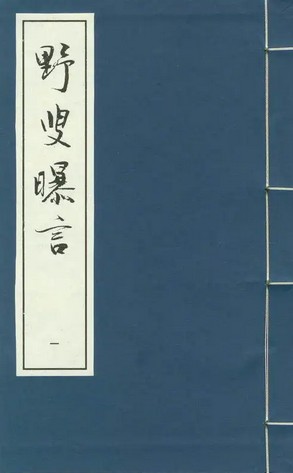忽见门外一个眉清目秀,扎着双丫髻的一个小孩子,朝着屋里嘻嘻的只自笑。只听李四嫂的一声直立起来道:“大姐,连日怎的恼着?这会子好风也吹了仙人下凡哩!这又不是我家,说不得贵人不踏贱地,屋里有两个美人,你可瞧一瞧,怎的就不进去呢?”石氏听说,向门外一望,只见雪白一个脸儿,在门缝里瞧着璇姑。李四嫂早已跑到门外,一把拖住,说道:“我白磨破了嘴唇皮,怎的声也不回我一句儿?”那姐总不言语,只是摇着头,迷迷的笑。慌得众妇女都赶出去,张妈推背,钱二嫂拉手,别的帮着扯劝,李四嫂便抱起小孩,与他亲着嘴儿,说道:“贵哥儿,可要豆炙饼吃?”那姐儿方始进门,石氏、璇姑只得站起身来,大家厮见。老实连忙送出一副杯箸,又向钱二嫂家借过一张竹椅,方才坐定。钱二嫂先向石氏说道:“这位大姐叫春红姐,是大奶奶房里第一位得用的姐姐,柴房、米房、银库、钱房,是处的钥匙都是他掌管,大戥的银子都托他称使,各处的帐目都靠他查算。”李四嫂接过说道:“这贵哥儿是大奶奶亲生的公子,别的人谁敢近他,只托这大姐照料。一家大大小小,里里外外,谁不承奉这大姐?谁敢在他跟前咳一个嗽儿?我这大姐,又且生得好性格儿,每日欢天喜地,待着我们,重话也不肯说一句和。我这大姐做得一手好针线,就是里面姨娘们一个赛一个的好花绣,都比他不上。还写得一笔好字,看得一肚好书,打得一手好算盘,猜得一口好灯谜,知机着窍,见景生情,与大爷、大奶奶就似合穿着裤儿,相好到没开交儿。”张妈道:“婶子们只顾说着话,也替我劝大姐吃杯酒儿。”李四嫂笑道:“我只见着他,心里就喜欢,把酒都忘记了!大姐,你可干了那一杯,我好来斟。大姐!那春红待说不说的道:“我实是吃不得,这几日不知怎么,心里烦,茶饭都懒待吃!里头作飨,我只呷了一杯酒,是样都给小莲吃了。这两位是那里人?几时来的?生得好模样儿!这位更是齐整,像还没出门哩。我常在这门口过,怎通不见一些影儿?”李四嫂道:“这位刘大娘是张大娘的婶子;这位璇姑娘是张大娘的姑娘,这是个闺女哩。他两位来得久了,因心里有事,总没出房。张大娘又是固执的人,我们也没敢来聒噪。今日大家都有节事,却被张大娘请得认真,才来扰他,才得见这般美人!刘大娘方才还说我取笑哩,如今连大姐也称赞,可知是真了!你还没有知道哩,就是上等画的人儿,他也不肯轻易说他一声好,他说好时,谁敢再说个不好?这就是瞎眼婆子,只好打入孤老院去了!”
李四嫂正在嘈杂,只见一个小丫鬟跑得气喘吁吁的,往门里一张,喊道:“大姐原来在这里,我那一处不寻到!快些进去罢,大爷要你去哩,快些罢,大姐,好大姐!”春红哕的啐了一声气道:“你看这个样儿,可是反了兵马渡过江来吗?也没这个样儿!”那小丫鬟揩拭着脸上唾沫道:“那里是反了兵马?是大爷等着出门,说是天热,要换单衫袍子哩。你只是坐着不肯去?”春红道:“你先去罢,不要装那腔儿,你说他也进来了。”那小丫鬟如何敢去。春红道:“我还要问问这位姑娘的话儿,你哭丧着脸儿怎的?你可也瞧过这样好美人儿?”那丫鬟真个仰着面,把璇姑孜孜的呆看。慌得张妈没做理会,只得劝道:“大姐,不是我不会做人,大爷的性子好不利害,你又不肯吃点东西,你和哥儿进去一进去,停会再和我家璇姑娘攀话罢。”春红笑道:“这倒也不怕他,他有性子便怎的”人在墙门里坐坐,怕跑了街上去,出着他的丑吗?”李四嫂笑将起来道:“好大姐,你这般玉人儿,你只不肯上街,你还说是出丑么?那些大官府家的太太、奶奶,都不敢见人了!张大娘,你是不知道他大爷的性子利害,可知这大姐的性子尊贵多哩!他见我们以下人儿,他倒和气,肯下意儿和哄着说笑;他大爷容易要他一个笑脸儿,倒是难哩!他也是与这大姑娘有缘,一见面就要与他叙个情儿;等闲大乡绅家姨娘、小姐,他还不肯和他甜甜的说句话哩。
四嫂正在奉承,只见外面又跑进一个丫鬟来,蓦地看见璇姑,呆了一呆,便骂着那小丫鬟道:“有你这丫头,大爷那样发急,你还在这里听说闲话!快进去捱马鞭子罢!”小丫鬟慌得哭起来道:“我什么不催,大姐总不动身!”春红斜瞅了一眼道:“就总推在我身上,我自爱说句话儿。玉梅妹,那单衫袍子折在里间第七只箱子上描金皮箱里;你也在房里的,须不比小莲吃饭还不知饥饱,什么就不记得了,总要支使着我!”那玉梅忙陪着笑脸道:“好大姐,是我说错了!我也知道,只是没钥匙。大姐你不进去也罢,却只苦了小莲,省了他一顿鞭子罢!”春红懒懒的立起身来,抱过贵哥儿道:“也罢,我进去了再来。”玉梅、小莲欢天喜地,簇拥而去。正是:
积宠成骄,积骄成贵;处士盗名,鄙夫窃位。骂得刻酷。
春红等刚跨进房,连公子便把小莲劈面一掌,被春红隔,说道:“做什么便打他?”大奶奶道:“春红,你也忒没要紧,小莲来寻你,你也就进来罢了。”春红笑道:“哥儿要往大巷里顽去,走到张老实家门口,只见里边两个女人,生得好模样儿;一个年纪小些的,更是齐整,我心里爱他。”那大奶奶瞅了春红一眼道:“你快去寻纱衣罢,有许多闲话!”春红哕了一声,慌忙放下贵哥,自向后房去了。这公子就如热石头蚂蚁,在房里团团的只顾打旋。春红拿着纱袍出来,笑道:“好性急的爷!只今日是好日吗?”那公子不及回言,披衣而去。大奶奶埋冤春红道:“你这张嘴生来是这样厂的,我可也掩得你住!你看,大爷听着你说话,喜得他那样儿,那魂灵儿已飞了出去了!你见他打旋,你说是为出门去这样性急。我倒猜着他要到张老实家去会那好模样的人儿。你就天生这张好厂嘴儿也!”这句话把春红更说呆了,懊悔不迭道:“我怎生这一张厂嘴儿?总为那一个生得可爱,把心就昏了!大奶奶,我看那个女子相貌端庄,性气高傲,不是容易上钩的鱼儿。”大奶奶道:“你倒说得好风凉话儿!你大爷的鬼见识儿,还是数得出来的么?更有那攀着臀,撮着屁,梯己的人儿,你不肯上钩,他没有大大的网儿,拦着河来撒你的吗?”春红道:“大爷真个把网撒下去,春红帮着大奶奶把砖儿、瓦儿、瓶儿、罐儿雪片的打下去,包管撩破了网儿,赶掉那鱼儿,他也只索提着空网儿走罢了!”春红自与大奶奶商议,公子却如飞跑到张老实家,在门缝里失惊打怪的张看。里面那些邻妇只顾张家长、李家短、夹七夹八的乱嘈,张妈只顾劝着吃酒、吃菜,石氏、璇姑只顾出神呆坐,由这公子窥觑,竟没一人瞧见。直到众人将及起身,公子方才进去,劈面撞着春红,迷迷的笑着说道:“大爷没去拜客么?在那里来?”公子并不回言,直奔凤姨房中去了。
这公子名叫连城,颇有才貌,性极慷慨。父亲连世,现任兵部尚书;母亲和氏,随任在京。因家中产业甚多,留他在家掌管。他却不耐烦这些收租放债事情,惟好炼丹采战,觅柳寻花。亏得正妻刘氏,强干有才,把持家事。正妻之外,尚有三妾。这凤姊姓单,名唤凤迎。父亲单财,是仁和县中仵作,因合钱二嫂有亲,凤迎时常来往,见公子垂涎其女,暗令通奸,潜行捕捉,诈了一主大财。然后嫁至府中,做了第二房的姬妾,家中俱呼为二姨。生得瘦小身材,心灵性巧。因大奶奶颇有醋意,拘管防闲,不能任听公子作为。他就翻转样儿,不做酽醋,却做饧糖,专一迎奉公子,替他出些鬼计,奸骗外边女子。公子爱之如同掌上之珠,爪中之肉。凭着大奶奶这般风力,一月之内,定要在凤姨房中睡着三夜五夜。凤姨见有功效,一发贴心贴意,替他画策设谋。这日,公子走进房中,一口就把璇姑之事说知。凤姨笑道:“这有何难?是在你家墙门内的人,怕他飞到那里去?只不要使大奶奶和春红知道,包你成事便了!”公子连忙抱在怀里,急求定计说:“今晚就要谢媒!”凤姨迷花眼笑,勾着公子的头,说道:“天下事,有了银子,没有做不来的!只消叫张老实到一秘密所在,许他些银子,叫他做牵头,或是与那女子明说,或是暗中照应,只要弄得上手。便是果然贞烈的人,也只索顺从了!却不可使春红知道。”公子道:“果是妙计!但张老实本分的人,从不肯做虚嚣的事,故此人都叫他张老实,就叫出了名;他如何肯做牵头呢?”凤姨笑道:“大爷怎这样没见识?随着他是个老实人,见了银子,就不老实起来了!你率性和他直说,做得成,给你许多银子,如今先给你许多;若不肯做,就送你到官,打你许多板子,连夜赶出屋去,叫你合妻子露天去睡觉!他漆黑的眼珠,见了雪白的银子,又怕没屋住,又怕捱板子,又想着后头的许多银子,他还肯老实,不依你吗?只要春红不知,大奶奶就无从知道,这女子就稳稳上钩,这就是你女儿一点子孝敬!”这几句话,喜得公子心花都开了,把嘴连连亲着道:“我的心肝,你怎便有这些意智?我若出兵时,筑坛拜将,定要封你做个军师哩!”说罢,放起凤姨,慌忙走出房来,恰好撞着春红,瞅着眼道:“大爷,你出去拜客,是几时回来的?这会子晚了,怕夜凉,换去单衫罢。”公子忙道:“我这会正热得慌,方才忘记拿扇子,如今还要出去哩。”春红笑道:“白日里就讲鬼话!现拿着湘妃骨儿扇子去的,敢是忘记在那一个房里也怎的?”公子已走过花厅,摇着头道:“正是,忘记在书房里,如今就去。”春红再要说时,连身影俱不见了。春红暗忖:大奶奶真好神猜!你看他那样儿,赤紧的干那茧儿去也!公子走出花厅,向夹巷里抄过花园中来。
那花园与这边住宅,是一样两所大房。这边房子靠西,前后共有七进;那边房子靠东,只得四进,后面三进基场,便做一个小小花园。这边前开大门,对着大街,后开水门,通着城河;那边前后俱是围墙。两边各不相通,中间夹一长巷,只第三进长巷中间,开一角门,通过东边去的。这公子因好外道,供养着些不三不四的道士在内,讲究炉火之事,只许男人进去服事,丫鬟仆妇,除做鼎器以外,脚尖儿也不敢跨进一个去。这日公子因凤姨嘱咐,怕走漏消息,故此走到东边来,不去惊动道士,自在前这一间密室坐下,着一个小厮,去把张老实叫将来。悄悄的把凤姨所教之言,从头至尾,说一个明白;在袖里摸出十两一锭雪花也似放着光的银子,说道:“事成之后,再找九锭。”吓得那张老实哑口无言,半晌出了神去。公子喝道:“你休装聋做哑,肯依则依;如不肯依,立刻押你去捱板子,撵你出门了!”张老实一则怕出屋受刑,二则从没见过这般银子,果如凤姨所料,把良心吓过一边,说道:“银子是不敢要的,小的回去与老婆商议停当,来回复大爷罢了。”公子大喜道:“这事成了,不特所许九十两银分毫不少,将来还要着实看顾你哩!只是明日就要给我回信。这银子你可收去,不可推却。”老实连忙答应,收了银子来家,悄悄与妻子说知。张妈甚是埋冤,老实道:“我原不肯应承;公子说要送官,今日就赶我们出屋,又要把你去拶拶子,你说当得起吗?”张妈也是害怕,却见老实拿出一锭银子,吃了一惊道:“怎银子有这样大的?我眼里从没见过!这是给那一个的?”老实道:“这是公子赏我的;事成之后,还有这样大的九锭,还要另眼看顾我们,许多好处在后头哩!”张妈变愁为喜,笑着说道:“这便顾不得许多了!只是如今怎样去说骗他呢?”
夫妻两个,捏紧了那锭银子,出神捣鬼了一会,总没计较。张妈道:“且藏好了银子,拿夜饭他们吃了,和你到床上去再想。”于是忙忙的拿着夜饭,送到石氏屋里,想要说些什么,又没处说起,只是呆立。石氏道:“姆姆请便,我们吃过,收到灶上来罢。”张妈只得出来,直到上床,两人爬在一头睡了,细细商量。老实忽然想着主意,张妈连忙根问。老实又道:“不妥,不妥!”张妈道:“我倒有主意了!”老实正待问时,张妈连连摇头道:“也不好,也不好!”直到更余,老实方欢喜道:“这是极妥的了!明日你骗了姑嫂两个,进去拜见大奶奶,再不就说大奶奶叫进去,料他不肯违拗。我自与公子说知,在二门里候着,抢到花园里成亲,你说好么?”张妈道:“几日前,我曾劝他里边去见见大奶奶,往各房走走,散散心,他们把头几乎摇落!况且里边人多口杂,白日里拖拖扯扯,闹得大奶奶知道,不是耍子!我如今真有一条好计了!”老实忙问:“何计?”张妈道:“你便出门去了,借宿在亲眷家。我便推着害怕,要刘婶子来相伴。教公子预先伏在灶下,等他自到璇姑娘屋里去。他见公子这样风流年少,敢也肯了?”老实大喜道:“真是妙计!他就不肯,男子汉的力量,璇妹可是拗得过的?到弄上了手,生米煮成熟饭,公子有的是银子,璇妹也是没见过大银子的,怕不情愿!我们这一锭银就得的稳了!”张妈笑将起来道:“可是我的主意好呢!我成日听见里边杀猪宰羊,哥儿姐儿,吃得满嘴的油;我和你好的时候,过冬过年,也只买得半斤四两的猪肉,这羊肉总没尝着他是啥仔味道!如今有了银子,要你买一斤羊肉,蘸着葱酱,和你吃一个快活!”老实道:“我和你还是做亲时节做的绵裤,才穿了两年,就当折了;至今没有傍着棉裤的影儿。这事若成了,我还要做两条蓝青布棉裤,大家受用哩!”张妈道:“这更好了!将来银子多了,每日买他两块豆腐,多着些油,和你肥肥嘴儿。我和你四五十岁的人了,又没有男女,有了银子,还不受用受用,真是个痴子了!”老实道:“休说后来许多看顾,只有了他后手九锭银子,也不愁没男女了!拚着一锭大银,讨一个瘌痢丫头,生得一男半女,我与你老来都有靠了!”
这张妈正在欢天喜地,忽闻此言,发极起来,骂道:“你这老失时、老短命!我嫁到你家,替你烧茶煮饭,洗衣刮裳,铺床扫地,捣米舂粮,一日到晚,手忙脚乱,略空闲些,还帮你上两只鞋儿。这样辛苦,可曾尝着你半斤四两鱼儿肉儿,有一顿没一顿的,捱饥忍饿!到如今,还是我出了主意赚来的银子,你就要讨起小老婆来,你叫人心里疼也不疼!你这天杀的,可比那强盗的心肠还狠着三分!我好苦也,我好苦也!”张老实急急辩说道:“不要哭,隔壁的人听见了,不是耍子!我和你说笑话哩,谁要讨小老婆,就是活乌龟!”张妈那里信他,只是呜呜的哭。石氏与璇姑晚上洗了脚,因剪鸡眼及脚指甲,还未去睡,听着老实夫妻唧唧哝哝,却也不在心上。这石氏脚上一个鸡眼老了,再剪不下,想起中间屋里切皮的刀儿,甚是快利,要起来拿,他因光着孤拐出来摸那皮刀;只听见张妈说帮赚银子就要讨小的话,老大疑心,要听他个下落。忽听张妈出声啼哭,老实又说隔壁人听的话,就悄悄的提着刀进来,自与璇姑猜想。这张老实只得再四苦劝,连罚毒誓,又爬上身去,把腰间挂的棉花条儿死推活塞在张妈阴户之内,陪了一会子不是,张妈方才住哭。老实拿着一块破布头,正在张妈下边揩试,忽然的身子直坐起来,失声道:“不好了!”手里布头便直抹到张妈嘴唇边。正是:
饱暖尚赊先纵欲,欢娱初罢忽成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