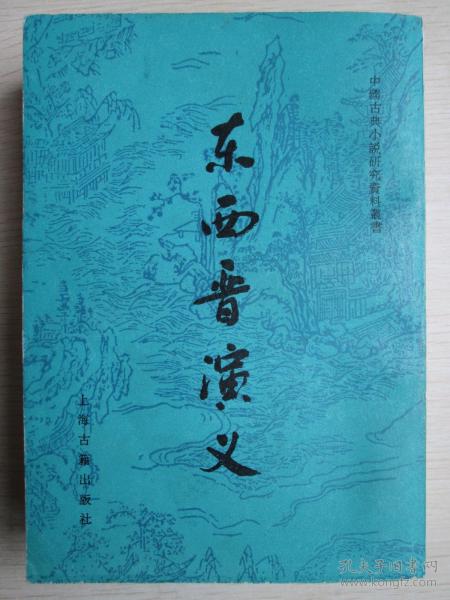怀祖驀地一惊,急忙举头,认是建威,问道:「兄又有何事?」建威道:「别无甚事。尊夫人檄文想已草就,弟急欲一读。」怀祖问其妇取稿,交在建威手中,随行随看,洋洋洒洒,写满了一张如意笺。首叙自己来歷,并回国的因由;中述例与约的分别;末叙开会的缘故。共分叁大段,其大意道:
妾不幸作女子身,尤幸不生於祖国,而呱呱堕地於新大陆极南之海角,以幼以长,以至於於归,肢体胸膈,未尝一日有拘孪束缚之苦,固自以為豪矣。乃与彼中诸姊妹,对镜而互观,内於家庭,外於社会,权利义务,思想之发达,无毫末不逮男子,有时几几若过之。及知凤凰之自有真,仅仅修饰羽毛、自夸文采者,终不离乎鸡群也已。且惭且愤且奋思得藉手,以显我同种诸姊诸妹之能力,卒之未获如愿。会禁约届满,海内外诸伯、诸叔、诸兄、诸弟,云合雾集,风发潮涌,锐然鼓无前之勇,毅然举自我作古,举世未為之义,妾始佩之,继感之,终乃飆然起曰:此我诸姊诸妹潜势力发生之机也。自顾五尺躯,虽纤弱无似,然得执鞭瞂,负牙旗,為前驱之走卒,非所敢惮。
月日横渡太平洋,东经地中海,出苏彝士河,北驰以抵上海。
上海者,全中国人材之所萃,而今者抵制之中心点也。十日来,飫问绪论,或改或废,相持者,要不出约之外。夫外人之视我华工,奴隶蓄於先,牛马鱼肉待於后,日循日酷,又旁决以虐待我商,又横溢以厄我学生,约為之乎,亦例為之耳。我诸伯、诸叔、诸兄、诸弟之明达,何遽见不及此?其始终言约不言例者,由乎中有所惮。何惮乎尔?则我诸姊、诸妹实有以致之。
嗟乎!我诸姊、诸妹有势力而自放弃也,又以為诸伯、诸叔、诸兄、诸弟之累,尽义务而若未尽,争权利而若未争,将不免為地球万万种种色色之外族笑。
且不独现在之地球而已,又将為未来地球為万為亿為兆為京為垓以至无量不可思议之外族笑。我姊妹苟一熟思之,必且蹙然不安,尽焉自伤,毋待妾之嘵嘵已。
而妾犹不敢自嘿者,则以我诸姊、诸妹蹙然不安,尽焉自伤之一心,即潜势力之发生於无兆无朕之中,而我诸姊、诸妹,或有一二犹未自觉也。充是势也,充是力也,无内无外,无坚无暇,无高无下,无一世十世百世千世乃至万万世之别。皆得弥纶鼓荡於其间,若犹不知之,犹不遂利用之,则真至可伤心者也。月日午后叁句钟,借座雅仙剧场,敬迓诸姊妹各贡伟抱,以匡妾之不逮,而為海外诸父老兄弟姊妹谋所以解倒悬之厄,仰企毋任。纫秋张氏谨白。
建威阅毕大喜,便约怀祖到一家印刷所,加倍许了钱,提前发印,约定明早叁。又到雅仙戏园,同园主说明就理。
原来这座雅仙园,专唱崑腔。自从京调盛行,听的人说是调高响逸,胜於靡曼之音,唱的人觉得发声收口,色色随人所便,比不得崑腔一手一足,都要应弦赴节,难易相去十倍。听戏的不爱听崑腔,唱戏的也不爱唱崑腔,从此雅颂之声,真应了两句老话,叫做「只应天上,难得人间」了。
那雅仙园主,偏是个李龟年,白发婆娑,不能够重描眉黛,学步时趋,一园一天卖不到二十个座儿,浑身一毛一孔,都填满了债主的金钱,偏又尚侠任义,脱不了旧时风范,掀髯笑向两人道:「我亦华人,一样也有耳有目有脏有腑,难道不该帮忙,要两位说个借字?临期竟请光降,茶水也由我承值。只是应该如何佈置,请两位预先吩咐,这倒是个门外。」
建威、怀祖出其不意,相顾起敬道:「既如是,我们也不说客话,事后另图补报罢。」前后看了地位,计议了一番,回栈告知。张氏惊诧道:「伶官中竟有此人,曾问姓名麼?」怀祖道:「也曾问来,陈姓,钊泉其名,是个梨园老辈。一切眾生,有声闻就有根器,有根器就能成佛,古人真不我欺哩。」
本日无话。明日去取了檄文,张氏按照建威开的校名坐落,挨排去送,每到一处,必与主人教员纵谈半晌,又看看学生的课程。张氏见这数年居然发达到这等地步,着实佩服。眾人见张氏和蔼亲人,谈言慷慨,也着实敬礼。又知开会这日,尚只张氏一人,便有自任干事的,有自任招待的,约定一句钟先到园中会齐。
连忙叁日,檄文方始派完,离会期只一日了。下午晡时,正自外归,茶房递过一张名刺,说这女人已来过两次了。张氏看是一张巨红纸,印着叁个不大不小的字,纸色古朴,笔势尤其苍健,不知何等人物,又不知居停所在,只知道叫做苏隐红,闷闷地无从索解。恰巧怀祖同着建威也已回寓,张氏提起有这女人,今日一连来了两次,不知為的何事。建威道:「无因而至,不速而来,形跡已是可疑。只这名字,若断若连,也是十分奇怪。」怀祖抚掌道:「吾知之矣!隐娘、红线不是个女侠麼?这人胸襟谅也不凡。依古来道高魔广,务自晦藏,他犹游戏人间,呈露色相,正如佛门中辟支禪,还没到上乘地步哩。」
正在互相议论,忽见一人,当顶挽个盘髻,横插一枝玉釵,髻边茉莉珠,中镶一朵大红月季花,耳垂一副翡翠叁连,一身金银罗的衫袴,脚上套了一双蛮靴,服色离奇,偏又脂粉不施,天然嫵媚,婷婷裊裊的走来,深深的万福道:「这位想是纫秋姊了。叁次登门,始得近接玉容,一消饥渴,也算前生缘法。」
张氏急忙答礼道:「是隐红姊麼?步虚声裡,习习天风,俗抱尘襟,霎时尽扫。始知天人真相,自非俗粉庸脂所能模拟。敬具皋卢,前谢失迎之罪。」当下谦逊坐定。
隐红不待动问,先自陈诉道:「家住黄山,客游沪瀆,昨闻豪举,深佩热肠。不自揣量,俗以肺腑之言,箴膏肓之疾,不知姊姊尚能垂纳麼?」张氏肃然正容道:「妹心长才短,不自知非,倾盖之间,即承匡正,正自求之不得哩。」
隐红道:「山有空穴,风所从生,海有归墟,水所奔赴。今日主持改约者,果如空穴之招风,不免示人以隙。然而登高一呼,海内响应,数千年酣酣之梦,居然一醒,其所见虽差,其苦心可敬。其魔力尤可佩。姊姊必欲抉症破结,一层时机已失,恐言易而行难,一层借人口实,因以疵议前议者之非,败坏团体,自便私图,姊姊一番普渡眾生的盛心,转不免负罪社会。黄河浩瀚,犹自朝宗,不如且退一步罢。」张氏道:「心知其是,而故相抵抗,是谓愎;心知其非,而盲相顺从,是谓媚。愎与媚,皆非妹所敢為。且自今以往,抵制之真结果,遥遥无期。此时而為废例之预备,不為失时,怀私挟诈者,苟闻妹言,方将深恶痛绝,怎肯借為口实,又怎麼能败坏团体?姊姊似乎过虑了。」
隐红道:「目前诸人,忽而言退货,忽而言不用之有害,倏反倏覆,正為个人的私计,与团体不能相容。无奈不曾搜到病根,倒觉进退狼狈。若然晓得改约之无济於事,自然而然要大声疾呼道,外不能救工人,内先自困生计,随声附和的,一经提醒,能无颓丧?人人都到意懒心灰的时节,抵制之局,立时可以解散。姊姊可不慎重麼?」
张氏道:「有為私谋破坏者,即有為公谋团结者,私情究胜不得公理。在妹愚见,尚属无妨。」隐红道:「是则然矣。姊姊亦知大祸之将至麼?主不用者,以為源不绝而流自清,主疏通者,以為利未睹而害先彰;各持一谈,各不相让,究竟都是空言。所可虑者,商人现定之货,期远而数多,压於断流绝潢之势力,出则停搁成本,不出则经年存栈,外人岂无烦言?妹尝私计,目前犹可相安,明岁交春,若辈非怂慂外人,出而以强力干预,即将輟业杜门,纷纷倒闭。外人干预,则主改约之诸君,必有受其害者,犹不过二叁人;倒闭人事若见,影响之广,将至不可思议,而其终皆足以解团体。姊姊与其言例,似乎别树一帜,实则更添歧路,不如从这两层,层层推勘,求一两全之策。但而来人情,类乎讳疾而忌医,掩耳而盗铃,姊姊如彩芻言,亦不是仓卒间可以从事的。」张氏道:「姊姊所说為商人虑者,妹与同人也曾想来,也会议过疏通的办法来,但总不外黏印花、给凭单,各有所利,也各有流弊。最难者,前定销通,后定或致混充,不消几时,大局例将瓦解。且有至要一层,必当先自分明。目前何為而议抵制,人人皆知是為排障碍,求便利。障碍如何而可排?便利如何而可得?是非废例不可。例之不废,就将约文修改完善,彼外人者,舍约而引例,我其将奈之何?故妹之意,第一当宣明抵制的宗旨,专為废例而起。宗旨既定,再就现在情形,谋所以维持商场,保全市面的方法。而如有於全局有害者,则只可以為多数人计公益,不当為少数人计私利。姊姊亦国民中之一人,既為此事出与社会周旋,家庭间亦尝有所论辩否?」
隐红笑道:「上天下地,独往独来,何处為我的家庭?」
张氏惊道:「姊姊并地室家麼?」隐红道:「不瞒姊姊说,小妹為先人遗腹,六岁又遭母氏之丧,幸為邻庵老尼收养,得至成人。向来於世事不闻不见。此番因佩姊姊的热心,才来踵门求教。本意想劝姊姊无劳笔舌,无如姊姊立志既坚,小妹又不工辞说,此时倒觉无从进言了。」张氏道:「姊姊来申何事?老尼曾否同来?」隐红道:「不妹行踪无定,来去不常,也无一定的事。老尼却尚在山中。」张氏正色道:「厌世主义,不合现时的趋势。姊姊稚龄弱质,也不在厌世的时候。」隐红不让说下,早截住道:「小妹别有怀抱,不入世也不出世,姊姊倒不劳掛怀。时已上灯,后会有期,姊姊凡百自重。」张氏道:「尚不曾问姊姊的寓处,妹真忘情了。」隐红道:「不妹居址,姊姊即知之,亦无从过访,明日如在此间,或者到会中奉候,也未可知。」说着已经离房。
其时怀祖避在建威房中,等张氏送客归来,又相议道:「其人言论无异常人,其形踪至為恍惚,真令人无从捉摸。」张氏道:「我视其人,虽饶有美姿,眉宇间时露英武慷爽之气,或者便是隐娘、红线一流人,也未可知。」谈论一会,夜色渐深。饭毕就寝。
明早,建威邀怀祖先至雅仙,园主陈钊泉早遵两人预嘱,安排妥贴,伶人也都遣开,只留几丁茶房在内承值。午后,张氏先到,未时,干事员、招待员陆续都来。一到申初,前前后后,到了竟有五百餘人,一半是闻风自来。
铃声一响,先有干事员宣明本会宗旨,是争例不是争约,所以即名為争例会。宗旨宣后,来宾中登坛演说的共有八人。
末后张氏才翔步从容,走近桌边,款款吐语道:「诸侠姊姊妹妹呀!我辈女子不是国民之母麼?為个人之母者,勿论子之贤不肖,念其為骨血所化分,只觉可爱,不觉可憎。為国民之母者,子之為上流、為中流、為下流,在他人虽有分别,在母之眼帘中,只见為子,不见有何阶级。并且他人视之愈贱,蹙之愈甚者,母之於子,则怜之愈深,护之愈力。例如道有饿夫,男子斜睨而过之,女子则必有多寡之助。足见人群的感情,女子自优於男子。而所以致此者,则由世界人类,都為我女子所生所產,故无声无臭中,遂相感而不自觉。
「今日言抵制者,為外人虐待我侨氓而起,侨氓之受虐者要以工人為多、為最烈。能使工人出苦海而入乐土,则商人学生相沿而及之,祸不扫自除。仅仅言改约,即能如愿,不过便商而止,便学生而止,工人要不得与。诸位姊姊妹妹啊!旅外之人,难道不是我女子所生所產麼?勿信外人,谓愿并改一二条,遂坦然不為我子若孙虑也。毋论现所续议,我工人去来出入,依旧不能自由,即使改至十分完善,不还有例在麼?我执约以相詰,彼引例经相绳,究竟管理之权,在人掌中,约之力断不及例。诸位姊姊妹妹啊!到那时,我工人果不消说,依旧是為鱼為肉,听人烹割了。我商人,我学生,自今以前,未尝得享约之利,自今以后,岂能免例之害麼?」
说到这裡,台下有人詰问道:「约何尝有利?商人学生如何能享呢?」张氏道:「第一次《禁约》说,此是专指华人续往美国承工者,其餘别等华人,均不在限制之列。第二次《禁约》说,此约专為华工而设,不与官员、传教、贸易、游歷人等,现时享受来寓美国利益有所妨碍。照这两条文义解释,商人学生犹在商约中最优相待之列,如何至与工人同受不可思议之奇辱?岂非例所使然麼?诸位姊姊妹妹啊!拒约的潮流,汹涌及於全国,我辈忽然说要争例,似乎势力薄弱,不免為所淘汰。不知我辈女子,在家庭内婉婉转转,以告我父兄夫婿,在社会上恳恳切切,在告我伯叔兄弟。理论果真圆足了,便容易动人听闻。小妹不量,奉劝我诸位姊姊妹妹,不要随人附仰,以改约為圆满功德。要知例而不废,改约不过虚名。今日男子既不敢言,我女子為国民之母,当尽為母之责任,万万不可自暴自弃啊!」
这时,台下拍掌声如春雷怒鸣,四壁摇动。忽地人丛中飞出一人,褰裳迈步,直上演坛,端端整整立在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