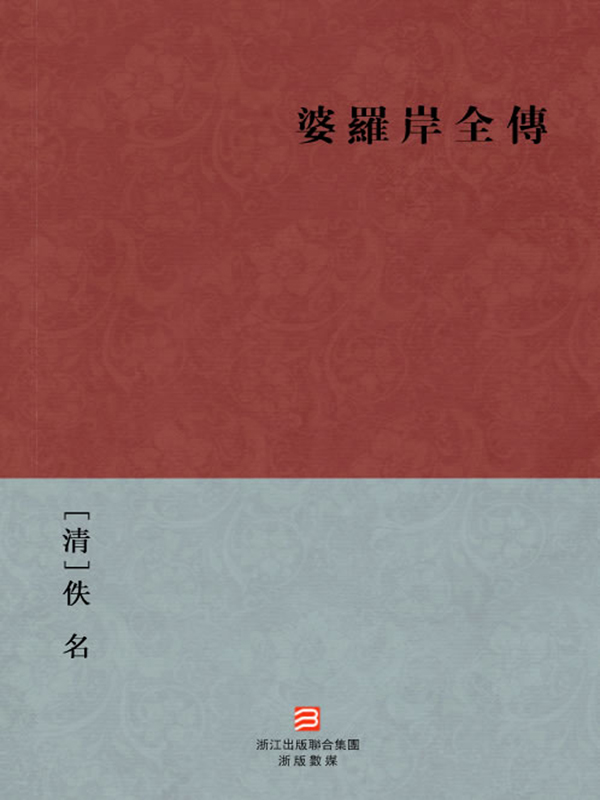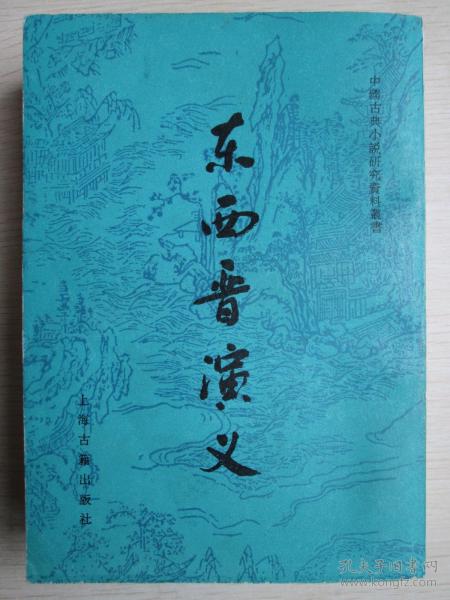张氏只觉眼前一晃,像是苏隐红闪到身后,回头一望,却并不是。正中立个四十餘岁佳人,妆饰朴素,举止从容,偏又眼角流波,眉尖敛黛,像含着十分幽怨,朝着台上台下鞠躬点头,呜呜咽咽的说道:「小妹应友兰,新会县人,家世务农。我父我舅,会香港初开,以工致富,始弃农习商。又因合资营业,情意相投,一子一女,自小订婚。妹年十六,即赋於归。夫婿区远龄,少有远志,每思破浪乘风,遨游域外,久久未遇机会。妹於此数年,始稍知生人之乐。不意金山分号的掌柜,忽传病信,亟须替人。夫婿欣然请之於舅,孑然独往。其时妹年二十有四,有子亦七龄矣。夫婿去不匝月,舅以猝病辞世。妹以弱女子,内支门户,外款亲朋,间时又赴乡间营亲窀穸,叁月之中,心力交疲,始知生人之苦。幸而夫婿闻讣归来,妹得稍稍息肩。乃未愈年,忽有戚串从金山来,传述号中各伙,滥支浪费,势将不支。夫婿不得已,匆匆就道。
「自此十年不归,我父亦已亡矣。子年渐长,酷肖其父,慕壮游。妹以膝前孤另,劝不使行。年十八,為之授室,未叁载,得一男。妹於是时,有儿有媳,又有稚孙,投怀索抱,几几乎只知有乐,不知有苦。但良宵深夜,繫念藁砧,犹时时以泪浪渍枕。不想此两年前,金钱空卜,只雁不来,妹固晨夕皇皇,儿尤傍徨万状。挨过八阅月,儿忍无可忍,坚欲赴金山省视,不得已,只可任其远行。出门之日,儿媳悲离怨别,泣不成声。妹回想当年,也不觉欷歔欲绝。惟盼早一日得一平安之报,便早一日慰我闺中之望。转瞬又已半年,竟也鱼沉雁杳。
「咳!那时那时,不瞒诸位姊姊妹妹说,妹与儿媳一时从好处想,或是父子两人双双回国,恍恍惚惚,好像已在面前,不觉莞然欲笑;一时从坏处想,或是父子两人双双都遇了意外,恍恍惚惚,好像已闻凶信,不觉嚎然欲啼。如是又逾一月,忽见一张《金山日报》,上记一条说:
太平洋会社之汽船,有一乘客,闻从广东新会县来,以违禁例,致被拨回。某月某日,船离桑港约五十哩,其人不知何故,自投入海。船员闻信,急放舢板施救,正遇风狂浪涌,无从打捞。其人何姓、何名、何事来美,尚待查访云。
妹骤睹此条,便猜是我至宝至贵至亲至爱之佳儿,酸痛彻心,便悠悠荡荡,神魂若失。良久良久,忽有小儿哭声,剌入耳轮,才得醒来。却见桌边地下,横卧一人,模模糊糊,尚不认是何人,俯身一视,咳!可怜呀!不想便是至宝至贵至亲至爱之儿媳,昏不知人,悠然若死。孙儿方幼,只是牵衣绕膝,极声嘶唤道:『娘醒醒呀!娘醒醒呀!』」这时旁听诸人,都听得万种悲伤,百般怨恨。友兰忍不住,已是失声。
停了刻许,拭泪重语道:「好容易延医觅药,才把儿媳救醒。却自此一姑一妇,楚囚相对,只觉死之可乐,生之可悲。偏偏两叁月来,尚无确信,邻家又夜夜隐约送来哭声,越引得望夫思子,不能自己。不瞒诸位姊姊妹妹说,妹虽商妇,然节财省费,犹似农家,未尝轻役佣人。
「偶以易米,与邻妇相遇,渠一啼一哭告妹道:其夫在外国作工,年前因事回家,甫及半年,乘船復往。近见同伴家书,知到埠时,适遇木屋新成,梁夫应对不知如何错误,便被押入。据闻木屋造在海滨,低潮黑暗,比囚牢尤苦几倍,体亏身弱的,一入其中,极易成病。渠又闻人传言,在木屋中染病不起者已有四五人,因此又惊又急,夜夜不能安枕。
「咳!诸位姊姊呀!诸位妹妹呀!妹当时若不生希冀之心,守着一孙一媳,苦楚已非人境,偏偏又想我夫或是抱病,我子或也被押木屋,因此音信杳然,不自揣量,亲身去探消息。诸位姊姊呀!诸位妹妹呀!那真自寻烦恼了!」
台上下、会内外,一切听者,都以為奇,便悄悄侧耳细听。张氏驀地记起陈氏前事,胸头不觉勃勃跳了几下。却听友兰接着说道:「妹既决定亲赴美洲探听父子两人消息的主意,便从新会到香港,在领事署请张护照上船,坐定的是下等舱,污秽的情形,不堪入目。上等舱固然比不来。即同白种的下等舱两相比较,亦有天渊之别。这还怪不得外人,我同胞确有些不知自爱的。借着解闷消閒的名色,赌钱、吃鸦片无所不至,无怪被人轻视。妹再叁再四的劝阻,在我一片婆心,有人反嫌為多事,真是无可奈何。
「及近桑港,妹已问知禁例的大概,默想夫婿号名、坐落,及贩运之货物,出入之赢亏,幸未模糊,至於姓氏年岁,是无待言,决不至於差误的。妹便坦然不以為虑。惟念我夫此来究竟如何?我子何时到美,何时入号,何以无片纸隻字报母妻?前番日报所载,是否另有其人?倒觉万感罗胸,颠倒不能自主。
「咳!不想一傍码头,目睹白种诸人纷纷上岸,渐渐黑种走,渐渐同种同舱之日本人走,渐渐同种同舱之高丽人亦走。此时举目四顾,在舱待问供的,只剩我中国之同胞。咳!诸位姊姊啊!诸位妹妹啊!......轩輊厚薄,一至於此?已令人万分抱怨!若然一样不来留难,一样许其上岸,仅仅少差时间,犹可於不平之中稍稍平心。不想关员上船,点验盘詰,竟无一人不被禁在舱中。直至第叁日,十成中有两成方算无事,四成便押进木屋,四成便原船拨回。
「妹先亦在拨回之例,窃不自量,力与争执道,如谓商人之妻,不应来此,则领事即不应给照,如谓填照不曾合例,本人何自而知之?其咎自在领事,不在本人。咳!诸位姊姊啊!诸位妹妹啊?惟口兴戎,妹因此便受有生未受之辱,尝有生未尝之苦。至今追念从前,犹觉饮恨含酸,悲肠尽裂!」说着说着,又是泪痕满面了。
旁听中有人问道:「姊姊争执的不差,如何会受辱,如何会吃苦,不成彼人竟不讲公理麼?」
友兰道:「公理两字,正与文明一般解释,是强权的护符,断非衰弱者所能借口。今日中国之弱如何,理长理短,皆非外人所顾。不然,禁约具在,何尝有量身囚禁这许多奇闻呢?妹就因抗辩了几句,关员以為倔强,几个如狼似虎的关差,前来揪扭。妹喝问何事?若辈谓既不服拨回,便须进木屋候审。咳!诸位姊姊啊!诸住妹妹啊!木屋的苦况,妹在家乡时已听邻妇谈及,知不是个好所在,惟念迟早终须释出,倘得与我夫、我子再见重逢,庶几不枉此行,便死也所甘心。咳!不想大谬不然,不但不如所愿,连性命几乎断送!天乎!厄我至此乎!」号号啕啕,更咽不能成声。又隔数分鐘,才说道:「妹谓关差,便进木屋,让我自行。关差不听,竟尔自船扭上,浑身磕伤了几处。初犹不知,入屋后,和着大眾席地而坐,渐渐痛上来了。此犹可忍。最难堪者,以女子身杂居男子之中,睡时坐时更衣时,处处分别不清。还比不得船中,无板无门,尚可用布遮拦。此时一身不由自主,便觉鬱火蒸腾,不能止遏。忽然转念此来何為,不忍不耐,便不免成病,在这不见风日的地方一病,将来不免死,如何得见我夫、我子,又如何慰我儿媳?如是一想,便当躯壳已死,只留灵魂与大眾周旋,平心静气,老守关员的查审,希冀查审后便可释放。
「不想一守一月,遥遥无期,想尽方法,要同外间通一消息。岂知被禁之人,例不准通书札,竟也未能行遂。妹默揣情景,此行恐是徒劳,不知不觉,鉤起满腔的懊悔。不悔受辱,也不悔吃苦,悔儿媳当时再叁力阻,说不听邻妇讲麼,渠夫曾到美洲,尚然会遇意外,姑年虽老,犹自女身,万一拨回,犹不过空劳往返,万一也被押入木屋,不听说是低潮黑暗,极易成病麼?不如出钱请人前往访查,或稟请县中行文金山领事,或者也可得个实在下落。妹意请人未必可靠,中国地方官民本非所重,未必肯管閒事,就算邀准,一纸往返,动须轻年,也嫌迟慢,故决计不从。
「目前身在牢笼,进退渺无凭准,拋下一媳一孙,轻年弱小,何等可怜?一日十二时,竟无一时不在方寸间盘旋往復。咳!诸位姊姊啊!诸位妹妹啊!从此越想越愁,越愁越悔,不上几时,遂昏沉不知人事。忽地甦醒,已在船中,身旁有人道,好了,姊已醒了。定睛细看,其人也是妇人,却又素昧平生,且如何出的木屋,如何上的轮船,恍恍惚惚,无从回想,因而转问其人。
「咳!不想此时便得了我夫、我子的凶问,知我夫於前年查册时备受凌辱,气愤身亡,号友昧良,匿不发书,横相吞灭。我子略闻消息,故於拨回时投身海中。咳!妹自此真為未亡人了!当下悲伤鬱结,亦欲从我子之后尘,以大海為佳城,累被其人所阻,便又昏昏沉沉,连睡叁昼夜。」
这时四围虽无大声若号,惺惺惜惺惺,情不自禁,早已珠泪偷弹,细声若泣。忽然承尘上巨响骤作,大眾都吃了一惊。
内外查视,梁櫞柱础,纹丝不动,才定了心。
友兰又道:「其人苦苦劝解,说我两人產业都已拋荒,真是同病相怜。不过我有夫有子,比姊似胜一筹,姊家中尚有何人呢?妹略告大概,转问其详。才知其人夫妇成室美洲,生子方得九龄,上春因事请照挈眷回国,事毕依然同来。关员只准其夫上岸,妻子谓不合例,均须拨回。其夫苦求不得,才将店务招人盘替,一家人依旧同来同往。但匆忙之际,子金不必说,自然无着,成本所收回者,亦不及十成之四。其夫与我夫之号,相去不过二十家,曾经一面。此番又闻人谈及妹之踪跡,假托亲戚,代稟关员,带回中国,妹才得离囚出禁。
「咳!诸位姊姊啊!诸位妹妹啊!白种女重於男,彼地為自由平等之產乡,女权尤為发达,乃同一神圣不可侵犯之女身,独独视我中国人以為可欺可侮,诸位姊姊啊!诸位妹妹啊!苟有血气,谁能甘心?并且彼国既有中国之男子侨居,或母或妇,乃概禁不使往,生生的离人家室,是何人情?是何法律?今日抵制这件事,男子之责任固然不可放弃,我姊姊妹妹所负的责任,也并不轻。
「為什麼缘故呢?在外之男子,一时之间,既不能全数归来,自然必有续往之女人。不趁此时并力与外人争持,受害安有已时?咳!诸位姊姊啊!诸位妹妹啊!妹一身所经歷者已经如是,尚有不堪言不忍言之奇丑极辱,使我女子含羞饮泣,无可如何,而其祸根都从《工商部或例案》孳乳化生。刚才会长宣言与外人争例,不废不解,探驪得珠,固不愧為扼要制胜之先着,倘然能如所愿,妹还有一层,要请与外人严明要约,例既废不得再引案。」
张氏起问道:「怎还有什麼案呢?」友兰道:「便是累年被禁、被逐、被焚屋、被伤人种种的旧案了。审时不许有公证人,只供判语不许载之报章,一任关员上下其手。所以例不具者,比之案,例所宽者,又附之案,我同胞遂无一人得出於网之外。并且例之繁苟,眾人犹可得见,案则遁於若明若昧之乡,虽公使领事,无权得而查阅。故争改约不如争废例,争废例并须争废案,不如是不足以满志。
「诸位姊姊啊!诸位妹妹啊!我辈今日若同政府通电,同疆吏通书,在中国的旧习,非但无人信从,且将以為荡检逾閒,论不定不生阻力。但谁无父?谁无夫?谁无兄弟子女?门内的言论,决无人能相顾问。却是由家可推之亲,由亲可推之友,势虽不可见,力量其实不小。诸位姊姊啊!诸位妹妹啊!其我旅外十万同胞的耶和华啊!」
一鞠躬,一点头,闪身便要下台。张氏急起,把他双手执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