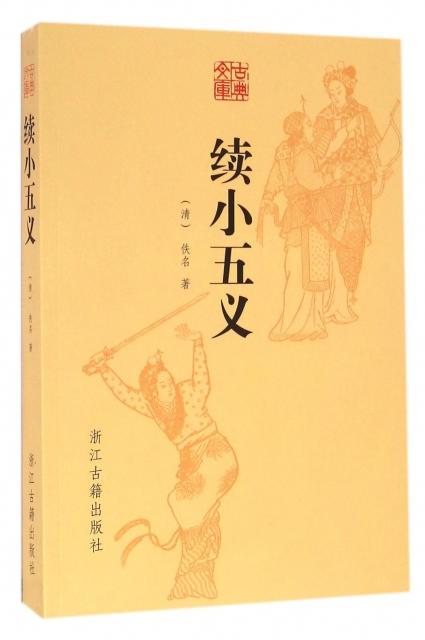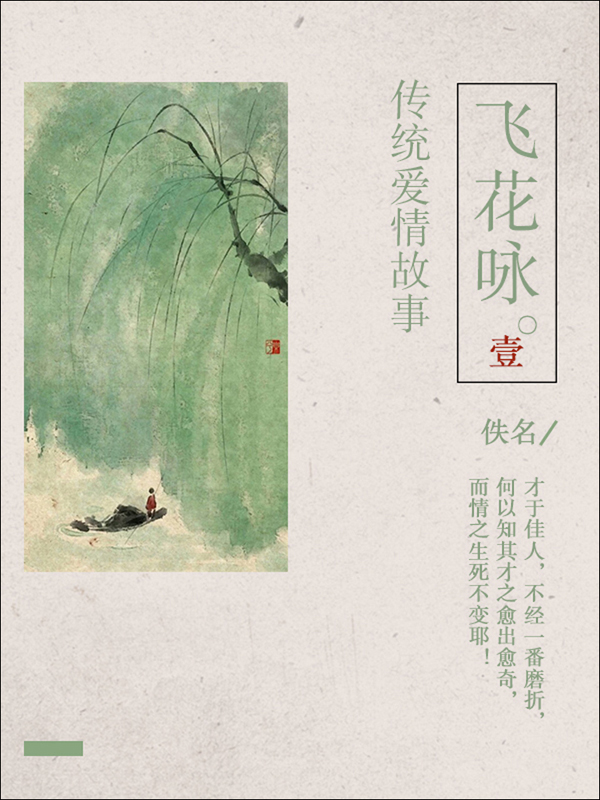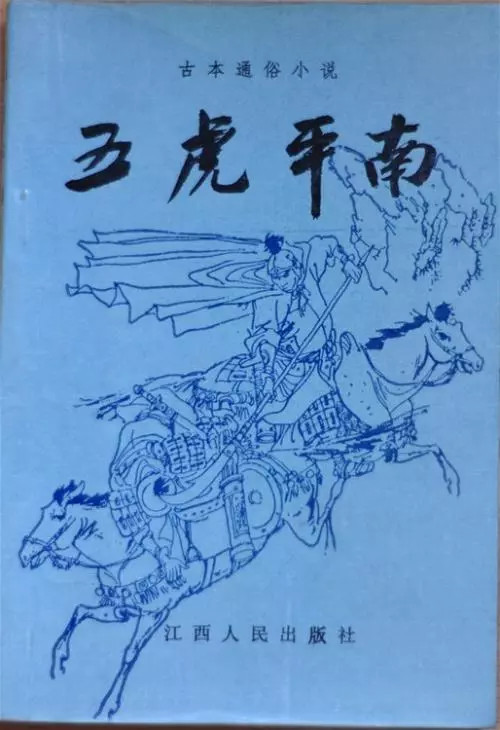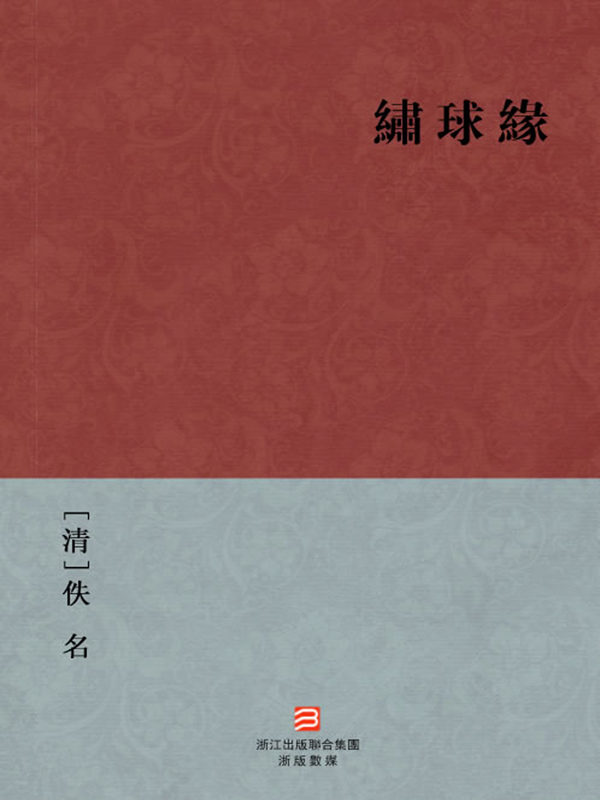古巴一岛,先属日斯巴亚,政苛税重,民不堪命,屡举义旗,以抗日人。军兴之际,土客不分,欧美侨民,也不免受池鱼之祸。幸亏警电朝传,兵轮夕至,不知保全了多少。独有我们的同胞,呼天无路,吁地无门,只好尽人欺侮。
后来美人战胜,从日人手中把古巴夺去。我同胞知美国為自由平等的祖国,以為从此可以拨云见日。不想禁约之苛,定例之烦,竟於东方人种中,用特别手段待我同胞。
其时太平洋中的华人,美利坚全国约有十餘万,檀香山约有二万餘,古巴约有四万餘。今天查册,明天照像,天准作商人,明天又改作工人。我同胞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正在人人悲愤。
忽然上海传来一电,说商会学界公议,所有美货,一概不定用,以為抵制,非待彼国改良禁约,不肯罢手。中国全国,到处响应,已经定期实行。旅外同胞,喜得以手加额,遥祝祖国诸君的胜利。谁知这消息,传到纽约一个巨商耳轮裡,驀地感动。除住宅同几只轮船依然留在公司,此外行厂、货物、地皮、房產,尽数变卖,净得美金八百万元,存放银行,收取子金,為家人日用,孑然附轮便回中国。
船上头等舱二十七间,这巨商住的九号。对面七号,一老一少,像是日本人,又像是菲列滨人,不曾理会。晚膳时,恰好排在一桌,彼此怀疑,只敷衍几句门面话,也不曾深谈。饭罢,同到甲板散步。这巨商听老少两人自谈衷曲,说的一口广东土白,才知也是本国人。赶忙上前,自通姓名,说:「小弟姓夏,双名建威,南直隶应天人氏。向在外国经商。此番因闻祖国有抵制禁约之举,亲往探听实在消息。不知两先生姓氏踪跡,能明以告我否?」那老者答礼道:「小弟姓何,号图南。这是小儿去非。踪跡离奇,非立谈所能罄尽。先生既是热肠人,且请回舱,倒几瓶葡萄酒,作竟夕清谈,当令先生始而怒发上指,继而引巾拭泪,终且破涕為笑。悲欢离沓,情不自禁哩!」
建威骤闻其言,虽是惝怳迷离,无从捉摸,大约必有奇文,便道:「闻君所言,使我欲狂。本是对门居,请更订连牀之约,破此岑寂。何君!何君!当不嫌僕唐突也。」当时回舱,图南呼侍者买六瓶酒,行篋中取叁隻玻璃杯,几种乾脯,邀了建威,开樽共饮。图南黄发皤然,精神弥满,饮兴又极豪爽,连引数巨觥,微有酣意,掀髯作色道:「建威先生,亦知广东猪仔之祸否?」
建威道:「固尝闻之,但未知其究竟。先生忽為此言,殆曾身受其害者?」图南道:「一语破的,先生真是解人。弟自有生以来,未尝一出国门。」指着去非道:「不想為这个孽障,垂白之年,倒要轻身万里,远渡重洋,真是梦不想不到的事。」
建威道:「怎麼是為着令郎呢?」
去非道:「我少就傅训,坐困经生,长而涉猎书传,始知九洲以外,尽有须弥,六合以内,何止拳石?便有乘风破浪之志。所愿不遂,鬱伊坐愁。那年偶出虎门,登高纵览,晚霞落日,绚烂波心,正如万顷琉璃,罩住了无数金星,游衍晃漾,照眼生花,不禁喝采道好。那知就这声中,转过一人,执手问讯。我以其突如其来,尚只虚与委蛇。其人却道:僕平生好观海,不想先生具有同癖。僕只恨家贫累重,不能於汪洋浩瀚中击楫高歌,一吐胸间宿鯁。天天在这浅水滩头,徘徊一晌,便算开了眼界。自谓井底之蛙,将见笑於鲸鯢,那知一夕之内,跬步之间,却与先生相遇,也是前生缘法。我笑说道:「楫转而為帆,帆转而為轮,瀛海茫茫,只如只尺。古人所谓如此风波,公无渡河,足下正不消重吟復唱。那人指道:「面前那枝高深若屋,横广若梁,不就是轮船麼?屡思登舟周览全船的结构,虽不能附之出海,也聊慰一时饥渴。但闻上有洋人,恐不容我辈涉足。因此欲前又止。我於此时笑不可仰,道:足下空具鬚眉,不殊巾幗。洋人是人,我辈不是人不成?何胆馁若此?僕虽不文,愿陪足下一行。那人欣然便就滩边唤枝小划,渡上大轮,先在舱面週游一遍,以次而至二层、叁层,到货舱堆货的所在,再不想入我眼帘,动我感情,竟载了一群上等动物,缩颈蜷足,苦脸愁眉,似有无限苦楚,欲言不敢言之形状。我不禁出神止步,细视他们面目,再不想便是同种同族的同胞,越发欲行不忍。再不想一霎时间,船身晁摇,地轴震动,彷彿竟似开轮。回首望那人时,早已杳无踪影。急急转身踏梯而上,再不想四处舱门,都关得没丝隙缝,竟是升高无路,无计奈何,便随着眾人去做牛做马了一遭。」
建威拍案道:「设计之巧,措词之工,彼辈何尝非人?怎便丧心昧良,至於此极!昔之所谓汉奸,彼辈大约就是缩影了。图南先生一颗掌珠,轻入匪人之手,并且茫无消息,那时怀抱又復如何呢?」图南道:「小儿平日朝出暮归,都有一定的时间,那天过时不归,错疑在戚串家酒食停留,再不想隔日尚无影响。到处探问,都道未尝见面。小弟就觉有些惶惑,还说偌大年纪,不见得被人拐骗。再不想隔了一日,就听见父母失子,兄失其弟,妇失其夫,乱哄哄通城闹动。再不想传来警信,说那天虎门口外,有条火轮船开往巴西,展轮时节,渔舟渡船上,都远远离有哭声。小弟想到以前古巴招工,闹过一回『猪仔』,这番儿小儿必被骗往巴西。」
说到此外,眼圈一红,不觉掉下两行血泪。接着又说:「小弟那时上顾天,下视地,无往或有生人之乐。荆人只生一子,倚门倚閭,呼名出入,朝夕只以眼泪洗面。小弟穷思极想,忽然得个计较。到本省节度使处,请咨游歷,想借钦使的斡旋,还我阶前玉树,再不想踏遍美洲,无从得知实在的下落,便拼得割恩断爱,且把这副老骨头,归正首邱,再不想回到纽约,忽然会合。」
建威引满一杯道:「昔於无意失之,僕為先生悲。」又送过一杯道:「今於无意得之,僕敬為先生贺。但去非兄既到巴西,怎又能来纽约呢?」去非道:「舟中情形,固已奇苦万状,及到工次,未明上工,见星始休。所居之室,矮不类屋,秽不如牢,挨挤不及马棚猪棚,秋霖霉雨,终夜如在水中。日食叁餐,请先生猜是何物?」建威道:「粥饭想不能,自然总是麵包,精美想不能得,自然总是粗糲了。」去非道:「真有粗糲的麵包倒不算苦了。每日每人只给叁合黑料豆,生吞活剥,虽不至和草咬嚼,其实与驴马所差几何?因此无人得饱,亦无人不病。我於平时粗习医理,开轮后自知失检,受人所愚,回想我父我母生我一人,骤然去而不返,不知我父我母若何悲痛,若何感伤?展转踌躇,七昼夜不能合眼,后来立定主意,与其客死中途,不如留此一身,尽出所学,普救眾生,稍赎不孝之罪,或者还有归见我父我母的日子。」
建威肃然动容,停杯不饮。看图南时,两行血泪,又掛胸前。去非也悲不自胜,呜咽半晌,才说道:「每晚工毕,除雨夜不能登山越怜,此外,天天趁着星光月色,遍出寻药,叁鼓始归。顺便带枝败叶,当作薪煤。用罐煎熬,分给我同灾共患至亲至爱苦力之同胞,咳!再不想瘦骨一把,怯不禁风的,叁天要挨六次皮鞭,病者自病,打者自打,我便劳而无功。」建威愕然道:「照这样说,我至亲至爱苦力之同胞莫非屈死不成?」去非痛泪盈睫,泣不成声。图南斟上酒,令去非饮毕,说:「我儿且将下文尽数说给建威先生听。」
去非又叹了几口气说:「我同灾共患至亲至爱苦力之同胞,始初陆续来有万人,病死屈死,到如今所剩不过叁百人,都是疮痍遍体,忧患餘生,进退郎当,莫知究竟,好不可怜人呢!」
建威道:「工作数年,也应薄有餘资,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况在地狱中还有什麼系恋呢!」去非道:「人孰无情,谁又愿葬身海外?无奈按月应领的工资,扣这样,扣那样,总不能如数领足。工限届满,又说某处不曾如法,某处违误限期,责令重新力作。先生请想,不要说迢遥数万里,膏秣之资无从应付,且一身不能自立,如何能作归计呢?」
建威道:「如此,去非兄如何脱身而出?愿闻其详。」去非道:「那就亏着採药的益处了。我每夜入山,志在得药,不问崎嶇险仄,只要有趾一可容,便穷探深入,久而久之,忽於无意中得一僻境,可以脱离巴西的国界。便连夜亡走,一路渴饮岩泉,饥餐山果,幸而未遇逻人,安然出险。展转到了纽约,有限工资,早已不存毫釐。正愁落魄穷途,将為翳桑之续,幸天假奇缘,即於此处与老父相遇,才得附轮东返。」
建威听去非说毕,叹谓图南道:「小弟旅美叁十年,只知美国人待我华工,惨刻无復人理,再不想除此而外,还有巴西。彼昏梦梦,当外交之衝,任保民之责者,胡亦无闻无见,如聋如瞽呢?」图南道:「个人自护之事,不一定倚赖政府。只我同胞能力薄弱,心计又粗,就处处吃人的亏了。譬如小儿,先前能窥破那人的狡计,就不至上船,不上船就不至九死一生,几终身不与父母相见。总怪自失检点。便要倚赖政府,也无从倚赖了。」建威点点头,举杯待饮,早已觴空瓶罄。再一看时,玻璃窗上隐隐透进亮光,便与图南父子作辞,回房略略歇息,重复起身。
从此将抵制问题,分外看得认真,穷日穷夜,与图南假作两造,一辩一驳,研究这裡头的利害得失。
这天船到伦敦,忽来个冠玉少年,后随两女子,首戴绒冠,足穿革履,长裙,羽衣蹁躚,唇无脂而红,脸不粉而白,宛然倾城绝世的美妇人,却又东方不似日本,西方不似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