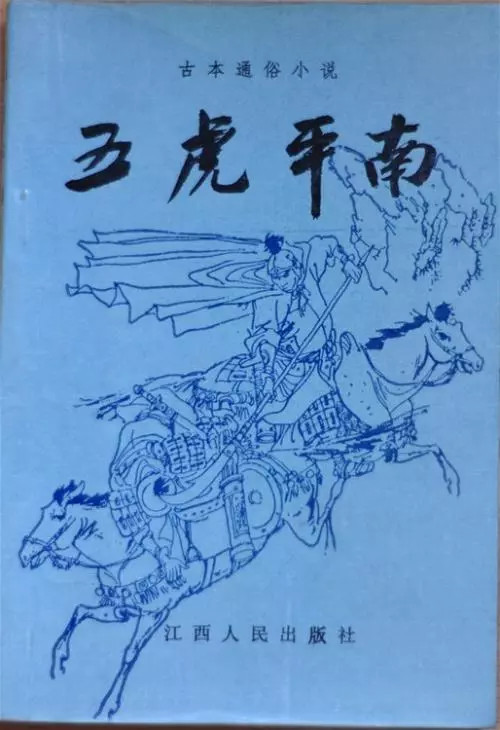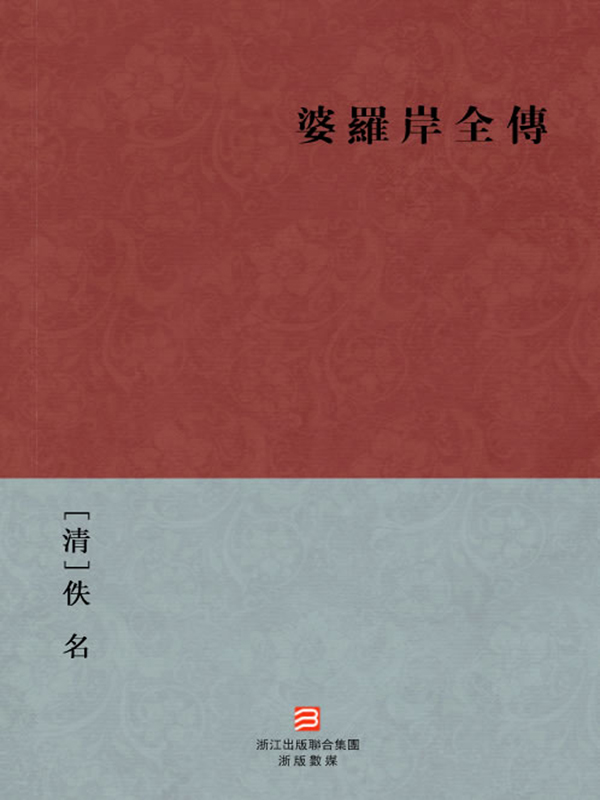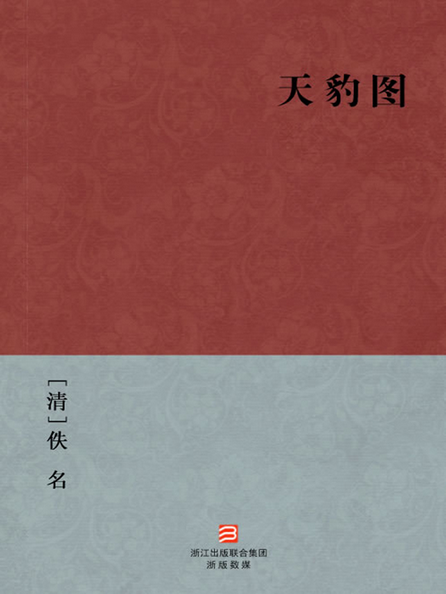陈氏这时喜极而悲,对叁麻子道:「真正感激,只祝你享百年的长寿。」叁麻子摇头道:「我不要活一百八十岁,做讨人嫌的老物,只愿从今以后,少担些惊恐,少受此磨折,便是莫大幸福。」建威问道:「救你那个老者,现在古巴麼?」叁麻子道:「他老人家住处,幽僻清静,轻易无人能到,我临走时,本意约他同行,他再叁不肯,说土人同日人争的政治上权利,繁华都府,军兴时虽不免玉石俱焚,全孙同尽,我这裡决无妨碍,倒劝我也搬去住。我是惊弓的鸟儿,闻了弦声,就觉心惊胆碎,只好同他老人家别过了。」怀祖对建威道:「安土重迁,人情不免,不听老者在古巴已有两代麼?随乡為乡,只好得过且过了。胡大哥暂时别过,隔天再细谈罢。」
携了建威,径回舱中,浩然长叹道:「盛衰兴亡,何代蔑有?这倒不足深论。只恨我同种积衰至此,单晓得忍气吞声,不知道振筋挺脊。凭何因由,酿為习惯,兄台能道其详否?」
那时图南也上来了,接口道:「我们中国人自私自利的心肠,超出於世界人种,只消一身有丝毫私利,就拿全体来供牺牲,也都心甘情愿。但看目前朱大哥同小儿的往事,不就是证据麼?」
怀祖道:「下流社会,见目前不见将来,果真不免此弊,但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岂有圆颅方趾,全然没些良心?但看那班工头,到利害生死的关头,一样结盟联会,互相提携,至死不易其志。像胡大哥后来见朱大哥脱难来归,便慇懃接待,往返相偕,足见初时虽贪小利,也由不知彼中苛的情形,以致冒昧尝试,并不是真肯以自己血肉,献给别人做刀俎之物。若然读书明理,上中社会的人物,自然更无此心了。」去非失笑道:「先生不知中国上中两社会人,还比不上下流社会呢。」
怀祖愕然道:「这是何说?」却听陈氏在问阿金道:「我正忘了,几个大工头后来怎样?」阿金道:「老贝為喂狗不得法,连受几顿毒打,第一个呜呼哀哉。其餘感瘴,害病的害病,只剩一个倪阿四,也是叁分像人,七分像鬼,我走时已堪堪待死了。」陈氏不胜伤感。建威道:「自作孽,不可活,那些怙恶不悛的,何消去可怜他?去非兄所说的从何见来,我亦急於欲闻呢。」
去非道:「中国上流的代表是官绅,中流的代表是士商。官呢,升官发财,是他的目的;钻营倾轧,是他的手段。等到退归林下,好的求田问舍,不好的便武断乡曲,侵吞公款,凭借越大,气燄越盛。小小州县的举人、秀才,便是绅了。若到省会,固然无可作為,并且人数过多。此之所是,彼之所非,此有所党,彼亦有所争,总不肯同心同德,做一件有益的事。
因此虚名虽好,实权倒不及商人。那些商人呢,乘时捷足,争先攘臂,是他的好处。同行嫉妒,互相贬抑,吞并了同类,倒便宜了外人,这是他的坏处。总而言之,私利的心盛,例无团体,团体一解,害公败群之事,相因而至。倒不如下流社会,日谋一饱,夜谋一睡,混混沌沌,还不失赤子之本心。有大力量,大慈悲,当头一棒,顶胸一椎,立地回悟,居然肯疾病相扶,痛痒相关,生死不相残害,请问上中两社会可做得到麼?」
建威道:「凡事不可从一面说,下流中有好人,何尝没有坏人?上中两社会有坏人,何尝没有好人?即如所说团体这一层,拿抵约事来作证,一人高呼,万眾响应。单就目前论,心何尝不齐?志何尝不坚?可见我同种全体,并非不能团结,若然得机得法,几十年和血吞牙,从此也渐渐扬眉吐气了。」
张氏是时也在旁听,说道:「团体的散结,半属男子,一半属之女人。我闻姊姊说,中国女人十九都不识字读书,既不识字读书,单靠天生的知识,现世界上的事事物物,形形色色,那时包罗得尽?就不免牵制丈夫。做男子的内有牵制,外有困难,一身尚顾不过来,那裡能谋全群的公益?团体两个字只成纸上的名词。就是抵约那件事,夜长梦多,正莫知所终哩。」
图南靠在一张椅上,捻鬚微笑道:「我亦云然。」建威道:「君等所见,皆过去之中国,现在名气日昌,女权逐渐回復,女教亦渐兴起。不过处於幼稚时代,有斲丧便退,无斲丧便进,真正极危极险。那斲丧两个字,不定要明侵暗阻,即如只看坏处,不看好处,使人人志衰气颓,以為我同种已进了十八层阿鼻地狱,万万不能再上天堂享幸福。这便叫做斲丧。我辈不明白这个道理,倒也罢了,既然自负前知,提倡扶持,责任正是不轻呢。」怀祖道:「若辈各恃一理,都能抉透同种的病根,大约进则使人敬,退则便受人侮,危机一发,连毫釐都不可差的。」建威点头道:「其然,将无同。」自此往復辨论,借船中做他们的议事堂,倒也颇不寂寞,阿金也长了许多见识。
船过锡兰,怀祖手持望远镜,在甲板上徘徊眺望,恰好图南走来,怀祖指给他看道:「那边隐隐约约巨人的足跡,不是我佛如来当年说法处麼?近数百年宗门歇绝,灯燄不明,七宝楼台,弹指间也做了强宾供养。天行回转,浩劫当前,入世的解脱不来,出世的又何尝不在旋涡中呢?」图南道:「人生无百年,忧乐且相忘,兄台為佛生愁,為禪预虑,真正何苦呢?」
怀祖默然。图南便邀他来找建威,问些美洲的胜景,说些海外的奇闻,怀祖渐渐面有笑容。图南又提直甲板上的问答,建威道:「我佛初地,早被外族点污了庄严,此外南洋叁国,也是佛教极盛的地方,而来缅甸归英,越裳属法,只剩暹逻暂留残喘,然為两大竞争的焦点,后来茫茫,事未可知。综其致亡就衰之跡,虽说别有原因,只是宗尚虚无,遗弃跡象,也就失了立国的本原了。」
怀祖道:「彩石者忘璧,买櫝者还珠,自是彩者买者之咎。信佛而得恶果者,毋乃类是?但我追想先朝,以楚昭之入随,似黎侯之寓卫,式微已甚,性命苟全。因以為利者,犹发叁患二难之议。迫诸逆旅,躡我游魂,莽酋亦弃旧事新,饰辞相紿。
遂致膏涂原野,血溅蒿莱,无争无尤,何為而致此?思之裂眥,言之痛心,迄今枝叶离披,根本摇动,哀我人斯,求如暹逻而不得,又将蹈缅甸、越裳之覆辙。祸福倚伏,得失循环,可胜浩叹麼?」欷歔相对了一回,图南觉有倦意,便先告睡。怀祖、建威也各回房歇息。
不数日,到了香港,图南父子,阿金夫妇,要换船上省,怀祖本是借此游歷的,也要领略五羊的风景,以与建威肝胆相照,意气相投,早结生死交情,坚邀同行。建威无可不可。便自应允。
於是相约买舟,登越王之台,揖赵佗之墓。溯江而上,把罗浮山的十五岭,四百叁十二峰,有胜必搜,无幽不入。游兴未阑,又復舟藤城,弄月鐔江,苍梧碧莲,然入望。建威觉得一尘不染,万象罗胸,块垒尽消,襟抱自远。
怀祖置身峰头,引领四顾,忽然东西乱指道:「那边不是瞿留守、张司马化血之地麼?这边不是焦宣国苦战立功之地麼?
世事如棋,人生若梦,而今又安在哉?」建威劝道:「白云苍狗,变幻无常,我辈留此一身,庶几言人所不能言,為人所不敢為,已往陈跡,兄台何必介介呢?」怀祖口虽无言,却自此鬱鬱不欢,神魂若失。张氏商之建威,来劝怀祖重回广州。刚进栈房,安下行李,瞥见陈氏揭帘而入。张氏惊问道:「我们不过才到,姊姊怎已得知?」陈氏道:「你们这回怎麼去了这许多日子?累我天天只在栈房查消问息,腿也走疼了。」怀祖道:「姊姊如此要紧,有无事故麼?」陈氏道:「没什麼事。五日前『海裡鰍』又到广州来,带的伦敦诸人给你书件,交在我处,我要紧交还你呢。」便在衣袋中取出各书。
怀祖一一看过,见无甚事,才问陈氏道:「『海裡鰍』已否他往?」陈氏道:「尚在香港,听说装货卸货,还有五六天耽搁。」怀祖喜对张氏道:「即今动身到香港,坐原船去游舟山。」陈氏道:「舟山不过一座孤岛,有什麼好玩?」张氏道:「古之伤心别有怀抱,姊姊如何知道呢?」怀祖却已出房去通知建威了。建威道:「图南兄自舟中一别,两次来广,不曾造访,我心已觉负负,这回又过门不入,未免薄情了。并且我之此行,专為抵约而来,兄虽所志不同,何妨姑赴春申,暗為我助,默窥同种之真相,以决将来之进退。过去之事,且请付之达观。」陈氏入问,接口道:「即如图南先生,相处数十日,交谊未尝不深,目前居忧坐困,不一存问,竟自匆匆上道,不怕人抱怨麼?」怀祖、建威同问何事?陈氏坚不肯说,但道去自知之。两人无奈,便同陈氏来望图南。却见阿金正从西边过来,陈氏迎上问道:「昨夜堂讯有无挽回麼?」阿金摇头道:「难!难!」建威十分关心,正待动问,恰已近门。阿金同门者讲明来歷,引进书室坐,陈氏自到上房。
一会,图南进门,神情萧索,意象牢骚,迥非在船时兴高采烈的模样。开口先问道:「两兄这些时间到那裡去来?令我眠思梦想,望眼欲穿!」建威约略告知,急问图南近况。
图南未言先叹道:「老夫承先人遗业,虽比不上郭家的金穴,邓氏的铜山,却也尽堪温饱。自从小儿遇骗,族中有些子弟,知我单丁,几次说辞,要我择人承继,我一概回绝,治装出洋,只荆人支持门户。族中见我日久不归,以為小儿决不无还之望,我偌大年纪,受不得煎熬辛苦,也要為异域之鬼。先用软语来说荆人。见荆人不為所动,便与婢僕内外勾串,把我田房用强硬占,差不多都被夺尽了。荆人投诉房族,袒彼抑此,不為理处。荆人又气又急,卧病在牀,至今行动尚自需人扶掖。今春有姑子自外贸易归来,闻知此事,代為不平,便劝荆人赴县呈告。不意县中不知因何,置霸產不问,只问姑子事不乾已,插身扛讼,把来收禁叁阅月,不问不释。老夫归国,想切已之事,不便叫至亲久累,因令小儿投请收审。谁想见一人押一人,姑子还未释放。好容易左呈右催,昨夜才算提讯,糊裡湖涂,问了几句话,依旧还押。老夫目前内有病妻,外有横祸,方寸中竟无片时寧静。幸亏朱大嫂代我料理医药,大哥又代我传递消息,閒时还婉劝慰,才得撑恃与两兄相见,不然也早累倒了。」怀祖叹道:「晚近官场,不过是苞苴世界,图南兄,不是我把不中的听的话来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