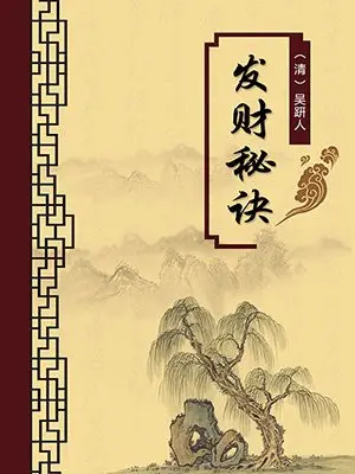却说施子顺从歇业回到京里,依旧开了一个剃头店,又慢慢的巴结上了几位阔京官。人家晓得他是打广东回来的,也有人要打听点广东事情。施子顺便捕风捉影的说了多少。末后说到宋媒婆,怎样的得宠,怎样的有权,候补实缺,老爷们如某人某人,无一不走他的门路,口若悬河的说了一遍。刚刚有一位都老爷听见了,便依着他的话开了一张名单,过了几天,上了一个折子。折子发到军机里,就派了一位侍郎,到广西去查办事件。
说是广西,却就是广东的事,因为怕漏泄了,所以说是广西。等到了广东,便给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原是郑重机密的缘故。但古来说的好:朝内无人莫做官。拿着一位广东抚台,怕没有几个耳目在军机里?这里钦差还不曾请训,广东已是知道了。并且所参的事件,都得了详细。抚台想不出法子,然而他那爱护宋媒婆的意思,还是照旧。把他喊进衙门告知他所以,又叫他搬到别处去住,等钦差来了,好同他硬赖。那晓得宋媒婆却又是一番主意,祇装作一个无可如何的样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他家穷的很,搬到别处去,亦是没有生意。祇有抵桩这条命交给他们罢。他这一回做作,倒把大人并太太弄得没有法子。后来,还是宋媒婆说:“我还有个儿子,心上本想给他捐个小功名,到广西去,自己亦就跟着他去混。无奈总是弄不到钱,祇求大人看着,赏他一个什么东西。或是功牌,或是奖札,能够混饭吃的东西,那是就好了。以后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大人、太太的好处。来世变牛变马,来报效大人、太太。”
大人这时候心里也有点明白,但还拿不定宋媒婆是求告他,还是挟制他?好在这个时候是捐局林立,且又减折上兑,便宜得很,便问了他儿子的名字。大人说“有福”两个字太蠢,改了个“攸福”罢。又问:“他姓甚么,还是就写宋攸福?”宋媒婆道:“随意改个姓罢。他的爹本姓卫,就是卫攸福罢。”大人就招呼出去,填了一张县丞的实收来。又给了三百银子,又替他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广西藩台邹士贤,一封是给边防大臣舒春元的。当日宋媒婆谢了又谢,回到家里收拾东西,暗暗的同着儿子到广西去了。这边的事,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的枕中秘诀,含糊过去,也就不必再提。
却说卫攸福到了广西,赁屋住下。衙参已过,还不敢张扬,打听广东这边无事,纔托大了胆,去投了藩台的信。哪知这位邹大人已经告了病,专等批折回来交卸。这封信虽是投进,竟如石沉大海,连点声息都没有。卫攸福过了半年光景,渐渐的觉得用度大了些,祇得求人去办分府的事。卫攸福虽然到省日浅,幸亏有的是钱,钱却很能说话。果然成功,就分到太平府去。太平府离龙州最近,便趁空一直来找舒大人,投了信。
诸公要晓得,这位舒大人本是一个营兵出身,从前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曾出力打仗。后来慢慢的升了起来,一直做到提督,做了广西的边防大臣。他是大鸦片烟瘾,一天总要四五两烟方得过瘾。这四五两烟,要是起的晚点,就是镇日吸也还吸不了,这不是句瞎话么?不知道这位舒大人,嘴里吸的烟不过一两多一天,那屁股里吸的烟,总得要三四两一天。列位一听这话,要说在下说谎,那有人能屁股里吸烟的哩?还是把烟枪塞在粪门里不成?却不是这个讲究。因为舒大人从前打仗的时候,就有烟瘾。不吸足了,马也骑不上。要吸足了,这一天祇够吃烟了,那里还有功夫打仗?就有一班同营里的老手,传了他一个法子,是把烟膏调厚了,搓成一个条子,或是一个饼子,塞在粪门边。不多一刻,烟膏顺着这一呼一吸的气,就进去了。有时或是用张荷叶,涂上烟膏,贴在那里,也是一样,荷叶上到是净光一点不留。这是吃烟的一个最上的妙法。诸公不信,不妨试试,便晓得在下不是谎话了。
当日舒大人得了这个法子,大是高兴。后来屡屡打仗,却从不曾误事。这时做到边防大臣,一呼百诺,原可以不再用屁股帮忙。但是,他已变成一个两路烟瘾,嘴里无论吸多少,总是无用,非得屁股眼里吃够了不成。在这广西边境日久,幸而边防无事,那带的营头的名额,就十分中不满三分,余外的却是他上了腰了。姬妾众多,这边防大臣能有几个钱,无非是多吞几分名饷。由他而下,一层层剥削下去,非但假名字的自然领不到钱,就是真名字的,也就所领有限。那些勇丁几次鼓噪,舒大人没有法子,祇得把营规格外放松。从此这些兵丁就无恶不作,看看这奷淫掳掠,都是些本等的事了。舒大人弄到后来,也晓得尾大不掉,却又没法子想,祇想换个地方,把这个担子给别人去挑。
现在正是胡弄局的时候,恰巧卫攸福赶来求见。上过手本,投过信,在外边等了有四五个钟头,纔得传见。舒大人还问了制台的好,又道是:“现在没有安插的地方,如果将来边防保案上附个名字,倒还可以。”卫攸福祇得请安谢了,又重复说道:“卑职此来并不在乎薪水,自己晓得年纪轻,是打算借此操练操练的。”舒大人道:“很好,既这样说,我这里有一个文案,他正要进京去。你如能办,就委曲你罢。”卫攸福虽然肚里不见得十分通达,却得宋媒婆替他请先生教了多年。所以寻常的东西,也还看得下去,祇是不晓得格式,动起笔来就不成功。但是要说不能,当下又恐怕把这个事错了,更没有事。这纔打定主意,姑且答应下来再作打算。天下这样顾前不顾后的人,却也不少。当时重复起身谢过,舒大人便招呼他过天就搬进来罢。
卫攸福下来,便去拜前手的文案。这位文案姓虞,名承泽,号子厚,是个湖南人。本是一位佐杂,在边防案里保过了知县。看见舒大人的举动,心上颇为担着忧虑,怕的是一旦边防有事,这些骄兵惰卒一个也不能得力,还怕这营规一坏,这些本营的兵就难免不倒戈相向。因此时常想告退,便托名要进京引见。舒大人祇不放他,后来见他屡次纠缠,纔答应了他,等请到人,就听凭他动身。
当日,听见有个卫攸福来接办,心里十分欢喜,便立刻请见。问答了一回,纔觉得卫攸福文才有限,恐怕敷衍不下去。但是自己要走,也顾不得了。又约计这个把月里没有事,便也放心。随即约定明日交代,交代过后连忙收拾行李,祇耽搁了一天,即行动身。却没有走正路,绕了一路弯子走,为的是怕舒大人还要来追他意思。走了多日,方纔到了广西省城,祇因走得局促,忘记了原保大臣的咨文,心上十分焦躁起来。就有些朋友对他说是没甚要紧,祇要在部办那里多化几两银子,就可以弥补过去了。也是虞子厚一时托大,便也不以为意。耽搁了半个月,张罗了些钱,便取道进京。一路水陆舟车,不必细说。
不一日到了京,住在香炉营二条胡同谢家的宅子里。托人介绍了一位部办,姓史叫伯方。虞子厚拜了他,又托他代办此事。史伯方摇了摇头道:“这事怕不成功,这是一定的规矩,没有原保大臣的咨文,就很费力了。”虞子厚又对他切实拜恳,并说他情愿多花部费的话,史伯方道:“我们的交情,原不在钱上。但是,这件事须要经几道手,转几个弯,少了也怕不成功,大约总得这个数。”说着,便把指头伸了三个出来。虞子厚道:“三百银子有限的很,就是如此。”史伯方道:“好说,你老哥真会说。要是三百银子,老实话,做兄弟的也不犯着伸这指头哩。”
虞子厚这纔晓得,他说三千。当时目瞪口呆,一言不发,满肚里打算:这次带来的盘缠费用一齐交给他,也不到三千银子,这事如何是好?祇得下气低声,再四求告。不料这位史伯方牙齿咬得紧,始终一文不让。虞子厚没法,祇得订期再谈,闷闷的回到寓里。刚下了车,跟班的便来说:“东昌府的专差来了。”虞子厚一面进去,一面问有什么事?跟班的道:“听说叔老太爷的病不好了。”说着专差也走进来,磕了头,起来就把信送上。虞子厚拆开一看,乃是他婶娘的笔迹,心里不禁一惊,脸上早已露出笑容来了。
原来他的叔子名叫尧年,是东昌府的同知,这个缺做过十八年了。东昌府同知的缺,本算山东第一个,叔子手里颇可过活,祇因没有儿女,从前本有要过继虞子厚的话。因为把话说反了,尧年大动其气,就也搁住。从此,叔侄之间格外生疏,便也不通闻问。后来子厚因为要进京引见,弄不到钱,姑且发了一封信,说要想借一千银子,以备出山的话。究竟一本之谊,尧年倒也极看得开,便如数汇到京里。得了回信,纔晓得他住处。尧年年纪高大,早得了一个头晕病,医治总不见好。五月端阳这一日,到府里去贺节,回来一下轿,一个头眩,就跌到在台阶前,头面踫在石头上,已经皮破血出,不省人事。一时七手八脚扶了过去,纔慢慢的还醒过来,还一连发了几个昏。
他婶子晓得家里没人,要出了事更不得了。又觉着上次汇过千金到京,虞子厚就以前有点嫌隙,也可以解释的了。这纔写了一封苦切的信,专人来请子厚。子厚看完信,晓得叔子那里并无弟妹,叔子一死,这分家私明明是自己的了,不禁乐的心花怒开。却因为当着来人,赶紧装出一付发急的样子,连忙把眉头皱起。无奈这两道眉毛忒杀作怪,勉强把他皱起,他又散开来,到弄得子厚没法。祇得一面叫来人出去歇歇,一面招呼家人收拾行李,雇车包站出京,把这引见的事暂且阁起。
第三天一早,便动身取路往山东东昌府来。走了十天半,已是到了。专来的人就先一步回去送信,子厚也就招呼车夫,一直拉到二府衙门口下了车。子厚的意思,以为他叔子是早已做过二七了,因此急不择步往里飞跑,忽见大门口还是两个红灯笼,心里已有点奇异。又到二堂上,看见堂红依旧,格外诧异,还当是新任的陈设,心里却老大有点发毛。刚转进二门,有几个家人站着伺候,子厚也不及问长问短,一径进去。到得厅上,忽然看见他叔子在那里同一个人闲谈。
子厚这一吓非同小可,既已到此,没有法想,祇得上去磕头问好。那一位也就站起来走出去了。尧年道:“辛苦你,路上走了几天?”子厚道:“听得叔父病重,连夜赶来,幸得叔父病已全愈,真是吉人天相。”尧年道:“幸亏这位名医,吃了几贴药就好了。头上也祇擦破了一块皮,今已结疤,并不碍事,并且头晕也不发了。”子厚道:“这位先生手段却是高强得很。”尧年道:“真正想不到,还能与你见面。但是你这次来,你引见的事怎么样了?”子厚道:“正打算验到,就得了这里的信,所以还未办。”尧年道:“你耽阁几天,还是赶紧去办。但是累了你,又耽误了你出山的日期,倒很对不住你呢。这里风大,我们里面坐罢。”子厚祇得跟了进去,见过婶子,寒暄了几句,就忙忙的收拾一间屋子给侄少爷住了。
子厚心里是满肚不开胃,打算这分家私是稳稳的自己独霸,那晓得他又会好了。出来坐了一会,正打算出来,忽然听见小孩子啼哭的声音。子厚心里一跳,忙问道:“是那里的孩子?”尧年道:“是你婶子的主意,替我置了一个妾。倒好,居然一索得男,现在还未满月哩。”子厚听见这句话,真如沸油浇心的一般,一言不发,把这照例恭喜的一句话也忘记了,坐在椅子上,身不由己的乱摇起来。尧年也不在意,还说道:“你一路辛苦,你到房里歇歇去罢。”子厚这纔定了神,辞了出来。到得房里一头倒下,心里十分不快,不免短叹长吁了一回。随即盘算道:“既是如此,我辛苦了这一回,至少千金是要送我的,就譬如我出来张罗盘费罢了。”
转眼住了七八天,子厚说是要回京,尧年也并不挽留,备了一桌酒送了行,又封了五百两银子,还说了多少客气话。子厚虽不十分满意,嘴里也说不出什么,就打算仍旧按站回京去。继又转念道:“我要是沿陆到清江,到上海搭船到广西去,自己去弄这咨文,所化也还有限,总比这部办要我的少多了。这时候,就是卫攸福办不下来,也是一定请了人。难道还会一定拉住我不成?”主意打定,便定了清江浦的车,一直到了清江浦。换了船,过了江,到得镇江。住在船上,心上要想去游一游金山寺,却又因为就是一个人,没甚意兴,便在满街上乱撞。忽然看见江里的炮船、兵轮,还有那炮台上,都挂了旗子。五彩翻飞,映着日光,十分好看。子厚便拉着路上的人问道:“今天是什么事?这般热闹。”那人道:“今天有个外国钦差过境,所以大家接他。大约不多一刻就到了,你瞧热闹罢。”子厚听见,便也不肯回船,祇在岸上踱来踱去的等。
不多一刻,果然远远的望见黑烟一缕,从下游直扬上来。自远而近,看看就将近到了。再看各炮台、炮船上的,都是手忙脚乱的情形。等到船已到得面前,祇听见轰轰的炮响,放了几个之后,忽然停住。正在诧异,又听得震天响的一声,仿佛有一样东西,随着这火药直冲到半天的样子。这时候,不但子厚吃惊,就是别处看的人都觉得奇怪。说时迟,那时快,那件东西早已向人丛里落了下来。大家死命的往外挤,发一声喊,冲倒的、踫翻的人实在不少。还有个买晚米稀饭、下饺子的担子,早已挤倒地下,担上的碗是砸了个粉碎,锅里的稀饭、饺子是泼得满地。正吵嚷间,那件东西已下来了,不是别的,却是一只人手臂。大家挤着看,就有人晓得炮勇出了岔了。再看那炮台上,还在那里放炮,半天一个,好容易放完了炮,又奏西乐。那外国船上也还了炮,却放得甚是爽利。
不多一刻,已经放完,然后启轮上驶,炮台上又吹了一回号,这纔大家卷旗押队,纷纷下来。末后有两个人,用一扇板门抬了一个人跟着走。在板上睡的人,却是鲜血淋漓,不住“啊唷”、“啊唷”的喊。再后就是营官骑了马,嘴里还在那里吩咐人,是叫送到医院去的话。还有两个人拦住马头,跪下道:“这个穆勇,在营当差有年,一向勤慎。此次横遭惨祸,总求不要开他的名字。”祇见那押队的点头道:“自然,自然,这不必说。要是不好,就叫他儿子顶了卯罢。”这两人说了一个“谢”字,便起来往前赶散闲人,让这骑马的如飞去了。
子厚看见,心里暗忖道:怪不得人家说中国的兵没用,这样看起来,真正没用。你看人家放的炮,多么利落。这炮台放了几个炮,还闹出这个岔来,要是真正打仗,那不用说,就是那三十六着的上着了。”一头想,一头走。正想回船,走到三义公门口,祇见一位客人,正同栈房里的茶房吵嘴哩。子厚不免站住,祇听见那客人道:“不拘怎样,中国人也得讲理,外国人也得讲理。我纔到,本来是想住六吉园的,你请我到这里,你怎么说的?东西交给你,是一件东西不得少的。我交给你不是八件吗?怎么就会成了七件呢?”伙计道:“放屁的话,你交给我明明是七件,那里有八件?你想要讹人,那可不行。你要张开眼睛认认招牌,我们是英商的招牌。你也要晓得点轻重,再要胡闹,我就去告诉洋东,办你个无故讹诈。送你到县里去,打你一千板子,枷号在门口示众。你当我办不到么?”
客人道:“洋商的招牌便怎么样?洋东难道也同你一样的不讲理?”伙计道:“别人不少,单是你少,可有这个情理?再者,你这样混闹,是明明毁我们的招牌,替我们回复生意。我们洋东要是生意不好,你可就按着日子赔罢。还有一句老实话对你说,就算洋东真不讲理,你又怎么样?”客人见说他不过,心里也有点怯他,祇得趁势收篷道:“我并不是说你们藏了,怕的是混在别人的行李里去,托你替我仔细找找。找到了自然顶好,找不到难道还要你赔不成?”伙计道:“没有这大工夫。像你这样客人,我不知道接过几十万哩。一个个都要我找东西,我当伙计的还要跑死了呢。”子厚在门外看了多时,忍不住进来解劝那客人道:“省一句罢。”那客人却也不敢再闹,祇得认了晦气,借此收篷。
子厚便同他出来走走,问起他名姓,纔晓得是扬州郭丕基,有事到江阴去的,还是生平第一次出门。两个人谈了一回,扬州人是最喜吃茶的,就约了子厚前去吃茶。素日晓得这里有一个大茶楼,叫做京江第一楼,便一路到了这座茶楼。果然起得壮丽,上面一块横匾是“京江第一楼”五个字。两边是一付对联,上首是“大江东去”,下首是“淮海南来”八个字,写得笔势遒劲。子厚同丕基就打楼梯上拾级而登,拣了一付座头坐下。堂倌泡了两碗茶来,两人细谈心曲。
郭丕基肚里很有点饥饿,就招呼要两分点心。堂倌看了一眼,也不则声,径自去了。郭丕基还当他没有听见,又高声叫喊堂倌,那知仍是不理,提着一个空壶已下了楼去了。郭丕基在扬州教场里吃茶,那堂倌是和气不过的,见了这个情形,不禁大怒,拿筷子把盘子敲得丁丁的响,也没有人理他。停了一刻,堂倌又上来冲开水,郭丕基厉声道:“同你说话,怎么不理?难道你耳朵是聋的么?”堂倌道:“我耳朵倒不聋,你眼睛是瞎了。”郭丕基道:“我同你说话,你不理,倒反顶撞,是个什么道理?”堂倌道:“楼上楼下,客人如许之多,也有个先来后到的。点心好了,自然要端上来。要早也早不来,难道我留着不卖,留着自己吃么?吵也无用,总而言之,我们馆里不能为一个人升火。”郭丕基道:“放屁!”正要往下再说,堂倌也怒道:“客人放尊重些。”立刻把水壶往桌上一放,又道:“这是洋商的牌子,你要张开眼睛看看,不要说你,任凭什么人,都不敢在这里撒野,你还不配在这里发狂哩!你嫌不好,你简直滚出去罢,这里不稀罕你的钱。你要逞凶,楼下的巡捕现成,你试一试看!”
郭丕基气的发抖,骂道:“混帐东西,敢这样混帐,我打你这个王八蛋。”正想站起来打,堂倌早已走到窗子门口,朝楼底下呼哨了一声。祇见一个戴红缨大帽,手里提了一个根子走上楼来,却是中国人。堂倌把手指着郭丕基,对他说道:“他在这里混闹。”巡捕便走上来,一把辫子拖着要走。子厚着急,忙上来解劝,陪着笑脸央告巡捕。巡捕道:“这是向来规矩,没有情分的。”
这个时候,吃茶的也不少了。有一个有胡子的人,上来对巡捕说了几句,这个人是认得巡捕的,巡捕方纔答应了,招呼叫他们会帐滚罢。堂倌便走过来道:“两碗茶九十二,点心两分,一百六十,共计二百五十八,又打破盘子一个,作钱六十,小帐六十,统共三百八十文。”郭丕基道:“这是个小酱油碟子,不过十个钱。况且,我并不曾吃点心。”堂倌道:“我们家伙都有定价。点心已是做了,你不吃不干我事,难道留给狗吃么?”子厚晓得明是讹诈,又晓得郭丕基舍不得,心上又要紧离开这里,便连忙替会了帐,拉着郭丕基下楼。堂倌还在那边笑骂,这边也祇得佯为不理去了。
走到街上,子厚道:“万想不到,这堂倌如此可恶。凭仗着洋人的势,就如此欺负人,实在可恨!”郭丕基道:“这种堂倌,要在我们扬州,早已被人打死了。他这样的混帐,如何他这个馆子里还有许多生意?可也作怪。大约本地人是被他欺负惯的。我想,自洋人进来以后,我们中国的人吃的亏真正不小,总得要想个法子出口气纔好。”子厚道:“这件事,照现在情形看起来,怕没有翻身的了。”郭丕基道:“其实,总是中国人不好。他的洋布有什么好,偏要买他的,难道我们中国自己织的布,穿在身上就有甚芒刺在背?他的洋货有什么好,难道我们中国的土货,用在身边就显出拙陋难看?即如洋油这件东西,他的气味是臭而不可闻的,我是最不欢喜。无奈人家都要点他,说是加倍的亮,这真是个天意。要是大家不买他的东西,他自然也不来了。要这个样子一直不改,十年之后,你看样子罢!”
一路谈着,还走不到半里路光景,看见前面围个圈子,闲人挤了不少。想进圈子去看看,那里还挤得上?忽然间围子散了,几个人没命的冲了出来,就有个巡捕似的将一人辩子扭着,望前拖去,后面还跟了无数闲人。有几个像发恼的,有几个像着急的,有几个说说笑笑,像是不知轻重的,闹烘烘的一群过去。子厚、丕基立在那里,是晓得他们的利害,也不敢前去多事,随后人也清了。
有一个画空圈抹鼻头的读书人,在那里低着头,踱得几步绝好的方步,直踱到子厚身旁,这人还不觉着。听他嘴里念着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难道竟没有王法的么?唉,放屁!放屁!”这人的“屁”声未绝,子厚实在忍不住,便道:“仁兄请了。”这人听见,连忙将眼镜除下,似揖非揖的向着子厚道:“雪斋兄几时来的?”原来这人号唤仁慕,听子厚叫他仁兄,声音又与他的朋友雪斋相似;况且一副近视眼,除下眼镜,更加弄不清楚,所以竟瞎缠了一回。子厚见他是斯文一派,也就含含糊糊的答应了几句。
这人郄兴高采烈的说道:“方纔被巡捕拉去的一个人,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弟。祇因抽上几口鸦片烟,跑到洋街上来,到这烟间里面开了一只灯。后来还帐的时候,拿出一个小洋夹,却放着两角洋钱,拿来交与堂倌。堂倌说不出嫌他钱少,面上就装着不愿意的样子。再把角子细看,却是奉天省造的,就要拿去掉换。但这小洋夹里没有第三角洋钱,祇得嘴里说道,奉天不是中国的省分么,你倒不要他起来?吵了一回,这堂倌就喊了巡捕,拖出来拉到巡捕房去了。巡捕果然强横,这鸦片烟有何好处?要去吃他则甚?弄到如此狼狈,不知他懊侮不懊悔?”子厚道:“堂倌的权力,洋街上竟大到如此。”这人道:“不是堂倌的硬,开烟间的人,说在洋人处做过细崽,会说几句洋泾说话,同巡捕头脑也有些认识,所以他们的堂倌,也靠了些些洋势,就耀武扬威的做起事来。”
两人讲得起劲,那郭丕基饿得难受,将子厚的衣裳拉上几拉。子厚觉着,就与这人告别。一路行来,没找着个点心店,看见一个山芋担子,买了二十钱山芋吃了。一头吃,一头说道:“我明天是要回家去了。”子厚道:“不是你要到江阴去吗?”郭丕基道:“不去了,不去了。我本是要到江阴找一个人,这纔出家门口四十里地,就是这个样子。若再走远些,我还有命吗?况且,出门也要取个吉利,这种不吉利,还不如回去好。”子厚道:“那也不然,有正事总是要办的。我还要到广西去呢,这路不更远了吗?”郭丕基道:“我这人真糊涂,也没有问你到广西去做什么事?”子厚道:“我是一个知县,因为要到广西去请咨文引见,这纔要去。”
郭丕基惊骇道:“原来是一位大老爷,我还不晓得。我请教大老爷一声,怎样就可以做知县呢?”子厚道:“有好几种不等,并不一样。”郭丕基道:“请你老人家说给我听听。”子厚道:“有的是中了进士,放的知县,叫做即用知县。这一班从前是极好的,所以叫做即用,后来各省人多,也压下班去了。有的是中了举人,三科之后,挑选一个知县,这叫做大挑知县。有的是拔贡考二等的,叫做拔贡知县。有的是优贡考一等的,叫做优贡知县。有的是打仗有功,或是出洋,或是办河保举的,这叫做劳绩知县。有的是银子捐的,叫做捐班知县,这些名目多着哩。”郭丕基道:“譬如捐的,要多少钱?”子厚道:“统通在内,也得四千银子。”郭丕基道:“很上算。我看见我们江都县的老爷出来,坐着四人大轿,前拥后卫,打着锣,开着道,又是红伞,又是街牌,他坐在轿子里自在得很,很羡慕他。听说他做一年,有好几万的银子呢。照你这样说,那不是几十倍的利钱么?”子厚笑道:“他是实缺,我那里能够?我们是候补,到了省,不知还要等多少年哩。”一路说说笑笑,早到了栈房。子厚便辞了郭丕基,自己回到船上。家人已打听得,明天有招商局的轮船,子厚便招呼归着东西。到了明日,便搭船到上海,取路往广西去了。
要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