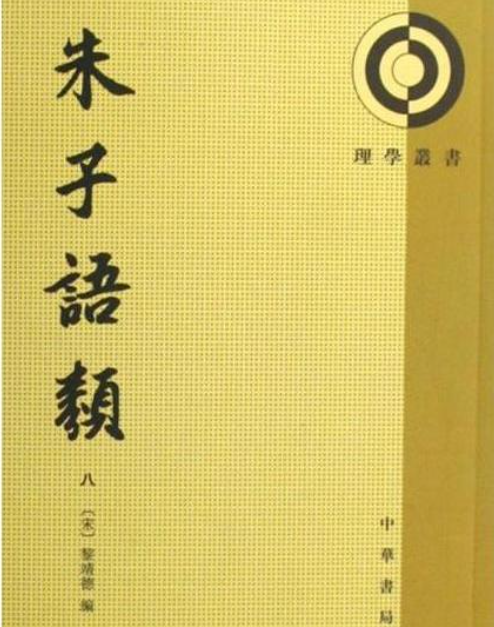陈君举陈同父叶正则附。
先生问德粹:「去年何处作考官?」对以永嘉。问:「曾见君举否?」曰:「见之。」曰:「说甚话?」曰:「说洪范及左传。」曰:「洪范如何说?」曰:「君举以为读洪范,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则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过于皇极,则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还他题目:一则五行,二则五事,三则八政,四则五纪,五则皇极;至其后庶征、五福、六极,乃权衡圣道而着其验耳。」又问:「春秋如何说?」滕云:「君举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谓其所载事多与经异,此则有说。且如晋先蔑奔,人但谓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书「奔」以示贬。』」曰:「是何言语!先蔑实是奔秦,如何不书『奔』?且书『奔秦』,谓之『示贬』;不书奔,则此事自不见,何以为褒?昨说与吾友,所谓专于博上求之,不反于约,乃谓此耳。是乃于穿凿上益加穿凿,疑误后学。」可学因问:「左氏识见如何?」曰:「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知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使孔子论此,肯如此否?尚可谓其好恶同圣人哉!又如论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是何等言谈!」可学曰:「此一事,公羊议论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可学又问:「林黄中亦主张左氏,如何?」曰:「林黄中却会占便宜。左氏疏脱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殃苦刘歆。昔吕伯恭亦多劝学者读左传,尝语之云:『论孟圣贤之言不使学者读,反使读左传!』伯恭曰:『读论孟,使学者易向外走。』因语之云:『论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走!读论孟,且先正人之见识,以参他书,无所不可。此书自传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没理会。』大抵春秋自是难看。今人说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且以胡文定传语之。」
陈君举得书云:「更望以雅颂之音消铄群慝,章句训诂付之诸生。」问他如何是雅颂之音?今只有雅颂之辞在,更没理会,又去那里讨雅颂之音?便都只是瞒人!又谓某前番不合与林黄中陆子静诸人辨,以为「相与诘难,竟无深益。盖刻画太精,颇伤易简;矜持己甚,反涉吝骄」。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他说「刻画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说得太分晓,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会不得,被众人拥从,又不肯道我不识,又不得不说,说又不识,所以不肯索性开口道这个是甚物事,又只恁鹘突了。子静虽占奸不说,然他见得成个物事,说话间便自然有个痕迹可见。只是人理会他底不得,故见不得,然亦易见。子静只是人未从,他便不说;及钩致得来,便直是说,方始与你理会。至如君举胸中有一部周礼,都撑肠拄肚,顿着不得。如游古山诗又何消说着他?只是他稍理会得,便自要说,又说得不着。如东坡子由见得个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开心见胆,说教人理会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静!子静却是见得个道理,却成一部禅,他和禅识不得。」
金溪之学虽偏,然其初犹是自说其私路上事,不曾侵过官路来。后来于不知底亦要强说,便说出无限乱道。前辈如欧公诸人为文,皆善用其所长;凡所短处,更不拈出来说,所以不见疏脱。今永嘉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头没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说一截话,终不说破是个甚么;然皆以道义先觉自处,以此传授。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胡季随亦从之问学。某向见季随,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无主人,所以纔闻他人之说,便动。季随在湖南颇自尊大,诸人亦多宗之。凡有议论,季随便为之判断孰是孰非。此正犹张天师,不问长少贤否,只是世袭做大。正淳曰:「湖南之从南轩者甚众且久,何故都无一个得其学?」曰:「钦夫言自有弊。诸公只去学他说话,凡说道理,先大拍下。然钦夫后面却自有说,诸公却只学得那大拍头。」
因说乡里诸贤文字,以为「皆不免有藏头亢脑底意思。有学者来问,便当直说与之,在我不可不说。若其人半间不界,与其人本无求益之意,故意来磨难,则不宜说。外此,说尽无害。我毕竟说从古圣贤已行底道理,不是为奸为盗,怕说与人。不知我说出便有甚罪过?诸贤所见皆如此。祇缘怕人讥笑,遂以此为戒,便藏头不说。某与林黄中争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说,不以为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说及某人,乡里皆推其有所见。其与朋友书,言学不至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处,则学为无用。先生曰:「近来人自要向高说一等话。要知初学及此,是为躐等。诗人这句自是形容文王圣德不可及处。圣人教人,何尝不由识入来!」
或曰:「永嘉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因说永嘉之学,曰:「张子韶学问虽不是,然他却做得来高,不似今人卑污。」又曰:「上蔡多说知觉,自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学蒙。
「古人纪纲天下,凡措置许多事,都是心法从这里流出,是多少正大!今若去逐些子搜抉出来评议,恐不得。凡看文字,也须待自有忽然凑合见得异同处。若先去逐些安排比并,便不是。」因问:「君举说汉唐好处与三代暗合,是如何?」曹曰:「亦只是事上看,如汉初待群臣不专执其权,略堂陛之严,不恁地操切;如财散于天下之类。」曰:「这也自是事势到这里,见得秦时君臣之势如此间隔,故汉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萧何是多少功劳!几年宰相,一旦系狱,这唤做操切不操切?又如周勃终身有功,后来也下狱对问。又如贾谊书中所说是如何?财用那时自宽饶,不得不散在郡县。且如而今要散在郡县,得也不得?上面又不储蓄财赋闲在那里,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时挨展将去。将汉初来看,要散之郡县得否?这只是闲说。第一项最是养许多坐食之兵,其费最州郡自是州郡底,如许多大军,见如何区处?无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无之兵。如州郡兵还养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会教他去攀些弓,射些弩,教他做许多模样,也只是不忍将许多钱粮白与他。到有冢杀时,你道他与你去冢杀否?只是徒然!」问:「君举曾要如何措置?」曰:「常常忧此,但措置亦未曾说出。」问:「看唐事如何?」曰:「闻之陈先生说,唐初好处,也是将三省推出在外。这却从魏晋时自有里面一项,唐初却尽属之外,要成一体。如唐经祸变后,便都有诸王出来克复,如肃宗事。及代宗后来,虽是郭子仪,也有个主出来。」曰:「三省在外,怕自隋时已如此,只唐时并属之宰相。诸王克复,代宗事,只是郭子仪,怕别无诸王。唐官看他六典,将前代许多官一齐尽置得偏官,如何不冗?今只看汉初时官如何,到得元成间如何,又看东汉初如何,到东汉末时如何,到三国魏晋以后如何:只管添,只管杂。」
器远言:「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着实,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终于败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说,某尚及见前辈都不曾有这话。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曾将这个分作两事。如所谓『推倒墙,撞倒壁』,如此粗话,那时都恁地粗,却有好处。南渡时,有许多人出来做得事。经变故后,将许多人都推折了。到而今却是气卑弱了,凡事都无些子正大,只是细巧。」曰:「陈先生要人就事上理会教实之意,盖怕下梢用处不足。如司马公居洛六任,只理会得个通鉴;到元佑出来做事,却有未尽处,所以激后来之祸。如今须先要较量教尽。」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说话。如温公所做,今只论是与不是,合当做与不合当做,如何说他激得后祸!这是全把利害去说。温公固是有从初讲究未尽处,也是些小事。如役法变得未尽,只是东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时节已自极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温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场出丑。今只将纸上语去看,便道温公做得过当。子细看那时节,若非温公,如何做?温公是甚气势!天下人心甚么样感动!温公直有旋乾转坤之功。温公此心可以质天地,通幽明,岂容易及!后来吕微仲范尧夫用调停之说,兼用小人,更无分别,所以成后日之祸。今人却不归咎于调停,反归咎于元佑之政。若真是见得君子小人不可杂处,如何要委曲遮护得!蔡确也是卒急难去,也是猾。他置狱倾一从官,得从官;置狱倾一参政,得参政;置狱倾一宰相,得宰相。看温公那时,已自失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后既加罪于蔡确之徒,论来安石是罪之魁,却于其死,又加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道要委曲周施他。如今看来,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当显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须是明显其不是之状。若更加旌赏,却惹得后来许多群小不服。今又都没理会,怕道要做朋党,那边用几人,这边用几人,不问是非,不别邪正,下梢还要如何?某看来,天下事须先论其大处,如分别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于中间酌量轻重浅深施用。」
器远言「陈丈大意说,格君,且令于事上转移他心下归于正。如萧何事汉,令散财于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爱民之心。说北齐宣帝」云云。曰:「欲事君者,岂可以此为法?自元魏以下至北齐,最为无纲纪法度,自家却以为事君法!」
永嘉看文字,文字平白处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寻节目以为博。只如韦玄成传庙议,渠自不理会得,却引周礼「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注云:「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遂谓周后稷别庙。殊不知太祖与三昭三穆皆各自为庙,岂独后稷别庙!又云:「后稷不为太祖,甚可怪也!」
季通及敬之皆云:「永嘉貌敬甚及与宫祠,乃缴之,云:『朱某素来迂阔,臣所不取。但陛下进退人才,不当如此。』」以问先生,先生云:「不曾见此文字。怎见得。」
德粹问陈君举福州事,曰:「如此,只是过当。作一添倅,而一州之事皆欲为之。益之初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下不厚事也。』初九欲为九四作事,在下本不当处厚事。以为上之所任,故为之而致元吉,乃为之。又不然,不惟己不安,而亦累于上。璘录云:「初九上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尽善而后无咎。若所作不尽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释之曰:『下不厚事也。』盖在下之人不当重事。若在下之人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尽善,自应有咎。」向编近思录,说与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则有时而有,岂可不书以为戒?』及后思之,果然。」璘录少异。
陈同父纵横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为讽说,反被他玩。陈同父。
说同父,因谓:「吕伯恭乌得为无罪?恁地横论,却不与他剖说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里。今来伯恭门人却亦有为同父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举只道某不合与说,只是他见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两边去,如何恁地含糊鹘突!某乡来与说许多,岂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这里,而今人虽不见信,后世也须有人看得此说,也须回转得几人。」又叹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圣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污浊,要担头出不得!」
同父才高气粗,故文字不明莹,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先生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直卿言:「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
陈同父祭东莱文云:「在天下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先生曰:「若如此,则鸡鸣狗盗皆不可无!」因举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虑?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又云:「同父在利欲胶漆盆中。」
郑厚艺圃折衷,当时以为邪说,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权。其说之行,犹使人知君臣之义。如陈同父议论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窥圣人,谓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逊尔。同父亦是于汉唐事迹上寻讨个仁义出来,便以为此即王者事,何异于此?
因言:「陈同父读书,譬如人看劫盗公案,看了,须要断得他罪,及防备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断他罪,及防备禁制他;只要理会得许多做劫盗底道理,待学他做!」
或问:「同父口说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这只是见不破。只说个是与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杀身,也是合当做底事。」
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
陆子静分明是禅,但却成一个行户,尚有个据处。如叶正则说,则只是要教人都晓不得。尝得一书来,言世间有一般魁伟底道理,自不乱于三纲五常。既说不乱三纲五常,又说别是个魁伟底道理,却是个甚么物事?也是乱道!他不说破,只是笼统恁地说以谩人。及人理会得来都无效验时,他又说你是未晓到这里。他自也晓不得。他之说最误人,世间呆人都被他瞒,不自知。叶正则。
叶正则说话,只是杜撰。看他进卷,可见大略。
叶进卷待遇集毁板,亦毁得是。
叶正则作文论事,全不知些着实利害,只虚论。因及许多云云。又见一文论社仓事。戴肖望尚有些实说,然不是如此。叶则都是闲说。
见或人所作讲义,不知如何如此。圣人见成言语,明明白白,人尚晓不得,如何须要立一文字,令深于圣贤之言!如何教人晓得?戴肖望比见其湖南说话,却平正。只为说得太容易了,兼未免有意于弄文。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