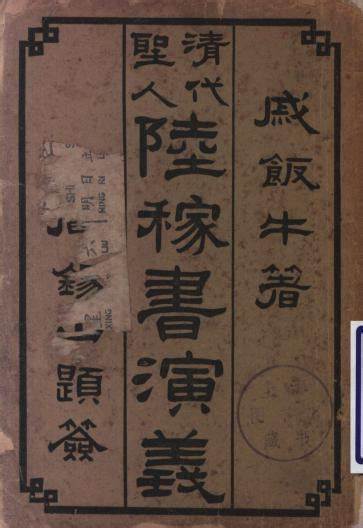吕伯恭
因说南轩东莱,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寿昌曰:「不然。」先生适闻之,遂问如何。曰:「南轩非寿昌所敢知,东莱亦不相识。但以文字观之,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先生然之。寿昌。
某尝谓,人之读书,宁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宁失之低,不可失之伯恭之弊,尽在于巧。
伯恭说义理,太多伤巧,未免杜撰。子静使气,好为人师,要人悟。一云:「吕太巧,杜撰。陆喜同己,使」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柄。
或问:「东莱谓变化气质,方可言学。」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则以为学乃能变化气质耳。若不读书穷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计较于昨非今是之间,恐亦劳而无补也。」
伯恭更不教人读论语。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论语是非问者。伯恭曰:「公不会看文字,管他是与非做甚?但有益于我者,切于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须有一个是与不是,是处便是理,不是处便是咈理,如何不理会得?赐。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吕丈旧时性极褊急,因病中读论语,于此有省,后遂如此好。广录云:「伯恭言,少时爱使性,才见使令者不如意,便躁怒。后读论语云云。某尝问路德章:『曾见东莱说及此否?』」
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诗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礼制度都不能言。邵数亦教季通说过一遍,又休了。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向尝与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据「治」字于理为是,他硬执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缘他先读史多,淳录作「读史来多而」。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李德之问:「系辞精义编得如何?」曰:「编得亦杂,只是前辈说话有一二句与系辞相杂者皆载。只如『触类而长之』,前辈曾说此便载入,更不暇问是与不是。」
或问系辞精义。曰:「这文字虽然是裒集得做一处,其实于本文经旨多有难通者。如伊川说话与横渠说话,都有一时意见如此,故如此说。若用本经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带得后。如程先生说孟子『勿忘,勿助长』,只把几句来说敬。后人便将来说此一章,都前后不相通,接前不得,接后不得。若知得这般处是假借来说敬,只恁地看,也自见得程先生所以说之意,自与孟子不相背驰。若此等处,最不可不知。」
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之佞臣。
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有人问他『忠恕』,杨氏侯氏之说孰是?他却说:『公如何恁地不会看文字?这个都好。』不知是如何看来。他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恁地时他方说不是。」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
先生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下面工夫又皆疏空。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可惜子约死了,此论至死不曾明!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问:「东莱大事记有续春秋之意,中间多主史记。」曰:「公乡里主张史记甚盛,其间有不可说处,都与他出脱得好。如货殖传,便说他有讽谏意之类,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间事是还是,非还非,黑还黑,白还白,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决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处,也只还他未是,如何硬穿凿说!」木之又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道理,全不似公谷。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如载刘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极精粹底。至说『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载之事实否?」曰:「也未必一一实。」子升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纂齐以后之书。」又问:「此还是当时特故撰出此等言语否?」曰:「有此理。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看此等书,机关熟了,少间都坏了心术。庄子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者,道之所不载也。』今浙中于此二书,极其推尊,是理会不得。」因言:「自孟子后,圣学不传,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如荀卿说得头绪多了,都不纯一。至扬雄所说底话,又多是庄老之说。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至柳子厚却反助释氏之说。因言异端之教,汉魏以后,只是老庄之说。至晋时肇法师,释氏之教始兴。其初只是说,未曾身为。至达磨面壁九年,其说遂炽。」
看大事记,云:「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大胜诗记。此书得自由,诗被古说压了。」
「伯恭解说文字太尖巧。渠曾被人说不晓事,故作此等文字出来,极伤事。」敬之问:「大事记所论如何?」曰:「如论公孙弘等处,亦伤太巧。」
伯恭大事记辨司马迁班固异同处最好。渠一日记一年。渠大抵谦退,不敢任作书之意,故通鉴左传已载者,皆不载;其载者皆左传通鉴所无者耳。有太纤巧处,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人。伯恭少时被人说他不晓事,故其论事多指出人之情伪,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至五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见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因说伯恭少仪外传多琐碎处,曰:「人之所见不同。某只爱看人之大体大节,磊磊落落处,这般琐碎便懒看。伯恭又爱理会这处,其间多引忍耻之说,最害义。缘他资质弱,与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广得大。想其于忠臣义士死节底事,都不爱。他亦有诗,说张巡许远那时不应出来。」
伯恭是个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个轻儇底人?如省试义大段闹装,说得尧舜大段胁肩谄笑,反不若黄德润辞虽窘,却质实尊重。馆职策亦说得慢,不分晓,后面又全无紧要。伯恭寻常议论,亦缘读书多,肚里有义理多。恰似念得条贯多底人,要主张一个做好时,便自有许多道理,升之九天之上;要主张做不好时,亦然。
或言:「东莱馆职策、君举治道策,颇涉清谈,不如便指其事说,自包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缘里面说大原不分明,只自恁地依傍说,更不直截指出。」
伯恭文鉴,有正编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众人以为佳者;有其文虽不甚佳,而其人贤名微,恐其泯没,亦编其一二篇者;有文虽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已亡一例,后来为人所谮,令崔大雅敦诗删定,奏议多删改之。如蜀人吕陶有一文论制师服,此意甚佳,吕止收此一篇。崔云:『陶多少好文,何独收此?』遂去之,更参入他文。」
先生方读文鉴,而学者坐定,语学者曰:「伯恭文鉴去取之文,若某平时看不熟者,也不敢断他。有数般皆某熟读底,今拣得也无巴鼻。如诗,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载那衰飒底。把作好句法,又无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无好意思;把作劝戒,又无劝戒。」林择之云:「他平生不会作诗。」曰:「此等有甚难见处?」淳录云:「伯恭文鉴去取,未足为定论。」
东莱文鉴编得泛,然亦见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历一篇,说浑天亦好。
伯恭所编奏议,皆优柔和缓者,亦未为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旧所编。后修文鉴,不止乎此,更添入。
尝语吕丈编奏议,为台谏怀挟。
伯恭祭南轩文,都就小狭处说来,其文弱。
吕伯恭文集中如答项平父书,是傅梦泉子渊者;如骂曹立之书,是陆子静者。其它伪者想又多在。
伯恭亦尝看藏经来。然甚深,不见于言语文字间。有些伯术,却忍不住放得出来,今害人之甚!
「可怜子约一生辛苦读书,只是竟与之说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间所寄书,犹是论『寂然不动』,依旧主他旧说。时子约已死。它硬说『寂然不动』是耳无闻,目无见,心无思虑,至此方是工夫极至处。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几多分晓!某尝答之云:『洪范五事: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方得!还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晓,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释氏之坐禅入定,便是无闻无见,无思无虑。」曰:「然。它是务使神轻去其体,其理又不同。神仙则使形神相守,释氏则使形神相离。佛家有『白骨观』,初想其形,从一点精气始,渐渐胞胎孕育,生产稚乳,长大壮实,衰老病死,以致尸骸胖胀枯僵,久之化为白骨。既想为白骨,则视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厌弃脱离而无留恋之念也,此又释氏之最下者。」以下子约。
「今日得子约书,有『见未用之体』一句,此话却好。」问:「未用,是喜怒哀乐未发时,那时自觉有个体段则是。如着意要见他,则是已发?」曰:「只是识认他。」士毅。广录云:「近得子约书,有『未发之本体』一句,此语甚好。人须是看得这个分晓,始得。」
答子约书云:「目下放过了合做底亲切工夫,虚度了难得少壮底时日!」
观吕子约书,有论读诗及刘壮舆字画一段。曰:「某之语诗,与子约异。诗序多附会,须当观诗经。渠平日写书来,字画难晓。昔日刘元城戒刘壮舆,谓此人字画不正,必是心术不明,故写此一段与之。子约书又云:「昨读左传刘康公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下云:『君子勤礼,小人尽力』,见得古人说道理平实,不张皇,而着实下手,随贵贱高卑皆有地位。非如后世此之为可,而此之为不可,人有所不可为,道有所不可行也。」先生曰:「此一段议论却好。」
吕子约死,先生曰:「子约竟赍着许多鹘突道理去矣!」
先生问:「吕子约近况如何?」曰:「吕丈在乡里,方取其家来,骨肉得团聚,不至落寞。」曰:「得渠书,多说仙郡士友日夕过从,以问学为乐。罪大责轻,迁客得如此,过分矣。亦是仙郡士友好学乐善,岂非衡州流风余韵所及乎!」嗟叹久之。又问曰:「识章茂献否?」曰:「尝见之,亦蒙教诲。」曰:「江西士大夫如茂献亦难得。」又言:「吴伯丰有见识,力学不倦。」祖道因言伯丰自植立事。曰:「此某知之有未尽,不意伯丰能如此。」
伯恭门徒气宇厌厌,四分五裂,各自为说,久之必至销歇。子静则不然,精神紧峭,其说分明,能变化人,使人旦异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以下门人。
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
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若迁则皆宗孔氏,如于夏纪赞用行夏时事,于商纪赞用乘商辂事,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盖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迁之意脉恐诚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谓迁能学孔子,则亦徒能得其皮壳而已。假使汉高祖能行夏时,乘商辂,亦只是汉高祖,终不可谓之禹汤。此等议论,恰与欲削乡党者相反。
先生出示答孙自修书,因言:「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动静间,全是这个本子,卒乍改换不得。如吕氏言汉高祖当用夏之忠,却不合黄屋左纛。不知纵使高祖能用夏时,乘商辂,亦只是这汉高祖也,骨子不曾改变,盖本原处不在此。」
伊川发明道理之后,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议论,又费力,只是云不要矫激。遂至于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如严子陵是矫激分明,吕伯恭作祠记,须要辨其非矫激。想见子陵闻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节,自前汉之末,如龚胜诸公不屈于王莽者甚多,汉书末后有传可见。光武是一个读书识道理底人,便去尊敬严子陵。子陵既高蹈远举,又谁恤是矫激不是矫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严子陵祠记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说得好!其议论什么正大!往时李太伯作袁州学记说崇诗书,尚节义,文字虽粗,其说振厉,使人读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近日浙中文字虽细腻,只是一般回互,无奋发底意思,此风渐不好。其意本是要惩艾昔人矫激之过,其弊至此。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又说:「固是矫激者非。只是不做矫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郑子上问:「昨日所说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矫激之名,莫学颜子之浑厚否?」曰:「浑厚自是浑厚。今浙中人只学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浑厚。浑厚是可做便做,不计利害之谓。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如陈仲弓送宦者葬,所谓有仲弓之志则可,无仲弓之志则不可。」因说,东汉事势,士君子欲全身远害,则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纵横,如何畏祸不与他理会得!若未免仕,只得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若既要为大官,又要避祸,无此理。
问:「前蒙赐书中,有『近日浙中学者多靠一边』,如何?」曰:「往往泥文义者只守文义,沦虚静者更不读书。又有陈同父一辈说又必求异者。某近到浙中,学者却别,滞文义者亦少。只沈晦叔一等,皆问着不言不语,说着文义又却作怪。」
近日浙中一项议论,尽是白空撰出,觉全捉摸不着。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却要起甚楼台,就上面添一层,又添一层,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实全不济事。又云:「空撰出许多说话,如掜眼生花。」
叔度与伯恭为同年进士,年又长,自视其学非伯恭比,即俯首执子弟礼而师事之,略无难色,亦今世之所无耳。叔度。
叔度应童子进士词科,然竟以不能随世俛仰,不肯一日置其身于仕路也。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无一人敢为非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