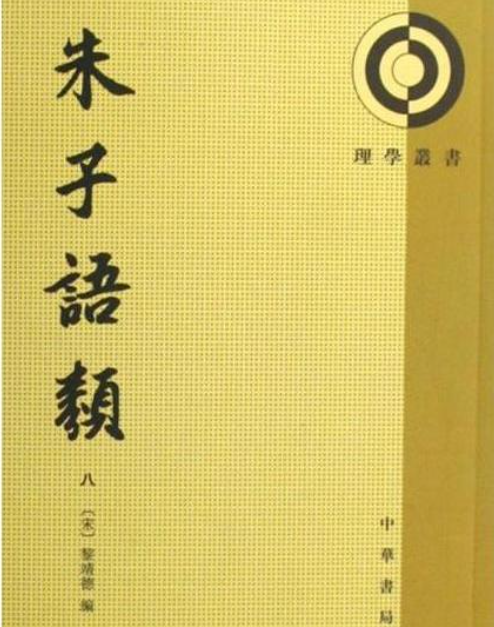易十二
系辞下
问:「『八卦成列』,只是说干兑离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类』,如何?」曰:「所谓『成列』者,不止只论此横图。若干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类』。」学履。
问:「『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干兑离震之象,未说到天地雷风处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项看,『象在其中』,又是逐个看。」又问:「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画到三画处,其中逐一分,便有干兑离震之象否?」曰:「是。」学履。
问:「『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变』字是总卦爻之有往来交错者言?『动』字是专指占者所值,当动底爻象而言否?」曰:「变是就刚柔交错而成卦爻上言,动是专主当占之爻言。如二爻变,则占者以上爻为主,这上爻便是动处。如五爻变,一爻不变,则占者以不变之爻为主,则这不变者便是动处也。」学履。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此两句亦相对说。刚柔者,阴阳之质,是移易不得之定体,故谓之本。若刚变为柔,柔变为刚,便是变通之用。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便与「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一样。刚柔两个是本,变通只是其往来者。学履。
「吉凶者,贞胜者也。」这一句最好看。这个物事,常在这里相胜。一个吉,便有一个凶在后面来。这两个物事,不是一定住在这里底物,各以其所正为常。正,是说他当然之理,盖言其本相如此,与「利贞」之「贞」一般,所以说「利贞者,性情也」。横渠说得别。他说道,贞便能胜得他。如此,则下文三个「贞」字说不通。这个只是说吉凶相胜。天地间一阴一阳,如环无端,便是相胜底道理。阴符经说「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间不陡顿恁地阴阳胜。又说那五个物事在这里相生相克,曰:「五贼在心,施行于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贼了。「五贼」乃言五性之德;「施行于天」,言五行之陈子昂感遇诗亦略见得这般意思。大概说相胜,是说他常底。他以本相为常。
问:「『吉凶者,贞胜者也。』『贞』字便是性之骨。」曰:「贞是常恁地,便是他本相如此。犹言附子者,贞热者也;龙脑者,贞寒者也。天下只有个吉凶常相往来。阴符云:『自然之道静,故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极说得妙。静能生动。『浸』是渐渐恁地消去,又渐渐恁地长。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阴符经云:「天地万物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学蒙。
贞,常也。阴阳常只是相胜。如子以前便是夜胜昼,子以后便是昼胜夜。观,是示人不穷。「贞夫一者也」,天下常只是有一个道理。又曰:「须是看教字义分明,方看得下落。说也只说得到偏傍近处。贞便是他体处,常常如此,所以说『利贞者,性情也』。」砺。
贞,只是常。吉凶常相胜,不是吉胜凶,便是凶胜吉。二者常相胜,故曰「贞胜」。天地之道则常示,日月之道则常明。「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之动虽不齐,常有一个是底,故曰「贞夫一」。阴符经云:「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刚柔胜。」若不是极静,则天地万物不生。浸者,渐也。天地之道渐渐消长,故刚柔胜,此便是「吉凶贞胜」之理。这必是一个识道理人说,其它多不可晓,似此等处特然好。
问:「『吉凶贞胜』一段,横渠说何如?」曰:「说真胜处,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说作『常』字,甚佳。易传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发出贞胜之理。盖吉凶二义无两立之理,迭相为胜,非吉胜凶,则凶胜吉矣,故吉凶常相胜。人杰录云:「理自如此。」所以训『贞』字作『常』者,贞是正固。只一『正』字尽『贞』字义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谓此虽是正,又须常固守之,然后为贞。在五常属智,孟子所谓『知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则不可。须是知之,又固守之。盖贞属冬,大抵北方必有两件事,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龙、白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龟、蛇二物。谓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属今年;后四十五日,便属明年;夜分子时前四刻属今日,后四刻即属来日耳。」人杰录略。
问张子「贞胜」之说。曰:「此虽非经意,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说,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
问:「爻者,效此者也。」曰:「爻是两个交叉,看来只是交变之义。卦,分明是将一片木画挂于壁上,所以为卦。」
问:「『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变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虚实而为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学蒙。
先生问:「如何是『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或曰:「阴阳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时,而吉凶乃见于成卦之后。」曰:「也是如此。然『内外』字,犹言先后微显。」学履。
「功业见乎变」,是就那动底爻见得。这「功业」字,似「吉凶生大业」之业,犹言事变、庶事相似。学履。
「圣人之情见乎辞」,下连接说「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连,乃各自说去。「圣人之大宝曰位」,后世只为这两个不相对,有位底无德,有德底无位,有位则事事做得。
「守位曰仁」,释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担当此,以为当从释文。
问:「人君临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财正辞』,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许多人,无财何以养之?有财不能理,又不得。『正辞』,便只是分别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辞』里面。」学履。
「理财、正辞、禁非」是三事:大概是辨别是非;理财,言你底还你,我底还我;正辞,言是底说是,不是底说不是,犹所谓「正名」。
右第一章
「仰则观象于天」一段,只是阴阳奇耦。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身,远取物」;「仰观天,俯察地」,只是一个阴阳。圣人看这许多般事物,都不出「阴阳」两字。便是河图洛书,也则是阴阳,粗说时即是奇耦。圣人却看见这个上面都有那阴阳底道理,故说道读易不可恁逼拶他。欧公只是执定那「仰观俯察」之说,便与河图相碍,遂至不信他。
「伏羲『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那时未有文字,只是仰观俯察而已。想得圣人心细,虽以鸟兽羽毛之微,也尽察得有阴阳。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见兔,曰:『察此亦可以画卦。』便是此义。」曰:「就这一端上,亦可以见。凡草木禽兽,无不有阴阳。鲤鱼脊上有三十六鳞,阴数。龙脊上有八十一鳞。阳数。龙不曾见,鲤鱼必有之。又龟背上文,中间一簇成五段文,两边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两边周围共有二十四段。中间五段者,五行也;两边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围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气也。个个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银杏、桐、楮、牝牡麻、竹之类皆然。又树木向阳处则坚实,其背阴处必虚软。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于水也亦然。盖男阳气在背,女阳气在腹也。」扬子云太玄云:「观龙虎之文,与龟鸟之象。」谓二十八宿也。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尽于八卦,而震巽坎离艮兑又总于乾坤。曰「动」,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丽」,曰「悦」,皆顺底意思。圣人下此八字,极状得八卦性情尽。
「盖取诸益」等,「盖」字乃模样是恁地。可学录云:「『盖』字有义。」
「黄帝尧舜氏作」,到这时候,合当如此变。「易穷则变」,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变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概说,则这个几卦也是难晓。
使民不倦,须是得一个人「通其变」。若听其自变,如何得?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天下事有古未之为而后人为之,因不可无者,此类是也。如年号一事,古所未有。后来既置,便不可废。胡文定却以后世建年号为非,以为年号之美,有时而穷,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缘无年号,所以事无统纪,难记。如云某年,王某月,个个相似,无理会处。及汉既建年号,于是事乃各有纪属而可记。今有年号,犹自奸伪百出。若只写一年二年三年,则官司词讼簿历,凭何而决?少间都无理会处。尝见前辈说,有两家争田地。甲家买在元佑几年,乙家买在前。甲家遂将「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则将出文字又在嘉佑之先,甲家遂又将嘉佑字涂擦作皇佑。有年号了,犹自被人如此,无后如何!
结绳,今溪洞诸蛮犹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时,以至人马粮草之数,皆刻板为记,都不相乱。
右第二章
林安卿问:「『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个『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意亦然。」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佛说,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见得道理多后,却须将来寄搭在上面说。
「易者,象也」,是总说起,言易不过只是阴阳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动也」,则皆是说那上面「象」字。学履。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试教一个民有两个君,看是甚模样!
右第四章
「天下何思何虑」一句,便是先打破那个「思」字,却说「同归殊涂,一致百虑」。又再说「天下何思何虑」,谓何用如此「憧憧往来」,而为此朋从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龙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则不来,不屈则亦不能伸也。今之为学,亦只是如此。「精义入神」,用力于内,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于外,乃所以「崇德」乎内。只是如此做将去。虽至于「穷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虑之有!
问:「『天下同归殊涂,一致百虑』,何不云『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从上说下,自合如此。」学蒙。
干干不息者体;日往月来,寒来暑往者用。有体则有用,有用则有体,不可分先后说。
「天下何思何虑」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义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问:「『天下同归而殊涂』一章,言万变虽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说得一头。尺蠖若不屈,则不信得身;龙蛇若不蛰,则不伏得气,如何存得身?『精义入神』,疑与行处不相关,然而见得道理通彻,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与『崇德』不相关,然而动作得其理,则德自崇。天下万事万变,无不有感通往来之理。」又曰:「『日往则月来』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来』而言。往来皆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则不可。」学蒙。
「尺蠖之屈以求信,龙蛇之蛰以藏身,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这个,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来,一阖一辟。大底有大底阖辟消息,小底有小底阖辟消息,皆只是这道理。
或问:「『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说是感应,如何?」曰:「屈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来皆是。」
尺蠖屈,便要求伸;龙蛇蛰,便要存身。精研义理,无毫厘丝忽之差,入那神妙处,这便是要出来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来自崇己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横渠云:「『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事豫吾内」,言曾到这里面来。至录略。
且如「精义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验。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处。一事一理上。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则自然安利;不循理,则自然不安利。
「未之或知」,是到这里不可奈何。「穷神知化」,虽不从这里面出来,然也有这个意思。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后,便能「穷神知化」,便如「聪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诚而明」相似。
「穷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将去底。一日复一日,一月复一月,节节挨将去,便成一年,这是化。神,是一个物事,或在彼,或在此。当在阴时,全体在阴;在阳时,全体在阳。都只是这一物,两处都在,不可测,故谓之神。横渠云:「一故神,两故化。」又注云:「两在,故不测。」这说得甚分晓。
问:「『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谓石不能动底物,学蒙录作:「挨动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须去动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学蒙录云:「『且以事言,有着力不得处。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间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则只得做。』曰:『自是如此。』」曰:「爻意,谓不可做底,便不可入头去做。」学履。学蒙录详。
「公用射隼」,孔子是发出言外意。学蒙。
问:「危者以其位为可安而不知戒惧,故危;亡者以其存为可常保,是以亡;乱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乱。」曰:「某旧也如此说。看来『保』字说得较牵强,只是常有危亡与乱之意,则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几其神乎!」便是这事难。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今有一样人,其不畏者,又言过于直;其畏谨者,又缩做一团,更不敢说一句话,此便是不晓得那几。若知几,则自中节,无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盖上交贵于恭,恭则便近于谄;下交贵和易,和则便近于渎。盖恭与谄相近,和与渎相近,只争些子,便至于流也。
「『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下面说『几』。最要看个『几』字,只争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说,道理易见;事已至而显然,道理也易见。惟事之方萌,而动之微处,此最难见。」或问:「『几者动之微』,何以独于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逊,才恭逊,便不知不觉有个谄底意思在里;『下交不渎』,亦是如此。所谓『几』者,只才觉得近谄近渎,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汉书引此句,『吉』下有『凶』字。当有『凶』字。」
盖人之情,上交必谄,下交必渎,所争只是些子。能于此而察之,非『知几』者莫能。上交着些取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之心,皆是也。
「几者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便须就这处理会。若到发出处,更怎生奈何得!所以圣贤说慎独,便是要就几微处理会。
魏问「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曰:「似是漏字。汉书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似说得是。几自是有善有恶。君子见几,亦是见得,方舍恶从善,不能无恶。」又曰:「汉书上添字,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自经于沟渎,而人莫之知也!」添个『人』字,似是。」
「知微,知彰,知柔,知刚」,是四件事。学履。
问:「伊川作『见微则知彰矣,见柔则知刚矣』,其说如何?」曰:「也好。看来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刚,言其无所不知,以为万民之望也。」学蒙。
「其殆庶几乎!」殆,是几乎之义。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是争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几』字为因上文『几』字而言。但左传与孟子『庶几』两字,都只做『近』字说。」
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尝复行」为难,殊不知「有不善未尝不知」是难处。今人亦有说道知得这个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随私欲做将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为是不曾知。
「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直是颜子天资好,如至清之水,纤芥必见。
「天地氤氲」,言气化也;「男女构精」,言形化也。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致一」,专一也。惟专一,所以能絪缊;若不专一,则各自相离矣。化醇,是已化后。化生,指气化而言,草木是也。
「致一」,是专一之义,程先生言之详矣。天地男女,都是两个方得专一,若三个便乱了。三人行,减了一个,则是两个,便专一。一人行,得其友,成两个,便专一。程先生说初与二,三与上,四与五,皆两相与。自说得好。「初、二二阳,四、五二阴,同德相比;三与上应,皆两相与」。学蒙。
横渠云:「『艮三索而得男』,干道之所成;『兑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损有男女构精之义。」亦有此理。
右第五章
「乾坤,易之门」,不是乾坤外别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两扇门相似,一扇开,便一扇闭。只是一个阴阳做底,如「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
问:「『乾坤,易之门。』门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两仪生四象』,只管生出邪?为是取阖辟之义邪?」曰:「只是取阖辟之义。六十四卦,只是这一个阴阳阖辟而成。但看他下文云:『干,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便见得只是这两个。」学蒙。
「干,阳物;坤,阴物。」阴阳,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天地之撰」,撰,即是说他做处。[莹田-玉]录云:「撰是所为。」
问「『其称名也杂而不越』,是指系辞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后面两三番说名后,又举九卦说,看来只是谓卦名。」又曰:「系辞自此以后皆难晓。」学蒙。
「『于稽其类』,一本作『于稽音启。其颡』,又一本『于』作『乌』,不知如何。」曰:「但不过是说稽考其事类。」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画卦时,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经历。到文王时,世变不好,古来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经历这崎岖万变过来,所以说出那卦辞。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此若不是经历,如何说得!
「彰往察来。」往者如阴阳消长,来者事之未来吉凶。
问:「『彰往察来』,如『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阴阳之变,皆已见在这卦上了;来,谓方来之变,亦皆在这上。」曰:「是。」学蒙。
「微显阐幽。」幽者不可见,便就这显处说出来;显者便就上面寻其不可见底,教人知得。又曰:「如『显道,神德行』相似。」学蒙。
「微显阐幽」,便是「显道,神德行」。德行显然可见者,道不可见者。「微显阐幽」,是将道来事上看;言那个虽是麤底,然皆出于道义之蕴。「潜龙勿用」,显也。「阳在下也」,只是就两头说。微显所以阐幽,阐幽所以微显,只是一个物事。
将那道理来事物上与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里面有这道理。「微显阐幽。」
右第六章
因论易九卦,云:「圣人道理,只在口边,不是安排来。如九卦,只是偶然说到此,而今人便要说,如何不说十卦?又如何不说八卦?便从九卦上起义,皆是胡说。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践履为本。『谦,德之柄』,只是要谦退,若处患难而矫亢自高,取祸必矣。『复,德之本』,如孟子所谓『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则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则可辨其非。损是『惩忿窒欲』。益是修德益令广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权』,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须是将心入那事里面去,顺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权。若心麤,只从事皮肤上绰过,如此行权,便就错了。巽,伏也,入也。」学蒙。
三陈九卦,初无他意。观上面「其有忧患」一句,便见得是圣人说处忧患之道。圣人去这里偶然看见这几卦有这个道理,所以就这个说去。若论到底,睽蹇皆是忧祸患底事,何故却不说?以此知只是圣人偶然去这里见得有此理,便就这里说出。圣人视易,如云行水流,初无定相,不可确定他。在易之序,履卦当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说干、坤。
郑仲履问:「易系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圣人论处忧患,偶然说此九卦耳。天下道理只在圣人口头,开口便是道理,偶说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说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尽有道理。且易中尽有处忧患底卦,非谓九卦之外皆非所以处忧患也。若以困为处忧患底卦,则屯蹇非处忧患而何?观圣人之经,正不当如此。后世拘于象数之学者,乃以为九阳数,圣人之举九卦,合此数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论九卦之后,因言:「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
三说九卦,是圣人因上面说忧患,故发明此一项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辨」,若说蹇屯亦可,盖偶然如此说。大抵易之书,如云行水流,本无定相,确定说不得。扬子云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间排将去,七百三十赞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昼夜,昼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参之,故吉凶有深浅,毫发不可移,此可为典要之书也。圣人之易,则有变通。如此卦以阳居阳则吉,他卦以阳居阳或不为吉;此卦以阴居阴则凶,他卦以阴居阴或不为凶:此「不可为典要」之书也。
问:「巽何以为『德之制』?」曰:「巽为资斧,巽多作断制之象。盖『巽』字之义,非顺所能尽,乃顺而能入之义。谓巽一阴入在二阳之下,是入细直彻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断得杀。若不见得尽,如何可以『行权』!」
问「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泽及于物,而井未尝动,故曰『居其所而迁』。如人有德,而后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尝动也。『井以辨义』,如人有德,而其施见于物,自有斟酌裁度。」砺。
「损先难而后易」,如子产为政,郑人歌之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人复歌而诵之。盖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强,在人亦有所难堪;久之当事理,顺人心,这里方易。便如「利者,义之和」一般。义是一个断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为和。如万物到秋,许多严凝肃杀之气似可畏。然万物到这里,若不得此气收敛凝结许多生意,又无所成就。其难者,乃所以为易也。「益,长裕而不设」,长裕只是一事,但充长自家物事教宽裕而已。「困穷而通」,此因困卦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盖此是「致命遂志」之时,所以困。彖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盖处困而能说也。困而寡怨,是得其处困之道,故无所怨于天,无所尤于人;若不得其道,则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迁」,井是不动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义」,辨义谓安而能虑,盖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义也?『巽称而隐』,巽是个卑巽底物事,如「兑见而巽伏也」,自是个隐伏底物事。盖巽一阴在下,二阳在上,阴初生时,已自称量得个道理了,不待显而后见。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个道理处置他,不待发露出来。如云:「尊者于己踰等,不敢问其年。」盖才见个尊长底人,便自不用问其年;不待更计其年,然后方称量合问与不合问也。「称而隐」,是巽顺恰好底道理。有隐而不能称量者,有能称量而不能隐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权」,都是此意。
问「巽称而隐」。曰:「以『巽以行权』观之,则『称』字宜音去声,为称物之义。」又问:「巽有优游巽入之义;权是仁精义熟,于事能优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细底意,说在九卦之后,是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权。某前时以称扬为说了,错了。」学蒙。
问:「『巽称而隐』,『隐』字何训?」曰:「隐,不见也。如风之动物,无物不入,但见其动而不见其形。权之用,亦犹是也。昨得潘恭叔书,说滕文公问『间于齐楚』,与『竭力以事大国』两段,注云『盖迁国以图存者,权也;效死勿去者,义也』;『义』字当改作『经』。思之诚是。盖义便近权,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义也;经则一定而不易。既对『权』字,须着用『经』字。」
问「井以辨义」。曰:「只是『井居其所而迁』,大小多寡,施之各当。」
或问「井以辨义」之义。曰:「『井居其所而迁。』」又云:「『井,德之地也。』盖井有定体不动,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穷;犹人心有持守不动,而应变则不穷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动底地头。」一本云:「是指那不动之处。」又曰:「佛家有函盖乾坤句,有随波逐流句,有截断众流句。圣人言语亦然。如『以言其远则不御,以言其迩则静而正』,此函盖乾坤句也。如『井以辨义』等句,只是随道理说将去,此随波逐流句也。如『复其见天地之心』,『神者妙万物而为言』,此截断众流句也。」
才卿问「巽以行权」。曰:「权之用,便是如此。见得道理精熟后,于物之精微委曲处无处不入,所以说『巽以行权』。」
问:「『巽以行权』,权,是逶迤曲折以顺理否?」曰:「然。巽有入之义。『巽为风』,如风之入物。只为巽,便能入义理之中,无细不入。」又问:「『巽称而隐』,隐亦是入物否?」曰:「隐便是不见处。」文尉。
郑仲履问:「『巽以行权』,恐是神道?」曰:「不须如此说。巽只是柔顺,低心下意底气象。人至行权处,不少巽顺,如何行得?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处忧患之道。」
「巽以行权。」「兑见而巽伏。」权是隐然做底物事,若显然底做,却不成行权。
右第七章
问:「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须臾离者,故曰『不可远』。」曰:「是。」学蒙。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
易「不可为典要」。易不是确定硬本子。扬雄太玄却是可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赞当昼,三百五十四赞当夜,昼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轻重,凶之中又自分轻重。易却不然。有阳居阳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阴居阴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应而吉底,有有应而凶底,是「不可为典要」之书也。是有那许多变,所以如此。
问:「据文势,则『内外使知惧』合作『使内外知惧』,始得。」曰:「是如此。不知这两句是如何。硬解时也解得去,但不晓其意是说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属。」又曰:「上文说『不可为典要』,下文又说『既有典常』,这都不可晓。常,犹言常理。」学蒙。
使「知惧」,便是使人有戒惧之意。易中说如此则吉,如此则凶,是也。既知惧,则虽无师保,一似临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惧。
右第八章
「其初难知」,至「非其中爻不备」,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晓他意不得。这下面却说一个「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后面说「二与四同功」,「三与五同功」,却说得好。但「不利远者」,也晓不得。学蒙。
问「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曰:「这样处晓不得,某常疑有阙文。先儒解此多以为互体,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间四爻观之,自二至四则为坤,自三至五则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备』。互体说,汉儒多用之。左传中一处说占得观卦处亦举得分明。看来此说亦不可废。」学履。
问:「『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则当柔和,远去则当有强毅刚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说。」
问:「上下贵贱之位,何也?」曰:「四二,则四贵而二贱;五三,则五贵而三贱;上初,则上贵而初贱。上虽无位,然本是贵重,所谓『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则为天子父,天子师;在他人则清高而在物外,不与事者,此所以为贵也。」
右第九章
问:「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曰:「『道有变动』,不是指那阴阳老少之变,是说卦中变动。如干卦六画,初潜,二见,三惕,四跃,这个便是有变动,所以谓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或贵,或贱,皆谓之等,易中便可见。如说『远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则凶』;『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又曰:「『列贵贱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见古人占卦,必有个物事名为『物』,而今亡矣。这个物,是那列贵贱,辨尊卑底。『物相杂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为君臣之文。是两物相对待在这里,故有文;若相离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阴爻,又有阳爻相间错,则为文。若有阴无阳,有阳无阴,如何得有文?」学履。
右第十章
「其辞危」,是有危惧之意,故危惧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倾覆。易之书,于万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废」。「其要」,是约要之义。若作平声,则是要其归之意。」又曰:「『要』去声,是要恁地;『要』平声,是这里取那里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右第十一章
或问:「干是至健不息之物,经历艰险处多。虽有险处,皆不足为其病,自然足以进之而无难否?」曰:「不然。旧亦尝如此说,觉得终是硬说。易之书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险而不进,不说是我至健顺了,凡有险阻,只认冒进而无难。如此,大非圣人作易之意。观上文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谓易之道也』,看他此语,但是恐惧危险,不敢轻进之意。干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说『见险而能止』,如需卦之类可见。易之道,正是要人知进退存亡之道。若如冒险前进,必陷于险,是『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岂干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险,故止于险而不陷于险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说。」又曰:「险与阻不同,险是自上视下,见下之险,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观上,为上所阻,故不敢进。」学履录少异。
问「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说健顺。好底物事,自是知险阻。恰如良马,他才遇险阻处,便自不去了。如人临悬崖之上,若说不怕险,要跳下来,必跌杀。」良久,又曰:「此段专是以忧患之际而言。且如健当忧患之际,则知险之不可乘;顺当忧患之际,便知阻之不可越。这都是当忧患之际,处忧患之道当如此。因忧患,方生那知险知阻。若只就健顺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皆因忧患说。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险之不可乘而不去,则不陷于险;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则不困于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间,其过乎刚者,虽知险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则陷于险矣;虽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则困于阻矣。只是顺理,便无事。」又问:「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则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险阻,这只是大纲说个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顺自是畏谨,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险,然却知险而不去,盖他当忧患之际故也。」又问「简易」。曰:「若长是易时,更有甚么险?他便不知险矣。若长是简时,更有甚么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当忧患之际方见得。」
「干,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来圣人无冒险之事,须是知险,便不进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别有一个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则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这只是说刚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说。」
因说:「乾坤知险阻,非是说那定位底险阻。干是个至健底物,自是见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顺底物,自是见那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胜物之谓刚,故常信于万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胆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险』,如『胆欲大』;至顺『恒简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相似。」李云:「如人欲渡,若风涛汹涌,未有要紧,不渡也不妨。万一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说到这里在。这个又是说处那险阻,圣人固是有道以处之。这里方说知险阻,知得了方去处他。」问:「如此,则干之所见无非险,坤之所见无非阻矣。」曰:「不然。他是至健底物,自是见那物事底。如人下山阪,自上而下,但见其险,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顺底物,则自下而上,但见其阻。险阻只是一个物事,一是自上而视下,一是自下而视上。若见些小险便止了,不敢去,安足为健?若不顾万仞之险,只恁从上面擂将下,此又非所以为干。若见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顾万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为坤。」所说险阻,与本义异。
干健而以易临下,故知下之险;险底意思在下。坤顺而以简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来,到那去不得处,便是险;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处,便是阻。易只是这两个物事。自东而西,也是这个;自西而东,也是这个。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因言乾坤简易,「知险知阻」,而曰:「知险阻,便不去了。惟其简易,所以知险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险徼幸之人,虽知险阻,而犹冒昧以进。惟乾坤德行本自简易,所以知险阻。」
问「干常易以知险,坤常简以知阻」。曰:「干健,则看什么物都剌音辣。将过去。坤则有阻处便不能进,故又是顺;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后复云:「前说差了。干虽至健,知得险了,却不下去;坤虽至顺,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进去,做甚收杀!」或录云:「干到险处便止不行,所以为常易。」学蒙。
又说「知险知阻」,曰:「旧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则所见为险;自下而上,则所向为阻。盖干则自上而下,坤则自下而上;健则遇险亦易,顺则还阻亦简。然易则可以济险,而简亦有可涉阻之理。」
因登山,而得乾坤险阻之说。寻常将险阻作一个意思。其实自高而下,愈觉其险,干以险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碍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
自山下上山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观山下为险,故指干而言。
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样事。「夫干,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说诸心」,只是见过了便说,这个属阳;「研诸虑」,是研穷到底,似那「安而能虑」,直是子细,这个属阴。「定吉凶」是阳;「成亹亹」是阴,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时,人自意思懒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将去,所以属阴。大率阳是轻清底,物事之轻清底属阳;阴是重浊底,物事之重浊者属阴。「成亹亹」,是做将去。
「能说诸心」,干也;「能研诸虑」,坤也。「说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属阳;「研诸虑」,有作为意思,故属阴。「定吉凶」,干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属乎阳,「定吉凶」所以为干;事之已为者属阴,「成亹亹」所以为坤。大抵言语两端处,皆有阴阳。如「开物成务」,「开物」是阳,「成务」是阴。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阳,「力行」是阴。周子之书屡发此意,推之可见。
「能说诸心,能研诸虑」,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见得通透了,自然欢说。既说诸心,是理会得了,于事上便审一审,便是研诸虑。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这事业。学蒙。
问「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曰:「上两句只说理如此,下两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阴阳则为变化,在人事则为云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于『变化云为』,则象之而知已有之器;于『吉事有祥』,则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问:「『器』字,是凡见于有形之实事者皆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说。」学履。
「变化云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来」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这事去;「占事知来」是他方有个祯祥,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祯祥」,「见乎蓍龟」之类。「吉事有祥」,凶事亦有。
问:「易书之中有许多『变化云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应,所以象事者于此而知器,占事者于此而知来。」曰:「是。」
「天地设位」四句,说天人合处。「天地设位」,便圣人成其功能;「人谋鬼谋」,则虽百姓亦可以与其能。「成能」与「与能」,虽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与能」,却须因蓍龟而方知得。「人谋鬼谋」,如「谋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
「百姓与能」,「与」字去声。他无知,因卜筮便会做得事,便是「与能」。「人谋鬼谋」,犹洪范之谋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学蒙。
「八卦以象告」以后,说得丛杂,不知如何。学蒙。
问:「『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辞屈』一段,窃疑自『吉凶可见矣』而上,只是总说易书所载如此。自『变动以利言』而下,则专就人占时上说。」曰:「然。」又问:「『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见得。盖远而不相得,则安能为害?惟切近不相得,则凶害便能相及。如一个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与之为邻近,则有害矣。」又问:「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课底,若是凶神,动与世不相干,则不能为害。惟是克世应世,则能为害否?」曰:「恐是这样意思。」学履。
「『中心疑者其辞支。』『中心疑』,故不敢说杀。『其辞支』者,如木之有枝,开两岐去。」德辅云:「『思曰睿』,『学而不思则罔』,盖亦弗思而已矣,岂有不可思维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维,则圣人著书立言,于后世何用!」德辅。
右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