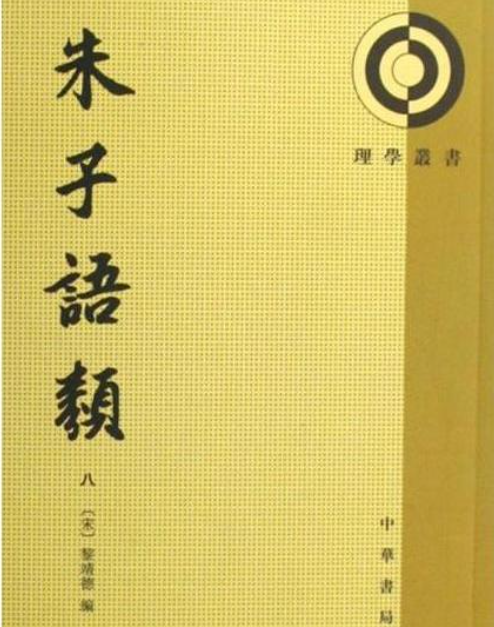易十一
上系下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赜」字在说文曰:「杂乱也。」古无此字,只是「啧」字。今从「赜」,亦是口之义。「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虽是杂乱,圣人却于杂乱中见其不杂乱之理,便与下句「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相对。
「天下之至赜」与左传「啧有烦言」之「啧」同。那个从「口」,这个从「●」,是个口里说话多、杂乱底意思,所以下面说「不可恶」。若唤做好字,不应说个「可恶」字也。「探赜索隐」,若与人说话时,也须听他杂乱说将出来底,方可索他那隐底。淳录云:「本从『口』,是喧闹意。从『●』旁亦然。」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正是说画卦之初,圣人见阴阳变化,便画出一画,有一个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样,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样。学蒙。
「拟诸其形容」,未便是说那水火风雷之形容。方拟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阳在二阴之下,则象以雷,一阴在二阳之下,则象以风。拟,是比度之意。学蒙。
问:「『拟诸其形容』者,比度阴阳之形容。盖圣人见阴阳变化杂乱,于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曰:「也是如此,尝得郭子和书云,其先人云:『不独是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谓之象,只是画卦便是象。』也说得好。」学蒙。
问:「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会通』者,观众理之会,而择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关着许多道理,也有父子之伦,也有君臣之伦,也有夫妇之伦。若是父子重,则就父子行将去,而他有不暇计;若君臣重,则行君臣之义,而他不暇计。若父子之恩重,则便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而『委致其身』之说不可行。若君臣之义重,则当委致其身,而『不敢毁伤』之说不暇顾。此之谓『观会通』。」
问:「『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是说文王周公否?」曰:「不知伏羲画卦之初,与连山归藏有系辞否;为复一卦只是六画?」学蒙。
问:「『观会通,行其典礼』,是就会聚处寻一个通路行将去否?」曰:「此是两件。会,是观众理之会聚处。如这一项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须是看得周遍,始得通,便是一个通行底路,都无窒碍。典礼,犹言常礼常法。」又曰:「礼便是节文升降揖逊是也。但这个『礼』字又说得阔,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学蒙。
「一卦之中自有会通,六爻又自各有会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进,为屯之义;乾坤始交而遇险陷,亦屯之义;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义。凡此数义,皆是屯之会聚处。若『盘桓利居贞』,便是一个合行底,便是他通处也。」学蒙。
「观会通以行其典礼。」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谓如庖丁解牛,于族处却『批大郄,导大窾』,此是于其筋骨丛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刃若新发于硎。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个通处,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处,自然通贯得,所以可『行其典礼』。盖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
问「『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此是说天下之事物如此,不是说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杂乱!」学蒙。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盖杂乱处,人易得厌恶。然而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会,故不可恶。「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盖动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乱。学蒙。
先生命二三子说书毕,召蔡仲默及义刚语,小子侍立。先生顾义刚曰:「劳公教之,不废公读书否?」曰:「不废。」因借先生所点六经。先生曰:「被人将去,都无本了。看公于句读音训,也大段子细。那『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是音作去声字?是公以意读作去声?」曰:「只据东莱音训读。此字有三音,或音作入声。」池录云:「或音亚,或如字,或乌路反。」先生笑曰:「便是他们好恁地强说。」仲默曰:「作去声,也似是。」先生曰:「据某看,只作入声亦是。池录云:「乌路切于义为近。」说虽是如此劳攘事多,然也不可以为恶。池录云:「也不可厌恶。」而今音训有全不可晓底。若有两三音底,便着去里面拣一个较近底来解。」池录略而异。
「天下之至动」,事若未动时,不见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语,水平不流,须是动,方见得。「会通」,是会聚处;「典礼」,是借这般字来说。观他会通处。却求个道理来区处他。所谓卦爻之动,便是法象这个,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动,亦未说事之动,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动,要求处置他,便是动。
问:「『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凡一言一动皆于易而拟议之否?」曰:「然。」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此变化只就人事说。拟议,只是裁度自家言动,使合此理,「变易以从道」之意。如拟议得是便吉,拟议未善则为凶矣。
问「拟议以成其变化」。曰:「这变化,就人动作处说,如下所举七爻,皆变化也。」学履。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此本是说诚信感通之理,夫子却专以言行论之。盖诚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上文「言天下之赜而不敢恶也,言天下之动而不敢乱也」,先儒多以「赜」字为至妙之意。若如此说,则何以谓之「不敢恶」?赜,只是一个杂乱冗闹底意思。言之而不恶者,精粗本末无不尽也。「赜」字与「颐」字相似,此有互体之意。此间连说互体,失记。「鹤鸣」、「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诸爻立象,圣人必有所据,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说象。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之类,孔子只说「群疑亡也」,便见得上面许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后人解说,便多牵强。如十三卦中「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备之意;却须待用互体,推艮为门阙,雷震乎外之意。「剡木为矢,弦木为弧」,只为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凿附会,就卦中推出制器之义。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盖取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尔。汉书所谓「获一角兽,盖麟云」,皆疑辞也。
问:「『言行,君子之枢机』,是言所发者至近,而所应者甚远否?」曰:「枢机,便是『鸣鹤在阴』。下面大概只说这意,都不解着『我有好爵』二句。」学蒙。
「其利断金」。断,是断做两段。又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圣人却恁地解。」学蒙。
右第八章
卦虽八而数须十。八是阴阳数,十是五行数。一阴一阳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盖一个便包两个: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为十。学履。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两个意: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是奇耦以类「相得」;一与六合,二与七合,三与八合,四与九合,五与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与己合,乙与庚合,丙与辛合,丁与壬合,戊与癸合,是「各有合」。学履。
「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先生举程子云:「变化言功,鬼神言用。」张子曰:「成行,鬼神之气而已。」「数只是气,变化鬼神亦只是『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变化鬼神皆不越于其间。」
「大衍之数五十。」蓍之数五十。蓍之筹,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数,则直谓之数耳。
「大衍之数五十」,以「天地之数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数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说也。数家之说虽多不同,某自谓此说却分晓。三天两地,则是已虚了天一之数,便只用天三对地二。又五是生数之极,十是成数之极,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说也。又,数始于一,成于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说。
系辞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别有文字,今不可见。但如「天数五,地数五」,此是旧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是旧文;「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为二」是本文;「以象两」是解「挂一」。「揲之以四」,「归奇于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时」,「以象闰」之类,皆解文也。「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则断之以「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则断之以「当万物之数」,于此可见。
蓍卦,当初圣人用之,亦须有个见成图算。后失其传,所仅存者只有这几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挂一。揲之以四。归奇于扐。」只有这几句。如「以象两」,「以象三」,「以象四时」,「以象闰」,已是添入许多字说他了。又曰:「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将这四个只管涵泳玩味,尽好。」
揲蓍法,不得见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说。如「分而为二」是说,「以象两」便是解。想得古人无这许多解,须别有个全文说。
挂,一岁;右揲,二岁;扐,三岁一闰也。左揲,四岁;扐,五岁再闰也。
揲蓍虽是一小事,自孔子来千五百年,人都理会不得。唐时人说得虽有病痛,大体理会得是。近来说得太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余为奇;扐者,归其余扐于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挂一为奇,而以揲之余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为策数,以为圣人从来只说阴阳,不曾说老少。不知他既无老少,则七八九六皆无用,又何以为卦?又曰:「龟为卜,策为筮。策,是余数厉录云:「筴是条数。」谓之策。他只胡乱说『策』字。」厉录云:「只鹘突说了。」或问:「他既如此说,则『再扐而后挂』之说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扐为扐,第二第三揲不挂为扐,第四揲又挂。然如此,则无五年再闰。厉录云:「则是六年再闰也。」如某已前排,真个是五年再闰。圣人下字皆有义。挂者,挂也;扐者,勒于二指之中也。」厉录小异。
二篇之策,当万物之数。不是万物尽于此数,只是取象自一而万,以万数来当万物之数耳。
「策数」云者,凡手中之数皆是。如「散策于君前有诛」,「龟策弊则埋之」,不可以既揲余数不为策数也。
「四营而成易」,「易」字只是个「变」字。四度经营,方成一变。若说易之一变,却不可。这处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是占得一卦,则就上面推看。如干,则推其「为圜、为君、为父」之类是也。学履。
问「显道,神德行」。曰:「道较微妙,无形影,因卦辞说出来,道这是吉,这是凶;这可为,这不可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子推出来,方知得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为也。」又曰:「须知得是天理合如此。」学蒙。
「神德行」,是说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为。若决之于鬼神,德行便神。
易,惟其「显道,神德行」,故能与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学履。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此是说蓍卦之用,道理因此显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决于蓍。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变。神又岂能自说吉凶与人!因有易后方着见,便是易来佑助神也。
右第九章
「易有圣人之道四。」「至精」、「至变」,则合做两个,是他里面各有这个。
问:「『以言者尚其辞』,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断事,如论语上举『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学履。
问:「『以言』,『以动』,『以制器』,『以卜筮』,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问:「辞、占是一类,变、象是一类。所以下文『至精』合辞、占说;『至变』合变、象说?」曰:「然。占与辞是一类者,晓得辞,方能知得占。若与人说话,晓得他言语,方见得他胸中底蕴。变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类也。」学履。
用之问「以制器者尚其象」。曰:「这都难说。『盖取诸离』,『盖』字便是一个半间半界底字。如『取诸离』,『取诸益』,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地土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问:「『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龟,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则是文势如此。」学履。
问:「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曰:「此是说君子作事,问于蓍龟也。『问焉以言』,人以蓍问易,求其卦爻之辞,而以之发言处事。『受命如响』,则易受人之命,如响之应声,以决未来吉凶也。」
「问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词。古人亦大段重这命筮之辞,『而以言』三字义若拗。若作『以易言之』,如所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则『不占』只是以其言之义,又于上下文不顺。」学蒙。谟录云:「言是命龟。受命,龟受命也。」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参,谓三数之;伍,谓伍数之。揲蓍本无三数五数之法,只言交互参考皆有自然之数。如三三为九、五六三十之类,虽不用以揲蓍,而推算变通,未尝不用。错者,有迭相为用之意;综,又有总而挈之之意,如织者之综丝也。
「参伍」,是相牵连之意。如三要做五,须用添二;五要做六,须着添一;做三,须着减二。错综是两样;错,是往来交错之义;综,如织底综,一个上去,一个下来。阳上去做阴,阴下来做阳,如综相似。
问「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曰:「荀子说『参伍』处,杨倞解之为详。汉书所谓『欲问马,先问牛,参伍之以得其实』。综,如织综之综。大抵阴阳奇耦,变化无穷,天下之事不出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陈列变态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经纶天下之事也。」
问:「『参伍以变。』先生云:『既三以数之,又五以数之。』譬之三十钱,以三数之,看得几个三了,又以五数之,看得几个五。两数相合,方可看得个成数。」曰:「是如此。」又问:「不独是以数算,大概只是参合底意思。如赵广汉欲问马,先问牛,便只是以彼数来参此数否?」曰:「是。却是恁地数了,又恁地数,也是将这个去比那个。」又曰:「若是他数,犹可凑。三与五两数,自是参差不齐,所以举以为言。如这个是三个,将五来比,又多两个:这个是五个,将三来比,又少两个。兵家谓『窥敌制变,欲伍以参』。今欲窥敌人之事,教一人探来恁地说,又差一个探来。若说得不同,便将这两说相参看如何,以求其实,所以谓之『欲伍以参』。」学履。
「参伍以变。」「参」字音「曹参」之「参」,犹言参互底意思。譬犹几个物事在这边,逐三个数,看是几个;又逐五个数,看是几个。又曰:「若三个两是六个,便多了一个;三个三是九个,又少一个;三个四又是十二个;也未是;三个五方是十五个。大略如此,更须仔细去看。」学蒙。
「『错综其数。』本义云:『错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谓也。』莫是揲蓍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干对坤,坎对离,自是交错。」又问:「『综者,总而挈之』,莫是合挂扐之数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阳,六压他不得,便当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须挨上,便是一低一昂。」学蒙。
手指画
六
五指
七
四指
八
三指
九
二指
或问「经纬错综」之义。曰:「错,是往来底;综,是上下底。综,便是织机上底。古人下这字极子细,但看他那单用处,都有个道理。如『经纶』底字,纶是两条丝相合,各有条理。凡用『纶』处,便是伦理底义。『统』字是上面垂一个物事下来,下面有一个人接着,便谓之『统』,但看『垂』字便可见。」又曰:「『错综其数』,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对九,七对八,便是东西相错。六上生七为阳,九下生八为阴,元本云:「七下生八为阴,八上生九又为阳。」便是上下为综。」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阳数九,少阴数八,少阳数七,太阴数六,初亦不知其数如何恁地。元来只是十数,太阳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个;少阴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个;少阳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个;太阴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个。这处,古来都不曾有人见得。」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是说易,不是说人。诸家皆是借来就人上说,亦通。
「感而遂通」,感着他卦,卦便应他。如人来问底善,便与说善;来问底恶,便与说恶。所以先儒说道「洁净精微」,这般句说得有些意思。
陈厚之问「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曰:「寂然是体,感是用。当其寂然时,理固在此,必感而后发。如仁感为恻隐,未感时只是仁;义感为羞恶,未感时只是义。」某问:「胡氏说此,多指心作已发。」曰:「便是错了。纵使已发,感之体固在,所谓『动中未尝不静』。如此则流行发见,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发,一齐无本了,终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错了!」
易便有那「深」,有那「几」,圣人用这底来极出那深,研出那几。研,是研摩到底之意。诗书礼乐皆是说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说那未有这事。「研几」是不待他显著,只在那茫昧时都处置了。深,是幽深,通是开通。所以闭塞,只为他浅。若是深后,便能开通人志。道理若浅,如何开通得人?所谓「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说「开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说个「成务」。易是说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深」就心上说,「几」就事上说。几,便是有那事了,虽是微,毕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奥;几在事,半微半显,「通天下之志」,犹言「开物」,开通其闭塞。故其下对「成务」。
极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几,故能「成天下之务」。
问:「『惟深也』,『惟几』,『惟神也』,此是说圣人如此否?」曰:「是说圣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能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黑窣窣地深,疑若不可测,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个端绪可寻。」又曰:「有路脉线索在里面,所以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研者,便是研穷他。」或问「几」。曰:「便是周子所谓『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也。」学蒙。
问:「系辞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此二『通』字,乃所以通达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晓,如所谓『开物』之意。」曰:「然。这般些小道理,更无穷。」问:「『极深研几』,『深几』二字如何?」曰:「『研几』,是研磨出那几微处。且如一个卦在这里,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几微毫厘处,都研磨出来。」问:「如何是『极深』?」曰:「要人都晓得至深难见底道理,都就易中见得。」问:「如所谓『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之类否?」曰:「然。」问:「如此说,则正与本义所谓『所以极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几者,至变也』,正相发明。」曰:「然。」
右第十章
问:「『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开物成务』否?」曰:「然。」学蒙。
「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读系辞,须见得如何是「开物」,如何是「成务」,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须要就卦中一一见得许多道理。然后可读系辞也。盖易之为书,因卜筮以设教,逐爻开示吉凶,包括无遗,如将天下许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为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则凡居下者不当厚事。如子于父,臣之于君,僚属之于官长,皆不可以踰分越职。纵可为,亦须是尽善,方能无过,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系辞自大衍数以下,皆是说卜筮事。若不晓他尽是说爻变中道理,则如所谓「动静不居,周流六虚」之类,有何凭着?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慊怕小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则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于无形,粗及于有象,如包罩在此,随取随得。「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后见;只是体察,便自见吉凶之理。圣人作易,无不示戒。干卦纔说「元亨」,便说「利贞」。坤卦纔说「元亨」,便说「利牝马之贞」。大畜干阳在下,为艮所畜,三得上应,又畜极必通,故曰「良马逐」,可谓通快矣;然必艰难贞正,又且曰「闲舆卫」,然后「利有攸往」。设若恃良马之壮,而忘「艰贞」之戒,则必不利矣。干之九三,「君子终日干干」,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厉」,然后「无咎」也。凡读易而能句句体验,每存兢栗戒慎之意,则于己为有益;不然,亦空言尔。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此只是说蓍龟。若不是蓍龟,如何通之,定之,断之?到「蓍之德圆而神」以下,却是从源头说,而未是说卜筮。盖圣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浑然是此道理,不劳作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退藏于密」。所谓密者,只是他人自无可捉摸他处。便是「寂然不动」,「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蓍龟,故曰「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圣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于天之道」以下,方说蓍龟,乃是发用处。「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既具此理,又将此理复就蓍龟上发明出来,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圣人之德,又即卜筮斋戒以神明之。圣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龟之理以神明之。
「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蓍与卦以德言,爻以义言,只是具这道理在此而已,故「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浑然此理,别无他物;「退藏于密」,只是未见于用,所谓「寂然不动」也。下文说「神以知来」,便是以蓍之德知来;「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体,「知来藏往」言用。然亦只言体用具矣,而未及使出来处。到下文「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方发挥许多道理,以尽见于用也。然前段必结之以「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只是譬喻蓍龟虽未用,而神灵之理具在;犹武是杀人底事,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
「六爻之义易以贡。」今解「贡」字,只得以告人说。但「神」、「知」字重,「贡」字轻,却晓不得。学蒙。
「易以贡」,是变易以告人。「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以那易来洗濯自家心了,更没些私意小智在里许,圣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蓍龟而知卜筮,所以说「神武而不杀」。这是他有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又说个「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
前面一截说易之理,未是说到蓍卦卜筮处,后面方说卜筮。圣人之心浑只是圆神、方知、易贡三个物事,更无别物,一似洗得来净洁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杀底物事,神武却不杀。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这个却方是说他理,未到那用处。到下面「是以明于天之道」,方是说卜筮。
「以此洗心」,都只是道理。圣人此心虚明,自然具众理。「洁静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许多,不是安排对副与人;看是甚人来,自然撞着。易如此,圣人也如此,所以说个「蓍之德」,「卦之德」,「神明其德」。
「圣人以此洗心」,注云:「洗万物之心。」若圣人之意果如此,何不直言以此洗万物之心乎?大抵观圣贤之言,只作自己作文看。如本说洗万物之心,却止云「洗心」,于心安乎?
「退藏于密」时,固是不用这物事。「吉凶与民同患」,也不用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于密」,是不用事时。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时,先安排在这里了;事到时,恁地来,恁地应。
「退藏于密」,密是主静处。「万化出焉」者,动中之静固是静。又有大静,万化森然者。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载、圣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见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来之事,便是「知来」。
「圣人以此洗心」一段。圣人胸中都无纤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纯一,都无一毫之累,更无些迹,所谓「退藏于密」也。及其「吉凶与民同患」,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是谁人会恁地?非古人「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杀者」,圣人于天下自是所当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费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这便是『神武不杀』。」又曰:「『神以知来』,如明镜然,物事来都看见;『知以藏往』,只是见在有底事,他都识得。」又曰:「都藏得在这里。」又曰:「如揲蓍然。当其未揲,也都不知揲下来底是阴是阳,是老是少,便是『知来』底意思。及其成卦了,则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下文所以云『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设为卜筮,以为民之乡导。『故』,只是事。圣人于此,又以卜筮而『斋戒以神明其德』。『显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这『神』字,犹言吉凶阴若有神明之相相似。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为。」又曰:「这都只退听于鬼神。」又曰:「圣人于卜筮,其斋戒之心,虚静纯一,戒慎恐惧,只退听于鬼神。」学蒙。
「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如譬喻说相似。
「圣人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盖圣人见得天道、人事,都是这道理,蓍龟之灵都包得尽;于是作为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这里面。
问:「『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论得到极处,固只是一个道理;看时,须做两处看,方看得周匝无亏欠处。」问:「天之道,只是福善祸淫之类否?」曰:「如阴阳变化,春何为而生?秋何为而杀?夏何为而暑?冬何为而寒?皆要理会得。」问:「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类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会得民之故,却理会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极时,固只是一理。要之,须是都看得周匝,始得。」
「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开民,使民皆知。前时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这个开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则神明民德;圣人用之,则自神明其德。『蓍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于用。『圣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这个是有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明道爱举『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虽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举之。干问:「此恐是『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谓『敬是常惺惺法』。」又问:「此恐非是圣人分上事。」曰:「便是说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毕,再三诵之。
「神明其德」,言卜筮。尊敬也,精明也。
阖辟乾坤,理与事皆如此,书亦如此。这个只说理底意思多。「知礼成性」,横渠说得别。他道是圣人成得个性,众人性而未成。
问:「『阖户之谓坤』一段,只是这一个物。以其阖,谓之坤;以其辟,谓之干;以其阖辟,谓之变;以其不穷,谓之通。发见而未成形谓之象,成形谓之器。圣人修礼立教谓之法,百姓日用则谓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离他不得。」又曰:「民之于易,随取而各足;易之于民,周遍而不穷,所以谓之神。所谓『活泼泼地』,便是这处。」学蒙。
太极中,全是具一个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恶,皆阴阳变化以后方有。
周子康节说太极,和阴阳滚说。易中便抬起说。周子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如言太极动是阳,动极而静,静便是阴;动时便是阳之太极,静时便是阴之太极,盖太极即在阴阳里。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则先从实理处说。若论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但言其次序,须有这实理,方始有阴阳也。其理则一。虽然,自见在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学履。
问「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极却是为画卦说。当未画卦前,太极只是一个浑沦底道理,里面包含阴阳、刚柔、奇耦,无所不有。及各画一奇一耦,便是生两仪。再于一奇画上加一耦,此是阳中之阴;又于一奇画上加一奇,此是阳中之阳,又于一耦画上加一奇,此是阴中之阳;又于一耦画上加一耦,此是阴中之阴,是谓四象。所谓八卦者,一象上有两卦,每象各添一奇一耦,便是八卦。尝闻一朋友说,一为仪,二为象,三为卦,四为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东西南北,无不可推矣。」去伪同。
明之问「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易有太极』,便有个阴阳出来,阴阳便是两仪。仪,匹也。『两仪生四象』,便是一个阴又生出一个阳,●是一象也;一个阳又生一个阴,●是一象也;一个阴又生一个阴,●是一象也;一个阳又生一个阳,●是一象也,此谓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这四个象生四阴时,便成坎震坤兑四卦,生四个阳时,便成巽离艮干四卦。震。
干|──┐
├──|──┐
兑|──┘
│
├──|───┐
离|──┐
│
│
├──|──┘
│
震|──┘
│
├──太极
巽|──┐
│
├──|──┐
│
坎|──┘
│
│
├──|───┘
艮|──┐
│
├──|──┘
坤|──┘
「每卦变八卦,为六十四卦。」
「易有太极」,便是下面两仪、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总为六十四,自六十四总为八卦,自八卦总为四象,自四象总为两仪,自两仪总为太极。以物论之,易之有太极,如木之有根,浮屠之有顶。但木之根,浮图之顶,是有形之极;太极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顿放,是无形之极。故周子曰:「无极而太极。」是他说得有功处。夫太极之所以为太极,却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指一阴一阳为道则不可,而道则不离乎阴阳也。
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枝干,又分而生花生叶,生生不穷。到得成果子,里面又有生生不穷之理,生将出去,又是无限个太极,更无停息。只是到成果实时,又却少歇,不是止。到这里自合少止,正所谓「终始万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龟。」人到疑而不能自明处,往往便放倒,不复能向前,动有疑阻。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
右第十一章
问「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一章。曰:「『立象尽意』,是观奇耦两画,包含变化,无有穷尽。『设卦以尽情伪』,谓有一奇一耦,设之于卦,自是尽得天下情伪。系辞便断其吉凶。『变而通之以尽利』,此言占得此卦,阴阳老少交变,因其变,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尽神』,未占得则有所疑,既占则无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轻手快,行得顺便。如『大衍』之后,言『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这又是言『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易不过只是一个阴阳奇耦,千变万变,则易之体立。若奇耦不交变,奇纯是奇,耦纯是耦,去那里见易?易不可见,则阴阳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问:「在天地上如何?」曰:「关天地甚么事?此是说易不外奇耦两物而已。『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是两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属前项事,谓渐渐化去,裁制成变,则谓之变;『推而行之』,属后项事,谓推而为别一卦了,则通行无碍,故为通。『举而措之天下谓之事业』,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谓卦体之中备阴阳变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是说出这天下之动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辞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个阴阳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与形而上之道相对说。自『形而上谓之道』,说至于『变、通、事、业』,却是自至约处说入至粗处去;自『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说至于『神而明之』,则又是由至粗说入至约处。『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则说得又微矣。」学履。
问:「『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圣人设问之辞?」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尽意,故立象以尽意;书不足以尽言,故因系辞以尽言。」又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元旧有此语。」又曰:「『立象以尽意』,不独见圣人有这意思写出来,自是他象上有这意。『设卦以尽情伪』,不成圣人有情又有伪!自是卦上有这情伪,但今晓不得他那处是伪。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辞支,诬善之人其辞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不知那卦上见得?」沈思久之,曰:「看来『情伪』只是个好不好。如剥五阴,只是要害一个阳,这是不好底情,便是伪。如复,如临,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学蒙。
问:「『立象』、『设卦』、『系辞』,是圣人发其精意见于书?『变、通、鼓、舞』,是圣人推而见于事否?」曰:「是。」学蒙。
「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立象」、「设卦」、「系辞」,皆为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趋吉,奋然有所兴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犹催迫天下之人,勉之为善相似。
问:「『变而通之』,如礼乐刑政,皆天理之自然,圣人但因而为之品节防范,以为教于天下;『鼓之舞之』,盖有以作兴振起之,使之迁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无所用力,自是圣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但乐占得分数较多,自是乐会如此而不自知。」因举横渠云云。巫,其舞之尽神者。『巫』,从『工』,两边『人』字是取象其舞。巫者托神,如舞雩之类,皆须舞。盖以通畅其和气,达于神明。」
问:「『鼓之舞之以尽神。』又言:『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鼓舞,恐只是振扬发明底意思否?」曰:「然。盖提撕警觉,使人各为其所当为也。如初九当潜,则鼓之以『勿用』;九二当见,则鼓之以『利见大人』。若无辞,则都发不出了。」
「鼓之舞之以尽神」,鼓舞有发动之意,亦只如「成天下之亹亹」之义。「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是因易之辞而知吉凶后如此。
「乾坤其易之缊。」向论「衣敝缊袍」,缊是绵絮胎,今看此「缊」字,正是如此取义。易是包着此理,乾坤即是易之体骨耳。人杰录云:「缊,如『缊袍』之『缊』,是个胎骨子。」
问「乾坤其易之缊」。曰:「缊是袍中之胎骨子。『乾坤成列』,便是干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都成列了,其变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阴一阳,则未有变易在。」又曰:「有这卦,则有变易;无这卦,便无这易了。」又曰:「『易有太极』,则以易为主;此一段文意,则以乾坤为主。」学蒙。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说二卦,此易,只是说易之书,与「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说易之道理。
问:「『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说两画之列?是说八卦之列?」曰:「两画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学蒙。
问:「『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晓。至如『易立乎其中』,岂非乾坤既成列之后,道体始有所寓而形见?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尔』之『立』乎?」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况所谓『如有所立卓尔』,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后世之论多是说得太高,不必如此说。」
「乾坤毁」,此乾坤只言卦。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只是阴阳卦画,没这几个卦画,凭个甚写出那阴阳造化?何处更得易来?这只是反复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只是说揲蓍求卦,更推不去,说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说较平。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体也;乾坤健顺,用也。
形是这形质,以上便为道,以下便为器,这个分别得最亲切,故明道云:「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虚,浑是道理;形以下底实,便是器。」
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
「形而上谓道,形而下谓器。」这个在人看始得。指器为道,固不得;离器于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里。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即事即物,便要见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实于事物上见得这个道理,然后于己有益。「为人君,止于仁;为人子,止于孝。」必须就君臣父子上见得此理。大学之道不曰「穷理」,而谓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实处穷竟。事事物物上有许多道理,穷之不可不尽也。
「伊川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须着如此说。』」曰:「这是伊川见得分明,故云『须着如此说』。『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开说,方见分明。如此了,方说得道不离乎器,器不遗乎道处。如为君,须止于仁,这是道理合如此。『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说,便不索性。两边说,怎生说得通?」
问:「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问:「阴阳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阴阳。寒暖生杀皆见得,是『形而下者』。事物虽大,皆『形而下者』,尧舜之事业是也。理虽小,皆『形而上者』。」
「『形而上者谓之道』一段,只是这一个道理。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圣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则谓之变;推而行之,则谓之通;举而措之,则谓之事业。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这个道。」曰:「是。」
问「化而裁之谓之变」。曰:「化,是渐渐移将去;截断处便是变。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断做一月,便是变。」又曰:「最是律管长短可见。」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为,变是变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须待一日日渐次进去,到那满时,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圣人去这里截做四时,这便是变。化不是一日内便顿然恁地底事。人之进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时便立,须从十五志学渐渐化去,方到。横渠去这里说做「化而裁之」,便是这意。柔变而趋于刚,刚化而趋于柔,与这个意思也只一般。自阴来做阳,其势浸长,便觉突兀有头面。自阳去做阴,这只是渐渐消化去。这变化之义,亦与鬼神屈伸意相似。方子录云:「阳化而为阴,只恁消缩去,无痕迹,故谓之化。阴变而为阳,其势浸长,便觉突兀有头面,故谓之变。」
变、化二者不同,化是渐化,如自子至亥,渐渐消化,以至于无。如自今日至来日,则谓之变,变是顿断有可见处。横渠说「化而裁之」一段好。
「横渠说『化而裁之谓之变』一句,说得好。不知本义中有否?」曰:「无。」「但寻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潜,而为九二之见,这便是化;就他化处截断,便是变?」曰:「然。化是个亹亹地去,有渐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气渐渐地凉将去,到得立秋,便截断,这已后是秋,便是变。」问:「如此,则『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问:「『化而裁之谓之变』,又云『存乎变』,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唤做变。下文是说变处见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这三十日裁断做一月,明日便属后月,便是变。此便是『化而裁之』,到这处方见得。」学履。
「化而裁之存乎变」,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变,如子丑寅卯十二时皆以渐而化,不见其化之之迹。及亥后子时,便截取是属明日,所谓变也。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义。谓如一岁裁为四时,一时裁为三月,一月裁为三十日,一日裁为十二时,此是变也。又如阴阳两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断,则岂有定体?通,是「通其变」。将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即是通。谓如占得干之履,便是九三干干不息,则是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于民,则谓之事业也。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头项:「推而行之」,便是见于事。如尧典分命羲和许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时」,便是「推而行之」。学履。
问:「易中多言『变通』,『通』字之意如何?」曰:「处得恰好处便是通。」问:「『往来不穷谓之通』,如何?」曰:「处得好,便不穷。通便不穷,不通便穷。」问:「『推而行之谓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这上行将去。且如『亢龙有悔』,是不通了;处得来无悔,便是通。变是就时、就事上说,通是就上面处得行处说,故曰『通其变』。只要常教流通不穷。」问:「如『贫贱、富贵、夷狄、患难』,这是变;『行乎富贵,行乎贫贱,行乎夷狄,行乎患难』,至于『无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右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