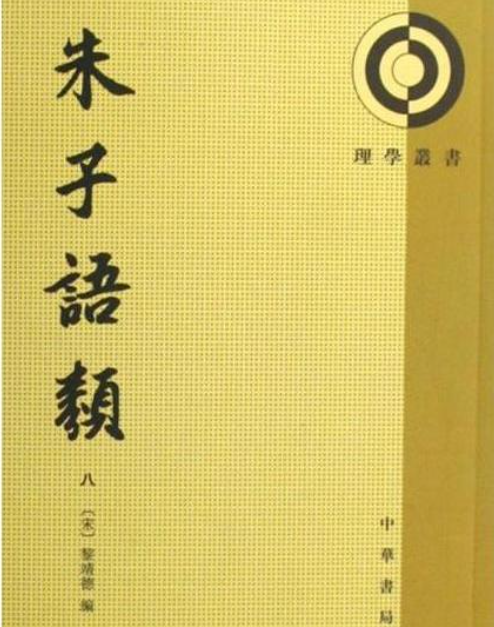论文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饶录云:「国语说得絮,只是气衰。又不如战国文字,更有些精彩。」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也!又曰:「国语文字极困苦,振作不起。战国文字豪杰,便见事情。非你杀我,则我杀你。」黄云:「观一时气象如此,如何遏捺得住!所以启汉家之治也。」
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楚词。
问离骚卜居篇内字。曰:「字义从来晓不得,但以意看可见。如『突梯滑稽』,只是软熟迎逢,随人倒,随人起底意思。如这般文字,更无些小窒碍。想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林艾轩尝云:『班固扬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今看来是如此。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这也须是敏,须是会说得通畅。如古者或以言扬,说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就纸上做。如就纸上做,则班扬便不如已前文字。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又云:「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将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杂。」
楚些,沈存中以「些」为咒语,如今释子念「娑婆诃」三合声,而巫人之祷亦有此声。此却说得好。盖今人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故下一半都晓不得。离骚协韵到篇终,前面只发两例。后人不晓,却谓只此两韵如此。
楚词注下事,皆无这事。是他晓不得后,却就这语意撰一件事为证,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经,皆是如此。
高斗南解楚词引瑞应图。周子充说馆阁中有此书,引得好。他更不问义理之是非,但有出处便说好。且如天问云:「启棘宾商。」山海经以为启上三嫔于天,因得九叹九辨以归。如此,是天亦好色也!柳子厚天对,以为胸嫔,说天以此乐相博换得。某以为「棘」字是「梦」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如郑康成解记「衣衰」作「齐衰」,云是坏字也,此亦是擦坏了。盖启梦宾天,如赵简子梦上帝之类。宾天是为之宾,天与之以是乐也。今人不曾读古书,如这般等处,一向恁地过了。陶渊明诗:「形夭无千岁。」曾氏考山海经云:「当作『形天舞干戚』。」看来是如此。周子充不以为然,言只是说精卫也,此又不用出处了。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道夫录云:「古今拟骚之作,惟鲁直为无谓。」
古赋虽熟,看屈宋韩柳所作,乃有进步处。入本朝来,骚学殆绝,秦黄晁张之徒不足学也。
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欧公蝉赋:「其名曰蝉。」这数句也无味。
楚词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
汉初贾谊之文质实。晁错说利害处好,答制策便乱道。董仲舒之文缓弱,其答贤良策,不答所问切处;至无紧要处,有累数百言。东汉文章尤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如杨震辈皆尚谶纬,张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会风角、鸟占,何愈于谶纬!陵夷至于三国两晋,则文气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如相如封禅书,模仿极多。柳子厚见其如此,却作贞符以反之,然其文体亦不免乎蹈袭也。汉文。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老苏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实。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比之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更实。到杜钦谷永书,又太弱无归宿了。匡衡书多有好处,汉明经中皆不似此。
仲舒文大概好,然也无精彩。
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佐录作「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
问:「吕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邹阳狱中书已自皆作对子了。」又问:「司马相如赋似作之甚易。」曰:「然。」又问:「高适焚舟决胜赋甚浅陋。」曰:「文选齐梁间江总之徒,赋皆不好了。」因说:「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时,皆有赋。』周美成闻之,遂撰汴都赋进。上大喜,因朝降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时,即合诵一遍。宰相不知是谁,知古赋中必有难字,遂传与第二人,以次传至尚书右丞王和甫,下无人矣。和甫即展开琅然诵一遍。上喜,既退,同列问如何识许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读傍文。』扬录作「一边」。吕编文鉴,要寻一篇赋冠其首,又以美成赋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凤楼赋为首,美成赋亦在其后。」
宾戏解嘲剧秦贞符诸文字,皆祖宋玉之文,进学解亦此类。阳春白雪云云者,不记其名,皆非佳文。
夜来郑文振问:「西汉文章与韩退之诸公文章如何?」某说:「而今难说。便与公说某人优,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须是自看得这一人文字某处好,某处有病,识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见优劣如何。若看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优劣!便说与公优劣,公亦如何便见其优劣处?但子细自看,自识得破。而今人所以识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细看。又兼是先将自家意思横在胸次,所以见从那偏处去,说出来也都是横说。」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间却不得用。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元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又云:「苏子由有一段论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郑齐叔云,做文字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着。横渠云:『发明道理,惟命字难。』要之,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或曰:「子瞻云:『都来这几字,只要会铺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岁以前气格都定,但有精与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较精。向见韩无咎说,它晚年做底文字,与他二十岁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远,此是它自验得如此。人到五十岁,不是理会文章时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后生时,每日便偷一两时闲做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识却会长进。」曰:「也是后生时都定,便长进也不会多。然而能用心于学问底,便会长进。若不学问,只纵其客气底,亦如何会长进?日见昏了。有人后生气盛时,说尽万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阘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学,便老而衰。」曰:「只这一句说尽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读书。某人戏之曰:『吾丈老年读书,也须还读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谓其不能发挥出来为做文章之用也。」其说虽粗,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笔写字,全无锋锐可观。」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学人做文章,后来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后来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岁做底文字。」又云:「刘季章近有书云,他近来看文字,觉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这个,虚心看文字。盖他向来便是硬自执他说,而今又是将这一说来罩正身,未理会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执他底横说,如王介甫陆子静都只是横说。且如陆子静说文帝不如武帝,岂不是横说!」又云:「介甫诸公取人,如资质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稳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说他转时易。大率都是硬执他底。」
张以道曰:「『眄庭柯以怡颜』,眄,读如俛,读作盼者非。」
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圣锡云:「国初制诏虽粗,却甚好。」又如汉高八年诏与文帝即位诏,只三数句,今人敷衍许多,无过只是此个柱子。韩柳。
先生方修韩文考异,而学者因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如辨鹖冠子及说列子在庄子前及非国语之类,辨得皆是。」黄达才言:「柳文较古。」曰:「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夔孙录云:「韩文大纲好,柳文论事却较精核,如辨鹖冠子之类。非国语中尽有好处。但韩难学,柳易学。」
扬因论韩文公,谓:「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书之真伪?」曰:「鹖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谓其书乃写贾谊鹏赋之类,故只有此处好,其它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韩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较含洪,便不能如此。」
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且教他在潮州时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
柳学人处便绝似。平淮西雅之类甚似诗,诗学陶者便似陶。韩亦不必如此,自有好处,如平淮西碑好。
陈仲蔚问:「韩文禘义,说懿献二庙之事当否?」曰:「说得好。其中所谓『兴圣庙』者,乃是叙武昭王之庙,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皋陶为帝,又尊老子为祖,更无理会。」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问:「子厚论封建是否?」曰:「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但说到后面有偏处,后人辨之者亦失之太如廖氏所论封建,排子厚太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类,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且如射王中肩之事,乃是周末征伐自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然封建诸侯,却大故难制御。且如今日蛮洞,能有几大!若不循理,朝廷亦无如之何。若古时有许多国,自是难制。如隐公时原之一邑,乃周王不奈他何,赐与郑,郑不能制;到晋文公时,周人将与晋,而原又不服,故晋文公伐原。且原之为邑甚小,又在东周王城之侧,而周王与晋郑俱不能制。盖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处,便可以降官放罢。古者大率动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在周官时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势不同,便是难说。」因言:「孟子所谓五等之地,与周礼不同。孟子盖说夏以前之制,周礼乃是成周之制。如当时封周公于鲁,乃七百里。于齐尤阔,如所谓『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以地理考之,大段阔。所以禹在涂山,万国来朝。至周初,但千八百国。」又曰:「譬如一树,枝叶太繁时,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则欲削去枝叶而自留一干,亦自不可。」
有一等人专于为文,不去读圣贤书。又有一等人知读圣贤书,亦自会作文,到得说圣贤书,却别做一个诧异模样说。不知古人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许多诧异!韩文公诗文冠当时,后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书,用「菁菁者莪」,诗注一齐都写在里面。若是他自作文,岂肯如此作?最是说「载沉载浮」,「沉浮皆载也」,可笑!「载」是助语,分明彼如此说了,他又如此用。韩文。
退之除崔群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别更无,不知如何。
或问:「伯夷颂『万世标准』与『特立独行』,虽足以明君臣之大义,适权通变,又当循夫理之当然者也。」先生曰:「说开了,当云虽武王周公为万世标准,然伯夷叔齐惟自特立不顾。」又曰:「古本云:『一凡人沮之誉之。』与彼夫圣人是一对,其文意尤有力。」椿。
退之送陈彤秀才序多一「不」字,旧尝疑之,只看过了。后见谢子畅家本,乃后山传欧阳本,圈了此「不」字。
韩退之墓志有怪者了。
先生喜韩文宴喜亭记及韩弘碑。碑,老年笔。
「唐僧多从士大夫之有名者讨诗文以自华,如退之送文畅序中所说,又如刘禹锡自有一卷送僧诗。」或云:「退之虽辟佛,也多要引接僧徒。」曰:「固是。他所引者,又却都是那破赖底僧,如灵师惠师之徒。及晚年见大颠于海上,说得来阔大胜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脱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
先辈好做诗与僧,僧多是求人诗序送行。刘禹锡文集自有一册送僧诗,韩文公亦多与僧交涉,又不曾见好僧,都破落户。然各家亦被韩文公说得也狼狈。文公多只见这般僧,后却撞着一个大颠,也是异事。人多说道被大颠说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会他病痛,彼他纔说得高,便道是好了,所以有「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之语。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且如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却解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若如此,非惟失圣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当时,必与他辩。」却笑曰:「必被他无礼。」友仁。
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更说些也不妨。封建论并数长书是其好文,合尖气短。如人火忙火急来说不及,又便了了。柳文。
柳子厚文有所模仿者极精,如自解诸书,是仿司马迁与任安书。刘原父作文便有所仿。
「宫沉羽振,锦心绣口」,柳子厚语。
韩千变万化,无心变;欧有心变。杜祈公墓志说一件未了,又说一件。韩董晋行状尚稍长。权德舆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许,欧苏便长了。苏体只是一类。柳伐原议极局促,不好,东莱不知如何喜之。陈后山文如仁宗飞白书记大段好,曲折亦好,墓志亦好。有典有则,方是文章。其它文亦有大局促不好者,如题太白像、高轩过古诗,是晚年做到平易处,高轩过恐是绝笔。又一条云:「后山仁宗飞白书记,其文曲折甚多,过得自在,不如柳之局促。」总论韩柳欧苏诸公。
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豊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但采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若班马孟子,则是大底文字。
韩文欧阳文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又云:「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了许多气力。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佑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国朝文。
刘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因言,杜诗亦何用?曰:「是无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益得人甚事?」因伤时文之弊,谓:「张才叔书义好。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胡明仲醉后每诵之。」又谓:「刘棠舜不穷其民论好,欧公甚喜之。其后姚孝宁易义亦好。」寿昌录云:「或问太极西铭。」曰:「自孟子以后,方见有此两篇文章」。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首卷潜书民言好,如古潜夫论之类。周礼论好,如宰相掌人主饮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论皆然,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如此好。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范文正公好处,欧不及。李晚年须参道,有一记说达磨宗派甚详,须是大段去参究来。又曰:「以李视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妇然。某人辈文字,乃蛇鼠之见。」
先生读宋景文张巡赞,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尝见其写六一泷冈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温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语。
六一文一倡三叹,今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如秘演诗集序『喜为歌诗以自娱』,『十年间』,两节不接。六一居士传意凡文弱。仁宗飞白书记文不佳。制诰首尾四六皆治平间所作,非其得意者。恐当时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缓,不及子细,不知如何。然有纡余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比。黄梦升墓志极好。」问先生所喜者。云:「丰乐亭记。」
陈同父好读六一文,尝编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丰乐亭记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编在拾遗。
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尝有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拱寿。
「钦夫文字不甚改,改后往往反不好。」亚夫曰:「欧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尽处,如五代史宦者传末句云:『然不可不戒。』当时必有载张承业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后既不欲载之于此,而移之于后,则此句当改,偶忘削去故也。」
因改谢表,曰:「作文自有稳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着这样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饶录作「见」。得他醉翁亭记稾,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饶录云:「有数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边注「环滁皆山也」一句。如寻常不经思虑,信意所作言语,亦有绝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
前辈见人,皆通文字。先生在同安,尝见六一见人文字三卷子,是以平日所作诗文之类楷书以献之。
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儒用。
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荆公文暗。
「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后来到中原,见欧公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苏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会大段巧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广问:「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丰文,但比南丰文亦巧。荆公曾作许氏世谱,写与欧公看。欧公一日因曝书见了,将看,不记是谁作,意中以为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广又问:「后山文如何?」曰:「后山煞有好文字,如黄楼铭馆职策皆好。」又举数句说人不怨暗君怨明君处,以为说得好。广又问:「后山是宗南丰文否?」曰:「他自说曾见南丰于襄汉间。后见一文字,说南丰过荆襄,后山携所作以谒之。南丰一见爱之,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后山为之,且授以意。后山文思亦涩,穷日之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为略删动否?』后山因请改窜。但见南丰就坐,取笔抹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所以后山文字简洁如此。」广因举秦丞相教其子孙作文说,中说后山处。曰:「他都记错了。南丰入史馆时,止为检讨官。是时后山尚未有官。后来入史馆,尝荐邢和叔。虽亦有意荐后山,以其未有官而止。」扬录云:「秦作后山叙,谓南丰辟陈为史官。陈元佑间始得官,秦说误」。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晓得义理底人,少间被物欲激搏,犹自一强一弱,一胜一负。如文章之士,下梢头都靠不得。且如欧阳公初间做本论,其说已自大段拙了,然犹是一片好文章,有头尾。它不过欲封建、井田,与冠、婚、丧、祭、搜田、燕飨之礼,使民朝夕从事于此,少间无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变。其计可谓拙矣,然犹是正当议论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碁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如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说无限道理。到得晚年过海,做过化峻灵王庙碑,引唐肃宗时一尼恍惚升天,见上帝,以宝玉十三枚赐之云,中国有大灾,以此镇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宝云云,更不成议论,似丧心人说话!其它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
问:「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当看其大者。」曰:「东坡文说得透,南丰亦说得透,如人会相论底,一齐指摘说尽了。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意又好。」因谓张定夫言,南丰秘阁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灵王庙碑无见识,伏波庙碑亦无意思。伏波当时踪迹在广西,不在彼中,记中全无发明。」扬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笔健。」曰:「然」。又问:「潜真阁铭好?」曰:「这般闲戏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韩文公庙碑之类,初看甚好读,子细点检,疏漏甚多。」又曰:「东坡令其侄学渠兄弟蚤年应举时文字。」
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东坡晚年文虽健,不衰,然亦疏鲁,如南安军学记,海外归作,而有「弟子扬觯序点者三」之语!「序点」是人姓名,其疏如此!
六一记菱溪石,东坡记六菩萨,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气象不类如此。
老苏之文高,只议论乖角。
老苏文字初亦喜看,后觉得自家意思都不正当。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欧曾文字为正。东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议论衰了。东坡初进策时,只是老苏议论。
坡文雄健有余,只下字亦有不贴实处。
坡文只是大势好,不可逐一字去点检。
东坡墨君堂记,只起头不合说破「竹」字。不然,便似毛颖传。必大
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尽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
统领商荣以温公神道碑为饷。先生命吏约道夫同视,且曰:「坡公此文,说得来恰似山摧石裂。」道夫问:「不知既说『诚』,何故又说『一』?」曰:「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处。」顷之,直卿至,复问:「若说『诚之』,则说『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说,盖诚则自能一。」问:「大凡作这般文字,不知还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据他一直恁地说将去,初无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说起头时,自未知后面说甚么在。」以手指中间曰:「到这里,自说尽,无可说了,却忽然说起来。如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某旧看二家之文,复看坡文,觉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尝闻东坡作韩文公庙碑,一日思得颇久。饶录云:「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忽得两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遂扫将去。」道夫问:「看老苏文,似胜坡公。黄门之文,又不及东坡。」曰:「黄门之文衰,远不及,也只有黄楼赋一篇尔。」道夫因言欧阳公文平淡。曰:「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却不是阘茸无意思。」又曰:「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坡公文如说不办后,对人闹相似,都无恁地安详。」蜚卿问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如唐鉴虽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评论总意不尽。只是文字本体好,然无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处;无气力,到后面多脱了。」道夫因问黄门古史一书。曰:「此书尽有好处。」道夫曰:「如他论西门豹投巫事,以为他本循良之吏,马迁列之于滑稽,不当。似此议论,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处。如论庄子三四篇讥议夫子处,以为决非庄子之书,乃是后人截断庄子本文搀入,此其考据甚精密。由今观之,庄子此数篇亦甚鄙俚。」
或问:「苏子由之文,比东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说利害处,东坡文字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晓。要之,学术只一般。」因言:「东坡所荐引之人多轻儇之士。若使东坡为相,则此等人定皆布满要路,国家如何得安静!」
诸公祭温公文,只有子由文好。
欧公大段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看得来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见欧公有不公处。」或曰:「圣俞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拱寿。
范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下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若做文字时,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
「后来如汪圣锡制诰,有温润之」曾问某人,前辈四六语孰佳?答云:「莫如范淳夫。」因举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辅之先;汉重王苍,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荆王;顾予冲人,敢后兹典!』自然平正典重,彼工于四六者却不能及。」
刘原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绝相似。有几件文字学礼记,春秋说学公谷,文胜贡父。
刘贡父文字工于摹仿。学公羊仪礼。
苏子容文慢。
南丰文字确实。
问:「南丰文如何?」曰:「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东坡则华艳处多。」或言:「某人如搏谜子,更不可晓。」曰:「然。尾头都不说破,头边做作扫一片去也好。只到尾头,便没合杀,只恁休了。篇篇如此,不知是甚意思。」或曰:「此好奇之」曰:「此安足为奇!观前辈文章如贾谊董仲舒韩愈诸人,还有一篇如此否?夫所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然细观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见,何尝如此不说破?其所以不说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独会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惟其好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
曾所以不及欧处,是纡徐扬录作「余」。曲折处。曾喜仿真人文字,拟岘台记,是仿醉翁亭记,不甚似。
南丰拟制内有数篇,虽杂之三代诰命中亦无愧。
南丰作宜黄筠州二学记好,说得古人教学意出。
南丰列女传序说二南处好。
南丰范贯之奏议序,气脉浑厚,说得仁宗好。东坡赵清献神道碑说仁宗处,其文气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丰不说。子由挽南丰诗,甚服之。
两次举南丰集中范贯之奏议序末,文之备尽曲折处。
南丰有作郡守时榜之类为一集,不曾出。先生旧喜南丰文,为作年谱。
问:「尝闻南丰令后山一年看伯夷传,后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则自然有自得处。」
江西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
「陈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楼铭,当时诸公都敛衽。」佐录云:「便是今人文字都无他抑扬顿挫。」因论当世人物,有以文章记问为能,而好点检它人,不自点检者。曰:「所以圣人说:『益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
馆职策,陈无己底好。
李清臣文饱满,杂说甚有好议论。
李清臣文比东坡较实。李舜举永乐败死,墓志说得不分不明,看来是不敢说。
桐阴旧话载王铚云,李邦直作韩太保惟忠墓志,乃孙巨源文也。先生曰:「巨源文温润,韩碑径,只是邦直文也。」
论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实,但奏议每件引春秋,亦有无其事而迁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论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晓。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论青苗,只是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他人皆说从别处去。
胡侍郎万言书,好令后生读,先生旧亲写一册。又曰:「上殿札子论元老好,无逸解好,请行三年丧札子极好。诸奏议、外制皆好。
陈几道存诚斋铭,某初得之,见其都是好义理堆积,更看不办。后子细诵之,却见得都是凑合,与圣贤说底全不相似。其云:「又如月影散落万川,定相不分,处处皆圆。」这物事不是如此。若是如此,孔孟却隐藏着不以布施,是何心哉!乃知此物事不当恁地说。
张子韶文字,沛然犹有气,开口见心,索性说出,使人皆知。近来文字,开了又阖,阖了又开,开阖七八番,到结末处又不说,只恁地休了。
文章轻重,可见人寿夭,不在美恶上。白鹿洞记力轻。韩元吉虽只是胡说,然有力。吴逵文字亦然。
韩无咎文做着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佐。
王龟龄奏议气象大。
曾司直大故会做文字,大故驰骋有法度。裘父大不及他。裘父文字涩,说不去。
陈君举西掖制词殊未得体。王言温润,不尚如此。胡明仲文字却好。
或言:「陈蕃叟武不喜坡文,戴肖望溪不喜南丰文。」先生曰:「二家之文虽不同,使二公相见,曾公须道坡公底好,坡公须道曾公底是。」
德粹语某人文章。先生曰:「绍兴间文章大抵粗,成段时文。然今日太细腻,流于委靡。」问贤良。先生曰:「贤良不成科目。天下安得许多议论!」以下论近世之文。
「诸公文章驰骋好异。止缘好异,所以见异端新奇之说从而好之。这也只是见不分晓,所以如此。看仁宗时制诏之文极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气象自恁地深厚久长;固是拙,只是他所见皆实。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当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识了不下,只是他当初自思量不到。然气象尽好,非如后来之文一味纤巧不实。且如进卷,方是二苏做出恁地壮伟发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张方平进策,更不作文,只如说盐铁一事,他便从盐铁原头直说到如今,中间却载着甚么年,甚么月,后面更不说措置。如今只是将虚文漫演,前面说了,后面又将这一段翻转,这只是不曾见得。所以不曾见得,只是不曾虚心看圣贤之书。固有不曾虚心看圣贤书底人,到得要去看圣贤书底,又先把他自一副当排在这里,不曾见得圣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某如今看来,惟是聪明底人难读书,难理会道理。盖缘他先自有许多一副当,圣贤意思自是难入。」因说:「陈叔向是白撰一个道理。某尝说,教他据自底所见恁地说,也无害,只是又把那说来压在这里文字上。他也自见得自底虚了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将两个要捏做一个得?一个自方,一个自圆,如何总合得?这个不是他要如此,止缘他合下见得如此。如杨墨,杨氏终不成自要为我,墨氏终不成自要兼爱,只缘他合下见得错了。若不是见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杨氏壁立万仞,毫发不容,较之墨氏又难。若不是他见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陈叔向所见咤异,它说『目视己色,耳听己声,口言己事,足循己行』。有目固当视天下之色,有耳固当听天下之声,有口固能言天下之事,有足固当循天下之行,他却如此说!看他意思是如此,只要默然静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听别人说话,不说别人是非,不管别人事。又如说『言忠信,行笃敬』一章,便说道紧要只在『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问道:『见是见个甚么物事?』他便说:『见是见自家身己。』某与说,『立』是自家身己立在这里了,『参于前』又是自家身己;『在舆』是自家身己坐在这里了,『倚于衡』又是自家身己,却是有两个身己!又说格物做心,云:『格住这心,方会知得到。』未尝见人把物做心,与他恁地说,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见为急。圣人尚说:『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若只恁地死守得这个心便了,圣人又须要人讲学何故?若只守这心,据自家所见做将去,少间错处都不知。」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若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晓,自是其所见未到耳。学者须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见。何尝如今人欲说又不敢分晓说!不知是甚所见。毕竟是自家所见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鹘突说在里。
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如舞讶鼓然,其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底。旧见徐端立言,石林尝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法尔。如言『湖州』,必须去『州』字,只称『湖』,此减字法也;不然,则称『霅上』,此换字法也。」盖卿录云:「今人做文字,却是胭脂腻粉妆成,自是不壮浪,无骨如舞讶鼓相似,也有男儿,也有妇女,也有僧、道、秀才,但都是假底。尝见徐端立言,石林尝云:『今世文章只是用换字、减字法。如说「湖州」,只说「湖」,此减字法;不然,则称「霅上」,此换字法。尝见张安道进卷,其文皆有直』」谦录云:「『今来文字,至无气骨。向来前辈虽是作时文,亦是朴实头铺事实,朴实头引援,朴实头道理。看着虽不入眼,却有骨今人文字全无骨气,便似舞讶鼓者,涂眉画眼,僧也有,道也有,妇人也有,村人也有,俗人也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过本样人。然皆足以惑众,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怀挟所致。』曰:『不然。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正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做起,一人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
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以下论作文。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欧公之文则稍近于道,不为空言。如唐礼乐志云:「三代而上,治出于一;三代而下,治出于二。」此等议论极好,盖犹知得只是一本。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也。寿昌。
诗律杂文,不须理会。科举是无可柰何,一以门户,一以父兄在上责望。科举却有了时,诗文之类看无出时芝。
一日说作文,曰:「不必着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
问:「要看文以资笔势言语,须要助发义理。」曰:「可看孟子韩文。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如欧曾却各有一个科段。却曾学曾,为其节次定了。今觉得要说一意,须待节次了了,方说得到。及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又云:「方之文有涩处。」因言:「陈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韩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坏了,如何更看韩文!」
因论文,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如张承业及宦者等传自然好。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殊不起发人意思。」
文章要理会本领。谓理。前辈作者多读书,亦随所见理会,今皆仿贤良进卷胡作。
每论著述文章,皆要有纲领。文定文字有纲领,龟山无纲领,如字说三经辨之类。
前辈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份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人却厌其常格,则变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时先差去声。异了。又云:「前辈用言语,古人有说底固是用,如世俗常说底亦用。后来人都要别撰一般新奇言语,下梢与文章都差异了,却将差异底说话换了那寻常底说话。
问「舍弟序子文字如何进工夫」云云。曰:「看得韩文熟。」饶录云:「看一学者文字,曰:『好好读得韩文熟。』」又曰:「要做好文字,须是理会道理。更可以去韩文上一截,如西汉文字用工。」问:「史记如何?」曰:「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问后山学史记。曰:「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然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又曰:「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去,没收煞。」
文字奇而稳方好。不奇而稳,只是阘靸。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颓塌,只略教整齐足矣。
前辈作文者,古文有名文字,皆仿真作一篇。故后有所作时,左右逢原。
因论诗,曰:「尝见傅安道说为文字之法,有所谓『笔力』,有所谓『笔路』。笔力到二十岁许便定了,便后来长进,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笔路则常拈弄时,转开拓;不拈弄,便荒废。此说本出于李汉老,看来作诗亦然。」
因说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
至之以所业呈先生,先生因言:「东莱教人作文,当看获麟解,也是其间多曲折。」又曰:「某旧最爱看陈无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谓诸生曰:「韩柳文好者不可不看。」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
因论今日举业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
尝与后生说:「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旧见某人作马政策云:『观战,奇也;观战胜,又奇也;观骑战胜,又大奇也!』这虽是粗,中间却有好意思。如今时文,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脚,三句题也要立两脚,这是多少衰气!」
后人专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辈云:「言众人之所未尝,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气魄!今成甚么文字!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须取入规矩;不然,荡将去。
因论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读汉书之类,便去收拾三两个字。洪迈又较过人,亦但逐三两行文字笔势之类好者读看。因论南丰尚解使一二字,欧苏全不使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长,照管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文皆说不曾尽。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
文字或作「做事」。无大纲领,拈掇不起。某平生不会做补接底文字,补协得不济事。
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只有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
因论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论古今利害,比并为说,曰:「不必如此,只要明义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与古人合者,只为理一故也。」
人做文字不着,只是说不着,说不到,说自家意思不尽。
看陈蕃叟同合录序,文字艰涩。曰:「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
因说作应用之文,「此等苛礼,无用亦可。但人所共享,亦不可废」。曹宰问云:「寻常人徇人情做事,莫有牵制否?」曰:「孔子自有条法,『从众、从下』,惟其当尔。」
大率诸义皆伤浅短,铺陈略尽,便无可说。不见反复辨论节次发明工夫,读之未终,已无余味矣,此学不讲之过也。抄漳浦课簿。
显道云:「李德远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强则精神折冲赋,其中一联云:『虎在山而藜藿不采,威令风行;金铸鼎而魑魅不逢,奸邪影灭!』试官大喜之。乃是全用汪玉溪相黄潜善麻制中语,后来士人经礼部讼之。时樊茂实为侍郎,乃云:『此一对,当初汪内翰用时却未甚好,今被李解元用此赋中,见得工。』讼者遂无语而退。德远缘此见知于樊先生。」因举旧有人作仁人之安宅赋一联云:「智者反之,若去国念田园之乐;众人自弃,如病狂昧宫室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