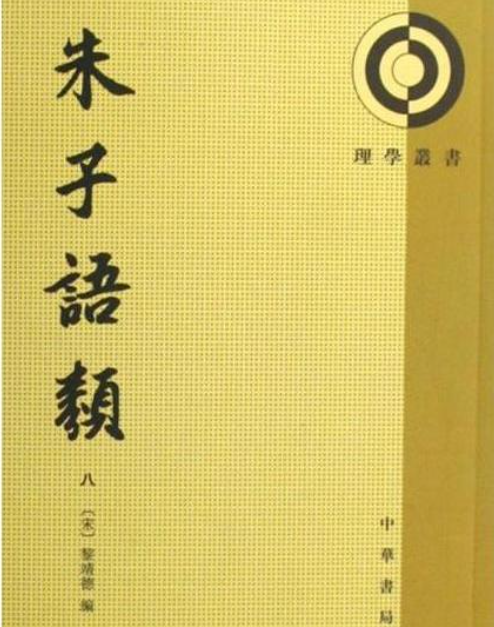乐古今
问:「古尺何所考?」曰:「羊头山黍今不可得,只依温公样,他考必仔细。然尺亦多样,隋书载十六等尺,说甚详。王莽货泉钱,古尺径一寸。」因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长者景表尺。」
十二律皆在,只起黄锺之宫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季通尝截小竹吹之,可验。若谓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则,不得中声,终不是。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牛鸣盎中」,谓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于周世宗时,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圣特异,初不曾理会乐,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声遂和。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笑云:「如此议论,又却似在乐不在德也。」
因论乐律,云:「尺以三分为增减,盖上生下生,三分损一益一。故须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厘,一厘分九丝,方如破竹,都通得去。人杰录云:「律管只以九寸为准,则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损一,如破竹矣。」其制作,通典亦略备,史记律书、汉律历志所载亦详。范蜀公与温公都枉了相争,只通典亦未尝看。蜀公之言既疏,温公又在下。」
无声,做管不成。
司马迁说律,只是推一个通了,十二个皆通。
十二律自黄锺而生。黄锺是最浊之声,其余渐渐清。若定得黄锺是,便入得乐。都是这里纔差了些子,其它都差。只是寸难定,所以易差。
乐声,黄锺九寸最浊,应锺最清,清声则四寸半。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六十四,则不齐而不容分矣。
音律如尖塔样,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惟五声者中声也。
乐律:自黄锺至中吕皆属阳,自蕤宾至应锺皆属阴,此是一个大阴阳。黄锺为阳,大吕为阴,太簇为阳,夹锺为阴,每一阳间一阴,又是一个小阴阳。
自黄锺至中吕皆下生,自蕤宾至应锺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礼记注疏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处,分明。
旋宫:且如大吕为宫,则大吕用黄锺八十一之数,而三分损一,下生夷则;夷则又用林锺五十四之数,而三分益一,上生夹锺。其余皆然。
问:「先生所论乐,今考之,若以黄锺为宫,便是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征,林锺为征,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若以大吕为宫,便是夹锺为商,中吕为角,林锺为变征,夷则为征,无射为羽,黄锺为变宫。其余则旋相为宫,周而复始。若言相生之法,则以律生吕,便是下生;以吕生律,则为上生。自黄锺下生林锺,林锺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锺,应锺上生蕤宾。蕤宾本当下生,今却复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锺;夹锺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相生之道,至是穷矣,遂复变而上生黄锺之宫。再生之黄锺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余。然黄锺君象也,非诸宫之所能役,故虚其正而不复用,所用只再生之变者。就再生之变又缺其半,所谓缺其半者,盖若大吕为宫,黄锺为变宫时,黄锺管最长,所以只得用其半声。而余宫亦皆仿此。」曰:「然。」又曰:「宫、商、角、征、羽与变征,皆是数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损,此其所以为妙。」问:「既有宫、商、角、征、羽,又有变宫、变征,何也?」曰:「二者是乐之和,去声。相连接处。」
「『旋相为宫』,若到应锺为宫,则下四声都当低去,所以有半声,亦谓之『子声』,近时所谓清声是也。大率乐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声不得过宫声。然近时却有四清声,方响十六个,十二个是律吕,四片是四清声。古来十二律却都有半声。所谓『半声』者,如蕤宾之管当用六寸,却只用三寸。虽用三寸,声却只是大吕,但愈重浊耳。」又问声气之元。曰:「律历家最重这元声,元声一定,向下都定;元声差,向下都差。」饶本云:「因论乐,云:『黄锺之律最长,应锺之律最短,长者声浊,短者声清。十二律旋相为宫,宫为君,商为臣。乐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声。如今方响有十六个,十二个是正律,四个是四清声,清声是减一律之半。如应锺为宫,其声最短而清。或蕤宾为之商,则是商声高似宫声,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宾律减半为清声以应之,虽然减半,只是出律,故亦自能相应也。此是通典载此一项。』又云:『乐声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乐中上声,便是郑卫。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当王朴造乐,闻其声太急,便令减下一律,其声遂平。徽宗朝作大晟乐,其声一声低似一声,故其音缓。』又云:『贤君大概属意于雅乐,所以仁宗晚年极力要理会雅乐,终未理会得。』」
律递相为宫,到末后宫声极清,则臣民之声反重,故作折半之声;然止于四者,以为臣民不可大于君也。事物大于君不妨。五声分为十二律,添三分,减三分,至十二而止。后世又增其四,取四清声。
宫与羽,角与征,相去独远。故于其间制变宫、变征二声。
问:「周礼大司乐说宫、角、征、羽,与七声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乐,如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锺为羽,自是四乐各举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吕为角,则南吕为宫;太簇为征,则林锺为宫;应锺为羽,则太簇为宫。以七声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说非也。」
律吕有十二,用时只使七个。自黄锺下生至七,若更插一声,便拗了。
七声之说,国语言之。
「律十有二,作乐只用七声。惟宫声筵席不可用,用则宾主失欢。」力行云:「今人揲卦得干卦者,多不为吉。故左传言『随元、亨、利、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
问:「国语云:『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云:『均谓均锺,木长七尺,系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韦昭是个不分晓底人。国语本自不分晓,更着他不晓事,愈见鹘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锺为宫,便用林锺为征,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成一均,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使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黄锺,只是散声。又自黄锺起至应锺有十二弦,要取甚声,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取定声。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来解书,最有一个韦昭无理会。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黄』字阙却上面一截,他便就这『六』字上解,谓六声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数,干色甚事!」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声,宫却属土,至羽属水。宫声最浊,羽声最清。一声应七律,共八十四调。除二律是变宫,止六十调。
乐声是土、金、木、火、水,洪范是水、火、木、金、土。
乐之六十声,便如六十甲子。以五声合十二律而成六十声,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属,而实相为用。遗书云「三命是律,五星是历」,即此说也。只晓不得甲子、乙丑皆属木,而纳音却属金。前辈多论此,皆无定说。
丝宫而竹羽。
丝尚宫,竹尚羽。竹声大,故以羽声济之;丝声细,故以宫声济之。
周礼以十二律为之度数,如黄锺九寸,林锺六寸之类;以十二声为之剂量斟酌,磨削刚柔清浊。音声有轻重高低,故复以十二声剂量。盖磬材有厚薄,令合节奏。如磬氏「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之类。
先生偶言及律吕,谓:「管有长短,则声有清浊。黄锺最长,则声最浊;应锺最短,则声最清。」时举云:「黄锺本为宫,然周礼祭天神人鬼地示之时,则其乐或以黄锺为宫,或以林锺为宫,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晓。先儒谓商是杀声,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声迭相为宫。未知其五声不备,又何以为乐?大抵古乐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锺、大吕、太簇、夹锺四清声,杂于正声之间,乐都可听。今古乐不可见矣。长沙南岳庙每祭必用乐,其节奏甚善,祭者久立不胜其劳。据图经云,是古乐。然其乐器又亦用伏鼓之类,如此,则亦非古矣。」时举因云:「『金声玉振』是乐之始终。不知只是首尾用之,还中间亦用耶?」曰:「乐有特锺、特磬,有编钟、编磬。编钟、编磬是中间奏者,特钟、特磬是首尾用者。」时举云:「所谓『玉振』者,只是石耶?还真用玉?」曰:「只是石耳。但大乐亦有玉磬,所谓『天球』者是也。」
问:「周礼祭不用商音,或以为是武王用厌胜之术。窃疑圣人恐无此意。」曰:「这个也难晓。须是问乐家,如何不用商。尝见乐家言,是有杀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无商调,不是无商音。他那奏起来,五音依旧皆在。」又问:「向见一乐书,温公言本朝无征音。窃谓五音如四时代谢,不可缺一。若无征音,则本朝之乐,大段不成说话。」曰:「不特本朝,从来无那征;不特征无,角亦无之。然只是太常乐无,那宴乐依旧有。这个也只是无征调、角调,不是无征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谓『黄锺宫,大吕羽』,这便是调。谓如头一声是宫声,尾后一声亦是宫声,这便是宫调。若是其中按拍处,那五音依旧都用,不只是全用宫。如说无征,便只是头声与尾声不是征。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个甚么欠缺处,所以做那征不成。徽宗尝令人硬去做,然后来做得成,却只是头一声是征,尾后一声依旧不是,依旧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会,这须是乐家辨得声音底,方理会得。但是这个别是一项,未消得理会。」
古者太子生,则太师吹管以度其声,看合甚律。及长,其声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乱,中华雅乐中绝。隋文帝时,郑译得之于苏祗婆。苏祗婆乃自西域传来,故知律吕乃天地自然之声气,非人之所能为。译请用旋宫,何妥耻其不能,遂止用黄锺一均。事见隋志。因言,佛与吾道不合者,盖道乃无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乐律,则有数器,所以合也。
六朝弹筝鼓瑟皆歌。
唐太宗不晓音律,谓不在乐者,只是胡说。易。
唐祖孝孙说八十四调。季通云,只有六十调,不以变宫、变征为调。恐其说有理。此左传「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之意也。
「自唐以前,乐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后,都无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数极精。但通典用十分为寸作算法,颇难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马诸公非惟不识古制,自是于唐制亦不曾详看;通典又不是隐僻底书,不知当时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览,笔谈所考器数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见此,则所论过于范马远甚。吕伯恭不喜笔谈,以为皆是乱说。某与言:『未可恁地说,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将五音、十二律写作图子,云:「且须晓得这个,其它却又商量。」
问乐。曰:「古声只是和,后来多以悲恨为佳。温公与范蜀公,胡安定与阮逸李照争辨,其实都自理会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说得极分明,盖此书在唐犹有传者,至唐末遂失其传。王朴当五代之末杜撰得个乐如此。当时有几锺名为『哑锺』,不曾击得,盖是八十四调。朴调其声,令一一击之。其实那个哑底却是。古人制此不击,以避宫声。若一例皆击,便有陵节之患。汉礼乐志刘歆说乐处亦好。唐人俗舞谓之『打令』,其状有四:曰招,曰摇,曰送,其一记不得。盖招则邀之之意,摇则摇手呼唤之意,送者送酒之意。旧尝见深村父老为余言,其祖父尝为之收得谱子。曰:『兵火失去。』舞时皆裹[巾璞-王]头,列坐饮酒,少刻起舞。有四句号云:『送摇招摇,三方一圆,分成四片,得在摇前。』人多不知,皆以为哑谜。」汉卿云:「张镃约斋亦是张家好子弟。」曰:「见君举说,其人大晓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处,见其教乐,又以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只用太常谱。然亦只做得今乐,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章尾只以某调终之,如关雎『关』字合作无射调,结尾亦著作无射声应之;葛覃『葛』字合作黄锺调,结尾亦著作黄锺声应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则是清声调,末亦以清声调结之;如『五月斯螽动股』,『二之日凿冰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浊声,黄锺调,末以浊声结之。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征、羽,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征、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
「温公与范忠文,胡安定与阮逸李照等议乐,空自争辩。看得来,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据通典中所说皆是,又且分晓。」广云:「如此则杜佑想是理会得乐。」曰:「这也不知他会否,但古乐在唐犹有存者,故他因取而载于书。至唐末黄巢乱后,遂失其传。至周世宗时,王朴据他所见杜撰得个乐出来。通鉴中说,王朴说,当时锺有几个不曾击,谓之『哑锺』,朴乃调其声,便皆可击。看得来所以存而不击者,恐是避其陵慢之声,故不击之耳,非不知击之也。」
范蜀公谓今汉书言律处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汉书有八字,所以与温公争者,只争此。范以古本为正。蜀公以上党粟一千二百粒,实今九寸为准;阔九寸。温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为准。汉书文不甚顺,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为之。然下粟时顿紧,则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为正排,又似非是。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纷纷如此。古人晓音律,风角、鸟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论兵,意出于此。仁宗时,李照造乐,蜀公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刘羲叟谓圣上必得心疾,后果然。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乐书,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
问:「温公论本朝乐无征音,如何?」曰:「其中不能无征音,只是无征调。如首以征音起,而末复以征音合杀者,是征调也。征调失其传久矣。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征音起,而不能以征音终。如今俗乐,亦只有宫、商、羽三调而已。」
蔡京用事,主张喻世清作乐,尽破前代之言乐者。因作中声正声,如正声九寸,中声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记「七」字多错,乃是「十分一」。其乐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徽宗时,一黥卒魏汉津造雅乐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学上丁用者是此乐。
季通律书,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说,自有按据。
问:「季通律书难晓。」曰:「甚分明,但未细考耳。」问:「空围九分,便是径三分?」曰:「古者只说空围九分,不说径三分,盖不啻三分犹有奇也。」问:「算到十七万有余之数,当何用?」曰:「以定管之长短而出是声。如太簇四寸,惟用半声方和。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与否耳。节五声,须是知音律之人与审验过,方见得。」
季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也是见成文字,如史记律历书,自无人看到这里。他近日又成一律要,尽合古法。近时所作律,逐节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必如此。这个若促些子,声便焦杀;若长些子,便慢荡。
陈淳言:「琴只可弹黄锺一均,而不可旋相为宫。」此说犹可。至谓琴之泛声为六律,又谓六律为六同,则妄矣。今人弹琴都不知孰为正声,若正得一弦,则其余皆可正。今调弦者云,如此为宫声,如此为商声,安知是正与不正?此须审音人方晓得。古人所以吹管,声传在琴上。如吹管起黄锺之指,则以琴之黄锺声合之,声合无差,然后以吹遍合诸声。五声既正,然后不用管,只以琴之五声为准,而他乐皆取正焉。季通书来说,近已晓得,但絣定七弦,不用调弦,皆可以弹十一宫。琴之体是黄锺一均,故可以弹十一宫。如此,则大吕、太簇、夹锺以下,声声皆用按徽,都无散声。盖纔不按,即是黄锺声矣,亦安得许多指按耶?兼如其说,则大吕以下亦不可对徽,须挨近第九徽里按之。此后愈挨下去,方合大吕诸声。盖按着正徽,复是黄锺声矣。渠云,顷问之太常乐工,工亦云然。恐无此理。古人弹琴,随月调弦,如十一月调黄锺,十二月调大吕,正月调太簇,二月调夹锺。但此后声愈紧,至十月调应锺,则弦急甚,恐绝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弹出便不可行。这便是无下学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习于此,故以之上达不难,盖下学中上达之理皆具矣。如今说古人兵法战阵,坐作进退,斩射击刺,鼓行金止,如何晓得他底?莫说古人底晓不得,只今之阵法也晓不得,更说甚么?如古之兵法,进则齐进,退则齐退,不令进而进,犹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则无人敢妄动。然又却有一人跃马陷阵,杀数十百人,出入数四,矢石不能伤者,何也?良久,又曰:「据今之法,只是两军相持住,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嬴,立不住退底便输耳。」
今朝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诗,甚好。其它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乐府做,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
今之乐,皆胡乐也,虽古之郑卫,亦不可见矣。今关雎鹿鸣等诗,亦有人播之歌曲。然听之与俗乐无异,不知古乐如何。古之宫调与今之宫调无异,但恐古者用浊声处多,今乐用清声处多。季通谓今俗乐,黄锺及夹锺清,如此则争四律,不见得如何。般涉调者,胡乐之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齐闻韶」,据季札观乐,鲁亦有之,何必在齐而闻之也?又,夫子见小儿徐行恭谨,曰:「韶乐作矣!」
「詹卿家令乐家以俗乐谱吹风雅篇章。初闻吹二南诗,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都不成模样。」因言:「古者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赵子敬送至小雅乐歌,以黄锺清为宫,此便非古。清者,半声也。唐末丧乱,乐人散亡,礼坏乐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声。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声,又有变声六。谓如黄锺为宫,则他律用正律;若他律为宫,则不用黄锺之正声,而用其子声。故汉书云「黄锺不与他律为役」者,此也。若用清声为宫,则本声轻清而高,余声重浊而下,礼书中删去乃是。乐律,通典中盖说得甚明。本朝如胡安定范蜀公司马公李照辈,元不曾看,徒自如此争辨也。汉书所载甚详,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载甚略,然都是要紧处。新修礼书中乐律补篇,以一尺为九寸,一寸为九分,一分为九厘,一厘为九毫,一毫为九丝。
乐律中所载十二诗谱,乃赵子敬所传,云是唐开元间乡饮酒所歌也。但却以黄锺清为宫,此便不可。盖黄锺管九寸,最长。若以黄锺为宫,则余律皆顺,若以其它律为宫,便有相陵处。今且只以黄锺言之,自第九宫后四宫,则后为角,或为羽,或为商,或为征。若以为角,则是民陵其君矣;若以为商,则是臣陵其君矣。征为事,羽为物,皆可类推。乐记曰:「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故制黄锺四清声用之。清声短其律之半,是黄锺清长四寸半也。若后四宫用黄锺为角、征、商、羽,则以四清声代之,不可用黄锺本律,以避陵慢。故汉志有云:「黄锺不复为他律所役。」其它律亦皆有清声,若遇相陵,则以清声避之,不然则否。惟是黄锺则不复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续笔谈说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则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说:「古人亦有时用黄锺清为宫,前说未是。」
音律只有人亦只是气,故相关。
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
今人都不识乐器,不闻其声,故不通其义。如古人尚识钟鼓,然后以钟鼓为乐。故孔子云:「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人钟鼓已自不识。
镈钟甚大,特悬钟也。众乐未作,先击特钟以发其声;众乐既阕,乃击特磬以收其韵。
堂上乐,金钟玉磬。今太常玉磬锁在柜里,更不曾设,恐为人破损,无可赔还。寻常交割,只据文书;若要看,旋开柜取一二枚视之。
今之箫管,乃是古之笛。云箫方是古之箫。
毕篥,本名悲栗,言其声之悲壮也。
俗乐中无征声,盖没安排处;及无黄锺等四浊声。
今之曲子,亦各有某宫某宫云。今乐起处差一位。
洛阳有带花刘使,名几,于俗乐甚明,盖晓音律者。范蜀公徒论锺律,其实不晓,但守死法。若以应锺为宫,则君民事物皆乱矣。司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于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说得分晓。史记律书说律数亦好。此盖自然之理,与先天图一般,更无安排。但数到穷处,又须变而生之,却生变律。
刘几与伶人花日新善,其弟厌之,令勿通。几戒花吹笛于门外,则出与相见。其弟又令终日吹笛乱之。然花笛一吹,则刘识其音矣。
向见一女童,天然理会得音律,其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
胡问:「今俗妓乐不可用否?」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