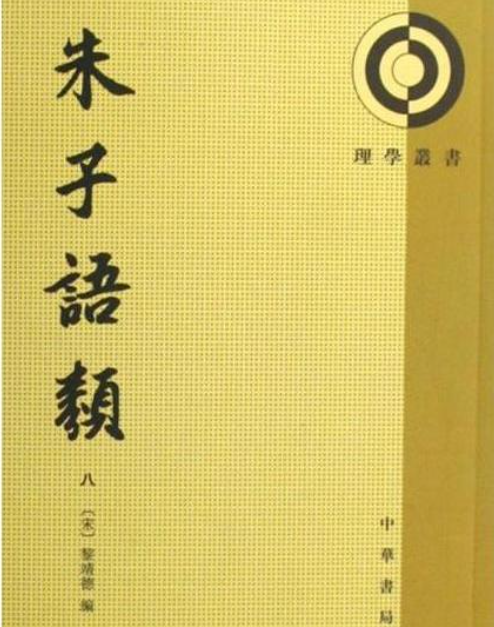程子之书一凡入近思录者,皆依次第类为此卷。
近思录首卷所论诚、中、仁三者,发明义理,固是有许多名,只是一理,但须随事别之,如说诚,便只是实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于万物,阴便实然是阴,阳便实然是阳,无一毫不真实处;中,只是喜怒哀乐未发之理;仁,便如天地发育万物,人无私意,便与天地相似。但天地无一息间断,「圣希天」处正在此。仁义礼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贞」,必统于元;如时之春秋冬夏,皆本于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
问:「伊川言:『「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动」是也。』南轩言:『伊川此处有小差,所谓喜怒哀乐之中,言众人之常性;「寂然不动」者,圣人之道心。』又,南轩辨吕与叔论中书说,亦如此。今载近思录如何?」曰:「前辈多如此说,不但钦夫,自五峰发此论,某自是晓不得。今湖南学者往往守此说,牢不可破。某看来,『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圣人能之,众人却不然。盖众人虽具此心,未发时已自汩乱了,思虑纷扰,梦寐颠倒,曾无操存之道;至感发处,如何得会如圣人中节!」
「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语,与横渠「心统性情」相似。
伊川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主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说出,如何明得?
问:「仁既偏言则一事,如何又可包四者?」曰:「偏言之仁,便是包四者底;包四者底,便是偏言之仁。」
郭兄问:「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以专言言之,则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则四者不离一者也。」
仁之包四德,犹冢宰之统六官。
问:「论语中言仁处,皆是包四者?」曰:「有是包四者底,有是偏言底。如『克己复礼为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便是包四者。」
问:「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这一个心,就里面分为四者。且以恻隐论之:本只是这恻隐,遇当辞逊则为辞逊,不安处便为羞恶,分别处便为是非。若无一个动底醒底在里面,便也不知羞恶,不知辞逊,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个春气,振录作「春生之气」。发生之初为春气,发生得过李录云:「长得」便为夏,收敛便为秋,消缩便为冬。明年又从春起,浑然只是一个发生之」方子、振同。
问:「仁包四者,只就生意上看否?」曰:「统是一个生意。如四时,只初生底便是春,夏天长,亦只是长这生底;秋天成,亦只是遂这生底,若割断便死了,不能成遂矣;冬天坚实,亦只是实这生底。如谷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断,亦死了。到十分熟,方割来,这生意又藏在里面。明年熟,亦只是这个生。如恻隐、羞恶、辞逊、是非,都是一个生意。当恻隐,若无生意,这里便死了,亦不解恻隐;当羞恶,若无生意,这里便死了,亦不解羞恶。这里无生意,亦不解辞逊,亦不解是非,心都无活底意思。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义礼知都是仁;对言,则仁义与礼智一般。」寓录云:「安卿问:『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统是个生意。四时虽异,生意则同。劈头是春生,到夏长养,是长养那生底;秋来成遂,是成遂那生底;冬来坚实,亦只坚实那生底。草木未华实,去摧折他,便割断了生意,便死了,如何会到成实!如谷有两分未熟,只成七八分谷。仁义礼智都只是个生意。当恻隐而不恻隐,便无生意,便死了;羞恶固是义,当羞恶而无羞恶,这生意亦死了。以至当辞逊而失其辞逊,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全无那活底意思。』」
问「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须先识得元与仁是个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么是仁,甚么是义、礼、智。既识得这个,便见得这一个能包得那数个。若有人问自家:『如何一个便包得数个?』只答云:『只为是一个。』」问直卿曰:「公于此处见得分明否?」曰:「向来看康节诗,见得这意思。如谓『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正与程子所谓『静后见万物皆有春意』同。且如这个棹子,安顿得恰好时,便是仁。盖无乖戾,便是生意。穷天地亘古今,只是一个生意,故曰『仁者与物无对』。以其无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体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棹子安顿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谓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恻然有隐,初来底意思便是。干录作:「要理会得仁,当就初处看。故元亨利贞,而元为四德之首。就初生处看,便见得仁。」所以程子谓『看鸡雏可以观仁』,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干录作:「亦是看其初意思。」问:「如所谓『初来底意思便是』,不知思虑之萌不得其正时如何?」曰:「这便是地头着贼,更是那『元』字上着贼了;如合施为而不曾施为时,便是亨底地头着贼了;如合收敛而不曾收敛时,便是利底地头着贼了;如合贞静而不能贞静时,便是贞底地头着贼了。干录作:「问:『物理固如此,就人心思虑上观之,如何?』曰:『思虑方萌,特守得定,便是仁。如思虑方萌错了,便是贼其仁;当施为时错了,便是贼其礼;当收敛时错了,便是贼其义;当贞静时错了,便是贼其智。凡物皆有个如此道理。』」以一身观之,元如头,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贞便是那元气所归宿处,所以人头亦谓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体之长也。』今若能知得所谓『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利之贞』,上面一个『元』字,便是包那四个;下面『元』字,则是『偏言则一事』者。恁地说,则大煞分明了。须要知得所谓『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贞之元』者,盖见得此,则知得所谓只是一个也。若以一岁之体言之,则春便是元之元;所谓『首夏清和』者,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干录作:「如春夏秋冬,春为一岁之首,由是而为夏,为秋,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谓仁包四德者,只缘四个是一个,只是三个。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贞之元。晓得此意,则仁包四者尤明白了。」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说『复其见天地之心』。复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将公所见,看所谓『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观之便见。」久之,复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岁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建邦之六典,则又统六卿也。」干录稍异。
问:「曩者论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看孟子『四端』处,似颇认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动之机也。惟其运转流通,无所间断,故谓之心,故能贯通四者。」曰:「这自是难说,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来,只见得一边,只见得他用处,不见他体了。」问:「生之理便是体否?」曰:「若要见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识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谓『克己复礼』;克去己私,如何便唤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则程子所谓『公』字,愈觉亲切。」曰:「公也只是仁底壳子,尽他未得在。毕竟里面是个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状得仁之体。」
直卿问:「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长』。从四时生物意思观之,则阴阳都偏了。」曰:「如此,则秋冬都无生物气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尽处,则阳气依旧在。且如阴阳,其初亦只是一个,进便唤做阳,退便唤做阴。」
问:「仁包四者。然恻隐之端,如何贯得是非、羞恶、辞逊之类?」曰:「恻隐只是动处。接事物时,皆是此心先拥出来,其间却自有羞恶、是非之别,所以恻隐又贯四端。如春和则发生,夏则长茂,以至秋冬,皆是一气,只是这个生意。」问:「『偏言则曰「爱之理」,专言则曰「心之德」』,如何?」曰:「偏言是指其一端,因恻隐之发而知其有是爱之理;专言则五性之理兼举而言之,而仁则包乎四者是也。」
问:「仁可包义智礼。恻隐如何包羞恶二端?」曰:「但看羞恶时自有一般恻怛底意思,便可见。」曰:「仁包三者,何以见?」曰:「但以春言:春本主生,夏秋冬亦只是此生气或长养,或敛藏,有间耳。」
伊川言:「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赋与万物言之,故谓之命;以人物之所禀受于天言之,故谓之性。其实,所从言之地头不同耳。
唐杰问:「近思录既载『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载『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风雨之属,二气良能是屈伸往来之理。」
人性无不善,虽桀纣之为穷凶极恶,也知此事是恶。但则是我要恁地做,不柰何,便是人欲夺了。
伊川言:「在物为理。」凡物皆有理,盖理不外乎事物之间。「处物为义。」义,宜也,是非可否处之得宜,所谓义也。
「在物为理,处物为义。」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义是于此物上自家处置合如此,便是义。义便有个区处。
问「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曰:「且如这棹子是物,于理可以安顿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义。」友仁。
问「忠信所以进德」至「对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个『终日干干』。在天之刚健者,便是天之干;在人之刚健者,便是人之干。其体则谓之易,便是横渠所谓『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者。自此而下,虽有许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皆是实理。以时节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气支体言之,便有人己,却只是一个理也。」
「忠信所以进德」至「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这个只是解一个「终日干干」。「忠信进德,修辞立诚」,便无间断,便是「终日干干」,不必便说「终日对越在天」。下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云云,便是说许多事,都只是一个天。
问:「详此一段意,只是体当这个实理。虽说出有许多般,其实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终日干干』,故说此一段。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说起。虽是『无声无臭』,其阖辟变化之体,则谓之易。然所以能阖辟变化之理,则谓之道;其功用着见处,则谓之神;此皆就天上说。及说到『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是就人身上说。上下说得如此子细,都说了,可谓尽矣。『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显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离了这个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离这个不得,下而万事万物都不出此,故曰『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然谓此器则有此理,有此理则有此器,未尝相离,却不是于形器之外别有所谓理。亘古亘今,万事万物皆只是这个,所以说『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叔蒙问:「不出这体用。其体则谓之性,其用则谓之道?」曰:「道只是统言此理,不可便以道为用。仁义礼智信是理,道便是统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来亦兼体、用,如说『其理则谓之道』,是指体言;又说『率性则谓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语上是就天上说,下是就人身上说。」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体、用言。如通书云:『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虽动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动而不正,则不是道。和亦只是顺理,用而和顺,便是得此理于身;若用而不和顺,则此理不得于身。故下云:『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动。』」直卿问:「太极图只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通书又说个『机』,此是动静之间,又有此一项。」又云:「『智』字自与知识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识便是察识得这个物事好恶。」又问:「神是心之至妙处,所以管摄动静。十年前,曾闻先生说,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贺孙问:「神既是管摄此身,则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处,滚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是气之精妙处,到得气,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于说魂,说魄,皆是说到粗处。」寓录云:「直卿云:『看来「神」字本不专说气,也可就理上说。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说。』先生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说,毕竟就气处多,发出光彩便是神。』味道问:『神如此说,心又在那里?』曰:『神便在心里,凝在里面为精,发出光彩为神。精属阴,神属阳。说到魂魄鬼神,又是说到大段粗处。』」
问:「『「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如何看『体』字?」曰:「体,是体质之『体』,犹言骨子也。易者,阴阳错综,交换代易之谓,如寒暑昼夜,阖辟往来。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盖与道为体也。寒暑昼夜,阖辟往来,而实理于是流行其间,非此则实理无所顿放。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实理寓焉。故曰『其体则谓之易』,言易为此理之体质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集注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即是此意。
「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理则谓之道」,在人则性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所谓易者,变化错综,如阴阳昼夜,雷风水火,反复流转,纵横经纬而不已也。人心则语默动静,变化不测者是也。体,是形体也,贺孙录云:「体,非『体、用』之谓。」言体,则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则形而上者也。故程子曰「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亦是意也。
「以其体谓之易,以其理谓之道」,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变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暑,暑了寒,日往而月来,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一阴一阳,只管恁地相易。
「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人杰谓:「阴阳阖辟,屈伸往来,则谓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则谓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测度,则谓之神。」程子又曰:「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只是就人道上说。」人杰谓:「中庸大旨,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谓教』,则圣贤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后世者,皆是也。」先生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犹心也;道,犹性也;神,犹情也。」翌日再问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摄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为春夏,所以为秋冬之理是也;至发育万物者,即其情也。」[莹田-玉]录别出。
正淳问:「『其体则谓之易』,只屈伸往来之义是否?」曰:「义则不是。只阴阳屈伸,便是形体。」又问:「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在人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为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发用便是情。」又问:「恐心大性小?」曰:「此不可以小大论。若以能为春夏秋冬者为性,亦未是。只是所以为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谓如以镜子为心,其光之照见物处便是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因甚把木板子来,却照不见?为他元没这光底道理。」
「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功用则谓之鬼神。」易是阴阳屈伸,随时变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阖辟,小阖辟,今人说易,都无着摸。圣人便于六十四卦,只以阴阳奇耦写出来。至于所以为阴阳,为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类蓦然而出,华时都华,实时都实,生气便发出来,只此便是神。如在人,仁义礼智,恻隐羞恶,心便能管摄。其为喜怒哀乐,即情之发用处。
「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此三句是说自然底。下面云「其命于人则谓之性」,此是就人上说。谓之「命于人」,这「人」字,便是「心」字。
问:「此一段自『浩然之气』以上,自是说道。下面『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体无乎不在。名虽不同,只是一理发出,是个无始无终底意。」林易简问:「莫是『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类泥着,但见梗碍耳。某旧见伊川说仁,令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看,看来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语,各随所说见意,那边自如彼说,这边自如此说。要一一来比并,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细逐件理会,待看得多,自有个见处。」林曰:「某且要知尽许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如且就知得处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两件做两件,贪多不济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轻费了时月。某谓,少看有功却多,泛泛然多看,全然无益。今人大抵有贪多之病,初来只是一个小没理会,下梢成一个大没理会!」
「明道『医书手足不仁』止『可以得仁之体』一段,以意推之,盖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则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尝不贯通也。虽其为天地,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实则有一条脉络相贯。故体认得此心,而有以存养之,则心理无所不到,而自然无不爱矣。才少有私欲蔽之,则便间断,发出来爱,便有不到处。故世之忍心无恩者,只是私欲蔽锢,不曾认得我与天地万物心相贯通之理。故求仁之切要,只在不失其本心而已。若夫『博施济众』,则自是功用,故曰何干仁事?言不于此而得也。仁至难言,亦以全体精微,未易言也。止曰『立人、达人』,则有以指夫仁者之心,而便于此观,则仁之体,庶几不外是心而得之尔。然又尝以伊川『谷种』之说推之,其『心犹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动乃情也』,盖所谓『生之性』,即仁之体,发处即仁之用也。若夫『博施济众』,则又是谷之成实,而利及于人之谓。以是观之,仁圣可知矣。」先生云:「何干仁事,谓仁不于此得,则可;以为圣仁全无干涉,则不可。」又云:「气有不贯,血脉都在这气字上。着心看,则意好。」又云:「『何事于仁?』言何止是仁?必也仁之成德;犹曰何止于木?必也木之成就;何止于谷?必也谷之成禾之意耳。」
伊川语录中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得太深,无捉摸处。易传其手笔,只云:「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传只此两处说仁,说得极平实,学者当精看此等处。
「『生之谓性』一条难说,须子细看。此一条,伊川说得亦未甚尽。『生之谓性』,是生下来唤做性底,便有气禀夹杂,便不是理底性了。前辈说甚『性恶』,『善恶混』,都是不曾识性。到伊川说:『性即理也』,无人道得到这处。理便是天理,又那得有恶!孟子说『性善』,便都是说理善;虽是就发处说,然亦就理之发处说。」如曰「乃若其情」,曰「非才之罪」。又曰:「『生之谓性』,如碗盛水后,人便以碗为水,水却本清,碗却有净有不净。」问:「虽是气禀,亦尚可变得否?」曰:「然最难,须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方得。若只恁地待他自变,他也未与你卒乍变得在。这道理无他巧,只是熟,只是专一。」
「人生气禀,理有善恶。」此「理」字,不是说实理,犹云理当如此。
「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理,只作「合」字看。
「生之谓性」一段,当作三节看,其间有言天命者,有言气质者。「生之谓性」是一节,「水流就下」是一节,清浊又是一
问:「『生之谓性』一段难看。自起头至『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成两三截。」曰:「此一段极难看。但细寻语脉,却亦可晓。上云『不是两物相对而生』,盖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却是言气禀之性,似与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气禀之性。盖言性本善,而今乃恶,亦是此性为恶所汩,正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水!」曰:「适所问,乃南轩之论。」曰:「敬夫议论出得太早,多有差舛。此间有渠论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难为拒之。」又问:「『人生而静』,当作断句。」曰:「只是连下文而『不容说』作句。性自禀赋而言,人生而静以上,未有形气,理未有所受,安得谓之性!」又问「纔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此处先生所答,记得不切,不敢录。次夜再问,别录在后。又问:「『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继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极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说『继之者善』。若就向上说,则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谓之性。」曰:「『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此言人生性与气混合者。」曰:「有此气为人,则理具于身,方可谓之性。」又问:「向滕德粹问『生之谓性』,先生曰:『且从程先生之说,亦好。』当时再三请益,先生不答。后来子细看,此盖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说,亦无害。而渠意直是指气为性,与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认告子语脉不差。果如此说,则孟子何必排之?则知其发端固非矣。大抵诸儒说性,多说着如佛氏亦只是认知觉作用为性。」又问孟注云:「『近世苏氏胡氏之说近此甚。』观二家之说,似亦不执着」曰:「其流必至此。」又问:「胡氏说『性不可以善恶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大。」曰:「不是要形容,只是见不明。若见得明,则自不如此。敬夫向亦执此说。尝语之云:『凡物皆有对,今乃欲作尖邪物,何故?』程先生论性,只云『性即理也』,岂不是见得明?是真有功于圣门!」又问:「『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无人如此说。若不是见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复问:「昨夜问『生之谓性』一段,意有未尽。不知『纔说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禀时说?已禀时说?」曰:「就已禀时说。性者,浑然天理而已。纔说性时,则已带气矣。所谓『离了阴阳更无道』,此中最宜分别。」又问:「『水流而就下』以后,此是说气禀否?若说气禀,则生下已定,安得有远近之别?」曰:「此是夹习说。」饶本云:「此是说」
问:「『生之谓性』一章,泳窃意自『生之谓性』至『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是本来之性与气质之性兼说。劈头只指个『生』字说,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泳曰:「恐只是都说做性。」泳又问:「旧来因此以水喻性,遂谓天道纯然一理,便是那水本来清;阴阳五行交错杂揉而有昏浊,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浊可以复清者,只缘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秽底水。」问:「也须可以澄治?」曰:「也减得些分数。」因言:「旧时人尝装惠山泉去京师,或时臭了。京师人会洗水,将沙石在笕中,上面倾水,从笕中下去。如此十数番,便渐如故。」或问:「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虽臭,想也未至污秽在。」问:「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问:「自『盖生之谓性』至『犹水流而就下也』一节,是说本来之性。」曰:「『盖生之谓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说。」又问:「『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人生而静』是说那初生时。更说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干元!万物资始』,只说是『诚之源也』。至『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便兼气质了。」问:「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质了。所以孟子答告子问性,却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说仁义礼智,却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去。盖性无形影,情却有实事,只得从情上说入去。」问:「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旧闻蔡季通问康叔临云:『凡物有两端。恻隐为仁之端,是头端?是尾端?』叔临以为尾端。近闻周庄仲说,先生云,不须如此分。」曰:「公如何说?」曰:「恻隐是性之动处。因其动处,以知其本体,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问「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一曰:「这水只是说」泳曰:「窃谓因物欲之浅深,可以见气质之昏明;犹因恻隐、羞恶,可以见仁义之端。」曰:「也是如此。」或问:「气清底人,自无物欲。」曰:「也如此说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声,人人皆然。虽是禀得气清,纔不检束,便流于欲去。」又问:「『如此,则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节,是说人求以变化然变了气质,复还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问:「『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至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一节,是言学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圣人之教人,亦不是强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见。」
或问「生之谓性」一段。曰:「此段引譬喻亦丛杂。如说水流而就下了,又说从清浊处去,与就下不相续。这处只要认得大意可也。」又曰:「『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一句,又似有恶性相似。须是子细看。」
问:「『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先生旧做明道论性说云:『气之恶者,其性亦无不善,故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明道又云:『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盖天下无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恶耳。』如此,则恶专是气禀,不干性事,如何说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曰:「既是气禀恶,便也牵引得那性不好。盖性只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所以说浊亦不可不谓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挠之,故浊也。」又问:「先生尝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还有病否?」曰:「若比来比去,也终有病。只是不以这个比,又不能得分晓。」
「『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疑与孟子抵牾。」曰:「这般所在难说,卒乍理会未得。某旧时初看,亦自疑。但看来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错,不相误,只着工夫子细看。莫据己见,便说前辈说得不是。」又问:「草木与人物之性一乎?」曰:「须知其异而不害其为同,知其同而不害其为异方得。」
正淳问:「性善,大抵程氏说善恶处,说得『善』字重,『恶』字轻。」曰:「『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此是气质之性。盖理之与气虽同,毕竟先有此理而后有此」又问郭氏性图。曰:「『性善』字且做在上,其下不当同以『善、恶』对出于下。不得已时,『善』字下再写一『善』,却傍出一『恶』字,倒着,以见恶只是反于善。且如此,犹自可说。」正淳谓:「自不当写出来。」曰:「然。」
问「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一段。曰:「『人生而静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时。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说性未得,此所谓『在天曰命』也。『纔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谓『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纔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也。然性之本体,亦未尝杂。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耳。『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识矣,如孟子言『性善』与『四端』是也。」未有形气,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谓之理;已有形气,是理降而在人,具于形气之中,方谓之性。已涉乎气矣,便不能超然专说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明道论性一章,「人生而静」,静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带却气质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说,盖此道理未有形见处。故今才说性,便须带着气质,无能悬空说得性者。「继之者善」,本是说造化发育之功,明道此处却是就人性发用处说,如孟子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之类是也。伊川言:「极本穷源之性,乃是对气质之性而言。」言气质之禀,虽有善恶之不同,然极本穷源而论之,则性未尝不善也。
问「人生而静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说性有本然之性,有气质之性。人具此形体,便是气质之性。才说性,此『性』字是杂气质与本来性说,便已不是性。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说气质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静』以下,方有形体可说;以上是未有形体,如何说?」
曾问「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曰:「此是未有人生之时,但有天理,更不可言性。人生而后,方有这气禀,有这物欲,方可言性。」
「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此只是理;「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此是要之,假合而后成。
「人生而静」,已是夹形气,专说性不得。此处宜体认。
或问:「说『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为天命之不已;感物而动,酬酢万殊,为天命之流行。不已便是流行,不知上一截如何下语?」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乃天命之本体也。」
问「人生而静以上」一段。曰:「有两个『性』字:有所谓『理之性』,有所谓『气质之性』。下一『性』字是理。『人生而静』,此『生』字已自带气质了。『生而静以上』,便只是理,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只说得气质,不是理也。」
「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也。」盖才说性时,便是兼气质而言矣。「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人生而静以上」,只说得个「人生而静」,上面不通说。盖性须是个气质,方说得个「性」字。若「人生而静以上」,只说个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便是如此。所谓「天命之谓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性,不杂气禀者而言尔。若才说性时,则便是夹气禀而言,所以说时,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濂溪说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说仁义礼智底性时。若论气禀之性,则不出此五者。然气禀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别有一种性也。然所谓「刚柔善恶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细推之,极多般样,千般百种,不可穷究,但不离此五者尔。
「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是只说性。如说善,即是有性了,方说得善。
问:「近思录中说性,似有两种,何也?」曰:「此说往往人都错看了。才说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堕入气质中,便熏染得不好了。虽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旧在此,全在学者着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气质之性,此大害理!」
问:「『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这『继』字,莫是主于接续承受底意思否?」曰:「主于人之发用处言之。」
程子云:「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易中所言,盖是说天命流行处;明道却将来就人发处说。孟子言「性善」,亦是就发处说,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盖因其发处之善,是以知其本无不善,犹循流而知其源也。故孟子说「四端」,亦多就发处说。易中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盖人便是一个小天地耳。
「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此「继之者善」,指发处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犹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见也。流出而见其清,然后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处,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谓「继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继之者善也」,在性之后。盖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发见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发见亦如此。如后段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某尝谓,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缘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来个个亦如此。一本故也。
问:「或谓明道所谓『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与易所谓『继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气质之性亦未尝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说『继之者善』,固与易意不同。但以为此段只说气质之性,则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气质之性处,有言天命之性处。近陈后之写来,只于此段『性』字下,各注某处是说天命之性,某处是说气质之性。若识得数字分明有着落,则此段尽易看。」
问:「明道言:『今人说性,多是说「继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说性之本体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说性之流出处,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之类否?」先生点头。后江西一学者问此。先生答书云:「易大传言『继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后。」是夕,复语文蔚曰:「今日答书,觉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继善』,是说天道流行处;孟子言『性善』,是说人性流出处。易与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处言,明道则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
「继之者善也」,周子是说生生之善,程子说作人性之善,用处各自不同。若以此观彼,心有窒碍。
问:「伊川云:『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曰:「物之初生,其本未远,固好看。及干成叶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时,恻隐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见得时却好看。到得发政施仁,其仁固广,便看不见得何处是仁。」赐。
问:「『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谓『初』之意否?」曰:「万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终,无非此理;但初生之际,淳粹未散,尤易见尔。只如元亨利贞皆是善,而元则为善之长,亨利贞皆是那里来。仁义礼智亦皆善也,而仁则为万善之首,义礼智皆从这里出尔。」
问:「『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对是物也,理安得有对?」曰:「如高下小大清浊之类,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浊,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当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独阴,必有阳;不能独阳,必有阴;皆是对。这对处,不是理对。其所以有对者,是理合当恁地。」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问:「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个是未有无对者。看得破时,真个是差异好笑。且如一阴一阳,便有对;至于太极,便对甚底?」曰:「太极有无极对。」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无对,然皆有对。太极便与阴阳相对。此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对过,却是横对了。土便与金木水火相对。盖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无方所,亦对得必大录云:「四物皆资土故也。」胡氏谓『善不与恶对』。恶是反善,如仁与不仁,如何不可对?若不相对,觉说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没个是处。」必大录云:「湖南学者云,善无对。不知恶乃善之对,恶者反乎善者也。」必大同。
问:「『天下之理,无独必有对。』有动必有静,有阴必有阳,以至屈伸消长盛衰之类,莫不皆然。还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来如此,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且如碁盘路两两相对,末梢中间只空一路,若似无对;然此一路对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谓『一对万,道对器』也。」
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语便有默,有动便有静,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人行出去是这脚,归亦是这脚。譬如口中之气,嘘则为温,吸则为寒耳。
问:「阴阳昼夜,善恶是非,君臣上下,此天地万物无独必有对之意否?」曰:「这也只如喜怒哀乐之中,便有个既发而中节之和在里相似。」
问:「『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亭亭当当,直上直下』等语,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体段如此。『出则不是』者,出便是已发。发而中节,只可谓之和,不可谓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
问「亭亭当当」之说。曰:「此俗语也,盖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问:「敬固非中,惟『敬而无失』,乃所以为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也。」
「天地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如此则是内。敬而无无失最尽。」居敬。方谓「居」字好。
问:「无妄,诚之道。不欺,则所以求诚否?」曰:「无妄者,圣人也。谓圣人为无妄,则可;谓圣人为不欺,则不可。」又问:「此正所谓『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否?」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诚,不欺是着力去做底。」
「无妄之谓诚」是天道,「不欺其次矣」是人道,中庸所谓「思诚」者是也。
味道问「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也」。曰:「非无妄故能诚,无妄便是诚。无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犹是两个物事相对。」
或问「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曰:「无妄,是兼天地万物所同得底浑沦道理;不欺,是就一边说。」泳问:「不欺,是就人身说否?」曰:「然。」
无妄,自是我无妄,故诚;不欺者,对物而言之,故次之。
问:「『冲漠无朕』至『教入涂辙』。他所谓涂辙者,莫只是以人所当行者言之?凡所当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临行事时,旋去寻讨道理。」曰:「此言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又问:「『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是如何?」曰:「是这一个事,便只是这一个道理。精粗一贯,元无两样。今人只见前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将谓是空荡荡;却不知道『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如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曰:「『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应』字是应务之『应』否?」曰:「未应,是未应此事;已应,是已应此事。未应固是先,却只是后来事;已应固是后,却只是未应时理。」
「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在这里。不是先本无,却待安排也。「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如既有君君臣臣底涂辙,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
子升问「冲漠无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时,此理已具,少间应处只是此理。所谓涂辙,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条路从源头下来。」
或问「未应不是先」一条。曰:「未应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这个道理。涂辙,是车行处。且如未有涂辙,而车行必有涂辙之理。」
问「冲漠无朕」一段。曰:「此只是说『无极而太极』。」又问:「下文『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是如何?」曰:「恐是记者欠了字,亦晓不得。」又曰:「某前日说,只从阴阳处看,则所谓太极者,便只在阴阳里;所谓阴阳者,便只是在太极里。而今人说阴阳上面别有一个无形无影底物是太极,非也。」他本小异。
问:「『近取诸身,百理皆具』,且是言人之一身与天地相为流通,无一之不相似。至下言『屈伸往来之义,只于鼻息之间见之』,却只是说上意一脚否?」曰:「然。」又问:「屈伸往来,只是理自如此。亦犹一阖一辟,阖固为辟之基,而辟亦为阖之基否?」曰:「气虽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气,自非既屈之气虽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谓『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
问:「屈伸往来,气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来者,是理必如此。『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其所以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者,乃道也。」
明道言:「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盖阴阳之变化,万物之生成,情伪之相通,事为之终始,一为感,则一为应,循环相代,所以不已也。
问天下只有个感应。曰:「事事物物,皆有感应。寤寐、语默、动静亦然。譬如气聚则风起,风止则气复聚。」
「感应」二字有二义:以感对应而言,则彼感而此应;专于感而言,则感又兼应意,如感恩感德之类。
问:「感,只是内感?」曰:「物固有自内感者。然亦不专是内感,固有自外感者。所谓『内感』,如一动一静,一往一来,此只是一物先后自相感。如人语极须默,默极须语,此便是内感。若有人自外来唤自家,只得唤做外感。感于内者自是内,感于外者自是外。如此看,方周遍平正。只做内感,便偏颇了。」
心性以谷种论,则包裹底是心;有秫种,有粳种,随那种发出不同,这便是性。心是个发出底,池本作:「心似个没思量底。」他只会生。又如服药,吃了会治病,此是药力;或温或叙,便是药性。至于吃了有温证,有叙证,这便是情。
履之问:「『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不善』章,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稳处。盖凡事莫非心之所为,虽放僻邪侈,亦是心之为也。善恶但如反复手耳,翻一转便是恶,止安顿不着,也便是不善。如当恻隐而羞恶,当羞恶而恻隐,便不是。」又问:「心之用虽有不善,亦不可谓之非心否?」曰:「然。」
问:「『发于思虑则有善不善。』看来不善之发有二:有自思虑上不知不觉自发出来者,有因外诱然后引动此思虑者。闲邪之道,当无所不用其力。于思虑上发时,便加省察,更不使形于事为。于物诱之际,又当于视听言动上理会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则身心内外肃然,交致其功,则自无二者之病。」曰:「谓发处有两端,固是。然毕竟从思虑上发者,也只在外来底。天理浑是一个。只不善,便是不从天理出来;不从天理出来,便是出外底了。视听言动,该贯内外,亦不可谓专是外面功夫。若以为在内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则内外支离,无此道理。须是『诚之于思,守之于为』,内外交致其功,可也。」
问:「『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体有善而无恶,及其发处,则不能无善恶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先生以为下句有病。如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岂可直以为心无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别得体与发处言之否?」曰:「只为他说得不备。若云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体无不仁,则意方足耳。」
问:「『心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如何?」曰:「心是贯彻上下,不可只于一处看。」
「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此句亦未稳。
「『心,生道也。』此句是张思叔所记,疑有欠阙处。必是当时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丰云:「何故入在近思录中?」曰:「如何敢不载?但只恐有阙文,此四字说不尽。」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道也。」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问:「『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恻隐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为心?盖在天只有此理,若无那形质,则此理无安顿处。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犹言『继善』,下面犹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盖理只是一个浑然底,人与天地混合无间。」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属天地,未属我在,此乃是众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则方是我底,故又曰:「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尝不在天地之间。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讨一物来安顿放里面。似恁地处,难看,须自体认得。
伊川云:「心,生道也。」方云:「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是人为天地之心意。」本文云。又曰:「生亦是生生之意。盖有是恻隐心,则有是形。」方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
敬子解「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词为工」,以为「人不知性,故怠于为希圣之学,而乐于为希名慕利之学」。曰:「不是他乐于为希名慕利之学,是他不知圣之可学,别无可做,只得向那里去。若知得有个道理,可以学做圣人,他岂不愿为!缘他不知圣人之可学,『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成空须讨个业次弄,或为诗,或作文。是他没着浑身处,只得向那里去,俗语所谓『无图之辈』,是也。」因曰:「世上万般皆下品,若见得这道理高,见世间万般皆低。故这一段紧要处,只在『先明诸心』上。盖『先明诸心』了,方知得圣之可学;有下手处,方就这里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以下第二卷。好学论入集注者,已附本章。
舜弼问:「定性书也难理会。」曰:「也不难。『定性』字,说得也诧异。此『性』字,是个『心』字意。明道言语甚圆转,初读未晓得,都没理会;子细看,却成段相应。此书在鄠时作,年甚少。」
「明道定性书自胸中泻出,如有物在后面逼逐他相似,皆写不辨。」直卿曰:「此正所谓『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见一个下手处。」蜚卿曰:「『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莫是下工处否?」曰:「这是说已成处。且如今人私欲万端,纷纷扰扰,无可柰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见与理皆是背驰,如何便得他顺应?」道夫曰:「这便是先生前日所谓『也须存得这个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纷扰,看着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这须是见得,须是知得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见得他如生龙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问:「定性书云:『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曰:「此一书,首尾只此两项。伊川文字段数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说将去,初看似无统,子细理会,中问自有路脉贯串将去。『君子之学,莫若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自后许多说话,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此是说『扩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此是说『物来而顺应』。『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应『廓然而大公』,『而观理之是非』是应『物来而顺应』。这须子细去看,方始得。」
明道答横渠「定性未能不动」一章,明道意,言不恶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恶则全绝之,逐则又为物引将去。惟不拒不流,泛应曲当,则善矣。盖横渠有意于绝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为须是内外合一,「动亦定,静亦定」,则应物之际,自然不累于物。苟只静时能定,则动时恐却被物诱去矣。
问:「圣人『动亦定,静亦定』。所谓定者,是体否?」曰:「是。」曰:「此是恶物来感时定?抑善恶来皆定?」曰:「恶物来不感,这里自不接。」曰:「善物则如何?」曰:「当应便应,有许多分数来,便有许多分数应。这里自定。」曰:「『子哭之恸』,而何以见其为定?」曰:「此是当应也。须是『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再三诵此语,以为「说得圆」。
问:「圣人定处未详。」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万物各有当止之所。知得,则此心自不为物动。」曰:「舜『号泣于旻天』,『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当此时,何以见其为定?」曰:「此是当应而应,当应而应便是定。若不当应而应,便是乱了;当应而不应,则又是死了。」
问:「『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学者卒未到此,柰何?」曰:「虽未到此,规模也是恁地。『扩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来,顺他道理应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见得道理是恁地;却有个偏曲底意思,要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这道理,不能顺应。圣人自有圣人大公,贤人自有贤人大公,学者自有学者大公。」又问:「圣贤大公,固未敢请。学者之心当如何?」曰:「也只要存得这个在,克去私意。这两句是有头有尾说话。大公是包说,顺应是就里面细说。公是忠,便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顺应便是『干道变化,各正性命』。」
「扩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动」,「物来而顺应」是「感而遂通。」
赵致道问:「『自私者,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者,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所谓『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所谓『普万物,顺万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谓;『无心无情』者,即『物来而顺应』之谓。自私则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物来而顺应』,所以不能『以明觉为自然』。」曰:「然。」
明道云:「不能以有为为应迹。」应迹,谓应事物之迹。若心,则未尝动也。
问:「昨日因说程子谓释氏自私,味道举明道答横渠书中语,先生曰:『此却是举常人自私处言之。』若据自私而用智,与后面治怒之说,则似乎说得浅。若看得说那『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则所指亦大阔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总人之私意言耳。」味道又举「反鉴索照」,与夫「恶外物」之说。先生曰:「此亦是私意。盖自常人之私意与佛之自私,皆一私也,但非是专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因横渠病处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疏不能应物;又有一般人,溺于空虚不肯应物,皆是自私。若能『豁然而大公』,则上不陷于空寂,下不累于物欲,自能『物来而顺应』。」贺孙录云:「汉卿前日说:『佛是自私。』味道举明道『自私用智』之语,『亦是此意。先生尝以此自私说较粗,是常人之自私。某细思之,如「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亦是说得煞,恐只是佛氏之自私。』先生曰:『此说得较阔,兼两意。也是见横渠说得有这病,故如此说。』贺孙云:『「今以恶外物之心,求照无物之地,犹反鉴而索照也」,亦是说绝外物而求定之意。』曰:『然。但所谓「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欲,也是不能「以有为为应迹」,如异端绝灭外物,也是不能「以有为为应迹」。若「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便都不如此,上不沦于空寂,下不累于物欲。』」
问:「定性书所论,固是不可有意于除外诱,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学,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学也不解如此,外诱如何除得?有当应者,也只得顺他,便看理如何。理当应便应,不当应便不应。此篇大纲,只在『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两句。其它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谓『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紧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扩然大公』,『观理之是非』便是『物来顺应』。明道言语浑沦,子细看,节节有条理。」曰:「『内外两忘』,是内不自私,外应不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内者为是,而在外者为非,只得随理顺应。」
先生举「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惟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旧时谓观理之是非,才见己是而人非,则其争愈力。后来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谓:『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横逆由是也,则曰:「此亦妄人而已矣!」』」
人情易发而难制。明道云:「人能于怒时遽忘其怒,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此语可见。然有一说,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见其直而又怒,则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于外复有一理时,却难,为只有此理故。
问:「圣人恐无怒容否?」曰:「怎生无怒容?合当怒时,必亦形于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为笑容,则不可。」曰:「如此,则恐涉忿怒之气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诛『四凶』,当其时亦须怒。但当怒而怒,便中节;事过便消了,更不积。」
问:「定性书是正心诚意功夫否?」曰:「正心诚意以后事。」
伊川谓:「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如杨墨何尝有邪心?只是不合正理。
先生以伊川答方道辅书示学者,曰:「他只恁平铺,无紧要说出一来。只是要移易他一两字,也不得;要改动他一句,也不得。」
问:「苏季明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事,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横渠门人,祖横渠『修辞』之说,以立言传后为修辞,是为居业。明道与说易上『修辞』不恁地。修辞,只是如『非礼勿言』。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便是理会敬义之实事,便是表里相应。『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便是立诚。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业,便是逐日底事业,恰似日课一般。『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如是心中实见得理之不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则德不期而进矣。诚,便即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只管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修辞』二字,便只理会其大规模。伊川却与辨治经,便理会细密,都无缝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尽。如讲习,不止只是治经。若平日所以讲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应事接物,有合讲者,或更切于治经,亦不为无益。此更是一个大病痛。」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为他元来见识自颜子才虽未尝不高,然其学却细腻切实,所以学者有用力处。孟子终是粗。
伊川曰:「学者须是学颜子。」孟子说得粗,不甚子细;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学者学他,或会错认了他意思。若颜子说话,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须解说方得。
蔡问:「『孟子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如养气处,岂得为无可依据?」曰:「孟子皆是要用。颜子须就己做工夫,所以学颜子则不错。」
问:「『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只是教人『鞭辟近里』。窃谓明善是致知,诚心是诚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诚,善才明,诚心便进。」又问:「『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便是应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仪制度。『所守不约,泛滥无功』,说得极切。这般处,只管将来玩味,则道理自然都见。」又曰:「这般次第,是吕与叔自关中来初见二程时说话。盖横渠多教人礼文制度之事,他学者自管用心,不近里,故以此说教之。然只可施之与叔诸人。若与龟山言,便不着地头了。公今看了近思录,看别经书,须将遗书兼看。盖他一人是一个病痛,故程先生说得各各自有精采。」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是且理会自家切己处。明善了,又更须看自家进诚心与未。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裁培。」识得与实有,须做两句看。识得,是知之也;实有,是得之也。若只识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须实有诸己,方是己物也。
问:「明道说『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一段,只缘他源头是个不忍之心,生生不穷,故人得以生者,其流动发生之机亦未尝息。故推其爱,则视夫天地万物均受此气,均得此理,则无所不当爱。」曰:「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见如此,硬桩定说不得。如云从他源头上便有个不忍之心,生生不穷,此语有病。他源头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说到不忍在。只有个阴阳五行,有阖辟,有动静;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说生物时,又是流行已后。既是此气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爱。假使天地之间净尽无一物,只留得这一个物事,他也自爱。如云均受此气,均得此理,所以须用爱,也未说得这里在。此又是说后来事。此理之爱,如春之温,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炙着底自然热,不是使他热也。」因举东见录中明道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云云,「极好,当添入近思录中。」
心只是放宽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碍,便大。心大则自然不急迫。如有祸患之来,亦未须惊恐;或有所获,亦未有便欢喜在。少间亦未必,祸更转为福,福更转为祸。荀子言:「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盖君子心大则是天心,心小则文王之翼翼,皆为好也;小人心大则放肆,心小则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
明道以上蔡记诵为玩物丧志,盖为其意不是理会道理,只是夸多斗靡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则意思自别。此正为己为人之分。
问:「『礼乐只在进反之间,便得情性之正。』记曰:『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恐减与盈,是礼乐之体本如此;进与反,却是用功处否?」曰:「减,是退让、撙节、收敛底意思,是礼之体本如此。进者,力行之谓。盈,是和说、舒散、快满底意思,是乐之体如此。反者,退敛之谓。『礼主其减』,却欲进一步向前着力去做;『乐主其盈』,却须退敛节制,收拾归里。如此则礼减而却进,乐盈而却反,所以为得情性之正也,故曰『减而不进则消,盈而不反则亡』也。」因问:「如此,如礼乐相为用矣。」曰:「然。」
问:「『礼乐只在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何谓也?」曰:「记得『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如凡事俭约,如收敛恭敬,便是减;须当着力向前去做,便是进,故以进为文。乐,如歌咏和乐,便是盈;须当有个节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为文。礼减而却进前去,乐盈而却反退来,便是得情性之正。」
「礼主其减」者,礼主于撙节、退逊、检束;然以其难行,故须勇猛力进始得,故以进为文。「乐主其盈」者,乐主于舒畅发越;然一向如此,必至于流荡,故以反为文。礼之进,乐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减者当进,须力行将去;主盈者当反,须回顾身心。」
礼乐进反。「礼主于减」,谓主于敛束;然敛束太甚,则将久意消了,做不去,故以进为文,则欲勉行之。「乐主于盈」,谓和乐洋溢;然太过则流,故以反为文,则欲回来减些子。故进反之间,便得情性之正。不然,则流矣。
问「礼乐进反」之说。曰:「『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以谦逊退贬为尚,故主减;然非人之所乐,故须强勉做将去,方得。乐以发扬蹈厉为尚,故主盈;然乐只管充满而不反,则文也无收杀,故须反,方得。故云:『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所以程子谓:『只在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
「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私!故虽「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这『体』字,只事理合当做处。凡事皆有个体,皆有个当然处。」问:「是体段之『体』否?」曰:「也是如此。」又问:「如为朝廷有朝廷之体,为一国有一国之体,为州县有州县之体否?」曰:「然。是个大体有格局当做处。如作州县,便合治告讦,除盗贼,劝农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须开言路,通下情,消朋党;如为大吏,便须求贤才,去赃吏,除暴敛,均力役,这个都是定底格局,合当如此做。」或问云云。曰:「不消如此说,只怕人伤了那大体。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为当急,便害了那大体。如为天子近臣,合当謇谔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处乡里,合当闭门自守,躬廉退之节,又却向前要做事,这个便都伤了那大体。如今人议论,都是如此。合当举贤才而不举,而曰我远权势;合当去奸恶而不去,而曰不为已甚。且如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雠耻,却曰休兵息民,兼爱南北!正使真个能如此,犹不是,况为此说者,其实只是懒计而已!」
「根本须是先培壅」,涵养持敬,便是栽培。
问「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曰:「此段只如『弟子入孝出第,行谨言信,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意耳。先只是从实上培壅一个根脚,却学文做工夫去。」
仲思问「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夹持』两字好。敬主乎中,义防于外,二者相夹持。要放下霎时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达天德。」
「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表里夹持,更无东西走作去处,上面只更有个天德。「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干道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顺。又曰:「非礼勿视听言动者,干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进德立诚,是甚模样强健!」
「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直上者,无许多人欲牵惹也。
因说敬恕,先生举明道语云:「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样人,里面谨严,外面却●苴;有人外面恁地宽恕,里面却都是私意了。内外夹持,如有人在里面把住,一人在门外把持,不由他不上去。」
问:「『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义如何分别?」曰:「道、义是个体、用。道是大纲说;义是就一事上说。义是道中之细分别,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来。」
问:「『正其义』者,凡处此一事,但当处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谋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则处此事便合义,是乃所以为明其道,而不可有计后日功效之心。『正义不谋利』,在处事之先;『明道不计功』,在处事之后。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说,也得。他本是合掌说,看来也须微有先后之序。」子蒙录云:「或问:『正义在先,明道在后。』曰:『未有先后。此只是合掌底意思。』」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或曰,事成之谓利,所以有义;功成则是道。便不是。「惠迪吉,从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
杨问:「『胆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胆大是『千万人吾往』处,天下万物不足以动其心;『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胆大。心小是畏敬之谓,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战战兢兢,临深履薄』是也。」问:「横渠言『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狭隘,事物来都没柰何,打不去,只管见碍,皆是病。如要敬则碍和,要仁则碍义,要刚则碍柔。这里只看得一个,更着两个不得。为敬,便一向拘拘;为和,便一向放肆,没理会。仁,便煦煦姑息;义,便粗暴决裂。心大,便能容天下万物。有这物则有这理,有那物即有那道理。『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
「胆欲大而心欲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方能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蜚卿云:「『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妄意四者缺一不可。」曰:「圆而不方则谲诈,方而不圆则执而不通。志不大则卑陋,心不小则狂妄。江西诸人便是志大而心不小者也。」
或问:「『智欲圆而行欲』智欲圆转;若行不方正而合于义,则相将流于权谋谲诈之中;所谓『智欲圆而行欲方』也。」曰:「也是如此。」又曰:「智是对仁义礼智信而言。须是知得是非,方谓之智;不然,便是不智。」
问「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广大,只是潜心积虑,缓缓养将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则是起意去赶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
问:「『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中要识得真与妄耳。』真、妄是于那发处别识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视听、思虑、动作皆是天理。其顺发出来,无非当然之理,即所谓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虽是妄,亦无非天理,只是发得不当地头。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为草木固无以异,只是那地头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之意。」
问:「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之所为。及发而不中节,则是妄。故学者须要识别之。」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道夫曰:「这正是颜子之所谓『非礼』者。」曰:「非礼处便是私意。」
役智力于农圃,内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济甚事!
「进德则自忠恕」,是从这里做出来;「其致则公平」,言其极则公平也。
问:「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个流动发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体之』,方谓之仁否?」曰:「此便是难说。『公而以人体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个晓得,方知这一句说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盖这个仁便在这『人』字上。你元自有这仁,合下便带得来。只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来;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沟中水,被沙土罨靸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担去沙土罨靸,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别担水来放沟中,是沟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则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别讨个天理来放在里面也,故曰:『公近仁。』」又问:「『公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爱是仁之发处,恕是推其爱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凑合不着,都无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么?所以只见不长进,正缘看那物事没滋味。」又问:「莫是带那上文『公』字说否?」曰:「然。恕与爱本皆出于仁,然非公则安能恕?安能爱?」又问:「爱只是合下发处便爱,未有以及物在,恕则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发处自是爱,恕是推那爱底,爱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爱也不能及物,也不能亲亲仁民爱物,只是自爱而已。若里面元无那爱,又只推个甚么?如开沟相似,是里面元有这水,所以开着便有水来。若里面元无此水,如何会开着便有水?若不是去开沟,纵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来?爱,水也;开之者,恕也。」又问:「若不是推其爱以及物,纵有此爱,也无可得及物否?」曰:「不是无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则不能及物。此等处容易晓,如何恁地难看!」
问:「『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体之,故曰仁。』窃谓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到处。公,所以能仁。所谓『公而以人体之』者,若曰己私既尽,只就人身上看,便是仁。体,犹骨也,如『体物不可遗』之『体』,『贞者事之干』之类,非『体认』之『体』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盖有形气,便具此生理。若无私意间隔,则人身上全体皆是仁。如无此形质,则生意都不凑泊他。所谓『体』者,便作『体认』之『体』,亦不妨。体认者,是将此身去里面体察,如中庸『体群臣』之『体』也。」
问:「向日问『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先生曰:『体,作「体认」之「体」亦不妨。』铢思之,未达。窃谓有此人则具此仁。然人所以不仁者,以其私也。能无私心则此理流行,即此人而此仁在矣。非是公后,又要去体认寻讨也。」先生顾杨至之谓曰:「『仁』字,叔重说得是了,但认『体』字未是。体者,乃是以人而体公。盖人撑起这公作骨子,则无私心而仁矣。盖公只是一个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则害夫仁。故必体此公在人身上以为之体,则无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
问:「『公而以人体之』,如何?」曰:「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此理。公却是克己之极功,惟公然后能仁。所谓『公而以人体之』者,盖曰克尽己私之后,就自家身上看,便见得仁也。」
「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盖公犹无尘也,人犹镜也,仁则犹镜之光明也。镜无纤尘则光明,人能无一毫之私欲则仁。然镜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镜元来自有这光明,今不为尘所昏尔。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来自有这仁,今不为私欲所蔽尔。故人无私欲,则心之体用广大流行,而无时不仁,所以能爱能恕。仁之名不从公来,乃是从人来,故曰「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为仁,须是「公而以人体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为仁」。世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者,须公而有恻隐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盖人体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则不仁矣。
「公而以人体之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则仁,私则不仁。未可便以公为仁,须是体之以人方是仁。公、恕、爱,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与爱在仁之后。公则能仁,仁则能爱能恕故也。
李问:「仁,欲以公、爱、恕三者合而观之,如何?」曰:「公在仁之先,爱、恕在仁之后。」又问:「公而以人体之」一句。曰:「紧要在『人』字上。仁只是个人。」
公所以为仁。故伊川云:「非是以公便为仁,公而以人体之。」仁譬如水泉,私譬如沙石能壅却泉,公乃所以决去沙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复也。
谓仁只是公,固若未尽;谓公近仁耳,又似太疏。伊川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此是先生晚年语,平淡中有意味。显道记忆语及入关语录亦有数段,更宜参之。镐。
或问:「『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施与用如何分别?」曰:「恕之所施,施其爱尔,不恕,则虽有爱而不能及人也。」
问:「『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施与用何以别?」曰:「施是从这里流出,用是就事说。『推己为恕。』恕是从己流出去及那物;爱是才调恁地。爱如水,恕如水之流。」又问:「先生谓『爱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窃谓仁如水,爱如水之润,恕如水之流,不审如何?」曰:「说得好。昨日就过了。」
问:「『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施与用如何分?」曰:「恕是分俵那爱底。如一桶水,爱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处一杓,故谓之施。爱是仁之用,恕所以施爱者。」
「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施、用」两字,移动全不得。这般处,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扬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有言「尽己之谓忠,尽物之谓恕」。伊川言:「尽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谓恕。」盖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处,极当细看。
或问:「『力行』如何是『浅近语』?」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问:「何以为『浅近』?」曰:「他只是见圣贤所为,心下爱,硬依他行。这是私意,不是当行。若见得道理时,皆是当恁地行。」又问:「『这一点意气能得几时了!』是如何?」曰:「久时,将次只是恁地休了。」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无事时,且存养在这里,提撕警觉,不要放肆。到讲习应接时,便当思量义理。
杨子顺问:「『涵养须用敬。』涵养甚难,心中一起一灭,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岂是无思?但不出于私则可。」曰:「某多被思虑纷扰,思这一事,又牵走那事去。虽知得,亦自难止。」曰:「既知得不是,便当绝断了。」
涵养此心须用敬。譬之养赤子,方血气未壮实之时,且须时其起居饮食,养之于屋室之中而谨顾守之,则有向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于风日之中,偃然不顾,岂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问:「伊川谓:『敬是涵养一事。』敬不足以尽涵养否?」曰:「五色养其目,声音养其耳,义理养其心,皆是养也。」
用之问:「学者思先立标准,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谓。而今虽道是要学圣人,亦且从下头做将去。若日日恁地比较,也不得。虽则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将来比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问:「学者做工夫,须以圣人为标准,如何却说得不立标准?」曰:「学者固当以圣人为师,然亦何须得先立标准?才立标准,心里便计较思量几时得到圣人?处圣人田地又如何?便有个先获底心。『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说,教人须以圣贤自期。又何须先立标准?只恁下着头做,少间自有所」
「尹和靖从伊川半年后,方见得西铭大学」,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么?想见只是且教他听说话。」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门,未知次第,骤将与他看未得。」先生曰:「岂不是如此?」又曰:「西铭本不曾说『理一分殊』,因人疑后,方说此一句。」
问:「『尹彦明见程子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处思量,自看平时个是不是,未欲便把那书与之读。」曰:「如此,则末后以此二书并授之,还是以尹子已得此意?还是以二书互相发故?」曰:「他好把西铭与学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间有个道理恁地开阔。」
「昨夜说『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盖且养他气质,淘潠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如学记所谓『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所以尹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须是如此,方得。天下事无所不当理会者,纔工夫不到,业无由得大;少间措诸事业,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当时大学亦未成伦绪,难看在。」曰:「然。尹彦明看得好,想见煞着日月看。临了连格物也看错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说,是看个甚么?」或曰:「和靖才力极短,当初做经筵不见得;若便当难剧,想见做不去。」曰:「只他做经筵,也不柰何,说得话都不痛快,所以难。能解经而通世务者,无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经筵,又都不肯。一向辞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盖他有退而著书立言以垂后世底意思,无那措诸事业底心。纵使你做得了将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说,岂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这『著书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说话也难。有说得响感动得人者,如明道会说,所以上蔡说,才到明道处,听得他说话,意思便不同。盖他说得响,自是感发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说话方,终是难感动人。」或曰:「如与东坡们说话,固是他们不是,然终是伊川说话有不相乳入处。」曰:「便是说话难。只是这一样说话,只经一人口说,便自不同。有说得感动人者,有说得不爱听者。近世所见会说话,说得响,令人感动者,无如陆子静。可惜如伯恭都不会说话,更不可晓,只通寒暄也听不得。自是他声音难晓,子约尤甚。」
问:「谢氏说『何思何虑』处,程子道『恰好着工夫』,此是着何工夫?」曰:「人所患者,不能见得大体。谢氏合下便见得大体处,只是下学之功夫却欠。程子道『恰好着工夫』,便是教他着下学底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