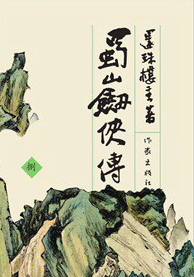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起来,风子见两个山人在用土语叽咕,先以为他们只是畏难,哪知一入野骡岭,便要告辞回去。后来又见他们脸上带着惊慌神色,问他们什么缘故,都不肯说,越发动了疑心。风子知道山人习性,便拔出锏来,大喝一声,平地纵起七八丈高下,一锏朝路旁一块丈许高的山石打去,叭的一声,那石被击碎了小半截,碎石纷飞,火星四溅。吓得两个山人跪在地上,浑身抖战,口中直喊小神饶命。风子喝道:“你们只管告诉我,为什么那样惊慌?”那山人被逼无法,四下偷望了望,才低声说道:“昨晚我二人在洞外大树上睡,看见那神了。想是因为那老真人师徒不准我们供他,供着外来的神,想抽空将大神和小神吃了解恨。我二人本想逃了回去,因还没走到野骡岭,怕黑神杀我们;不逃又怕走在路上,连我二人一起吃了去。如今被小神逼着说了,他如吃不了大神小神,我二人回去时是没命的了。死我们不怕,只是被神吃了,是不能投生转世的。好歹想个法儿,救救我二人吧。”说罢,便鬼嗥般哭了起来。
风子知他说的便是所供的狼面神,山人惯会见神见鬼,又说是什么不常见的野兽虫豸之类,便问:“既是你二人亲见,可曾看清是什么形状?”二山人又做张做智答道:“昨晚月光很亮,我们正说明午可以回去,忽见那神背着一个和大神差不多高矮生相的神,比飞还快地跑来,一到,便直进洞去。待了一会儿,两个神出来,站在地上争论。我们才看清那神是一张人脸,两手极长,并不算高。那另一个神,说话神气也和大神、小神差不多,只上下身都穿着虎皮,脑后从头到背生着一把金毛,直放光,腰间也围了一张虎皮。和另一个争了一阵,末后吼了一声,仍然背了便走。刚一动步,从南山上又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神,更是怕人,除脑后生着极长的金毛外,周身俱是黄光,脸有点像猴,眼睛又红又绿,比闪电还亮。一见前面两个神已走,也没进洞,便追了去。走起路来和风一样,转眼追上先前两个,一会儿便没了影子。刚起步时,有一株大树正碍他路,被他长臂一扫,便成两段。我们先时原要在那树上睡来着,因为枝叶太密,才换了另一株。幸亏不在那树上,要不昨晚就没命了。当时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悄悄从树上溜下来,寻了一个土窟窿伏了一夜。算计这三个神必跟在我们后面,哪还敢说回去?这一说,神必见怪,只好死活都随大神一路了。”
风子正因前路不熟,山人事前说明不愿再送,觉着不便。不想这一来,不用劝,反而志愿跟去。与云从对看了一眼,暗自心喜,风子知道山人蠢而畏鬼,昨晚所见,必是梦境。要不自己不说,云从素来睡觉警觉,稍有响动,便自醒转,昨晚怎么毫不知觉,那东西也没甚侵犯?又想两个山人怎会同时入梦,所见分厘不差?也许是什么奇兽,凭自己和云从的本领,再加上那口霜镡剑,也没什么可虑之处。乐得借此威吓二人道:“你二人不说,我已知道。昨晚那神进洞,原是被我们大神打跑,因为我们贪睡,没有追赶,没想你们这等害怕。本来到了野骡岭,我们原用不着你们引路,只是那神吃了我们的亏,保不得拿你二人出气,待我与大神说,如念你们可怜,便准你们同往峨眉,再行分手。此去路上,再不许像刚才那样做张做智。晚来露宿,你们在外边,如见动静,不论他是人是怪,只管进来报信,我大神自会除他,保你无事。”二人因眼见昨晚二神入洞好一会儿,云从、风子并未受伤,闻言甚是相信,立现喜容,一一应允。云从因二人所说那东西的形状好似在哪里见过,苦于一时想不起来,只管沉思不已。风子与二人把话说完,便请上路,因有二人报警,毕竟有些戒心,各将宝剑、铁锏持在手内,随时留意,往前赶路。
不消多时,走进一座山谷,便入野骡岭。云从望见山形果然险恶,两边危崖壁立,高耸参天。长藤灌木,杂以丹枫,红绿相间,浓荫遮蔽天日。红沙地上,尽是荆榛碍足,径又窄小。这种路,山人素常走惯。只云从没经历过,仍是风子在前开路。走没多远,便将这条狭谷走完,又横越了一片满生荆莽的小平原,便到野骡岭的山麓底下。这山纵横数百里,林丰草长,弥望皆是。须要越过此山,才能到达峨眉,一行四人便往山上走去。荒山原本没路,危崖削嶂间,尽是些蚕丛鸟道。有时走到极危险处,上有危石覆额,下临万丈深渊,着足之处又窄又滑溜,更有刺荆碍足。走起来须要将背贴壁,手扳壁上长藤,低头蹲身,提着气,镇定心神,用脚找路,两手倒换,缓缓前移。一个不留神,抓在腐木枯藤上面,脚再往下面一滑,便要粉身碎骨,坠落深渊。除风子外,休说云从,连那惯走山路的山民,都有些心寒胆战。有时又走到了头,无路可通,再从数十百丈高崖上攀藤缒身而下。深草里蛇虫又多,一不小心便被缠住。好在四人俱有武器,所带包裹又不甚大,还不碍事。这一路翻高纵矮,援藤缒登,费力无穷。且喜这般极危险之处,路均不长。
走有两个时辰,居然走到较为平坦的山原。虽在秋天,因是山中凹地,四面挡风,草木依旧丰盛。那极低湿之处,因为蓄了山水,长时潮润,丛莽分外丰肥。顶上面结着东一堆西一堆的五色云霞,凝聚不散,乃是山岚瘴气,还得绕着它走。两个山人更如狸猫一样,一路走着,不住东张西望。云从问他们何故?二人说是本山惯出野兽,往往千百成群,行走如飞。人遇上纵不被它们吃了,也被它们冲倒,踏为肉泥。还有昨晚那神更是厉害,所以心中害怕。云从见草木这般茂盛,明明没有兽迹,闻言也没放在心上。四人且谈且行,不觉又穿过了那片盆地,翻越了一处山脊,走入一座丛林里面。山那边野草荆棘,何等丰肥。这森林里外,依然也是石土混合的山地,却是寸草不生。树全是千百年以上古木,松柏最多,高干参天,虬枝欲舞,一片苍色,甚是葱茏。风子偶然看见两株断树,因为林密,并未倒地,斜压在别的树上,枝叶犹青,好似方折不久,断处俱留有擦伤的痕迹,心中一动,便喊三人来看。二人见了便惊叫起来,说这树林之中必有水塘,定是什么猛恶野兽来此饮水,嫌树碍路,将它挤断,来得还不在少数。说罢便伏身地面。连闻带看,面带凄惶说:“趁日色正午,野兽出外觅食,不致来此,急速走出林去才好。因为林中松柏气味太盛,闻不出什么异味,但地上已经发现兽迹了。”
风子照他所指,看了又看,果然地上不时发现有不明显的碗大蹄痕。再往前走,越走蹄迹越多,断树也越多,有的业已枯黄。又走了一二里地,果然森林中心有一个大的水塘,深约数尺,清可见底,清泉像万千珍珠,从塘心汩汩涌起,成无数大小水泡,升到水面,聚散不休。塘的三面,俱有两三亩宽的空地。地的尽头,树林像排栅也似的密。只一面倚着一个斜坡,上面虽也满生丛林,却有一条数丈宽的空隙,地上尽是残枝断木,多半腐朽。地面上兽迹零乱,蹄印纵横,其类不一,足以证明山人所见不差。那斜坡上面,必是野兽的来路。
可是那林照直望过去,已到了尽头,广壑横前,碧嶂参天。漫说是人,乌兽也难飞渡,非从那斜坡绕过去不可。明知这里野兽千百成群,绕行此道,难保不会遇上。少还好办,如果太多,不比山人杀一可以儆百。一来便往前不顾死活地乱冲,任是多大本领,也难抵挡。但是除此之外,又别无他途。风子和云从一商量,想起无情火张三姑来传醉道人的仙柬时,原说此行本有险难,途中应验了些,既下决心,哪还能顾到艰危?决计从那斜坡上绕行过去。因一路都见瘴气,有水都不敢饮。一行四人,均已渴极,难得有这样清泉。见那两山人正伏身塘边牛饮,二人便也取出水瓢,畅饮了几口,果然清甜无比。饮罢告诉山人,说要绕走那个斜坡。二人一路本多犹疑,闻言更是惊惶。答道:“这条路,我二人原是来去过两次,回来时节,差点没被野骡子踹死。当时走的,也是这片树林,却没见这个水塘,想是把路走偏了些,误走到此。照野骡子的路走,定要遇上,被它踏为肉泥。只有仍往回走,找到原路,省得送命。”
风子哪肯舍近求远。事有前定,野兽游行,又无准地,如走回去,焉知不会遇上?便对二人再三开导,说大神本会神法,遇上也不妨事。如真不愿行,便听他二人自己回去。二人闻言,更是害怕,只得半信半疑地应允。风子因路已走错,用不着二人引导,好在方向不差。二山民怕鬼怕神,此时也绝不会逃跑。便和云从将身背行囊解下来交与二山民,自己一手持刀、一手持锏,在前开路。那路上草木已被野兽踏平,走起来本不碍事,不多一会儿,便将那斜坡走完。想是不到时候,一只野兽也未看见。二人却越加忧急,说和他们上次行走一样,先时如看不见一个,来时更多。云从、风子也不去理他们,仍是风子在前,二人在中,云从断后,沿着前面山麓行走。走了一会儿,忽见林茂草深,兽迹不见,也没有什么动静,二人方自转忧为喜。
四人俱已走饿,便择了一空处,取出食粮,饱餐一顿,仍自前行,按照日色方向,顺山麓渐渐往山顶上走,也不知经了多少艰险的路径,才到山巅。四顾云烟苍茫,众山潜形。适才只顾奋力往上走,没有回头看,那云层也不知什么时候起的,来去两面的半山腰俱被遮没。因为山高,山顶上依旧是天风冷冷,一片清明。四人略歇了歇,见那云一团一团,往一处堆积,顷刻成了一座云山。日光照在云层边上,回光幻成五彩,兀自没有退意。山高风烈,不能过夜,再不趁这有限阳光赶下山去,寻觅路径,天一黑更不好办。反正山的上半截未被云遮,且赶一程是一程,到了哪里再说哪里。能从云中穿过更好,不然就在山腰寻觅宿处,也比绝顶当风强些。商议停妥,便往下走。渐渐走离云层不远,虽还未到,已有一片片一团团的轻云掠身挨顶,缓缓飞过。一望前路,简直是雪也似白,一片迷茫,哪里分得出一些途径。而从上到下,所经行之处,截然与山那面不同。这面是山形斜宽,除了乱草红沙外,休说岩洞,连个像样子的林木都没有。丛草中飞蚁毒蝇,小蛇恶虫,逐处皆是,哪有适当地方可以住人。这时那云雾越来越密,渐渐将人包围。不一会儿,连上去的路都被云遮住,对面不能见人,始终未看清下面途径形势,怎敢举步,只各暂时停在那里,等云开了再走。正在惶急,忽听下面云中似有万千的咯咯之声,在那里骚动,时发时止,两个山人侧耳细听了听,猛地狂叫一声,回转身便往山项上跑去。
风子一把未抓住,因在云中,恐与云从相失,不敢去追。却是行囊全在二山人身上,万一被他们带了逃走,路上拿什么吃?同时下面骚动之声越听越真,二人渐渐闻得兽啸。那两个山人逃得那般急法,知道下面云层中定有成千成百的兽群。来时由上望下,目光被云隔断,没有看出,忙着赶路,以致误蹈危机。如今身作云中囚,进退两难。虽然人与兽彼此对面不见,不致来袭,不过野兽鼻嗅最灵,万一闻见生人气味,从云雾里冲将过来,岂不更要遭殃?反不如没有这云屏蔽,还可纵逃脱身了。二人虽有一身本领,处在这种极危险的境地,有力也无处使,就在这忧惶无计之际,云从无意中一抬手,剑上青光照向侧面,猛一眼看见风子的双脚。再将剑举起一照,二人竟能辨清面目,不禁想起昔日误走绝缘岭,失去书童小三儿,黑夜用剑光照路寻找之事。方要告诉风子,自己在前借剑光照路,风子在后拉定衣角,一步一步地回身往上,觅地潜伏。言还未了,风子倏地悄声说道:“大哥留神,下面云快散了。”云从和风子说话时,正觉他的面目不借剑光也依稀可以辨认。闻言往下一看,脚底的云已渐渐往上升完。仅乘像轻纳雾縠般那么薄薄一层和一些小团细缕,随着微风荡漾。云影中再看下面山地,只见一片灰黑,仍是看不很清。抬头一看,离头三二尺全被云遮,那云色雪也似白,仿佛天低得要压到头上。银团白絮,伸手可以摸捉,真是平生未见的奇景。
刚想举剑到云中去照,试试剑光在云中可以照射多远,恰值一阵大风劈面吹来。适才在云雾中立了一会儿,浑身衣服俱被云气沾湿,再被这剧烈山风一吹,不由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刚道得一声:“好冷!”猛听下面又有兽啸,接着又听风子惊咦一声。这时那脚底浮云已被山风一扫而空。化成万千痕缕吹烟一般,四散飞舞而去,浮翳空处,那下面的一片灰黑,竟似在那里闪动。定睛一看,并非地色,乃是一种成千成万的怪兽聚集在那里,互相挤在一起,极少动转,间或有几个昂颈长嘶。其形似骡非骡,头生三角,通体黑色如漆,乌光油滑。黑压压望不见边,也不知数目有多少,将山下盆地遮没了一大片,这一惊非同小可。这山从上到下,地形斜宽,无险可守。山这面比山那面,从上到下要近得多,立身之处与群怪兽相去也不过二里高下,五七里远近。风子知道,这种野兽生长荒山,跑起来其疾若飞。虽自己与云从俱都身会武功,长于纵跃,无奈听山人说,杀既杀不完,跑又跑不及,更不能从成千成万野兽头顶飞越而过。除了不惊动它们,让它们自己散去外,别无法想,山形是那般一览无遗,急切间寻不出藏身之所。只得用手一拉云从,伏身地上,眼前先不使它们看见,再想主意。
二人身才一蹲下去,云从头一个听到离身不远的咻咻之声。昔日误走荒山,路遇群虎,有过经验,听出是野兽喘息声。忙和风子回头一看,不知何时,在相隔数丈以外,盘踞着七八只与下面同样的野兽。兽形果然与地名相似,头似骡马,顶生三角,身躯没马长,却比马还粗大。各正瞪着一双虎目,注定二人,看去甚是猛恶。内中有一只最大的,业已站起身来,将头一昂,倏地往下一低。风子自幼生长蛮荒,知道这兽作势,就要扑过,刚喊“大哥留神!”那只最大的早已把头一低,呜的一声怪吼,四条腿往后一撑,平纵起数丈高下,往二人身前直冲过来。当大的怪兽一声吼罢,其余数只也都掉身作势,随着那大的一只同时纵到。云从、风子原不怕这几只,所怕的乃是下面盆地里那一大群。知道这几只大的定是兽群之首,已经被它们发现,吼出声来,下面千百成群的怪兽也必一拥齐上。此时逃走,不但无及,反而勾起野兽追人习性,漫山遍野奔来,再说天近黄昏,道路不熟,也无处可以逃躲。擒贼先擒王,如将这头几只打死,下面那一大群也许惊散。
二人心意不谋而合,便各自紧持兵刃,挺身以待。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动念间,那七八只似骡非骡的怪兽,业已纵临二人头上不远。风子未容它们落地,腿一使劲,手持铁锏,首先纵起空中,直朝那当头最大的迎了上去。这怪兽四脚腾空,将落还未着地,无法回转。被风子当头迎个正着,奋起神威,大喝一声,一铁锏照兽头打去,叭的一声。那怪兽嘴刚张开,连临死怪吼都未吼出,立时脑浆迸裂,脊背朝天,四脚一阵乱舞,身死坠地。风子就借铁锏一击之劲,正往下落,猛听山下面盆地中万兽齐鸣,万蹄踏尘之声,同时爆发出来,声震山岳。心里一惊,一疏神,没有看清地面,脚才点地,正遇另一只怪兽纵到,低头竖起锐角,往胸前冲来。这时两下迎面,俱是猛劲,风子如被撞上,不死必伤。风子一见不好,忽然想起峨眉剑术中弱柳摇风、三眠三起败中取胜的解数。忙举手铁锏,护着前脑面门,两足交叉,脚跟拿劲,往后一仰,仰离地面只有尺许。倏地将交叉的双脚一绞。一个金龙打滚,身子便偏向侧面,避开正面来势。再往上一挺身,起右手锏,朝兽头打去,这一锏正打在兽的左角上面,立时折断。风子更不怠慢,左脚跟着一上步,疾如飘风般一起手中腰刀,拦腰劈下,刀快力猛,迎刃而过,将那怪兽挥为两段。刀过处,那怪兽上半截身子带起一股涌泉般的血水,直飞穿出去丈许远近,才行倒地。风子连诛二兽,暂且不言。
那云从不似风子鲁莽,却杀得比他还多。总是避开来势,拦腰一剑,一连杀了三只。剩下两只,哪禁得起二人的宝剑、铁锏,顷刻之间,七只怪兽全都了账。二人动手时,已听见盆地中那一大群万声吼啸,黑压压一片,像波浪一般拥挤着往上奔来。先以为兽的主脑一死,也许惊散。谁知这类东西非常合群,生长荒山,从未受人侵袭。除了天生生克、一物制一物外,只知遇见敌人一拥齐上。由上到下,原是一个斜平山坡,相隔又近。这一大群怪兽奔跑起来宛如凭空卷起千层黑浪,万蹄扬尘,群吼惊天,声势浩大,眼看就到眼前。这时二人处境,上有密云笼罩,下有万兽包围,进既不可,退亦不能;再加斜阳隐曜,暝色已生,少时薄暮黄昏。那些怪兽全是纵跃如飞,一拥齐来,任是身有三头六臂,也是杀不胜杀。一经被它扑倒,立时成为肉泥。就这危机俄顷之际,虽然明知绝望,不能不作逃生之想。正在张皇四顾之际,头上云雾又往上升高约有两丈。云从猛一眼看到云雾升处,离身数丈远近的山坡上面,露出二三株参天古树,大都数围,上半截树梢仍隐在云雾之中,只有下半截树干露出。急不暇择,口里大声招呼风子,脚底下一连几纵,便到了树的上面。风子因为那万千野兽漫天盖地奔来,相隔仅有半里之遥,知道逃已无及,二人说话声音又为万啸所乱,也没听清云从说的什么,一见云从纵到树上,便也跟着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