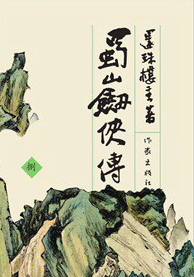那赵心源原名崇韶,乃是江西世家,祖上在明朝曾为显宦。赵心源从小随宦入川,自幼爱武,在青城山中遇见侠僧轶凡,练了一身惊人的本领。他父亲在明亡以后,不愿再事异族,隐居川东,课子力田。去世之后,心源袭父兄余产,仗义轻财,到处结纳异人名士,艺业也与日俱进。江湖上因他本领超群,又有山水烟霞之癖,赠他一个雅号,叫做烟中神鹗。他与陆地金龙魏青,乃是同门师兄弟。近年因在四川路上帮助一家镖客,去夺回了镖,无意中与西川八魔结下仇怨。因常听魏青说起陶钧轻财好友,好武而未遇名师,便想去投奔于他,借以避祸。好在他的名江湖上并无人知道,八魔只以为四川是他的老家,暂时不会寻访到江西来。又见陶钧情意殷殷,便住在他家中,用心指导他内外功门径。三年光阴,陶钧果然内外功俱臻上乘。对于心源,自然是百般敬礼。
有一天,陶钧正同心源在门前眺望,忽然觉得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飞来,再看心源,已将那东西接在手中,原来是一支银镖。正待发问,忽见远处飞来一人,到了二人跟前,望着心源笑道:“俺奉魔主之命,寻阁下三年,正愁不得见面,却不想在此相遇。现在只听阁下一句话,俺好去回复我们魔主。”说罢,狞笑两声。心源道:“当初俺无意中伤了八魔主,好生后悔。本要登门负荆,偏偏又被一个好友约到此地,陪陶公子练武。既然阁下奉命而来,赵某难道就不识抬举?不过赵某还有些私事未了,请阁下上复魔主,就说赵某明年五月端午,准到青螺山拜访便了。”那人听了道:“久闻阁下为人素有信义,届时还望不要失约才好。”说罢,也不俟心源还言,两手合拢,向着心源当胸一揖,即道得一声:“请!”心源将丹田之气往上一提,喊一声:“好!阁下请吧!”再看那人,无缘无故,好似有什么东西暗中撞了似的,倒退出去十几步,面带愧色,望了他二人几眼,回身便走,步履如飞,转眼已不知去向。
陶钧见心源满脸通红,好似吃醉了酒一般,甚觉诧异。刚要问时,心源摇摇头,回身便走。回到陶家,连忙盘膝坐定,运了一会儿气,才说道:“险哪!”陶钧忙问究竟。心源道:“公子哪里知道。适才那人,便是四川八魔手下的健将,名叫神手青雕徐岳的便是。”说罢,将手中接的那支银镖,递与陶钧道:“这便是他们的请柬。只因我四年前,在西川路上,见八魔中第八的一个八臂魔主邱舲,劫一位镖客的镖,他们得了镖,还要将护镖的人杀死。我路见不平,上前解劝,邱舲不服,便同我打将起来。他的人多,我看看不敌,只得败退。不知什么所在,放来一把梅花毒针,将他们打败,才解了镖客同我之围。放针的人,始终不曾露面。八魔却认定了我是他们的仇敌。我听人说,他非要了我的命不可。我自知不敌,只好避居此地。今日在庄外遇见徐岳,若非内功还好,不用说去见八魔,今日已受了重伤。那徐岳练就的五鬼金沙掌的功夫,好不厉害。他刚才想趁我不留神,便下毒手。幸喜我早有防备,用丹田硬功回撞他一下,他就不死,也受了内伤。我既接了八魔请柬,不能不去。如今离明年端午,只有九个多月,我要趁此时机,做一些准备,不能在此停留。公子艺业未成,我也不要做公子的师父,辱没了公子资质。天下剑仙异人甚多,公子如果有心,还是出门留心,在风尘中去寻访。只要不骄矜,能下人,存心厚道,便不会失之交臂的。”陶钧听心源要走,万分不舍,再四挽留不住,又知道关系甚大,只得忍痛让心源走去。由此便起了出门寻师之念。好在家中有陶全掌管,万无一失。于是自己也不带从人,打了一个包袱,多带银两,出门寻觅良师异人。因汉口有先人几处买卖,心源常说,蜀中多产异人,陶钧就打算先到汉口,顺路入川。
行了月余,到了汉口。陶家开的几家商店,以宏善堂药铺资本最大,闻得东家到来,便联合各家掌柜,分头置酒洗尘。陶钧志在求师,同这些俗人酬应,甚觉无聊。周旋几天之后,把各号买卖账目略看了看,逢人便打听哪里有会武术的英雄。那武昌城内赶来凑趣的宏善堂的掌柜,名叫张兴财,知道小东家好武,便请到武昌去盘桓两日,把当地几个有名的武师,介绍给陶钧为友。陶钧自从跟心源学习武功之后,大非昔比。见这一班武师并无什么出奇之处,无非他们经验颇深,见闻较广,从他们口中知道了许多武侠轶闻,绿林佳话,心中好生歆慕。怎奈所说的人,大都没有准住址,无从寻访。便想再住些日,决意入川,寻访异人。众武师中,有一个姓许名钺的,使得一手绝好的子母鸳鸯护手钩,轻身的功夫也甚好,外号展翅金鹏。原是书香后裔,与陶钧一见如故,订了金兰之好。这时已届隆冬,便打算留陶钧过年后,一同入川,寻师访友。陶钧见有这么一个知己伴侣,自然更加高兴。因厌药店烦嚣,索性搬在许钺家中同住。
有一天,天气甚好,汉口气候温和,虽在隆冬,并不甚冷,二人便约定买舟往江上游玩。商量既妥,也不约旁人,雇了一只江船,携了行灶酒食。上船之后,见一片晴川,水天如镜,不觉心神为之一快。二人越玩越高兴,索性命船家将船摇到鹦鹉洲边人迹不到的去处,尽情畅饮。船家把船摇过鹦鹉洲,找了一个停泊所在。陶、许二人又叫把酒食搬上船头,二人举酒畅谈。正在得趣之际,忽见上流头远远摇下一只小船,这只船看去简直小得可怜,船上只有一把桨,水行若飞。陶钧正要说那船走得真快,还未说完,那船已到了二人停舟所在。小船上的人是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在数九天气,身上只穿着一件七穿八洞的破单袍,可是浆洗得非常干净。那小船连头带尾不到七尺,船中顶多能容纳两人。船头上摆了一把瓦茶壶,一个破茶碗,还有一个装酒的葫芦。那老头将船靠岸,望了陶、许二人两眼,提了那个葫芦,便往岸上就走,想是去沽酒去。那小船也不系岸,只管顺水漂泊。陶钧觉得稀奇,便向许钺道:“大哥,你看这老头,想是贪杯如命,船到了岸,也不用绳系,也不下锚,便上岸去沽酒。一会儿这船随水流去,如何是好呢?”说时那船已逐渐要离岸流往江心。陶钧忙命船家替他将船拢住。船家领命,便急忙用篙竹竿将那船钩住。说也可笑,那船上除了几件装茶、酒的器具外,不用说锚缆没有,就连一根绳子也没有,好似那老头子根本没有打算停船似的。船家只得在大船上寻了一根绳子,将那小船系在自己船上的小木桩上。许钺年纪虽只三十左右,阅历颇深,见陶钧代那操舟老头关心,并替他系绳的种种举动,只是沉思不语,也不来拦阻于他。及至船家系好小船之后,便站起身来,将那小船细细看了一遍。忽然向陶钧说道:“老弟,你看出那老头有些地方令人可疑么?”陶钧道:“那老头在这样寒天只穿一件单衫,虽然破旧,却是非常整洁。可是他上岸的时候,步履迟钝,又不像有武功的样子。实在令人看不透来历。他反正不是风尘中异人,便是山林内隐士,绝非常人。等他回来,我们何妨请他喝两杯,谈谈话,不就可以知道了么?”许钺道:“老弟的眼力果然甚高,只是还不尽然。”
陶钧正要问是何缘故,那老头已提着一大葫芦酒,步履蹒跚,从岸上回转。刚到二人船旁,便大喝道:“你们这群东西,竟敢趁老夫沽酒的时候,偷我的船么?”船家见老头说话无礼,又见他穿的那一身穷相,正要反唇相骂。陶钧连忙止住,跳上岸去,对那老头说道:“适才阁下走后,忘了系船。我见贵船随水漂去,一转眼就要流往江心,所以才叫船家代阁下系住,乃是一番好意,并无偷盗之心。你老休要错怪。”那老头闻言,越发大怒道:“你们这群东西,分明通同作弊。如今真赃实犯俱在,你们还要强词夺理么?我如来晚一步,岂不被你们将我的船带走?你们莫非欺我年老不成?”陶钧见那老头蛮不讲理,正要动火,猛然想起赵心源临别之言,又见那老头虽然焦躁,二目神光炯炯,不敢造次,仍然赔着笑脸分辩。那老头对着陶钧,越说越有气,后来简直破口大骂。
许钺看那老头,越觉非平常之人,便飞身上岸,先向那老头深施一礼道:“你老休要生气,这事实是敝友多事的不好。要说想偷你的船,那倒无此心。你老人家不嫌弃,剩酒残肴,请到舟中一叙,容我弟兄二人用酒赔罪,何如?”那老头闻言,忽然转怒为喜道:“你早说请我吃酒,不就没事了么?”陶钧闻言,暗笑这老头骂了自己半天,原来是想诈酒吃的,这倒是讹酒的好法子。因见许钺那般恭敬,知出有因,自己便也不敢怠慢,忍着笑,双双揖客登舟。坐定之后,老头也不同二人寒暄,一路大吃大喝。陶、许二人也无法插言问那老头的姓名,只得殷勤劝酒敬菜。真是酒到杯干,爽快不过。那两个船家在旁看老头那份穷喝饿吃,气忿不过,趁那老头不留神,把小船上系的绳子悄悄解开。许钺明明看见,装作不知。等到船已顺水流出丈许,才故作失惊道:“船家,你们如何不经意,把老先生的船,让水给冲跑了?”两个船家答道:“这里江流本急,他老人家船上又无系船的东西,通共一条小绳,如何系得住?这大船去赶那小船,还是不好追,这可怎么办?好在他老人家正怪我们不该替他系住他的小船,想必他老人家必有法子叫那船回来的。”那老头闻船家之言,一手端着酒杯,回头笑了笑道:“你说的话很对,我是怕人偷,不怕它跑的。”陶钧心眼较实,不知许钺是试验老头的能耐,见小船顺水漂流,离大船已有七八丈远,忙叫:“船家快解缆,赶到江心,替老先生把船截回吧。”
船家未及答言,老头忙道:“且慢,不妨事的,我的船跑不了,我吃喝完,自会去追它的,诸位不必费心了。”许钺连忙接口道:“我知道老前辈有登萍渡水的绝技,倒正好借此瞻仰了。”陶钧这才会意,便也不开口,心中甚是怀疑:“这登萍渡水功夫,无非是形容轻身的功夫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在水面行走。昔日曾听见赵心源说过,多少得有点凭借才行。看那船越流越远,这茫茫大江,无风三尺浪,任你轻身功夫到了极点,相隔数十丈的江面,如何飞渡?”仔细看那老头,除二目神光很足外,看不出一些特别之点。几次想问他姓名,都被他用言语岔开。又饮了一会儿,小船隔离更远,以陶、许二人目力看去,也不过看出在下流头,像浮桴似的露出些须黑点。那老头风卷残云,吃了一个杯尽盘空。然后站起身来,酒醉模糊,脚步歪斜,七颠八倒地往船边便走,陶钧怕他酒醉失足江中,刚一伸手拉他左手时,好似老头递在自己手上一个软纸团,随着把手一脱,陶钧第二把未拉住,那老头已从船边跨入江中。陶钧吓了一跳,“不好”两字还未喊出口,再看那老头足登水面,并未下沉,回头向着二人,道一声“再见”,踢里趿拉,登着水波,望下流头如飞一般走去。把船上众人,吓得目定口呆。江楚间神权最盛,两个船家疑为水仙点化,吓得跪在船头上大叩其头。
许钺先时见那老头那般作为,早知他非常人。起初疑他就会登萍渡水的功夫,故意要在人前卖弄。这种轻身功夫,虽能提气在水面行走,但是顶多不过三四丈的距离,用蜻蜓点水的方式,走时也非常吃力。后见小船去远,正愁老头无法下台,谁知他竟涉水登波,如履平地。像这样拿万丈洪涛当做康庄大路的,简直连听都未听说过。深恨自己适才许多简慢,把绝世异人失之交臂。陶钧也深恨自己不曾问那老头姓名。正出神间,忽觉手中捏着一个纸团,才想起是那老头给的。连忙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迟汝黄鹤,川行宜速”八个字,笔力遒劲,如同龙蛇飞舞。二人看了一遍,参详不透。因上面“川行宜速”之言,便想早日入川,以免错过良机。同许钺商量,劝他不要顾虑家事,年前动身。许钺也只得改变原来安排,定十日内将家中一切事务,托可靠的人料理,及时动身。当下嘱咐船家,叫他们不要张扬出去。又哄骗说:“适才这位仙人留得有话,他同我们有缘,故而前来点化。如果泄露天机,则无福有祸。”又多给了二两银子酒钱。船家自是点头应允。不提。
二人回到许家,第二天许钺便去料理一切事务。那陶钧寻师心切,一旦失之交臂,好不后悔。因老头纸条上有“迟汝黄鹤”之言,临分手有再见的话,便疑心叫他在黄鹤楼相候。好在还有几天耽搁,许钺因事不能分身,也不强约,天天一人跑到黄鹤楼上去饮酒,一直到天黑人散方归,希望得些奇遇。到第七天上,正在独坐寻思,忽然看见众人交头接耳。回头一看,见一僧一俗,穿着奇怪,相貌凶恶,在身后一张桌子上饮酒。这二人便是金身罗汉法元和秦朗,相貌长得丑恶异常,二目凶光显露。陶钧一见这二人,便知不是等闲人物,便仔细留神看他二人举动。那秦朗所坐的地方,正在陶钧身后,陶钧回头时,二人先打了一个照面。那秦朗见陶钧神采奕奕,气度不凡,也知他不是平常酒客。便对法元道:“师父,你看那边桌上的一个年轻秀士,二目神光很足,好似武功很深,师父可看得出是哪一派中的人么?”法元听秦朗之言,便对陶钧望去,恰好陶钧正回头偷看二人,不由又与法元打了一个照面。
法元见陶钧长得丰神挺秀,神仪内莹,英姿外现,简直生就仙骨,不由大吃一惊。便悄悄对秦朗说道:“此人若论功行,顶多武术才刚入门;若论剑术,更是差得远。然而此人根基太厚,生就一副异禀。他既不会剑术,当然还未被峨眉派收罗了去。事不宜迟,你我将酒饭用完,你先到沙市相候,待我前去引他入门,以免又被峨眉派收去。”师徒用了酒饭,秦朗会完饭账,先自一人往沙市去了。法元等秦朗走后,装作凭栏观望江景,一面留神去看陶钧,简直越看越爱。那陶钧起先见法元和秦朗不断地用目看他,一会儿又见他们交头接耳,小声秘密私谈,鬼鬼祟祟的那一副情形,心中已经怀疑。后来见秦朗走时,又对他盯了两眼,越发觉得他二人对自己不怀好意。陶钧虽造诣不深,平时听赵心源时常议论,功夫高深同会剑术的人种种与常人不同之点,估量这两个人如对自己存心不善,绝不容易打发。那和尚吃完不走,未必不是监视自己。自己孤身一人,恐难对付;欲待要走,少年气盛,又觉有些示弱。自想出世日浅,并未得罪过人,或者事出误会,也未可知。于是也装作凭栏望江,看街上往来车马,装作不介意的样子。
正在观望之间,忽见人丛中有一个矮子,向他招呼。仔细一看,正是他连日朝思暮想、那日在江面上踏波而行的那个老头,不由心中大喜。正要开口呼唤时,那老头连忙向他比了又比,忽耳旁吹入一丝极微细的声音说道:“你左边坐着的那一个贼和尚,乃是五台派的妖孽,他已看中了你,想收你做徒弟。你如不肯,他就要杀你。我现时不愿露面,你如想拜我为师,可用计脱身,我在鹦鹉洲下等你。那和尚要想等你下楼,用强迫手段将你带走。你不妨欲取故与,先去和他说话,捉弄他一下。”说完,便不听声响。再看那老头时,已走出很远去了。
说到这里,阅者或者以为作者故意张大其词,否则老头在楼下所说这些话,虽然声小,既然陶钧尚能听见,那法元也是异派剑仙中有数人物,近在咫尺,何以一点听不见呢,阅者要知道,剑仙的剑,原是运气内功,臻乎绝顶,才能身剑合一,可刚可柔,可大可小。那老头说话的一种功夫,名叫百里传音,完全是练气功夫。他把先天真气,练得细如游丝,看准目标,发将出去,直贯对方耳中。声音虽细,却是异常清楚。漫说楼上楼下,这十数丈的距离,就是十里百里,也能传到。剑仙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也是这一种道理。闲话少提,书归正传。
话说陶钧闻听老头之言,才明白那和尚注意自己的缘故。又听那老头答应收他为徒,真是喜出望外。又愁自己被和尚监视,脱身不易。望了望那和尚,好似不曾听见老头曾经和自己说过话一般,就此已知他二人程度高下。于是定了定心神,暗想脱身之计。那法元本想等陶钧下楼时,故意自高身价,卖弄两手惊人的本领,好让陶钧死心塌地前来求教。后来见陶钧虽然看了他两眼,也不过和其他酒客一样,并不十分注意,不由暗暗骂了两声蠢材。他和陶钧对耗了一会儿,不觉已是申末酉初,酒阑人散。黄鹤楼上只剩他两个人,各自都假装眺望江景,正是各有各的打算。陶钧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但因听那老头之言,自己如果一走,那和尚便要跟踪下楼,强迫他同走,匆遽间委实想不出脱身之计。
正在凝思怎样走法,偏偏凑趣的酒保因陶钧连来数日,知是一个好主顾,见他独坐无聊,便上来献殷勤道:“大官人酒饭用完半天,此时想必有些饥饿。适才厨房中刚从江里打来的新鲜鱼虾,还要做一点来尝尝新么?”陶钧闻言,顿触灵机,便笑道:“我因要等一个朋友,来商量一件要事,原说在傍晚时在此相会,大概也快来啦。既有这样新鲜东西,你就去与我随便做两样。我此时有点内急,要下楼方便方便。倘如我那位朋友前来,就说我去去就来,千万叫他不要走开。”说罢,又掏出一锭银子,叫他存在柜上,做出先会账的派头,向酒保要了一点手纸,下楼便走。
法元正在等得不耐烦,原想就此上前卖弄手段。及听陶钧这般说法,心想物以类聚,这人质地如此之高,他的朋友也定不差。便打算索性再忍耐片时,看看来人是谁。估量陶钧如厕,就要回来,也就不想跟去。又因枯坐无聊,也叫酒保添了两样菜,临江独酌。等了半日,不见陶钧回来,好生奇怪,心想道:“此人竟看破了我的行藏么?”冬日天短,这时已是暝色满江,昏鸦四集。酒保将灯掌上,又问法元为什么不用酒菜。法元便探酒保口气道:“适才走的那位相公,不像此地口音,想必常到此地吃酒,你可知道他姓甚名谁,家居何处么?”那酒保早就觉着法元相貌凶恶,荤酒不忌,有些异样,今见他探听陶钧,如何肯对他说真话。便答道:“这位相公虽来过两次,因是过路客人,只知他姓陶,不知他住何处。”法元见问不出所以然来,好生不快。又想那少年既然说约会朋友商量要事,也许如厕时,在路上相遇,或者不是存心要避自己。便打算在汉口住两天,好寻觅此人,收为门下,省得被峨眉派又网罗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