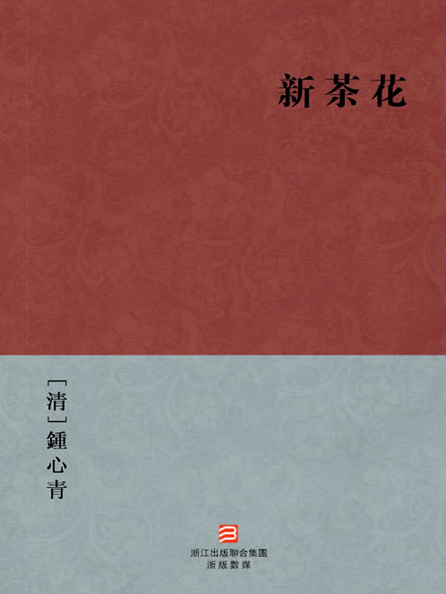那日庆如请了两席酒,算是暖房。除了公一、季留、君实、小牧外,又请了几个邻居,子青是已经回去了。当下林林梳妆出来,与诸人相见。大家见他已改了内家的装束,不施脂粉,淡冶天然,脚上却穿一双京鞋,上绣两只蛱蝶,走起来阁阁的响,季留笑道:「林林改了妆,倒可以入得天足会了。」林林也笑道:「我的脚本来不十分小,一向把他拘束得好不苦脑。最可恶的是,堂子里的恶习,偏是大姐要大脚,小姐要小脚,成为牢不可破的例,好端端的脚指头,生生的拿他弯过来,迭在脚底里,上面又载着若大一个身躯,好像拿干百斤石头,压在已经折转的嫩骨上,你道痛不痛?如今是好了,我不于这营生,也就好放他自由了。」季留笑道:「林林你说女人的脚,是小的好看,还是大的好看?」小牧抢说道:「如果不讲他的痛苦不痛苦,只说他好看不好看,并且也不必说男女子权的道理,只当女人是男人一个玩物,却也是大的好看,小的不好看。为什么呢?小脚的女人,虽是尖瘦可爱,但里头却是污秽,并且疤痕密布,其色黑紫,真是不堪目击。反是没有缠过的脚,血脉流通,柔如凝脂,脱剥出来,自有一种荡人心魄的姿势,你道好看不好看?」公一听了笑道:「说得刻划入细,但不嫌太秽亵么?」林林微笑不言。君实也说道:「林林,你把脚放了,可以做些文明事业,不如进女学堂去读书罢。」林林摇头道:「罢罢,中国此刻的女学,真还在幼稚时代,那女学生一进了学堂,就如封了王一般,一根便纸条还写不出,就只当自己是个文明人,带起眼镜,拖起辫子,看人不在眼里。像我们这种人去就学,是他们不屑与伍的,以为是个卖淫妇,其实他们的行为,也未必高如我辈,不过不好说罢了。像金小宝被学堂里革出来,就是一个榜样。好在我此刻有庆如在此,他是我的师傅。我想别的科学还不要紧,我第一要学琴歌,觉得这件事可以和平我的心志,增进我的幸福。我从前虽学过什么胡琴、琵琶,但觉得声音或是噍杀,或是淫靡,总不及这个好。就是那曲调,也不离这两种毛病,没有发抒性情的好处,你们道是如何?」庆如笑道:「你要学琴,这是很容易的,我明天就去搬一张批阿拿来,我教你就是。」季留拍手道:「本来马克格尼尔姑娘的琴,是巴黎第一,此刻要做上海的首唱了。」大家附和了一阵,方才席散。
却说季留,那一天正在寓所,忽地外间传进一张请客票来,是请到百花里花如玉家酒叙的。主人的姓,是个何字,另外又缀小字,是「君实已到,即候速临」等语。季留心想:这姓何的,莫不是子青出来了?但他并不做花如玉,且字迹不对,决是别人。本想不去,又想君实在彼,借此叙叙也好,便回一声晓得了,自己穿上一件大衣,径来赴席。走进门来,只见房中已经坐席。君实果在那里,背后坐着小花四宝,旁边却空一位。
季留与主人招呼了,便坐在君实旁边。那主人向着君实、季留道:「久仰二君是个江东豪侠,咱小弟也在江湖上颇有名,人多称我『落坑虎』。今日小酌,奉屈一叙,以后便可时常往来了。」
说着把手指首坐一个肥胖大汉道:「这是我们的老大朝天狮子马德芳,想二君必定闻过名的。」季留吃了一惊,暗问君实如何认识他们,君实轻轻说道:「这主人还是今天初会面,我因听得草泽英雄很有几个好的,所以想来物色物色。」季留尚要说时,只见马德芳忽然说道:「这几年我的威名也够了,两江两湖四川云贵的小弟兄,足有上万,那一个不奉着我号令。一到上海,那一个不来孝敬。他们如果吃了外国官司,只消我去同他说一声,应该十年的,减作五年;应该永远监禁,减作廿年。巡捕房里的外国人,只听我的话,所以他们越发怕我了。有哪个不识的人,得罪了我,我吩咐了他们,任你逃到哪里,总要结果了性命。几年来不晓得有许多人死在我手里,真是赛过梁山及时雨哩。」正在说得高兴,只听楼梯上一阵脚声,德芳回过头来,直挺挺的站着一个外国人,顿时吓得呆了,望桌子底只一钻,那花如玉还当是请的客人,想要招呼,只见那外国人把手中棒一指,说了一句,顿时走上许多外国包探、印度巡捕、中国巡捕,把主客都围住了,吓得娘姨大姐鬼哭神号。君实见势不妙,恰好座旁有个窗口,便一脚跨上,钻出窗来,喜得就是连着隔壁人家一个露台,往上跳去,伏作一堆静听消息不题。那西探将各人一一用手铐铐,看见季留没有头发,问他是那个人?季留说是中国人,那人不信,道:「你的面孔赤黑,一定是个安南人。如果真是安南人,我可送到法国领事处去保释。」季留发怒道:「我真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冒充那亡国的奴隶?」那西探被他一喝,倒吃了一惊,也不来铐他,一面把马德芳从桌下拖出,只听得马德芳没口的喊饶命道:「我的姊夫是法兰西巡捕房二头脑,看他的面上,饶了我罢!」西探也不理他,拣一付大铐铐了。再查点人数时,只有七个,缺了一人,却见小花四宝的哥哥,拿着一根胡琴,跟着妹子来出局,此时躲在扶梯背后发抖,西探指道;「就是他!」
一把抓过来,吓得那乌龟只是叫。看官,那乌龟本是不会叫的,此刻逼得他叫了,已经杀尽胜会,如何还听得出他叫的是些什么呢?当下把八个人赶下楼来,到了马路上,一个个把辫子连起,幸得季留没辫子,不会吃这一苦。一径押到巡捕房来,关了一夜,等候明天解到公堂去审。
却说君实伏在露台上,听得巡捕已去,慢慢的爬出来,真是弄得漏网余生,心上还跳不住。只见小花四宝还在那里,见了君实一把拉住,只是哭泣。君实十分不安,又见这里历乱翻腾,存身不住,便同小花四宝回家。他家中听说提去龟子,自是慌乱,君实只好安慰一番。出来探信,原来这次举动是捉拿长江盗匪,打听得这晚在百花里吃酒,恰如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只苦了季留,也凑一个数。到了明天,送到公堂,只因还要听候上宪派员会审,所以并不判断,只将马德方、千季留连那龟子取保候审。一则因是留学生,究竟体面一些,一则因是龟奴,委系误拘。那马德方却因他姊姊姘了一个法国巡捕,他来说情,靠在这裤带的分上,所以一并保出。到后来会审,平季留同龟奴无罪释放,余者杀的杀、监的监,轻重不一,只有这马德芳是个匪首,正要办他,谁知他一保出来,便行了三十六计中的上计,办他不动,直到四五年后,才在宁波拿住,死在狱中。这是后话,不提。却说平季留,自经此一番挫折,从此灰心世务,绝意进取,只在家中务农,连上海也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