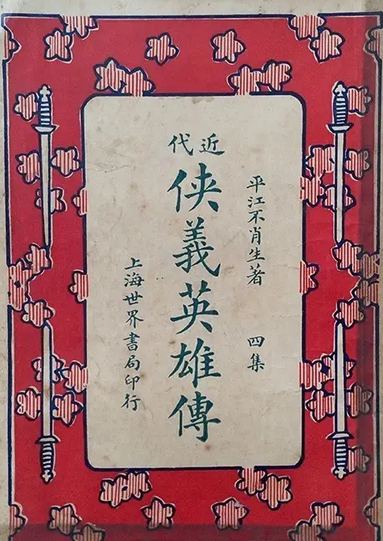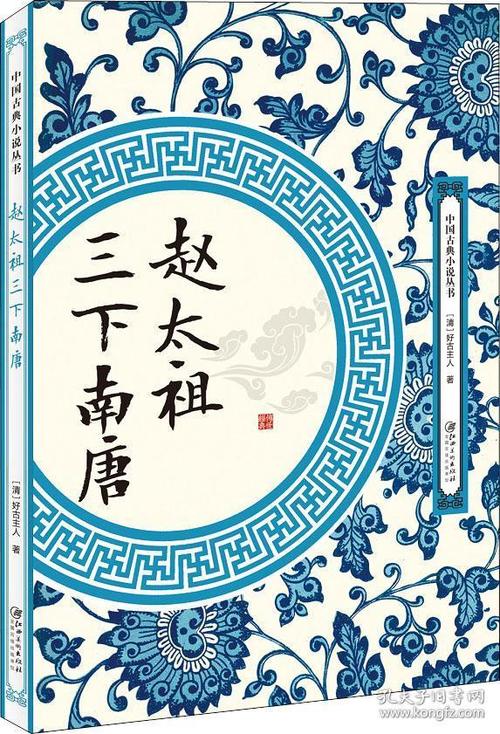话说霍俊清听了刘震声哭诉的话,错愕了半晌,心想这事真是出人意外,也不能责骂刘震声,也不能归咎于摩霸的哥哥,只能怪摩霸的气量过于褊仄。但是,这么一来,教我怎生对得起李爷呢?正要止住刘震声莫哭,打算出去看有没有解救的希望,只见李富东泪流满面的走了进来,见面就跺脚叹气道:“霍爷,你看!这是从哪里说起。我的老运怎的这般不济,仅仅一个如意些儿的徒弟,都承受不了,还要是这么惨死,真比拿快刀割我的心肝更加厉害。”
霍俊清也两眼流泪的叹道:“谁也想不到有这种岔事闹出来。这只怪我这小徒不是东西。”李富东连忙摇手,止住霍俊清的话,一面弯腰拉了刘震声的手,一面用袍袖替刘震声揩了眼泪道:“怎么能怪他呢?”接着就温劝刘震声道:“刘大哥心里快不要如此难过。我徒弟的性情我知道。他今日悬梁自尽,可知你昨日对他很客气。他在我跟前二十多年,我索知他是这么的脾气,服软不服硬,最要强,最要面子。他赌输了房屋,没得交割你,刘大哥若一些儿不客气,硬问他要,倒没事了,他决不会自尽。你越是对他客气,用言语去宽慰他,他心里越觉难过,越觉没有面子,做不起人。这全是由于我的老运不济,谁也不能怪。”
霍俊清问道:“已解救过了,无望吗?”李富东悠然叹道。“哪里还用得着解救,大概巳经去世好几个时辰了。”霍俊清道:“李爷若不强留我师徒久住在这里,或者还不至出这种岔事。”李富东摇头道:“死生有命,与霍爷师徒住在这里有什么相干!”李富东虽则是这么说;然霍俊清师徒总觉得心里过不去,走到摩霸的尸体跟前,师徒都抚尸痛哭了一场。就在这日,辞了李富东和王老头,回天津来。闷闷不乐的过了两个多月。
这日正是三月初十,霍俊清独自坐在账房里看账。忽见刘震声笑嘻嘻的走了进来,手中拿着红红绿绿的纸,上面印了许多字迹。霍俊清掉转身来问道:“手里拿的什么?”刘震声笑道:“师傅看好笑不好笑,什么俄国的大力士跑到这天津来卖艺,连师傅这里也不来拜望拜望,打一声招呼。这张字纸便是他的广告,各处热闹些儿的街道都张帖遍了。我特地撕几张回来,给师傅看看。”
霍俊清伸手接那广告,旋正色说道:“我又不是天津道上的头目,他俄国的大力士来这里卖艺。与我什么相干。要向我打什么招呼?”说着,低头看那广告,从头至尾看完了一道,不由得脸上气变了颜色,将广告纸往地下一摔,口里连声骂道:“混帐,混帐!你到我中国来卖艺,怎敢这般藐视我们中国人,竟敢明明白白的说我们中国没有大力士!”
刘震声问道:“广告上并不曾说我们中国没有大力士,师博这话从哪里听得来的呢?”霍俊清道:“你不认识字吗?这上面明说,世界的大力士只有三个:第一个俄国人,就是他自己;第二个是德国人;第三个是英国人。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说我中国人当中没有大力士吗?他来这里卖艺,本来不与我相干,他如今既如此藐视我中国人,我倒不相信他这个大力士,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得去和他较量较量不可!”
刘震声正待问怎生去和他较量的话,猛听得门外阶基上有皮靴声响,连忙走出来看,原来是霍俊清的至好朋友,姓农名劲荪的来了。这农劲荪是安徽人,生得剑眉插鬓,两目神光如电,隆准高颧、熊腰猿臂。年龄和霍俊清差不多,真是武不借拳、文不借笔,更兼说得一口好英国活,天津、上海的英、美文学家,他认识的最多。想研究中国文学的英、美人,时常拿着中国的古文、诗词来请农劲荪翻译讲解,研究体育的英、美人,见了农劲荪那般精神、那般仪表。都不问而知是一个很注重体育的人,也都欢喜和他往来议论。那时中国人能说英国活的,不及现在十分之一的多,而说得来英国话的中国人,十九带着几成洋奴根性,并多是对于中国文字一窍不通,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认得、都写不出,能知道顾全国家的体面和自己的人格的,一百人之中大约也难找出二、三个。这农劲荪却不然,和英、美人来往,不但不敢对他个人有丝毫失敬的言语和失体的态度,并不敢对着他说出轻侮中国的国体和藐视一般中国人的话。有不知道他的性格而平日又欺凌中国人惯了的英、美人,拿阼一般能说英国话的洋奴看待他,无不立时翻脸,用严词厉色的斥驳,必得英、美人服礼才罢。不然,就即刻拂袖绝交,自此见了面决不交谈。英、美人见他言不乱发,行不乱步,学问、道德都高人一等,凡和他认识的,绝没一个不对他存着相当的敬仰心。他生性喜游历,更喜结交江湖豪侠之士,到天津闻了霍俊清的名,就专诚来拜访,彼此都是义侠心肠,见面自易投契。
这日,他来看霍俊清,也是为见了大力士的广告,心里不自在,想来和霍俊清商量,替中国人争争面子。刘震声迎接出来,见面就高兴不过,来不及的折转身高声对霍浚清报告道:“师傅!农爷来了。”说罢,又回身迎着农劲荪笑道:“农爷来的正好,我师傅正在生气呢!”
农劲荪一面进房,一面笑答道:“我为的是早知道你师傅要生气,才上这里来呢!”霍俊清已起身迎着问道:“这狗屁广告,你已见着了么?”农劲荪点头道:“这广告确是狗屁,你看了打算怎样呢?”霍俊清道:“有什么怎样,我们同去看他这个自称世界第一个的大力士,究竟有多大的力?你会说外国话,就请你去对他说,我中国有一个小力士,要和他这个大力士较量较量。他既张广告夸口是世界第一个大力士,大概也不好意思推诿,不肯和我这小力士较量。”农劲荪高兴道。“我愿意。担任办交涉,我求之不得,哪里用得着你说出这一个请字呢!”
刘震声也欢喜得要跳起来,向农劲荪问道:“我同去也行么?”农劲荪道:“哪有不行的道理。广告上说六点钟开幕,此刻已是五点一刻了,今日初次登场,去看的人必多,我们得早些去。”刘震声道:“广告上说头等座位十块钱一个人,二等五块,我们去坐头等,不要花三十块钱吗?”农劲荪没回答,霍俊清说道:“你胡说!我们又不是去看他卖艺,去和他较量也要钱吗?他若敢和我较量,他的力真个比我大,莫说要我花三十块,便要化三百块、三千块,我也愿意拿给他,不是真大力士,就够得上要人花这么多钱去看他吗?”农劲荪点头道:“不错,二位就更了衣服去吧。”
霍俊清师徒换了衣服,和农劲荪一同到大力士卖艺的地方来,见已有许多看客,挤拥在卖入场券的所在。农劲荪当先走进入口,立在两旁收券的人伸手向农劲荪接券,农劲荪取出一张印了霍元甲三字的名片来,交给收券的人道:“我们三人不是来看热闹的,是特来替你们大力士帮场的,请将这名片进去通报一声。”这收券的也是天津人,天津的妇人、孺子都闻得霍元甲的声名,收券的不待说也是闻名已久,一见这名片,即连忙点头应是,让霍俊清三人进了入口,转身到里面通报去了。
这时不到六点钟,还不曾开幕。三人立在场外,等不一会,只见刚才进去通报的人,引着一个西装的中国男子出来。农劲荪料想这男子,必是那大力士带来的翻译,即上前打招呼说道:“我等都是住在天津的人,见满街的广告,知道贵大力士到天津来卖艺,我等异常欢迎,都想来赡仰瞻仰,不过广告上贵大力士自称世界第一,觉得太藐视了我中国,我等此刻到这里来,为的要和贵大力士较一较力,看固谁是世界第一个大力士。”
那翻译打量了三人几眼,随让进一问会客室。请三人坐下说道:“兄弟也是直隶人,此次在这里充当翻译,是临时受聘的。汉文广告虽系兄弟所拟,然是依据英文广告的原文意义,一字也不曾改动。如今三位既有这番意思,兄弟也是中国人。当然赞成三位的办法。只是依兄弟的愚见,这位这番举动,关系甚是重大,敝东既敢夸口自称世界第一个大力士,若言藐视,也不仅藐视我中国,法、美、日、意各大国,不是同样的受他藐视吗?这其间必应有些根据,现在我们姑不问他根据什么,他免不了要登场演艺的,且屈三位看他一看,他演出来的艺,在三位眼光中看了,也能称许是够得上自称世界第一,那就没有话说,若觉得够不上,届时再向兄弟说,兄弟照着三位说话的意思,译给敝东听,是这么办法似觉妥当些。”农劲荪不住的点头道:“是这么办最好。”霍俊清也说不妨且看看他。于是那翻译,就起身引三人入场,在头等座里挑了三个最便于视览的座位。请三位坐了,一会儿派人送上烟、茶来,又派人送上水果、点心来。
这时已将近开幕,看客渐渐的多了。头等座里除了霍俊清等三个中国人外,全是西洋人。那些西洋人,见三个中国人坐在头等座里,并且各人面前都摊了许多点心、水果,比众人特别不同,都觉得诧异,很注目的望着。其中有和农劲荪认识的英国人、美国人,便趁着未开幕的时分,:过来和农劲荪握手,顺便打听霍、刘二人是谁。农劲荪即对英、美人将来意说明,并略表了一表霍俊清的历史。英、美人听了,都极高兴,互相传说。今日有好把戏可看。
一刻掌声雷动,场上开幕了。那翻译陪同着一个躯干极雄伟的西洋人出场,对看客鞠躬致敬毕!那西洋人开口演说。翻译照着译道:“鄙人研究体育二十年,体力极为发达,曾漫游东、西欧,南、北美,各国的体育专家多曾会晤过,较量过体力,没有能赛过鄙人的。承各国的体育家、各国的大力士承认鄙人为世界第一个大力士。此度游历到中国来,也想照游历欧美各国时的样,首先拜访有名的体育家和有名的大力士,奈中国研究体育的机关绝少,即有也不过徒拥虚名,内部的组织极不完备,研究体育的专家更是寻访不着。也打听不出一个有名的全国都推崇的大力士,鄙人遂无从拜访。鄙人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的病夫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体育一科,关系人种强弱、国象盛衰。岂可全国无一完善专攻研究的机关?鄙人为欲使中国人知道体育之可贵,特在天津献技一礼拜,再去北京、上海各处献技,竭诚欢迎中国的体育专家和大力士,前来与鄙人研究。”
演毕,看客们都鼓掌,只气得霍俊清圆睁两眼,回头瞪着一般鼓掌的中国人,恨不得跳上台去,将一般鼓掌的训斥一顿才好。农劲荪恐怕霍俊清发作,连忙拉了他一把,轻轻的说道:“且看这大力士献了技再说,此时犯不着就发作。”霍俊清最是信服农劲荪的,听了这话,才转身望着台上,板着脸一言不发。看那演台东边,放着一块见方二尺的生铁,旁边搁着两块尺多长、六七寸宽、四五寸厚的铁板,演台西边摆着一条八尺来长、两尺来宽、四寸多厚的白石,石旁堆着一盘茶杯粗细的铁箍,仿佛大轮船上锚的链条。那大力士演说罢,又向看客鞠了一躬,退后几步,自行卸去上衣,露出那黑而有毛的胸脯和两条筋肉突起的臂膀来,复走到台口,由那翻译说道:“大力士的体量重三百八十磅,平时的臂膊大十八英寸,运气的时候大二十二英寸,比平时大四英寸,胸背腰围运用气力的时候,也都比平时大四英寸。这一幕专演筋肉的缩胀和皮肤的伸缩给诸君看。”翻译说毕。立在一旁。
大力士骑马式的向台下立着,一字儿伸开两条手膀,手掌朝天,好象在那里运动气力,约有一分钟久,翻译指着大力士的膀膊对看客说道:“请诸君注意,筋肉渐渐的膨胀起来了。”霍俊清三人坐的最近,看得分明,只见那皮肤里面仿佛有许多只小耗子在内钻动,膀膊胸腰果然比先时大的不少。坐位远的看不清晰,就立起来,遮掩了背后的人,更看不见,便哄闹起来。大力士即在这哄闹的声中,中止了运动,走到那盘铁链跟前,弯腰提起一端的铁环,拖死蛇似的拖到台心。翻译说道:“这铁链是千吨以上的海船上所用的锚链,其坚牢耐用不待说明,诸君看了大约没有不承认的。大力_ 士的力量,能徒手将这链拉断。”看客们听了,登时都现出怀疑的神色。
农劲荪、刘震声二人,不曾试演过。也有些疑惑是不可能的事。大力士将提在手中的铁环,往右脚步尖上一套,用不丁不八的步法,把铁环踏住,然后拿起那链条从前胸经左肩绕到背后,复从右胁围绕上来,仍从左肩绕过,如此绕了三、四周,余下来的链头,就用两手牢牢的握住。当铁链在周身围绕的时候。大力士将身体向前略略的弯曲围绕停当,两手牢握链尾一些儿不使放松,慢慢的将身体往上伸直,运用浑身气力,全注在左肩右脚,身体渐摇动渐上伸,到了那分际,只听得大力士猛吼了一声,就在那吼声里面,铁链条从左肩上反弹过去,“啪”的一声响,打在台上。原来用力太猛,铁链挣断了,所以反激过去。台上的吼声、响声未了,台下的欢呼声、鼓掌声已跟着震天价响起来。农劲荪留神霍俊清淡淡的瞧着,只当没有这回事的一般。
大力士挣断铁链之后,从右脚上取下那铁环和剩下的尺多长铁链。扬给台下人看了一看,解下身上缠绕的铁链,仍堆放在原处,又向看客鞠了一躬,带着翻译进去了。看客们都纷纷的议论,说真不愧为世界的第一个大力士。头等座里的西洋人,便都注目在霍俊清身上。农劲荪正待问霍俊清看了觉得怎样,台上的大力士又大踏步出来了,遂截住了话头,台上的翻译已指着放在东边台口的那方生铁道:“这方生铁足重二千五百斤,中国古时候的西楚霸王,力能举千斤之鼎,历史上就称他力可拔山,以为是了不得的人物。如今大力士能举二千多斤,比较起西楚霸王来超过倍半以上,真不能不算是世界古今第一个大力士了。大力士在南洋献技的时候,曾特制一个绝大的木笼,笼里装着二十五个南洋的土人,大力士能连人带笼举将起来,土人在里面并可以转侧跳动。这回只因大力士嫌木笼太笨,而招集二十五个人也觉得过于麻烦,才改用了这方生铁。但是大力士的力量,还不止二千五百斤,这方生铁已经铸就了,不能更改,只得另添这两块铁板。这铁板每块重一百斤,合计有二千七百斤。据大力士说,惟有德国的大力士森堂,能举得起二千五百斤,所以称世界第二个大力士,彼此相差虽仪二百斤,然力量到了二千斤以上,求多一斤都不容易,这是大力士经验之谈。相差二百斤,就要算差得很远了。诸君不信,请看大力士的神力。”说完退开,远远的站了,好象怕大力士举不起生铁,倾倒下来打伤了他似的。
这时大力士身上,穿了一件贴肉的卫生汗衫,两边肩头上贴着两条牛皮,遮盖着两条臂膀,是防生铁磨破汗衫伤了皮肤的,两个膝盖上系了两方皮护膝,护膝里面大约填塞了两包术棉,凸起来和鹤膝相似。大力士先将那方生铁,用两手推移,慢慢移至台心,方向台口蹲下身体,两手攀住生铁的一边,往两膝倒下。就在这个当儿,从里面走出四个彪形大汉的西洋人,分左右立在大力士旁边,以防万一有失,生铁跌下来不致惊了台下的看客。大力士伸两手到生铁的下方,缓缓的将生铁搬离了地,搁在膝盖上面、停了一停。立在东边的两个助手,每人双手捧起一块铁板,轻轻加在那方生铁上面。大力士一心不乱的运足两膀神力,凭空向头顶上举将起来,演台座位都有些摇摇的晃动,满座的看客没一个不替大力士捏着一把汗,悬心吊胆的望着,全场寂静静的没一些儿声息。
大力士双手举起那方二千七百斤的生铁,约支持了半分钟久,两膀便微微的有些颤动,举着这么重的东西颤动,自然牵连得演台座位都有些摇荡似的,吓得那些胆小嘴快的看客,不约而同的喊道:“哎呀!快放下来,跌了打伤人呢!”胆壮的就嗔怪他们不该多事乱喊,你啐一口,他叱一声,一个寂静的演场,登时又纷扰起来了。
大力士初次到中国来,在欧美各国游历的时候,从来不见过这般没有秩序的演场,这时被扰乱得很不高兴,他不懂得中国话,以为看客们见他手颤,口里喊的是轻侮他的话,又见叱的叱,啐的啐,更误会了,以为叱的是叱他,啐的也是啐他,哪里高兴再尽力支持呢!就在纷扰的时候,由两边四个健汉帮扶,将生铁放下来了。
霍俊清回头对农劲荪道:“这小子目空一切,说什么只有德国的森堂能举二千五百斤,什么中国没有体育家,没有大力士,简直当面骂我们,教我怎能忍耐得下!我不管他有多少斤的实力,只要他跟我在台上较量。若他的力大,我打他不过,被他打伤了或打死了,他要称世界上第一个大力士,他尽管去称。伤的死的不是我,只怪他太狂妄,不能怪我打伤了他。我在这里等你,请你就去和他交涉吧!”
农劲荪知道霍俊清素来是个极稳健的人,他说要上去较量,必有七、八成把握,决不是荒唐人冒昧从事的,当下即起身说道:“我且去谈判一度。他如有什么条件,我冉来邀你。”霍俊清点头应“好”。
农劲荪向内场行去,只见那翻译也迎面走来,笑问农劲荪道:“先生已见过了么,怎么样呢?”农劲荪看那翻译说话的神情,象是很得意的,估量他的用意,必以为大力士既已显出这般神力来,决没人再敢说出要较量的话,所以说话露出得意的神情来。农劲荪心里是这么估量,口里即接着答道:“贵大力士的技艺,我等都已领教过了。不过敞友霍元甲君,认为不能满意,非得请贵大力士跟他较量较量不可,特委托兄弟来和贵大力士交涉,就烦先生引兄弟去见贵大力士吧!”
翻译听完农劲荪的话,不觉怔了一怔,暗想:霍元甲的声名,我虽曾听人说过,然我以为不过是一个会把式的人,比寻常一般自称有武艺的人略高强点儿,哪里敢对这样世界古今少有的大力士,说出要较量的话呢?当初他未曾亲见,不怪他不知道害怕,如今既已亲目看见了三种技艺,第一种或者看不出能耐,第二种、第三种是无论谁人见了,都得吐舌的,怎的他仍敢说要较量呢?他说认为不满意,难道霍元甲能举得再重些吗?只是他既派人来办交涉,我便引他去就得了。我巴不得中国有这么一个大力士。翻译遂向农劲荪说道:“贵友既看了认为不满意,想必是有把握的。先生能说得来俄国话么?”农劲荪道,“贵大力士刚才在台上说的不是英国话吗?”翻译连忙点头,转身引农劲荪到内场里面一间休憩室,请农劲荪坐了,自去通知那个大力士。
农劲荪独自坐在那里,等了好一会,仍是那翻译一个人走了来,问农劲荪道:“先生能完全代表贵友么?”农劲荪道:“敝友现在这里,用不着兄弟代表。兄弟此来,是受敝友的托,来要和大力士较量的。若大力士承认无条件的较量,兄弟去通知敝友便了。如有什么条件,兄弟须去请敝友到这里来。”翻译道:“那么由兄弟这里派人去请贵友来好么?”农劲荪连说:“很好!”翻译即招呼用人,去请霍俊清。
不一时,霍、刘二人来了,翻译才说道:“敝东说他初次来中国,不知道中国武术家较量的方法,不愿意较量,彼此见面作谈话的研究,他是很欢迎的。”霍俊清笑道:“他既自称为世界第一个大力士,难道中国不在世界之内,何能说不知道中国武术较量的方法呢?不较量不行,谁愿意和他作谈话的研究!他说中国是东方的病夫国,国人都和病夫一般,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士,却怕我这个病夫国的病夫做什么哩!烦足下去请他到这里来吧。我霍元甲是病夫国的病夫,在世界大力士中一些儿没有声名的,也没有研究过体育,也不曾受全国人的推崇,请他不必害怕,我此来非得和他较量不可。”
霍俊清说时盛气干霄,翻译不敢争辩,只诺诺连声的听完了,复去里面和大力士交涉。这回更去得久了,约莫经过了一点多钟,霍俊清三人都以为在里面准备比赛,那翻译出来将农劲荪邀到旁边说道:“敝东已打听得霍先生是中国极有名望的武术家,他甚是钦佩,但确是因未曾研究过中国的武术,不敢冒昧较量。他愿意交霍先生做个朋友,如霍先生定要较量,可于交过朋友之后再作友谊的比赛,教兄弟来将此意,求先生转达霍先生。”
农劲荪道:“霍先生的性情,从来是爱国若命的。轻视他个人,他倒不在意。他一遇见这样轻视中国的外国人,他的性命可以不要,非得这外国人伏罪不休。贵大力士来中国卖艺,我等是极端欢迎的,奈广告上既已那们轻藐中国,而演说的时候更加进一层的轻藐,此时霍先生对于大力士已立于敌对的地位,非至较量以后没有调和的余地。大力士当众一干的轻藐中国,岂可于交过朋友之后作友谊的比赛?假使没有那种广告并这种演说,兄弟实能担保霍先生与大力士做好朋友,此刻只怕是已成办不到的事了,只是兄弟且去说说看。”
农劲荪回身将和翻译对谈的话,向霍俊清说了一遍。霍俊清道:“好不知自爱的俄罗斯人,侮辱了人家,还好意思说要和人家做朋友。我如今也没有多的话说,只有三个条件,听凭他择一个而行。”农劲荪忙问哪三个,霍俊清道:“第一个,和我较量,各人死伤各安天命,死伤后不成问题;第二个,他即日离开天津,也不许进中国内部卖艺;第三个,他要在此再进中国内部卖艺也行,只须在三日内,登报或张贴广告,取消‘世界第一’四个字。他若三个都不能遵行,我自有对付他的办法。”农劲荪随将这条件,说给那翻译听了。那大力士不敢履行第一条,第三条也觉得太丢脸,就在次日动身到日本去了,算是履行了第二条。
农劲荪觉得霍俊清这回的事,做得很痛快。过了几日,又来淮庆会馆闲谈,谈到这事,农劲荪仍不住的称道,霍俊清叹道:“这算得什么!我虽则一时负气把他逼走了,然他在演台上说的话,也确是说中了中国的大毛病。我如今若不是为这点儿小生意,把我的身子羁绊住了!我真想出来竭力提倡中国的武术。我一个人强有什么用处?”农劲荪极以为然说道:“有志者事竞成。你有提倡中国武术的宏愿,我愿意竭我的全力来辅助你成功,但也不必急在一时。”这是霍俊清后来办精武体育会的伏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一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