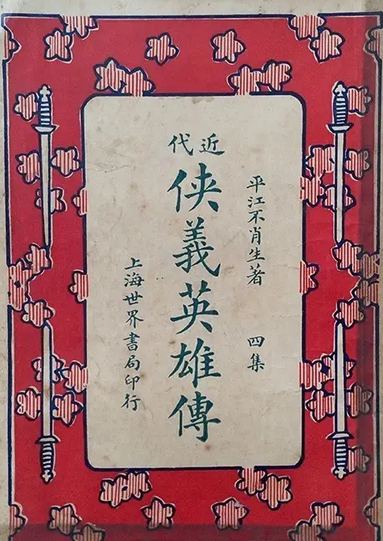话说农劲荪见问,说道:“四爷不用忙,若没有更可气的事,我也不说险些儿把胸膛气破的话了。原来余伯华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完全上了人家的当,活活的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卜妲丽断送了。魏季深那个丧绝天良的东西,假意殷勤做出十分关切他,尽力援救他的模样,其实是承迎方大公子和张知县的意旨,设成圈套,使余伯华上当的。余伯华若是个有点儿机智的人,就应该知道魏季深与自己并无深厚的交情,同学而兼同事的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至少也有几十人,何以有深交的来也不来,而没有深交却忽然来的这么诚恳,并且来的这么迅速,不是很可疑吗?魏季深本人既可疑,他托付的人倒可信吗?那书记所说卜妲丽的情形,分明是有意捏造这些话,好使他对卜妲丽绝望的,怎么可以信以为实呢?他直到出衙门打听,才知道卜妲丽虽确是迁居在美领事馆,然无日不到天津县衙哭泣,出钱运动衙差狱卒,求与余伯华会面。怎奈张知县受了方大公子的吩咐,无论如何不能使他两人见面,知道见了面,就逼不出离婚字来了。美领事并没有羁押卜妲丽的行为,不过也与方大公子伙通了,表面做出保护卜妲丽的样子,实际也希望天津县逼迫余伯华离婚。卜妲丽不知道底蕴,还再三恳求美领事设法援救余伯华。美领事若真肯出力援救,哪有援救不出的道理?可惜卜妲丽年轻没有阅历,见理不透,余伯华写的离婚字,一到张知县手里,即送给方大公子。方大公子即送给美领事,美领事即送给卜妲丽看。卜妲丽认识余伯华的笔迹,上面又有指模,知道不是假造,当下也不说什么,回到她自己房里,一剪刀将满脑金黄头发剪了下来,写了一封埋怨余伯华不应该写离婚字的信,信中并说她自己曾读中国烈女传,心中甚钦佩古之烈女,早已存不事二夫之心,如今既见弃于丈夫,何能再腼颜人世,已拚着一死,决心绝食。可怜一个活跳跳的美女,只绝食了六昼夜,竟尔饿死了。”
霍元甲托地跳了起来叫道:“哎呀!有这等暗无天日的事吗?余伯华出牢之后,何以不到美领事馆去见卜妲丽呢?”农劲荪道:“何尝没去!只是他已亲笔写了与卜妲丽离婚的字,卜妲丽听说他来了,气得痛哭起来,关了门不肯相见,美领事也不愿意他两人见面。余伯华去过一次之后,美领事即吩咐门房,再来不许通报,因此第二、三次去时,倒受那门房的白眼。然也直到卜妲丽饿死后,传出那封绝命的信来,才知道她的节烈。此刻余伯华也悲伤得病在床褥,一息奄奄,你们看这事惨也不惨!”
吴鉴泉道:“这事虽可怪余伯华不应该误信魏季深,但是方大公子和张知县伙谋,设下这种恶毒的圈套,便没有魏季深,余伯华也难免不上当。为人拚一死倒容易,拘禁在监牢里,陆续受种种痛苦,又在外援绝望的时候,要始终坚忍不动,却是很难。总之,他们夫妻,一个是年轻不知世故的小姐,一个是初出茅庐、毫无权势、毫无奥援的书生,落在这一般如狼似虎、有权有势的官府手里,自然要怎么样,只得怎么样。余伯华若真个咬紧牙关不写那离婚字,说不定性命就断送在天津县监里,又有谁能代他伸冤理屈呢?”
霍元甲点头道:“这话很对!余伯华若固执不肯写离婚字,方制台的儿子与张知县吃得住余伯华没有了不得的来头,脚镣手铐之外,说不定还要授意牢禁卒,三日一小逼,五日一大逼的,将余伯华吊打起来,打到受不了的时候,终得饮恨吞声的写出来,怎样拗得过他们呢?这种事真气破人的肚子。农爷,你是一个有主意的人,有不有方法可以出出这口恶气?”
农劲荪摇头道:“如今卜妲丽也死了,二三百万遗产已没有下落了,余伯华也已成为垂死的人了,无论有什么好方法,也不能挽救。只可恨我得消息太迟了,若在余伯华初进监的时候,我就得了消息,倒情愿费些精神气力,替他夫妻做一个传书的青鸟,一方面用惊人的方法,去警告陷害余伯华的人,那么或者还能收点儿效果,事后专求出气,有何用处呢?”
吴鉴泉道:“事前能设法挽回,果然是再好没有的了,但是此刻若能设法使设谋陷害余伯华的人,受些惩创,也未始不可以惩戒将来,使他们以后不敢仗着自己有权有势,再是这么无法无天的随意害人家的性命。”
农劲荪慢慢的点着头,说道:“依你老兄有什么高见可以惩戒他们?”吴鉴泉摇了摇脑袋笑道:“我们家属世代住在北首的人,不用说做,连空口说说都难。兄弟今日虽是初次登龙,不应如此口不择言,只因久慕两位大名,见面更知道都是肝胆照人的豪杰,为此不知不觉的妄参末议。”
霍元甲连忙说道:“兄弟这里是完全做买卖的地方,除了采办药料的人而外,没有闲人来往,不问谈论什么事,从来是在这房间里说,便在这房间完了,出门就不再谈论。老兄有话尽管放胆说,果有好惩戒他们的方法,我等有家有室在北首的不能做,自有无家无室的人可以出头。他们为民父母的人,尚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陷害无辜良善,我们为民除败类,为国除奸臣,可算得是替天行道,怕什么!”
农劲荪道:“四爷的话虽有理,但是为此事犯不着这么大做,因为事已过去了,就有人肯出头,也无补于事,无益于人。至于奸臣败类,随处满眼皆是,如何能除得尽?”
吴鉴泉点首称赞道:“久闻农爷是个老成练达的豪杰,固是使人钦佩。霍四爷得了农爷这样帮手,无怪乎名震海内。兄弟在京听得李存义谈起两位,在上海定约与外国大力士比武的话,不由得异常欣喜。中国的武艺,兄弟虽不能称懂得,只是眼里却看的不少,各家各派的式样,也都见识过一点,惟有外国的武艺,简直没有见过,不知是怎样一类的手法,久有意想找一个会外国武艺的人,使些出来给我瞧瞧,无如终没有遇着这种机会。前几年在京里听得许多人传说,有一个德国的大力士,名叫森堂,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士,行遍欧美各国,与各国的大力士相比,没有一个是森堂的对手,这番到中国来游历,顺便在各大码头卖艺,已经到了天津。兄弟那时得了这消息,便打算赶到天津来见识见识,有朋友对我说道:”森堂既是到中国来游历,已到了天津,能够不到北京来吗?北京是中国的都城,他在各码头尚且卖艺,在北京能不卖艺吗?他送上门来给你看,何等安逸,为什么要特地赶到天津去看?‘兄弟一听这话有理,就坐在京里一心盼望他来,每日往各处打听,看森堂来了没有,转瞬过了十多日,仍没有大力士来京的消息,很觉得诧异。一日遇了一个从天津来京的朋友,遂向他探问,据他谈起来,却把我笑坏了,他说半月前果有一个体魄极魁伟的、红面孔外国人,带了一个中国人做翻译,还同着几个外国人,身体也都强壮,到天津来在外国旅馆里住着,登时天津的人,都传说德国大力士森堂来了,不久就有外国武艺可看。谁知过了几日,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们初来的一两日内,街上随时都看见他们游行观览,三日以后,连街上都不见他们行走了。又过了两日,才知道什么大力士已在登岸的第四日,被一个卖艺的童子打跑了。原来那日,森堂独自带了那个翻译,到街上闲游,走到一处,遇到一老一少两个人在空处卖艺,围了不少的闲人看热闹。森堂不曾见过的,自然要停步看看,他看了打拳使棍,似乎不明白是做什么,向那翻泽,翻译是中国人,当然说得好听些。他听说这就是中国的武艺,不由得面上现出鄙薄的神气,复问在街上显武艺做什么,翻译说也是卖艺,不过不象外国卖艺的有座位,有定价,这类卖艺,看赀是可以随意给的,便不给一文也使得。森堂听了,即从口袋里取出皮夹来,抽了一张五元的钞票,交给翻译。那翻译口里对森堂虽说得中国武艺很好,心里却也不把那卖艺的当人,用两个指头拈了那张钞票,扬给卖艺的童子看道:“这里五块钱,是世界最有名的第一个大力士森堂大人赏给你的,你来领去,快向森堂大人谢赏。’那童子虽只有十四、五岁,志气倒不小,森堂面上现出鄙薄的神气,他已看在眼里了,已是老大的不愿意,但不敢说什么。及见翻译这么说,才知道是世界第一个大力士,也就做出鄙薄的样子说道:”我拿武艺卖钱,谁要他外国人赏钱,我不要!‘翻译见他这么说,倒吃了一惊,不好怎生说话。森堂听不明中国话,看童子的神情不对,忙问翻译什么事?翻译只得实说,森堂禁不住哈哈大笑,对翻译说了几句,翻译即向童子说道:“你拿去吧!森堂大人说,是可怜你穷苦。你这种行为,不算是卖艺,只能算是变相的乞丐,你这是什么武艺,如何能卖钱?’这几句话,把那童子气得指手划脚的说道:”他既说我使的不是武艺,好在他是世界第一个大力士,叫他下来与我较量较量,我若打胜了他,休说这五块钱,便是五十块、五百块我都受。我打不过他,从此也不在江湖上卖艺了。‘翻译道:“你这小子不要发糊涂,森堂大人打尽全世界没有对手,你乳臭未除,有什么了不得的本领,你敢同他较量?打死了你,是你自己讨死,和踏死一个蚂蚁相似,算不了什么!须知你是我们中国人,失了中国人的体面,这干系就担的太大了。’那童子道:”我又不是中国有名的第一个大力士,就被他打死了,失了中国什么体面?‘翻译没法,照着要比较的话对森堂说了,森堂倒看着那童子发怔,猜不透他凭这瘦不盈把的身材,加以极幼稚的年龄,为什么居然敢要求和世界第一个大力士较量?森堂心里虽不明白是何道理,然仍旧异常轻视,看热闹的人,横竖不关痛痒,都从旁怂恿较量。森堂遂脱了外褂,走进围场,问童子将怎生较量?那童子随意将手脚舞动了几下,森堂也就立了个架势,那童子身手很快,只将头一低,已溜进了森堂的胯下。森堂没见过这种打法,措手不及,被摔了一个跟斗,还不曾爬起来,那童子已溜到翻译跟前,将五元钱钞票取到手中了,回身扬给那些看热闹的看道:“这才是武艺卖来的钱。’看热闹的都拍手大笑。森堂爬起来,羞得面红耳赤,一言不发的带着翻译走了。从这日起,天津街上便不见森堂等人的踪影,大约已上船走了。我听得那朋友这般说,虽欢喜那童子能替中国人争体面,然想见识外国武艺的心愿,仍不能遂。过不到几年,又听得人说,又有一个什么俄国大力士,也自称世界第一,到了天津卖艺。这回我是决心要到天津来看的,不凑巧舍间有事,一时不能抽身,因听说那大力士在天津卖艺,至少也得停留十天半月,不至即刻离津,我打算尽一、二日之力摒挡家事,即动身到这里来,谁知道还没动身,就听说这大力士又被霍四爷撵走了。所以今番听李存义提起霍四爷在上海定约的话,就忍不住来拜访,请问两位定了何时动身去上海?我决计同去见识一番。”
霍元甲笑道:“外国武艺,在没见过的,必以为外国这么强盛,种种学问都比中国的好,武艺自然比中国的高强。其实不然,外国的武艺可以说是笨拙异常,完全练气力的居多,越练越笨,结果力量是可以练得不小,但是得着一身死力,动手的方法都很平常。不过外国的大力士与拳斗家,却有一件长处,是中国拳术家所不及的。中国练拳,棒的人,多有做一生世的工夫,一次也不曾认真和人较量过的,尽有极巧妙的方法,只因不曾认真和人较量过,没有实在的经验,一旦认真动起手来,每容易将极好进攻的机会错过了。机会一错过,在本劲充足、工夫做得稳固的人,尚还可以支持,然望胜已是很难了。若是本劲不充足,没用过十二分苦功的,多不免手慌脚乱,败退下来。至于外国大力士和拳斗家,就绝对没有这种毛病。这人的声名越大,经过比赛的次数越多,工夫十九是由实验得来的,第一得受用之处,就是无论与何人较量,当未动手以前,他能行所无事,不慌不乱,动起手来,心能坚定,眼神便不散乱。如果有中国拳术的方法,给外国人那般苦练出来,我敢断定中国的拳术家,决不是他们的对手。你既有心想到上海玩玩,这是再好没有的事。与我订约比赛的奥比音,我至今不曾会过面,也不知道他的武艺,与我所见过的大力士比较怎样。我这回订约,也是极冒昧的举动,在旁人是断不肯如此鲁莽从事的,人还没有见面,武艺更摸不着他的深浅,就敢凭律师订比赛之约,并敢赌赛五千两银子的输赢,我究有何等出奇的本领,能这般藐视外国人,万一比赛失败了怎么办?输五千两银子,是我姓霍的私家事,算不了什么,然因此坏了中国拳棒的威名,使外国人从此越发瞧不起中国人,我岂不成了中国拳术界的罪人吗?在我们自家人知道,中国的拳术,从来极复杂,没有系统,谁也不能代表全国的拳术。只是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社会的情形,与外国完全不同,他们以为我薄有微名,是这么争着出头与外国人订约,必是中国拳术界的代表,这样一来,关系就更重大了。我当时因痛恨外国人无时无地的不藐视中国人,言语神气之间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论机器、枪炮,我们中国本来赶不上外国,不能与他争强斗胜,至于讲到武艺两个字,我国古圣先贤刨出多少方法,给后人练习,在百十年前枪炮不曾发明的时候,中国其所以能雄视万国,外国不能不奉中国为天朝的,就赖这些武艺的方法,比外国的巧妙。我自信也用了半生苦功,何至不能替中国人争回这一口气!因此不暇顾虑利害,冒昧去上海找奥比音较量。不凑巧,我到上海时,奥比音已经走了,然我一腔争胜之气,仍然不能遏抑,所以有订约比赛之事。约既订妥,我却发生自悔孟浪之心了,但是事已至此,悔又何益!就拚着一死,也得如期而去,见个高下。最好象老哥这种高手,能邀几位同去,一则好壮壮我的声威胆量,二则如果奥比音的本领真了得,我不是他的对手,有几位同去的高手,也好接着和他较量,以求不倒中国拳术的威望。”
吴鉴泉笑道:“四爷这番话说的太客气了。四爷为人素来谨慎,若非自信有十二分的把握,又不是初练武艺,不知此中艰苦的人,何至冒昧去找人赌赛?这件事也不仅四爷本人能自信有把握,便是同道中的老辈,也无不相信四爷有这种担当,有这种气魄。换一个旁人,尽管本领够得上,没有四爷这般雄心豪气也是枉然。四爷越是自悔孟浪,越可以见得四爷为人谨慎,不敢拿这关系重大的事当儿戏。四爷打算在何时动身,我决定相随同去,并且我久闻上海虽是商务繁华之地,然也有几位内家工夫做得不错的人,早已存心要去拜访拜访,这回才可以如我的心愿。”
霍元甲因将在上海会见秦鹤岐等人的话,说了一会道:“此去上海的轮船便利,原可以临期前去,不过我惟恐临时发生出什么意外的事来,使我不能动身,那就为患不小,不但照条约逾期不到的,得罚五百两银子,赔偿人家的损失,无论中外的人,必骂我畏难退缩,这面子失的太大了。我曾和农爷商量,如今正二月里,正是我药栈里清闲的时候,我就住在栈里也没有什么买卖可做,三月以后,才是紧张的月份,不如早些去上海,可以从容联络下江的好手,倘能借此结识几个有真实本领的人物,我们开诚布公的结合起来,将来未必不可以做一番事业。农爷是在外洋留过学的人,他常说,外国的枪炮果然厉害,但是使用那厉害枪炮的,也得气力大,体魄强的人方行。象我国现在一般普通的人,都奄奄没有生气,体魄也多半弱到连风都刮得动,便有再厉害的枪炮,这种衰弱的人民能使用么?我很佩服农爷这话不错,所以有心在这上面用一番心力,做出一番事业来。”
吴鉴泉连连称赞道:“非农爷没有这般见地,非四爷不能有这般志愿,我国练武艺的人,因为有一些读书人瞧不起,多半练到半途而废。近年来把文武科场都废了,更使练武艺的人,都存一个练好了无可用处的心,越发用功的少了。象农爷这样说起来,若有人果能用武艺使全国人的体魄练强了,谁还敢瞧不起练武艺的人呢?我虽是一个没能耐的人,但也曾得着家传的艺业,很愿意跟在两位后头,略尽我一些力量。”
霍、农、吴三人谈论得十分投机,当即议定了在正月二十五日一同动身去上海。霍元甲并托吴鉴泉多邀好手,同到上海凑热闹。吴鉴泉当面虽已答应了,只是出了淮庆会馆之后,心想我知道的好手虽然不少,但是各人都有各人的职业,这种看中国与外国人比武的事,凡是欢喜练武艺的人,无不想去看看,不过路途太远,来回至少得耽搁半月或二十天,还要掏腰包破费几十块钱的盘缠,不是有钱有闲工夫的人,谁能去得呢?独自思量了一会,不禁喜道:“有了!李禄宾、孙福全这两个人,我去邀他,必然很高兴的同去。”
吴鉴泉何以知道这两人必高兴同去呢?原来这两个人在当时的年纪,都还在三十岁左右。两人的家业,又都很宽舒,平日除了练武艺而外,双肩上没有担着芝麻大小的责任。两人都是直隶籍,同时从郭云深、董海川练形意,又同时从李洛能练八卦,两人都是把武艺看得和性命一般重。不过李禄宾为人粗率,不识字,气力却比孙福全大,孙福全能略通文字,为人精细,气力不及李禄宾,但工夫灵巧在李禄宾之上。两人因为家境好,用不着他们出外谋衣食,能专心练艺,只要听得说某处有一个武艺好、声名大的人,他两人必想方设计的前去会会。如果那人武艺在他两人之上,孙福全精细,必能看得出来,决不冒昧与人动手,若是纯盗虚声的,遇了他两人,就难免不当场出丑。
那时吉林有一个道人,绰号叫做“盖三省”。据一般人传说,盖三省原是绿林出身,因犯的案件太多,又与同伙的闹了意见,就到吉林拜了一个老道人为师,出家修道。其实修道只是挂名,起居饮食全与平常人无异。老道人一死,他就做了住持,久而久之,故态复作,仗着一身兼人的气力,更会些武艺,与人三言两语不合,便动手打将起来。吉林本地方有气力、会武艺的人,屡次和他较量,都被他打败了,就有些无赖的痞棍,奉他做首领,求他传授武艺。文章、武艺都是一样,在平常人会的不算希奇,少人注意,惟有僧道、妓女这几种人,只要略通些文墨,人家便得特别的看待,说是诗僧、诗妓、文人学士、达官贵人无不欢喜亲近,欢喜揄扬,武艺一到这几种人手里也是一样,推崇鼓吹的人分外多些。盖三省既得了当地一般痞棍的拥戴,又有若干人为之鼓吹,声名就一日一日的大了。奉天、黑龙江两省也有练武艺、想得声名的人,特地到吉林来访他,与他较量,无如来的都不是实在的好手,竟没有打得过他的,盖三省的绰号就此叫出来了,他也居之不疑。他的真姓名,本来早已隐藏了,在吉林用的原是假姓名,至此连姓名也不用了,居然向人自称是盖三省。
孙福全,李禄宾闻了盖三省的名,两人都觉得不亲去会一面,看个水落石出,似乎有些放心不下的样子。两人就带了盘缠,一同启程到吉林来,落了旅店,休息了一夜,次日到盖三省庙里去拜访。在路上孙福全对李禄宾道:“我们和盖三省见过面之后,彼此谈论起工夫来,你看我的神气,我若主张你和他动手,你尽管和他动手,决不至被他打败,如果我神气言语之间,不主张和他打,便打不得。”李禄宾时常和孙福全一同出外访友,这类事情已经过多次了,很相信孙福全看的必不错。此时走进了盖三省的庙门,只见门内有一片很宽大的草场,可以看得出青草都被人踏死了,仅剩了一层草根,惟四周墙根及阶基之下,人迹所不到之处,尚长着很茂盛的青草,练气力的石锁、石担,大大小小、横七竖八的不知有多少件放在场上,使人一望就知道这庙里有不少的人练武。不过在这时候,尚没有一个人在场上练习,这却看不出或是已经练过了,或是为时尚早,还不曾来练。两人边走边留神看那些石锁、石担的重量,也有极大的。李禄宾自问没这力量能举起来,即悄悄的对孙福全说道:“你瞧这顶大的石锁、石担,不是摆在这里装幌子吓人的么?不见得有人举得起。”孙福全摇头笑道:“装幌子吓人的倒不是,你看这握手的所在,不是都捏得很光滑吗?并且看这地下的草根,也可以看出不是长远不曾移动的,就是举得起这东西,也算不了什么,何能吓的倒有真本领的人!”两人走到里面,向一个庙祝说了拜访盖三省的来意,原来盖三省因为近来声名越发大了,拜访的人终年络绎不绝,他也提防有高手前来与他为敌,特地带了几个极凶猛横暴的徒弟在跟前,以备不测。逆料来拜访的,同时多不过二、三人,决没有邀集若干人同来与他为难的,以他的理想,两三人纵有本领,也敌不过他们多人的混斗,因此凡是平日有些名头的把式去访他,他必带着几个杀气腾腾的徒弟在身边。他自己却宽袍缓带,俨然一个有身份的人物。
李、孙两人在当时声名不大,天津、北京的人知道他两人尚多,东三省人知道的绝少。加以两人的身体,都是平常人模样,并没有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气,盖三省没把他两人放在眼里,大着胆独自出来相会。孙福全看盖三省虽是道家装束,然浓眉大目,面如煮熟了的蟹壳,颔下更长着一部刺猬也似的络腮胡须,越发显得凶神恶煞的样子。孙福全看他的模样虽是凶恶,但是走近身见礼,觉得没有逼人的威风。彼此通姓名、寒喧几句之后,渐渐的谈到武艺,盖三省那种自负的神气,旋说旋表演自己的功架,目中不但没有李、孙二人,简直不承认世间有工夫在他之上的人物。李禄宾看不出深浅,不住拿眼望孙福全,孙福全只是冷笑,等到盖三省自己夸张完了,才从容笑问道:“你也到过北京么?”盖三省哈哈笑道:“北京如何没有到过?贫道并在北京前后教了五班徒弟,此刻都在北京享有声名。”孙福全故作惊讶的样子说道:“在北京有声名的是哪几个?”盖三省不料孙福全居然追问,面上不由得露出些不快的样子,勉强说了几个姓名。孙福全冷笑了一声道:“北京不象吉林,要在北京享声名,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问你在北京的时候,见过董海川、郭云深及杨班侯兄弟么?”盖三省随口答道:“都见过的。”孙福全道:“也谈论过工夫、较量过手脚么?”盖三省扬着胳膊说道:“当今的好手,不问谁,十九多在贫道手里跌过跟斗的。贫道打倒的人多,姓名却记不清楚了。”孙福全即大声说道:“我两人就是董海川、郭云深的徒弟,因听说你打倒的好手很多,特地从北京来领教你几手,想你打倒的好手既多,必不在乎我们两个,请你顺便打倒一下如何?”
盖三省想不到这样两个言不惊人、貌不动众的人物,大话竟吓他们不倒,一时口里说不出不能打的话来,正在踌躇如何回复,孙福全已向李禄宾使眼色。李禄宾知道是示意教他放心动手,即立起身来,将上身的衣服脱下,紧了紧纽带,对盖三省问道:“在什么地方领教呢?”盖三省被这样一逼,只得自己鼓励自己的勇气,也起身将道袍卸下说道:“我看两位用不着动手,大家谈谈好了,若认真动起手来,对不起两位。人有交情可讲,拳脚确没有交情可讲,两位多远的道路到这里来,万一贫道工夫不到家,失手碰坏了两位的贵体,贫道怎么对得起人呢?”孙福全笑道:“我两人都是顽皮粗肉,从来不怕碰,不怕撞,其所以多远的道路跑来,就是为要请你多碰撞几下。你我初次见面,没有交情可讲,请你不必讲交情。若因讲交情不肯下手,倒被我们碰坏了贵体,那时人家一定要责备我们,说我们不懂得交情。”盖三省一听孙福全这话,知道这两人不大好惹,想把几个徒弟叫到跟前来,一则好壮壮声威,二则到了危急的时候也好上前混斗一场,免得直挺挺的被人打败了难看。只是当初出来相会的时候,不曾把徒弟带在身边,此时将要动手了,却到里面叫徒弟,面子上也觉得有些难为情。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喜得他的几个徒弟,虽不曾跟在他身边出来会客,但是都关心自己师傅,一个个躲在隔壁偷瞧偷听,此时知道要动手了,都在隔壁咳嗽的咳嗽,说话的说话,以表示相离不远。盖三省听了,胆气登时壮了许多,对孙、李二人说道:“两位既是定要玩玩,贫道也不便过于推辞。这里面地方太小,施展不来,请到外面草场中去吧!”
孙福全偷着向李禄宾努嘴,教他将脱下的衣服带出去。三人同步走到草场,只见草场周围,就和下围棋布定子的一样,已立了七、八个凶神恶煞一般的汉子在那里,都是短衣窄袖的武士装束。孙福全一看这情形,就猜出了盖三省的用意,是准备打败了的时候,大家一拥而上,以多为胜的,细看那些壮汉眉眼之问,没有丝毫聪悟之气,都是些蠢笨不堪的东西。暗想这种蠢材,断练不出惊人的技艺,专恃几斤蛮力的人,纵然凶猛,纵然再多几个,又有什么用处?李禄宾看了那七、八个壮汉的神情,心里便有些害怕起来,走过孙福全跟前,低声说道:“草场上站的那些人,如果帮助盖三省一齐打起来怎么办呢?”孙福全笑道:“不打紧!他们一齐来,我们也一齐对付便了,怕什么呢?我有把握,你只放胆与盖三省动手,他们不齐拥上来便罢,如果齐拥上来,自有我对付,你用不着顾虑。”
李禄宾平日极相信孙福全为人,主意很多,照他的主意行事,少有失败的,见他说不怕,说有把握,胆气也登时壮了。跳进草场,对盖三省抱拳说道:“我因拳脚生疏,特来领教,望手下留情。”说着立了个架式,盖三省也抱了抱拳,正要动手了,孙福全忽跳进两人中间,扬手说道:“且慢,且慢!”不知孙福全说出些什么话来,两人比较的胜负怎样,且俟第五十六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