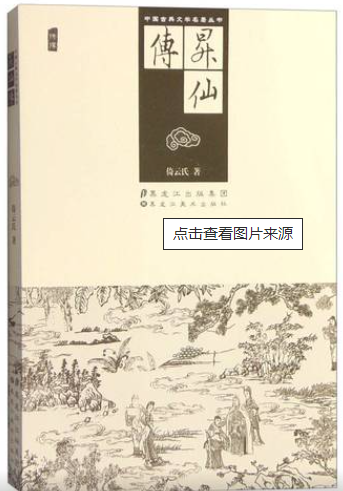话说小塘言道:“天杀的,坑死我了,将我的银子,尽情偷去,这可叫我怎样回家!”说着说着放声大哭。主人说:“相公莫要如此,你只保养身体要紧,银钱皆是人挣之物,恼他怎的。到明日我与你请个医者看看脉,吃两剂药就好了,你家在何处?我自送你回去。”小塘听了这话,把气平了一平,故意的要东要西,百般的试探,这主人百依百随,并无怨言。
一连三天,皆是如此。到了第四日上,小塘起来,向主人言道:“多承照管学生病体痊愈。不知贵姓尊名,为何放着空机,却不织绢?”房主见问,叹气言道:“在下姓邓名叫存仁,只为平生好友,把资本叫人坑去,因此连年未做生意。”小塘顺口答言,说:“学生也是姓邓,怪不的这样有缘,既然缺少资本,这却不难,我有个贩丝的朋友,现在此处发货,待我找着他,赊他两担,包管会依。”言罢出门,向西走了几步,见路北有一座七圣祠,走进去看了一看,原来是座空庙,走到正殿,口诵灵文,把搬运神拘来,朝上打躬。小塘说:“烦驾到北京城中,捡那富户丝线铺子,把织绢的上好青丝运两担来。可要记清他的字号住处,日后好还他的本银。”搬运神领命,去不多时背了四捆青丝回来,放在小塘面前,说:“启上法官,这丝是鼓楼东路北,陈明字号的货物,请法官查收。”
小塘说:“有劳尊神,请归本位。”打发搬运神走了。出来找了两个闲汉,把丝担到邓存仁家。存仁一见,满心欢喜,说:“相公真赊来了!不知什么价值?几时要钱?”小塘说:“按时价计算,对月交还罢了。你可快去料理机房,不要迟了时日。”
邓存仁不敢怠慢,把机房打扫干净,找来旧日的机匠,立时之间热闹起来。到了晚上,机房停工,各自散去,小塘等至夜静,把织女星请来助工。织女星领了法旨,一夜的工夫,八疋绢俱已织完,交旨升天而去。次日早晨众机匠一进机房,看了看绢,皆已完备,一齐乱嚷,俱说是活见鬼了。邓存仁从院内出来,闻知此事,心中甚是惊疑,走到机前,依次一看,八疋绢果然皆完,经纬又齐,颜色又俊,单丝尽成双丝。小塘假装不知,也走过去看了一看,说:“众位不必惊疑,想是主人时来运转,神人相助,列位以后就照此样织来,包管买卖兴旺。”众人听说,一齐动手,将八正绢卸下机来,邓存仁治办香烛,供献答谢神灵,机匠从新安机,拿这八疋作样,织出来大不相同,这话暂且不表。
且说小塘推故有事,独自出门,走不上半里多远,迎着徼、苗二人,说:“二位贤弟,如今且别回去,到晚上可要如此这般。”吩咐已完,回至邓家。天色将晚,徼、苗二人在外而叫门,邓存仁将门开放,一见就问,说:“二位道爷,这二日那里去来,把你们伙计气的了不得了。”二人故意惊道:“此话怎讲,倒要问个明白。”说着走进房中。小塘一见,说:“哎哟!好两个大胆的狠贼,将我二百银子偷去,还敢回来见我,有何理说?”一枝梅说:“我的哥,你可错怪了人了,俺两临出去时,恐怕露白,将银子放在炕洞里边,没有言语。这也怪不得哥生气。”邓存仁听说,秉上灯烛望炕洞中一看。一个布包放在里面,拿出来打开,果然是二百银子,存仁交与小塘,说:“相公几乎屈了好人,快收起来罢。”大家说笑一回,各自安歇,邓存仁那知是小塘弄的法术,完他前日假病的案件。
且说到了次日,就有南京客夹买绢,邓存仁就将那现成八疋拿来,客人一见心中爱慕,比别的机房里的货物多卖一半银子,一定五十疋,先留定银一百两。邓存仁打发客人去了,将银子交与小塘,叫小塘还那两担丝的客账,小塘接来,仍烦搬运神送去。这且不提。
且说邓存仁家的买卖,从此兴旺,就把小塘弟兄三人留在家中待如上宾。那日,小塘思念韩生,正遇大比之年,写了一封书信,把乌鸦拘来一个,将书给它拴在尾巴之上,叫它把书送至江南,这乌鸦如通人性的一般,展翅飞翔,一直飞到江南隐仙庄韩庆云家楼角以上,不住的乱叫。韩生正在楼上看书,被乌鸦叫的心乱,用袍袖一甩,那乌鸦把双翅一展,飞在书案上边,把尾巴一撅,朝着韩生又叫。韩生才要伸手去拿,见那尾巴之上拴着一封书信,连忙解将下来,拆开一看,原来是小塘给自己的书信。上边写着:
劣兄小塘亲笔踪,拜上江南一友朋。
自从那日分別后,时常悬念在心中。
只因目今开大比,奉请贤弟奔前程。
早到南京先纳监,随后收拾上北京。
千万莫过九月九,包管金榜中头名。
韩生看罢,满心欢喜,心想:济兄真神仙也!这些飞鸟也听他使唤,我想科举的规矩乃是八月中秋,他这书中说是别过九月九日,难道今年改了日子不成?一行想着,下楼走到景氏奶奶跟前,说:“母亲,方才有一件奇怪事情。”奶奶说:“什么事呢?”韩生就把乌鸦带信的话说了,将书呈与奶奶,奶奶看了一遍,说:“我的儿,你的主意怎么样呢?”韩生说:“儿的主意是要上京,但恐日子有限误了日期。”奶奶说:“依我看来,你济兄有半仙之体,定有先见之明,既许你金榜有分,管什么八月、九月,你去了自有好处。”韩生说:“虽然如此,但不忍与母亲远离,如何是好?”奶奶说:“这也不难,我有积下的二百银子,可作盘费,把房产地土交与管家韩禄看守,咱母子带着书童,一同进京,岂不两全。”韩生大喜,说:“母亲见的极是。你老人家收拾行李,为儿的先去定船。”说罢走到河口,雇了一只江船回家,吩咐韩禄看守房产,将行李叫人送上船去,然后,韩生扶他母亲一同上船。
船家开船,正遇顺风,不多几日,已到南京水西门。景奶奶把银子交与韩生,韩生上岸进城,到在户部里报名,兑清银子,要了北京科举的文书,收在身边,出城上船,渡过江北,离船上岸,雇了一辆小车,书童将行李搬上,扶侍奶奶上去,韩生也坐在一边,两个车夫前拉后推,走将起来。此乃八月天气,秋雨连绵,在路上走了一月,倒误了半月的工夫,及至到了北直交界,已是八月二十以外。韩生看了看场期已过,且是路上泥泞难走,正要与他母亲商议回家,忽见路旁有人说话,韩生定睛一看,认的是徼、苗二人,连忙下车,紧行几步深深一躬,说:“二位兄长从何而来?”承光说:“俺奉大哥之命特来迎接贤弟。”韩生听说,连忙称谢,说:“二位兄长,老母现在车上,请去相见。”二人听说,上前请安。奶奶一见吓的面目改色,说:“二位到此有何事情?”苗庆说:“俺奉济大哥之命,迎接老母、贤弟进京。”奶奶听说,把韩生叫到跟前,附耳言道:“从前二人在咱家中,一个神偷,一个讹诈,几乎没把老母吓死。今日此来必无好意,须要远着他些。”韩生领命,走到二人跟前说:“二位兄长,小弟承济兄美意,叫小弟上京,谁知路遇阴雨,误了场期。如今进京,也是无益。方才母亲吩咐不如回家,还省几两银子,敢求二位兄长回去见了济兄,代小弟说罢。”承光说:“贤弟有所不知,今年场期已经改在九月,莫要迟疑,误了功名大事。”
韩生立意回家,要远二人,遂向二人言道:“老母已经吩咐,不敢不从,就此告别了罢。”承光向苗庆言道:“贤弟,你听见了么,半路之中忽要回去,咱大哥算的真是不错。如今把那话给他使上罢了。”说罢,向韩生言道:“既然如此,俺也不好相强,待俺别过老母,咱再分路。”言罢,齐走到小车跟前,这一个老母长、老母短,装说闲话。那一个把张神符贴在小车底下,说:“贤弟回家,一路保重。就此请了。”言罢向北而去。
韩生打发二人去后,叫车夫掉转车子,仍旧回家,给他来回的脚费。车夫听说要转车子,直觉着重如泰山,左右转不过来。韩生与书童一齐助力,扭了半日,竟不相干。韩生心下着忙说:“莫非他二入使了什么法儿了么?”一句话还没说完,只见一个小厮带着车夫往北直走。韩生一见,心下着忙,领着书童往前就赶,谁知越赶越快,正然跑的汗流,忽见徼、苗二人在路旁站着。韩生说:“二位兄长快忙替我赶赶车子。”二人言道:“你若上京,俺就替你赶赶;你若回家,我们不管闲事。”韩生恐怕吓着母亲,说:“只要赶上车子,弟就情愿上京。”苗庆听说,用手一指,那车子猛然站住,韩生这才跑到车子跟前说:“母亲没吓着么?”奶奶说:“却也无妨。”
说着,徼、苗二人来到跟前说:“老母不要害怕,此皆济兄长命俺如此,必请老母同贤弟上京,功名自然有分。”奶奶见是不能回去,无奈点头应允。苗庆走去,雇来四个脚驴,弟兄三人连书童骑上,车夫推起小车,竟上北京。到了八月底,那日到了北京城外,从东直门绕到六里屯邓存仁门口,小塘将韩生迎接进去,邓存仁家服侍奶奶下了车子,让进院中,小塘给韩生开发了车子、脚驴。邓存仁也给韩生叔礼,摆酒接风,韩生母子就在邓存仁家住下,这且不提。
且说这一年,嘉靖爷正宫娘娘殡天,正是八月中间,所以把考期改到九月。韩生听见这个信息,心中大喜,连忙到顺天府投文,买了卷子,等九月初八进场,到了这日,书童拿着考场用具,济、徼、苗弟兄三人同送韩生下场,走至庄外,韩生向小塘言道:“仁兄,小弟夜得一梦,不知吉凶?”要知后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