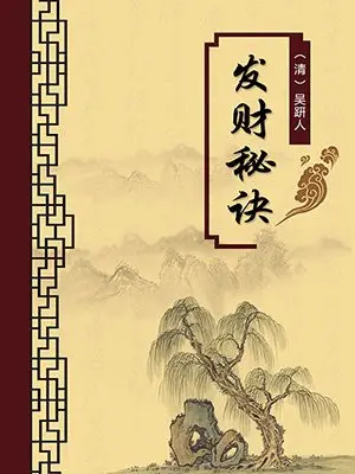话说湘林听得衣云说起,到舅舅家教读去,心房里无端起了一阵酸潮,不知不觉,把手里一支翡翠簪子,猛向石桌上敲一下。衣云惊道:“不好了!”湘林一瞧,已碎作两段。当下并不吃惊,冷冷道:“一支簪子值得甚么!人心敲碎,也只索敲碎。”说着,口音微带酸涩。衣云道:“湘妹,你很达观的,为何也这样愤恨。我中秋即回,一月小别,算不得久。”湘林道:“我何尝愤恨,预备欢送你哩。你福慧双修,此去……”衣云插嘴道:“湘妹你敲碎了簪子,又要来敲碎我的心么?我原打算把这颗心,寄给你妹妹处呀。”湘林道:“谁好接受你的心,我也不是接受的人,你留着待该给的给罢。”衣云那时愤愤道:“妹妹,我自问此心已属于你,前一番话,算得掬心相示,你信得过我,请你原宥苦衷,一身飘泊,原非得已,我当你面这样,背了你也是这样,倘有口是心非,二三其德,此身和你的那支簪子一样……”湘林道:“云哥,你别说愤话罢。”衣云泪如绠下,湘林也觉凄咽。停一会,湘林把断簪杯内花汁,觉得尽成可怜之红,一阵酸心,滴下几点泪珠在杯内。衣云道:“湘妹,你今晚欢送我,该快快活活的,不宜这样悲哽。”湘林给他提醒,拭干泪痕,把帕子授给衣云道:“都是你引我哭的,现在大家拭干了,你再哭罚你。”衣云接过帕子拭泪道:“罚甚么?”湘林想了想道:“罚你染红指甲,将来惧内。”衣云笑道:“染红指甲韵事,惧内更属韵事,我愿罚愿罚,你快替我染。”说着,伸只手,搁在湘林面前。湘林笑道:“你明天做先生去,给学生见了,要叫你‘红爪先生’的。更有一层,给你那个表妹见了,也要疑心你,取笑你的。”衣云道:“表妹问我,我说另一表妹替我染的。”湘林道:“你喜染,我当真替你染。”说着剥下自己指上一片瓜子壳,重调杯中花汁,把断簪挑一些在壳内,剔成个形,合在衣云左手大指甲上,也把豆壳套好,衣云问隔几日好取去?湘林道:“一夕便红。”衣云道:“妹妹,你留这纪念,使我摩挲一点猩红,联想到猩红里面,有你妹妹送别的泪痕,心旌格外沉痛。”湘林羞着道:“只怕猩红一褪,你便想不起我了。”衣云没有回答,秋菊走来,湘林吩咐道:“今晚留云少爷吃饭,多煮几色菜。”秋菊点头自去。衣云道:“今夕别后,你只要望一颗月亮,圆过一度,第二度圆时,我又好到这里来了。”湘林只觉默然,泪莹莹。衣云轻轻拍一下桌子道:“湘妹,你也再不许哭了,再哭,我要罚你。”湘林道:“谁哭,受你罚,我可不怕你的。”衣云笑道:“你年年染红指甲的,难道不惧
外么?”湘林向衣云瞪了一眼,衣云又道:“那么你不怕我,便是我怕你,算你今天替我染指甲的效验。你替我染一个指甲,我已怕你,明年你替我把十个指甲统统染了,我好演《梳妆跪池》去哩。”湘林嗔道:“你总喜占便宜,甚么《梳妆跪池》呢!”衣云道:“你要明白,只消瞧《缀白裘》便是陈季常的故事。”湘林道:“《缀白裘》不是昆剧曲本么?我瞧不懂的。”衣云道:“你瞧不懂,只有将来我扮演你看。”湘林道:“你又是占我便宜么?”衣云道:“这是我把便宜奉送你占的,你想我向你跪,这便宜谁占的?”湘林道:“我不想占你便宜。”衣云道:“那么你对我跪,便宜算我占。”湘林道:“别多谈罢,你明天几时开船,可要我来送你。”衣云道:“拂晓便行,你要送我,请你一径送到我灵岩山下。”湘林道:“真的,我中秋来游天平、石湖、虎邱,任便到你那边望你,怕你要不相识我了。”衣云道:“一定倒屐出迎,怕请不到你,灵岩山的艳迹不少,你来点缀其间,那更是锦上添花。”湘林道:“锦上本来有花,不容我来点缀得,我来翻为不妙,冷淡你们俩的爱情,简实不是锦上添花,变以做雪中送炭了。”衣云道:“你的话算了罢,越说越不像了。”
湘林再要说时,秋菊来唤吃饭。两人走到厅上,湘林便把衣云要出门的话,告知祖母母亲,大家心里不忍衣云离开澄泾,席上很不快活。吃罢夜饭,两人又谈了一阵,衣云别过老太太等,走出门去。湘林依恋不舍,握一柄薄葵扇,送出门来。见塘岸乘凉的人坐着不少,湖上也是扁舟点点,人影惮惮,衣云、湘林又站定在柳阴下闲谈。衣云道:“往日我见了一湖秋水,非常快乐,今晚只觉得心惊胆怕,你道甚么缘故?因为一到明日,那湖水决不肯留住我一艘船。须臾片刻,非直送到我瞧不见你处才休。”湘林听得,也不免对着湖光出神。那时一阵凉风,忽把一片清澈的歌声,吹送到两人耳内。这歌曲是农人唱的一种男女相悦的俚辞,其间也不少天籁。两人听道:结识私情东海东,路程远信难通。等到路通花要谢,路通花谢一场空。湘林和衣云听得,触动悲怀,心中只是别的跳荡。又听道:
结识私情路迢迢,星稀月暗那能跑。露水里去了浓霜里返,伤风咳嗽自家熬。
衣云道:“湘妹,这歌倒也有些意思,不算粗俗。”湘林羞着,只管听。又听道:
结识私情隔条泾,东西两岸那能行。青竹造桥给你娘踏断,快刀切藕断私情。
湘林道:“不要去听他罢。”衣云道:“却也不味。”再听道:结识私情隔层帘,隔帘亲嘴咬碎舌尖尖。雪白样汗衫染了一点鲜红血,亲娘问你哪回言?衣云拍掌道:“妙啊,想不到渔夫牧竖口中,也有阳春白雪的调。”湘林道:“他们大概也在那边送你,这便算得一曲骊歌。”衣云再听时,歌声已歇。湘林道:“有许多田歌粗俗不堪,这还算得雅俗共赏。”衣云道:“我从前听得一般踏车戽水的人,唱着不知甚么调,合罕……合罕…我问他,他却有典可数,回答我道:这支歌,从前种田祖师傅下,最老的歌,你们读书人难道不懂吗?当时诸葛亮在蜀中教人种田,怕种田汉寂寞,教他们唱歌,又怕种田汉夜里胆小,便造出这支合罕……合罕……的歌,也是壮种田汉的胆子。我们虽不懂这支歌甚么意思,只是世代相传下来,说这支歌能够吓退鬼祟的,究竟鬼祟听了吓不吓,因为我不是鬼祟,简直不能断定。当下我听他说得有理,倒也很佩服他。”湘林道:“可是你文皱皱的书生,给那赤脚汉盘驳倒了。”衣云道:“赤脚汉他们自有一部赤脚经的,往往秀才举人,驳翻在他们手里。他们村上聘了个先生,便要一窝蜂去掂先生的斤两。前年我们村上有个秀才先生刚开学,便给那东家盘翻。你道他问的甚么?他道:请问先生,天下国家有几斤重?先生把《四书》《五经》统统翻到,找不出来。那东家笑道:先生,难道大学也没有读过?大学上明明说‘天下国家有九经’,你怎会不知,足见你先生书生,省得误人子弟,请你回府罢。那先先生这一气,真气得日月不明,风云失色,只好回去抱小囝。后来那东家又聘到一位先生,和东家同行,一样赤脚种田的。东家问先生道:请问你先生统共识几个字?先生道:“不瞒东翁,我只识我东翁所识的几个字。东家又问:‘学而时习之’的而字怎么解?先生笑吟吟答道:这是我们种田人的吃饭家伙,一柄铁耒像不像?东家道:“不差不差。又问先生道:“像蓑衣一般的甚么字?先生道:“雄的斋字,雌的齐字。又问像狲一般的甚么字?先生道:“拖尾巴的及字,断尾巴的乃字。又问像牌位一般的甚么字?先生道:缩脚的且字,伸脚的具字。东翁佩服得一恭到地,叮嘱道:我家小儿,也不想中状元考举人,只要你老夫子把几个要紧字眼传给他,待他将来也会盘驳先生一番,便算你老夫子赤心忠良了……”衣云说得湘林笑着道:“云哥,你明天做先生去,倒要当心那个盘驳你的人,他却比不得种田汉,怕连你先生的生辰八字都要盘驳到咧,你肚子里可曾准备准备?”衣云道:“湘妹,我听你说的话,不知怎样,总觉得弦外有音,好像话里有骨子似的。我不再和你谈了,中秋会罢。”湘林黯然不语,半晌答道:“我早晏一去,你去罢,我待你吃月饼,你可放在心上。”衣云点点头,慢慢挨步回家,整理整理行装,一只书箱,一只衣箱,一个铺盖,三件法宝,一家一当,尽在于此。当晚一宿无话,明晨别过叔父,再去拜辞老师。老师不免教训一番,咬文嚼字道:“师严道尊,小子不可玩忽。更有一层,吃我们这碗板凳饭,最容易生病,不活长寿的。当时孟老夫子有句话,叫做‘人之患在好为人
师’,那个患字,便是患病的患,衣云你要当心啊。”衣云抽了一口冷气,心想大概怕我夺他饭碗,特地咒骂我,也为的同行嫉妒起见,当下无话可答,只好笑着道:“先生年纪大了,更要小心。学生此去回来,不知可能再见先生的面咧。”先生鼻子里哼了一声。衣云登舱开船,经过湘林水阁下,探首望望,一片湘帘内,隐隐约约有钗光鬓影。衣云心中迷迷糊糊,忍着十分疼痛,一路离澄泾向苏州木渎进发。从此澄泾湖上,少了一位风流蕴藉的少年。灵岩山下,平添着一片玉笑珠香的韵事,暂且按下不提。
作者另寻出一条线索叙叙南溟庄一位庄主赵肖虎。赵肖虎五十多岁,只有一位千金小姐,肖虎和他的夫人陆氏珍怜玉惜,从小聘个蒙师教读。十四岁便送到苏州城里一所自立女校住读,现在已交十八岁,将近毕业,肖虎挣下四五万家私,很热心地方公益,修桥补路,缘簿上总有他的大名。一百二百文,总肯化的。现在因为女儿毕期近,心下老大替女儿筹划一番事业。肖虎有个心格高傲的脾气,专喜结交乡绅官长,一心要把女儿抬到天上,恨不得运动全中国人,选举他女儿做女大总统,他自己好做个太上总统。在乡间呼么喝六,只是做不到,便退一步想,要叫女儿做个小学校长,只恨城中学校,聘不到他女儿。乡下学校又少,他便想自掏腰包,办个私立学校,好让女儿过一过校长瘾。主意打定,便和钱福爷商量妥贴,一面报县立案,一面筹备开学。借张太城隍庙暂充校舍,划出一只大殿作教室,两间厢房,一间作学生休息室,一间作教员卧室,定名赵氏私立国民小学,并吞三个半私塾,不到二三十学生,等到一切校具、图书、课本筹备妥贴,择定七月二十开学。他女儿乐得眉开眼笑,只因自己要到寒假才毕业,不得不聘下两个教员,一个私塾教师升任助教,一个专诚到城里聘下的主任。助教姓强号惕生,已六十多岁。主任姓黄号胄民,也是近六十岁了。开学那天,肖虎精神抖擞,发下二三十张请柬,一时观礼的济济一堂,校门上挂一块黑漆白字“赵氏私立国民小学校”的牌子,一面校旗,一面国旗,交叉着插在庙门前一个铁香炉内。走进校门,两傍八个黑面红须,伸拳怒目的泥皂隶,里面一个方方的天井,两棵大银杏树,绿荫成幄。正中大殿上一块金字横头写着“来了么”三字,那“来了”两个字上,粘着两方红纸,写的“教室”两字,远远望着变作“教室么”三字。教室内正中悬挂着一艘很大很大的阴船,船上有肃静回避的行牌执事,却也威灵显赫。其他匾额,横七竖八,挂着不少。一边新挂上一块黑版,下面一只半桌,三四十张洋松黑漆的学生坐椅,七高八低,分作四行排着。两间厢房,左面本来供着十殿阎王,现在改作学生休息室,排两条长凳在内。右面本来皂隶阴马的公事房,现在改作教员卧室,搁着两张铺在里面。后进仍让张太爷作公馆。当时庭心内排一张大菜台,是把两只方桌凑成的,台上铺一块白布,围着十来位老者,其中乡懂钱福爷,来宾汪四先生,李老师,主任黄胄民,助教强惕生,校主赵肖虎等一班人,以外另有几个学生家长,说说谈谈。等到学生到齐,一片铃声,助教强先生走到教室内,高唱道:“请乡董训词。众学生欢迎。”乡董大老爷行三鞠躬礼,肖虎推福爷站上讲台,强先生把学生一个个的拉了起来,教他们学着鞠躬。福爷也还了个礼,干咳了几声嗽,又咽了几口唾沫,约略说道:“此地赵老爷开办学校,本乡董始终赞成,你们学生,从此好不进私塾,不出钱读书了,大概也很开心,本乡董希望你们大家永远来塌这个不出钱读书的便宜货,还希望有第二第三个赵老爷肯出来做呆子,出钱请先生,给便宜货你们塌,那么本乡董有厚望焉。”这时台下一片掌声,钱福爷也就在这一片掌声里溜下讲台。其次赵肖虎答词,大致说费了一番心血,现在聘定主任黄先生,教员强先生,将来还有一位校长,便是我的女儿,醒狮女士,现在他还在苏州读书,遥领着这里的校长,你们学生总要像爷娘一般的尊敬长教员,校长好像你们的娘,教员好像你们的……”说到这里,肖虎望望强惕生面上红红的,自己便觉说不下去,只得接下几个“譬如!”“譬如!”又道:“你们视校长教员像爷娘,校长教员自然也当着子女一般的珍惜你们了。”那时旁边闪过一个赤脚妇人,拉了个学生便走,口中嚷着道:“谁要来塌你们这个便宜货,我给了十分面子你们,送儿子来读读书,索性当他子女,要叫你们爷娘了。爷娘一人只有一个,你们那个爷娘,自己把镜子照照面孔,生像没有。”说着,一路走出校去。此时赵肖虎早已下台,黄胄民、强惕生相继演说了一阵,摇铃散席。明日起便正式上课。谁想赵肖虎费尽心血,开办那所学校,讨女儿的好,不到一礼拜,那位醒狮女士回来参观了一次,把他父亲埋怨得险些哭将出来。他女儿道:“爹爹,你办的简实不是学校,是一所养老堂了。聘着这样两个棺材撑头的教员,暮气冲天,把儿童活泼的天机一起葬送尽了。其他教授上的荒唐,更说他不尽。翻翻作文簿子,有甚么‘试述你的妈’,‘试述你的姊’等题目。有一位学生,只做得两句文章,他写道‘我的妈早已死掉,现在只有述述我的校长妈妈’,你想可气不可气。那位主任先生,更是一件柴窑老古董,体育智识全无,居然在庭心里教学生体操,挺尸一般的身子,领着学生跑步,口中还喊着大转弯、小转弯、立春、小雪,我始终不懂他甚么话,笑得嘴歪,退了出来。爹爹,你办这样的学校,还是把银子丢在南溟河中,倒有几个水花瞧瞧,不致害人子弟。”肖虎听着,气得眼睛翻白,恨恨道:“我这所学校,本来为你办的呀,你是校长,你该去整顿整顿。”女儿道:“学校不比私塾。非聘请师范毕业生来办理不可。”肖虎道:“那里有甚么师范毕业生呢?”女儿道:“有是有一位,只是……”肖虎道:“谁呀?”女儿只不肯说,他母亲在旁插嘴道:“你对爷说了,好待爷去聘来。”女儿免不得低低道:“只是怕他师范还没毕业哩,说他则甚!”母亲道:“稀饭没逼热,那么等稀饭逼热吃了再说罢。”肖虎道:“谁要你胡缠,你替我滚开。”女儿不禁卟哧的笑了一声,停一会,醒狮对他的父亲道:“你要聘师范生,只消和钱福爷商量商量,他总有认识的,我们那所学校,非根本改良不可,否则化了钱,还担个误人子弟的罪名,那真要冤枉到十八层狱里去了。”肖虎只有听他女儿的吩咐,过得几天,女儿到学校里去了。肖虎约下福爷来家吃饭,席间要他引荐个师范生。福爷道:“师范生我们乡里实在不多,只有三四个,大家有事,未必肯来。有个镇上的尤璧如,他在蠡口做教员,前在碰见他在家里,谈起蠡口那所学校学生太少,很不满意,或者肯到此间来,我替你问问他再说,他的确是老牌师范生。其他镇上汪四先生的儿子汪绮云,去年的师范讲习所,今年暑假,听说也毕业了。和璧如一起在蠡口同校教授”。肖虎道:“汪四先生的儿子,更是家学渊源,一定不差的,倘两人肯同来更妙。否则,随便那人都好,薪水从丰,费心介绍。”福爷连声答应,回家问起玉吾,玉吾道:“爹爹,这件事巧极巧极。绮云、璧如现今通在家里闲着没事,蠡口那所学校,因学生少,给县里取缔了。”福爷道:“那么你去知照他们,待我肖虎处去一封信,解决下薪水问题,便好去上课。”当下玉吾去见了璧如,说起这事,璧如道:“那也很好。近一些,每星期可以常常回家逛逛”。说罢,一同去见绮云。绮云一听这个消息,快活得两脸通红,鼓掌称谢,简实比乞丐做了大总统还要快活。
看官一定疑惑我过甚其辞,不知一些也不说谎。汪绮云前一番事,做书的没交代过。汪四先生只生他一个儿子,从小替他定下澄泾一头亲事,便是沈衣云家李老师的女儿。谁知绮云一到十六七岁,瞧了几册甚么“饮冰子自由书”等,顿时的醉心自由起来,闹得汪四先生摇头跺脚。去年十一月里,绮云到城中参观联合运动会,无意中在会场内拾得一个线结的名片袋子,里面有五六张名片,一帧二寸小影,一只小线戒子。绮云瞧瞧名片上刊着赵万雄,下面一行小字道醒狮苏州南乡。反面又一行小字道:通讯处苏州胥门自立女校。又瞧瞧那小影一个女子,生得粗眉大眼,雄纠纠气昂昂,却也英挺有生气。绮云心下十分合意,自以为天假其缘,又想到自己最怕荏弱女子,甚么腰如柳枝,婷婷,我都不赞成,这样像一个雄壮威武的女子,正中下怀,便是将来偶然发几个寒热,也不吃惊,从楼窗上跌到阶沿下,也不能损他毫发。绮云越想越喜,不免一封连封的肉麻情书,寄给那位醒狮女士。醒狮女士今年十八岁了,只怨父亲肖虎,本钱太足,大约生我时,虎力太猛,因此害得我像四金刚一般,瞧着全校的同学,都有甚么黑漆板凳啦,甜心啦,我爱啦,闹不清,独有自己无人顾问,有一回,经同学姊妹介绍一位男学生,约在西园相见。醒狮振刷精神到西园大殿上踱来踱去,守守不来,便在三世佛前求签。每停五分钟求一条签,连求了十三条,统统下下,自知没望,正要想走出大殿,跑进一个矮小侏儒的学生来,仰着脖子,对醒狮只一望,吓了一跳,当下那学生说不出别的话,望望三世佛,望望赵醒狮,好像在那里把三世佛的丈六金身,和赵醒狮比较长短大小,比较了一会,翻身便逃。醒狮气得挺着肚子,更像前殿的弥勒佛,踱了出来,碰见介绍人对醒狮笑道:“那人见你一面,吓得倒退不迭。我问他怎样,他只管摇头,说不敢仰攀。”醒狮气愤回校,想出一个妙策来,趁运动会人头挤挤,做下三十六鸳鸯数的名片袋子,每只里塞一张照片,五六张名片,一只戒子,在会场内四下散布着相思种子。这条妙计,果然效力不小,不满一星期,便络续接到情书一百六十五封半,其间也有一人连写三四通的,也有甲拾得,给乙偷见了,私下投函的,也有学生拾得,给教师瞥见,收没下来,教师自己投函去约会的。有一张还是写的明信片,只好算他半通。在这个星期内,赵醒狮的情书,把邮差和校中收发员,忙得不亦乐乎。全校同学,人人眼红,醒狮把一封封的信,汇集拢来,细细评阅,觉得汪绮云最多,一人有十九通,其愚不可及,其情很可怜,免不得复他一信,叫他把籍贯和三代履历详细开来。绮云如获纶音,连夜寄去,醒狮一瞧,又是同乡关系,便把终身相许,勉他入校读书。绮云接到这封信,好似空手白手,在草地上拾到一个美人,其喜可知。当下回府和汪四先生家庭革命起来,结果把李老师那头亲休退,又拼命拼到二百块钱,去考取了师范讲习所,在校里时和醒狮通信,只不曾会面过。醒狮要待毕业后,和绮云自由结婚,不知绮云那所师范讲习所,只半年已毕业。绮云早知醒狮的父亲叫肖虎,便是南溟庄财主,所以听得玉吾、璧如来说肖虎办学,请他去做教员,快活得不可名状,心肚五脏,险些笑了出来。
当下绮云、璧如两人,跟玉吾到家,见过福爷,相烦引荐。福爷写下一封信,专足送去给赵肖虎,肖虎欢喜不迭,回信福爷。福爷又把信给玉吾,分头向璧如、绮云接洽,信内说明璧如主任,薪水按月十六元。绮云助教,按月十二元。聘书要等校长醒狮女士签下字送上。璧如见得,很觉那个校长突兀,心中纳罕。绮云见了,喜不自胜,心想那个字,何用签得,醒狮便是我,我便是醒狮,何不叫我签签便好。当下专待聘书到,便去上课。一面赵肖虎把两位老古董停止了职务,写信给女儿,说明详情,写就两张工楷的延聘书,空着校长下一个名字,附在信内寄给女儿,叫他签字寄来。停了两天,肖虎接到聘书,也没回信,当时匆匆忙忙,把两张聘书寄给福爷。玉吾知道肖虎送来,一定璧如、绮云的聘书,拆开一瞧不差,一式两纸延聘书,当即送到璧如店里,绮云也在一桌喝酒。玉吾把各人一张,分给他们,璧如先一瞧,心下猛吃一惊,指示给玉吾瞧道:“你瞧怎样和前天信上说的不符啊。”玉吾细细读下一遍,又把绮云的,读一遍,方始觉得不对。绮云升了主任,薪水十六元。璧如降级助教,薪水十二元。绮云心下,早已明白,不由得一阵开心,卟哧的笑了一声。璧如瞧瞧那个歪歪斜斜的校长签名“赵醒狮”三字,心下明白了一半,也不和绮云多说,笑道:“我和你彼此老友,既不在名分上,又不在区区四块钱一月薪水上,总说得通的,照聘书办事好了。”玉吾不知底细,还道:“肖虎写错的,要收还去问问明白。”无如两张聘书,统通给两人塞进袋里去了,也只好不去顾问。当下三人谈谈说说,约定出月初六星期一去授课,吩咐玉吾代复一封信去,玉吾应允。绮云道:“音乐一科我弄不来,你担任罢。”璧如道:“技能科,当然是助的职务,我认定算术、音乐、体操四科,其余国文、修身等科,该你主任先生担任。只是我教授音乐,非用我自己那座风琴不可。我那座风琴,买了好几年,用熟了,现在风箱有些走气。黑白键也有几个捺不响,非送到苏州裕昌去修理一下不可。我想明天礼拜六,去开一次,回来再休息一礼拜,便要去上课了。绮云,你苏州有甚么事,可要同去?”绮云道:“我苏州没有要干,似乎不必去,你到裕昌,任便替我在隔壁大文印刷所,取一百名片,钱已付清,一个多月,总印好了。”璧如道:“可有收条凭居?”绮云道“你只要说明汪绮云名字,便比收条凭据效力还大。因为这东西,别人没用的,谁愿冒领。”璧如道:“说不定有同名同姓的汪绮云,拿去凑现成哩。”绮云道:“我的姓名,是向内务部注册立案的,他人决不敢冒牌,自己也有暗记号,决不和人缠差的。”璧如一笑道:“那么他们不肯付我,我却不管帐。”说着天已黑暗,各自回去。明日清晨,璧如吩咐店中学徒,把家里一座风琴,搬到航船上,等到开船,璧如跳到船中,一路开往苏州。下午已到齐门,璧如叫一个苦力,把风琴送往观前裕昌,吩咐立刻修理,当日要带回去的。店员含糊答应着。璧如去买了些零碎东西,取了名片,见那名片匣盖上,粘着一张,只汪绮云三个大字,并没小字,璧如塞在袋内,走过裕昌瞧瞧那座风琴,尚没动手,不免和店员争吵。另一老者走来解围,把风琴下面的气箱一瞧道:“只细小一个出气洞,不要紧的,我送你一些鱼膏,送你一张皮纸,你拿回去把个小洞粘一粘没,便不走气,不消修理得。几个音键不响,更不要紧,只消回去把里边铜音键抽出,将一些灰尘吹去,便响。”璧如听他一说,也觉很易,无修理之必要,给了两毛小洋,又叫个苦力送到船上。那时船中一个乘客也没有,璧如便把鱼膏粘上皮纸,等下一刻工夫,捺捺果然响了,只二三个音键不响,没有修理家伙,只好回去修理。停了一会,璧如正在舱内捺风琴,猛觉得那艘船荡了一荡,左右动摇不定,艄公叫道:“对不住,脚步轻些,船要翻的。”船头上那人发出洪钟般的声音道:“你的船又不是纸糊的,站不起人。”艄公伸颈对船头上望望,便不敢声响。璧如待要望时,船头上那人弯着身子钻进舱来,璧如猛吃一惊,只见那人不男不女,一个身子胖得像牯牛一般,两只小腿比灯笼还粗,一双印度金莲,走路绰拍有声,一身粉红纱衫裤,一条齐膝短裙,头发蓬松,像个雀巢,方面大耳,阔口巨鼻,握一顶纺绸伞,挟一册英文书,跳进舱内,一艘船顿时沉下三四寸。璧如吓得躲过一边。列位明人不必细说,这副神气的女子,舍赵醒狮有谁呢!只是尤璧如虽经他委任为“赵氏私立国民小学校”助教,罚咒不认识这位文明校长。醒狮女士坐在舱中,好似不屑向璧如顾盼,只管把册英文书翻阅。一会子船开了,再也没有第三个搭客。璧如枯坐觉得寂寞,又翻开琴盖,捺琴消遣。”醒狮女士目在书上,耳在琴上,只听得那琴声捺的“点点杨花谱”……
迷沙沙沙□□笃□沙……迷沙迷□□□独□□□迷来……笃笃笃□迷迷迷□迷□笃□□……笃笃□笃□笃□笃……沙沙沙□沙!
琴声戛然而止。醒狮听得那座破洋琴,七个音倒坏了三个,只是笃笃笃沙沙沙,肚里忍着笑,又听得捺着
“秋之夜谱”道:……
独独迷□□独□□迷迷沙……□□□沙笃笃□□沙沙沙迷□……独独独□□沙沙□迷迷沙沙□……笃笃□□□沙沙□□□□笃……笃笃笃笃□笃□沙沙迷独□……迷迷独迷沙沙□□□……
醒狮女士再也忍不住,吃吃的笑了一阵。璧如觉得那只破风琴,再也弄不出什么花巧,自家听听也不成甚么调,捺下不肯响,真叫气力不大出,也只好中止,可怜高山流水之音,钟期在旁,琴不争气,也只有辜负知音。璧如放下手,又觉纳闷,摸摸怀里那只香烟嘴,一时摸不到,把一切东西统摸出来,甚么香烟头、火柴匣、皮夹子、断铅笔、日记簿,又绮云的一匣名片,一起放在琴盖上。
这当儿奇不奇巧不巧,醒狮女士两道电光似的视线,直射到那只名片匣上,和汪绮云三个字,打了个照面,脑系里蓦地起了一阵甜热,对璧如面上端相一会,璧如觉得受宠若惊,生平没有受过女性这样热烈的欢迎,反低下头,不敢平视。醒狮女士不由得轻移莲步,坐过一边来。忽听艄公喊道:“慢些,船要侧翻了。”醒狮女士只好依旧坐到原位去。原来小船里面,像醒狮女士一般的身子,举足轻重,岂容妄动。璧如心中好笑,不料那位女士,笑嘻嘻的和璧如搭讪道:“先生不是汪绮云吗,谁想今天这样巧遇,同舟共济起来。”璧如只笑着点头,并不辩明不是绮云,醒狮越加胆大起来道:“绮云,你认得我吗?”说着,吃吃吃笑了一阵。接着道:“怕你只认得我笔迹,不认得我面貌,我的面孔,今年格外胖了,怕和从前给你那帧照片上差得多了,莫怪你要不认识了。”璧如听得话里有因,索性含糊着道:“简实不相识,女士是谁呀?”醒狮女士忽向璧如瞅了一眼道:“可是你心不在焉,没有我这样一个人在你脑筋里,你终究是个有口无心的人,信札一封连一封,说得天花乱坠,当了面,边我的名字也想不起了。”璧如那时,装作假痴,笑道:“我拭拭你呀,我有你的照片,怎会不认识你的?”说着,把一张汪绮云的名片,授给醒狮女士道:“你瞧这张名片印得还好么??你的名片,用石印的呢,铅印的?”醒狮女士道:“我前回的不是你见过排铅字的吗?现在讲究了,排的仿宋字。”说着,掏出一张给璧如。璧如不瞧犹可,一瞧在面上绯红,亏得镇静工夫,加人一等,不曾当场现出原形,片上印着赵万雄三个大字,醒狮两个小字,角上又有赵氏私立国民小学校校长一行头衔。璧如心想:今天无端碰见上司,撒下这个弥天大谎,那还了得。只是事到其间,真叫有口难分,索性将错就错罢。我十二块钱一月的薪水,情愿牺牲了。当下面上做出不慌不忙,把醒狮一张名片,塞进自己袋里。醒狮又道:“我们校里,新的风琴,早已置办,你那座蹩脚风琴,还要他做甚?”璧如道:“那却捺熟了,不舍得抛弃。”醒狮又道:“绮云,我家那所学校,给我的爹爹办坏了,非你去整顿不可。那位助教尤璧如,大概你总和他要好的,前天家父来信,说他资格老,原定他的主任,你的助教。我想资格老不卖钱的,你在其内,当然是你的主任,只好冤屈他做助教。现在办事,不论大小,免不来感情作用。绮云,你道对吗?当下我把两张聘书,重行写过,这番事情,怕你还不知。”璧如听得,荡气回肠,暗暗说声:“惭愧。”面子上装出十分感激的样子道:“承你的情,要你包涵。”醒狮道:“你怎样客气到如此”自家人何必装出虚伪来,谁想你写信一样,谈话又是一样。我问你,有几副态度呢?”璧如道:“好好,我不客气了,你今天回来之后,隔几日返校?”醒狮道:“礼拜一便去,下星期校中要旅行到西湖,耽搁几天,回来之后,便要中秋节假,那时候又好回来小住。你近来忙得怎样?我有一两个月没接到你的信,你前回要求提早结婚,我不是不赞成,怕手续上来不及,所以拒绝你的,难道你因此消极,不和我通信吗?”璧如对于这几句话,简实无从回答起,只好呆望不响。醒狮又道:“我们俩总算神交,比不得他们鬼鬼祟祟,一认识便厮混在一块儿。我们通信了半年,今日才得碰面,碰面以后,又增添了一层情感,你毕竟要提早,那么我允许你中秋节罢。只是结婚之后,我仍旧要到校考毕业,好在功课早已完结了,结婚期内,多请几天假,也不打紧的,你道这个办法好吗?”璧如这时索性放大着胆子,装出一副嬉皮笑脸道:“可是我实在
等不及了,你做做好事罢。此番回去,行一行礼就算了,何必检日子呢。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孤孤凄凄的住枯庙里,简实住不惯。结婚以后,那就好住到你府上了。”醒狮那时,挤着一双粗眉大眼,向璧如白了几白,接着道:“婚姻在事,也没这样便当。你校里住不惯,等我回去办好交涉,你住下我家,也不妨事。”璧如道:“毛脚女婿,那是我不做的,非要合卺洞房,才觉得有味。”醒狮又对璧如瞅了一眼道:“怕你嘴里说说,家里真办不到哩。”璧如道:“结婚是我个人的事,自己有主张,随便那一时那一刻,只要你愿意和我结婚,我马上和你结婚。”醒狮道:“呸!结婚的手续,也很烦琐,怎好立时立刻举行呢!”璧如道:“我说的不是形式上的结婚,是实际上的结婚,两人睡在一块儿,结婚的实际便尽了,形式随便他们几时想着做,我们便几时做,可是和我们不相干的,我们只求实惠好了。”醒狮那时也有些情不自禁起来,两只水汪汪的眼珠子,对璧如惟似嗔非嗔,似喜非喜。璧如心想:肚子里这口鸟气,非趁此机会,出他个干净不行。索性畅快说道:“醒狮,瞧你不出倒是个民国孔二奶奶,这样一点一划的规矩,现在外面跑跑的女士,真讲不到结婚两字哩。他们说的,结婚便是爱情的一个坟墓,等到行结婚礼,爱情早已葬送尽了。真正的爱情,便在未结婚以前,偷怜窃爱,彼此郎情如蜜,妾意如胶,若即若离,难分难舍,这其间真有说不出的好处。可惜我和你都没有尝过,倘要等到红氍毹上拜过了,才行那个周公之礼,真如大嚼江瑶柱,索然无味了。醒狮女士,你道我的话对吗?枉为你是个赫赫有名的新人物,讲恋爱自由的,这一些真正恋爱的味儿也没有尝过,说你听也不知甜酸苦辣,真可惜可惜。你既没有尝过,也不能怪你办不出好味儿,只是你要尝时,我也不惜牺牲,尽力报效。你一经上口,包要片刻舍不得我哩。”醒狮女士此时一颗心,别别的跳荡,面子上呵叱璧如道:“我不要听你的油嘴,规规矩矩问你,几时来上课?”璧如假作摸摸袋里道:“哎哟,一张延聘书不知那里去了?我本想寄还你呀。我不贪你家十六块钱一月,冷庙里总也住不惯的。我今儿当你校长先生面辞职,不干!不干!”醒狮道:“你又要作难我了,你要怎样,才肯担任,请你开出条件来。”璧如道:“也没有甚么条件,第一你先给我好处,别的都容易商量。”醒狮道:“要甚么好处呢?”璧如道:“明人不细说。好处者,好处之好处也。我得了你好处,包你办事办得处处都好。”醒狮羞答答道:“你半年挨下了,两三个星期难道……”璧如摇头幌脑道:“难挨哪!难挨哪!度夜如年,守身如杀头。”醒狮卟哧的笑了一声。
那时忽听得艄公喊道:“南溟庄塘角边登岸!”醒狮惊道:“我家到了,绮云你倒底那天来上课?明朝我在家里等你,你来有要言对你说,包你满意,你别失约。”璧如笑着只不开口。艄公又催着快快上岸,船已停泊。醒狮钻出舱去,站在船头,又叠问璧如怎样怎样?璧如道:“我不但教务请代表,将来一切都请代表。”醒狮道:“什么话?”璧如道:“你登岸罢,日子长久哩,隔天再谈罢。”醒狮免不得跳上岸去,璧如暗暗好笑,心想这口冤气,总算出得爽快,只是暂时不能漏脸,将来那件双包案破裂起来,终有一番唇舌哩。当下航船到得福熙镇,璧如走回店里,吩咐学徒把风琴搬送回家,自己便在店中吃罢夜饭,一宿无话。明日绮云走来。璧如把一匣名片给他道:“幸不辱命,只是少了一张,给我一位朋友取去了。”绮云道:“一张名片,值得甚么,你未免太忠厚了。”璧如道:“我出名的忠厚人,不得不报告明白。”绮云一笑而去。过得几天,璧如父亲偶沾小恙,璧如便借此为由,辞去职务。绮云直到礼拜二才去上课,醒狮女士此次还家,无端受璧如一番语言的兴奋,不免性欲冲动起来,回家提出婚姻问题,和肖虎谈判,结果父女俩决定挽钱福爷执柯。福爷向汪四先生商议,汪四惯于绮云革命手段,只好子命是从,当下议定八月十四吉期,一切仪式从简,全用文明礼制,略备几桌喜筵,开个茶话会,行三个鞠躬,便算成礼。在这两个星期内,绮云发柬请客,布置新房,忙得汗流浃背。校中另聘了一位助教,绮云也没有去上过几次课。吉期既到,绮云请玉吾、璧如帮忙,玉吾乐从其事,璧如惭莫能助,心想这个爆裂弹爆发起来,不是耍子。当下虚应一声,只匿在自己店里。绮云衣冠簇新,精神抖擞,准备合卺交杯,消受柔乡艳福。一交午正,宾朋满座,觥筹交错,说不尽盈庭喜气。绮云向四座一望,大为诧异道:“咦!”正是:
长生殿里虚前席,专盼杨环踏月来。
不知汪绮云为甚么诧异?说出甚么话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