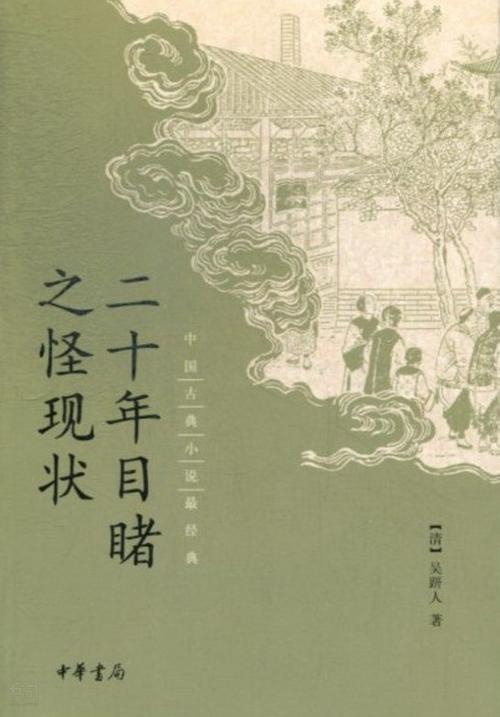话说庙中香伙,清早走进城隍神张太爷新房里请安,偷眼瞧床上新嫁娘时,那偶像忽地大吼一声,扑将起来,把香伙吓倒一旁。当时那偶像却不慌不忙,走下床来,扶起香伙,拍拍他胸脯,捏捏他人中,把他悠悠忽忽的一缕痴魂,从鬼门关拘了回来。香伙张眼细看时,何尝是个新嫁娘金珠小姐的偶像,那人便是安乐村一个游手好闲金三,又叫金小弟,便是上回书里所说金大的小兄弟,自被金大、金二赶出后,住在牛棚上,日夜无拘无束,闲逛各乡,大家都叫他日夜游神。他这几天因嫂子回来,羞着上门去吃饭,每天总在外面随处觅食,昨晚逛到南溟庄来瞧热闹,等到夜深,溜进厨房,见剩下许多鱼肉酒饭,凌乱杂陈,他一时馋性发作,吃一个光。谁想酒喝得太多,身不由主,摸进张太爷新房瞧瞧,阒无一人,新床上倒陈设得花团锦簇,他便把张太爷神像抱放床底下,新娘偶像翻过一旁,和衣睡下,口中还模模糊糊的说道:“对弗住,新娘子,陪陪我。”说着呼呼睡去,直到天明,宿醉始醒。听得香伙叫他,他才觉心中惊慌,吼了一声,扑将起来,险把香伙吓死。香伙惊定,要叫庙王来扭打,小弟陪个罪说:“老阿爹,马虎点罢,闹起来你也不能脱干系,说你当甚么心,太爷新娶姨娘,第一夜便给外人睡去,你该当何罪!”香伙胆小,果然软化,小弟依旧替他陈列好了,对着香伙笑眯眯道:“你瞧,我虽和新娘子同床合被,可是汗毛都没碰歪她一根咧。”香伙啐了他一口,小弟便也溜出庙门,一路向福熙镇鬼混去了,暂且按下。
福爷昨天劳了全日的神,回家已过午夜,委顿异常,睡到晌午,还没起身。他儿子玉吾,乐得心花怒放起来。清早写三张字条,差家人去约三位朋友,到隔河一座尼姑庵里吃中饭。这庵本来是座富室家庵,叫紫竹庵。现在富室凌夷了,当家的尼姑只好出来募化度日。当家的名叫妙贞,年虽迟暮,风韵犹存。有两个徒弟慧静、慧娴。慧静十八岁,生得明眸巧笑,妙舌粲莲。慧娴只十五岁,玲珑活泼,婉转娇憨。那双慧出身,都是乡村女儿,从小送进庵去剃度的。每日礼忏诵经以外,倒也不大到外间闲逛。因此皮肤生得白雪之白,面孔生得白玉之白。施主一见,谁不动怜香惜玉之心。玉吾更是年少英俊,丰姿秀逸,吉士的资格,当然魁首。只恨家教太严,管束太紧,不能在外乐个畅快。平日在家里,瞒着老子,点盏油灯,在枕头旁边偷看看《红楼梦》、《金瓶梅》以及《倭袍》《三笑》那种弹词小说,看得兴浓,便觉出外游逛,更不容缓。他母亲陆氏,因只养他一子,很钟爱他,偷偷地每月十块八块钱,总有塞他。他有了钱,便如鱼得水似的,悠然而逝。那天约的三个朋友,一个汪绮云,街上汪四先生的儿子。一个尤璧如,街上杂货店里的小开。一个沈衣云,附近澄泾村一家穷读书人家的儿子。当下玉吾先摆渡过河,一路跑到紫竹庵,敲门入内。妙贞素来敬重他的,因他是乡董福爷的儿子,怎敢怠慢,陪笑着引进一条通幽竹径,直达一间静室,静室里面悬个匾额,题着“天香深处”四字,窗外两棵桂花,一丛芍药,墙上一个福字,一副刻竹对联,刻着八个字“问花笑谁”,“听鸟说甚”,是沈其蓁所书。其蓁便是沈衣云的祖父,文名煊赫一时,本来是个老举人,衣云的父,没有进学,发愤读书,呕血而死,家道因之中落。衣云不能自存,依他叔父度日,与钱玉吾很亲善。当下玉吾对着窗外那副对,正在出神,慧娴憨跳而来,叫道:“玉少爷,你来了,师兄在里面叫你呀!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你在那里玩呢?”玉吾也不开口,只管捏她的手,捋她的袖子管,一段嫩藕似的小臂,给玉吾摩挲了一阵,又伸手去摸她长领里露出一块雪白的肉。慧娴格格笑不可仰,正在撑拄之间,慧静慢慢走来,穿件秋色香色的家常袈裟,光着个留海顶,慧娴忙叫道:“师兄快来帮我,肉痒煞哉!”玉吾只不肯放,好像要在她胸前挖出件什么东西似的。慧静叫道:“玉少爷,像甚么样子,动手动脚!”玉吾听得才放了手,慧静又道:“今天甚么风,把你吹过河来,你一去总像断线风筝似的,那一句话有实在?当了面,甜言蜜语说得人心软,背了人又不知在那里寻欢作乐。你们男子的话,我再不信了,真靠不住哪。”说着,两只睃眼一横。玉吾也不回话,只把个头凑上去,面擦面擦了一擦,只管嬉皮涎脸的笑。慧静又道:“孩子气又来了,年纪一年大一年,怎么改不掉?吾问你,今天可要请客吃饭?”玉吾道:“有什么客不客,依旧几个老朋友,你去煮几色素菜,荤的不要,并且要你亲自动手煮。”慧静笑了笑道:“我手上又没仙露,偏要点我,我不煮。”玉吾道:“你又来了,你烧火,吾来煮。”慧静噗哧一笑说:“不长进,你明儿讨了家婆,要给她打到床下去咧。煮小菜,女儿的事,你会煮。。”玉吾道:“那末你是个女儿,你该煮,吾本不会,激激你呀!”
说时,慧娴在旁,推慧静去煮说:“师兄,你去煮吧!园里有青菜、扁豆,叫李佛婆挑去。”慧静又向玉吾瞟了一眼,始飘然而去。玉吾又和慧娴说笑了一阵,尚不见朋友到来,独自踱进里面一间小轩里去。轩里悬块银杏绿文的匾额,上题“松籁山房”四字。靠壁一橱经卷,一张小桌,桌上茶壶茶杯,文房用具,正中供一尊古铜小佛,两个古磁花瓶,瓶中插两枝木芙蓉。靠西设张湘妃榻,一床被褥,折叠整齐。轩前有棵古松,树根合抱,根荫成幄。这轩里便是双慧的卧室,只有玉吾做过入幕之宾。玉吾坐在榻上,翻翻枕边,找到两件法宝,一串普渡香珠,一册《双珠凤》小说。玉吾把香珠闻一闻,小说约略瞧了半页,依旧替他放好。静娴进来叫道:“朋友来了!”玉吾连忙走出,见三人一同来的,迎上问道:“你们怎碰得巧?”衣云道:“我们在璧如店里约会的,你酒菜预备好么?”绮云道:“他起早起来这里,怎会不预备。”璧如接嘴道:“起早起来,可曾碰见什么隔夜人?”玉吾听得,很觉难堪。正说着,妙贞走来,搭讪着道:“两位云少爷,玉少爷,璧少爷,通来了,我们小庵里便热闹起来。难得的几位少爷,平常请也请不到,请坐喝茶罢。”叫声李佛婆,端上四碗茶,玉吾喝了一口道:“茶叶很好。”妙贞道:“这是春上在杭州买的龙井呀。”玉吾道:“哦,怪不得清凉有味。”妙贞又道:“你们在这里喝茶,我要到澄泾接生意去,来不及回来陪你们了,再会吧。”说着,出门自去。当下汪绮云最赏识慧娴,说这小妮子,天真流露,真像只小鸟,你看她两只眼睛里溢出水来。一张河豚小口,不到一寸阔,见了怎不动心。璧如道:“这也是他爷娘加工制造的,然而也不容你动心。”说得众人大笑。慧娴羞着,把璧如打了一下。里面慧静叫道:“师弟,你和李婆把桌子椅子排好,菜好了,吃饭吧。”李婆走来,一一端正,四人合坐一桌。玉吾叫李婆再排两只椅子,璧如拉慧娴坐,慧娴不肯,和绮云坐了。停会慧静出来,说一点菜没有,你们喝什么酒,吾去拿来。玉吾道:“木樨烧吧。”璧如道:“白玫瑰好。前会的木樨烧,好像出了味,上口很淡,还是白玫瑰来得凶些。”绮云道:“怎么尼姑庵里开了酒店似的,任便什么酒都有呢?”玉吾道:“慧静自己浸的,三大瓶高粱,一瓶木樨,一瓶白玫瑰,一瓶代代花。”正说着,慧静捧出一柄古磁小酒壶来,把四只玻璃高脚小杯,各敬上一杯,坐下玉吾一旁。李婆端上四只碟子,一只菌油拌嫩豆腐,一只白扁豆子合冬笋,一只豆腐衣卷子,一只豆腐干屑拌马兰芽,都很精致。绮云对着玉吾道:“谢谢主人。”璧如指慧静道:“你要谢她的,她忙了半天。”慧静道:“谢什么,承你们少爷肯来吃素斋,连我都修福的,只怕吾不会煮,不配你们的胃口。”璧如道:“胃口怕再配不得,再配要连碟子都不剩了。”说着大家喝酒。衣云把个腐衣卷子解开,内有香菌屑、冬笋屑、青豆屑、枸札屑、五香腐干屑,不觉称赞道:“有味啊!”绮云也道:“当真妙手调羹,害得‘厨房娘子费功夫’。”璧如道:“这句话要改去两字方称。”衣云接着道:“当改‘厨房师太费功夫’才说得过去。”慧静羞得两颊飞红。绮云道:“现在的师太,便是将来的娘子,安见一生一世做师太。”慧静道:“我们出家人,当然一生一世的事,你越说越不成话了。”绮云道:“便是你要一生一世做师太,玉少爷不放你做怎样?”说着慧静更难为情,叠向绮云飞了几个白眼。接着叹口气道:“可怜我们出了家,这条心就像死了一样,也不省得红尘中有什么好处?”衣云接着道:“红尘中的好处也不过如此而已,怕还没有这样清静快乐咧。”璧如插嘴道:“一个女子,等到出头露面去做人家的娘子,已是没有什么好处了。最好在暗地里偷怜密爱的做娘子。”这话说得玉吾的脸都红了,慧静更羞得要站起身来。那时恰巧李婆端上四色菜来,一碗口麻红烧豆腐,一碗冬菇菜心,一碗什锦素鸡,一碗清汁腐皮卷子,都满满的装着,众人赞不离口。衣云道:“菜太多了,真要谢谢师太呢。”玉吾道:“谢她一杯酒吧。”慧静不肯喝,绮云道:“半杯吧。”玉吾把自己一杯酒喝了一口,递过慧静,一饮而尽。璧如道:“这是玉吾敬的,我们三人各敬一杯。”吓得慧静要逃走,玉吾拉住道:“公敬半杯吧。”慧静只不肯喝,对过慧娴,伸过手来,抢去喝了,说:“我替师兄喝吧。”慧静道:“你要醉咧,高粱怎好一杯一喝。”众人都称赞慧娴爽快。慧静虽只了半杯酒,面泛桃红,分外娇艳。慧娴席间周旋,真如小鸟依人。衣云道:“太阳已西斜,怕要三点钟了,我们再也吃不下什么。”慧静道:“我去煮碗青菜面吧。昨天剩下自己做的面条子,倒很柔滑,我去煮来。”玉吾道:“我最喜欢吃,只是待李婆弄去吧。你心不在窝,不要做倪阿凤,把面切断了煮。”慧静瞅了玉吾一眼道:“你倒把《双珠凤》读得滚熟。”玉吾道:“吾只瞧这一段,还是昨夜在你枕头旁边瞧的哩。”慧静啐了口道:“你一定今天早上偷见的,我昨夜真瞧到这里。”玉吾道:“那末我也瞧到这里。”那时璧如插嘴道:“你们大家听着,她枕头旁边的事,玉吾会得瞧见,本事真不小啊。”绮云道:“慧静,你瞧《双珠凤》不如瞧《玉蜻蜓》来得有味。”慧静没见过《玉蜻蜓》,便问怎样好看法?璧如接嘴道:“《玉蜻蜓》内的申贵升和一个三师太,爱好得说弗出,怕比你和玉吾还要爱好咧。”慧静羞极,叫李婆煮面。玉吾佯道:“你串香珠送了我罢。”慧静惊道:“这是师父的,怎好给你。”说着要搜玉吾的袋,玉吾道:“没拿,你莫发急。”这时各人吃了一碗青菜面,散席喝茶。
衣云道:“我们讲点正经吧。”璧如道:“真经不到庵里讲。”衣云道:“莫胡缠,我劝劝玉吾,别管闲事。你尊大人做了乡董,叫没法子想,你吃饱了自己的饭,去管什么闲帐。断得无论怎样公平,只有一方面说你鲁仲连排难解纷,其他一方面,总说你压制,说你武断,你又不拿人家的钱,为什么要给闲人批评?你道对么?”绮云说:“不差。”玉吾也以为是。绮云道:“便是你一条尊辫,也早好付诸并州快剪。”衣云道:“这是他老子的性命,万不可碰歪的。他老子见别人剪辫,总要叹口气,说什么‘不敢毁伤’‘用夏变夷’等话,那么玉吾怎敢有违严命?他条尊辫,怕要待之将来,和他老子的苫块同休哩。”说得大众粲然。当下重和双慧说笑了一阵,玉吾塞了四块钱给慧静,一同走出紫竹庵来。璧如喝得白玫瑰太多,老大有点醉意了。
走到将近摆渡口,一处绿树浓荫里,看看是家田家,几个农妇,正坐着,把根细竹梢,削去稻柴尖上的余谷。瞧见四个少年走过,一起停了手,斜睇着。其中有个大姐,认识玉吾的,唤声:“玉少爷,你要摆渡么?摆渡船此刻正在驳苏州小轮上的客人,要停一会哩。”玉吾点点头。旁一妇人,让条凳道:“你们坐会吧!”四人暂且坐下。那时候刚巧东边有个姑娘走来,二十来岁光景,外罩件鱼肚白竹布单衫,系一条元色布裙,穿双蝴蝶花鞋,挽个风凉髻,倒也生得眉清目秀,走起路来,更是娉娉婷婷,右手臂挽个小包裹,走近村中,唤出一缕娇脆声音道:“……调水碗,……捉牙虫,……抽牌算命呀!”村上闲人,也有叫住她道:“来!来!抽一抽几文?一百文抽几抽?”那姑娘只把一双媚眼瞟一瞟,并不答话。另一闲人,把只手按住口,叫着:“捉牙虫!我好难过啊!非捉他个干净不行!”姑娘问道:“真的么?”那人道:“谁谎你!”姑娘把个包裹放在一旁,说你去拿碗水来。那人并不回答,只把个身子靠在稻柴堆上,张着口,直挺挺像个死人,姑娘一望情形,瞧到八分是胡调,挽了个包裹便走。那边坐着四人,见了好笑。那姑娘瞧玉吾生得面如冠玉,衣云更出落得丰裁隽逸,不觉呆了呆,两只脚好像不肯轻意走过似的。玉吾更飞了一眼笑一笑,那姑娘失魂落魄起来,搭讪着道:“几位少爷们,要作成我一点生意经么?”接着一笑,这一笑笑得娟媚入骨。璧如忍不住道:“我问你,什么唤调水碗?你碗里的水,怎样调法”姑娘道:“这就是简便的关亡呀,和家亲死鬼讲讲话。”璧如道:“准不准?几文一调?”姑娘伸个指头说:“一百文,那是不准不要钱。”璧如便装出很郑重的模样,叫她调起水碗来,自向田家借只碗,盛碗水,放在姑娘面前。姑娘搬只凳子坐了,喝点水,漱漱口,问璧如道:“你问的是你长辈呢平辈?男亡呢女亡?”璧如道:“女亡,好算是平辈。”又问:“什么门”璧如呆了呆,望见对门有棵杨树,触机道:“他是戴门杨氏。”又问生年几岁,几月几日死的?璧如又编了个谎,说罢装出十分伤悲似的,不时把可怜的眼光望着姑娘。那姑娘闭一闭目,凝一会神,连打三四个呵欠,忽的两颗眼珠子,向眼眶里一插,呜呜咽咽哭起来,把众人都吓昏了。听她哭罢一阵,接着娇滴滴的唤道:“嗳!我的亲丈夫呀!你掉得我好苦啊!你在阳间像荷叶上露水般,不向东边圆,定向西边圆,说不尽的快活,谁想我短命的人儿,在阴司里受苦啊!”那姑娘一边哭,一边拭眼泪,当真也有一两滴洒下,众人一哄而笑。璧如假做陪泪,肚子里笑得肠断,更不得不也学着她呜咽道:“我的妻呀!你说我快乐,我一点不快乐。我听你哭,好心酸啊!你快点不要哭吧,你再哭我也要哭哉呀!”那姑娘听得便宜已给人讨去,好像做一场交易,已经银货两清,拭拭眼泪,不哭了。玉吾、衣云两人笑得肚子肉疼。玉吾道:“算了吧,只是你的眼泪,为什么卖得这样便宜啊?我不舍得你再哭了,我问你,今年几岁,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什么人?”姑娘道:“二十岁,东乡人,船泊在南溟庄,只有两个哥子,做走方郎中的。”绮云问她,为什么老大年纪不嫁个人?姑娘绯红着脸,只不做声。绮云爱她抚媚,怜她浪漫,不忍胡调,给她二毛钱,说算了,不要找吧。玉吾道:“该应璧如出,亲丈夫权利,是他享的。”璧如道:“那么霉头也是我触的啊!”衣云有接着道:“不差,他新结婚咧。”绮云道:“他自寻霉头触,无非要讨几声亲丈夫的便宜吧了。他新夫人晓得,定要气个半死,说你们男子真没良心,一出门便咒家婆死。”璧如道:“我死的戴门杨氏呀,不关家婆事。”玉吾道:“那末还算你有良心。”说罢,那姑娘也向西去了。
玉吾等走到渡口,摆过河来,那时已是日落衔山。衣云、绮云各自还家。璧如邀玉吾店里小坐,一路走去,璧如当先。忽地一个妇人迎面奔来,和璧如撞个满怀。璧如把她一推,那妇人又拚命向前奔去。一只绣鞋,掉在街心,只是不顾。街上闲人,大家纳罕道:“难道是女强盗吗?”玉吾、璧如缓缓走过去,到积善寺前,聚着一堆人,纷纷传说不一。有的说,青天白日,僧房里关个女人,不晓得做点什么,大约会的缺乏小和尚,所以连日连夜赶造。有的说,天下善人真多,和尚没婆娘,便有善女人把肉身供献到佛前布施,功德真是无量啊。璧如不知底细,拉个街上说小说的胡小石问他,他详细的说道:“丁全茶馆里坐个日游神金小弟,暗地瞧见个妇人走进寺里,好久不出。他进去搜了好一会,影迹全无。他不信那妇人会土遁,用耳朵去察听,听到根云和尚房里,发出一种女人笑声来。那笑声仿佛笑里带着喘,他如获至宝,奔到孙三燕子窠,报告道:方才我眼见积善寺根云师在寺后掘得一坛子横财,此刻师徒俩在房间里分赃,我看得真切,一卷一卷,搬进搬出,通通雪白的现洋,你们快跟我去分。众人一哄跟他进去,跌门而入,可怜那时根云和尚的佛牙,还没有给那妇人看完呢。幸亏妇人眼快脚快,飞奔脱险。根云给他们拳足交加的打了一顿,还把他房间里的东西,卷一个空,此事可笑不可笑。”璧如道:“哦!恨不得那妇人一路乱撞乱奔,像没命兔子一般。”玉吾道:“青天白日,佛地宣淫,那还了得。这个贼秃,非赶出他不行。”璧如道:“你又来了,你难道只许尼姑受用,不许和尚开心?你瞧寺里的三世佛,做在他眼里,他一言不发,要你多什么嘴。俗家人要吃饭,和尚也要吃饭。俗家人要敦伦,和尚也要敦伦。这是人情之常,你不能禁他吃饭,便也不能管他敦伦。我不做大总统,我做了大总统,出一条命令,把合天下尼姑一律配给和尚。”玉吾道:“呸!这还成什么世界,委实混帐。”璧如冷笑道:“你不要发急,混帐不混帐,无论怎样,紫竹庵里慧静,总要留给你的。玉吾气苦不过道:“你的嘴巴太凶,说你不过。”那时已走到璧如店里,原来璧如的杂货店,单间两进,店里百货杂陈,只用得一个学徒。璧如的父亲已四十多岁,名叫燕山,半生刻苦成家,莫说店里一切事务都要他管,便是家里种五六亩田,一亩多蔬菜,都要他和妻子亲自动手。七八月里种菜,一块菜圃在桥南,一只粪坑在桥北,燕山夫妇俩扛粪过桥,每天晚上总要往返十来次。那时璧如尚幼,在城里高级小学校读书。中秋节假回来,身上穿套新操衣,足上套双白皮鞋,挺胸凸肚,走过桥去,走上狭狭的一条桥板,还要练习他的兵操步伐,一二一二的开步向前走,不提防他娘老子扛一桶粪迎面走来,一眼瞧见儿子回家,眉开眼笑,忙把桶子停在一傍,让他走过,不留心粪桶里泼一滴粪汁在他一只白皮鞋上,变了白璧之瑕。璧如回去鼓着两爿小颊,只不理他爷。爷问问他,便哭吵起来。他爷要太平,一时没有法想,在粉墙上挖一块石灰,矮着身子扒上前去,把他白皮鞋上一滴污渍擦白了,才算引得他快活。现在璧如由小学到中学,中学到师范,毕业了回来做亲,听说满月之后,便要去做教员,他父亲乐得心花怒放,不但反当他爷看待,简直当他十七八代的始祖看待。只要他说得出,爷便做得到。自己每天吃两碗粥,儿子早上一碗大肉面,还要加十。爷笑在面上,痛在心头。一天爷儿俩在店里吃中饭,璧如瞥见街上汪绮云走过,留进店里吃饭。燕山起初道是儿子虚邀虚邀,后见绮云当真坐下,心里别的一跳,面孔上依旧堆着笑容道:“残肴了,怠慢世兄。”璧如连忙吩咐店中学徒,到隔壁三娘娘酒店里打一斤酒,炒碗蛋,煮盆虾。燕山口中搭讪着,心里正在盘算,猪圈里养两只小猪,一只丢了,好不心疼。璧如和绮云酒兴勃发,猜起拳来。燕山听在耳中,好像声声是猪叫。一会子两人吃饭,璧如又叫学徒添两尾鲫鱼汤来。燕山疼上加疼,心想两只小猪,一只都不保,可怜哪,我已养到两个足月,今天算是他的末日到了,命尽禄绝,无可挽救。想到苦处,两滴眼泪,从丹田中吊到眼眶子里。绮云见他呆呆不吃,还道是主人客气,敬他个鱼尾,他那里吃得下,只咬得一口,忍不住眼泪要夺眶而出,打个寒噤,走向里面拭泪。绮云怪问,为的什么?燕山干笑着道:“不留心鱼骨梗的,不要紧,不要紧,世兄你请用饭,没什么小菜,鱼汤淘淘吧……”此情此景,只有他儿子心中略知一二。然而璧如朋友面子要紧,也顾不得他。当晚璧如要留玉吾吃夜饭,玉吾风闻燕山量窄,不肯叨扰。怎奈璧如再四苦留,只觉却之不恭,便坐下一傍。璧如殷勤劝酒,玉吾不敢多喝。燕山因为玉吾是镇上乡董钱福爷的儿子,格外趋奉着道:“世兄,饭菜少,隔壁去添些菜吧。”玉吾道:“不必客气。”三人说说谈谈,谈到安乐村的金大。燕山道:“便是我家璧如的连襟。”玉吾道:“他兄弟金二妻领回的那孩子,相貌很端正,将来说不定有些造化。”璧如冷笑一声道:“愚夫愚妇,说也可笑,什么总长的儿子孙子,无非哄哄人罢了,那有好好人家养了儿子不收管的。此种说数,正是齐东野人之谈。你老哥读读书的,也不信他则甚?”玉吾道:“我听他们说得凿凿有据的咧。”璧如道:“我总不相信。耳闻不如目见,即使是什么总长的私生子,也决不会如此不值钱,丢到乡下来。这种荒唐说数,无非骗骗村夫俗子,你我知识阶级的人,听也别去听他。”玉吾道:“我却有三分相信,明天想到安乐村去瞧他一瞧咧。老哥,你要见见么?”璧如道:“我真不要见,我总当他们是笑话而已。”玉吾笑了笑道:“你说起笑话,我们各讲个笑话吧。”璧如道:“我笑话很多,那么我来讲笑话,你听笑话吧。”玉吾对燕山面上瞧瞧,说:“璧如你算讨我便宜,你家老伯也在听笑话之列。”燕山不懂,只管听着。璧如道:“我想起方才的和尚,便讲个和尚。城里广福寺僧,他的口才伶利,没人说得他过。一天,在路畔小便,碰见个大律师,口才也来得,他刚买顶新帽子带着走来,瞧见某僧调侃他道:老和尚,你们师徒俩,在这里商量点什么事情?那和尚却不慌不忙回答他道:我们商量不出什么,正在这里量一量他的头寸,想买顶新帽子给他,等他还俗做大律师去。……”玉吾笑道:“这大律师也算自取其辱,我来讲个量窄的人,留客吃饭。”燕山听得,呆了呆,璧如神色自若。玉吾道:“那主人留的客,却两天没吃饭了。见着一粒一粒珍珠般的米颗,心花怒放,只管狼吞虎咽,一碗连碗的添。主人心里,痛得如丧考妣,苫块昏迷似的,那客人有些觉得,要想寻句话来拍拍他马屁,可是一时无机可乘,只得套着老调道:足下真今之小孟尝也。不料这句话,拍到马脚上去了。主人道是他再要想添饭,预先伸只后脚,不得不截住他道:你说我小孟尝,吾自觉得是个伍子胥。那客不懂什么,求他解释,主人笑着道:也没别有故事,不过想到伍子胥过昭关唱的两句‘你一添一添又一添,吾心中好比滚油煎’。那客不觉喷了一口饭,从此不敢再添。”玉吾说得燕山、璧如又羞又笑,璧如假意搭讪着道:“那有这一件事,心中滚油煎着,吃个鸡蛋下肚,顿时变个蒲包蛋,吃块肉骨头下肚,顿时变块五香排骨,真要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哩。”玉吾道:“这所以叫做无稽之谈,说说笑笑罢了。”
当下玉吾在璧如店里,吃过晚饭,璧如送玉吾回去,碰见福爷坐在书房里,面上罩着秋霜一般,两眼把玉吾瞪了瞪,将要骂出口,璧如趋上前去,抵挡替他编个谎,玉吾先接口答道:“我今天清早,碰见璧如兄,一同到他母亲家里,吃了中饭回来,他家老伯又苦留我吃了夜饭,才叫璧如送吾回家。”璧如听得把尼姑庵当他娘家,不禁又羞又恨,见福爷没有话说,两人退了出来。璧如把玉吾大腿上拧了一把,低低道:“你说鬼话,还要讨便宜,可称全无心肝的了。吾明天来问你。”说着自去。福爷停了一会,不免又走出书房,指着玉吾,数说一番。幸亏这当儿,忽有一个客来,福爷撇下玉吾,那客夜来拜访,总有急事,和福爷在书房里,剪烛谈了好一会。这客是谁,为的甚事?著者暂守秘密,诸君阅后自知。下面姑且另寻一条线索,牵到金小弟身上。小弟在城隍庙宿了一宵,走到福熙镇混了一日,垂晚又到积善寺去捉根云和尚的奸,强抢了一副被褥,卖去化用,又喝了三杯高粱,一路走向安乐村来。时黄昏已阑,月黯星稀,西风吹芦管,吁吁作声,俨如鬼泣。旁岸木叶滚滚,在惨月之下。百步外遥望,更像髑髅追人。寻常人当此。那得不心惊胆战。小弟凭三分酒力,毫不馁怯。走到将近村前,忽听得一缕幽细的哭,呜咽凄楚,若断若续。当下小弟把顶毡帽,推了推,露出额角,又拍了拍道:“吾活了二十六岁,从没见过鬼祟,难道今夜城隍奶奶跟我回来吗?阳世淫妇常有跟人逃走的,难道城隍奶奶也学起时髦来吗?哼!我小弟不怕,你来,我给颜色你看。”口中说着,在路旁小便一次,听听哭声越近,凄凄切切,酸人胸臆。那时四野弥漫,白杨萧瑟,和着那哭声的,只有一只夜鸱,接着苦啊苦啊的几声,小弟有点胆怯,只顾向前奔走。走过个绿荫浓郁的坟墓边,觉得哭声,就在这坟墓里发出来的。他不敢去瞧一瞧,飞奔而回,气喘着扒上牛棚睡去。一觉醒来,四望已是星移斗转,人静夜阑,忽一片西风,又夹着一缕哭声,吹到耳边。小弟细听很近,一时火发,自言自语道:“今宵那哭鬼,偏和吾作对,只管钉着吾哭,吾与他无仇无怨,倒要去问他个明白。”一骨落跳下牛棚,细迹哭声的由来,慢慢走过两三家门面,一个小窗子里,帖耳细听,哭声便在里面。
小弟从窗缝里细瞧,一个少妇,对着一盏孤灯,呜呜啜泣,那妇人头蓬眼枯,二十来岁,小弟认得是秦家寡媳,不知为甚如此伤悲?台上放个木主,对那木主亲夫亲哥,只管干号。听他哭到伤心之处,晕过醒来。小弟心中,倒也老大不忍,只得自去安息。看官尚忆前回书中,托金大上鞋子的秦寡妇么?此人要算得在下这部书中开头一个伤心人,身世之悲,惊心怵目。他母家倒也是福熙镇一家好好人家,只因父亲早亡,从小攀给炳奎儿子小奎为妻,不料过门之后,短短夫妻,只合得一年三月。当去年四月初二那一天,镇上循例迎神赛会,小奎夫妇俩,同返岳家,还嘻嘻哈哈一桌子吃饭。晚上小奎妻要想留他在母家,又恐闲人说笑,只好在房里握握手道:“你去吧,明晨一早就来,我亲自去买两尾你最欢喜吃的鲫鱼,塞了精肉煮你吃。”小奎道:“你娘说还有两个糟蛋留着,明天一起煮了吧。”小奎妻点点头。小奎又道:“你今晚为何不留我在这里?我们俩结婚以后,两床分睡,今晚还是第一遭咧。你在这里冷静吗?你冷静好和你娘一床睡,我回去又没娘,只好抱个枕子睡,你好忍心,逼我回去,唉!我回去了,非但明天不高兴来这里,永远不高兴来这里。并且你回来,我也不容你睡在一床了。”小奎妻把他手紧紧一捏道:“分睡一夜,有甚气苦?这里屋小,床只一张,留你,人家要说笑的。回去又没多路,跑跑有甚要紧?你说甚么回来也不和我睡,很好,各归各吧。江西人钉碗自顾自,你也难弗杀我的。”说着向小奎瞪了一眼。小奎伸手掠一掠妻子的鬓发道:“那么你送我一条田岸吧。”小奎妻道:“要好在心里,做到场面上,人家要说笑的,你趁早走吧,我不送你了。”小奎勉强别过丈母,慢吞吞走回去,小奎妻送过他一条板桥,立定脚,等他走远了,才跑到板桥面上,再回头望望,见小奎也正在回头远望,向妻子扬扬手。小奎妻心里,老大有点不忍。四望天色垂晚,没精打采走回娘家,胡乱吃过夜饭,心里记挂丈夫,重复走到桥上望望,已伸手不见五指。暗想这时候,小奎不知到家没有?心中兀自不安。当晚宿在娘家,已将近半夜,小奎匆匆走来,妻子道:“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奎笑道:“我何尝去过,我钻在你床底下呀!我和你睡在一头吧。”他妻子瞧瞧母亲,不知哪里去了,也就默许他睡下。小奎口中含一块薄荷糖,剩下薄薄一片,却还嘴对嘴喂到妻子口中。他妻子觉得这片糖,冰药似的苦寒彻骨,连忙吐出,起身把茶漱漱口,忽见母亲在床背后转出,觉得面上羞涩,忙叫小奎起身,让母亲睡。小奎走下床来道:“你好忍心啊,吾好好在被窝里,被你逼回去,从此你再莫见我的面吧,我和你永别了。”说罢,两条眼泪,挂在面前。小奎妻叫他道:“你说的什么话?”他并不回话,正要去拉他时,醒来原是一梦。这晚小奎妻未曾合眼,明日等了一天,小奎没来,心里委决不下,晚上不免走回家去,一眼瞧见小奎睡在床上,炳奎和医生正在商量药方。小奎妻连忙走近床前去问小奎,小奎此时,盖着三条棉被,满身汗如浴雨,热得人事不省。他妻子叫他,只摇着头。那医生对炳奎说道:“令郎阴虚夹邪,第一发表驱邪;第二寡欲养精。令媳最好叫他避避病人,因病人邪退之后,阴虚火抗,易犯色情,尤虚尤难治,非慎之又慎不可。”炳奎连连点头,送医生去后,叫媳妇前来,委婉曲折的说了一番,叫她明日仍还娘家,待病势退了些,再来接你。你要在这里,爱他实以害他。小奎妻没法,明日含了一包泪,仍还福熙镇来。只过得一日一夜,报信来说,炳奎叫媳妇快去。小奎妻尚未知病状好坏,听得巴不能插翅飞回,踏进自己房门,见小奎只剩一口气了。小奎见着妻子,已不能开口,两只眼睛,张得铜铃般。妻子叫他声:“小奎,你心里好过么?”他只把头点一点,接着一包眼泪泻了出来。两腿一伸,眼珠一插,那时随你千呼万唤,他已声息全无了。可怜只有二十二岁,子息全无。他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也是没用。炳奎自己虽进过学,家里未见十分丰裕,草草殓葬,埋在附近一个老坟上。自从小奎死后,炳奎口口声声,说是媳妇害死他的,把媳妇要骂便骂,要打便打。平日想起儿子,便骂媳妇,娼根淫货,无所不骂。小奎妻哭得形消骨立。炳奎骂她打她,她好像不曾觉得。中元冬至,捧碗麦饭,到坟上哭哭啼啼。她娘来劝她,也不能减她一分一厘的悲哀。当晚金小弟路上听得一缕幽细的哭声,便是这可怜的寡妇。那一天十月念七,正交冬至,日间和炳奎要钱,买点羹饭纸绽,炳奎非但不给,反把她大骂一顿道:“你害死了他,祭他哭他也是没用,还是你死掉,好让吾不想着儿子。你不死,吾总要想他,你快快去死吧!”小奎妻又悲又气,含着一包眼泪,跑回母家,烧几色菜,捧到坟上,哭奠一番,从午晌起,直哭到黄昏已尽,回到家里,索性把小奎木主,搬到房内,点一盏灯,插三枝香,把娘家带来两个糟蛋、两尾鲫鱼,供在前面,抽抽咽咽,哭诉着道:“这是你生前最喜欢吃的,你在阴间还想吃么?可怜哪!阴间还有人亲手煮你吃么?……我在娘家那天,逼你回来,你眼泪汪汪说,永不再来,这话真应了……可怜见你半路上对我扬扬手,谁想你对吾扬手之后,就永不见你的手,再对吾举一举。……便是你临死那只手,也不能再举。只有两包眼泪对我了。……你说我回来也不和我再睡一床,可怜你是怕冷静的,现在我苦命人,怎可来陪你呢?……你梦魂当夜便来见我,给片苦糖我吃,我就知不好,谁想你丢得我苦命人这样的快啊!……我一闭目,就见你的影子立在我面前,你知我苦命人活在世上,是没好处了,你快快来领我一同去吧。”当下秦寡妇哭得肝肠寸断,便是铁石人听得,也要下泪。她哭罢一会,只见灯焰像一粒谷,灯光晕作惨绿色,一室之中,冷彻毛骨,风吹纸窗,嘘嘘作声,她两只眼睛凝视在一盏灯上,觉得这一粒谷大的灯火渐渐张大开来,像顶火伞,伞里立一个美男子,笑眯眯对他招招手。她悲极了,见那美男子正是小奎,即便张着双臂,迎将上去,紧紧互抱着,豪啕大哭了一阵,小奎替她揩揩泪痕道:“你在人世,也没有什么生趣,快快随吾来吧。只是人世有爱情可讲,到这里便只好各归各,江西人钉碗自顾自。”她忽又大哭起来道:“这两句话,前天和你说说罢了,你怎还记得?我们俩是结发的恩爱夫妻呀,生睡一床,死同一穴,你在阴间,我来了怎好丢我呢?”小奎一声冷笑道:“你在阳间,黑夜尚且忍心逼我回去,到得这里,还要说什么夫妻结发之情么?那夫妻结发之情一句话,在人间世上,夫骗骗妻,妻骗骗夫,什么天荒地老,两情不渝,什么海枯石烂,此心不负,这话儿都是骗骗人的。现在我已是个鬼了,也不容你再骗。人世有爱情,阴间没爱情。你快快醒悟吧,我和你各走各的路去。”说着小奎把妻子一推,只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正是:
情缘转眼成虚幻,梁孟何曾到白头。
不知小奎把妻子推到那里,小奎妻走那一条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