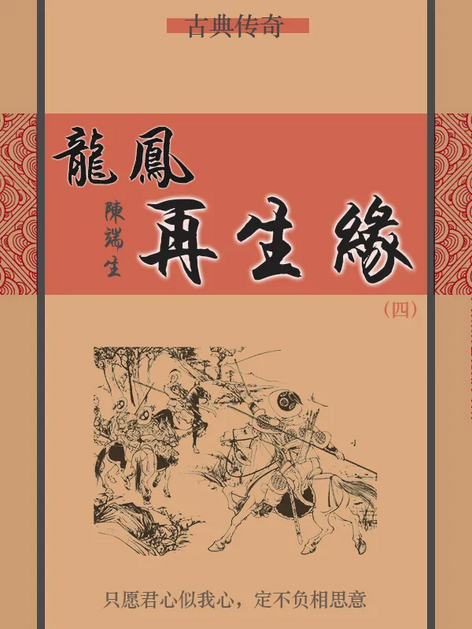却说太郡回归卧房,哭倒牀上。江三嫂教燕玉曰:“趁今太郡痛子之时,小姐可假意小心伏侍,太郡自然不忍使尔出嫁。”燕玉曰:“向来我曲尽女道,自是嫡母分别亲疏耳。”即时刻不离太郡牀前,百饯安慰。到次耳,太郡谓燕玉曰:“尔爹爹已把尔姻缘许配翟攀风,我又方寸俱乱。无心备办妆奄,只将前日出嫁物件与尔带去,待日后再行补足。”说罢,燕玉苦辞曰:“大哥夫妻远在边庭,二哥失陷娥巢,我若出嫁,母亲举目无亲。若要出嫁,须待大嫂回来,女儿方得放心。”太郡曰:“难得我儿孝心,如此极妙。”燕玉暗喜,加倍小心孝敬。
到第三日早饭后﹔女婢报曰:“二舅老爷前来请安。”太郡曰:“请他进来。”燕玉退出。须臾间顾宏义进入房来,太郡坐在牀上,令女婢移椅,请舅老爷坐下。茶罢,太郡曰:“痴儿好勇,自请出征,失陷贼巢,令我肠断。”宏义劝曰:“奎璧虽暂时失陷,姊夫必设计,不久自然回家,不必过虑。”二人说些闲话。宏义曰:“姊夫回书,甥女姻事已定,大约即要择日行聘完娶。”太郡大怒曰:“姊姊太无良心,我家现有横祸,还说甚亲事!尔做兄弟也不量力,何厚于彼而薄于此?”将手捶牀,大叫曰:“尔们要迫杀我!”顾宏义愧羞无地,只得说曰:“姊姊不欢喜便罢,何必发恼。”又说些闲话,方才辞别。燕玉小姐暗自欢喜。
过了五六日,顾太郡起牀,料理家事。忽报崔母来探,太郡迎接坐下,说了许多闲话。翟母曰:“大孩儿夫妻一月间便要进京,次孩儿亦欲进京捐监,侯来年考举,我又老迈,家无次丁,若二侄女相伴亦好。”太郡曰:“前日贤弟来说,我因无心料理妆营,既如此,如今就可择日而行。”崔母大喜。那燕玉偷听,惊得魂消魄散,奔到后楼,来见江三嫂,说出前情,求其速定计策救已。江三嫂只得安慰曰:“小姐不须着急,待我设计。”不多时,翟母辞别回去。
不觉又到第三日已牌后,顾宏义送日课前来曰:“崔家亦已择定四月十八日行聘,二十五日完娶,吩咐各物从便,不必费心。”太郡看了日课应允。宏义辞出。燕玉急推江三嫂:“五日后便要行聘,尔今计策若何?”三嫂曰:“我蠢人无计可施,且从容商议。”燕玉曰:“此乃缓兵之计,罢了,奴惟有一死,以保名节,免得忧虑。”江三嫂恐其自尽,乃曰:“计策却有一条,恐小姐难受苦楚。”燕玉问曰:“计将安出?”江三嫂曰:“我有一个胞妹,十七岁时,出嫁于张姓,妹丈忽然病故。吾妹自知命苦如此,决投在万缘庵削发为尼,法名赘如。伊师善灵,年已四旬,乃是庸中住持,师徒六人在庵。其庵名万缘庵,离此有十二三里路。不若尔我到庵中潜身,其庵中房屋甚多,未知小姐意见若何?”小姐道:“三嫂专说混话,庵庙寺院,乃庵人所到,俗女同居,动人疑心。倘被母亲知道,性命不保厂江三嫂曰:“这万缘庵虽供奉仙佛神祇,从无男人入庵点灯问筹,香火最是冷落庵内深远,房屋颇多。小姐须打算定方可前去。”燕玉曰:“我若守名节,虽死无恨。”江三嫂曰:“只可尔我阿走,太郡好洁,尔走恐辱坏家门,必不敢说起。”燕玉曰:“说得是。当密差尔先住,见善灵诈说如此如此,看尼姑肯收留否,免我优虑。”江三嫂曰:“尼姑贪财,闻得避难,必有银两,一定收留。待我着儿子前往问明。”燕玉曰:“证是,速当前去约定。”
江三嫂下楼,寻见江进喜,密把刘小姐欲同我避住万缘庵﹔伺候皇甫公子出头等情言明:“尔可往见善灵,不可说实事,只说如此如此,若肯收留,有些银两送她应用。”江进喜曰:“今小姐贞洁,天道必有好报﹔但善灵贪财,小姐并无大银两,难免受其欺侮,切不可往。”江三嫂曰:“我已说过,小姐但愿守节,虽死无恨。尔可往说个定着。”江进喜曰:“待我来朝前往。”言未毕,只见女婢从内出曰:太郡吩咐,四日后崔家要来行聘。”
过数日,到了四月十八日行聘日期,顾宏义着其侄顾本仁亦是文举人押聘前来,一路音乐喧天。太郡无心,收了聘礼,发了回聘回去。是晚赏了众家人花红,次日即整顿孟氏的嫁妆,赔嫁女儿。燕玉急着江三嫂催促儿子,速往万缘庵议定,来晚即欲避走。江进喜应允。
早饭后,进喜,拽开大步,急奔往万缘庵,正遇着善灵。问曰:“江大叔何事,如此着急?”江进喜曰:“要见姨母商议一事。”即进内寻见究如,曰:“有不事与姨母商议。”道:“贤侄请坐,有话说来。”江进喜坐在旁边,诈言曰:“刘燕玉小姐我太郡原许配皇甫家,今又改嫁翟家为妻。二小姐怎肯改嫁失节,欲寻死路。家母苦劝,是以家母欲同,小姐来到庵内避难,帮作女工﹔待皇甫家出头相认,自当重谢庵主,未知庵主可肯收留否?”焚如摇头曰:“鹿中香火冷落,庵主善灵又贫穷贪财,二小姐并无私房银两,到此定受欺侮,须寻别处安身,断不可到此地狱来。”江进喜曰:“善灵贪财。侄赤曾听说过,奈无别处可投。小姐仕愿守节,甘心同作针指度日。姨母同侄前去恳求善灵收留便好。”
赞如曰:“她若有利,无不应承,有何不肯之理。待我请她来说。”随出房门,顷刻间同善灵进来,江进喜见礼坐下。江进喜乃诈言太郡赖婚,二小姐同吾母要借此守节。善灵曰:“难得小姐节操,里面尚有两座房,并可安身。只是只有两张空牀,连席盖赤无,况吾等穷苦,菜羹蔬食,小姐须多带些银两葡来应用为妙。”江进喜曰:“吾家小姐日食最俭,女工针黹,板是嫡熟,到此便可帮作针黹。”焚如扫:“未知儿时来,亦当约定。”江进喜曰:“来晚二更后即来,劳烦师父开门。”善灵曰:“就是三更后前来何妨,我等自当守候。”江进喜辞别退出。
刘小姐首饰包做一拜匣,那百余两银子亦浅一拜匣,取下楼来。江进喜一路开门,直到庞园后门,共六重门。江进喜便拙衣服包裹灯笼放下,白广待我去牵一匹马来,与母亲小姐同乘。好得赶路尸燕玉曰:“极好,假不可使马夫知道。”江进喜去了一会,取了一匹青鬃马,鞍智俱备,牵出花园门,关上园门,先扶母亲上马,后扶小姐坐在前面。燕玉顶上盖着缎帖。
三人起身,行了里许路,再向前赶了一会,已到万缘庵前,即扶二人下马,,上前扣门。香公开门请迸,六个尼姑尚在伺候,一齐接进。后边有一座空房,迸内只见有两张空牀,连席苏无。江三嫂见这光景,问曰:“连席办无,如何安身?”燕玉曰:“来早自当备赤铺陈便是。”焚如曰:“我里面述有两领旧席。”卸去取出二领旧席,安顿牀上。江送喜把包裹放下,曰:“我要回去了,若有急享,即来通知。”燕玉曰:“难为尔了,被有急务,须当来报。”江进喜称是,出门上马面去。
当下燕玉与众尼始见礼,各通名号,开一个拜匣,一看却是藏首饰的,燕玉即解开螺包,秤了十两银子,放在一边曰:“此银留下,备二付键盖应用。”又秤下十两,送与众尼曰:“奴在此守节,有劳列位师父,权为一茶之敬,幸列位笑纳。”众尼大喜称谢。又将银交付善灵曰:“此是十余两银,付与婶父料理我等二人粮食,若有女工针黹自当尽心相帮。”善灵只望取许多银两,今见只有这些银子,甚为不便,只得接了。众尼退去安歇。
江进喜赶罔花园,将马仍带进玛房缚下,把锁并匙俱丢在地上。这花园只有江进喜住宿,从无他人混杂。当下江递喜回房,把门虚掩,解衣上牀假睡。
且说飞窍睡到五更醒来,有些腹疼,即忙起牀解手,火已熄了。飞蓄最是胆怯,遂要往江三嫂房中来取火,把门推开,残灯尚明,房中无人,只道在小姐房中,及到小姐绣房,门却虚掩,火尚未灭,小吏害怕,即点火燃照着,并无一人。随即下楼要报太郡,忽一阵狂风把火扑灭,那飞骂大惊,哭叫起来,即到太郡房中,便狂叫太郡不绝。
顾太郡亦已醒了,忽听得哭叫,吓了一跳,暗想时运已退,次子娥巢被陷,此所谓祸不单行,谅必是凶事。忙叫曰:“不频啼哭,快快前来。”即披衣坐起牀上。小婢已开房,飞茧进房,就说小姐及三嫂不知何往,只有小婢,故言害怕。太郡疑惑曰:“江三嫂或有事起身,亦未可定,小姐不在,却是何故?”叫起众婢,点灯奔上晓云阁,四处一看,并无人影,遂进小姐房中,开首饰匣一看,却暗自骇然曰:“莫非与人逃走,连首饰带去?”
再开箱看,好衣服俱失,只留几件旧衣裙,急得手足失措,明是家世该败,做出这败家声事来。太郡寻思,此必江三嫂代女儿牵马,奸夫方得进来,即下楼坐下,吩咐女婢,速唤江进喜前来。早有一婢起身前去。又嘱众婢曰:“家丑不可外扬,此事不可令家将知道,倘有多言漏泄,定即活活处死。”一面喝问飞鸯曰:“尔在楼上,可有男人上楼,快快说来,免得受刑!”就令女婢速取皮鞭荆条前来。飞骂曰:“哪有男人上楼,即女人亦不敢上楼。”太郡提起皮鞭,向桌一拍曰:“既无人上楼,小姐如何逃走了,再不实说,一定打死尔这贱人!”飞鸯放声大哭曰:“自在上年太郡带小姐往顾孵探亲回来,小姐就时刻与江三嫂密语,甚至叹息流泪,只是不许小婢窃听。近来京城国丈回书,许婚崔家,小姐更加着急,日夜同江三嫂密语。昨夜灯后、小姐叫小婢先睡,小婢只得先睡,不知小姐因何逃走,只此便是真情。”太郡怒曰:“江进喜因何不来?”再着一个女婢速去催来。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