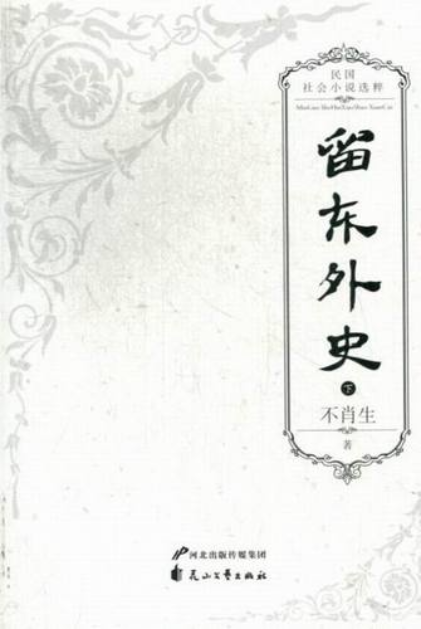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后三时,尘雾半天,阴霾一室。
此时此景就是不肖生兀坐东京旅馆,起草《留东外史》的纪念。
这《留东外史》是部什么书?书中所说何事?不肖生著了这书有何好处?说来话长,诸君不必性急,待不肖生慢慢讲来。
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读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第四种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诸君须知,此次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拼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在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此虽由于少数害群之马,而为首领的有督率之责,亦在咎不容辞。
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自顾于四种之中,都安插不下。既非亡命,又不经商,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倒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还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的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第一种、第二种,与不肖生无笔墨缘,不敢惹他;第三种、第四种,没奈何,要借重他做登场傀儡。远事多不记忆,不敢乱写。从民国元年起,至不肖生离东京之日止。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人有骂我者,则“不肖生”三字,生固是我的美名,死亦是我的佳谥,由他骂罢。倘看此书的,不以人废言,贝怀肖生就有三层请愿:一愿后来的莫学书中的人,为书中人分过;二愿书中人莫再做书中事,为后来人做榜样;三若后来的竟学了书中人,书中人复做了书中事,就只愿再有不肖生者,宁牺牲个人道德,续著《留东外史》,以与恶德党宣战。诸君勉之,且看此书开幕。
话说湖南湘潭县,有个姓周、名撰、字卜先的书生,四岁失了怙恃,依着叔父度日。他叔父原做木行生意;稍有积聚,中年无子,遂将周撰做自己的儿子教养,十六岁上替他娶了一房妻室。这周撰虽是在三家村里长大,却出落得身长玉立,顾盼多姿。笑貌既逾狐媚,性情更比狼贪。从村塾先生念了几年书,文理也还清顺。乙巳年湖南学校大兴,周撰就考入了陆军小学。当时清廷注重陆军,周撰实欲借此做终南捷径。奈他赋体不甚壮实,每到了操场上做起跑步来,就禁不住娇音喘喘,香汗淫淫。住了半年,觉得不堪其苦。
那年湖南咨送学生出洋,周撰就想谋一官费,然苦无门径。恰好他同学杨某,也因想得官费,求同县大僚某,修于封书,向湖北制台关说。那大僚作书的时候,原嘱杨某亲到湖北呈递,不料杨某的母亲病丁,不能前往。周撰知道此事,遂乘机诡言适有要事须往湖北。杨某不知是计,就托信与他带去。
周撰得了信,到私处拆开看了,就弄神通添了自己名字进去,径往湖北。投信之后,果然效力发生,得了一名留东官费,在日本混了几年。中国革命事起,留学生十九回国。周撰也跟了回去,在岳州镇守府,充了一名副官。那时岳州南正街茶巷子内,有一个同升客栈。这客栈的主人,姓翁,原籍浙江。夫妇二人,带着亲生女定儿,不知因何事到岳州,开此客栈,已有八九年光景。那定儿年纪虽在二十以外,然尚没有婆家,颇有几分姿色,远近有大乔的名目(岳州有小乔墓,故名)。
一日,周撰到栈内会朋友,无意中与定儿见了一面,两下里都暗自吃惊。周撰打听得是栈主女儿,没有婆家,想必可以利动,遂每日借着会朋友,与栈主通了几次殷勤。那革命的时候,在军界的人,谁人不怕?谁人不想巴结?况且周撰容仪秀美,举动阔绰,又是东洋留学生,栈主岂有不极力拉拢之理。
往来既熟,就时时与定儿眉眼传情。真是事有凑巧,一日,周撰到了栈内,恰好栈主夫妇均不在家,只有定儿一人坐在窗下。
周撰心中喜不自胜,忙跨进房去。定儿见是周撰,止不住红呈双颊,心中冲冲的跳动。慢慢立起身来,说了声请坐,就低着头一声不响。此时正是十一月天气。周撰看定儿穿了件竹青撒花湖绉羔皮袄,罩了件天青素缎坎肩,系条桃灰摹本裤,着了双纤条条白缎地青花的鞋;高高的挽了发结,淡淡的施了胭脂。
周撰见了这种娇羞模样,心痒难挠,也不肯就座,涎着脸儿挨了拢去,扯着定儿的手,温存说道:“定姑娘,发慈悲,救我一命罢!”定儿将手轻轻的摔了一下道:“周先生你待怎么?快放尊重些,外面有人听见,成什么样儿!”周撰乘他一摔,脱出手来,抱过定儿之颈,乘势接了个吻道:“我方才从外面来,一个人都没有。定姑娘依了我罢!”定儿道:“先生家自有妻室,何必枉坏了人家身子?快离开些,我爹娘就要回了。”说着,想推开周撰。周撰到了此时,哪里肯放她走,连忙辩道:“我家中虽有妻室,然我叔父无子,已将我承祧,本说还要替我娶房妻小。并且我家中妻子,现已害着痨病,想已不能长久,将来接了你回去,定将你做结发妻看待。如说了半句欺心话,敢发个誓。”说时,真个接着发了个瞒天大誓。定儿听了想了一想,也就心允意允了。事情才毕,翁老儿夫妇恰走了回来。见了二人情景,知道自己女儿又被人家欺负了。周撰怀着鬼胎,不便久坐,辞了出来,说不尽心中快活。翁老婆子见周撰去了,唤过定儿问道:“方才周先生说了些什么?”定儿将周撰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翁老婆子听了道:“少年人的话,只怕靠不住。你如信得他过,须要他赶紧请两个岳州正经绅士做媒,光明正大的娶了过去才好。这偷偷摸摸的,终不成个结局。”定儿答应了。
次日,周撰到了栈内,定儿就悄悄的和他说了。周撰忙点头道好。归到镇守府内,与同事的商量。同事中也有说好的,也有说定儿是岳州有名的养汉精,不宜娶她的。周撰胸有已成之竹,也不管人家议论,即着人请了岳州的一位拔贡老爷黎月生、一位茂才公周宝卿来,将事情对他二人说了,求二人作伐。
这二人最喜成人之美,欣然应允。翁家夫妇见有这样两个月老,知道事非儿戏,只一说即登时妥帖。也照例的纳采问名,择吉十二月初十日迎娶。周撰就在城内佃了一所房子,初三日就搬入新房子住了。也置办了点零星木器,使用了几个下人,将房子收拾得内外一新,居然成了个娶亲的模样。转瞬到了初十,周撰同事的来道贺的也不少,倒很费了几桌酒席打发他们。
定儿自过门之后,真是一对新人,两般旧物,男贪女爱,欢乐难名。周撰自初十日起,只每日里名花独赏,哪有心情去镇守府理事。如此过了十来日,这风声传到镇守使耳朵里去了。
起初还作不知,后来见他全不进府,只得将他的缺开了,索性成全了他两人的欢爱。周撰得了这个消息,不觉慌急起来,忙托了同事的柳梦菰与镇守使关说。这柳梦菰平日很得镇守使的欢心,这事他又曾赞成,周撰以为一说必有效验。第二日,柳梦菰走了来说道:“这镇守府衙门不久就要取消,镇守使不出月底,便当上省。你这缺就复了,也不过多得十几日薪水。”
周撰听了无法,只索罢休。
于是又过了十多日,镇守府果然取消了。同事的上省的上省,归家的归家,只剩他一人在岳州过了年。所发下的薪水,只用于两个多月,已看看告罄,天气又渐渐暖了起来。他去年归国的时候,已是十月,故没有做得秋季衣服。此时见人家都换了夹衣,自己还拖着棉袍,虽不怕热,也有些怕丑。又筹不出款来置办,只得与定儿商量,要定儿设法。定儿想了一计,要周撰将棉袍的絮去了,改做了一件夹衫。周撰依了定儿的计。
又过了半月,终觉手中拮据,想不出个长久的计划。
一日,那柳梦菰因公事到了岳州,知道周撰尚贪恋着定儿,就走到周撰家内。只见周撰靶着双鞋,衣冠不整的迎了出来。
看他容颜,已是眼眶陷落,黄瘦不堪,哪里还有从前那般丰采?
彼此寒暄了几句,周撰即叙述近来窘迫的情形,求柳梦菰代他设法。柳梦菰笑道:“只要你肯离开岳州,法是不难设的。现在咨送学生出洋,老留学生尤易为力。你从前本是官费,只求前镇守使替你说声就得了,仍往日本去留学,岂不好吗?”周撰也心想:再不趁此脱身,把什么支持得来?等柳梦菰去后,即入内与定儿说知,检了几件衣服当了,做上省的船费。定儿虽是难分难舍,然知道周撰手头空虚,断不能长久住下,没奈何只得割舍。次日,周撰果然上省,那时谋公费的甚是容易,所以周撰不上几日就办妥了。领了路费、执照,仍回到岳州,定儿接了,自是欢喜万分。二人朝欢暮乐,又过了半月。周撰遂和定儿计议,退了房子,将定儿寄养在同升栈内,与翁家夫妇约定一二年后回来搬取。翁家夫妇虽不愿意,然也没得话说。
这日,周撰写了船票,与定儿别了,就向东京进发。船上遇了几个新送的留学生,他们知道周撰是老居日本的,就说起有许多事要倚仗他的意思。周撰是个极随和的人,最知情识窍,即一口承应到东京一切交涉,都在周某身上。那些初出门的人,有了这样的一个识途老马,哪得不诸事倚赖?不几日到了上海。落了栈房,周撰即出去打听到横滨的船只,恰好当日开了,只得大家等候。第二日,周撰即买了副麻雀牌,逗着他们消遣。
他们问道:“我们在此又不能久住,专买副麻雀牌,斗不到几日,岂不可惜,难道到日本还可斗吗?”周撰笑道:“有何不可?我不是特买了带到日本去,买来做什么?若专在上海斗,租一副岂不便宜多着。”他们又问道:“听说日本法律禁赌很严,倘被警察查出了待怎么?”周撰道:“放心,决不会查出来的。日本禁赌虽严,然须拿着了赛赌的财物与骰子作证据,方能议罚。我们若先交了钱,派作筹码,如警察来了,只急将骰子藏过,仍做不知有警察来了似的斗牌如故。警察拿不着证据,必悄悄的去了。万一骰子收藏不及,被警察拿着了,也不要紧,我们只装作全不懂日本话的。来的警察问不出头脑,必将我们带到警察署去。我们到了警察署,切不可写出真姓名来。
他就登报,也不过写支那人如此这般的罢了。他既葫芦提的写支那人,则现在日本上万的中国人,谁知道就是你我?”那新留学生听了,都很佩服周撰的见识不差。几个人在上海盘桓了几日,买了春日丸的船票,到东京来。
不日抵了横滨,周撰带着新来的上岸,坐火车到新桥。唤了几乘东洋车坐了,兼拖着行李,径投早稻田风光馆来。这风光馆系中国人住的老旅馆。周撰拣了楼上一间八叠席子的房间住了(日本房间大小以房中所铺席子多少计算,每席长乒尺宽二尺五寸)。新来的各人也都定了房子。
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