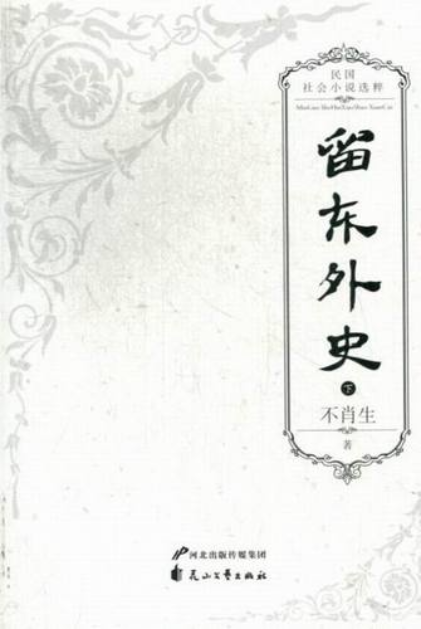话说李锦鸡和王立人谈笑了一会,各自安歇。次日;李锦鸡尚未起床,即有下女进来说道:“外面有个女学生来会,说要请李先生出去说句话。”李锦鸡大喜,连忙说快去请进来。
下女去了,李锦鸡起来拿了洗面具,想赶着去洗脸。下女已回来说道:“她说不进来了,请你将昨天遗下的书包给她,等着要去上课。”李锦鸡道:“等我下去请她。”说着趿了拖鞋跑到下面。藤子见了李锦鸡有些羞答答的,行了个礼。李锦鸡连说请进去坐坐。藤子笑着说道:“现正忙着暑假试验,下次来坐罢,请将昨日遗下的书包给我。”李锦鸡复请了几句,见藤子抵死不肯进来,当着人不便伸手去拉,两个对立了一会。藤子催着要书包,李锦鸡无奈,只得教她等着,自己跑上楼去,从柜里将书包拿出来。忽然心生一计,打开书包,将一个手写本留下,夹了一张自己的名片在教科书里面,照原式包好提下来,交给藤子笑道:“请打开看看,有遗失没有?失了尽管来这里寻找。”藤子笑着点头收了,并不开看,弯弯腰走了。李锦鸡知道她必再来,仍是得意,回房盥漱,用了早点,往邮局办交涉。写了张领钱的证,邮局自去回复赵明庵,以后交涉,自由赵明庵与李锦鸡直接,不与邮局及东乡馆相干。李锦鸡办完交涉,回到东乡馆,与馆主言明,伙食帐限三个月内陆续交还。馆主只要邮局的交涉妥了,伙食帐倒容易商量。李锦鸡的难关已过,归家一心一意的等藤子来接书。等了几日,竟没有影响。李锦鸡无法,仍立在上野馆门口等候。谁知各学堂已放了暑假,藤子不上课了。李锦鸡在神保院徘徊了几日,并不见藤子出来,怨恨东乡馆主不置。这段姻缘,不知何日是了。暂且将他搁住。
于今且说苏仲武,因高等商业学校放了暑假,久有意想去日光避暑。打点了盘缠,带子随身行李,由上野火车站坐奥羽线火车到宇都宫。换了日光线火车,五点多钟便到了。苏仲武虽没到过日光,因通语言,却没有什么障碍,拣了个极大的旅馆住下。这旅馆名小西屋,两层楼,有数十间房子,甚是精洁。
旅馆中下女,见苏仲武容仪韶秀,举止温文,不像日本学生粗鲁。衣裳固是阔绰,行李虽少,却是富家子旅行模样,因此招呼甚是周到。苏仲武因到馆日已向西,便想休息一夜,明早再去各处游览。当时脱了衣服,换件浴衣,往浴堂洗澡。洗完了回房,喝了口清茶,吃着雪茄烟,觉得神清气爽,绝不像在东京时的烦闷。坐了一会,抄着手踱出来,在廊檐下闲走了几步。
见天井里一个大金鱼池,池中养着许多的鱼,池旁摆了几盆花。
苏仲武换了双草履,走下天井,踱到池边。看那几尾鱼,在水藻中穿梭也似的游泳。心想:这鱼必因白昼太阳过烈,逼得它躲在水底不敢出来,此刻天已快阴了,水上有了凉意,它快活起来,所以成群结队的在藻里左穿右插。苏仲武正在凝思,忽见池里露出个美人的脸来,不觉吃了一惊。仔细看去,几尾鱼穿得水波荡漾,美人的面影也闪个不定。再看美人面旁,竖着一根圆柱。苏仲武心中疑惑,更仿佛现出楼阁的影子来,美人还在那里理鬓呢。苏仲武忙走过美人那方去看,楼阁美人都不看见了,却有许多的白云,在水中驰走。苏仲武凝神想道:我着了魔吗?怎清清白白的露出这些幻境来?再走到原立的地方一看,楼阁美人,可不是依然宛在?苏仲武一脚跨在池边,蹲下来定睛看去。一个不留神,将池边的土踏崩了一块,塌下水去,水花四溅,楼阁美人,又不住的荡动,弄得苏仲武眼花撩乱。偶一抬头思索,水中的美人,分明立在楼上,白云也分明在半空驰走,哪是什么幻境,竟是千真万确的眼前之景。苏仲武恍然大悟。看那美人,年纪约十六七,明眸皓齿,柳弱花柔,禁不住心中突突的跳个不了。立起身来仰面去看,美人并不理会,将脸倚着圆柱,凝想什么入了神似的。苏仲武目不暇瞬的看呆了,不觉得站了几多时间。下女叫他吃晚饭,才点头觉得颈痛。
苏仲武哪有心吃饭,胡乱用了点,又跑到天井里来看。只有那根倚美人的圆柱,还竖在那里顶着房檐,美人早不知何处去了。苏仲武怅惘了一会,心想:美人必是这馆里的住客,大约也是来避暑的。这样美人,不论她有知识没有,娶了她做女人,任是什么英雄豪杰,大学问家,也不能说辱没。我苏仲武长了二十二岁,并不曾见过这般的美女,虽到日本来,也曾尝试过几个,哪一个能称我的心愿?黄文汉人人知道他是老东京,偷香窃玉的本事,没人敢说不佩服。他引荐给我的,都算是很有美名的,哪里比得上这个十分之一?那些所谓美的,不过具美人之一体,有些动人的地方罢了。间有一两个稍完全的,又是妖冶之态,都摆在面上,没一点儿幽闲贞静的样子。矜贵的更是没有,只能使人见了动淫心,怜爱的心广点也不会发生,何能如这女子使人之意也消?等我慢慢的打听她住在哪房里,寻机会和她亲近亲近。若是有希望,我情愿为她破家。想念时,天色已晚。此时正是七月初间,一弯新月,早到天河。微风振衣,萧萧有凉意。缓步从容走到门外,月色溶溶,日光山如浸在水里。苏仲武想乘着月色去游,因恐不识途径,只在就近树木密茂的地方踱了一会。一心想再遇那女子,复走回馆。只在天井里来回的走,却怪那女子并不再出来。到九点多钟,苏仲武有些疲倦起来,回房安息。次早六点钟即起来,走到洗脸的地方,恰好那女子也正在洗脸。苏仲武喜极了,倒不敢过去同洗,生恐吓走了她似的。停了停步,复鼓起勇气,硬走过去。
那女子转脸望了苏仲武一眼,仍低着头洗脸。苏仲武被她这一望,虽觉是分外之荣,只是倒弄得手足无措。刹时间好像自己通身都是龌龊之气,很不配和这样美人同立着洗脸似的。放开自来水,只管低着头洗,望也不敢望她一望。二人都还没洗完,又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女子望着妇人说道:“妈,到这里来洗。”苏仲武听那声音,直柔脆得和吹箫一般。看那妇人,年纪虽有四十多岁,却还是个半老佳人,面皮甚是丰腻,相貌和女子有些相似,只身材略为高大。知道是母女,不敢再看,恐她疑心。匆匆忙忙的洗了,回房梳头,用了早点。思量今日去游日光山,看华严瀑,或者能分我一点想念之心。但是只要她不搬走,总有机会和她亲近。换了衣服,戴了草帽,乘着早凉,慢慢的向日光山走去。
苏仲武知道德川氏祠是最有名的祠宇,便先投这里来。走到阳明门,这阳明门便是德川氏祠的正门,屋瓦都用铜铸成,楹柱屋梁雕刻的人物花草,生动欲活。门式中间一层楼,左右有回廊,四角檐牙,悬着铜铃。此时火红的朝日,照在上面,和屋上的铜瓦灿然相射。天花板上画了两条龙,在那里吞云吐雾,日本的画龙名手狩野守信的手笔。苏仲武正看得入神,木屐声响,回头见来了两个日本人,都像是很阔的绅士。听得他们一边走一边笑着说道:“这门本是阳明门,本地的人,却都叫它日暮门,是什么道理?”一个说道:“你这都不懂得吗?这是说这门建筑得好。游观的人到了这里,就舍不得走开,必看到日暮。不看见了,才肯回去,所以叫作日暮门。”二人说笑着,已走到苏仲武跟前,打量了苏仲武两眼。苏仲武正愁一个人不知道这山上诸名胜的历史,瞎游一顿,没多意味。见二人打量自己,便连忙脱下帽子,点头行礼,二人也慌忙答礼。
苏仲武笑道:“我初次来日光,很有意探讨这日光的名胜。方才日暮门的出处,不是二位我还不知道呢。二位想也是来游山的,愿同行领教领教。请问二位贵姓?”二人对望着笑于一笑,点点头道:“听足下说话,想是中国人。我们也是来游山的。我姓上野,他姓松本。足下贵姓?”苏仲武说了。上野问道:“苏君来日本很几年么?这日光是我日本第一名胜之处,万不可不来游游。我曾来过多次,尽可以做足下的向导。”苏仲武点头谢了,同进了阳明门。走不到几十步,上野指着前面一座中国牌坊式的门道:“这门叫唐门。我日本从前凡中国式的东西,都加个唐字。这门都是中国的材料做的,又是中国的样式,所以叫唐门。”苏仲武看那门比阳明门要矮十分之二,屋上排列些铜铸的异兽,外面的柱雕着两条龙,一升一降,很有生气。
大约也是狩野守信画了刻的,刻工精致到了极处。内面柱上,也是雕着两条盘龙,两边狮子楣上,雕着许多古代衣冠的像。
上野指指点点道:“这是巢父的像。这是许由的像。这是尧舜禹汤的像。这是竹林七贤的像。”松本不待上野说完,拦住笑道:“你又不认识巢父、许由,为什么硬说是他们的像?”上野笑道:“巢父、许由哪有什么像留在今日?没说那时没有写真术,便有,也留不到今日,不过想象而为之罢了。”松本笑道:“你这话才糊涂。各人的想象不同,古人的像,不由各人心理而异吗?你只说是个木偶罢了,分别他们的姓名籍贯做什么?免得苏君听了笑话。他是中国人,中国的历史他是知道的,哪本历史说过有他们的肖像留在人间?”上野不服道:“你不要管我。前人姑妄作之,我便姑妄述之,有何不可?历史上的事原不足信,只是当闲话说说,也未尝不可。你定要凿穿来讲,又有什么趣味哩。”松本不做声了,三人都无言语。
瞻仰了一会,上野走前,到三代庙。这庙在日光二荒山神社之南,又名大献院。上野对苏仲武说道:“这庙是德川时代建筑的。庆安年间,德川家康公死了,遗命要葬这里,要因建了这庙。你看这仁王门,不都是朱漆吗?”苏仲武点头,看那左右设的偶像,庄严非常。上野问松本道:“你道这偶像是谁?”松本笑道:“我知道你又要任意捏造了。”上野笑道:“胡说。这也可以捏造的吗?你自己没学问罢了,怎的尽说人家捏造?这左边的是罗廷金刚,右边的是密迹金刚,后面的是二王像。你去问地方的耆硕,没有不知道的。”松本笑道:“你是个理学博士,怎的倒成了个博物学者?”上野笑了一笑,引着苏仲武走过二天门,迎面一道石级,足高十来丈。三人一步步登上去。苏仲武留心数着,有七十二级。行时苏仲武心想:上野是个理学博士,怪道举动这般文雅;松本想是个有些身分的人物,听他和上野辩论的话,很像是个有知识的。今日游山,得了这样的两位伴侣,倒不辜负。三人在大猷院游观了一会,都有些疲意,各拿出手帕,铺在地上,坐着休息。上野道:“日光山中名胜?除这两庙外,有中禅寺湖、雾降瀑、里见瀑、华严瀑、慈观瀑、德川家康的墓塔。瀑布中惟有华严瀑最壮观,由中禅寺湖水鞺鞳直下,高七十五丈,关东第一条大瀑布。瀑布之下,断崖千尺,亘古以来,人迹不到。去看瀑布的,都得攀萝拊葛,一步步爬上去,我们穿木屐的去不得。雾降瀑有两层,上层名一之瀑,下层名二之瀑,高三十多丈,宽只有三丈。只慈观瀑最宽,有九丈,里见瀑也只有八丈。这些胜处,我都去过十来次。中禅寺湖边有旅馆,我前年在茑屋(旅馆名)住了个多月。苏君你住在什么旅馆?”苏仲武道:“小西屋。”上野道:“我住在会津屋,隔小西屋不远,你若图在中禅寺湖荡舟,还是住在湖旁边的好。中禅寺湖与箱根的芦芦湖不相上下,我日本谓之东西二胜。你既到了这里,可慢慢的领略一日两日工夫,也游观不尽。此刻已将午了,我要归家午餐了。”说着起身。松本也立起来,和苏仲武点点头。走下石级去了。
苏仲武本是一人来游,原有很高的兴致;自遇了二人,游兴愈烈。二人虽去,应该还存着原来的兴致。作怪得很,二人一走,苏仲武游兴一点没有了。立着四处望了一会,不知往哪去的好。此时一轮红日当空,地上热气烘烘的不耐久立,思量不如归去的好。现在那女子不知道怎么样,回去或可遇点机会。
归心既决,便由旧路走来。心中计算女子的事,也无暇流览景物。回到小西屋叫下女来问,楼上有空房没有,下女应道:“有一间八叠的,不过当西晒。”苏仲武道:“不妨事。你将我的行李搬过去。”问明了房号,自己先上楼来,周围看了一看,见八叠房对面房间门外放着一双拖鞋,是早间洗脸时低着头见那女子所穿的,知道住在这房间里。见外面没人,便从门缝里张了一张。见那女子斜躺在席上,手中拿着一张新闻在那里看。
苏仲武不敢久窥,轻轻退到自己房里。下女搬好了行李,即开上午餐来。苏仲武想问对面住的女子姓什么,恐怕下女见笑,停了嘴不问。然而心中总是放不下去,忽然得了一计,问下女道:“这馆子里住了多少客?”下女道:“共有二十多位。”
苏仲武道:“有名册拿来给我看看,可有熟人住在这里。”下女答应着去了。苏仲武才吃了几口饭,已将名册送来。苏仲武记得对面是二十五号,即放了筷子,接过来翻看。二十五号的格子内写着加藤春子,下面还写着“梅子”两个略小的字。春子旁边注四十三岁,梅子旁边注十六岁。苏仲武记在心里,故意随便翻了一翻,交给下女道:“没有熟人,你拿去罢。”下女捧着去了。
苏仲武吃了午饭,躺在席上冥想。她母女住在一房,有话如何好说?须设法将她吊到僻处地方才能说话。这事情急切不能成功,得从容和她调眼色,有了几分光,再写字给她,看她如何。可惜在东京时不曾带几个匹头来,暗地送她。我手上的戒指,是我母亲给我的,送她有些不便。但是只要有心对我,肯受我的,便送了她,也没要紧。想时太阳已渐渐的由窗子里钻了进来,房中热腾腾的。躺着出了些汗,坐起来揩干,走出房外,顿觉得凉爽。就靠着栏杆立着,看太阳正照着对面的门,映得那房间里都是红的。心想:这样的日光,隔着窗纸,照在她脸上,就是朝霞,料也没有那般鲜艳。可惜我无福,不能消受。更想到她昨日倚柱凝神的情景,尤欲销魂。低头看池中的鱼,又都浮上水面,和昨日一般在水藻里穿插。正在凝想的时候,猛听得对面门响。急抬头,见梅子从斜阳光现出来,云鬓不整的更妩媚有致。只恨阳光射注她的眼帘,致她不能抬头望自己,低着头走向楼下去了。苏仲武料她是往厕屋里去,心想:去厕屋必从洗脸的地方经过,我何不借着洗脸,到那里去等她出来?连忙进房拿了条手巾,跑到洗脸的所在,面向女厕屋的门站着。不一会,开门出来了,见苏仲武望着她,羞红了脸,低着头走了几步。偶抬头看苏仲武,恰好苏仲武的眼光并没旁射,钉子一般射在她面上。梅子急忙将脸转过去。苏仲武因她转脸过去,得看见她笑靥微窝,知道她低鬟忍俊,真是心喜欲狂,故意轻轻咳了声嗽。梅子复望了一望,微笑着低头走过去了。
日本女人喜笑,中国女人喜哭,本成了世界上的公论。梅子的笑,本不必是有意于苏仲武。只是苏仲武因她这一笑,便如已得她的认可状似的,凭空生出许多理想上的幸福来,下手的胆也放大了。只调了两日的眼色,二人居然通起语言来。彼此略询家世,梅子是爱知县人,同住的是她母亲,家中颇有财产。她母亲因她父亲在外面置了外室,不时归家,和她父亲吵了几次嘴,赌气带子她到日光来,想借着日光名胜,开开怀抱。
梅子天真未凿,也不管苏仲武是外人,家中细事,一点一滴都说出来。苏仲武以为她很爱自己,所以无隐不白。用言语去挑拨她,她又不解,然也知道怕她母亲看见,叮咛嘱咐的不许苏仲武见她母亲的面。苏仲武知她有些憨气,想拉到自己房里来强污她,她却和知道的一般,抵死也不肯进房。弄得苏仲武无法,便冒昧和她提出约婚的话。梅子连忙摇头道:“不用说,我母亲必不许可。我母只我一个女儿,岂肯将我嫁到外国去?”苏仲武道:“只要你愿意,你母亲不许是容易说话的。”梅子道:“我虽有些愿意,只是我母亲不容易说话。你不知她老人家的脾气,和人大是不同,最不好商量的。”苏仲武道:“这事她或者容易说话也未可知。”梅子道:“没有的话。我不要你和她见面,就是为她的脾气不好。她最不欢喜模样儿好的男子,她说模样儿好的男子,爱情总是不能专一,倾家荡产,抛子撇妻,都是因模样儿生的好原故。你的模样儿,她见面必不欢喜。”苏仲武知道她母亲理想,必是因她父亲生得好,在外面游荡的日子多,这议论是有为而发的,对他人必不尽然。
因将这意思说给梅子听,梅子道:“不是,不是,她确是不欢喜模样儿好的。生田竹大郎面貌生得好,向我求婚,我父亲已要允了,她硬说不愿意,毕竟没有成功。”梅子说完了,觉得有些后悔,不该逞口将事说出来,急得红了一阵脸。苏仲武也觉得梅子痴憨得有趣,想娶她的心思益发坚了。只是据她这样说法,不知将如何下手才好。独自思量了一会,实在一筹莫展。
忽然想道:我何不回东京一趟,和黄文汉商量,看他有什么妙法?他最惯和人办这样事的,时常对我吹牛皮,说无论什么女子,只要安心去吊她,没有不成功的。横竖我守在这里也没有方法,再过几日,或者她们回爱知县去了,更无处着手。主意已定,即乘便和梅子说知暂返东京,梅子也似不解留恋。苏仲武即束装坐火车到东京,归家放下行李,即去玉名馆访黄文汉商量办法。
著书的写到这里,却要效小说家的故智,赶紧要的关头将笔搁住,引看官的眼光,到第三集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