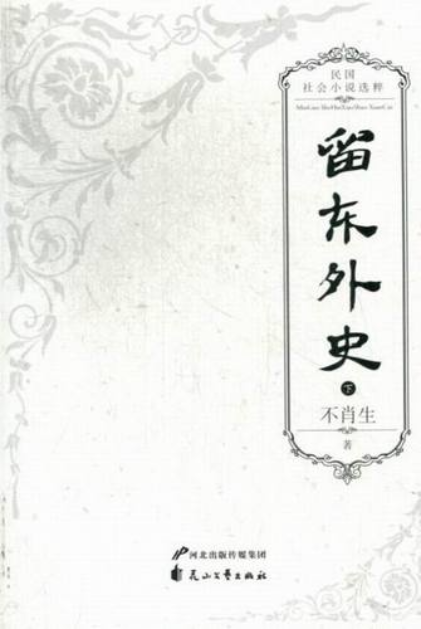话说黄文汉吃得大醉,睡到半晚两点多钟才醒来,喝了几口冷茶,仍旧睡下。天一明,伏焱即进房推黄文汉道:“中山的船七八点钟的时分便要泊岸,我们须早点去等。”黄文汉道:“我只在火车站等便了,你上船去,宫崎他们必是要上船的。人太多,我跟着挤无味。”伏焱想了想不错,便不多说,自去料理。黄文汉也起来洗脸。下女见了他,便笑嘻嘻的跑。黄文汉也自觉昨晚的事好笑。吃了饭,这些人都纷纷往码头上去。
伏焱招呼了黄文汉一声,也去了。热哄哄的一个旅馆,登时鸦雀无声。黄文汉慢条斯理的穿好了衣出来,几个下女都赶来送。
黄文汉笑着说了几句骚扰的话,举手为别。跳上一乘车,叫拉到火车站,就坐在车站里等。等得火车到,恰好一大群人拥着孙先生来了。日本政府早预备了特别车,这些人即拥孙先生上去。黄文汉见刘天猛并未穿礼服,也钻进了特别车去,不觉好笑,自己便跳上一等车坐了,即刻开车。午后换船过了门司海峡,在门司的中国商人,都排班在码头上欢迎。日本人男女老少来欢迎的,来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孙先生上岸,举着帽子,对大众答了礼,跨上自动车。到长崎欢迎的中日人士,或坐马车。或坐自动车,或坐东洋车,都跟着孙先生的自动车往车站进发。黄文汉也坐了乘东洋车,在上面左顾右盼。见两边粉白黛绿的夫人、小姐、艺妓、下女,充街塞巷。有两个艺妓在那里指手画脚的说笑,恰好黄文汉的车子挨身走过,听得说道:“前面坐自动车的便是孙逸仙,好体面人物。”黄文汉暗恨车夫跑得太快,没听得下面还说了些什么。转瞬到了车站,已有火车在站上等着。中日贵绅大贾,在那里候着的也不知有多少,齐拥着孙先生上了特别车。黄文汉就在相连的一乘一等车上坐了。看那些来看孙先生的,还是络绎不绝,竟到开车,挤得车站满满的。每人用手举着一顶帽子,那手便不得下去。
万岁之声,震山动岳。车子走了多远,不看见人影,方不听得声响。
车行到五点钟的时分,黄文汉有些倦意,正待打盹,忽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穿着礼服,黑瘦脸儿,几根疏疏的胡须,分着八字,手中拿一本袖珍日记,一张白纸,写着几个寸楷字,从特别车里走到一等车来。肩膊耸了两耸,望着黄文汉对面坐的一人点了点头,坐拢去,口中说道:“讨厌,讨厌。我忙极了的人,定要派我来欢迎什么孙逸仙。戴天仇那该打的东西可恶,做出那种骄傲样子。孙逸仙也不像个人物,袁世凯到底好些。”黄文汉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真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方才的瞌睡不知抛往哪儿去了。拔地立起身来,指着那人说道:“你才说什么?我虽是中国人,你的话,我却全然懂得。孙先生到日本来,并没有要求你来欢迎。既不愿意,何必来?戴天仇对你有什么失礼,何不当面责问,要出来对着大众诽谤?就是诽谤人,也须有个分际,何得说出那种丑话来?你且说,你来欢迎,是团体资格,是个人资格?”
那人见黄文汉起身指实自己说话,知道自己失了检点,吓得翻着双眼望了黄文汉。听黄文汉说完了,忙抽了张名片出来,起身递与黄文汉,用中国话说道:“先生请坐,先生误会了我的话。我是大阪每日通信社的记者,叫中川和一。戴天仇因与我往日有隙……”黄文汉不接名片,止住道:“你用日本话说,我懂。”那人仍用中国话说道:“先生请坐,等我慢慢说。我到过贵国多年……”黄文汉始终用日本话道:“谁问你的历史?戴天仇与你往日有嫌隙,你是个男子,当日不能报复,背后诽谤人,算什么东西!这个我且不问你,戴天仇本也不算什么人物。但是同孙先生来,你也应得表相当的敬意。你知道孙先生是中华民国什么人,可能由你任意诽谤?你是个新闻记者,怎么有这种不懂礼节的行为?”那人还是用中国话说道:“先生请坐,不要动气,有话好说。”同车坐了许多日本绅士,都望着他二人,不好拢来劝解。一个车掌走拢来,劝黄文汉坐。
黄文汉叱了声道:“你无劝解的资格,站开些!”转身逼近那日本人道:“你有什么理由可辩,就说。没有理由,就当着大众赔礼。不肯赔礼,就同到孙先生那里去,说明我和你决斗就是。怎么样?”那人听得要决斗,登时变了脸色,忙用中国话说道:“我赔礼就是,求先生恕我说话鲁莽。”黄文汉冷笑了一声道:“你既知道赔礼,求我恕你鲁莽,就饶了你罢。”回头指着自己的手皮包,对车掌道:“替我送到二等车去。这种卑劣东西。谁屑与他同坐!”说完,取了帽子,同车掌忿忿的走到二等车坐了。
次日午后九点多钟,安抵新桥驿站。黄文汉从窗眼里往车站上一望,吓了一跳。车站上的人哪里像是来欢迎的呢,竟是有意来凑热闹罢了。就是天上有数十条瀑布倾了下来,有这些身子挡住,大约也没有一点落在地下。孙先生一出火车门,犬养毅、柴口侯爵等一班贵绅就围裹拢来。站得远的人,都争先恐后。孙先生用手举着帽子,被人浪几推几拥,转瞬即卷入漩涡之中,哪里还能自主?戴天仇、马君武等五个随员,都被冲散。黄文汉下车,同卷了出来,隔着孙先生不远。才出车站门,只见刘天猛同一个穿军服佩刀的中国军人,强捉着孙先生的手臂,从众人中奋勇冲出,拥上了一乘马车。那时来欢迎的几千留日男女学生、商人,及日本人来欢迎的、来凑热闹的,从车站门口排起,十多层,径接到电车路上。中间分出一条路,马车即从路上跑去了。哪晓得那马车并不是接孙先生的,接孙先生的是一乘自动车,上面插了五色旗子。欢迎的人,都注定了那乘车,一个个要等那乘车子过,才行礼,叫万岁。马车过去,故都没有留意。及马君武和戴天仇挤出来,孙先生早已不知去向,料得是先走了,便跨上那插旗的自动车。那车呜呜的叫了两声,开起便走。幸喜夜间看不真面目,欢迎的认作是千真万确的孙先生,都行礼,霹雳般的叫万岁。戴、马二人居之不疑,便偷受了这般隆礼。黄文汉在背后看得清楚,心中暗恨刘天猛与那穿军服的不是人。欢迎的人见自动车已去远,才一队队的走散。
黄文汉不见伏焱出来,便站在僻静处等。见许多的贵绅飙发潮涌的出来,马车、自动车、东洋车,嘈嘈杂杂,纷纷扰扰,闹个不清。知道伏焱必在内同去见孙先生,用不着自己,便不去找他。望着大家走了八成,正待要走,忽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国人,穿着先生衣服,又胖又矮,满头油汗,慌手慌脚,口中操着英语,上跑到下,下跑到上的找人问话。恰好一个西洋人走来,那人如获至宝,谈了几句,西洋人找着驿长,用日语说:“这人是孙先生的秘书官,初次到日本,挤失了伴,不知路径,因在美国多年,本国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好,所以用英语问路。”驿长听了,忙着人叫马车,送到日比谷帝国旅馆去会孙先生。黄文汉听得,笑了一声,离了车站,回代代木,到家已是十二点钟。安歇无话。
次日午后伏焱来道谢,黄文汉问昨晚何以刘天猛同那军人挟着孙先生走,秘书官何以那般慌手慌脚。伏焱道:“中山原不认识刘天猛,那军官也不认得是谁,因被人挤得立脚不住,回头看随员不见一个,心中便有些不自在。刘天猛和那军人知道日本小鬼素来无礼。那年俄国皇太子(即现在的俄皇)来日本,无缘无故的中了一手枪。李鸿章在马关定条约,也冤枉受了两枪。恐怕中山这回来,又有意外,故紧贴住中山左右。见中山回顾了两次,一时神经过敏,便一边一个挟着中山跳上马车便跑。那秘书官却是好笑,我也没有问他姓什么。我正到帝国旅馆不久,见他坐马车来了,一见了中山,开口便道:‘好危险、好危险。我以为你们中了炸弹。’中山忙问:‘你这是什么话。’他指手舞脚的道:‘那停车场上,白光一闪,轰的一声炸弹响,你们没有听得吗?’中山笑道:‘你该死。在美洲这么多年,连夜间摄影用镁你都不晓得吗?’他才明白了。”
黄文汉听了大笑起来,说道:“中华民国地大物博,就有这种怪人物。今日报上五个随员都有名字,我记得是戴天仇、马君武、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五个。戴、马二人,我亲眼见他坐自动车跑了。这三个,我不认识,矮胖子必是三人之一。”伏焱笑道:“管他是哪个,知道这笑话便罢了。这种无名之英雄,就调查出来,也不过如此。”黄文汉点头道是。伏焱道:“明日午后一时,留学生在日本青年会开欢迎会,你去么?”
黄文汉道:“去听听也使得。”伏焱道:“早点儿去才好,不然,恐怕没有坐位。”黄文汉应了,伏焱别了回去。
第二日,黄文汉吃了早饭,便到神田来,计算着到刘越石家吃午饭。他与姜清、胡庄、张裕川都认识,见了面也是无所不谈,不过少共嫖睹罢了。这日四人都在家,黄文汉会着,笑谈了几点钟往长崎欢迎孙先生的事。吃了午饭,都同到美土代町青年会,就是姜清演戏的所在。那会场楼上楼下,也是一般的挤得没有多少空隙。有些想出风头的人,见孙先生未到,讲台空着,便借着这机会,上场去演说,图人叫好。于是你说一篇,我争一篇,他驳一篇,都好像有莫大的政见,只怕孙先生一来,说不出口,非趁这时机发表不可似的。如此犬吠驴鸣的,闹了两点多钟。孙先生一到,才鸦雀无声。主席的致了欢迎词,孙先生上台。那满场的掌声?也就不亚于去年除夕,不过少几个发狂叫好的罢了。孙先生的演说词,上海报纸有登得详悉的,难得细写。胡庄听到“中华民国正在建设时代,处处须人。诸君在这边无论学什么,将来回国,都有用处,决不要愁没有好位置”的话,已不高兴,心想:我们开欢迎会欢迎你,倒惹起你来教训人。你知道我们都是将来回去争位置的吗?未免太看轻了人家的人格。更听得掌声大作,哪里还坐得住,赌气走了出来。暗骂这些无人格、无脑筋、无常识、无耳朵的东西,只晓得拍手便是欢迎。一个人归到家中,闷闷不乐。下女近前调笑,也不答白,只叫热酒来,靠着火炉,自斟自饮,深悔不曾喊姜清同出来。
不一刻,姜清回了,说被掌声掩住,并没有听得孙先生几句话。胡庄道:“散会没有?他们怎的不回?”姜清道:“孙先生已下台,恐是去了。跳上了几个不知姓名的人,在那里演说,我懒得听,就回了。老刘说同黄文汉到代代木去,老张不知挤到什么地方去了,大约就会回的。你怎么跑回来就吃酒?”胡庄道:“我听了不高兴,天气又冷,不如回来吃酒的快活。你也来吃一杯。”姜清摇头道:“不吃。”胡庄道:“我问你,昨日下午同你在神乐坂走的是哪个?”姜清吃惊道:“没有,我不晓得。”胡庄道:“不是你,就是我看错了。那个女子,我仿佛前晚在新桥欢迎孙先生的时候,见她隔你不远站着,时时拿眼睛瞟着你。”姜清道:“我不曾见。”胡庄道:“可惜你那晚没和我同回,我在电车上遇了个极美的女子,你见了,必然欢喜。”姜清道:“谁教你走那么快,瞥眼就不见你了。”胡庄道:“你这就冤枉死人。我们让女学生先走了才走,那时候哪里有你的影子呢?你不用瞒我,你的举动,我尽知道。”姜清低头不做声。胡庄拉了他的手,温存说道:“你告诉我是谁,我决不妨害你。”姜清忽地改变了朱颜,摔手道:“你不要把朋友当娱乐品,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说是不说的。”胡庄忙作揖赔笑道:“你就是这种公子脾气不得了,动不动就恼人。我方才又没有说错话,你不欢喜听,我不说了就是,动气怎的?”姜清道:“你分明把我当小孩子,你既说尽知道,何必再问?爽爽直直的问也罢了,偏要绕着道儿,盘贼似的。谁做事负了,要告诉人的责任么?”胡庄笑道:“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要依你的见解说去,我一片好心,都成了坏心了。我平日对别人尚不如此。我是因他人在你眼前说话,每每惹你动气,故过于留神。我何尝不知道爽直的问好,只是问唐突了,你又怎么肯说?”
正说着,张裕川回了。胡庄忙换了几句别的话。接续说下去。张裕川进房坐了,大家烤火,说老刘散了会同黄文汉去了,今晚不得回。胡庄起身,到厨房看下女弄饭。这时候的下女,与刘越石、张裕川都脱离了关系,一心一意的巴结胡庄,差不多明目张胆同睡。刘、张虽有醋心,奈不是胡庄的对手,更兼下女偏向胡庄,只得忍气丢手。当晚吃了饭,三人闲谈了一会,安歇。
次日,李锦鸡来邀打牌,姜清不去。胡庄与张裕川三人同到东乡馆,加入一个锦鸡的同乡赵名庵,四人打了一天的麻雀,收场时约了次日邀刘越石再来。第二日真个又打了一天,至午后十一点钟才散。胡、刘、张到家,已是十二点钟。外面北风异常紧急。都各自睡了。胡庄拥着下女,正在不亦乐乎的时候,猛听得警钟铛铛铛敲了四下,知道是本区有了火警,忙披衣起来。接连又听得四处警钟乱响,一个更夫敲着警锣,抹门口跑了过去。下女吓得慌了,拉了胡庄叫怎么得了。胡庄道:“不要紧,你快检东西,我到晒台上去看看远近。”即跑到隔壁房将刘越石推醒,说隔壁发了火,快起来。刘越石从梦中惊觉,听得隔壁发了火,即扒起来,一手拖了件皮袍子,一手挟了个枕头要跑。胡庄拦住道:“乱跑不得,同我到晒台上去看看。只要人醒了,是没有危险的。”刘越石才放了枕头,穿了皮袍,同上楼。姜清已被惊醒,喊起了张裕川,四人同上晒台。那北风吹得连气都不能吐,只见红光满天,出火焰的所在,正在三崎町。胡庄道:“不相于,无论如何,烧不到这里来。小姜,你看那几十条白光在那里一上一下的,是什么?”刘越石、张裕川都聚拢来看,姜清道:“是消防队的喷水,”胡庄道:“啊呀,火烧过了街。老罗、老张那里只怕难保,等我快去替他搬行李。你们不要慌,西北风这里是不要紧的。”说罢匆匆下楼,只见下女打开柜子,七手八脚的在那里检行李,铺盖都捆好了。胡庄忙止住道:“不要检了,隔的很远。你上晒台去看,我要去招乎个朋友。”说着,披了件雨衣,开门到外面,叫下女将门关好,急急走到神保町。
那火光就在面前,沿街的铺户都搬出了家计。街上的男女老幼,提的提,担的担,挟的挟,一个个两手不空,来来往往的混撞。那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那烈焰腾空,只听得劈劈拍拍一片声响。任你有多少消防队的喷水管,就如喷的是石油一般,哪里能杀它千万分之一的威势呢!胡庄见三崎町、猿乐町两边分着烧,哪敢怠慢?三步两步窜到表猿乐町张全门首,见已围着几个中国人,每人背着一件行李,只叫快些出来。即听得楼上罗福的声音喊道:“我这口箱子太重了,搬不动呢。”胡庄分开人,钻进去道:“呆子,我来替你搬。”张全挟了个很大的包袱,迎面走出来,几乎被胡庄撞倒,忙退一步道:“老胡吗?来得好。我还有东西,请替我接了这包袱,我再进去搬。”罗福又在楼上叫道:“老胡,老胡,你快来帮我。”
胡庄连靴子跳了进去,几步窜上楼,只见罗福一身臃肿不堪,提脚都提不动似的,站在那里望着口皮箱。胡庄一手提着放在肩上,问道:“还有什么没有?快走,隔壁家已着了火。”罗福道:“你先走,这挂衣的钉子我摇去。”胡庄听了,也不做声,迎面就是一个巴掌道:“还不给我快滚下去!”罗福才一步一步的扭下楼。胡庄跳到外面,一看张全他们都跑了,隔壁的屋角上已烘烘的燃了起来,照耀得四处通红,只不见罗福出来。胡庄着急,翻身进屋,只见他还坐在那里穿靴子,左穿穿不进去,右穿也穿不进去,拿着双靴子,正在那儿出神呢。胡庄气急了,劈手夺了靴子,往外面一丢,拖了他的手就跑。才出巷口,回头看那房子,已燃了。胡庄道:“快跑!对面的火又要烧来了,暂且同到我家里去。”说完,驮着箱子先走,叫罗福快跟来。罗福答应晓得,胡庄跑了几丈远,回头看罗福又退了后,胡庄骂道:“你怎的空手也跑不动呢?”罗福忙跑了几步道:“来了,来了。”胡庄见他跑得十分吃力,身上又这般臃肿,疑心他这几日病了,便用左手掖住他的右手,拖着跑,累得一身大汗。到了家,放了箱子,进房脱衣,用手巾抹汗,坐着喘气,罗福才慢慢的走进房来。胡庄见他并没有病容,正要问,楼梯响,刘越石、张裕川走下来道:“好看,好看。”
罗福掉转身,道:“还烧吗?”刘越石走近前,打量罗福道:“你身子怎的这么大哩?”罗福道:“多穿了几件衣,待我脱了。”说着解开腰带,脱了外面的棉和服,三人看他里面,穿的是一身冬洋服。脱了,又现出身秋洋服来,脱了,还是很大。
接连脱了三身卫生衣,才是里衣裤。三人都纳罕,问他怎么穿这么多,他说箱子里放不下,穿在身上免得跑落。胡庄气得笑道:“你这种人,真蠢得不可救药。”便朝他脚上一看道:“你没有穿靴子,怎的袜子还干净哩?”罗福道:“已脱了双丢在门口。我这里还有几双。”说着,坐在席上,一双一双的脱了下来,足足的十只。胡庄笑了一声,懒得理他,一个人上楼。到晒台上。见下女呆呆的站着看火,远近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
消防队用喷水管?只在近火的人家屋上乱喷。那火越延越远,满天都是火星飞舞。大火星落到一处,即见一处上黑烟一冒,随着喷出火焰,连风又卷出许多火星来,在半空中打几个盘旋,疾如飞隼。扑到别家,别家又是一样的,先冒烟后喷火。最坏事的就是神保町几十家书铺,那着火的书,被风卷了出来,才是厉害,飞到几百步远,还能引火。一家书铺着火。半空中即多千百个火星,冲上扑下。时而一个大火星冲上来,风一吹,散作几十百个。时而几十百个小火星,待扑下去,风一卷,又聚作一团。平时东京发火,有几区的消防队凑拢来,都是立时扑灭。这回东京所有的消防队到齐了,灭了这处,燃了那处。
有些当风的地方的消防夫不是跑得快,连自己性命都不能救,莫说救人家的房屋。警察也吓慌了,还讲什么秩序,昏了头,跟着避火的人乱跑。起初那些近火之家,一个个望消防队努力救熄,愁眉苦脸的搬东西。后来见消防夫都几乎烧死了,倒索性快活起来,部忘了形,不记得搬东西。只张开口望着火笑,烧近身,又走退几步。哪一处火大,便哪一处笑的人多。
胡庄忽想起怎么不见了姜清,即问下女姜先生到哪去了。
下女道:“你出去不久,他就出去了,说看个朋友。”胡庄料道是帮陈女士去了,便留心看棉町南神保町一带的火,正在烘烘烈烈,心中也有些替陈女士着急。只恨自己不知她的番地,不能帮姜清去救。心想:我何不到那一带去看看,若碰见了,岂不可以替小姜分点劳吗?于是复下楼,见三人都不在房里,罗福的衣丢了一地,诧异道:“罗呆子没有靴子怎样出去得呢?”走到门口一看,自己的靴子不见了,即叫下女下来,另拿双靴子穿了。也不披外套,走至外面,见火势丝毫未息。由东明馆(劝业场)穿出锦町,看那火如泼了油,正在得势的时候。
顷刻之间,锦町三丁目一带,已是寸草不留。幸风势稍息,没有吹过第二条街。胡庄在未着火的地方穿了一会,因往来的人太多,找不着姜清,只得仍回家。见罗福三人已回了,即问他们去哪里来。罗福跳起来道:“我一个被包烧了。”胡庄道:“烧了就烧了,要什么紧!你们方才想去抢吗?”刘越石道:“方才你到晒台上去了,我和老张正笑他穿衣,他忽然跳起来说,还有个被包放在柜里,没有拿,定要我们大家去抢。我们还没有走到神保町,看那一块的房子,都已烧塌了,只得回来。”胡庄笑道:“事也太奇怪了,一点钟的时候起火,你的被包还在柜里,难道你夜间蠢得不睡吗?”罗福急道:“不是没有睡,听说发了火,才起来捆好的。捆了后,因放在房中碍手碍脚,将柜里的箱子拖出来,被包就搁在柜里,才打开箱子穿衣服。穿好了,把桌上的书籍,抽屉里的零碎东西,捡到箱里,锁了。老张的朋友不肯上来,恰好你来了,提了箱子,就催我走,故忘记了被包。”胡庄笑道:“亏你亏你,还可惜了个好挂衣钉子。不是我说句没良心的话,连你这种蠢东西,烧死了更好。”说话时,天已要亮了。四人又到晒台上去看,火势已息了一半,消防队这时候都奋勇救火了。那一线一线的白光,在空中如泻瀑布,煞是好看。火无风,便失了势,哪里是水的对手。可怜它看看没有抵抗的能力,消防队打跛脚老虎似的,怎肯放松一步呢。不到两个钟头,眼见得死灰无复燃之望。四人下楼洗洗,姜清已回。刘越石问他哪里来,姜清说替朋友搬行李。胡庄知道,便不问。
是役也,日本总损失上二千万,中国总损失近二十万,湖南省断送了一个求学青年。
不肖生写到这里,笔也秃了,眼也花了,暂借此做个天然的结束,憩息片时,再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