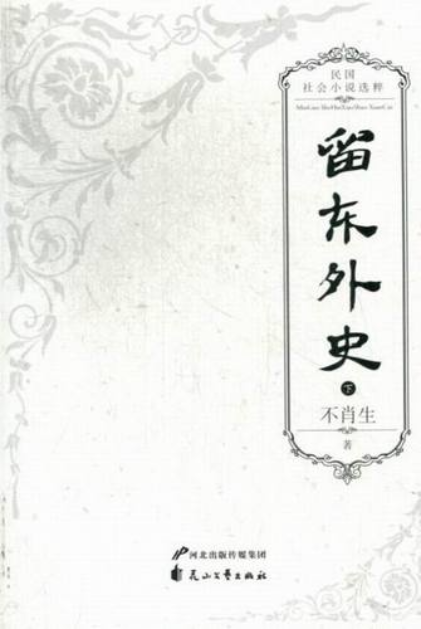话说黄文汉走到苏仲武家里,苏仲武迎着问道:“你交字给她,她看了说些什么?”黄文汉且不答话,将外套脱了,从怀中抽出那个信封来,往苏仲武面前一掷道:“还有她来看你的字?她去见阎王只隔一层纸了!”苏仲武大惊失色道:“她的病又厉害了吗?”黄文汉道:“只差死了。我也没进房去看,圆子不教我进去。说她从我们出来之后,受了她母亲几句话,急得她一阵肚子痛,登时小产了。此刻还在那里发血昏,院长说非常危险。她母亲一气一个死,现在也躺在床上,咬牙切齿的,也不知她恨哪个?”苏仲武连连跌脚道:“那一定是恨我了。但是我也不怕她恨,我去看看,她要打她要骂,都由她。
可怜她和我如胶似漆的几十天,于今被我害得她这样。就是她母亲架着把刀在那里,我也得去看看。”说着眼眶儿又红了。
黄文汉道:“去是自然要去,就是我也不能因春子恨就不去。
不过此刻去,有院长在房里,听了不像样。我们再等一会同去就是。”苏仲武点头道:“她若万一有差错,我也决不一个人活在世上。”黄文汉道:“呆子!你不必这般着急。她小产了倒是她的幸事。带着肚子回到爱知县去,算是什么?死生有命,不该死的,决不会是这样死。就是死了,莫说她还不是你正式妻室,便是你正式妻室,也只听说丈夫死了老婆殉节,从没有听说老婆死了丈夫殉义的。你把这‘死’字看得太容易了。你父母养你,送你到日本来读书,是教你这么死的吗?”
苏仲武叹道:“我也知道是这般想,但是计利害太清楚了。照你说来,人生除了病死,就没有可死的事了?我此刻的心理觉得死了快活。与其活着受罪,不如死了干净。她若果真死了,我就不自杀,你看我可能活得长久?我自从和她做一块儿住,我的性情举动,完全变了一个人。时常想起我平生所遇的女子,实在也不少,没一个能牵我的心的。我和她们混的时候,不过觉着有这们么回事罢了。惟有她,一见面就牢牢的钉在心上似的,一时也丢不掉。直到于今,没时没刻我这心不是在她影子里颠倒。同住的时候,我就是有事,要出外访个朋友,总是上午挨下午,下午推夜间,夜间更不愿意出外。第二日实在不能再挨,才匆匆忙忙的跑一趟,在人家喝一杯茶的时候都很少。我从来并不欢喜说话,和女人更是没得话说。只和她,不知是哪里来的话,那么多,夜间直说到两三点钟。一边说,一边朦跳着答不上话来才罢。我也时常对她说:‘我们太亲密了,恐怕不祥,世界上没有这般圆满的事。’她说,她并不觉着十分亲密,她还有亲密的心事,没有用尽似的。她是这样说,我登时也觉得待她的心还不十分满足。忽然生出一种极奇怪的心理来,极希望她待我不好,我每天还是这样待她,以表示我对她的心思。后来愈想愈奇,希望她瞎了一只眼睛,或烂掉一只鼻子,人人见了害怕,我还是这样待她。以表示我爱她是真心,不是贪她的颜色。哪晓得还不到两个月,这些事都成了我伤心的陈迹。你看我以后触物伤情,这凄凉的日月如何过法?我于今二十多岁的人,以后的光阴长得很,有了这种影子在脑筋里面,以后还有鼓得起兴的日子吗?”
黄文汉听了,也觉凄然,叹息说道:“你精神上受的痛苦,不待说是受得很深。但是此刻正在锋头上,还不能为准。你年内回家去一趟,享享家人团聚之乐,每日和亲戚故旧来往,也可扯淡许多心事。明年二三月再来日本,包管你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苏仲武只管摇头道:“这影子我毕生也不能忘掉。我于今设想将来,就是有个玉天仙来和我要好,我有了梅子的影子在脑筋里,我也不得动心。”黄文汉道:“果能是这样,倒是你不可及处,我老黄是做不到。我为人生来只有见面情的,在一块的时候,混得如火一般热,都能做得到。分手后,我脑子里就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只要不再见面,我总能不再想念她,一见面就坏了。圆子对我实不错,她也知道我的性格,不肯和我离开。”苏仲武道:“你将来带她回中国去么?”黄文汉道:“到那时再说。我暑假的时候就打算回去的,因结识了她,你又要我替你办梅子的事,就耽搁下来了。此刻回去,横竖没有可干的事,说不定还要受‘乱党’两个字的嫌疑。在这里有一名公费供养着,一年再贴补几个进去,也就足够敷衍的了。圆子也十分可怜,她父亲在日,谁能说她不是官家小姐?及至遇人不淑,不得已牺牲她千金之体,来营皮肉生涯。遇了我,她欢喜得如危舟遇岸。我若丢了她,她便是举目无亲,不能不重理旧业,就也是一桩惨事了。若带她回中国去罢,我的家境,你是知道的,那一点祖遗的田地,有父母、妻室、儿女,不能不靠它供养。想抽一点出来供给我,是不行的。我归国不可一日无事,于今是这样的政府,我犯着在他们这班忘八龟子手下去讨饭吃吗?前日郭子兰毕业归国,我还很替他踌躇。他若是公费,我无论如何也要留住他,等等时机。”苏仲武道:“你将来万不可丢圆子,带回去是你一个很好的内助。模样固是不错,就是门第也不辱没你。”
黄文汉笑道:“和我讲什么门第?我又不是忘八龟子出身,和人讲什么门第?我的怪脾气,越是圆子这样营皮肉生涯出身,我越看得她重。”苏仲武笑道:“你这话却未免矫枉过正了。”黄文汉摇头道:“不然,越是这样营皮肉生涯出身的人,阅历得人多,她只要真心嫁这个人,决不会给绿帽子你戴。像中国于今这班做官的人家小姐,旧式家庭的,还知道略顾些面子,姘姘马夫小子罢了。新式家庭的,简直可以毫无忌惮,和野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中握手、接吻,说是行西洋的礼节。自家男人翻着眼睛看了,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即如杨议长的女儿,近来哪一夜不穿着西洋装,打扮得娇滴滴的,在锦辉馆帝国剧场吊膀子?吊上了就到旅馆里去睡,一点也不客气。”苏仲武道:“她家里就没人说话吗?”黄文汉笑道:“她家里谁有说话的资格?四十岁以内的,谁不曾上过旅馆?杨小姐在北京的时候,和杨议长的姨太太在中央公园吊膀子,被杨议长的令弟杨督军看见了,如此长短的对议长说。议长听了,登时气冲牛斗,亲自出马到中央公园拿奸。拿了回来,将姨太太痛打了一顿,拘禁起来。小姐不服打,议长更怒不可遏,说:‘这种贱东西,要她做什么?’立刻驱逐出来,不许再回家。杨小姐就趁此在外面追欢取乐。还是她令叔杨监军看不过意,设法收了回来。这都是我湖北的出色人物。正应了湖北一句俗话:‘乌龟化龙,不得脱壳。’杨议长也就是这壳脱不掉,你去讲门第呢,杨家的门第还不算高吗?还有广东蔡次长的妹子,生得如花似玉,嫁得四川姓毛的。她嫌丈夫不中用,不许丈夫进房。每日装饰得玉天仙一般,在上海逗得,那些青年子弟颠颠倒倒。她一出来,和狗婆子走草一样,后面总跟着一大堆油头滑脑的东西。她便择肥而噬,也是一点忌惮也没有。她家的门第还不高吗?于今中国的官僚,像杨、蔡两家的,一百家之中,敢说一句,有九十八家是不干不净的。这两家必是正太太上了年纪,没有小姐,没有姨太太。不过其中有掩饰得周密的,外人不知道罢了。你想想,他们男子做官,尽干的是冤枉事,弄的是冤枉钱,不拿姨太太、小姐来报答这些人,还有天理吗?”说得苏仲武大笑起来。黄文汉笑道:“我只说说做官人家的姨太太、小姐,就扯淡了你许多心事,难怪那些人专一寻做官人家的姨太太、小姐开心。你将来归国去了,少不得做官的帽子又要染绿几顶。”
苏仲武听了,又触动了心事,低头半晌说道:“我们此刻可去病院了,你看四点多钟了。”黄文汉看壁上的钟,果是四点一刻,即起身推开窗子一看,不禁叫了声:“哎呀!雪下尺来深了。”窗户一开,苏仲武觉得寒冷,起身看了看雪,正手掌般大一块一块的只下。连忙教黄文汉推关窗户,换了洋服,从箱子里拿出貂皮外套来披上。又罩上雨衣,戴了暖帽,加上围襟。在箱子里寻皮手套,寻了一气寻不着。黄文汉等得不耐烦了,说道:“哪里就会冷死了?你们阔人真麻烦,我不带手套,也还是热烘烘的手。”苏仲武知道黄文汉的脾气,欢喜说牢骚话,便关了箱子道:“不寻了,不寻了,就光着手去罢!”黄文汉转身就往外走,套上靴子,站在门外等。苏仲武穿了靴子出来,二人冒雪向顺天堂来。
走到病室门口,黄文汉轻轻在门上敲了一下。看护妇开门出来,黄文汉悄悄的问:“病人怎样了?”看护妇点点头道:“此刻宁贴了许多,大约不妨事了。”黄文汉举着拇指头对看护妇轻轻的道:“这个人睡着没有!”看护妇笑着摇头。苏仲武急于要见梅子,在背后推黄文汉进去。黄文汉进房就闻得一种血腥气。只见春子坐在梅子床边,梅子仰面睡在床上,面如白纸一般,比吐血的时候还难看。圆子靠着梅子的床柱坐了,低头想什么似的。见黄文汉同苏仲武进来,忙起身接外套,示意教二人不要高声惊醒梅子。黄、苏二人就春子的床边坐下。
春子望了二人一眼,掉过脸去不做声,面上表现一种极不欢迎的样子。苏仲武忍不住,轻轻走到梅子床边,低头看梅子一脑青丝,乱堆在枕上,脸上也蓬蓬的覆了几根,眼眶消瘦得陷落下去,合不拢来。虽然睡着,那眼皮仍张开一线,看见瞳人在里面动,一望就知道是有痛苦,睡不安稳的样子。嘴唇枯白得和脸色一样;不是还有一丝气息,谁也要说是已经去世的人了。
苏仲武心酸难禁,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十分想放声痛哭一场。
又怕惊动了她,反为不好,揩了泪极力的忍住。可煞作怪,梅子合上眼,半日不曾开,苏仲武只在旁边站了一分多钟,梅子好像知道似的,慢慢的将眼睛睁开,转过脸朝苏仲武望着,将头摇了一摇,含着一泡眼泪,发出极微细的声音说道:“你好生保重罢,我是不能再和你好了。我常用的东西,在你那里不少,你都留着做纪念罢!这房里脏得很,不要在这里久坐,回去罢!以后也不必来了。我大约也挨不了几日,我实在舍不得就是这样死。生成了是这样的,没有法子。”梅子说时,自己也把不住流泪。圆子、春子、苏仲武更是呜咽得转不过气来。
连黄文汉、看护妇都流泪不止。苏仲武强止住啼哭,说道:“你只管安心调养,院长已说了不妨事。你万一有个不好,我的罪更重了。我一条命为你死了,不算什么,母亲后半世没了你,如何过活?你的病完全是急出来的。你只想想你这身子,关系多大?”梅子道:“我都知道了,你去罢!”说时,尽力从被卧里伸出手来,给苏仲武握。苏仲武忙道:“我的手冷,莫侵了你不好。”梅子不依,苏仲武只得呵了呵,握了梅子的手。
梅子紧紧捏了一把,抽咽起来。春子急得在旁边跌脚。梅子将手一松道:“你去罢!”说完,将手缩入被卧里,掉过脸,仍仰面合眼睡着。
苏仲武此时如失了魂魄,站在床边不知道转动。圆子低声向黄文汉道:“你还是送他回去,以后不必来看也好,她这病是不能再加症候了。”黄文汉点头。圆子拿外套替黄文汉披上。
看护妇拿外套给苏仲武披,推了几下,苏仲武的魂灵才入壳,也不做声。披上外套,拿起围襟,泪眼婆娑的开了房门就往外走。黄文汉跟出来,追上去替他揩了眼泪。问他:“还是家去,还是上馆子去吃点东西?”苏仲武也不答话,径往家中走。黄文汉跟在后面,也觉很伤感。苏仲武走到家中,将衣服脱下来,也不折叠,一件件往房角上撂。从柜里扯出铺盖来,胡乱铺了,纳倒头睡着,掩面痛哭起来。黄文汉知道劝慰无效,一时心中也没话可劝,连外套坐在铺旁,望着他哭。苏仲武越哭越伤心,哭一会又停住嘴,拖着黄文汉说梅子如何好,如何好,说到伤心之处又哭。黄文汉心想:我在这里,他有人诉说,自然越说越伤心。我不在这里,他一个人哭一会,必然哭倦起来,或者会睡着。我此刻正肚子饿了,且去吃点东西,再来看他,岂不甚好?想罢,也劝了苏仲武几句,说去吃点东西再来,苏仲武也不挽留。
黄文汉去了,苏仲武又哭了一会,果然哭倦了,矇眬睡去。
仿佛梅子乱发蓬松的从外面走来,望着他笑。梦中的苏仲武倒忘记梅子病了。问她:“为什么头也不梳,这样乱蓬蓬的就在外面走?”梅子笑答道:“你还问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苏仲武在梦中正自疑讶,梅子忽然不见了。仿佛又到了日光,在那旅馆池子里看见梅子,靠着廊檐柱子站着,在那里掠鬓。
苏仲武想走拢去,一提脚便踏入池子里面。“扑冬”一声,全身跌下去了。急得喊了声“哎哟”!惊醒转末。看外套洋服,撂了一房,一个冷侵侵的电灯,发出白光来,连房子都像浸在水里。揉了揉眼睛,叹道:“这样凄凉的景况,我如何过得来?她的病,医生虽说不妨事,我看那情形,是万无生理。纵然如天之福,留得一条性命,她已经有了人家,也不是我的人了。并且她和我那样的情分,也不见得肯嫁旁人,十九要忧伤死了。总之,她不嫁旁人就是死。两个消息,我听了都不能堪。我想我以后没有她,决没再有她这样的人来嫁我,填补我这缺恨,我还有什么幸福在后面可以希望吗?倒不如趁这时候死了。她得了我的死信,就不死也要急死,我和她两人在阴世,还怕不得见面吗?这世不能做夫妇,来世是一定可以团圆的。”苏仲武这般一想,果是死的好。但是当如何个死法?跳火车罢,觉得太惨。用刀自杀罢,又怕手软,杀不死反要进医院医伤。服砒霜罢,药店里没有医生的证书,必不肯卖。想来想去,要死容易,寻死的法子实在没有。坐起来又想了一想,喜道:“有了,我记得前回新闻上载了段故事,说一个日本人因伤寒服安知必林散,服得太多,中毒死了。这样看来,安知必林散里面必含有毒质,我何不买些来?若怕毒性发得不快,再喝上几杯酒,一定不要一点钟就完了事。”
想罢,心中异常高兴。跳起来连忙穿衣服,披外套,戴暖帽,围领襟,出房穿靴子。此时外面的雪已住了。电光、雪光,照耀得如银世界一般,煞是好看。苏仲武要寻死的人,也无心玩景,三步作两步的跑到猿乐町一家药店里,买了十包安知必林散。又到春日馆料理店内买了一瓶牛庄高粱酒,提回家中。
将安知必林散一包一包打开,和做一块儿,足足有一酒杯。拿起来想往口里倒,一想:我既要情死,何能不留一封绝命书,使人家知道我是为什么事自杀的呢?并且家中父母俱全,受了一场养育之恩,也不能不将我自杀的原由说出来,使两个老人家知道我这死,是出于万不得已,不是那些不孝子孙,轻生不顾父母的可比。苏仲武想着不错,便仍将安知必林散放在桌上,
坐下来,揭开墨盒盖,拿了几张信纸,吮了笔,正要写,忽又想:绝命书就用这样普通墨写了,不觉哀痛,必得用血书才好。
我横竖要死了,留着这些血在这里有什么用?等我咬破指头,取半杯把血出来,再写不迟。这笔也不能用……遂又起身寻了一枝新笔,拿了一个小茶杯来盛血。从容坐下来,想右手咬痛了不好写字,咬左手罢。将左手就电灯下,反复看了一看,点点头道:“小指头,小指头,我还没有自杀,请你先与我脱离关系,借你一点血来表明我的心迹。”说着,将小指头往口里一送,闭着眼睛,用力一咬。
不知咬下来怎样,且俟下章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