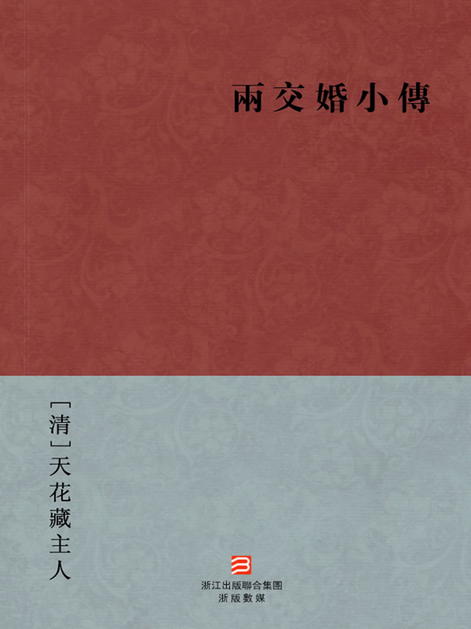词曰:
偶尔占三巴,便想扬州第一花。况是色香都长就,根芽。不怕夭桃不破瓜。
谁道事还差,凤去楼空啼暮鸦。惊得断魂无一语,嗟呀,锦片前程浪滚沙。 —右调《南乡子》
话说王知县看见甘颐,青年貌美,举止风流,又动了一片怜才之心。欲要说起,因先问道:“甘兄既在扬州与敝座师,诗酒往还,则他令爱荆燕小姐才美之名,再没个不闻之理了。”甘颐见问,不觉怅然道:“生员不但闻,而色香嗅味亦已浅浅深深,领略一二矣。”王知县道:“既是如此,何不求为佳偶,庶不负上天生才之心。”甘颐道:“岂不反侧愿求!但每一自反,而孤寒远人,又无贵重良媒,何以启齿?”说到此处,因对着王知县深深打一恭道:“惟蒙老父母大人,垂天地之心,书中微露一斑。故生员方得借此陈情,而邀贵座师隐然之许可。又明命努力功名。故生员遄归,一为受聘,一为秋闱也。今乃又蒙老父母大人殷殷念及,深恩厚德,直不啻天地父母矣。”王知县道:“天地生才甚难,而才之遇才又不容易,故本县每恐失之。今以令妹之才,得配辛解愠之才,再以甘兄之才,得配了辛荆燕之才,便妹妹哥哥,姐姐弟弟,一双两好。今日之交婚,可成千秋之佳话矣。既敝座师与甘兄有了成言,容本县再写书去撮合,自如所愿矣。甘兄只须拾两闱之青紫,以为婚姻光,便万全矣。”甘颐道:“蒙老父母大人,事外尚如此垂怜,生员切己,敢不努力。”王知县又定了行聘之期,甘颐方才辞谢而出。正是:
天地生才原有伦,最堆得者爱才人。
若有爱才人撮合,何愁秦晋不朱陈。
甘颐别了县尊来家,与母亲妹子说知县尊已定了行聘之日,并许与辛小姐做媒之事,田氏甚是欢喜。
到了行聘这日,县尊果代辛祭酒,行了千金厚聘过来,鼓乐吹打,十分丰盛。知县又吉服亲自到门,甘颐迎接到堂,盛筵款待。因是父母官,又是前番审讼恩人,田氏率领着女儿甘梦,也亲自出来拜谢。
县尊看见甘梦,金镶玉饰,比前青衣装束,大不相同,更加欢喜。因对田氏说道:“令爱才美,固是出类惊人,而令婿才华,亦自不凡。今秋明春,定然同令郎高发,方知本县不是孟浪。”田氏因谢道:“父母老爷的天恩,举家也陈说不尽,也感激不了,惟有顶戴祝赞而已。”王知县听了大喜,略吃得几杯,恐路远,就起身去了。
甘颐见秋闱渐近,因闭门读书。到了宗师科考,又是一名入场。到了入场之时,只得别了母亲、妹子,到成都省中去赴试。论起来,甘颐还是初次入场,不期场中,只论文,不论老少。过了三场,候到揭晓这日挂出榜来,这甘颐竟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
报到巴县,先是王知县喜个不了。再报到横黛村来,田氏与甘梦又喜个不了。
甘颐在省中吃鹿鸣宴,谢座师,谢房师,会同年,又谢宗师,直忙了二十余日,方得脱身回家。一到家,拜见过母亲,又见过妹子,即到县中来拜谢王县尊。王县尊接着,以为鉴赏不差,彼此欢喜异常。随命送匾立旗杆,凡事过于加厚。
又过了些时,南场的乡试报到县中。王知县看见辛发,也中了南场第八名亚魁,愈加欢喜。随叫报人,写了报条,报到横黛村甘解元家来。
甘颐此时,正贺客盈门,忽又见一伙报人,拥进来报喜,俱惊讶不知是哪里来的。不多时,众报人将报条高贴在堂中报解元的报条一带。大家争看,只见上写着:
捷报贵府令坦辛讳发高中南场乡试第八名亚魁。
报人张才、李福。
甘颐看过,喜之不胜。忙入内报知母亲与妹子,大家俱欢喜不尽。因问报人,何以得知?报人道:“是大爷差来的。”甘颐听了,一面赏了报人,一面就来拜谢知县。起先是一番贺客,如今又添了一番贺客,终日忙个不了。
却说刁直,自从讨了一场没趣,便不好上门。后闻甘颐回家,就要上门修好。只因自家又加纳了个三考外郎,见人也称相公。见甘颐不过是一个秀才,也差不甚远,故忍耐住了。不期到了秋闱,甘颐忽中了解元,十分动火。又见报人久知他与甘家是表亲,报条都报将来。又不好回说不是亲,却暗暗的出赏银,自家却不好上门,心下甚是急躁。欲要老着脸,竟上门贺,又恐怕甘颐倚着举人发作他。再三思量,并无计策。忽想到:“且待我在路上试他一试,讨个消息,再作区处。”
因打探他进城的日子,竟立在街旁,候甘颐的轿子,将抬到面前,便走到街心拦住轿子,深深打一恭道:“愚表兄罪人刁直,恳求一面,不知大贵人还认得么?”
甘颐在轿中突然看见,因想起他是母亲同胞姊妹生的儿子,在轿前打恭,过不得意去。忙喝住轿,走了出来,用手搀住道:“原来是刁表兄,为何不着人先通报一声,使小弟得罪。”因与作揖。揖罢,刁直就说道:“罪人下情,苦未上达。欲求至舍一诉其由,不知贵履可肯下临?”甘颐道:“此处到府不远,何不同步而去。”刁直道:“怎敢劳尊。”甘颐道:“书生步履之常,何劳之有。”遂同到刁家,叫家人送上一个表弟的名帖,又重新施礼。
刁直一面叫人治酒,一面就诉说道:“向因一时痴妄,得罪姨娘、表妹,故至今无颜,不敢登门。就是表弟大喜,日思走贺,恐遭斥辱,故不敢耳。”甘颐道:“母姨至亲,怎说此话。就是金钗求亲,止不过爱舍妹也,原非恶意。事又不成,彼此又无伤,往来何碍。”刁直听了大喜道:“表弟之心,天也;表弟之量,海也。既蒙赦过,感戴不胜。”一面席完,送上酒来;一面又邀了几个亲邻来陪。甘颐绝不装腔,放量而饮,直饮到日暮酣然,方才谢别回去。
刁直到次日,又备了许多礼物来称贺。甘颐与母亲、妹子说知,嘱咐前事休提,以礼相待。刁直又见招的女婿,也中了亚魁,回想前事,十分惭愧。又请姨娘、表妹相见。田氏偏领了甘梦出来见他。刁直看见甘梦,花嫣柳媚,绰约如仙,拖逗的心目中青黄无主,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作了两个揖,就出来了。甘颐留他饮酒,直饮到午后,方放他进城。正是:
至亲原好又何修,若要修时便带羞。
何不往来无话说,欢欢喜喜更绸缪。
甘颐因人事缠扰,直挨到十月尽,方得动身进京去会试。因与母亲约道:“孩儿此去,若是不中,自然就回来事奉甘旨。倘托母亲福庇,侥幸中了,便恐要在京中耽搁。母亲、妹子,远远悬隔,实为不便。便要差人来迎请,或是上京,或是赴任。况妹子婚姻已在扬州,到蜀远接,亦殊费力。”田氏道:“这个自然,且候你的捷音再处。”
甘颐又到县中,求了王县尊一封书,与辛祭酒求亲,方才起身长行。一路上暗想道:“我幸已中了解元,又有王父母的书信,便开口去求,也不为非分了,况辛祭酒已有成言。”又想道:“求虽不妨去求,只怕成还未必便成。必须中了进士,方得遂心。然就情理揣度,辛小姐这等才华,再无个不嫁我,而又嫁他人之理。但黎青曾说,恐有意外之变。我想意外二字,尚属虚虑,未必当得意中实事。”遂欢欢喜喜,催赶舟马,晓夜前行。
不几时到了扬州,船一泊岸,也等不得寻下处,也等不得见黎青,早先袖了王知县的书,带了王芸,一径到辛衙来,指望相见欢然留饮。不期走到门前,竟静悄悄不见一人。再走进大门里去看,只见门旁贴着一张告示,上写着:
光禄寺少卿辛为禁约事。
徒侵损扰害。如有此等情弊,随即具禀府县究治。看守家人,亦不得因而生事取罪。特示。
甘颐看了告示,方知辛祭酒升了光禄少卿,带着儿子进京去会试了,心下早吃了一磴道:“他父子俱进京去了,这亲事却问谁求?”又想道:“他父子虽然进京去了,小姐自然在家,且进去问个消息。”因又走了入来,直走到厅门口,方看见老家人王禄,在那里坐着晒日色。看见了甘颐,是认得的,因走起身来叫道:“甘相公几时来的?”甘颐答道:“方才到,尚未曾起船。”王禄就说道:“老爷与相公俱进京去了。”甘颐道:“我看见告示,方才得知。但不知小姐还是在家,还是也随老爷进京去了。”王禄听了,白瞪了眼看着甘颐愕然道:“原来甘相公还不知道。”甘颐道:“不知道甚么?”王禄道:“我家小姐已嫁与人去了。”
甘颐忽然听见,就像闻了霹雳一般,竟将魂魄都震痴了。呆了半晌,方才又问道:“果是真么?”王禄道:“嫁也嫁去了,怎么不真。”甘颐道:“且问你嫁与甚么人?”王禄道:“嫁与暴元帅的暴六公子去了。”甘颐道:“这等说是武官的公子了。小姐这等选择人才,为何就肯嫁他?”王禄道:“说来也奇怪。那暴公子来考诗时,人人尽道决不中意。不期那暴公子止写得三首旧唐诗,小姐竟看中了意,就和诗三首,许嫁与他。叫家老爷一时转不过口来。那暴元帅又势焰赫赫,叫本府太爷为媒,见小姐诗已许下,便立逼着娶去了。”
甘颐见王禄姓名、事迹俱说得凿凿有据,便气得软瘫做一团,走也走不动,只坐了半晌,没瞅没睬方才走了出来。思叹道:果不出黎青所料。今去见她,必为她所笑。然一肚皮气闷,除了她别无人可说,只得勉强走到砖街上来。
刚到得门前,恰好黎青出门撞着,便笑吟吟迎了进房去道:“还凑巧,再迟一步,便要错过了。”甘颐虽也勉强支持了几句说话,只觉精神暗淡,颜色惨然。黎青看见因笑嘻嘻说道:“闻郎君已高占鳌头,今又千里远来,自应欢颜道喜,笑面言情。为何凄凄不乐?想定为闻了辛小姐嫁暴公子之信故耳。”
甘颐见黎青说着他的心事,不禁感触,竟落下泪来道:“正为此也。这段心事,他人不知,须瞒芳卿不得。我为辛小姐,也不知费了多少心机,守了多少岁月,陪了多少小心,担了多少惊怕,刚刚求得王父母一封书来,以为金屋可期,蓝桥有望。不料盼到而今,而金屋早已无人,蓝桥又忽淹断,纵使心如铁石,亦难为情。”黎青笑道:“此事若是确然,便怪郎君不得。今此事,以妾看来,不过移云掩月,以骗聋聩之人耳。大有可疑,郎君何便深信?”甘颐道:“卿为此言者,宽慰弟也。岂有事已确然,尚有可疑之理。”黎青道:“郎君何以知其确然?”甘颐道:“暴六公子为婿,人已确然矣。知府作伐,媒又确然矣。笙箫鼓乐,万耳万目,嫁娶又确然矣。若疑辛小姐不愿,而和诗三首,又已确然矣。有甚不确?”黎青道:“和诗郎君曾见否?”甘颐道:“这却未见。”黎青道:“此事大有可疑。郎君初闻信,心志慌张,未及细察。妾为郎君察之久矣。且少饮一杯,待郎君神情稍定,然后容妾细道其详,以拨郎君之闷。”
甘颐听了,终只认做宽解之言,因谢说道:“多谢芳卿美意。只怕香醪纵美,不能解愁;快论甚奇,安能拨闷?然而卿卿高雅已铭五内矣。”
须臾酒至,不但黎青苦劝,而甘颐亦借此稍宽。只恨神情不畅,饮不得四五分酒力早已有七八分醉意。黎青因说道:“贱妾说此事可疑,郎君以为贱妾宽慰,故置之若罔闻。然此事实有可疑,故妾敢为郎君一剖也。”甘颐道:“芳卿既有所疑,请试言之。”黎青道:“且请问,郎君视辛小姐为何如人?”甘颐道:“辛小姐乃当今灵心慧性之才美女子也。又何待言?”黎青道:“郎君请忖度一忖度,这暴元帅的第六公子为何如人。”甘颐道:“人固不易知,然就事论人,他一个武官的儿子,纵有才学恐亦有限。”黎青道:“却又来。况闻这暴公子去考诗时,又止写得李太白《清平调》三章,并未曾自有一句。况又闻这暴公子,考诗时是一人,亲迎时却又是一人,则其无才诡谲可知矣。如此无才诡谲之人,而辛小姐灵心慧性之才美女子,选才几许,阅人几许,历时几许,略无一入目之人,而竟为暴公子三首唐诗,遂输心服意,不顾父母,竟随之而天南地北,不问所之,岂有是埋哉?即使辛小姐果爱其人,寓意于诗,而才人下笔,亦不过一字半字中微露其情。岂肯直书曰:‘何幸仙郎意外逢’,又直书曰:‘倘得吹箫乘凤去’,又直赞其美道:‘五陵公子姓名香。’为此者,不过别有权移,假此以快其心,使之喜而无察也。使辛小姐果然真为此诗以自媒,果真仰望斯人以终身,则是一不孝不智,无廉无识之妇人矣。郎君又何取焉?”
黎青一席话,说得甘颐恍然有省,豁然大悟道:“芳卿之论,深为有理。但恐辛小姐才美绝伦,谁无耳目?岂易挪移!”黎青道:“若论美,北人见惯肥痴,若睹南妆,袅袅娜娜,自易生怜。况辛小姐盛名之下,惟有夸张,谁敢道个不字。若论才,只要拿得笔动,便是大才子了。谁能识其中深浅,一发易于耸动。况辛小姐所遣之人,不是许飞琼,定是董双成,谅非等闲,安能与人识破。辛小姐不深藏金屋,即暂隐桃源,相会自有期也。郎君但当安心待之,不可作无益之悲。”
甘颐听了,渐渐想出意味来,心下一喜,不觉连酒都醒了。因说道:“若据芳卿如此剖来,只恐辛小姐还藏在家里,芳卿何不试往一探。”黎青笑道:“郎君何看得事情儿戏。辛小姐此事,乃偷天换日,干系不小。就藏在家里,安肯见人?就是贱妾所言,只好你知我知,外人面前一字也露不得。走了消息,便要遗祸于她,断断不可。”
甘颐听了,又惊讶起来道:“是呀,是呀。但只是凤去台空,已无踪影,而又畏首畏尾,不敢寻消问息。纵使相公有期,而天长地久,等到何日?岂不令人闷杀!”黎青道:“妾闻赫赫之势,从来不能耐久。再加以骄矜强横,其败可立而待。况兵凶战危,不出周期,定有变故。郎君幸努力春闱,夺了会状二元,完了功名大事,妾包管美满婚姻,欢然到手。”甘颐道:“得如卿言,则是弟已死而复生也。”甘颐被黎青说得愁心变喜,闷臆生欢,又不知吃了许多酒。因分付王芸先回船去,自己留在黎家宿了。正是:
入情妙论应须信,达理微言自可听。
听到一天忧散后,几回醉了又重醒。
甘颐次日起来,因对黎青说道:“卿之料事,吾所不及。又肯尽心竭虑,佐予之不逮,弟之感铭久矣,不在今日。此去倘侥幸成名,玉人尚在,果能遂愿变男儿之志,则卿之美意,决不敢忘。三星在天,定当留一星之座以报卿。卿幸勿视我为虚言。”黎青听了,不胜欢喜道:“妾一见郎君,即怀此志,然而自揣青楼贱质,又不敢作非分之想。后蒙郎君错爱,得荐枕衾,又不忍自央蒹葭之倚。虽未敢明言于郎君,而一片眷恋之诚,想郎君亦已鉴察久矣。郎君若有虚言诳妾,不待今日,然而绝不蒙许可。今忽怜而见许,此必有感妾仰望之诚,念妾于归之切而不忍辜负者,故慨许而不疑也。郎君一段真诚,可格禽鱼。妾非禽鱼,安敢复以为虚?葑菲有托,已不胜庆幸矣。”说罢,甘颐吃过饭,就要别黎青进京道:“辛小姐既不可问,我在此也无用。况岁云暮矣,春闱之期渐近,只得要勉强行矣。”黎青道:“春闱期近,妾不敢强羁留郎君。但郎君此行,妾还有一言奉嘱。”甘颐道:“尚有何言,愿乞见教。”黎青道:“郎君到京,少不得要见辛公子。他父子少不得要对你说他小姐嫁公子之事。郎君听了,千万不可惊慌悲戚,信以为真。若信以为真,他便道郎君无识,不知他女儿之为人,非知己也。又千万不可微言嘻笑,道破其假。若道破其假,他又虑郎君口舌不稳,打破他盘中之谜,又生疑忌。凡有所言,郎君只宜唯唯诺诺而已。倘有求婚之书,竟自达上。倘有别议婚之事,竟以有聘辞之。使辛小姐闻之,自服郎君之有识,而又感郎君之有情有义也。”
甘颐听了,大喜道:“何卿之论事,尽合机宜,真可谓女中之陈平矣,感谢感谢。”黎青道:“还有一言。”甘颐道:“更有何言?”黎青道:“郎君至京,倘辛公接郎君同寓,万万不可住在一处。”甘颐道:“得能亲近,亦是好机,为何转不可同住?”黎青道:“郎君不知。那暴公子住在京师,如今做了辛公女婿,自时时来往。郎君若住在一处,与他认熟了,后来做亲,未免又多一番议论。莫若远远的生疏些,好做手脚。”
甘颐听了,更加欢喜道:“卿怎么就算到这个田地也。可谓心细于发,异日得朝夕相依,使我心腹中,又添许多智慧,真快事也。”说罢,黎青又取酒与甘颐送行。二人绸缪婉转,只饮到痛醉,方才分手而别。只因这一别,有分教:功名得意,婚姻遂心。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