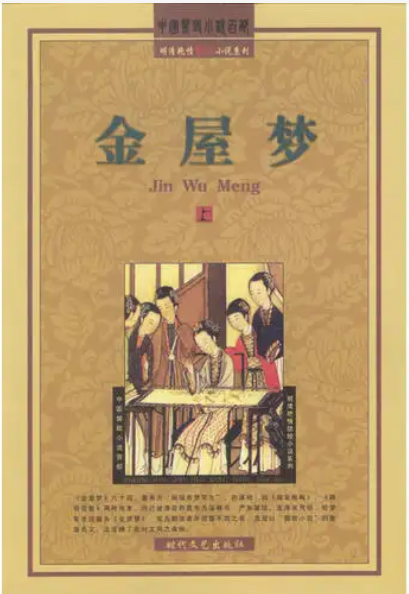非想非非想,如是复如是。
我欲礼法华,法华原不二。
舌上青莲花,化为苍蝇翘。一笑复一跳,
高卧吴山寺。
却说黎寡妇见桂姐魂不附体,终日里见神见鬼,又弄成一件血症奇疾。正然愁恼,不料女婿刘瘸子开封府告下状,来门首吵闹,到晚去了。黎寡妇请了医生诊脉,说是血虚邪想,取了一点定神丸来吃了。母子相守,连夜不敢吹灯;日里还哼哼地叫,半夜才醒,直到天明,才得合眼。如此半月,金桂姐略吃些饭,梳的头,才下得床了。只有血症不止,终日浸淫淋漓的,浑身不净,流的个美人面如黄蜡一般;又长出一件奇怪的病来,从此再不消想那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是件甚么病?这个病是天地间女子固闭血脉不通,以横骨塞其阴窍,止留一线走小水的路儿。人有此奇疾,遂致终身失偶,医家无药可治,俗名石姑,佛经中说是石女儿,随你西子的美貌,也是中看不中吃的。倒是一种愚蠢幼女,不曾经人道的,有了此疾,他不痛不痒,做了枯木死灰,到象绝欲参禅忘情息念的一个得道的女僧。那金桂姐生来色根不断,欲念方新,如何捱得这个病。如今弄的有了色心,没了色相,好不难受。自此病长成了横骨,那血症也止了,那邪魅也不来缠了,依旧调脂抹粉,打扮似帝女天仙一般。
刘瘸子探着桂姐好了,使张都监娘子过来面央。说情愿进门招赘,做养老女婿,绱鞋结帽子,尽是养的家。问众亲戚打个醵,讨几贯钱来,买几疋布绢来,完成他一生的事。也是女儿的命,定下的亲,谁不指望个好女婿,要不依从到了当官。我当初提亲是实,谁敢不实说。这黎寡妇因女儿大了,又感了一场恶疾,怕日久求亲不便,见张都监娘子一面劝他,又一面说硬证的话,没奈何了只得应承道:“既是亲家来好话,我也没奈何了。甚么大财大礼,指望来光彩,我看个好日子,买几匹布来,把他两口儿成了家,在这门口开个鞋铺,我娘女管着做鞋,他就管绱鞋底,到是好事。这样一个女儿,招了个皮匠,也省了去求人。他先消了这张状进来不迟。”说毕,张都监娘子谢了又谢,回去了。过了二日,刘瘸子写张和息状子,勾消了官司。他把个宅基卖了,却买了一抬礼,四个布绢,簪环首饰,也费有十两银子。进来见丈母,同张都监娘子,磕了头。看定十一月初三日成婚,招赘进门。那金桂姐大病方好,看着刘瘸子满眼落泪。正是:好马却驼痴汉,拙夫偏遇佳人。世上多少不相配的事,说来命苦。
今年春比去年春,北院翻成南院贫。
淡色桃花偏遇雨,苦心梅子不成仁。
红梢拭泪香犹剩,锦字裁书梦未真。
自自名芳无主卖,随风片片付沟茵。
金桂姐虽是女身未破,从与梅玉二人,昼夜演习淫欲,占花弄蕊,久已知趣;又两经鬼魅采取元红,把那男女的乐处,比久惯的还深一层。到了十一月初三,刘瘸子上浴堂里沐浴了,穿了一套新布衣服,请过张都监娘子来,与金桂姐上头完房。草草地治买了一付新被褥,添上些花粉首饰,随身衣服又做得一个红袖衫儿。那日张都监娘子,来看着金桂上了头髻,修脸剃眉,送进房来,和刘朝坐着,也斟了一杯合卺杯。桂姐满眼是泪,哭不出声来,也不肯接,瘸子取了,一口吃尽。留张都监娘子,也不好住下,拜了两拜回去了。
却说这金桂姐平日想起丈夫来常似眼里出火,一似妖精见了唐三藏,恨不得一口咽下肚去。今日见了刘瘸子,好似木偶人得了道的一般。那刘瘸子见了金桂姐回脸朝里,全不看他,他却自己取了一壶酒,将两碟卤菜,一顿吃干,弄的醉醺醺的,要做新郎。这两条瘸腿,要步步巫山神女行云的路,上上那银汉牛郎度鹊桥。将一条白布裤子脱了,一口吹灭了灯,才跳两跳,趴上床上,被金桂姐推了一交仰巴踏。好一似癞蛤蟆吃苍蝇,前合后仰,通趴不起来。挣扎了半日,起来向金桂姐肩上一搂,叫道:“姐姐,睡了罢。”被桂姐劈脸又是一个巴掌,连身一推,好似癞鳖趴深缸,把头伸一伸,通上不来。滚过身子,向金桂姐又是一搂,被桂姐连脖子是又两拳,好一似热锅的白鳝,把腰卷在一堆,再动不得了。
只这三推三搂,瘸子身子稀软的,金桂姐又恼又笑道:“可不煞人罢了。”心里恨着,却使手去摸他腰间的物,原来是有名无实的半瓶醋,二尾子,缩了好一似蚕蛹儿模样,鳖嘴儿骨突着。原来瘸子搂了桂姐三搂,又被推打不过,不得上手,早已津津淫液倾囊出,汩汩元阳见面投。这叫作是见面礼,不曾进门,先投了一个领谢的帖子进去了;又叫做是隔墙醉,不曾吃酒,但见了望竿就醉倒了。原来是刘瘸子是经金兵砍伤了腿胯,把肾缩了,只一个卵子;又常肿的光光,行不的人道;又见桂姐生得美貌,搂了一把,即时走泄,算完了一场洞房花烛了。岂不省了多少邪态?金桂姐见此光景,只得自己脱衣而睡。刘瘸子自知内外本钱俱空,不来惹事,自己睡得打起磕睡来。一头倒下,通不似人,两条瘸腿伸开,金桂姐起身细看一看,但见身腰短促,好似八九岁婴孩;肾缩卵枯,又象七八旬老叟;垂囊如败枣经霜,里顶似疆蚕在茧;土作泥人成体相,傀儡学舞少提梁。
睡到半夜里,金桂姐想了一想道:如今这厮已是辞不得,他只好留他做了个死椿,正好随便寻个得意人来,做些风流事儿,料这瘸子也捉不得奸,也管不得我。寻思已定。到了天明,刘瘸子起身谢了丈母,自己门首收拾一间门面,开个皮匠铺,也买了几双旧鞋在门首做晃子。桂姐带上鬏髻,也就常来帘子前看街上的人。瘸子哪敢问他一声,还恨不得找个好汉子奉承他。一句话不来,就骂个死,又是武大郎似的旧样子。
到了迎春时节,三教堂因今年科举大场,招了许多秀才,在此会课读书。河南八府生员,那没有盘费的贫士,多有来三教堂做公所的,时常在金桂姐门首经过,也有来他家里缝鞋的。金桂姐有时在帘子里,也看上了三五个少年书生,风流的秀士。自己的住房,却与那书楼相接,只隔了一块太湖石上的老梅枝,探过一半来,在这院子里。这秀才们手里拿着本书,探头探脑的,金桂姐也半掩半遮;人不看他,他又要看人,哄的人看他,却口里胡骂。大凡淫妇多是如此。
那时有一秀才姓潘名芳,字子安,生的风流俊雅,惯走花街,接了一个婊子刘素素,在三教堂书楼上宿。时常开了楼窗,看着这院子里,见金桂姐打扮俊俏,不象似个良家。在楼上刘素素望着桂姐说道:“借个针来与相公缝缝衣带子。”金桂姐道:“俺家里没人送去,你自己来取。”刘素素跑下楼来,到金桂姐房里,说些话儿,吃了茶,才知是皮匠的老婆。好一个妙人儿,回去说与潘秀才,又是一个在行,积年惯钻狗洞的。只使了一两银子,两枝玉簪儿,托着刘素素送来道:“潘相公有心要会你会儿。又不使一个人知道。”这金桂姐正是久缺着这个衙门,要借个署印的松松腰儿。笑了笑也不推辞,相约在半夜里,越墙在楼上相会,金桂姐连声应了。刘素素过那边去了。
忽然天下起雨来,从午后起下了一夜,把这个佳期误了。天明却是宗师考遗才的日子,一群秀才们,原是没有科举,来考遗才的。连夜各将被褥送入城去宿,五更预备进开封府考去了。刘素素也回了勾栏。三教堂秀才一个也不住。只有王魁宇,绰号王雷公,他原不科举,落下他看守书房。在楼中间两条长凳上睡,把卧房门的钥匙也带去了。那时天气炎热,王雷公吃烧酒,灌得烂醉,脱得赤条条的,仰卧着两腿黑毛粗腿,将他那话儿取出来,累垂垂如剥免悬驴,足有一尺余长。每日盘腰,甚觉坠的沉重,取一把大学士椅子来,把那话平平搁住,好似一轴古画相似。然后侧身而卧,好不快活。只觉鼾鼾入梦,鼻中响如雷。乘着酒兴,那物挺得又长大许多。王雷公睡去不提。
却说金桂姐前夜私约下,书楼相会潘生,因雨阻隔,一夜无眠。用手摸摸刘瘸,略借发兴,那得有些人气儿。天分既小不堪用,又有一卵子在外支撑,略一到门,又犯了前病,门外先谢了恩,常被金桂打出房去,在鞋店里打个冷铺睡,不敢言语。那夜月明如昼,金桂要偷墙赴潘生之约,先将刘瘸子打发在铺子里睡去了。等至二更将尽,内外不听人声,全无人影,用一个杌踏着,扳那梅枝儿上的花园墙。原不甚高,却接着太湖石下来。园中静悄悄,不见人影,走过三教堂,到了三空阁上,是潘相公卧房,或者不料我今夜亲来,先自睡了。桂姐欲火烧心,上得楼来,见楼门大开,月明中照见一个人睡声如雷,两脚长伸,一身黑肉,如镇殿将军一般,不是那潘相公的风流模样。想了一想,既到此处,怎肯空回,就在此人身上略泼一泼心中的火,也不枉来了这一次。
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