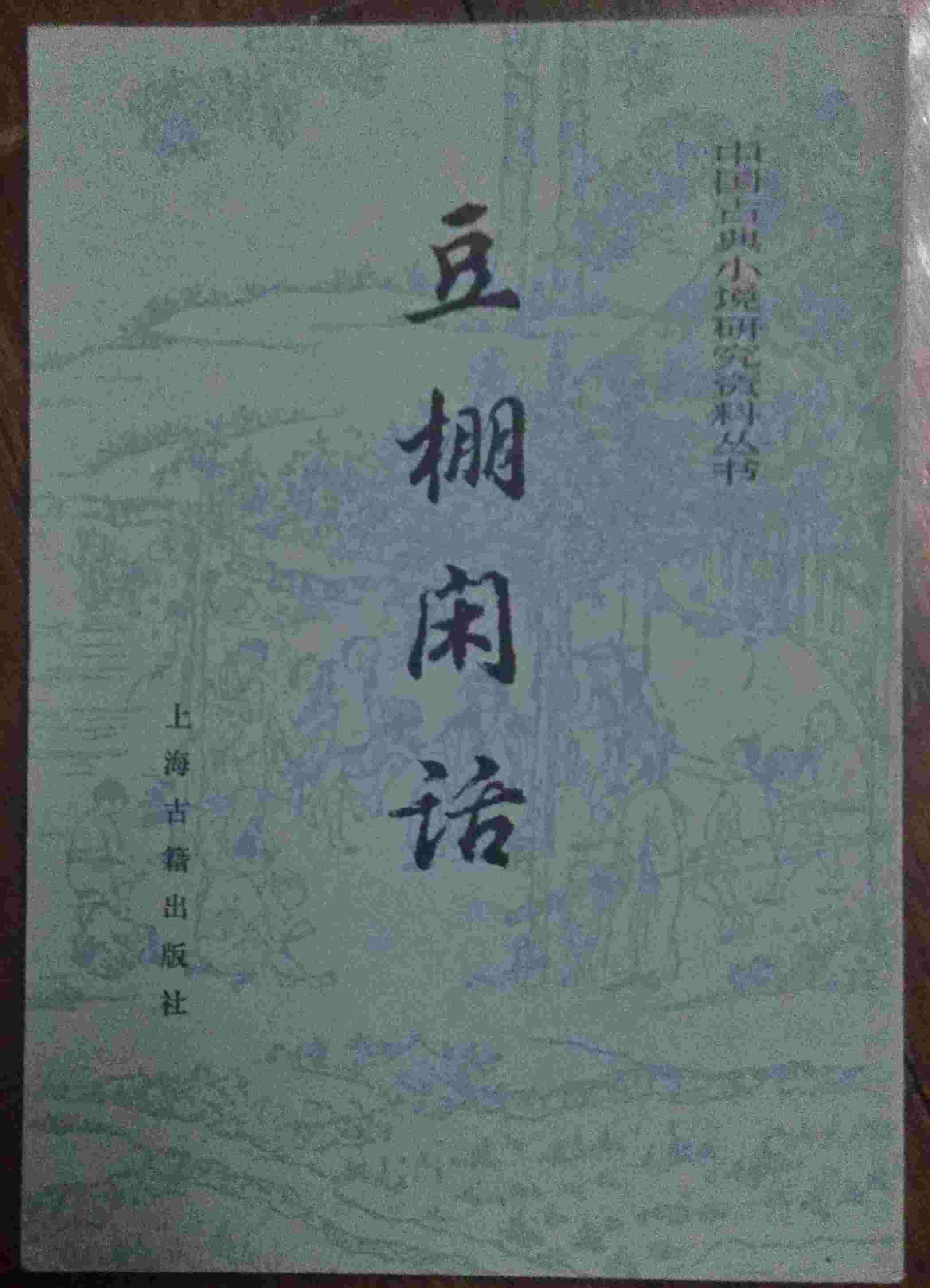朝奉郎挥金倡霸自那日风雨忽来,凝阴不散,落落停停,约有十来日纔见青天爽朗。那个种豆的人家走到棚下一看,却见豆藤骤长,枝叶蓬松,细细将苗头一一理直,都顺着绳子,听他向上而去,叶下有许多蚊虫,也一一搜剔干净。那些邻舍人家都在门外张张望望,嚷道:『天色纔晴就有人在豆棚下等说古话哩,我们就去。』不多时就有许多坐下,却不见那说故事的老者。众人道:『此老胸中却也有限,想是没得说了,趁着天阴下雨,今日未必来也。』内中一人道:『我昨日在一舍亲处听得一个故事,倒也好听,只怕今日说了,你们明日又要我说。我没得说了,你们就要把今日说那老者的说着我也。』
众人道:『也不必拘,只要肚里有的便说,如当日东坡学士无事在家,逢人便要问些新闻,说些鬼话,明知是人说的谎话,他也当着谎话听。不过养得自家心境灵变,其实不在人的说话也。』那人遂接口道:『我正说的就是苏东坡。他生在宋朝仁宗时,做了龙图阁学士,自小聪明过人,凡观古今书史,一目了然。看见时事纷更,权奸当道--如王安石“青苗”等事,也不尝要把话讥刺他或做诗打动他。聪明尖酸处固自占了先头,那身家性命却干系在九分九厘之上。倒不如嘿嘿痴痴、随行逐队依着仕路上画个葫芦,倒得个一路功名,前程远大,顺溜到底。可见苏东坡只为这口不谨慎,受了许多波咤。一日在家困顿无聊之极,却向壁上题下一首诗来,说道:“人家生子要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这四句诗也是讥嘲当道公卿的话,却是老苏的旧病,不在话下。后来又有个老先生于仕途上不肯通融,屡遭罢斥,看见那聪明伶俐的做了大官,占了便宜,也向壁上学那东坡题下四句道:“只因资禀欠聪明,却被衣冠误此生。但愿我儿伶且俐,钻天蓦地到公卿。”此一首诗似与坡公翻案,然而讥诮当道亦与坡老相同,只好当个戏言。难道人家生的儿子聪明伶俐就是好的不成?也有生来不聪不竣不伶不俐,起初看来是个泥团肉块,后来交了时运,一朝发作起来,做了掀天揭地事业、拜将封侯的。譬如三国时有个孔文举,年方十岁,随着父亲到洛阳任所。那时有个司隶校尉李元礼,极有名头,大官府要去见他,无论本官尊重,那门吏也十分装腔作势,一时难得通报。
彼时文举乃十岁小儿,大模大样持了通家称呼的名帖,来到李府门上,说道:“我是李府通家。”门吏看见小小聪俊孩儿,即与通报。后来李公接见,问道:“足下与我那里通家?”那孔文举不慌不忙,从容对道:“昔先人仲尼与尊公伯阳有师友相资之谊,在下与老先生就是奕世通家也。”许多宾客在座听了,各各称奇。彼时座中有个陈建,最后方来,李元礼将此言说与陈建,陈建便道:“小时虽则聪明,无不了了,大来未必果佳。”文举应声说道:“看来老丈小时定是聪明,无不了了的了。”满座之人俱各笑将起来,称道:“如此聪明,异日不知至何地位!”那知这张利嘴人人忌刻,后因父亲朋党之祸,毕竟剪草除根了。
可见小时聪明太露,乃是第一不妙的事。』如今再说一个小时懵懵懂懂,后来做出极大的功业,封了极大的爵位,纔是奇哩!
此人出在隋末唐初,正当四海鼎沸之际,姓汪名华。初时无名,只有小字兴哥。祖居新安郡--如今叫做徽州府--绩溪县乐义乡居祝彼处富家甚多,先朝有几个财主,助饷十万,朝廷封他为朝奉郎,故此相敬,俱称朝奉。
却说汪华未生时节,父亲汪彦是个世代老实百姓,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徽州风俗,原世朴实,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做到十余年,刻苦艰辛,也就积攒了数千两本钱。到了五旬前后,把家赀打总盘算,不觉有了二十余万,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
算帐完了,始初喜喜欢欢,举杯把盏,饮至半酣,忽然泪下。
众伙计问其原故,那汪彦道:“我也不为着别的,只因向日无子,从南海普陀洛迦山求得一子,叫名兴哥。看来面方耳大,也成个人形,其如呆呆痴痴,到了十五岁,格格喇喇指天划地,一句说话也不明白,却似哑子一般。遇着饮食,不论多少,好像肚内有热炉热灶,无有不纳,岂不是个焦员外的令郎、胡永儿的丈夫?虽挣了泼天家俬,也是一盘瞎帐。”说毕便凄凄惨惨、呜呜咽咽哭将起来。伙计中有那当心的上前劝慰宽心,有劝到扬州、苏州再娶一妾,另生几个好的;有拿酒复来相劝,猜拳行令的,都也不在话下。临了来有个老成的伙计,走近前来,说道:“老朝奉,不消着忙,明年小主十六岁了。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我看小主虽则不大言语,心中也还有灵机,面貌上也有些福气,不若拨出多少本钱,待我帮他出门学学乖,待他历练几年就不难了。”一面就与兴哥说知,兴哥也就把头点了几点。众伙计尽道:“小朝奉心里是明白的,不难!不难!”俱各散讫。』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众伙计会同拜年吃酒,中间老成的伙计也就说起小朝奉生意的事。
汪彦道:“他年小性痴,且把三千两到下路开个小典,教他坐在那里看看罢了。”约定二月起身。
言之未已,那兴哥斯斯文文立起身来,却明明白白说道:“我偌大家俬,唯我一个承载,怎么止把三千两与我,就要叫找出门?却是不够!”众尽骇异。连那老朝奉听了也不觉快活起来,接口连声说道:“果然奇了,也说的话公然不差!想是福至心灵了。”满堂人俱各称羡,只待二月初头整备行李,拜别父母起身。汪彦占卜得往平江下路去好。那平江是个货物马头,市井热闹,人烟凑集,开典铺的甚多,那三千两那里得够?
兴哥开口说:“须得万金方行,不然我依旧闭着口,坐在家里。”那老朝奉也道:”他说得有理。”就凑足了一万两。未免照例备了些腌菜干、猪油罐、炒豆瓶子,欢欢喜喜出了门。那老伙计已预先托人把铺面房屋、招牌、架子、家伙什物俱已停当,拣了黄道吉日开张,挂得一面招牌。就有一个人拿着十个盒子进来,说道:“贺喜!贺喜!愿小朝奉开典铺,就趁了十对盒利钱,权且当银十两做个采头。”小朝奉听见说得快活,他道:“我也不要你的盒子,送你二十两,酬你这个好意。”那伙计道:“小朝奉不可听他!这是从来市井光棍打抽丰、讨采头,都是套子,不可与他!”小朝奉道:“第一次也让我一个顺利。”伙计就闭口了。不多时,又见一伙衣冠济楚,捧着表礼走将进来,看名帖上整齐数来四十位,道是上下排邻,闻得朝奉开当,各人备了一两分资外,又添出五分,备了花红糕酒,都来贺喜。
那伙计们少不得请出兴哥来做主人,众邻舍俱各唱喏称贺,分宾坐了,奉茶而别。兴哥回转身,欣欣喜色,对众伙计道:“怪不得老朝奉卜得此地开典好,就是这邻舍高情却难得的。”一面就把那封的分资扯开两个,众伙计上前把手按住道:“这是套礼,收不得的。过日备戏设席请他后就返璧了。”兴哥道:“方纔二十两出门,今就有四十两进门,就是对合利钱佳兆,如何方纔当盒子的不要赏他!”说毕,仍旧把众分一卷拿了进去。急得众伙计没些布摆,只是叫苦。少刻,唤一个小郎进去,兴哥打开银库,拣出十两一锭的银子,齐齐整整封作四十封,一面换了衣服,备了名帖,走出铺中,说:“我如今要答拜了。”众道:“四十封银为何?”兴哥道:“陌生所在,难得他们盛意,备礼答他。”众伙计道:“只消费二十两一席戏足够了,如何要这许多?”兴哥道:“你们只晓得小家子局面,既在他地方开铺赚钱,就要结识地邻,日后有些事情也得便宜。自古道,他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这十两头也只照历来规例,亦未见得从厚。”言毕径出门去,各家一一送了。那些邻舍个个喜欢,人人快活,称道:“小朝奉是个大方。”那些伙计齐齐叹气跌脚,只好付之无可奈何。兴哥拜完客,回到铺中坐着,忽见一人牵着匹马进门道:“在下是个马贩子,贩了二十匹马来,马价都是百金一匹的。遇着行情迟钝,众马嗷嗷,只得将一匹来宝铺,当五十两买料。卖出依旧加利奉赎。”兴哥心中爱着骏马,一眼看了就笑起来,那伙计道:“开口货从来不当,出去!出去!”兴哥道:“省会地面马也是要用的,若不当与他,那四十九匹都饿死了,岂不可怜!”说毕就进里边去。那伙计越发回他,那马贩蜘蹰半晌,只要候小朝奉出来讨个下落。那知不多时,兴哥捧出元宝两锭,就招马贩进中门递与他。马贩说:“当一锭够了。”兴哥说:“你辛苦来此,须要趁钱方好。如何百金的价止当五十两?却不折了本么。快去!快去!”那马贩倒地四拜,称谢恩主而去。众伙计尚自不知,兴哥又到铺内坐定。又见一个穷人手拿铁锅一只,伙计上帐当去三钱。纔出门去,兴哥把头一侧,想道:“这个穷人家里不过一只锅子,将来当了,老婆在家如何煮饭?三钱银值得恁么?”便走出铺来,提了锅子出门就上了马,一溜烟追去。毕竟寻着那个穷人还了他去。
铺中众人沸沸的说起方纔当马之事,又吃了一惊,只等兴哥回,大白日里就把当门关上,接着兴哥到厅上。众伙计一齐依次坐下,老伙计道:“小主人,你从幼未经出门,你的身命干系都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万两本钱也是在老朝奉面前包定加三利息来的。纔得一二日,如此颠颠倒倒,本钱倒失去了一大块,将来怎么算帐?”兴哥道:“不难,不难。若说加三利息,你们众人就提了三千两去,余下本钱听我发挥罢了。你们众伙计旧规俱已晓得,不过以旧抵新,移远作近,在日用使费上扣刻些须,当官帮贴中开些虚帐,出入等头银水外过克一分,挂失票、留月分、出当包、讨些酒钱,就是你们伎俩,这都不在我心上。你们要去就去,难道我迷失了路头不成?”众人被他数落,顿口无言。那老者谅来不可挽回,同众人备细写了禀帖,第二日就回徽州报信去了。兴哥看见老者去了,心中不觉又松了一松。不久传闻出去,那些邻舍也都装了套子,或有说官司连累、急急去救父母的,或有说钱粮拖欠、即刻去比卯救家属的,或有说父母疾病临危、要去调治结果的,或有说修盖庙宇、砌造桥梁,一时工钱要紧的。兴哥一一都不要当头,悉如来愿,应手给散去了。不一月间,那一万两金钱俱化作庄周蝴蝶。正要寻同乡亲戚写个会禀接来应手,那老朝奉风快的到来,进门前后一看,叫屈连声,揪着兴哥就打。兴哥只是嘻嘻笑道:“人若不把钱财散去,老朝奉在家只消半间草屋,几件布衣,数担粗米,一罐猪油,就够一生受用,何必艰难险阻,-一搬到土窖中藏着,有何享用?”老朝奉听了又气又恼,晚年止得此子,也无可奈何。次日即收拾行李,退还房屋,一伙回家去了。就把兴哥关闭一室,不许在外应酬。』不觉过了四五个月,不知那里寻得五千青蚨,把家中做生意的伙计都送一百文,按月要收二百文。众人在他门下也就胡乱送些与他,不半年也就积起三万上下。老朝奉知道,说“此子如今晓得生放利钱,比当初大不相同。”兴哥只做不知,终日在私下盘放钱债。老朝奉一日道:“你既知积财当积的,何不再拿一万出门去?”兴哥道:“前番一万胡乱散去,如今却要多些,刻苦翻转那一万本来纔好。”老朝奉道:“说得有理。”问道:“依旧开当罢?”兴哥道:“典铺如今开的多了,不去做他。须得五万之数,或进京贩卖金珠,或江西浇造瓷器,或买福建海板,或置淮扬盐引,相机而行,随我活变。再不像前番占卜到平江府做的故事也!”老朝奉听了,爽快就兑下五万两,选下八个家人,仔细包包裹裹,共有三十担行李。兴哥依旧骑着那马,潇潇洒洒起身,同管家在路上商量得明州晒白鲞生意绝好,径往明州进发。
访得浮桥外下塘街有几家大财主经纪,可以安身,就在他家住下,安顿行李。那知这晒鲞生意三月中方得通行,兴哥却早到半月。下处甚是寂寞,带了几个家人且到洛迦山游玩数日。一者进香,再者观海,亦是畅事。那山上清净道场并无俗客。次日单身步月而行,不觉信步一直到那钓鳌矶上,对着汪洋大海盘膝而坐。月色正中,海气逼得衣袂生凉。正待回步,忽见矶边树林影里走出一人来,兴哥也道:“奇怪,奇怪!”依旧坐下。
那人将到面前,兴哥看见,唬了一跳。看那人时,生得好生怪异:只见两只突眼,一部落腮。两鬓蓬松,宛似钟馗下界;双眉倒竖,犹如罗汉西来。雄纠纠难束缠的气岸,分明戏海神龙;意悠悠没投奔的精神,逼肖失林饿虎。
兴哥上前将欲迎他,他却高足阔步,全不相照,竟靠在一块凌空奇峭石崖嘴上,大叫一声道:“老天,难道我老刘就罢了不成?安得五万金,成我一天大事也!”兴哥听见说得奇异,上前问道:“君家于此地要这五万两何用?”那汉把眼一横道:“乳臭小子,那知我事!”兴哥道:“我非乳臭,足下亦不免为田舍翁。看得五万金恁难得也。”那汉一闻此言,便回身下拜道:“我诚小人,不识君家何以应我。倘能周旋,明年此月此日,仍纳于此地。还君十万,不食言也。”兴哥道:“去此不远,我当为君谋之。”即相拉下船,随从约有十五六人,一径回到下处。请出主人,唤小郎们搬出行李,将五万两一一交付那汉收去。那汉道:“足下此马无甚用处,一井付我驰去,异日仍以此马还君。”兴哥连忙解辔送他。两人拱手而别,并无他言。
主人与小郎在侧看了,心目俱呆,不知甚么来历。
主人只道是洋里捕鱼客人或是沿海卫所经纪,也都只在那晒鲞的生意上作想。问道:“此君何姓何名?住居何处?”兴哥道:“我也不知。”即便叫小郎们收拾回去。小郎道:“官人此来为何?”兴哥道:“此番生意对本利钱,甚是省力爽快。”小郎也只得随口含糊谢别主人,依着旧路回去。总来不及两月,已到家里。老朝奉问道:“甚么生意回身得快?”且见行李轻松,吃了一惊。兴哥道:“对年对月对本利钱,也是顺利的了。”老朝奉仔细问其下落,并无一字回答。问及小郎,那小郎拿指头指着道:“只去问他,我们一毫不知。”那老朝奉急得心躁,兴哥且自意气扬杨,指着前边该造大厅,指着后边该造大园,不痴不颠,说来的都是迂阔之论。老朝奉揪发乱打,兴哥嘻嘻道:“不要难为了十万贯的财主,且自耐烦到了明年此时,若无本利到家再吵再闹也未迟哩。”老朝奉只索忍气吞声,且自排遣过去。』不觉倏忽已到次年二月初边,老朝奉便要催他起身,兴哥道:“不消早去,只要此月、此日、此夜到那此地便了。”果然俟到边际,兴哥束装前往。先一日已到彼处,暂借僧房歇下。到那晚上,依旧单身坐在钓鳌矶上。黄昏已过,二更悄然,将及三更,那树影里果见一人大踏步走上矶来,叫道:“思兄何在?”兴哥向前相见,把臂道:“真信人也!去年所事如何?”那汉道:“多承恩兄慷慨施助,将这五万银子即在沿海地方分头籴得粮食,接济六郡义师,方无脱巾之变。幸叨天庇,自去年四月起兵,所到之处,犹如破竹。今总计之,闽粤以及浙西已得三十郡县,那海中倭夷岛寇归并百十余处,令海中所称海东天子刘琮即弟也。去年潜身上普陀窥探,亦因营中缺乏粮食,欲向洛迦僧房借些布施,不料大大丛林也就荒凉这个模样。敢问恩兄高姓大名?”兴哥道:“山野鄙人,毫无施展,留此姓名为何?”刘琮道:“一言相许,五万衔恩,尸以祝之,犹难为报。何姓名之见吝也?”兴哥遂将姓名、住居一一道破。不料从旁扈从的人早已闻报,一面将十万金钱差人送至徽州汪宅去矣。兴哥一些不知,这是后话未题。且说刘琮邀了兴哥,搬了行李,到得河口,舣舟相待。不一时间,到了大港,却有数十彩鹢鳞次而集,旗帜央央,就有许多披甲荷戈的,整齐环列。
刘琮扶了兴哥过船,便令发擂鸣金,挂帆理帜,出洋而去。未及五更,大洋中数万艨艟巨舰,桅灯炮火震地惊天,到了大船即唤出许多宫妆姬嫔,匍伏舱板之上,齐称恩主,不减山呼。
兴哥也不自觉,如在云梦之际。一面开筵设席,极尽水陆珍馐;一面列伍排营,曲尽威严阵势。异方音乐,队队争先;海外奇珍,时时奏献。兴哥整整住了十余日,即欲辞归。那刘琮苦苦相留,情难被袂,心知兴哥不能再住,一边备了船只,逐程相送;一边捧出盖世奇宝,举以相赠。兴哥眼也不看,一概固辞。刘琮道:“此非酬报恩兄之物,聊伸万一之敬。今既不受,弟有锦囊三个,异日要紧之际开看便得。此时未可预泄其机也。”兴哥再拜,受之而别。一路归家,也不知刘琮将钱十万早已送到家下,不题老朝奉喜得不了。』且说兴哥依旧潇潇散散而回。老朝奉闻得兴哥回来,举家迎接。一门势利都来道喜。兴哥心已知之,绝不露一毫于颜色。
那些积年伙计俱来备席接风,兴哥也一家不领,每人却送青蚨五万文,以偿日来相与之意。却在后园造起百尺高台,做那观星望气的勾当。耳边厢听得道路传闻,说海东天子占了某州某县,渐渐逼近徽州,人头上荒荒乱乱,俱作逃窜之计。兴哥道:“此时事势已急。”开一锦囊看时,如此如此。彼时隋朝既灭,唐主登基。兴哥即便具了一道章疏投在节度使李冕衙门,求其代为申奏。自认团练义兵三千,不费朝廷一文一粒,保障一方,直待平定之后方受朝廷封赏。李节度正在求贤枯渴之际,得此一疏,即便转奏,奉了唐皇新旨,暂授南路总管之职,听其便宜行事。兴哥整师振旅,即使起行,驻师温、睦之间。那些倭夷岛寇不奉正朔,听得义师初集,即便整兵秣马,一拥前来,把那兴哥全营密密层层围得铁桶相似。正在危急,再拆一个锦囊看时,他便营中立起十丈高竿一面黄旗,上书“海东十三路水陆全师都总管汪”。外边这些岛夷看见旗号,许多头领即便把旗从左一招,兵分四路,左右前后屯扎住了。不多时西南角上一队兵马约有百十余人,牵着白马一匹,飞星相似,直奔前来。一人口称“奉海东天子命令,特送白马奉还恩主汪老爷的”。营中接应报去,即令先锋出来接了来书,验看明白,果是当初之马。此马浑身雪白,背上前后却有黑斑二十四点,唤名葡萄雪,乃是一匹龙马。始初当在铺中,兴哥原是爱上他的,却叫不出他的名色。自从刘琮借去,一到海滨如鱼得水,刘琮骑了他,到处成功。海东一带地方都认得一条白龙现世,不但人人畏惧,就是万马见了亦个个攒蹄委鼠,无不慑服他的。
兴哥骑了此马,那沿海地方都认做刘老爷领兵到来,处处摆围迎接,俱应殷懃,不烦一矢,俱已贴然归顺。始初止得义兵三千,不及一载已就招徕有五万之众。俱是刘琮有令在先,要让漳南十镇报他做个绝世奇功。不料第三年间,天时亢旱,师次建南,米价腾涌,至六两一担。人民汹汹,军士嗷嗷,朝暮将有不测之变。兴哥心急,又将一个锦囊拆看,却也正为此着。
即传令沿海烽台俱将白带号旗挂起。海上哨探小卒不日报知刘琮,即便传令速备粮米五百万石,沿海前来接济。军民欢声振地,一路太平。兵马已抵漳南大镇,建牙开府,大布雄威。节度藩镇屡屡奏有奇功,不时颁有钦赏,官爵加封至吴国公,衮衣玉带,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不啻天子行为。正在热闹之际,一日刘琮连宗千号,直进南海小洋,要与吴国公相会。吴国公开营列队,倍加整肃威严,一如前日刘琮相见故事。酒至三巡,刘琮即问:“恩兄自前岁出山,闻得尚未娶有尊嫂。若不相弃,舍妹年已及笄,情愿送来,以备箕帚。”吴国公见说,逊谢不敢。刘琮决意再三,吴国公道:“婚姻大事,在家入告父母,身在海外当奏明朝廷方敢应允。但弟又有一说,既与吾兄结为姻亲,方今圣天子正位之初,四海闻风向化。吾兄与其寄身海外,孰若归奉王朔?在内不失纯臣之节,在外不损薄海之威。
那人道:『在下幼年不曾读书,也是道听途说。远年故事,其间朝代、官衔、地名、称呼,不过随口揪着,只要一时大家耳朵里轰轰的好听,若比那寻了几个难字、一一盘驳乡馆先生,明日便不敢来奉教了。』众人道:『太谦,太谦!尊兄口比悬河,言同勒石,胸中必多异闻异见,正要拱听。』各各称谢而去。
总评读此一则者,不可将愚鲁、伶俐错会意了,就把汪兴哥看作两截人。其所以呆痴哑巴,万金散尽,正其所以保五州、封越国根基作用也。天下奇材大侠,胸彻万有,心中具不可窥测之思,观人出寻常百倍之眼。一言一动,色色不欲犹人,况区区守钱之虏、卖菜之佣,锱铢讨好,尤其所鄙薄而诽笑之也久矣。如隋末兵乱,世事可知,不能为唐太宗,则为钱武肃。
若虬髯海外,又是一着妙棋,彼固不屑为北面事人之辈者也。
处此乱世,倘不克藏身,露出奇材大侠,非惟无可见长,抑且招祸。即五代歙人汪台符,博学能文章。
徐知诰出镇建业,台符上书陈利病,知诰奇之,宋齐丘嫉其纔,遣人诱台符痛饮,推石城蚵皮矶下而死。此不能呆痴哑巴之验也。篇中摹写兴哥举动,极豪兴、极快心之事,俱庸俗人所为懮愁叹息焉者。孰知汪君等算然,掀天揭地,已如龜卜而烛照之矣。锦囊一段波澜,固是著书人宽展机法耳。此则该演一部传奇,以开世人盲眼,当拭目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