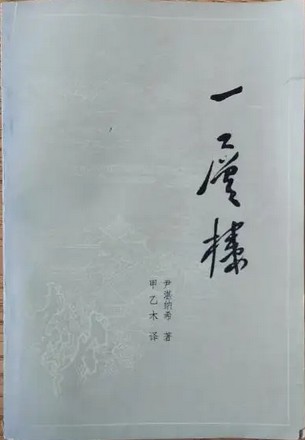话说鄂氏太太带了女儿湘妃往忠信府而来,一路上也无雨水之耽搁,但见柳丝拂尘,金风掠衣,一日来到贲府前,因前头报信的先已到了,至大门前下车时,早有垂花门的媳妇们迎出拜见。
至忠信堂侧门时,金夫人带着众姑娘们迎了出来,与鄂氏太太携手相见了。炉湘妃向前跪着请安,金夫人忙扶起来,只见他玉容憔悴,柳腰益细,芳体颤颤,娇喘吁吁。不觉泪水满目,失声道:“哎哟!这孩子如何瘦成这个样儿了,这般气弱,如何又行跪礼,与姊妹们相见时不必跪着了。”
彼时,德清、圣萃芳、琴自歇、熙清等都请过了鄂氏太太安,又与炉姑娘相见,看他那般光景,大家无不心酸。
金夫人笑道:“今日晚了,不必进见老太太,明早再去请安吧。”遂不入垂花门,走过润翰书屋旁边,入逸安堂院中来了。只见贲夫人在彼立候,大家互相厮见,说说笑笑入逸安堂坐了后,鄂氏先问候了老太太,再问贲夫人何时来的。贲夫人一一说了,又笑道:“鄂氏太太,我二人真个算是有奇缘了,每到这里都能相见,那年来时,我也在家来着,这会子我回家来,你也来了。”又问金夫人道:“老爷说书房有客人,先去了。璞玉在那里?怎么这时候还不出来。”金夫人笑道:“我因他病刚好了些,怕他听见说来了,出来迎接累着,所以没叫他知道先报的消息。”说毕,回头道:“丫头们在那里,去一个叫你们大爷来。”众丫头们如莺啭燕语,齐声答应着,玉清忙叫璞玉去了。
且说,璞玉望着湘妃来,直等得日乏心烦,所以病也不能除根,大夫刘兼让也就不能抛了去,隔一日投一药的养着。璞玉也有时往介寿、逸安二堂来请安,只不曾到学里去。那日中觉,直睡到日影西斜,待孟嬷嬷叫了几遍后,才醒了起来,无精打采的吃了一碗茶,靸着鞋,手中拄根细竹杖,出至松月轩回廊檐下,看玉儿喂雀儿。忽然玉清从外边走进来,笑道:“看你这病人,却在这里喂鹦鹉呢,快跟了我来吧,老爷叫你呢。”璞玉拄着杖浑身打战道:“老爷叫我做甚么?”玉清见他那般可怜样儿,笑道:“我告诉你实话吧,不是老爷叫,炉姑娘、鄂氏太太他们来到了,福晋太太叫你去相见呢。”璞玉听了,如奉九重恩诏,也不管是真是假,抛了竹杖,靸着鞋,慌忙跑去。福寿在后,一头笑,一头拾起杖,赶上来道:“你且穿好鞋,整一整衣裳,这是甚么样子呢。”璞玉方止住脚步,催促丫头们,取衣裳帽子来换了,依旧拄着杖,往逸安堂来。只见廊檐下锦屏、丁香等众丫头们,都围着画眉说话。画眉见璞玉来了,佯做不知,扭过脸去与别人说笑,毫不理他。璞玉也无暇问话,将竹杖依在门旁,入外间看时,又不见炉湘妃,只有鄂氐太太坐在中间,金、贲二夫人两侧对坐,吃茶说话。璞玉向前跪下请安,鄂氏太太见了,拉起手来道:“嗳哟,外甥哥儿,又如何这么瘦了,你的病可好了?那好大夫可还在这里?”一连问个不了。璞玉一一答应着。金夫人向璞玉道:“你炉姐姐也来了,在里间呢,你不进去见见?”璞玉遂入内间来看时,只见在窗前炕上,德、圣、琴、炉、熙等众姊妹们正坐着说话。璞玉遂屈膝打千儿问道:“姐姐身上可大安了?”
湘妃忙起身还礼,四目相视,两心双悲,几乎没落下眼泪来。湘妃见璞玉病虽不重,但面容赢瘦,衣领宽转,带扣已松。璞玉怎能收回已出来的眼泪,故意打个喷嚏,泪涎一齐流了出来,方问道:“炉姐姐得了甚么病,瘦成这个样儿了?”湘妃勉强笑道:“想必是伤寒时疫,耽延开久了,所以病了这些日子才好的。”
璞玉道:“甚么时症,如此久缠人?”湘妃未及回话,琴自歇接过来笑道:“病症的事那里能够说得准。你去年冬天那个喷嚏症,原已好了的,如今见了炉妹妹,如何又发作起来了呢?”说得德清等满屋人都笑起来了。一时搬过饭来,大家在逸安堂吃了饭。未几,贲侯入内相见毕,即打发鄂氏太太母女二人都住在绿竹斋了。
那大夫,如料敌用兵,度病投药,不过几日,二人病已大愈,渐渐平复如故了。也是因金夫人常叫二人一处饮食,真个心病投以心药,那得不好。常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也不知是大夫有才,还是大夫行运,不知二者孰是。
且说那时,因贲府本家,贲寅的儿子瑶玉娶亲,因此,这边府内,自老太太起,金、贲二夫人,德、圣、琴、熙四位姑娘,一连几日都去赴宴。待事将完,贲寅夫人德氏,又亲领自己女孩儿宫喜过来,将鄂氏太太请过去了。只璞玉、湘妃二人,都在调养,所以没去。
是日,璞玉往绿竹斋来。一则因前几日,二人虽在一处饮食,当着众人,不好畅谈心事,所以趁此清静时,说几句话。再则要问明他临回去时,如何翻脸不理,至今疑心不解之故。一面想着跨进门槛来,只见湘妃方吃完药漱口呢。见了璞玉抬身让坐,璞玉忙坐在先来几次时常坐的椅子上,笑道:“自姐姐去后,这屋里空落落的,檐下栖雀,院中翠竹,也都似思慕姐姐的,雀声悲伤,竹露滴泪,真个使人不胜其悲了。”炉湘妃笑道:“你还说那些哄人的假话做甚么,当我未去之前,你本已不理我了的,既去之后,还未必到这屋里来呢。”璞玉听了此言,心下焦急起来,道:“姐姐如何这般说,我璞玉虽愚,也没有不知爱与恨之理,我自幼得识姐姐以来,一身一心,除了姐姐别无知心者,只当终此一生,除了姐姐再无可依可靠的人了呢。”说到这里,声泪俱下,又道:“姐姐如果这么说起来,可真是冤死人了,别的不说也罢了,但说自姐姐去后,对此壁上书画,也不知伤过多少心了。”一头擦眼泪,一头抬头看时,那壁上的画早已换了。
原来,湘妃一回来,看了那诗,羞往日不警之题,忙收起来了。如今见璞玉如此焦躁哭泣,知其心诚,心中也不免酸楚,只是暗中流泪,又勉强说道:“璞玉你说话须说明白了,你这‘知心’是甚么话?”璞玉道:“是极好的话了,古言云:‘士为知己者死,妇为悦己者扮。’”湘妃道:“既如此,你的知己,这府内也不只我一个人了,自你亲姐妹起,圣萃芳、琴自歇等众姑娘,皆可称为你的知己了,你一人一身,那里替这许多人死得及呢?”璞玉道:“知己也有个分别,也有知彼不知己的,象你我二人,可称为彼此相知了。只是欲问姐姐一句话,去年临去时,如何忽然总不理兄弟了?”湘妃起初听他讲论知己,已自伤心,噙了一眼泪,如今忽然听他说不曾理自己的话,正中前日怨恨之心,再不能按捺,泪落如雨,声音颤抖,道:“倒是我不曾理你了?其实你自己拿大起来,不理我了,反来排我的不是。我本是来人家这里,看着人家脸子过日子的人,而且又不似人家有别的知己,我如何不理人呢。”越说越哭,手里的帕子都已湿透了。璞玉见此光景,心中一阵酸痛,又焦急道:“这算得甚么要紧事,姐姐就如此着急,我如果是因为有了别的知己不曾理你,只好叫这颗心迸了出来给你看就是了。”不待说完,失声大哭,泪如泉涌,二人不言不语,对哭起来。湘妃见璞玉未带巾子,只管用那绛色宫绸衫袖拭眼泪,便一头哭,一头伸手拿起搭在衾上的青丝巾子扔了过来。
璞玉忙接过来擦眼泪。又见湘妃手里拿的帕子都已湿透,眼泪又簌簌流个不住,遂向前到炕沿上坐下,一手搭在湘妃肩上,一手拿巾替他擦脸上的泪。湘妃忽然推开手,往自己榻上坐了,道:“璞玉你这是戏谁,我们也不似从前那么小了,如何这等粗鄙!”
璞玉跌足道:“你看你这性子,这样又如何叫我亲近呢?所以了,怕你生气,谨慎起来罢,你又说我不理你了,尽着这么闹起来,叫愚弟如何才是呢?”湘妃越发哭了起来,啐道:“‘如何才是’是甚么话?你要理起人来,偏这么鄙薄不成?”璞玉越发焦急道:“我并无敢轻慢姐姐之处,若说姐姐不想兄弟,我病时你如何也病了?若说是想,偏又这般寻疵责怪,这是甚么意思?”湘妃不语,又哭个不了。
画眉在外间站着,听得不耐烦,料道叫他两个尽着这样纠缠起来,没个了局,遂入内问来,将璞玉从炕上拖了下来,道:“我的大老爷,你请回家吧,我实说与你吧,你若敬重我们姑娘,就看看我们那边敬重你们德姑娘之例。不然,趁早请往一边去,你不可拿着我们姑娘与你那别的知己比,姑娘虽然也心里想着你,却不是非礼与你一言一笑的人。我的至诚忠言,就止于此。我们这里也没开眼泪铺,你只管到这里来哭着给谁看?你记住我这话就是了。走吧,走吧!”耍笑似的,一推一拉的把璞玉推出绿竹斋去了。
炉梅初时见画眉这般做作,骂道:“这丫头疯了不成?”画眉全不理,将璞玉推了出去,返身进来。湘妃责备道:“女孩儿家,全不知羞惧,拉着爷们的手,成何体统!”画眉笑道:“若不这么着,那赖皮子如何肯动,若不这么说他,那愚顽如何知道。只管放赖坐着,昧心哭着,一时来人看见了,岂不又当做甚么错处打趣起来呢?”湘妃道:“我们的事正当清白就罢了,何须怕小人打趣。”画眉道:“虽然如此,燕雀安知千里鹏程?他们只比着自己当做真的想罢了。”湘妃道:“虽然,你的口角、行事儿也太粗鲁了。”
彼时,璞玉还不曾去,站在窗外听了那些话,虽因画眉鄙薄自己过分而怒,却把个疑心冰块化为乌有,通悉了炉湘妃的心底。方欲再说话时,玉儿走来道:“老太太他们都散席回来了。”遂忙往介寿堂请安来了。
且说,老太太见了贲寅的儿子瑶玉所娶的媳妇,容貌见识都极好,亦且喜事办的也极热闹,心中也觉欢喜。回来闲坐时,笑道:“看人家喜事有多好,多热闹!近来我们家里虽也办过姑爷纳礼的喜事,终是打发人的勾当,毕竟不热闹,怎么想个法儿,办个筵席,大家乐乐才好。”圣萃芳笑道:“我记得,璞玉兄弟是七月十七日的生日来着,再过两日便到了,届时我们大家凑份子作贺,请老太太和舅母乐一乐如何?”德清道:“如此真个最好,我们也趁这机会乐一乐。”琴自歇笑道:“‘趁乐’这话也奇了,谁说要存心难为你了呢?”说的众人都大笑起来。德清转身向琴自歇笑道:“好呀!近日来,你行动就来奚落我,偏把你娶给璞玉,那时我便成了你大姑子,看你还怕我不怕了。”圣萃芳笑道:“琴妹妹,可听见了?常言道:‘晴干开水道,须防暴雨时。’你这时趁早设法叫大姑子欢喜着,日后也好做兄弟媳妇呢。”
老太太越发笑了起来。琴自歇不待他说完,即走了出去。刚出至介寿堂后门时,正遇璞玉顶头走来,看他两眼都哭红了,遂柔声说道:“兄弟只管哭做甚么,人家要给你作生日呢!”璞玉因好几日不曾听他说话,如今见他又忽然出此奇言,不觉心中欣慰,忙问道:“谁给我做生日呢?”琴自歇不待他说,早走过去了。
璞玉忙入介寿堂,请了老太太及贲、金、鄂三位夫人安,说了几句话,遂转身出来,往海棠院追问那话来了。
琴自歇正与瑞虹说着,告诉家里的话,见璞玉进来,起身笑道:“贵人来了,请坐。”说着让了坐。璞玉问道:“姐姐和瑞虹说甚么呢?”瑞虹道:“我们姑娘九月里要回去,已说给家里差人来接了,就说这个事呢。”璞玉笑道:“好好的住着,如何又忽然想来回去的事来了?”琴自歇笑道:“好好的住着不回去,偏病了才回去不成?”璞玉无言可对。过了一会子,琴自歇叹道:“唉!不回去怎么着,来了,住了,托老太太、姑母的福,吃了,穿了,姊妹兄弟的心意,笑了,玩了。我也有你们一般的家园,有父母,有兄弟,难道我是不想家、不想父母的人了?”璞玉道:“虽然如此,也须等着大舅太太、炉姑娘他们一同回去罢了,何必这么忙呢。”琴自歇笑道:“我如何能等炉妹妹,他们原是受过深恩的,即能以此地为家。我是父母俱在,不能自主的人。”璞玉听了,又无言可对,遂问道:“姐姐方才说,给我做生日是哄谁?”琴自歇道:“是萃芳姐姐起的事,领着大家出份子,为要使老太太行乐的。”璞玉问道:“那么,姐姐入不入呢?”琴自歇笑道:“如何不入,住近一年了,颇蒙贤弟高情厚谊,今将归去,正不得答谢处,遇此现成喜宴,敬杯寿酒,也是尽我一番薄意了。”璞玉深深打了一躬道:“愚弟本无分毫好处,承蒙姐姐如此错爱,真个叫兄弟愧赧无地了,但因无可相报,只好且谢恩德,铭于肺腑了。”琴自歇笑道:“何须必言相报,只望贤弟日后果真不忘,到建邑地方,倘能一探愚姊,即感恩不尽了。”
不说二人说得投机,早已日色昏黑,不一对点上灯来了。璞玉无奈,只得离去。琴自歇送至房檐下,见外边黑了,因璞玉在炕上脱鞋久坐,又因下台阶时,看不清阶磴,只顾踉踉跄跄起来,琴自歇忙唤凭霄,扶着璞玉送回松月轩去了。
后天便是璞玉的生日。次日松月轩的丫头们,黎明即起,洒扫室内时,见璞玉卧床下放的两只鞋,却成了两样的,一只原是璞玉穿的鞋,一只却是个半旧的厚底绣花鞋。大家不禁惊异,当是本屋丫头的鞋,查了一遍,却又不是,大家只管交头接耳嘁嘁喳喳起来。福寿听了,悄悄喝住,道:“你们别只管声张不相干的事了,昨儿午饭后,大爷不是靸着鞋,说大小两样来着吗?”说着拿过鞋来看时,真个不是自己屋里丫头们的鞋,正拿着细看时,玉儿从旁道:“我前儿见凭霄穿着这么一双鞋来着,昨儿夜里又是他送来的,莫不下台阶时窝了脚,二人错穿了,也未可知。”不待说完,福寿道:“知道了,别说了。”因喝住玉儿,袖了鞋,来至介寿堂东北门洞里看时,往翠云楼入海棠院的两个门中间,放着璞玉的鞋,福寿见了大惊,忙抛了那只绣鞋,拾起璞玉的鞋袖了。回看两边时,东西两门都依然关着,心中暗喜道:“亏我们见得早,不然,若是传到老太太耳内,几乎成了大事呢。”遂转身回来,因起的早,各屋里人都方醒未起,所以未遇一人。福寿来时,璞玉还睡着,遂叫了小丫头们来,再三叮咛:“不可叫一个人听着。”日出后,玉儿抽空儿至福寿放鞋处看时,早已不见了,东西两门都依然关着,心中惊异而回,不提。
早饭后,姑娘们都聚在介寿堂,商议贺生日出份子的事,老太太笑道:“如何叫姑娘们出份子呢,用几桌席问明白了,告诉大厨房里预备着就是了。姑娘们要尽人情,各自预备礼物送罢了。”
又唤孟嬷嬷来,吩咐:明儿叫璞玉早早起来,好好教给他过生日的诸般礼节。孟嬷嬷答应了,见老太太无话,方慢慢回道:“服侍璞玉的丫头们都大了,一早一晚不方便,所以先时曾回了福晋太太,添了一个小丫头了。如今跟璞玉的小厮们,越发不能入内,一个小丫头服侍不过来,望再添个小丫头,能换着班儿服侍才好。”
老太太向金夫人道:“近日也没送丫环进来,那屋闲丫头们多,我也不知道。”金夫人道:“若说闲丫头,还是凭花阁里,除了服侍姑娘们的丫头,还有五、六个闲着。”老太太道:“既如此,调个伶俐些的给他就是了。”琴自歇趁便道:“我看凭花阁有个叫代小儿的小丫头,既伶俐又懂事,正好与玉儿一对。”老太太命唤来看时,真个清秀姣俏,叫到身边,只顾端详起来。金夫人笑道:“老太太想是不认得,他是马圈里叶儿的丫头呢。”老太太笑道:“可不是吗,我看就象是咱们院里生的人,只是想不起那个媳妇的丫头了。他爹不是叫甚么王三的么?那两口子倒养了这么个丫头。”又问了几句话,便交与孟嬷嬷跟去了。孟嬷嬷刚出去,即有垂花门的舒二娘进来回道:“那府里德二太太领着新媳妇磕头来了。”只见从外边已有一群穿红着绿的媳妇丫头们,跟着德氏进来。欲知新媳妇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