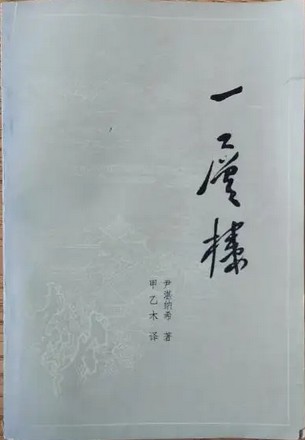话说璞玉追问“银沙园中足迹圆”的缘故,琴默笑着慢慢说道:“你们自己不解诗意,偏又爱寻疵责人。我且问你,这首诗的题意是甚么?”璞玉道:“这诗倒并非专以梅花为题,大要以今日之事为题的。”琴默道:“既如此,总得把今日诸事都烘染出来才是,只因不是长诗,不能备述诸事,但须得说出其主要几件,而今日主要的莫过于风雪了。这诗头句说了花瓣,次句也只说了花蕊,第三句方并述‘寒’,‘去’二事了,这三句中全不曾说风雪,所以第四句中虽将园雪与人全写出,只是未能写出风,故趁便用一个‘圆’字写出来的。足迹本是长方的,却如何又成了圆的了呢,思想此事,可知风吹漫没了足迹之半,岂不成了圆的又如何?此乃文义双关之法,贤弟如何一时昏愦如此?”璞玉听了这话,真个字字说得有理,竟无言可对,只低了头,受他肆意数落。德清大笑道:“琴妹妹也不必只顾编了,雪也下大发了,天也快黑了,这会子我们吃了饭,赶早归上房去吧。”丁香、槟红等忙盛上饭来。
且说那腊八粥,原是调得好,又因煮得久了,其实香甜。璞玉因腹内无文,空空如也,不言不语,坐着吃饭,一连嚷了三碗,又叫盛饭来。原来取来的饭早已吃完,再去取的人还没回来,因此,槟红又忙遣人催去了。德清笑道:“好道这里没外人,若当着客人这么缺起来,这可成了甚么体统了,你们多取些来不好?”丁香哼了一声,笑道:“如今都是量着头做帽子的时候,断无多出些来的事。”德清道:“你们素日耗费的还不够使的。吃剩的饭食肉菜也总不爱惜,随意喂猫喂狗的糟蹋,厨房里的和管事的们见这般,如何不管束管束呢。”璞玉听了,放下箸,合掌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到外边见了那起穷苦人,一饮一食之艰难,回家来又见咱们家里糟蹋的,真个也够使的了。常言道:‘豪家一席宴,穷户半年粮。’慢说我们这一桌饭,就是下头人们吃的剩菜残饭,也可比庄户人家的新年宴席了。况且我们花园里的那么多果子菜蔬,除一年大家吃的送人的外,也不知奢霍了多少!我这会子出去查田,进个庄户人家看了,那家也算是个够吃够用的人家,宅旁也有个果树园子,我闲逛着问他家的孩子时,他们说:‘那园一年出的果菜,除自吃还能卖二、三十吊钱呢。’由此看来,不说我们园内果物,就是我们丫头们戴了扔的花儿,大家吃剩的竹笋,一年也值二百吊钱呢!我自那日方知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也都是值钱的。”琴默笑道:“这可真是膏粱纨绔之是,虽然原不知道这些事,你也是个读过书识过字的人呢,别的书也罢了,竟没看过朱子的《勿自弃》文?”璞玉笑道:“虽也看过,也不过勉人向善的虚喻浮言罢了,那知他自行如此呢?如何能信他说的都是真的!”琴默道:“难道朱子也是虚喻浮言的人吗?他的话句句都是实事。看你刚到外边应了几天差事,只见了一见世面便把朱夫子也都看虚浮了,倘或见了外边那些大事业,越发将孔夫子也都看虚浮了呢。”璞玉笑道:“你这等一个达人,原来竞没看过姬子的书。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外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琴默道:“底下怎么说的?”德请笑道:“他念的是断章取义,若念出底下一句来,便骂了自己了。”璞玉大笑不止。琴默道:“天下无不可用之物,既可用之,便能值钱,难为你这般个聪明人,竟不知如此明事,也真奇了。”又说笑了一会子,当时饭已吃毕,遂各自披了斗篷,走出凭花阁来看时,因是浓云天,日虽不落,早已黄昏。媳妇们都捋裙扫雪清道。四人遂齐往介寿堂请安来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转眼间又已冬尽春来。且不说璞玉在内院随心适意安闲享乐,枉自蹉跎岁月。
且说,贲侯画客司丹青者,名春,号田人,乃是青州府义兴县人氏,生性孤傲,为人恬淡,自幼精工笔墨。虽生长衣冠门弟,礼乐丛中,倒有个山林逍遥之风。少年时节,也曾磨穿铁砚,坐破寒床攻读过的。然纵有凌云之志,争奈时运不通,几番应试,功名无缘。故他常对人言:“二十年试场,只可入五次,若及出仕之年,不得为官,只宜弃儒冠自寻事业。搴须入试之事,余绝不为也。”不想年过三旬,须发已白了好几根了,那年赴京应试,依然无分。因此,无颜返归故里,羞见父老,竟烧了诗文经注,但袖了写字画画的笔砚,仿列国诸侯食客,周游去了。
也因田人的缘分好,有人举荐与贲侯,一见如故,情投意合,遂待以贵宾之礼。那田人不独有挥笔成画的一手绝技,尤可敬者,素日与朋友交往,无一字之欺妄,殊喜据实论理。盖因贲侯自幼所逢之人,不是冷暖迎送之辈,便是躬背阿谀之徒,所以一见田人,为人朴诚,举止端方,心中大悦。这田人也见贲侯屈尊礼贤,虚怀养士,凡有碍于名分,牵嫌负疑之事,别人不能直言,独田人能正颜提醒。至于摇扇谈文,剪烛论古,更是他熟惯的学问,所以贲侯待他与别人不同,爱如骨肉,敬若师保。相与日久,越发处得情投意合,虽一茶一饭,也不能相离了。
且说忠信府左近,富贵之家,贤达之士,也不止他们两家,素常往来于贲府之豪门贵族,凡知田人的,无不与之相善,因此,不是来探望他的,便是来邀请他的,终日不绝。田人一身迎送,那里应酬得过来。更兼笔欠纸债繁如毛发,不是这一个求画这个,便是那一个请写那个,索画请书者相继而来。倘或疏忽了一件,便生出许多责怪来。说甚么,我们一般相交的,如何分金砖玉瓦,厚此薄彼,云云。
田人弃了秀才不欲进取,原是为“清闲”二字,如今不但不得清闲,反招了许多繁忙。自以为老大屈辱,一日忽然大怒,泼了颜料,砸了器具,焚了笔,碎了砚。他契交问:“这本与应考全不相干的,你既弃了进士前程,正该以书画等事解闷,如何又这般毁了呢?”田人说道:“重书画原是世俗沽名之计。权贵之书画,纵使平平,能为世人视重罢了,若似我等山野之人,虽身为墨客,纵使十分好了,也只被看作一分,不惟不能赖为生计,便是枉费了笔墨送给人,反成为世人讥讽之笑柄。所以不如一发不做此事为上。”
不料招请田人的那些人家,原怕他多心为书画劳动了他,所以请一次不去也就罢了。如今听说他竟已止了书画,倒全没了碍难,或亲身来央求,被逼不过只得去的,或自己不来,差人回过贲侯,戏耍一般的捉去的,直急得田人无计可施,忽然想出个避秦之计来了。也是因他素性但悦山谷林泉,不喜都市繁华,常怀耕云钓月之心,所以暗地里寻了凌河南岸距贲府四五十里远近的一个去处,筑起几间茅舍,买了几亩山田,以为终身之计。
初时不令一人得知,临行方回明了贲侯。贲侯乍闻,心中甚是不乐,后来知其不可挽留,无计奈何,只得择了吉日,邀会亲友,设宴饯进田人。又商议,大家凑份,资助田人。当下,田人举杯相嘱,慢慢向众人道:“在下此番迁徙,不可以寻常移居相比,盖此一去,终此一生,闲游田野,不复返此尘世矣。在喧闹去处,若有遇我司春者,当可啐我面也。”众人听了此话,都不悦起来,说道:“司公此一举,实是无趣了。古语云‘小乱避自乡,大乱避自城’,纵然驱兵马动干戈之秋,村庄百姓尚避聚大去处呢,如今圣人在位,百姓安堵,无烽火之惊,无夜吠之犬,却如何忽然兴此村野之雅爱,又言语决绝如此?”
田人笑道:“正是趁此太平无事之秋,方欲迁居村野。设或犬吠月影,烽烟报警之时,欲为绿野田翁,岂可得乎?古人有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我不争名,又不争利,志在一身之温饱而已。甘美无如躬耕之粟,温暖无如自绩之布。况且,我索性不喜喧闹,但愿高卧安居,倘我仍居此地,虽可杜门辞客,仰卧安椅,然喧笑之声,搅我深梦,高卧不可得矣。往来函仪,蔽我清兴,安居不可得矣。希夷老祖之睡隐,谷子先生之坐眠,皆由其不居喧闹之地使然也。倘居闹市,必有人来搅扰,虽坐亦不过几时,虽眠亦不过兼刻,岂得携仙遨游于枕上,信步壁间之画中哉?”众人听了又道:“你果真不愿住在城内,如何不寻个离此不远半野半城的僻静去处呢?如此你既好避喧闹,我们也好寻你去。若搬到那远处,我们这几人,因有家务之累,何得时闻尊教呢?”田人道:“入山惟恐不深,我既欲遁离尘寰,岂有居人耳目之地之理?半野半城之繁务,反比城里为多,这事断断使不得。”众人无奈,也无扳辕卧辙之理,只得相揖告别。
次日,田人便携了妻儿,辞出贲府,入山去了。从此正合了田人闲云野鹤之心,自由安闲度日,胜似得道仙人了。朝缚数木而筑一楼,夕设一石而架小桥,相地栽花,因时种树,过了数十日。一日清晨起来,点视了自家院落毕,饭后登山,席地而坐,因述诸事之便易,吟成二首,回来写了出来:
耕种之便
篱门外有十亩田,栅栏下逝一水湾,
归就午餐鸡鸣时,不劳妇女肩荷担。
观耕之便
窗通院外四下观,垂杨绿草在眼前,
掀幕视彼农夫励,教读儿女亦不耽。
田人作罢诗,又自低吟,诵了几遍,只觉得心旷神怡。才放下笔时,忽听外边敲得柴门响,只见一人,手持书信,走了进来。田人见是贲府中人,遂相让坐下。拆缄看时,原来贲侯自他入山以来,思念不已,所以邀会众故友,写了一纸竭诚的书信,请他依然归来。田人方才入山,已得山水之乐的人,这岂能合他的心,遂提起方才现成的笔,在书尾批了几个绝然不去的字,交给来人去了。
原来那些大人先生们,自田人去后,都扫了兴,别人犹可,不过口头说说罢了。惟贲侯,非但示于声色,亦且现于形容,非但现于形容,更见诸梦寐之中了。思想田人临去之前,索居一间斗室,留了多少如药似玉的良言,一字一句无不有其教益。想到其问,心心念念,一刻也不能忘怀,又命璞玉写了一面“奈何斋”三字匾,悬在那门上。又过了些日子,越发思念,因此与众人商议,命李宪章写了书信,差人前往相请的。
智缚日中金乌去,计捉月心玉兔来。
再说,内院深闺,欢度了正月,天已渐长,时亦渐暖,姑娘丫头们都做起各自的针线活儿来,璞玉依旧上学读书。
一日,金夫人、吴姨娘带着德清姊妹们,在老太太跟前闲话,只见垂花门的舒二娘走进来回道:“南边祁府的太太,昨日到此。今日往会宁寺上香,明儿要来我们府里看老太太呢,先差两个媳妇送礼请安来了,如今在外边等候。”说毕,献上礼物。金夫人看是上用内造国缎二匹,上用宁绸二匹,白玉如意一个,荷包一匣,遂命妙鸾收了。
原来这祁府与贲府世代相交,况且这祁夫人是这里老太太姐姐的女儿,因此如今趁着在庙里上香,探望老太太来了。当时老太太闻信大悦,忙命唤进差米的两个媳妇。舒二娘忙出去将那两个媳妇引进来了。看他们身上穿戴的也都象夫人小姐似的,二人都是过了四十岁的光景。一一见礼请安毕,老太太命他们坐,二人等吴姨娘坐后,方在下首坐了。老太太问道:“你们甚么时候到的?”二人忙起身回道:“昨日方到,今日我们夫人往庙里上香,先差我们来请老太太、太太安,看姑娘们的。”老太太笑道:“多年不见你们了,今日忽然来了,真个没想到。”两个媳妇也笑道:“多年不曾来,所以我们夫人想念老太太,来看望来了。”老太太问道:“可带姑娘们来了不曾?”二人道:“没带别人来,只领我们公子来了。”老太太问道:“你们哥儿今年几岁了?可是常在你们夫人跟前呢,还是跟着他奶奶呢?”二人回道:“今年十四岁了,因我们老太太喜爱非常,终日淘气,不肯读书。”老太太笑道:“这又不是和我们那个一样了?你们哥儿叫甚么名字?”两个媳妇回道:“叫璞玉。”老太太向金夫人笑道:“他如何也叫璞玉?”德清在旁笑道:“自古至今同时隔代的同名的也尽多着呢。”两个媳妇也笑道:“自起了这个名儿,也曾听我们那边的几个老人说,好象在那里听过这名儿似的,只是这十几年没再听说。”老太太道:“叫这名字的就是我的孙子了。”遂唤媳妇们吩咐:“传外头的,叫我的儿子来。”众人齐应了个“是”,一时把璞玉自学里叫回来了。
老太太笑道:“你们二人看我这孩子,比你们的璞玉如何?”两个媳妇见了忙起身笑道:“可真是个奇事,我们若是在别的地方遇着,只怕当作我们的大爷了呢。”说着齐向前拉着璞玉的手问长问短,璞玉无奈,只得笑着问了好。老太太笑问道:“比你们的璞玉如何?”吴姨娘等忙道:“方才听他们二人说,可知模样儿也仿佛了。”
老太太笑道:“那里有这等奇事,大家儿的孩子,自幼娇养着,又生得柔嫩,看来多是齐整是有的,未必都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媳妇笑道:“据我们看,这哥儿的性情究竟比我们那个好多着呢。”老太太忙问道:“怎见得?”两个媳妇回道:“我拉着这哥儿的手问话时就知道了,若是我们那个慢说拉他的手,就是他的东西上,我们略沾沾手,就说弄腌臜了,便丢了不用。”话犹未了,吴姨娘、德清等都笑了起来道:“如果我们这里差了人去,见了你们的璞玉,且又拉着他的手说话,他也只得勉强忍耐了。”老太太也笑道:“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不管他怎么淘气,见了外人,也须大大方方的有礼数,他若不大方,不知礼数,素日也不能叫他尽着淘气了。大人所以喜爱他们,一则因他生得讨人欢喜,二则见了人札数上头竟比大人还强,能叫人喜欢,叫人爱惜,所以背地里纵着他们一些。他若不分内外,一味的淘气,不顾大人的脸面时,纵然生得如何好,令人喜爱,也该往死里打他。”两个媳妇听了齐笑道:“老太太说的极是,虽然如此,我们那个璞玉,有时见了宾客,礼数上头真个比大人还强呢,所以凡见的人都喜欢他,只说又何必严管他呢。岂知他背地里淘气的厉害,大人想不到的,他都能作得出来呢。”又说了些话,茶罢,才跟着金夫人往逸安堂来了。
这里老太太唤舒二娘来,吩咐赏了那两个媳妇的东西。又唤叶儿命同两个管家媳妇,到祁夫人下处回拜请他。分排已毕,心中惊喜,逢人便说:“他们也有个璞玉,说是性情儿也是一样的。”众人想来天下为官宦的大家里,同名的也极多,祖母溺爱孙子也是常事,所以也不以为奇。惟璞玉心中不悦,无情无绪的跟着德清等往凭花阁来。德清一见便说:“好了,这会子,你放心淘气去吧,先是‘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如今又出个对子来了。往后淘气,要挨打的时候,好往南跑寻那一个去。”璞玉道:“姐姐倒信了他们那谄言谎语了?那里还有个甚么璞玉了。”
德清道:“怎么没有,列国时有个蔺相如,汉朝的时候如何又有了个司马相如了?”璞玉哼了一声笑道:“这也罢了,模样儿偏又如何成了一样的了,这可真是没有的事。”德清道:“怎么,匡人见了孔子如何误认作是阳货了呢?”璞玉笑道:“孔子、阳货虽同貌却不同名,蔺相如、司马相如二人虽同名却不同貌,偏我与他两般都一样了不成?”德清道:“你只会拌嘴,我也不与你分证,慢说两般相同,也许是三般都相同了呢。有也罢,没也罢,与我甚么相干,明儿见了面,是真是假你自己知道就是了。”说毕,歪着身子睡了。正是:
移灯方知月色明,雀静始闻蟋蟀声。
诗曰:
芳艳群花各自谢,诸色丽雀四散飞,
东寺晨钟一声响,唤我醒转痴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