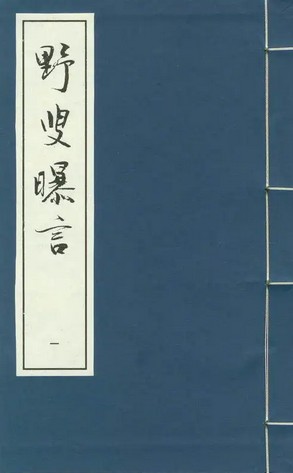大奶奶在凤姨房中,打发了管帐的出去,心里略安贴些。方去收拾凤姨的钥匙、锁把、衣裳、头面,见箱笼中间抖得雪乱,知是乘着闹弄了些去!叹口气道:“满船的芝麻翻掉了,何况这糖饼上屑儿?”正在自解自叹,忽听外边一片喊声,甚是惊疑。只见几个丫鬟飞跑进来报说:“许多人打进来,把厅上的交椅、台凳、羊角珠灯,都打得稀烂了!”大奶奶吃吓,摸不着路。又只见家人小厮赶进来说:“单老爷的舅子们,领了许多罡神泥鬼认做亲戚,在厅上百般打闹,口口声声要打死老爷,替二奶奶偿命哩!”大奶奶生气道:“啥仔二奶奶?献这景儿的勤!老爷在那里,快不要出去,吩咐管帐的去答话。”刚说未了,又只见玉梅乱滚进来道:“不好了!老爷死在床上了!”这一信把大奶奶的魂灵提出了顶门,直吹到三十三天之上,七跌八撞的赶扑进房。看见公子躺在床上,面如纸灰,手足僵直,竟如死人一般!便去一把抱住,放声大哭。跟进去姨娘、姐儿、丫鬟、仆妇,乱叫乱掐了一会,公子方才醒转,叹口气道:“前世的孽帐,总是逃不去的了!”大奶奶哭劝道:“你不要急坏了!只得再苦银子,料想没有做不来的事!”
正在急乱,小厮、丫鬟报说:“西街上大老爷、二老爷来了。”这两个是大奶奶的嫡哥子,俱做过京官,丁忧在家。一竟走进房来,埋冤道:“妹夫是个男子汉,没些见识!妹子,你是有胆量,会策画的,怎遇着这点子事体,就没分豁起来,躲在房里光哭?方才那些光棍,我已吩咐,不许罗唣了!依我们主意,该送他到县里去,每人打一顿板子。只是我们还摸不着头路,见你们管家许了他二十两银子,折做孝布,事体小,也就罢了。这二姨究竟是怎样死法的?”大奶奶道:“你妹子向来也不是这样的,如今把胆子吓破了!本等这事,连一连二的挤上来!前日春红的哥哥们是知道的了,又谢嫂嫂们叫丫头来送;忽然又碰出这样的事来!这里也没外人,哥哥们不要向着人说;玉梅,你站门口,看一看人。这死的弄出丑事来,你妹夫撞破了,也该就叫起人来,便不怕他天生就的破军星,独自一个打门进去,被奸夫一脚踢倒了!哥哥们不看他面上么?做妹子的半夜在更赶起来,看看一个是舌头也拖出来了,眼睛也宕了,吊死在床上;这一边他又血铺满面,晕死在地板上,你叫我的胆大到那里去?我这魂还有在身上么?到得救醒了转来,又怕坏脸面,死的身上又弄出伤痕来了,叫了他老子来,花了些银子,方才扭捏过了。又是雪片的打进来了,你妹夫又晕死在床上了,还没有一钟茶的时候,哥哥们跨进房,还没醒转来哩!我所靠何人,叫我不要哭着叫唤?你叫我做妹子的怎样分豁得来呢?真个好命苦也!”说毕,竟大哭起来。
两个哥子齐劝道:“我们不知道这些缘故,但见你们同在床上哭泣,错埋冤你了!如今第一将息自家身子,妹夫固是要紧;你也不是当耍的,你是这一家子擎天柱哩!房里的人,死掉几个,算得什么数儿?他既是这样死的,你们倒也没有苦处。这些衣衾棺木,一切发送的事,你两人俱不必管他,外面的事,交与管帐的,里面的事,交与大姨、三姨,就有不到之处,也就罢了;只保养自己身子要紧!我们去了,再来看你罢。你嫂子们不知道,都要来看你,出殡时还打帐来吊。如今是不必了!妹夫,你面上有伤,你身子不好,不要送了。”说罢,自去。公子要送,大奶奶推住道:“你倒不要罢,你看,一立起来,就是这般乱晃,当不的再弄出来了!恭敬不如从命,哥哥们也不怪你的!家去谢声嫂嫂,茶也没有拿。你看这玉梅,倒累我又想起春红来了!”
须臾,管帐的在门口回说:“又许了二十两银子,诸事停妥,棺木已到,现在一切入殡成服诸事,怎样备办?请老爷夫人吩咐出来,小人们好分头去干。”论起来,也没该替他戴孝,拖了出去就是;如今要遮世人眼目,除着我房里,其余的人都戴三日孝,送殡转来,脱掉罢了。发送的事你去酌量,总比春红的丧事要着实减省;一切银钱在外边帐上支用,过后销算便了。”管帐的答应出去。复叫玉梅取了两小封银子,提了一麻袋钱,交给大姨、三姨道:“我是只好照管老爷了。你两人替我去分豁罢,外面居邻,一概都回;墙门内住房邻舍,若必要进来,都给他一顿酒饭;那钱二嫂的要丰盛些,另外叫他在死的房里坐罢;镇宅的福物要加意些,吩咐多请几个道士,这不比春红,是个横死的,防他作怪哩!”大姨、三姨应诺而去。
公子放心不下,趁大奶奶下去解手,溜出房来,叫人去打听璇姑消息,回来说:“并没曾死,方才哭声,是晕了过去,一会子就救活了。”公子心上一块石头方得落下。走进房来,大奶奶再三埋冤,公子不敢做声,往床上去睡了。小厅上,匠人漆棺材,裁缝做孝衣;大厅上,摆开七八张桌子,大鱼大肉,给单老爷合一班凶神去吃嚼。凤姨房里丫鬟、仆妇,乱着探帐子,烧衣服,化纸钱,念经卷,替凤姨洗尸穿衣,插花戴朵。大奶奶自陪着公子,在房里将息。天色晚了,凤姨入木,单老进来哭了一场,单老的舅子也挤了几点眼泪,出去与众人照份,分了银子,欢欢喜喜的散了。大姨、三姨本等要哭一场,怕公子合大奶奶不快,哭了几声,就住了。丫鬟、仆妇,平日受凤姨些恩惠的流了几点泪儿,其余也就罢了。夜里没人肯进去伴材,大姨作主,叫了两个挑水的水夫,给他三百文钱,又打了三斤烧酒,吩咐他伴材,才妥贴了。
到了次日,单老叫人来说:“要替女儿传神。”公子不许,也只得罢了。外边邻舍要来祭奠,门上人回去了。墙门里住房的老婆进来拜了,叫两个姐儿还了拜,打发了酒饭;单把钱二嫂留在凤姨房中,酒菜更是丰盛,吃完时谢了又谢,各自散了。大姨、三姨回绝了本家,便没有人来了。单家亲族备了一桌羹饭,赶了一二十个男妇进来,在材前磕头化纸,管帐的留到外边,堆头满碗的鱼肉荤菜搬上去,吃得个个心满意足,发还了筵力,每人给了一疋白布,二百文钱,欢天喜地的去了。家里众人乱着拜完了,大奶奶自在房里。与公子商议道:“论起来,算是你的侧室;可要立个铭旌,叫玉梅抱着贵哥儿坐轿去送一送,遮遮众人的眼?”公子暴跳如雷的道:“你还没听见那淫妇的尸穴声浪气哩!他是我啥仔侧室!这样发送,我心里已是气得昏了!一发要立铭旌,叫贵哥送起那淫妇来了!”大奶奶听说,也就不言语了。
次日黎明,也有诸色人来伺候起身,大奶奶主张,叫大姨、三姨房里丫鬟,合灶下一个烧火老婆,凑了三乘轿子去送丧,一早乱烘烘的,发送去了。日中回来,各人除了孝衣,烧了孝髻,请了九众道士,全猪全羊,在大厅上做了半日半夜的法事。后半夜,法师戴了金冠,披了鹤氅,朝衣朱履,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攥了净瓶,踏罡步斗,焚符化纸,其余的道士都穿着法衣,拿着法器,叮叮当当的,敲得一片声响。家人小厮,都烧着醋炭,焚着甲马,放着爆竹,打着金锣,乒乒乓乓的,闹进凤姨房里。法师将法水乱喷,宝剑满房砍斫,众家人把凤姨那床拆将出来,架着木架,烧得一片通红,火光烛天。大奶奶在房里看见,忙教小怜去问:“那条鸾带可曾烧掉?”大姨、三姨慌忙寻着,丢在火里去了。法师出房,把剑在房门上左劈右划,口里喃喃的念着法语,吆喝了一声,把门闭好,贴上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的封皮。然后往各房并厅堂、廊巷、厨厕、井灶一切处所镇了一遍,谢了神将,收了科仪,散了福物,已是天明了。
公子与大奶奶将息了两三夜,神气略好。过两日上明之后,大姨、三姨合管帐家人都来缴帐,连解铺发票,共用去四百八十余两银子。公子道:“原来这淫妇的性命,也只值得四百多两银子!”大奶奶道:“你也不要只顾骂了,已死之人,提他怎的?当初没做出来,便风吹肉痛,不论长话短话,只沾着他些影儿,就与人变面变嘴的;如今眼见了,就淫妇长、淫妇短的骂个不耐烦!一个房里边人,市井见识,也比着大家闺女,读书知礼,晓得名节的么?当得你擎在手里,颠将起来,他还有甚顾忌?一来也是你的福分大,轻轻的便过去了;一来也是春红的报应!”公子慌道:“你也见春红来?”大奶奶道:“我见甚来!他日常与春红赤紧的做尽对头,前日春红死了,我便苦坏了,你也哭得发昏,一家子都可怜他,淌不了的眼泪!你看,他把两只眼睛耸上落下的,往死里挤,可挤得出一点子水气?落后怪我没总成他老子棺材,极得眼皮红红的,几乎要挂出泪来!你不是要留一个神子?这原也不该!他就不等我开口,极声的拦住了。大姨、三姨虽也说来,只有他那脸儿变得那样难看,颈皮上根根扛起红筋来!大姨、三姨帮着丫头们,替春红揩抹身上,穿衣着裤,探帐烧纸,那样忙乱,他十个指头,可曾轮动一节儿?一张嘴合不拢来,嗤嗤的只待要笑,见我看了他一眼,慌忙回过头去,只推着解手,跑到床背后去了。春红虽是个姐儿,他性子才是利害,他又刚死,魂还没出房哩;他见你这样狠心,怕不在暗里报你一箭儿?这是我猜着春红在那里报冤,谁见他来呢!你说我也见他,是你见过他的了;你可说给我听,是几时见过他来?”公子顿了一顿,说道:“我那日听有响动,起来查看,只见前面有个丫头行走,我便直跟到死的房门边,那丫头忽然就不见了,把我吓得要死,蹲在地下,才听见房里的事。后来细想,那丫头背后的身影,合走的那一步路,竟是与春红一样的;你说,不是他是谁呢?”大奶奶道:“这不消说了,我也便疑心是他。你说着丫头,又提起我一件事来了,大怜这奴才,逃走了去,几日心里昏腾腾的,没想起他,你也该报了官,捉回来处治处治,叫丫头、小厮们看个样子才好!”公子道:“我倒想着的,只怕到了官,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剥尽脸面,这臭水缸不如不去搅他了!”大奶奶便不做声。
公子说着臭水缸,痴心不死,又想起璇姑来,忖道:“休说他的美貌家中没人可比;只就那晚誓死不从这一种节操,那里去寻?我家里算是夫人正气,但看他交媾之时那一种意兴,也不是激烈的人;其余更不消说。我被那枉死鬼剥尽脸面,若得这样人在身边,岂不争气?但如今伤口不知会否平复?将来如何偎得转他的性来?死的死了,又没人替我策划,怎生区处?”想了一会,忽然记起道:“有了,有了!当初我与三姨未上手时,原是聂兄的妙计,何不与他商议?”因急急走到丹房里,先拜过了吕祖,后与聂静等相见,三个道士各唁凤姨之变。只见陶真进房辞行,说:“明日即往匡庐,特来作别。”公子心颇疑惑,却因他做人本分老实,也就不疑到凤姨身上,略留一留,便应允了。陶真辞了过去,公子便扯聂元到密室中,把璇姑之事述与他听,求他设计。聂元听见有此美人,浑身骚痒;却因前日与凤姨行奸,正在兴浓,忽被公子打门直入,猛力一提,闭住精管,后来赤身上房,跳墙回去,又着了些风寒劳碌,竟成了白浊之症,一时医治不好;又且听着璇姑光景,是难于入手,一边便安心替公子打算道:“少年女子,那个不爱风流?况遇公子这等才貌,这般富贵,岂有不动心之理?据贫道看来,其中大约有两个缘故:其一,他自有心上之人,富贵才貌,也与公子相仿,与彼先有成言,不肯负约;其一,尚系深闺淑女,情窦未开,不知此事之好。今须兼而行之,一面叫人去做说客,于女眷中择一能言舌辩者,朝夕把风月之事诱动其心;一面考访他所思何人,所约何言。或假传死信,以绝其念;或伪托其言,以移其志。然后公子之才学相貌,富贵奢华足以满足其愿,飘荡其情;虽月里嫦娥,亦将飞下蟾宫,况区区人间丽质乎?”
公子把聂元之言与璇姑情景细细的揣摩印证一番,不觉死灰复燃,喜动颜色,说道:“道兄所料,一毫不错;那女子实是情窦未开,已许了富贵风流之子,故把我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到得事急,便不顾性命了!”因谢了聂元去后,把李四嫂叫来,先问璇姑的病势。四嫂道:“命是可以不伤的了;只吃亏他不肯给医生看,所以不得收口。”公子道:“他可在那里咒骂我呢?”四嫂道:“小媳妇也打帐他,说及老爷,便把话打入去劝解,岂知他一字不提,故此也没敢说起。只帮着张老实夫妻烧茶煮粥,赎药买炭,熬桂圆莲心汤,伏伺着他。”公子道:“我如今要托你一件事!”因将身边带的十两一封银子安放桌上,说:“拿去买果儿吃,事成之后,再谢一个元宝。我想这璇姑定有个心上人儿,又恐他年幼不谙风情,故无心向我。如今要你去打探,他所思何人、是何名姓、何等人物、如何定约、先来回我。朝夕再说些风月,引动他的春心,然后把我的富贵风流,去打动他。他既一言不发,便有个挽回;你又知机识窍,见景生情,这事大有可成。只要你用心去做就是了。”
李四嫂见了银子,听了话头,因说道:“此事在别的女人,就如井中汲水,伸手便来;在这个女子,却如天上捞云,脚踏不到!不是小媳妇夸口,凭着这个舌头,两爿牙齿,抓星酌斗,拨雨撩云,能使南海观音偷嫁西池王母,银河织女私奔月窟嫦娥!”公子笑道:“这你说错了,四个都是女人哩。”四嫂道:“老爷有所不知,媳妇岂肯说错?要想那没鸡巴的还去跟他,若有了鸡巴岂不踢做一堆,化作一块呢。”公子大笑道:“这是极好的了,怎还拿不定这璇姑呢?”四嫂道:“这璇姑大约不出老爷所料,年还幼小,未谙风情;或是已有豪家,业经许定;小媳妇去探明回报。兼以伏侍为名,妆痴作傻,极言夫妻交合,俪若登由;孤枕单衾,凉冻难忍。只要他一点凡心微微而动,便把我千般引诱,娓娓而谈,弄得他欲火攻心,桃花上脸,两只金莲怕不一步步踏上小媳妇船头,浑身羊肉,自然一块块咽入老爷肚里。到那其间,一双两好,难拆难分,却休要忘记我这凌烟阁上第一个功臣也!”公子听了四嫂的话头,如天花乱坠,喜得心窝奇痒,连连称赞,嘱咐:“用心去干,停会还叫人去送五斗新舂米给你煮粥吃哩。”四嫂假作推辞,谢而又谢,袖了银子去了。公子进来,把陶道辞别之事说知,备了一席饯行,又封了十二两折程,打发过去。
到了次日,正是中秋佳节,公子想着璇姑,如木头一般呆呆坐着。大奶奶见公子不快,也是没情没绪的。大姨、三姨也就没有高兴。在大月亮里吃了几杯闷酒,就各自散了。这边李四嫂得了公子大主银子,自己破悭,买了几味可口嗄饭,几色新鲜果儿,装了一大盘洋糖月饼,打着三斤陈酒,与张妈说明公子之意,搬到璇姑房里同赏中秋。四嫂一屁股就坐在璇姑床沿,劝着璇姑吃酒,风风势势的说了几个半村不俏的笑话,和哄着吃了几杯酒儿,便装着酒醉哈哈的笑将起来道:“刘大娘,你我都是女人,大姑娘又是身上不好,闷的慌,我们说个风话儿耍子,也替大姑娘散散心。你家刘大爷出去了这许多时,你可也想他么?”石氏道:“丈夫出外没信,做妻子有个不想念的,也还是人么?”四嫂道:“原说是该想的,只是想他不到,这心里难过。记得那一年,我家男人出了门,夜里做梦,与他同睡,正在好处,惊醒转来。这一夜工夫,实是难熬,不知这身子是死是活!”石氏怫然道:“四嫂怎说出这等话来?”四嫂笑道:“我是心直口快的人,有一句,说一句。大姑娘是个含花闺女,他不知道趣味,这还罢了。大娘你是过来人,怎也假撇清,说这道学话儿?这夫妻的事体,是天生就的。你看那苍蝇儿这点东西,兀自爬在背上,死也不肯下来,那底下的更是扑着翅儿,说不出的那种快活。何况你我俱是有情之人?莫说交欢的时候,你贪我爱,恨不得把身子化作一堆,就是大家压着腿、搂着腰,睡这一觉,也是浑身松爽的。今日遇着这样佳节,夫妻们搂抱着,一递一杯,吃着酒,看着那月亮儿,到了床上,颠鸾倒凤,那一种欢误,谁肯要去做那仙人哩?偏生我男人要赚钱,走啥仔水,丢我在家受尽凄凉。正不知这一夜怎样捱法,才捱得过去?”
石氏变了脸道:“四嫂,不是我吃了你的酒,还说你不是;但不该说这些混话,实在难听!”四嫂格格的笑道:“好道学先生,恼起来了,你越恼,我越要说,要引动你的凡心哩!”璇姑微笑道:“嫂嫂,你凭着四嫂说罢,何必认真?”四嫂眉花眼笑的说道:“大姑娘,是你说的话,便叫我喜欢。天下的事,那一件认得真的?我今年三十多岁了,就是成日成夜干那快活的事,也不及十年光景,一到四十外边,就没啥仔趣哩!你会快活,也是这一世,不会快活,也是这一世,转转眼,大家都入了土了!夫妻交合,是周公制下的。由得我肉骨肉髓的快活!人也不好笑我,笑我的就是痴子,白白的苦了一世。我娘家有个邻舍,生着姊妹两个,也住着一位少年公子房屋。公子要与他姊妹相与,那姐姐是个傻子,不知道风流的趣味,生生推脱了;那妹子生定是有福之人,就与那公子相好了。两个年纪相当,才貌厮称,你贪我爱,夜去明来,无比恩情,非常快乐;那公子娶了回去,穿的是绫罗锦绣,吃的是鹅鸭猪羊,住的是高堂大厦,睡的是翠被牙床,冬天来围炉饮酒,夏天来水阁乘凉;正经的娘子都打靠背后,独与他像漆投胶水,蜜拌糖霜;那一种的风流富贵,不同着受用?那一节的良辰美景,不同着庆赏?真个是夜夜元宵,朝朝寒食!独苦那呆打孩的姐姐,嫁子卖柴蠢汉,守着一根扁担,受尽了万种凄凉!这妹子果然欢娱嫌夜短,那姐姐真个寂寞恨更长!后来公子的正室死了,把妹子册立起来,就做了一品堂堂;那公子直升到尚书阁老,这妹子便受了凤诰鸾章,戴起那珠冠宝髻,与公子到老成双;生下来儿孙满膝,说不尽种种风光;被文人编成歌句,到如今万口称扬。”
璇姑笑道:“四嫂出口成章,原来是个女才子哩!”四嫂道:“这是我们街坊上一段风流佳话,那家子不买本来念念,我自小就读得烂熟的。啥仔柴积米积,后来那姐姐想起当初自己守了那卖柴的穷汉,每日两餐稀粥,夏天没帐子,冬天没被头,终日怨恨,终年冻饿,生生的把一个美貌佳人,弄成了一根枯杆儿,苦了几年,就苦死了!方才大姑娘说的好,认不得真,那姐忒认真,以致苦死,这妹子不认真,才享受那无穷快乐!所以说,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不及早寻些风流事体干干,一旦大限来时,懊悔嫌迟了!”张妈道:“你既明白这样大道理,当初看中意一个富贵公子去嫁他,怎肯配着李四叔,与我们一般受苦呢?”四嫂叹口气道:“我们是前世不修,没有带得那种福气!那富贵公子爱的是聪明女子,美貌娇娃,便把他如珍似宝,百般怜惜;他见了我这麻脸婆子,你中意他,他肯中意你么?我若有大姑娘这般才貌,怕没有王孙公子来求到我?我就倾心与他相好,做一对恩爱夫妻,夜夜在销金帐里,去享人间极乐,肯嫁你李叔叔这样蠢人,受这凄凉罪吗?我也今日醉了,率性和你们说罢:做男人的,便有三妻四妾,摸丫头,偷婆娘,嫖婊子,骗小官这许多快活事做;做女人的,就该守着一个丈夫的吗?看得破,不认真,就是花间月下,结识一两个情人,也不算甚罪过!如今大官府家夫人小姐,那一个不开个便门,相与几个人儿?只苦着我们这样人家,房屋浅窄,做不得事罢了!是痴子傻子,才讲贞节;那贞节,可是吃得穿得快活的东西?白白的愁得面黄肌瘦,谁来替你表扬?便有人来表扬,已是变了泥土,痛痒不知的了!”那武则天娘娘偷的汉子还有数儿的吗?她也活到七八十岁,风流快乐了一世,没见天雷来打死了他。死去的时节,十殿阎王领着判官、小鬼,直到十里长亭来迎接他,还俯伏在地下,满口称着万岁哩!
四嫂这一席话,说得张妈如顽石点头,石氏如金刚怒目;再看那璇姑,如庄周化蝶,酣然入梦去了。不觉意兴索然,只得立起身来,说道:“今日吃了几杯急酒,嚼了一会臭蛆,倒耽搁了你们。大姑娘已经睡熟,不去惊动他,明日再来看他罢。”张妈送了四嫂出去,进来收拾过家伙。石氏关好房门,呼唤璇姑不应,伸手去替他把被头盖好,脱了鞋袜,要上床去,忽转过念头,想起一桩事来。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