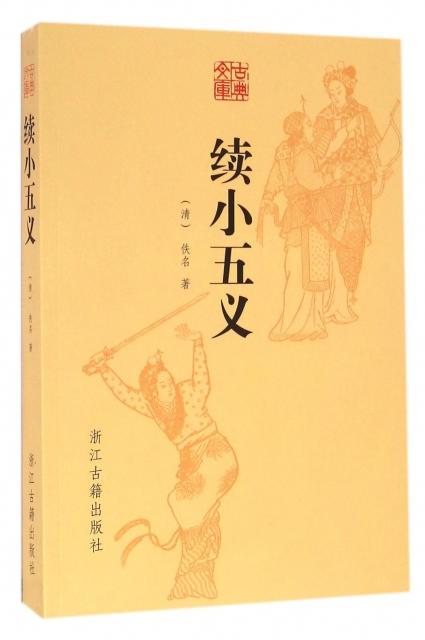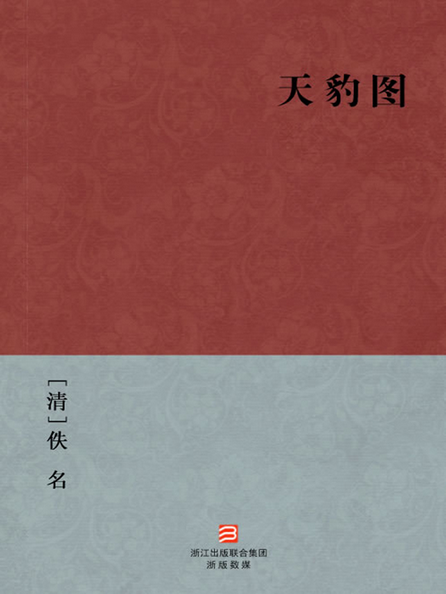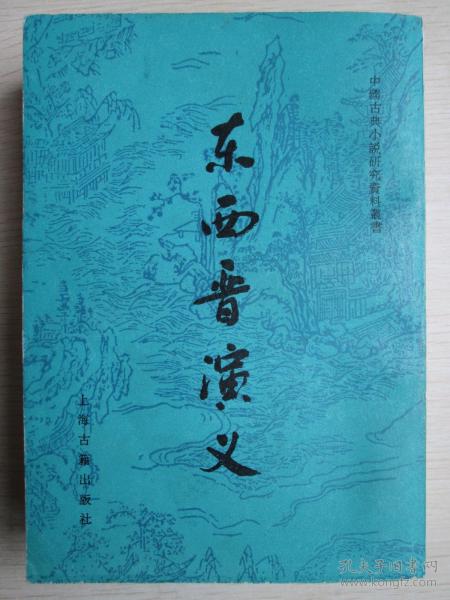建威长叹一声道:「怀祖,拒约两个字,本為全体公益,不為一人私计,然在他人不过牲些钱财,方事之始,冯君乃并性命牺牲之,难道不自知其愚,不自知其无名麼?正恐长夜漫漫,前路茫茫,拼以一身,鼓我全国的锐气,激我全国的决心,想其定志决策时,不知流了若干血泪,绞了若干脑髓,然后毅然引药,长往不返。但生之前既有无限的踌躇,死之后自有无限的希望,轻轻地把『徒死』两个字一笔抹煞,中国的舆论可想而知了,中国的人心也可想而知了。」
怀祖嘿然不答。建威沉吟一回道:「怀祖,我想明后日,倘有上海邮船,便要动身了。」图南道:「内子近来饮食日强;精神日復,留小儿在家侍奉,我与诸君同行,既可开拓胸襟,展舒怀抱,或者有什麼事,也好為诸君分劳。」建威道:「以地望论,上海自是中心,以感情论,旅外工人,粤人独居多数,桑梓之情,竔榆之谊,容易动人,就容易成事,我们还是分途各任的好。请兄留粤,我与怀祖两人同舟共济,也不為孤了。」
陈氏道:「我在此无所事事,愿到上海走〔一〕遭。」怀祖道:「此行迟速未能预期,本岛的消息,海船的贩运,要仗大嫂代谋,请与大哥同到香港,俟我南归。大嫂如欲北游,那时再去,尚不為迟。」陈氏方始无言。
后日是六月十八日,恰好招商班期,建威同怀祖夫妇,午后僱夫搬运行李,上得飞鲸船来。陈氏已同其夫先在船中,图南父子直至解缆开船,作辞上岸。船到香港,陈氏同着阿金也就分手自行。一路经过福建洋面、浙江洋面,四週山峰,时隐时见,灵奇雄厚,各有各的胜境。怀祖经一处徘徊一处,见一处感伤一处。张氏素来达观,到此亦鬱伊万状。亏得建威极力开解,才略略定了痛肠,止了痛泪。
不知不觉,已近崇明洋了。怀祖凴栏四望,战舰、巡洋舰、炮舰、鱼雷舰,衔尾分列,从叁夹水直进黄浦江,两面树林似的高桅,桅顶掛满了各色旗帜,临风招豋,映日飞扬。细数龙旗,只得四竿,还是二叁等巡船,有两条只堪迎送。怀祖愕然,顾谓建威道:「地球上日所出入,有了白种的足跡,便是白种的世界。以今所睹,证昔所闻,能不令人惊心动魄麼?」建威道:「古今往来,新陈代谢,尽我力量,做一步算一步,计什麼利害,问什麼强弱?」怀祖摇头道:「理虽不差,势不相敌。兄所说的,究竟只指未来,不指现在。」正要辩论,离岸不远,便各回房收拾。
待傍码头,挑夫、车夫、栈房的接客,纷纷上船。建威等叁人,却由长发栈随船伙计预先邀定,便代僱两乘马车,到栈中看定房间,略略歇息。建威出门自去,调查近事,怀祖与其妻本為游歷而来,并也举目无亲,便先高驾双轮,遨游四达,遇便也暗暗物色。
倏忽数日,十里洋场,奇奇怪怪,琐琐屑屑的情形,大略已在胸中。这晚回栈,建威恰已先归,正叫了两样菜,引杯痛饮。怀祖取只杯子,倒了一杯酒,随饮随谈道:「建威兄!吾今而知『开放主义』四个字,主之於主,又有实力以為之护,是為通商互市之通例,无所忌惮,亦无所用其议论;主之於客,又有强权以為之继,便是侵疆掠地的代名词,言虽动听,实则尽丧,正难為主人呢。」建威道:「兄何自而知之?」
怀祖道:「吾与兄现所居处,不是租界儿?既名租界,地主之為何人,不言而喻。然虚名在我,实权在人,试就表面侦察,就内容研究,反客為主,早成為他人殖民之地。即一隅,推全局,大概可知。可再轻信甘言,自忘实祸麼?」建威道:「是由他人之国家,有治外法权,其领事即因而有裁判权,以至於是。然我名义既尚保全,只望法律上有日回復,种种障碍,都可消灭,似毋庸长虑却顾的。」
怀祖道:「谈何容易?吾闻日本之争,法律尚在维新之初年,而至辽东战胜,契约始定,苟无实力,无强权,至今不过付诸梦想。即人观我,则我仅仅以修改刑律,骤望与列强改订同等之约,能乎不能?既自知其不能,则无论為佔领,无论為开放,其必至為我害者。只争隐显,不争轻重,名义是假,法律才是真呢。」建威道:「事在人為,日本当年与我正復同病,今乃巍然居於头等强国之列,我中国人种不定弱於日本。」怀祖急道:「日本以武士道為第一之大和魂,中国之国魂何在?」
建威道:「国魂麼?咳!殆已死矣!我今日正一肚皮不合时宜,聊借浊醪,自浇块垒,见兄来,正思尽情吐露,倒為开放问题争执了半天。其实就事实上讲起来,兄所云云,真是窥脏见结之谈,我心不死,遂於无可希冀中强生希冀。然而魂之不存,身将焉用?东国鲁连,恐转瞬即将蹈海哩。」怀祖诧异道:「兄台何為鬱鬱若此?」建威道:「兄幸未见其人,未与之谈,不然,此时也必不欢。」怀祖道:「小弟连日出游,正未知兄所调查者如何?今日所见,又是何人?」
建威举瓶斟酒,连引叁巨觥,復杯在案,先吁了两口气,才道:「调查之事,迟再相告,先告兄今日所之人,与所谈之言。其人為谁?则海上巨商孙问锄是也。孙君与外人交易极广,势力极雄,拒约议起,亦復身与其列,一时视线交集於其身,以卜斯事之胜负。不定美货之决议,未尝有人强迫,毅然签允,眾遂坦然以為无恐。弟初意,我国商人乃肯牺牲个人莫大之利源,以谋全群之益,甚心仪其為人。
「昨日造门请謁,握手深谈,意识之坚定,言词之慷慨,益令弟五体投地,顾影自惭。故今日不辞烦数,重往把晤,以自开农牧,自兴製造,自辟路矿之叁说,反覆陈说,请与合谋。大约我辈半年来熟思深虑者,虽未一一吐露大端,总纲业已不遗一字。乃孙君唯唯诺诺,无可无否,弟於是心為以疑。徐视其面,若重有不豫者然,又若有所深思者然。弟问其故,初犹隐而不言,久而久之,弟怒谓之曰:僕亦商人,凡商人之甘苦,久已亲尝身受。此次破產东归,虽欲谋海外侨氓之便利,亦决不致有害君等。如君有疑於我,或以我為不足言,则我请从此辞。
「孙君沉吟良久,入内取两纸示弟,乃他处学堂中所发不用美货之传单。弟阅毕,问孙君以此示弟之意。孙君谓弟,君不尝言凡商人之甘苦已亲尝身受麼?我辈商人一时之嬴亏犹在其次,最怕是销路滞钝,成本停搁,万一运掉不灵,虽有巨资,每為一二小故,牵连倒闭,不要说是全数不销,还经得起麼?偏我行中底货尚多,外洋定而未到者,计算货价,又在五百万两上下,一经他们提倡,人人抱定不用的宗旨,货无去路,本无归期,外人没要紧,我第一个先不免倾家破產。在他们只想害外人,那知倒害的自己人,并且又先害的我。君自外来,彼此又都是商人,目前我之奇厄,君有良策為我助否?
「弟沉思至再,始答道:如以私言,则僕谨谢不敏,如以公言,或实迫於势所无可如何者。僕苟能為,必為君尽力。但以僕所闻,有人建议,凡原存底货,送交商会,黏贴印花,仍准行销,则君所虑底货之一层,当已无碍。孙君忽然失笑道:我辈经商,凡事向贵自由,如今无缘无故,强受他人之干涉,请问夏君,易地以处,甘乎不甘?弟又晓之道:是将以释用户之疑,示非拒约后续定之货,正為君等求疏通,不得谓之干涉,君何為而不甘心?孙君又笑道:万一他人横挟私见,强指某货為应销,某货為不应销,不免终受其害,至受害而后悔,已嫌其迟,何如此时不从其言之為愈呢?
「弟彼时细味其言,觉得必有不可告之隐情,多言亦属无益。因问定货之价值至五百万两上下,自非一时所定,能将日期告我否?孙君於时面色骤变道:是非君所宜问。忽然转為沉静,又道:日期过多,仓卒不能记忆。弟因是益知其必有私,笑谓孙君道:货价之鉅如是,安有不记日期之理?即使偶有遗忘,至近之数期必能记忆。度君於僕,终始不免怀疑,故不愿以实告。但君语僕,僕或者能為君助,若不语僕,亦不便相强。惟君牌号,僕已剌知,尽可传电出洋,详细查探,彼时必发君復於同胞之前,幸君毋怪。
「孙君於时色乍红而旋青,顏将舒而復惨,囁嚅答道:「前者犹可,临期所定為最多,以是有忧,幸君勿宣。弟不禁失声叹道:自作之孽,夫復何尤?但僕所忧,有大於君者,连类而及,又不得不為君忧。愿君尽出定单,告罪於我同胞之前,请其仍照印花办法,一体销售。惟君当宣誓,现单而外,不再续定。
「乃弟之言未终,突有一人疾趋而入,谓此事我辈别有办法。夏君请毋多言。弟於时平心静气,以谓其人道:孙君定货,价值如许,一通一滞,於市面大有影响。為商言商,安能不為代忧?既為代忧,又安能无言?君既以僕為多言,又谓别有办法,谅君自有良法,僕益愿得与闻。其人瞪斜视道:宗旨不同,我不乐為君言。
「弟见其人奇横至妄,鬱火上衝,几不可遏。一转念,忍而又忍,转谓孙君道:此事当争是非,不当争意气。君之目前,不过於我同胞之前一下气耳。然此小损於君,亦有大利於君,君如从我所言,而又惧我同胞或不谅於君,不敢呈身自请,僕愿以君万无可奈之苦衷,代告我同胞,请為君谅。孙君!孙君!全体之害,固可成於个人,个人之利,却必资於全体。未有皆在荆棘中,个人独能迴旋自适者,幸毋执迷,重自取忧。
「后来之人,忽又接口道:夏君!夏君!我不尝言我辈别有力法麼?君犹执呈单请罪之说以强孙君,无乃多事?弟问孙君:其人為君何人?孙君道:同行之来议事者。弟本不乐与其人言,继念其人所谓别有办法,或出於破坏之一途,不可不预防其渐,又復忍之又忍,平心静气,冀以婉言回其人之听。乃弟唇舌俱敝,其人除别有办法,君无多言八字之外,竟无一语。弟乃拂衣而出,至今思之,犹有餘恨。」
怀祖屏气侧耳,直待建威讲完,才道:「其人之奇横至妄,自由成竹已定,适与兄所见者相反,觉其逆耳,故不乐闻。但孙君临期放手定货,自丧之利犹小,败群之罪实大,应使薄受惩创,為类似者之警。如兄所言,呈单请罪,盖印并销,是转為其疏通,又示人以拒约之无实际也,是万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