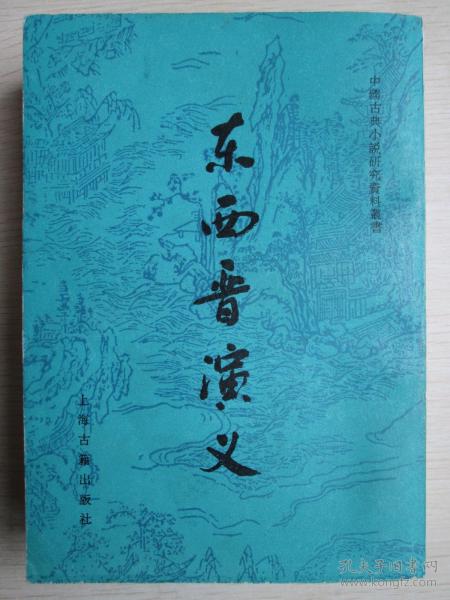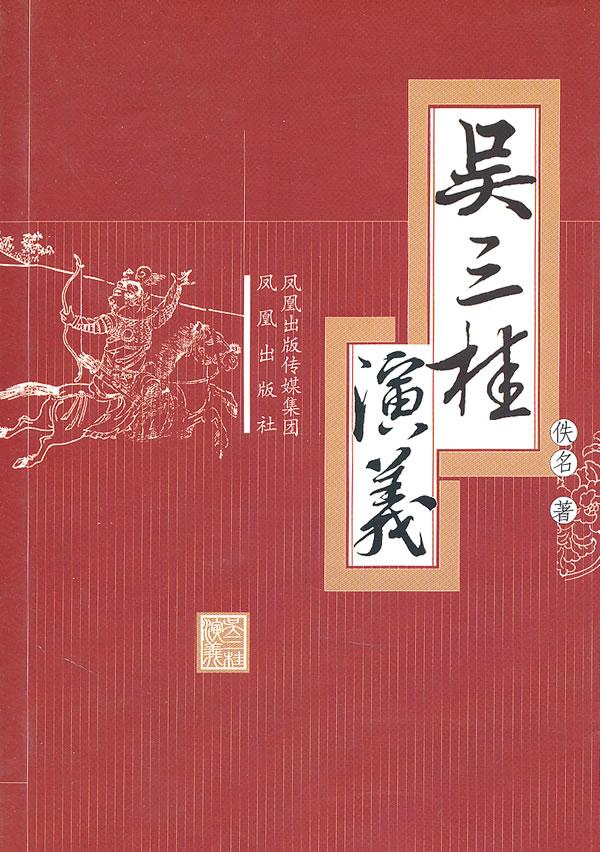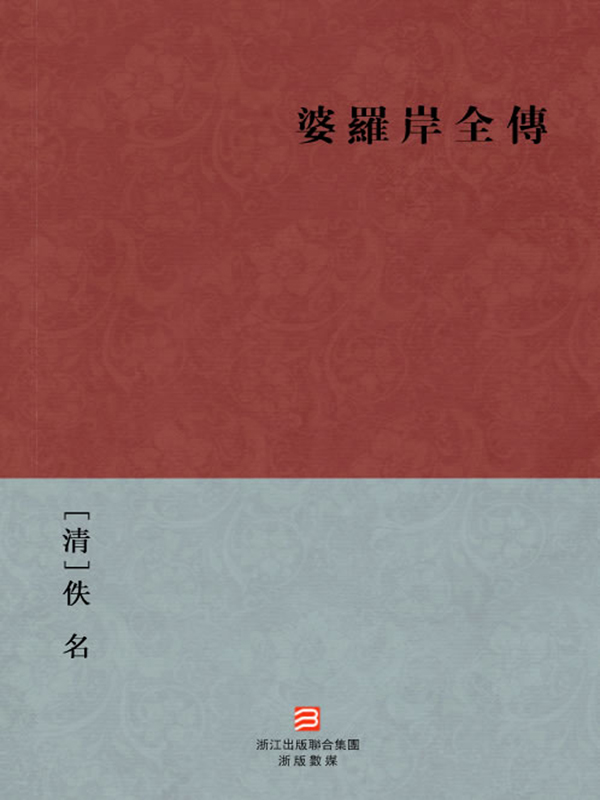风声一过,电光叁闪,平地起个霹靂,屋簷四角,顿时无数的瀑布,悬空下泻,地沟中宣泄不及,一霎时盘满庭心,渐渐衝进房门。楼下寓客的牀榻,在水中央,都不能安眠稳卧,这还是件小事。听风声越吹越紧,雨声越下越大,水势便不知何时始退。又有人记起今日正是大潮的汐期,趁着风威雨势,外江内沟,自然同时暴涨。万一继长增高,满房的箱笼杂物,不免都要打潮。
只听一片声嚷着茶房,乱哄哄都望楼上搬来。怀祖夫妇本未就寝,揭帘出房,看建威负手立在栏杆边,挨上问道:「兄也没睡麼?」建威縐眉道:「今夜风狂雨骤,江中海中,不知要坏几许船隻,要伤几许生命,思之心悸,如何睡呢?」张氏指道:「那边堆满了物件,那边站满了男男女女,只这栈房,一夜中挨挨挤挤情景,已是可怜哩。」怀祖道:「英界地形低似法界,各处货栈此时想都积水,若不速睛速退,货物必致霉变。」建威道:「可不是哩。但听这风声雨声,夜中决不得停。」张氏道:「钟上针指寅初,再隔一时,也可天明了。」建威道:「夜色已深,我们虽不安睡,静坐片时,养一养神,方不致过於疲倦。」怀祖道:「好。」便同张氏回房。
建威绝早冒雨踹水,孑身出门,午后来寻怀祖,已不在栈,一抹地走转,直到跑马场,才见夫妇两人,同坐一部亨斯美,观海不足,来看这一洼浅水。
建威叫道:「怀祖兄!你真会自寻快乐呢。」怀祖回头,见他浑身拖泥带水,笑问道:「兄如何这等狼狈?」建威道:「话长哩,停会细谈罢。」各转马头,践着细石,一步步颠将回去。
建威更衣易履,又洗过脸,吃了几杯热茶,才告怀祖道:「早上出门时,安步当车,先过洋涇桥,直出法马路,看中间稀泥滑(水达),稍有点水痕。望东到外滩,又从外滩进英马路,高高低低,一尺二尺不等,竟无一处无水。才僱车到虹口新闸,四处相望一遭,顺便去看几人。谈起此番大水,尚是六十年来第二回发现。沿海沙地田庐人畜,漂没的不知其数。江中大小船舶,断链走锚,撞沉碰翻,也伤了好些人,岸上堆栈,受潮各货,约计要值一千叁四百万两。现虽有人创议疏通,然学界中坚持不用不买,极力鼓扇,与商界為难。将来因潮渐霉,因霉渐毁,商人血本,岂非尽付东流?定货一到,无银应付,后患殆不可测。
「又取一张日报,指着蹇参议所復部中的信道:君试想已到未到,合计如许巨资,本不应令其悬搁。目前天灾流行,义賑诸君方筹银筹米,赡恤被难的穷民,然不从商家着想,何处筹巨款?商家若自顾不暇,又安有餘力,可以舍已耘人?故无天灾,已亟需谋疏通,才能保守商场,有天灾,尤亟需谋疏通,才能兼顾灾民。君自海外来,与商界学界都不容心,能為鲁仲连替两面解纷排难麼?
「弟谓其人道:拒约领袖主改良,争约学会主废约,与鄙人所持之宗旨皆不相合,不相合即难相入,如何能為调人?且商家现存之货,照蹇参议所查,通年约销数,西八月以后,应再存六七百万两。目前计价,乃至千万以外,岂非一半之货,已应归入下年。虽说预為储备,以防市情之涨落,也不应於上年前四月间,存至强半有餘。昧良取巧,乃至於此!这次风潮,正由人力不以施,假手於天,以為儆戒。鄙人如何肯為调人?其人闻言,忸怩不能答,施又强辩道:君毋信学界之谰言,二叁商人犹无能联為一体,全中国的用户保等散漫,真能万眾一心麼?说时容易,做时恐就艰难了。弟怫然怒道:君亦中国人,乃敢薄视中国人,是何可忍?且试问现在美货,商会中不定有疏通之法麼?究竟卖者几家,买者日有几人,两相比较,便可知此番团体之坚不坚,人心之死不死,何用轻唇舌,好為非薄?
「其人忽又装出惶恐的样子,吞吞吐吐说道:正為买者日少,商力恐不能支,才想求学界中人暂敛言论啊!弟叹谓之道:言论為人之自由权,或止或发,凭乎一心。畏人而不言,与哀人而不言,為情虽异,丧权则一。学界中辨之必明,必不致轻為动摇。君辈果情不能已,鄙人却有两法,任君辈所择。其人喜问道:肯代谋疏通麼?愿闻其详。」
怀祖愕然,便欲詰问,张氏止之道:「且听建威说明了再辨不迟。」
建威道:「怀祖兄勿忧,诚行弟之两法,於抵制有百利而无一害,无奈已成空言。弟初谓其人道:美之货不尽销於中国,欧洲日本何地非其市场?君辈暗中运动日本欧洲之商人,以现定美货,略减原价数釐,请其转售,即以买货之资,还而如价买彼之货,一出一入,彼已有利可图,君辈虽薄有所耗,然将来货搁不销,栈租拆息亏数谅不能小,何如急谋脱手,内保成本,外又不开罪於社会之為得策呢?
「其人道:日本欧洲所销的美货,年年亦有定额,不能无故骤增,彼之商人如何肯认售呢?弟道:合一则多,分為数国,则所增正自有限。君辈尚可与之约明,请其电告本国,此处多定,即於彼处少定,若再為难,料想叁数年中,我中国之实业未必兴起,君辈又何妨许以后来销货之利益?彼之商人知我所求者只一年之事,彼之所利者将两年叁年而不止,未必不能许我。
「其人摇头道:许我犹可,因此开罪於强国,要非日本欧洲商人所乐為,君此法不可从,愿闻其次。弟道:次策非始甚不利於君辈,其终则大利為君辈独享,但恐君辈始终不我从。」
怀祖道:「兄究竟如何设策?怎麼不利於先,能有大利於后呢?」
建威道:「弟劝其人邀集商界学界两类人会议,设一大公司,公举数人总理,凡上海美货,不论已到未到,均令减成买入,由公司逐件盖用硬印,匯总批发。」怀祖道:「且慢,六七千万之本银,兄将何处筹措呢?」建威道:「各号卖与公司,现货少,定单多,公司与各号,亦不用现银,而用股份票。譬如定单值银一千万两,公司即出九百作一千之股票,交各号收执,货到时仍令备银出栈。如此於商人岂非甚有所不利麼?却是每千一百之虚数,公司必从卖价收回,即以之制物植產,另再计数填票,分给各号,从此各号又為新厂地之主人。将出產日多,销路日拓,所有餘利,不归主归於何人?归主则不归各号又归何人?岂非可以独享大利麼?」
怀祖道:「兄所谈总不离疏通,岂至今尚為商人顾虑麼?」
建威道:「有限制的疏通,与无限制的疏通,自有分别。且能借此以兴实业,於持久之策,不為无裨。无奈其人以為后来之利,总属渺茫,目前每千先受百两之实耗,此策又断不可从。弟因不復多谈,辞赴酒肆,自斟自饮了半天。又到茶楼品名,忽在新闻纸上,见有一件奇事,兄可知这事如何起因?原来禁演说,阻抵制的告示,是燕云节度主谋,恼动一位大侠,前往行刺,误入文案房,為人所捕。」
怀祖击掌道:「这人胸襟胆量真也不小,可惜一击不中,先要把一颗好头颅轻轻断送了!」建威道:「弟初亦作如是想,及看下文,那知刺者出奇,被刺者更出奇,竟自开门解放。」
怀祖直从椅上站起来道:「燕云节度本负盛名,即从这事揣想,其度量也非常人所及,如何一时糊涂,又与全体反对?真令人无从索解。」
张氏道:「戟门深阻,宿收森严,行刺非其所惧。若然取怨外人,责言日至,头上猩红孔翠,便怕不能安稳。今之节度,谁无此心?只看那年立约互保之疆臣,表面上说為民命,愿其本心,也只為功名而起,有什麼难解呢?」
建威道:「俄之尼古喇士,不毙於虚无党的炸药麼?刺客之可畏,不自今始。坦然释放,怎能不服其度量呢?」张氏道:「苏菲亚之类,中国今无其人。若说一刀一枪,即我辈尚不知畏,况彼身為节度,左右居处,在在有人防护麼?」建威方始无言。
茶房送进一封信来,拆开看时,是会长因事来邀,张氏匆匆坐车而去,至晚方归。第二日下午开会,张氏直到散场,回告怀祖道:「会长已彩我议,将下手方法透澈宣明,会友都已赞成,愿任运动。」怀祖道:「单任运动麼?也有几人能醵貲营业否?」张氏道:「只得十数人。此外,当学生的尚权力,当教习的类都孤寒,自然只能运动别人,不能反求诸已。全会叁百餘人,不望尽数,有一半得手,便可创立规模了。」建威听说,也是欢喜。问张氏道:「约在几日,可得会友的报告?」
张氏道:「想应陆续而来,不能拘定日子。」建威道:「此会倘有成议,我愿以家财一半附属其中。」怀祖道:「弟有时虽不能专主,然必尽力以助其成。」
如是连守五日,建威天天只催张氏去探消息,不想绝无影响。那天晚上,建威觉得枯坐无聊,约怀祖同到剧场听戏,未及两出,又觉厌烦,怀祖无奈,陪着回寓。听房内有人说话,正是会长声音,建威不知不觉,竟自止步。
只听会长道:「运动的无成功,还是在人意中,自允醵貲者,不日便已反覆,真正出人意外。」建威愕然,悄悄问怀祖道:「兄听清楚麼?可奇不奇?」怀祖略略点头。又听会长道:「妹当时有些气愤,詰问诸友,要令讲明缘故,咳!等诸友一说,却也真难相怪了。」
其时张氏侧耳諦听,门外建威、怀祖也自屏气息声的静守。
会长连着说道:「诸友言,虽有此私蓄,然都存之夫婿,有的又须请命姑嫜,不能自由自主。初时应允者,為属固有之财,并非取之公中,自不致横相阻挠。谁知归谋之室,不以為创举之事,男子尚受人侮,每每无以善后,便以為经商服贾,非女子所应為,必致招人姍笑。眾口相合,一人便觉势孤,不能相敌。尚有数友,已与家人同化,索性不来回復了。」建威听到这裡,气得双手如冰。又听张氏道:「我姊妹生在中国,享不到丝毫权利,一举一动,都要受人监视,听人束缚,妹早料有一着,也不怪几位会友食言的不是。但担任运动的姊妹究竟如何回復呢?」
会长道:「姊姊还待问哩。内受家庭的唾骂,外受亲族的讥讽,无一人不来挥泪诉冤,倒使妹几乎置身无地。」怀祖悄向建威道:「兄听清楚麼?照这样说,中国女子的苦情,正如蚕茧,一层深一层,岂不可怜麼?」建威道:「兄且低声,会长还没讲完哩。」
只听说道:「那些唾骂的,无不过说女孩儿家,只应谨守闺门,不该為读几句书,认几个字,便也学着洋派,预闻外事。那些讥讽的,不过说中国以前借着开矿造厂立公司的名色,到处骗钱,却还只得几个男人,如今翻新出奇,女娘们也和在裡间混闹,还成什麼世界?姊姊请想,有这两种议论,诸姊妹虽有粲花之舌,也不能轻下一辞。运动两个字,只索付之梦想。」
张氏道:「从此看来,当时提倡废例的一层,诸姊姊之在家中,怕也受些鬱气了。」会长道:「这却不曾,来妹处报告的,人人都有喜色,那天会中,妹才敢表明全会赞成的这句话。如今推想,怕其家人并非出自真心,不过觉得无关得失,便随声附和,等到要他挑上一副担儿,顿时本相皆露。这是中国人通病,姊姊可不必因后疑前呵!」张氏叹道:「男子不肯担责任,女子肯担,偏又力与心违,大势将不可问了。」
会长忽然呜呜咽咽,掩面悲啼,把门内张氏,门外建威、怀祖,都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