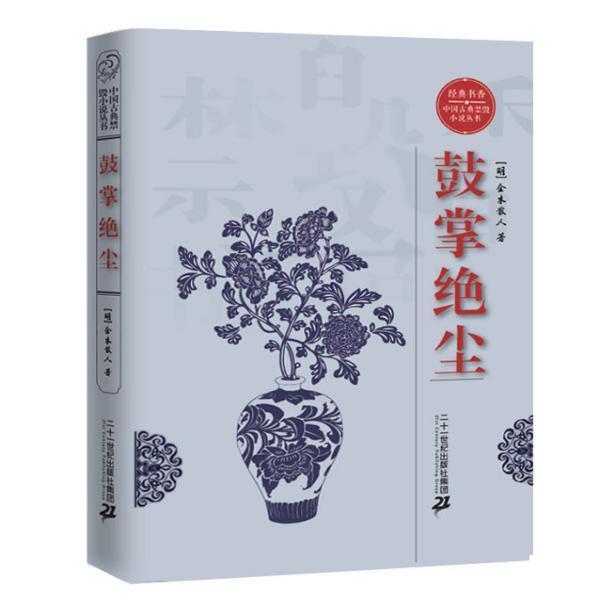遭阉割监生命钝 贬凤阳奸宦权倾
诗:
朝夕炎凉大不同,谩将青眼觑英雄。
半世功名浑是梦,几年汗马总成空。
附势自然生羽翼,肆奸何必说雌雄。
不如解组归林下 ,消遣年华酒数钟。
说那陈珍,受了那场耻辱,恐怕亲族邻里中有人谈笑,也不归家,也不到馆,带了些盘缠,竟到苏州虎丘散闷。来得三四个月,金陵有人来报讣信,说他父亲和嫡母,双双都亡过了。陈珍听说,自忖道:“今番若是回去,怎么好见那些亲戚朋友?便掬尽湘江,也不能洗我前羞。若是不回去,又恐被外人议论。终不然父母双亡,不去奔丧,可是个做人子的道理?”即便收拾行囊,买下船只,星夜赶将回来。
家中果然停着两口灵柩,只见左边牌位上写着:“先考陈公之位,孝男陈珍奉祀。”陈珍看了,抱住棺材,止不住放声嚎啕大哭道:“爹爹,孩儿不能够替你光门耀户,反累你受了万千呕气,教孩儿今日怎么想得你了?怎么哭得你了?”
众亲友见他痛哭不住,齐来劝解道:“陈官人,死者不可复生,今日不须悲苦,往事也不必重提。趁你年当少壮,正好努力前程,一来替你老员外、老安人争了生前的气,二来他在九泉之下,也得双双瞑目。”那众人有慈心的,听说得凄惨,纷纷都掉下泪来。陈珍转身又拜谢众人道:“小侄虽是不才,不能够与先人争气,今日先人亡过,凡事还望众尊长亲目一亲目。”众人道:“惶恐,惶恐。”陈珍便去筑下坟茔,拣了日期,把爹妈灵柩殡葬。自此杜门不出,在家苦读了两年。
真个光阴迅速,看看守制将满。一日与母亲王氏道:“不瞒母亲说,孩儿向年被先生愚弄,做得不老成,费了三四百两银子,买得个秀才。不想金石来做对头,当堂面试,反被他夺了去,只当替他买了。如今孩儿饮恨吞声,苦志勤读,两年不出门,书句也看得有些透彻,文章到也做得有些意思。目今守制将满,孩儿要把身下住的这间祖房,将来变卖了几百银子,再收拾些盘缠,带了母亲、媳妇,进京纳监。明日若挣得一顶小小纱帽,一来不负孟母三迁之教,一来不枉爹爹生前指望一场。”王氏道:“孩儿,你既指望耀祖荣亲,这也任你张主。只恐又像向年,做得不甚好看。那时再转回来,却难见江东父老。”陈珍道:“母亲,古人云,男子志在四方,孩儿这回若到得京中,指望要发科发甲,衣紫腰金,却不能够;若要一个小小纱帽,不是在母亲跟前夸口说,就如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王氏见陈珍说得嘴硬,只得依着他。
陈珍就把房屋卖了五百两银子,零零碎碎,把家中什物又典卖了六七百两,共约有千金余数。拣了好日,拜辞故乡亲友,即便起程。众亲友晓得他进京纳监,都来整酒饯行,纷纷议论说:“看他这遭进京,定弄个前程回来,要和金秀才做场头敌哩。”
那陈珍带了母亲、妻子,逢山玩景,一路游衍,直至三个月,才到得京师。先去纳了监,就在监前赁下一间房屋居住不题。
却说此时,正是东厂太监魏忠贤 当权的时节。京师中,有人提起一个“魏”字儿,动不动拿去减了一尺。那魏太监的威势,就如山岳一般,哪个敢去摧动分毫。一应官员上的奏本,都在他手里经过。若是里面带说个“魏”字,不管在京的、出京的,他就假传一道圣旨,立时拿回处死。因此不论文臣武职,身在矮檐下,岂敢不低头,只得都来趋附他的炎势。不上一二年,门下拜了百十多个干儿子。那第一个,你道是谁?姓崔名呈秀,官任江西道御史。
这崔呈秀,自拜魏太监做了干爷,时常去浸润他。魏太监见他百般浸润,着实满心欢喜,便与别个干儿子看待不同,有事就着他进去商议。两个表里为奸,通同作祟,要动手一个官儿,竟也不要讲起,犹鼓洪炉于燎毛,倾泰山于压卵,这般容易。
一日,是魏太监的生辰。崔呈秀备下无数稀奇礼物,绣一件五彩蟒衣,送与魏太监上寿。魏太监看了那些礼物,便对崔呈秀道:“崔儿,生受了你这一片好心。怎的不留些在家与媳妇们享用?都拿来送与咱爷。”崔呈秀道:“今日殿爷寿诞,孩儿便剖腹剜心,也不能尽孝。怎惜得这些须微物?”魏太监道:“这五彩的是甚么物件?”崔呈秀道:“是一件蟒衣,儿媳妇与孙媳妇在家绣了半年,特送殿爷上寿的。”魏太监道:“好一件蟒衣,只是难为了媳妇们半年工夫,怕咱爷消受不起哩。”便接过手仔细一看,道:“崔儿,怎的这两只袖子,就有许多大哩?”崔呈秀笑道:“袖大些,愿殿爷好装权柄!”魏太监笑了一声,便分付:“孩子们,都收下罢。”
崔呈秀道:“殿爷,这几日觉得清减了些?”魏太监道:“崔儿,你不知道么?近日为起陵工,那些官儿甚是絮烦,你一本,我一本。你道哪一个不要在咱爷眼里瞧将过去?哪一件不要在咱爷手里批将出来?昼夜讨不得个自在,辛苦得紧哩。”崔呈秀道:“殿爷,陵工虽系重务,贵体还宜保全!何不着几个孩儿们进来,替殿爷分理一分理?”魏太监道:“咱爷常是这样想,只是那些众孩儿们,如今还吃着天启爷家俸粮,教咱爷难开着口哩。咱爷到想得一个好见识,却是又难出口。”
崔呈秀道:“殿爷权握当朝,鬼神钦伏。威令一出,谁敢不从?有什么难出口处?”魏太监道:“崔儿,讲得有理。咱爷思量要把那些在京有才学的,监生也使得,生员也使得,选这样二三十名,着他到咱爷里面效些劳儿,到也便当。”崔呈秀道:“殿爷见识最高,只恐出入不便。”魏太监道:“崔儿,这个极易处的事。一个个都着他把鸡巴阉割了进来就是。”崔呈秀道:“殿爷,恐那些生员和监生,老大了阉割,活不长久哩。”魏太监道:“崔儿,你不知道。咱爷当初也是老大了阉割的,到也不伤性命。只是一件,那有妻小的却也熬不过些。”
这崔呈秀欣然领诺,辞了魏太监出来。一壁厢分付国子监,考选在京监生二十名,一壁厢分付儒学教授,考选生员二十名,尽行阉割,送上东厂魏爷收用。你看那些别省来坐监的监生,听说是要阉割了送与魏太监,一个个惊得魂飞魄散,星夜逃去了一大半。
却说陈珍是个小胆的,听见这个风声,便与母亲计议道:“孩儿指望挈家到京,做个久长之计。怎知东厂魏公,要选二十名监生,二十名生员,都要阉割进去。孩儿想将起来,一个人阉割了,莫说别样,话也说不响,还要指望做什么前程?不如及早趁他还未考选,且出京去寻个所在,躲过了这件事。待他考选过了,再进京来,却不是好?”王氏道:“事不宜迟。若选了去,莫说你的性命难保,教我姑媳二人,倚靠着谁?快连夜早早收拾出京便好。”噫,这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陈珍带得家小出京,不上一月,那王氏母亲不伏水土而亡。他便带了妻子,奔了母亲灵柩,回到金陵,与父亲、嫡母合葬不题。
说那崔呈秀,考选了二十名生员,二十名监生,阉割停当。两三日内,到死了一二十。崔呈秀便把那些带死带活的,都送与魏太监。这魏太监一个个考选过,毕竟是生员比监生通得些。魏太监道:“崔儿,这二十名监生,还抵不得十个生员的肚量。”崔呈秀笑道:“殿爷,这也难怪他,原是各省风俗。那通得的,都思量去讨个正路前程出身。是这样胡乱的,才来纳监。”魏太监道:“教那朝廷家,明日哪里来这许多胡乱的纱帽?”崔呈秀道:“殿爷还不知道,这都是选来上等有才学的。还有那一窍不通的,南北两监,算来足有几千。”魏太监笑道:“这也莫怪他,亏杀那一窍不通,留得个鸡巴完全哩。崔儿,咱爷虽有百十多个干儿子,那个如得你这般孝顺,做来的事,件件都遂着咱爷意的。”
崔呈秀便道:“前日孩儿铸一个金便壶,送上殿爷,还中用得么?”魏太监笑道:“若不是崔儿讲起,咱爷险些儿到忘怀了。怎么一个撒尿的东西,也把 ‘崔呈秀’三字镌在上面,可不把名污秽了?”崔呈秀道:“孩儿只要殿爷中意,即便心下喜欢,就再污秽些何妨。”魏太监拍手大笑道:“好一个体意的崔儿,好一个体意的崔儿。咱爷便是亲生了一个孩儿,也没有你这样孝顺。”
崔呈秀道:“如今十三省百姓,诵殿爷功德,替殿爷建立生祠,可知道么?”魏太监道:“这个咱爷到没有知道,甚么叫做生祠?”崔呈秀道:“把殿爷塑了一个生像,那些百姓朝夕焚香顶礼,愿殿爷与天同寿。”魏太监道:“崔儿,这个使不得。如今咱爷正待做些大事,莫要折杀了咱爷,到与地同寿哩。”便呵呵笑了一声,又道:“崔儿,既是十三省百姓诵咱爷功德,替咱爷建立生祠,也是难得的,莫要阻他的好意。只是一件,那河间府,千万要传一道文书去,教他莫替咱爷建罢。”崔呈秀道:“殿爷,这却怎么说?”魏太监道:“崔儿,你不知道。咱爷当初未遇的时节,曾在那肃宁地方,做了些卑陋的事儿,好酒贪花,赌钱顽耍,无所不至。那里人一个个都是认得咱爷的。明日若建了生祠,不是流芳百世,到是遗臭万年了。”崔呈秀道:“偏是那里百姓感诵得殿爷多哩。”魏太监笑道:“这等讲,也凭他建罢。”
这魏太监见各省替他建了生祠,威权愈炽。从天启二三年起,不知害了多少官员。那周、杨、左、万一班大臣,被他今日弄死一个,明日弄死一个。看看满275朝廷上,都是些魏珰 。
谁知崇祯圣上即位,十分聪慧,满朝中玉洁冰清,狐潜鼠遁,怎容得阉宦当权,伤残臣宰,荼毒生灵。把他逐出大内,贬到凤阳。那些科道官,见圣上贬了他,就如众虎攒羊,你也是一本,我也是一本,个个都弹劾着魏忠贤的,崔呈秀一班干儿子,削职的削职,逃躲的逃躲。那些魏珰的官员,尽皆星散。
魏太监晓得祸机窃发,便与众孩子们道:“咱爷只指望坐了大位,与你众孩子们同享些富贵。怎知当今圣上十分伶俐,把咱爷贬到凤阳。你众孩子们可晓得,古人讲得好,大厦将倾,一木怎支?快快收拾行囊,只把那随身细软的金银宝器,各带些儿,做了盘缠,随咱爷连夜回到凤阳,别寻个生路儿罢。”众孩子纷纷垂泪道:“当初殿爷当权,众孩子们何等煊赫,如今殿爷被逐,众孩子那里去奔投生路?”魏太监道:“事已到此,不必重提。咱爷想起古来多少欲图大事窃重权的豪杰,至今安在?这也是咱爷今日气数当绝,你众孩子们也莫要啼哭,只是早早收拾行囊,还好留个吃饭家伙在颈上罢。”众孩子听说,不敢迟滞,即便去打点起程。
这魏太监星夜逃出京城,来到密云地方,忽听报子来说:“圣上差五城兵马汹涌追来,要捉爷回京取斩哩。”魏太监垂泪道:“我那孝顺的崔儿,却往哪里去了?”报子道:“那崔呈秀先已缢死了。”魏太监便把胸前敲了几下,仰天叫了几声“崔儿”。他也晓得风声不好,连夜寻了一个客店,悄自服毒而亡。众孩子各各四散逃生。那五城兵马追到密云,见魏太监服毒身死,星夜回京复旨不提。噫,正是:
人生枉作千年计,一旦无常万事休。后人以词讽云:
《满庭芳》
世事纷纭,人情反复,几年蒙蔽朝廷。一朝冰鉴,狐鼠顿潜形。可愧当权奸宦,想而今,白骨谁矜?千秋后,共瞻血食,凛凛几忠魂。
再说那些阉割的监生,也是晦气,活活的苦了四五年,见魏太监贬去,尽皆逃出。你道那生员去了鸡巴,难道指望还去读得书?那监生没了卵子,指望还去坐得监?只得到太医院去授些方儿,都往外省卖药过活。
却说陈珍奔得母丧回去,便生下一个孩儿。原来四五年里,守了亲娘服满,依旧进京,干了个袁州府判。随即出京,带着妻子,竟临任所。不想那袁州府九龙县知县,半月前已丁忧 去任,他到任就带署了县事。次日是十五日,众吏书齐来上堂画卯。陈府判就将卯簿过来,逐名亲点。却有陈文、张秀二名不到。陈府判便着恼起来,对众吏书道:“你这九龙县吏,就有多大?明明欺我署不得堂事,朔望日画卯也不到齐,快出火笺拿来!”众吏书禀道:“禀上老爷,这陈文因送前县老爷回去,至今未到。这张秀是一月前得了疯症,曾在前县老爷案下告假过的,至今在家调理。”陈府判哪里肯信,便出火笺拿捉。众吏书见他初任,摸他性格不着。都只得起来躬身站立,两旁伺候。
毕竟不知拿得张秀到来,如何发落?还有甚么说话?再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