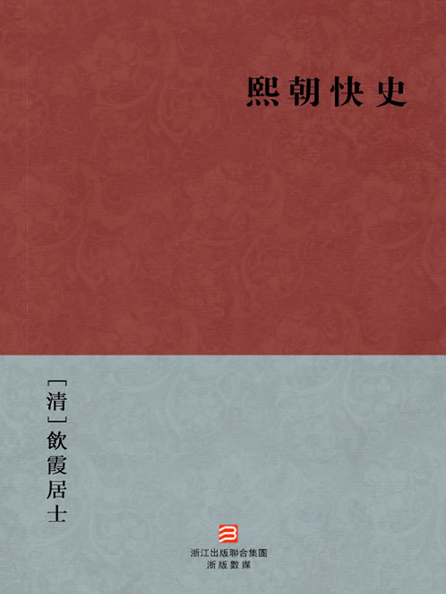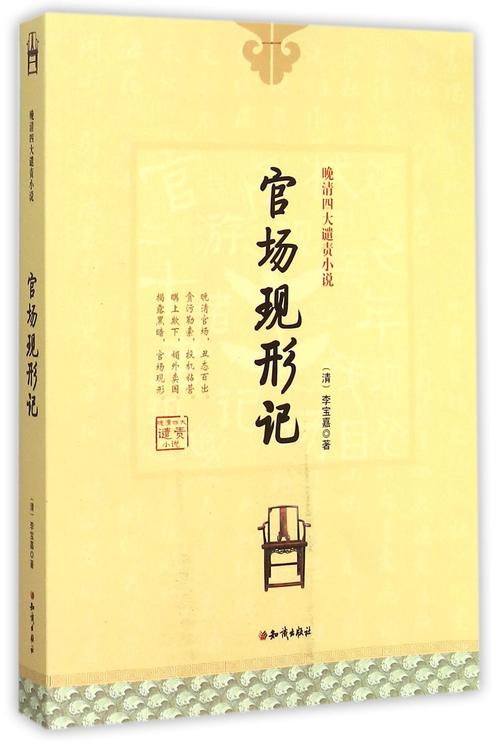话说宝玉自开春以来,忙忙碌碌,十分辛苦,晏眠早起,绝少空闲的时候,一直忙过了正月。将近二月中旬,渐渐的风和日暖,春色融融,最是恼人天气,欲眠不得,他人则春宵苦短,珍重一刻千金;自己则春夜嫌长,怨恨孤栖独宿,虽迩来旧好新知,不乏相交之客,然欲求潘安、卫!,竟无如意之君,因此闷闷不乐,愈思十三旦不置。
那天日间无事,阿金、阿珠陪伴闲谈。宝玉终觉无情无绪,眉蹙春山,闷恹恹懒于对答。阿珠不解其故,问道:“大先生,啥落格两日一点兴致才呒不,戏也勿看,花园也勿去白相,到底阿有啥心事佬?”宝玉道:“奴格心事终猜勿着格,去问里哉。”阿珠又道:“我想想故歇生意实梗好,旧年先多仔几化,大先生落得寻寻快活,日里坐坐马车,到各处花园里去兜兜,夜里有空工夫,再到戏馆里去看看戏,有啥格勿开心?还要上心事,叫我真真猜勿着格哉。”
阿金在旁,却早猜透宝玉心事,便笑嘻嘻的插嘴道:“大先生肚皮里格念头,勿是我勒里海外,惟我末猜得着六七分格。”宝玉道:“既然猜得着,倒说拨奴听听看。”阿金道:“我猜着仔,赖介?”宝玉道:“奴本要告诉唔笃商量格件事体,故歇能够猜得出,奴还赖俚作啥呢?”阿金笑道:“格末我猜哉,我看大先生格心事,别样才呒啥,眼睛门前,单差少一个。”说到这里,停住了嘴,只管嘻嘻的笑。阿珠道:“说末勿说,独讲好笑啥格嗄?据我想想看,大先生勿少啥。”宝玉道:“阿珠去睬俚,让俚笑完仔勒说,奴眼睛门前少啥一个介?”阿金低声笑说道:“少一个人夜头陪陪大先生哉,格句猜得阿准?”宝玉老着脸答道:“算一屁弹着,不过奴心浪格人,阿猜着是啥人介?”阿金道:“我到底勿是仙人,亦做肚皮里向格蛔虫,格落我说勒前头,只猜得出六七分淘成,若然才晓得末,我亦说仔出来哉。”
宝玉道:“格末拿耳朵凑过来,奴来告诉仔罢。”阿金听了,即将左耳凑将过去,宝玉就切切错错说了几句,无非说:“奴故歇心里要想到北京去,找寻十三旦,带道勒京城里做生意,想阿能够格?”阿金听着话,皱着眉头,只是转念不答。阿珠坐在旁侧,不知他们讲什么话,又见阿金这付神情,熬不住问道:“唔笃格私房闲话,阿可以告诉声我介,啥落板要实梗鬼鬼祟祟格嗄?”阿金方开言道:“问得格,听倪讲下去,自然明白哉,勿懂末,我停歇解释拨听罢。”阿珠始点头不语。
宝玉道:“奴搭商量格,究竟以为哪哼嗄?啥一句才勿回答介?”阿金道:“我格大先生吓,我劝去格好,如果去仔,碰勿着俚末哪哼?就算俚一寻就着,俚倒忘记脱仔倪哉,勿搭要好,阿要弄得勿尴勿尬介?况且现在间搭生意来得格兴旺,甩脱仔勒到格搭去末,阿可惜嗄?虽则倪到仔京里也要做点生意,勿见得坐吃格,不过现钟勿撞,倒去巴望赊帐,只怕终有点勿稳格。”宝玉不等他说完,便插嘴道:“奴到格搭去做生意,原是带脚罢哉,亦勿想啥发大财佬,奴格心里,轧实单为仔俚呀,俚搭奴格情义,实梗深法,别人才比勿上格,格格辰光才勒眼睛骨里。后来俚进京去,约奴一年后再见,勿是俚来,定是奴去,奴皆为呒不空工夫,格落耽搁下来格。故歇奴去寻俚,一定搭奴要好,勿会忘恩负义,弄得奴尴尴尬尬格,所以奴放心托胆,敢闯到京里去走一埭。”
阿金道:“唔笃前头格情义,看是看见格,不过大先生终有点一相情愿勒海,阿晓得眼下格时世,靠勿住格人实在多,嘴里说得蛮蛮好,心里其实约约乎,况且格套戏子,愈加靠勿住,格落我勒里劝,去仔勒懊悔,懊悔是来不及格。大先生,格格稳瓶阿要捏哉。”宝玉不悦道:“管稳瓶打碎勿打碎,奴终决勿懊悔格,去仔好,是奴格命,去仔勿好,亦是奴格命,有啥要紧嗄?至于眼门前生意,可得可失,才勿勒奴心浪,下埭回转来,怕道呒不佬,要可惜煞哉?”阿金道:“大先生问仔我,格落我说格,我勒里想,间搭上海场化,顶顶闹猛,各处格人才有格,难信道除脱仔俚,一个才呒不好格,板要到京里去看俚,俚真真变仔活宝贝哉。”宝玉道:“勿实梗讲格,‘麻油拌青菜,各人心爱’,奴随便哪哼,一定要寻着仔俚,难末奴心死得来。”
阿金听了,晓得劝之无益,我何必再做戆人,徒然惹他动怒呢?即便改了口气道:“大先生要去末,倪阿敢拦当嗄?但是现在二月里,天还勿哪哼暖热,我看三月里动身末最好。大先生想阿对呢勿对佬?”宝玉点头称是。阿珠不甚明白,正想动问赴京之故,忽来了几位客人,当时暂将此事不言。晚上阿金方细细告诉阿珠,阿珠亦不以为是,然知宝玉去志已坚,也不便再劝了。这几十天,别无紧要书说。
忽忽已至三月初旬,宝玉取历本观看,拣定十四开日动身。屈指尚有十天,然此刻众客面前犹未吐露,惟那日唤秀林进房,说明赴京一节,并嘱我去之后,论不定一年两载归来,汝不妨自开门户,独做生涯。好在艳史列名,声誉渐播,断不如从前寂寞的了。所有我的节客帐,待到端午,汝当遣人取讨,存在汝处,俟我回申交还可也。此外我之动用木器等物,一并寄留在此,倘汝欲搬场,须写信关照我一声,至要至要。秀林忽闻宝玉一篇说话,知他行志已决,动身在即,也甚依依不舍,惟说干娘到京后,早写信来,开明住址,以免此间悬望。宝玉点点头,又将闲话讲了一回。秀林因房中来了客人,方才退出。
话休烦琐。又过了几天,宝玉预先同阿金、阿珠收拾箱笼各物,一共有十余件之多,因此次出门至少一二年,不得不多带东西,以备应用。收拾停当,复命阿金、阿珠取了自己名片,向各客处辞行,各客得此信息,
或将帐目算结,或与宝玉饯行,直忙到十四那一天。船票早已购定,午后将行李装了一部大塌车,命带去的相帮押了下船,好得那两个相帮一个即是他的哥哥,尽可放心托他在船看守。自己却到晚膳后,方与阿金、阿珠一同坐着马车,来至金利源码头下船。临行之际,重又嘱咐了秀林几句,无非是老套的话儿,恕不一一细表。
单说宝玉等下船后,坐着一间大房舱,甚是宽畅。两个相帮让他们乘了客舱,更觉十分舒齐。当晚无话。次日,轮舟出了吴淞口三夹水,径望大洋中驶去,波涛汹涌,不减赴粤时形景,幸而宝玉出门已惯,尚不至呕吐狼藉,惟在舟中闷睡而已。颠簸了数天,那日将抵津门,阿金偶然步出房舱,向各处闲看一回,瞥见那边一间小房舱门儿开着,里坐着两个女人,在那里讲话,都打着苏州的口音,细细一瞧,却略略有些认识,原来一个是新出道的校书林黛玉,一个是他用的娘姨模样,大约往天津去做生意的。阿金不便上前叫应他们,问他们的底细,仍旧退回自己房舱,告诉宝玉。宝玉听了,略把头点了一点,并不放在心上。
少停船到紫竹林,抵埠停泊。宝玉的箱笼物件,以及零星东西均已聚在一处,却巧各栈房接客的人上船招揽主顾,手中都拿着栈票,宝玉见是佛照楼大客栈,就命相帮唤住。那个接客的得了生意,笑容可掬,便说:“奶奶的行李,点一点数,都交与我,发往栈里去。包管一件都不少的,请奶奶放心就是了。”宝玉却因有贵重物件,终究不甚放心,吩咐相帮跟着照料,自己即与阿金、阿珠上岸。阿珠曾经到过此地不止一次,所以甚为熟悉,便在码头上雇了一部马车,三人坐着,一径向佛照楼而来。宝玉看那沿路风景不让春申,也是繁华的所在,尽可托足,但此番专意进京寻访情郎,至多在此耽搁三四天。心中正当思想,马车已至佛照楼栈门跟首停下,三人下车进栈,自有茶房等招接,引领入内,看定了一间官房。刚正坐下,吃得一杯茶的时候,行李已经发来,均由相帮等查检,无须细叙。
因宝玉在天津并无要事可记,这两天,无非坐坐马车,游览洋场各处的景致,出出风头罢了。惟阿珠独至侯家窝,顺便探望几个亲戚。他的亲戚有好几家开堂子的,一闻胡宝玉到此,人人羡慕,意欲托阿珠转致,留宝玉在此做生意,被阿珠一口回绝,方才断了这个念头。阿珠至晚回栈,告诉了宝玉。宝玉听了,惟有付之一笑,而心中急欲入京,便差阿珠唤茶房进来,问了赴京火车的价目与开车的时候,茶房一一对答。宝玉又说明日午前准定动身,所有许多行李仍托你们押赴车站,安置妥贴,我当重重的赏你酒钱就是了。茶房连声唯唯而退。是晚用过夜膳,大家早睡。不到天明,均已起身。及至宝玉等梳好了头,又将零星应用各物收拾收拾,不觉已是日上窗纱,茶房早走进来伺候。宝玉先将房金算清,然后交代茶房与带来的两个相帮,把行李发至车站等候,自己与阿金、阿珠又饱餐了一顿点心,舒齐舒齐,略停片刻,方坐着马车赶来。比及车站,茶房等也不过才到。宝玉是初次坐火车,不甚在行,就叫茶房购了三张头等票、两张二等票,又写了十几张行李票,始开销了茶房酒钱,同阿金、阿珠上车,坐的是头等,两个相帮是二等。
头等车中,坐客寥寥,甚是舒畅。宝玉靠窗观看,十分快乐。忽闻汽笛怒鸣,大约将要开行了,又见上来了一位阔客,年纪约有四十开外,方面大耳,一部漆黑的须髯,清朗见肉,身上衣服丽都,谅必是官界中人,带着两个跟班在旁伏侍。坐定之后,宝玉又正对他定睛细视,渐觉有些面善,好像从前在那里会过的,却又想不出是何许样人。及至听他吩咐下人,操着广东的口音,忽然心中会悟,只怕就是他了。但容颜比前肥白,须髯也觉得浓厚些,不要是面目相同,其实并非是他,我休要错认了。况我自粤返申的时节,未与他们辞行,私自溜归,谅他们必然议我无情,此番见面叙话,颇有些不好意思。所幸事隔多年,他又非伍大人可比,我尚不难饰词对答,但不知果是他否,因此踌躇满志,颇费疑猜。且见他目不转睛,也呆呆的向着我看,仿佛不敢贸然叫应我的样子,待我问问阿金、阿珠,他们的眼光比我更好呢。所以宝玉回转头来,正要问阿金、阿珠,阿珠先低声说道:“大先生,阿看见后来上来格人,认得呢勿认得?”宝玉道:“奴记性勿好,有点面熟陌生哉,想必认得格?”阿珠道:“就是倪勒广东,俚搭伍大人一淘格区老爷呀!啥忘记脱哉介?”宝玉道:“嗄,实头是俚,提醒仔奴,奴记得俚格名字,叫啥格德雷,搭奴勿哪哼要好格,格落隔仔几年,勿放勒心浪哉,加二故歇面孔壮仔点,所以奴疑心勿定,认勿煞哉,亦认差仔介!”阿珠道:“决勿会认差格,倪老亦勿老来,勿见得眼睛已经花格哉,况且倪勿比大先生,专靠格双眼睛认得人。”宝玉道:“拨俚听见仔,难为情格。既然认得准,搭阿金一淘过去招呼一声,先搭俚实梗实梗说,听俚哪哼回答仔,难末唔笃请奴过去叫应俚,想阿好?”阿珠凑着耳朵答道:“以前亦搭俚十分亲热歇,故歇去叫应俚作啥介?只做看见末,拉倒哉!”宝玉道:“啥能格想勿出念头佬?阿晓得倪初到京里,究属地脉生疏,要末认得两个人,倪是一个方勿认得,故歇碰着是俚,总算认得仔个把,就托俚照应照应,也是好格,作兴有一时尴尬,倪好俚发财,不过拿俚防防荒。奴格闲话,阿差呢勿差?”阿珠连连点头,说:“大先生格见识,倪落里想得到、及得来嗄?”正说之间,又闻汽笛鸣了三声,火车就此开行,起先觉得缓缓的,继而渐渐的快了又快,轮机鼓动,正不啻逐电追风。凤翔馆主有诗赞之曰:
大错休疑铸九州,利权从此可全收。
愿今天下歌同轨,掣电奔雷快壮游。
开车之后,宝玉见阿珠贪看野景,伸手将他衣袖一拉,催促道:“独讲看,毫燥点拉阿金过去说罢。”阿珠听了,方与阿金附耳说了几句。其实阿金早已听得清楚,即时立起身来,同阿珠走至德雷那边。不过相离二丈多路,难道德雷没瞧见宝玉吗?然方才宝玉看德雷,德雷也目不转睛的看宝玉,又难道隔了几年,有些不认识宝玉吗?但此刻只有宝玉一人,或者不甚留意,想不到在这里火车上相会;今宝玉仍与阿珠聚在一处,彼时俱见过面,说过话,且非一次两次,那有一个都不认识之理?然则这样说起来,何以不先叫唤宝玉等三人呢?其中有几个缘故,一来恨他从前私回上海;二来要装做官的身份;三来脾气极大,不比伍大人随俗,定要宝玉等先去招呼他,方显自己的官体。故虽阿金、阿珠走近身旁,他还眼睛向着窗外,一手捋着胡须,装作未见的样儿。阿金、阿珠睹此神情,心中着实不愿意,怎奈吃了这碗堂子饭,又奉了主人差委,只得低声下气,到他面前叫应了一声“区老爷”。正是:
莺燕纵知飞絮贱,蝶蜂犹为落花忙。
欲知与德雷所说何语,以及宝玉到京后情形,下回再行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