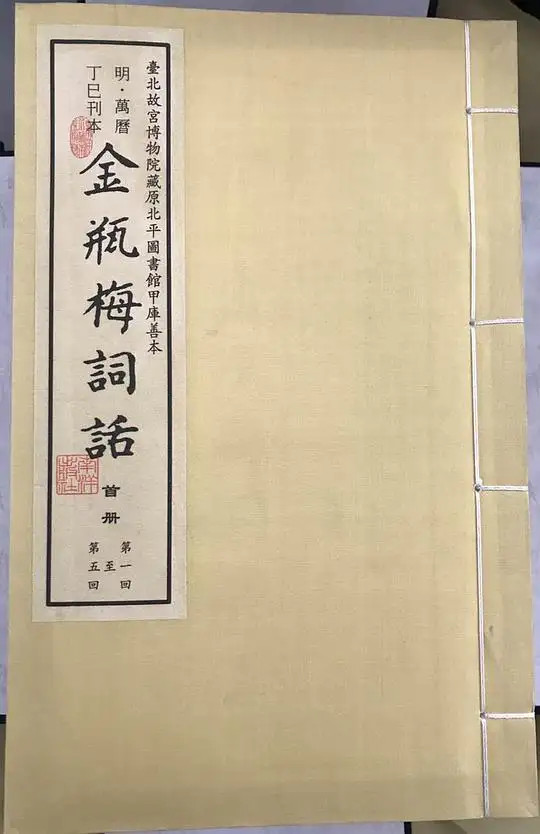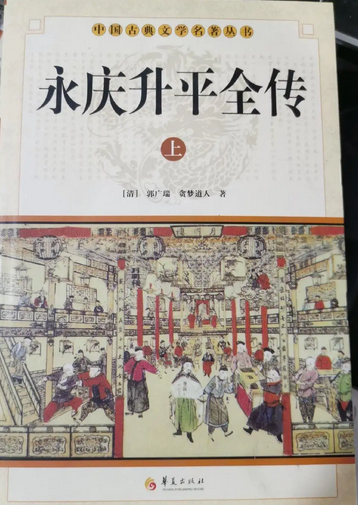第五十四回 应伯爵郊园会诸友 任医官豪家看病症
「来日阴晴未可商,常言极乐起忧惶,
浪游年少耽红陌,薄命娇娥怨绿窗;
乍入杏村沽美酒,还从橘井问奇方,
人生多少悲欢事,几度春风几度霜。」
话说西门庆在金莲房里起身,分付琴童、玳安送猪蹄羊肉到应二爹家去。两个小厮政送去时,应伯爵政邀客回来,见了就进房,带邀带请的写一张回字:「昨扰极,兹复承佳惠,谢谢!即刻屈吾兄过舍,同往郊外一乐。」写完了,走出来,将交与玳安。玳安道:「别要写字去了。爹差我们两个在这里伏侍,也不得去了。」应伯爵笑道:「怎好劳动你两个亲油嘴,折杀了你二爹哩!」就把字来袖过了。玳安道:「二爹,今日在那笪儿吃酒?我们把卓子也摆摆么?还是灰尘的哩!」伯爵道:「好人呀,正待要抹抹。先摆在家里吃了便饭,然后到郊园上去顽耍。」琴童道:「先在家里吃饭,也倒有理,省得又到那里吃饭,径把攒盒酒小碟儿拿去罢。」伯爵道:「你两个倒也聪明,正合二爹的粗主意。想是日夜被人钻掘,掘开了聪明孔哩!」玳安道:「别要讲闲话,就与你收拾起来。」伯爵道:「这叫做接连三个观音堂,妙妙妙!」两个安童刚收拾了七八分,只见摇摇摆摆的走进门来,却是白来创。见了伯爵拱手,又见了琴童、玳安道:「这两个小亲亲,这等奉承你二爹?」伯爵道:「你莫待捻酸哩!」笑了一番。白来创道:「哥请那几客?」伯爵道:「只是弟兄几个坐坐,就当会茶,没有别的新客。」白来创道:「这却妙了!小弟极怕的是面没相识的人同吃酒。今日我们弟兄辈小叙,倒也好吃顽耍。只是席上少不得娼的,和吴铭、李惠儿弹唱弹唱,倒也好吃酒。」伯爵道:「不消分付,此人自然知趣。难道闷昏昏的,吃了一场便罢了?你几曾见我是恁的来?」白来创道:「停当停当,还是你老帮衬。只是停会儿,少罚我的酒。因前夜吃了火酒,吃得多了,嗓子儿怪疼的要不得,只吃些茶饭粉汤儿罢。」伯爵道:「酒病酒药医,就吃些何妨?我前日也有些嗓子痛,吃了几杯酒,倒也就好了,你不如依我这方,绝妙。」白来创道:「哥你只会医嗓子,可会医肚子么?」伯爵道:「你想是没有用早饭?」白来创道:「也差不远。」伯爵道:「怎么处?」就跑的进去了。拿一碟子干糕、一碟子檀香饼、一壶茶出来,与白来创吃。那白来创把檀香饼一个一口,都吃尽了,赞道:「这饼却好!」伯爵道:「糕亦颇通。」白来创就哔哔声都吃了。只见琴童、玳安收迭家活,一霎地明窗净几。白来创道:「收拾恁的整齐了,只是弟兄们还未齐。早些来顽顽也得,怎地只管缩在家里,不知做甚的来?」伯爵政望着外边,只见常时节走进屋里来。琴童政掇茶出来,常时节拱手毕,便瞧着琴童道:「是你在这里?」琴童笑而不答。吃茶毕,三人刚立起散走。白来创看见橱上有一副棋枰,就对常时节道:「我与你下一盘棋。」常时节道:「我方走了热剩剩的,政待打开衣带搧搧扇子,又要下棋!也罢么,待我胡乱下局罢。」就取下棋枰来下棋。伯爵道:「赌个东道儿么?」白来创道:「今日扰兄了,不如着入己的,倒也径捷些儿,省得虚脾胃,吃又吃不成。倒不如人己的有实惠。」伯爵道:「我做主人不来,你们也着东道来凑凑么?」笑了一番。白来创道:「如今说了,着甚么东西?还是银子。」常时节道:「我不带得银子,只有扇子在此,当得二三钱银子起的,漫漫的赎了罢。」白来创道:「我是赢别人的绒绣汗巾,在这里也值许多,就着了罢。」一齐交与伯爵,伯爵看看,一个是诗画的白竹金扇,却是旧做骨子。一个是簇新的绣汗巾。说道:「都值的,径着了罢。」伯爵把两件拿了,两个就对局起来。琴童、玳安见家主不在,不住的走在椅子后边,来看下棋。伯爵道:「小油嘴,有心央及你来再与我泡一瓯茶来。」琴童就对玳安暗暗里做了一个鬼脸,走到后边烧茶了。却说白来创与常时节棋子原差不多,常时节略高些,白来创极会反悔,政着时,只见白来创一块棋子,渐渐的输倒了。那常时节暗暗决他要悔,那白来创果然要拆几着子。一手撇去常时节着的子,说道:「差了差了,不要这着。」常时节道:「哥子来,不好了。」伯爵奔出来道:「怎的闹起来?」常时节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后又重待拆起来,不算帐,哥做个明府,那里有这等率性的事?」白来创面色都红了,太阳里都是青筋绽起了,满面涎唾的嚷道:「我也还不曾下,他又扑的一着了。我政待看个分明,他又把手来影来影去,混帐得人眼花撩乱了。那一着方纔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断一断,怎的说我不是?」伯爵道:「这一着便将就着了,也还不叫悔,下次再莫待恁的了。」常时节道:「便罢,且容你悔了这着。后边再不许你『白来创』我的子了。」白来创笑道:「你是『常时节』输惯的,倒来说我。」政说话间,谢希大也到了。琴童掇茶吃了,就道:「你们自去完了棋,待我看看。」正看时,吴典恩也正走到屋里来了。都叙过寒温,就问:「可着甚的来?」伯爵把二物与众人看,都道:「既是这般,须着完了。」白来创道:「九阿哥,完了罢,只管思量甚的?」常时节政在审局,吴典恩与谢希大旁赌。希大道:「九弟胜了。」吴典恩道:「他输了,恁地倒说胜了?赌一杯酒。」常时节道:「看看区区叨胜了。」白来创脸都红了,道:「难道这把扇子是送你的了?」常时节道:「也差不多。」于是填完了官着,就数起来。白来创看了五块棋头,常时节只得两块。白来创又该找还常时节三个棋子,口里道:「输在这三着了。」连忙数自家棋子,输了五个子。希大道:「可是我决着了。」指吴典恩道:「记你一杯酒,停会一准要吃还我。」吴典恩笑而不答。伯爵就把扇子并原梢汗巾,送与常时节。常时节把汗巾原袖了,将扇子拽开卖弄,品评诗画,众人都笑了一番。玳安外边奔进来报,却是吴银儿与韩金钏儿两个相牵相引,嬉笑进来了,深深的相见众位。白来创意思迟要下盘,却被众人笑了。伯爵道:「罢罢,等大哥一来,用了饭,就到郊园上去。着到几时?莫要着了。」于是琴童忙收棋子,都吃过茶。伯爵道:「大哥此时也该来了,莫待弄宴了,顽耍不来?」刚说时,西门庆来到,衣帽齐整,四个小厮跟随,众人都下席迎接,叙礼让坐,两个妓女都磕了头。吴铭、李惠都到来磕头过了。伯爵就催琴童、玳安拿上八个靠山小碟儿,盛着十香瓜、五方荳豉酱油浸的花椒、酽醋滴的苔菜 、一碟糖蒜 、一碟糟笋干、一碟辣菜 、一碟酱的大通姜 、一碟香菌 摆放停当。两个小厮见西门庆坐地,加倍小心,比前越觉有些马前健。伯爵见西门庆看他摆放家活,就道:「亏了他两个,收拾了许多事,替了二爹许多力气。」西门庆道:「恐怕也伏侍不来。」伯爵道:「忒会了些。」谢希大道:「自古道强将手下无弱兵,毕竟经了他们,自然停当。」那两个小厮摆完小菜,就拿上大壶酒来,不住的拿上廿碗下饭菜儿,蒜烧荔枝肉 、葱白椒料 桧皮煮的烂羊肉 ,烧鱼、烧鸡、酥鸭 、熟肚 之类,说不得许多色样。原来伯爵在各家吃转来,都学了这些好烹庖了,所以色色俱精,无物不妙。众人都拏起筯来,嗒嗒声都吃了几大杯酒,就拿上饭来吃了。那韩金钏吃素,再不用荤,只吃小菜。伯爵道:「今日又不是初一月半,乔作衙甚的?当初有一个人,吃了一世素,死去见了阎罗王,说:『我吃了一世素,要讨一个好人身。』阎王道:『那得知你吃不吃?且割开肚子验一验。』割开时,只见一肚子涎唾。原来平日见人吃荤,咽在那里的。」众人笑得翻了。金钏道:「这样捣鬼,是那里来!可不怕地狱拔舌根么?」伯爵道:「地狱里只拔得小淫妇的舌根,道是他亲嘴时会活动哩。」都笑一阵。伯爵道:「我们到郊外去一游何如?」西门庆道:「极妙了!」众人都说妙。伯爵就把两个食盒,一坛酒,都央及玳安与各家人抬在河下。唤一只小舡,一齐下了,又唤一只空舡载人。众人逐一上舡,就摇到南门外三十里有余,径到刘太监庄前。伯爵叫湾了船,就上岸,扶了韩金钏、吴银儿两个上岸。西门庆问道:「到那一家园上走走倒好?」应伯爵道:「就是刘太监园上也好。」西门庆道:「也罢,就是那笪也好。」众人都到那里,进入一处厅堂,又转入曲廊深径,茂林修竹,说不尽许多景致。但见:
「翠柏森森,修篁簌簌。芳草平铺青锦褥,垂杨细舞绿丝绦。曲砌重栏,万种名花纷若绮;幽窗密牖,数声娇鸟弄如簧。真同阆苑风光,不减清都景致。散淡高人,日涉之以成趣;往来游女,每乐此而忘疲。果属奇观,非因过誉。」
西门庆携了韩金钏、吴银儿手,走往各处,饱玩一番。到一木香棚下,荫凉的紧,两边又有老大长的石凳琴台,恰好散坐的,众人都坐了。伯爵就去交琴童两个舡上人,拿起酒盒、菜蔬、风炉、器皿等上来,都放在绿荫之下,先吃了茶,闲话起孙寡嘴、祝麻子的事。常时节道:「不然,今日也在这里。那里说起!」西门庆道:「也是自作自受。」伯爵道:「我们坐了罢。」白来创道:「也用得着了。」于是就摆列坐了。西门庆首席坐下,两个妓女就坐在西门庆身边。吴铭、李惠立在太湖石边,轻拨琵琶,漫擎檀板,唱一只曲,名曰水仙子:
「据着俺老母情,他则待祅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腾,生分开交颈。疎刺刺沙鞲雕鞍,撒了锁鞓,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支楞楞筝弦断了不续碧玉筝。咭叮叮当,精砖上摔碎菱花镜,扑通通冬,井底坠银瓶。」
唱毕,又移酒到水池边,铺下毡单,都坐地了。传杯弄盏,猜拳赛色,吃得恁地热闹。西门庆道:「董娇儿那个小淫妇,怎地不来?」应伯爵道:「昨日我自去约他,他说要送一个汉子出门,约午前来的。想必此时晓得我们在这里顽耍,他一定赶来也。」白来创道:「这都是二哥的过,怎的不约实了他来?」西门庆就向白来创耳边说道:「我们与那花子赌了。只说过了日中,董娇儿不来,各罚主人三大碗。」白来创对应伯爵说了。伯爵道:「便罢。只是日中以前来了,要罚列位三大碗一个。」赌便一时赌了,董娇儿那得见来?伯爵慌得只管笑。白来创与谢希大、西门庆、两个妓女,这般这般,都定了计。西门庆假意净手起来。分付玳安交他假意嚷将进来,只说董姑娘在外来了,如此如此。玳安晓得了。停了一会时,伯爵正在迟疑,只见玳安慌不迭的奔将来道:「董家姐姐来了!不知那里寻的来?」那伯爵嚷道:「乐杀我老太婆也!我说就来的。快把酒来,各请三碗一个。」西门庆道:「若是我们嬴了,要你吃你怎的就肯吃?」伯爵道:「我若输了,不肯吃,不是人了!」众人道:「是便是了。你且去叫他进来,我们纔好吃。」伯爵道:「是了。好人口里的言语呢!」一走出去,东西南北都看得眼花了,那得董娇儿的魂灵?望空骂道:「贼淫妇,在二爷面上这般的拔短梯,乔作衙哩!」走进去,众人都笑得了不的。拥住道:「如今日中过了,要吃还我们三碗一个。」伯爵道:「都是小油嘴哄我,你们倒做实了我的酒了。怎的摆布?」西门庆不由分说,满满捧一碗酒,对伯爵道:「方纔说的,不吃不是人了。」伯爵接在手,谢希大接连又斟一碗来了,吃也吃不完,吴典恩又接手斟一大碗酒来了,慌得那伯爵了不的,嚷道:「不好了,呕出来了。拏些小菜我过过,便好。」白来创倒取甜东西去。伯爵道:「贼短命,不把酸的,倒把甜的来混帐!」白来创笑道:「那一碗就是酸的来了。左右咸酸苦辣,都待尝到罢了。且没慌着!」伯爵道:「精油嘴,碜夸口得好!」常时节又送一碗来了,伯爵只待奔开暂避。西门庆和两个妓女拥住了,那里得去?伯爵叫道:「董娇儿贼短命小淫妇!害得老子好苦也!」众都笑做一堆。那白来创又交玳安拿酒壶,满满斟着。玳安把酒壶嘴支入碗内一寸许多,骨都都只管筛,那里肯住手。伯爵瞧着道:「痴客劝主人也罢。那贼小淫妇惯打閛閛的,怎的把壶子都放在碗内了!看你一千年,我二爷也不撺掇你讨老婆哩!」韩金钏、吴银儿各人斟了一碗送与应伯爵。应伯爵道:「我跪了杀鸡罢!」韩金钏道:「都免礼,只请酒便了。」吴银儿道:「怎的不向董家姐姐杀鸡,求他来了?」伯爵道:「休见笑了,也勾吃了。」两个一齐推酒到嘴,伯爵不好接一头,两手各接了一碗,就吃完了。连忙吃了些小菜,一时面都通红了。叫道:「我被你们弄了。酒便慢慢吃还好,怎的灌得闷不转的!」众人只待斟酒。伯爵跪着西门庆道:「还求大哥说个方便,饶恕小人穷性命,还要留他陪客。若一醉了,便不知天好日暗,一些兴子也没有了。」西门庆道:「便罢,这两碗一个,你且欠着,停征了罢。」伯爵就起来谢道:「一发蠲免了罢,足见大恩!」西门庆道:「也罢,就恕了你。只是方纔说,我们不吃,不是个人。如今你渐有些没人气了!」伯爵道:「我倒灌醉了。那淫妇不知那里歪斯缠去了!」
吴银儿笑伯爵道:「咳,怎的大老官人在这里做东道顽耍,董娇姐也不来来?」伯爵假意道:「他是上台盘的名妓,倒是难请的。」韩金钏儿道:「他是赶势利去了。成甚的行货,叫他是名妓!」伯爵道:「我晓得你想必有些吃醋的宿帐哩!」西门庆认是蔡公子那夜的故事,把金钏一看,不在话下。那时伯爵已是醉醺醺的。两个妓女又不是耐静的,只管调唇弄舌,一句来,一句去,歪斯缠到吃得冷淡了。白来创对金钏道:「你两个唱个曲儿么?」吴银儿道:「也使得。」让金钏先唱。常时节道:「我胜那白阿弟的扇子,倒是板骨的,倒也好打板。」金钏道:「借来打一打板。」接去看看道:「我倒少这把打板的扇子。不作我赢的棋子,送与我罢。」西门庆道:「这倒好。」常时节吃众人撺掇不过,只得送与他了。金钏道:「吴银姐在这里,我怎的好独要。我与你猜色,那个色大的,拿了罢。」常时节道:「这却有理。」就猜一色,是吴银儿赢了。金钏就递与银儿了。常时节假冠冕道:「这怎么处?我还有一条汗巾,送与金钏姐,补了扇罢。」遂送过去。金钏接了道:「这却撒漫了。」西门庆道:「我可惜不曾带得好川扇儿来,也卖富卖富。」常时节道:「这是打我一下了。」那谢希大蓦地嚷起来道:「我几乎忘了!又是说起扇子来!」交玳安斟了一大杯酒,送与吴典恩道:「请完了旁赌的酒。」吴典恩道:「这罢了。停了几时纔想出来,他每的东西都花费了,那在一杯酒?」被谢希大逼勒不过,只得呷完了。那时金钏就唱一曲,名唤荼{艹縻}香:
「记得初相守,偶尔间因循成就,美满效绸缪。花朝月夜同宴赏,佳节须酬,到今日一旦休。常言道,好事天悭,美姻缘他娘间阻,生拆散鸾交凤友。坐想行思,伤怀感旧,辜负了星前月下深深咒。愿不损,愁不煞,神天还佑,他有口不测相逢,话别离,情取一场消瘦。」
唱毕,吴银儿接唱一曲,名青杏儿:
「风雨替花愁,风雨过花也应休。劝君莫惜花前醉,今朝花谢,白了人头。乘兴再三瓯,拣溪山好处追游。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无花也,好选甚春秋?」
唱毕,李惠、吴铭排立,谢希大道:「还有这些伎艺,不曾做哩。」只见弹的弹,吹的吹,琵琶箫管,又唱一只小梁州:
「门外红尘滚滚飞,飞不到鱼鸟清溪。绿阴高柳听黄鹂,幽栖意,料俗客几人知。山林本是终焉计,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后世,追前辈;五月五日。歌楚些吊湘累。」
唱毕,酒兴将阑。那白来创寻见园厅上,架着一面小小花框羯鼓,被他驮在湖山石后,又折一枝花来,要催花击鼓。西门庆叫李惠、吴铭击鼓,一个眼色,他两个就晓得了,从石孔内瞧着,到会吃的面前,鼓就住了。白来创道:「毕竟贼油嘴,有些作弊!我自去打鼓。」也弄西门庆吃了几杯。正吃得热闹,只见书童抢进来,到西门庆身边,附耳低言道:「六娘子身子不好的紧,快请爹回来。马也备在门外接了。」西门庆听得,连忙走起告辞。那时酒都有了,众人都起身。伯爵道:「哥,今日不曾奉酒,怎的好去?是这些耳报法极不好。」便待留住。西门庆以实情告诉他,就谢了上马来。伯爵又留众人,一个韩金钏霎眼挫不见了。伯爵蹑足潜踪寻去,只见在湖山石下撒尿,露出一条红线,抛却万颗明珠。伯爵在隔篱笆眼,把草戏他的牝口。韩金钏撒也撒不完,吃了一惊,就立起,裈腰都湿了。骂道:「碜短命,恁尖酸的没槽道!」面都红了,带笑带骂出来。伯爵与众人说知,又笑了一番。西门庆原留琴童与伯爵收拾家活。琴童收拾风炉餐具下舡,都进城了。众人谢了伯爵,各散去讫。伯爵就打发两只舡钱,琴童送进家活,伯爵就打发琴童吃酒。都不在话下。却说西门庆来家,两步做一步走,一直走进六娘房里。迎春道:「俺娘了不得病,爹快看看他。」走到床边,只见李瓶儿咿嘤的叫疼,却是胃腕作疼。西门庆听他叫得苦楚,连忙道:「快去请任医官来看你。」就叫迎春:「唤书童写帖,去请任太医。」迎春出去说了。书童随写侍生帖,去请任太医了。西门庆拥了李瓶儿,坐在床上,李瓶儿道:「恁的酒气!」西门庆道:「是胃虚了,便厌着酒气。」又对迎春道:「可曾吃些粥汤?」迎春回道:「今早至今,一粒米也没有用,只吃了两三瓯汤儿。心口肚腹两腰子,都疼得异样的。」西门庆攒着眉,皱着眼,叹了几口气。又问如意儿:「官哥身子好了么?」如意儿道:「昨夜还有头热,还要哭哩!」西门庆道:「恁的悔气!娘儿两个都病了,怎的好?留得娘的精神,还好去支持孩子哩!」李瓶儿又叫疼起来了。西门庆道:「且耐心着,太医也就来了。待他看过脉,吃两锺药,就好了的。」迎春打扫房里,抹净卓椅,烧香点茶。又支持奶子,引鬬得官哥睡着。此时有更次了,外边狗叫得不迭,却是琴童归来。不一时,书童掌了灯,照着任太医四角方巾,大袖衣服,骑马来了。进门坐在轩下。书童走进来说:「请了来了,坐在轩下了。」西门庆道:「好了,快拿茶出来。」玳安即便掇茶,跟西门庆出去迎接任太医。太医道:「不知尊府那一位看脉?失候了,负罪实多!」西门庆道:「昏夜劳重,心切不安。万惟垂谅!」太医着地打躬道:「不敢!」吃了一锺熏豆子撒的茶,就问:「看那一位尊恙?」西门庆道:「是第六个小妾。」又换一锺咸樱桃的茶 ,说了几句闲话。玳安接锺,西门庆道:「里面可曾收拾?你进去话声,掌灯出来照进去。」玳安进到房里去话了一声,就掌灯出来回报。西门庆就起身打躬,邀太医进房。太医遇着一个门口,或是阶头上,或是转弯去处,就打一个半喏的躬,浑身恭敬,满口寒温。走进房里,只见沉烟绕金鼎,兰火爇银缸。锦帐重围,玉钩齐下。真是繁华深处,果然别一洞天。西门庆看了太医的椅子,太医道:「不消了。」也答看了西门庆椅子,就坐下了。迎春便把绣褥来,衬起李瓶儿的手,又把锦帕来拥了玉臂,又把自己袖口笼着他纤指,从帐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来与太医看脉。太医澄心定气,候得脉来却是胃虚气弱,血少肝经旺,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须要降火滋荣。就依书据理,与西门庆说了。西门庆道:「先生果然如见,实是这样的。这个小妾,性子极忍耐得。」太医道:「政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肝经原旺,人却不知他。如今木克了土,胃气自弱了。气那里得满?血那里得生?水不能载火,火都升上截来。胸膈作饱作疼,肚子也时常作疼。血虚了,两腰子浑身骨节里头,通作酸痛,饮食也吃不下了。可是这等的?」迎春道:「正是这样的。」西门庆道:「真正任仙人了!贵道里望闻问切,如先生这样明白脉理,不消问的,只管说出来了。也是小妾有幸!」太医深打躬道:「晚生晓得甚的?只是猜多了。」西门庆道:「太谦逊了些。」又问:「如今小妾该用什么药?」太医道:「只是降火滋荣,火降了,这胸膈自然宽泰;血足了,腰胁自然不作疼了。不要认是外感,一些也不是的,都是不足之症。」又问道:「经事来得匀么?」迎春道:「便是不得准。」太医道:「几时便来一次?」迎春道:「自从养了官哥,还不见十分来。」太医道:「元气原弱,产后失调,遂致血虚了,不是壅积了,要用疏通药。要逐渐吃些丸药,养他转来才好。不然,就要做牢了病。」西门庆道:「便是极看得明白。如今先求煎剂,救得目前痛苦。还要求些丸药。」太医道:「当得。晚生返舍,即便送来,没事的。只要知此症,乃不足之症;其胸膈作痛,乃火痛,非外感也;其腰胁怪疼,乃血虚,非血滞也。吃了药去,自然逐一好起来,不须焦躁得。」西门庆谢不绝口。刚起身出房,官哥又醒觉了,哭起来。太医道:「这位公子好声音。」西门庆道:「便是也会生病,不好得紧。连累小妾,日夜不得安枕。」一路送出来了。却说书童对琴童道:「我方纔去请他,他已早睡了。敲得半日门,纔有人出来。那老子一路揉眼出来,上了马,还打盹不住,我只愁突了下来。」琴童道:「你是苦差使。我今日游玩得了不的,又吃一肚子酒。」政在闲话,玳安掌灯,跟西门庆送出太医来。到轩下,太医只管走。西门庆道:「请宽坐,再奉一茶,还要便饭点心。」太医摇头道:「多谢盛情,不敢领了。」一直走到出来。西门庆送上马,就差书童掌灯送去。别了太医,飞的进去。交玳安拿一两银子,赶上随去讨药。直到任太医家,太医下了马,对他两个道:「阿叔们,且坐着吃茶,我去拿药出来。」玳安拿礼盒,送与太医道:「药金请收了。」太医道:「我们是相知朋友,不敢受你老爷的礼。」书童道:「定求收了,纔好领药。不然,我们药也不好拿去。恐怕回家去,一定又要送来,空走脚步。不如作速收了,候的药去便好。」玳安道:「无钱课不灵,定求收了。」太医只得收了。见药金盛了,就进去簇起煎剂,连瓶内丸子药,也倒了浅半瓶。两个小厮吃茶毕,里面打发回帖出来,与玳安、书童。径闭了门,两个小厮回来。西门庆见了药袋厚大的,说道:「怎地许多!」拆开看时,却是丸药也在里面了。笑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方纔他说先送煎药,如今都送了来!也好也好。」看药袋上是写着:「降火滋荣汤。水二锺,姜不用,煎至捌分,食远服,查再煎。忌食麸面油腻炙煿等物。」又打上「世医任氏药室」的印记。又一封筒,大红票签,写着「加味地黄丸」。西门庆把药交迎春,先分付煎一帖起来。李瓶儿又吃了些汤,迎春把药熬了,西门庆自家看药,泸清了查出来。捧到李瓶儿床前,道:「六娘,药在此了。」李瓶儿翻身转来,不胜娇颤。西门庆一手拿药,一手扶着他头颈,李瓶儿吃了叫苦,迎春就拿滚水来过了口。西门庆吃了粥,洗了足,就伴李瓶儿睡了。迎春又烧些热汤护着,也连衣服假睡了。说也奇怪,吃了这药,就有睡了。西门庆也就熟睡去了。官哥只管要哭起来,如意儿恐怕哭醒了李瓶儿,把奶子来放他吃,后边也寂寂的睡了。到次日,西门庆将起身,问李瓶儿:「昨夜觉好些儿么?」李瓶儿道:「可霎作怪!吃了药,不知怎地睡的熟了。今日心腹里,都觉不十分怪疼了。学了昨的下半晚,真要痛死人也!」西门庆笑道:「谢天谢天!如今再煎他二锺吃了,就全好了。」迎春就煎起第二锺来吃了。西门庆一个惊魂,落向爪哇国去了。怎见得?有诗为证:
「西施时把翠蛾颦,幸有仙丹妙入神;
信是药医不死病,果然佛度有缘人。」
毕竟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