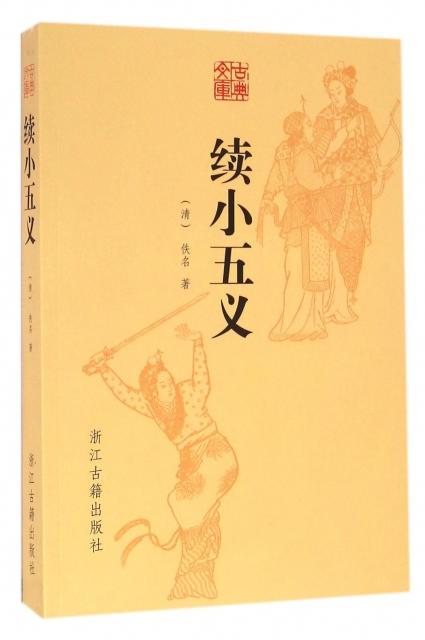且说艾虎往下一跳,工夫不大,夹着贼人翻身上来,往岸上一扔,说:“你们捆罢。”大家上前一看,徐良过去要绑,细细瞧了瞧,微微一笑,回头叫:“老兄弟,你拿的是年轻的是上岁数的?”艾虎说:“哪有上岁数的淫贼哪?”徐良说:“对了,你来看罢,这个有胡子,还是花白的。”艾虎过来一看,何尝不是,衣服也穿的不对,还是青衣小帽,做买卖人的样儿。艾虎一跺脚,眼睁睁把个白菊花放走了。这个是谁哪?徐良说:“这个人还没死透哪,心口中乱跳。咱们把他搀起来行走行走。”张龙、赵虎搀着他一走,艾虎说:“那贼跳下水去,料他去的不远。我再入水中,务必将他拿将上来。”智爷说:“你等等吧,你蒋四叔到了。”就见蒋四爷带着邢如龙、邢如虎直奔前来。皆因是在酱园内,与掌柜的说话,伙计进来告诉,又从楼上蹿下几个人来,往西去了。蒋爷说:“不好,我们走罢。”就带着邢家弟兄,仍出了后门,蹿上西墙,也是由墙上房,见下面做买卖那伙人说,房上的人往白沙滩去了。蒋四爷往白沙滩就追,将至白沙滩,远远就看见前面一伙人。蒋爷追至凉水河,见张龙、赵虎二人搀着一个老人在那里行走,看那人浑身是水,又瞧艾虎也浑身是水。智爷高声叫道:“四哥你快来罢。”蒋爷来至面前,智化就把白菊花下水,艾虎怎么夹上一个人来的话说了一遍。蒋爷说:“张老爷、赵老爷把他放下罢,再搀着走就死了。”又说:“艾虎,你这孩子实在是好造化。”艾虎说:“我还是好造化哪!要是好造化,把白菊花拿住,才是造化。”蒋爷说:“不遇见白菊花是好造化,遇见白菊花你就死了。”艾虎问:“怎么见得?”蒋爷说:“你在水里不能睁眼,白菊花在水内能睁眼视物。你在水内闭目合睛一摸,他赶奔前来给你一剑,我问你这命在与不在?这不是万幸么,正走好运呢。”又对着智爷说:“你还叫黑妖狐哪?”智爷说:“怎么样?”蒋爷说:“谁的主意,搀着这个老头子行走?”智爷说:“我的主意。”蒋爷说:“你打量他是上吊死的,搀着他走走就好了?他是一肚子净水,不能出来,又搀他行走,岂不就走死了吗?”智爷一听,连连点头说:“有理。”蒋爷过去,把那老头放趴着,往身上一骑,双手从胁下往上一提,就见那老头儿口内哇的一声往外吐水,吐了半天,蒋爷把他搀起来,向耳中呼唤,那老头才悠悠气转。
蒋爷问:“老人家偌大年纪,为何溺水身死?你是失脚落河,还是被人所害?”那老者看了看蒋爷,一声长叹说:“方才我落水是你把我救上来的?”蒋爷说:“不错,是我救的。”老者说:“若论可是活命之恩,如同再造,无奈是你救我可把我害苦了。”蒋爷说:“此话怎讲?”老者说:“人不到危急之间,谁肯行拙志?这阳世之间,实在没有我立足之地了。”蒋爷说:“你贵姓?有甚大事,我全能与你办的。”老者说:“惟独我这事情你办不了。”蒋爷说:“我要是办不了然后你再死,我也不能管了。”老者说:“我姓吴,叫吴必正。我有个兄弟,叫吴必元,我今年五十二岁,在五里屯路北小胡同内,高台阶风门子上头,有一块匾,是吴家糕饼铺,我们开这糕饼铺是五辈子了。皆因是我的兄弟,比我小二十二岁,我二人是一父两母,我没成过家,我兄弟二十六岁那年给他说的媳妇,过门之后到他二十八岁,我弟妇就故去了。自他妻子一死,苦贪杯中之物,净喝酒。我怕他心神散乱,赶紧找媒人又给他说了一房妻子。谁知上了媒人之当,是个晚婚。我一想,他又是续娶,晚婚就晚婚罢。我兄弟今年三十岁,娶的我弟妇才二十岁,自从她过门之后,就坏了我的门庭了。我兄弟终日喝酒,她终日倚门卖俏,引的终朝每日在我们门口聚会的人甚多,俱是些年轻之人。先前每日卖三五串钱,如今每天卖钱五六十串、二三百串,还有银子不等。只要她一上柜,就有人放下许多钱,给两包糕饼拿着就走,还有扔下银子连一块糕饼也不拿,尽自扬长而走。我一见这个势头不好。我们铺中有个伙计,叫作怯王三,这个人性情耿直,气的他要辞买卖。我们这铺于前头是门面,后面住家,单有三间上房,铺子后面有一段长墙,另有一个木板的单扇门。从铺子可以过这院来,又恐怕我这弟妇出入不便,在后边另给她开了一个小门,为她买个针线的方便。这可更坏了事情了,她若从后门出去,后边那些无知之人就围满啦;她若要前边柜台里坐着,那前边的人就围满了。那日我告诉我兄弟说:“你得背地嘱咐你妻子,别教她上柜才好,太不成个买卖规矩了。”我兄弟就打了她一顿,不料我兄弟又告诉她是我说的。我们把仇可就结下了。这日晚间我往后边来,一开后院那个单扇门,就见窗户上灯影儿一晃,有个男子在里头说话。我听见说了一句:‘你只管打听,我白菊花剑下死的妇女甚多,除非就留下了你这一个。’我听到此处,一抽身就出来了,骇得我一夜也没敢睡觉。次日早晨,没叫兄弟喝酒,我与他商议把这个妇人休了,我再给他另娶一房妻子,如若不行,只怕终久受害。我就把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我兄弟一听此言,到后边又打了她一顿。谁知这恶妇满口应承改过,到了今日早晨,后边请我说话,我到了后边,她就扯住我不放,缠个不了,听得兄弟进来,方才放手。我就气哼哼的出来,可巧我兄弟从外边进来,我弟妇哭哭啼啼,不知对他说了些个什么言语,他就到了前面,说:‘你我还是手足之情哪,你说我妻子不正,原来你没安着好心。’我一闻此言就知道那妇人背地蛊惑是非,我也难以分辩,越想越无活路,只可一死,不料被爷台把我救将上来。我说着都羞口,爷台请想,如何能管我这件事情?”蒋爷说:“我能管。我实对你说,这位是展护卫大人,我姓蒋名平,也是护卫,难道办不了这门一件小事吗?论说这是不洁净之事,我们原不应该管,皆因内中有白菊花一节,你暂且跟着我们回公馆,我自有道理。”吴必正闻听连连点头,与大众行了一回礼,把衣服上水拧了一拧,跟着大众,直奔五里新街。蒋爷同着展爷先上饭店,那些人就回公馆。
蒋展二位到了美珍楼,往里一走,就听那楼上叭嚓叭嚓,韩天锦仍然在那里乱砸乱打。掌柜的见着蒋展二位认识他们,说:“方才你们二位,不是在楼上动手来着吗?”蒋爷说:“不错,我们正为此事而来。”到了柜房,把奉旨拿贼的话对他们说了一遍。仍然不教他们泄露机关,所有铺内伤损多少家伙俱开了清单,连两桌酒席带贼人酒席都是我们给钱。那个掌柜的说:“既是你们奉旨的差使,这点小意思不用老爷们拿钱了,只求老爷们把楼上那人请下来罢,我们谁也不敢去。”蒋爷说:“交给我们罢,晚间我们在三元店公馆内等你的清单。”说毕出来,蒋爷上楼,把韩天锦带下来。天锦问道:“四叔拿住贼了没有?”蒋爷说:“没拿住。”天锦说:“不教我出来嘛!我要出来就拿住了。”蒋爷说:“走罢,不用说话了。”出了美珍楼,直奔公馆。进得三元店,此时艾虎与吴必正全都换了衣服。蒋四爷说:“方才这老者说在五里屯开糕饼店,白菊花在他家里,我想此贼由水中一走,不上团城子,今晚必在这糕饼店中。你们谁人往那里打听打听?”问了半天,并没有人答应。连问三次,一个愿去的也没有。蒋爷说:“徐良,你去一趟。”徐良说:“侄男不去。”又问艾虎,他也是不去。蒋爷一翻眼,这才明白,说:“哎呀,你们怕担了疑忌。你们全都不愿去,只得我去了。”冯渊在旁说:“你们都不愿去,我去。心正不怕影儿斜,我不怕担了疑忌。”徐良说:“你就为这件事去,这才对了你的意思呢!”冯渊说:“我要有一点歪心,叫我不得善终。”蒋爷一拦,对徐良说:“先前你可不肯去,如今冯老爷要去你又胡说,你们两人从此后别玩笑了。冯老爷,可有一件事要依我的主意,你若到五里屯访着白菊花,你可别想着贪功拿他,只要见着就急速回来送信,就算一件奇功。”徐良说:“他拿白菊花?连我还拿不住哪,他要拿了钦犯,我一步一个头给他磕到五里屯去,从此我就拜他为师。”冯渊气得浑身乱抖。智化在旁说:“你去罢,冯老爷,不用理他。”蒋爷说:“我告诉你的言语要牢牢紧记。”
冯渊拿了夜行衣靠的包袱,一出屋门,碰见艾虎,说:“兄弟,你这里来,我与你说句话。”艾虎跟着他,到了空房之内,冯渊说:“贤弟,论交情,就是你我算近,我的师傅就是你的干爷,他们大家全看不起我,我总得惊天动地的立件功劳,若得把白菊花拿住,他们大众可就看得起我了。”艾虎说:“皆因你素常好诙谐之故,非是人家看不起你。”冯渊说:“我若拿住白菊花,你欢喜不欢喜?”艾虎说:“你我二人,一人增光,二人好看,如亲弟兄一般,焉有不喜之理?”冯渊说:“我可要与贤弟启齿,借一宗东西,你若借给,我就起去,你要不肯借,我就一头碰死在你眼前。”说着双膝跪倒。要问借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