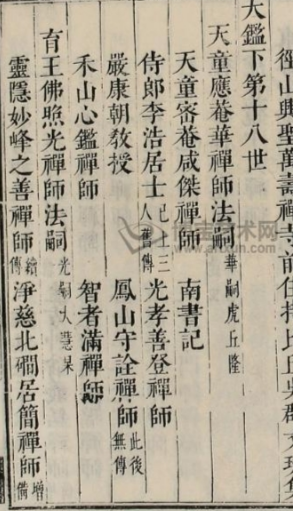新泉问辩续录
门人邵阳陈大章校刊
程世洪问:「圣人之心,天理浑全,不知其亦有体认功夫否?意者顾諟明命,乃圣人之体认,特与人生熟之不侔。未知是否?」
圣人岂无体认?但天机熟,故自然耳。中庸聪明睿知达天德,便是圣人体认。
世洪问:「人以静坐为善学,然静必有物,有物者,天理也,参前倚衡之谓也,未知其气象为何如?抑不知一念正时便是否也?」
自于一念正时自识取,气象难说。
或曰:「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亦气也,二气果将同乎?」洪意气本无二,有主客之少异尔。
皆是气,气一也,人之气即天地之气,以为主客者,非是。
徐文清问:「高公敬尝论迩来功夫。文清云:『只在调停此心,不缓不急,不驰不滞,平铺自在,而参前倚衡之体见矣。』渠云:『要见参前倚衡,则有逐物之病,莫若于此时节,有见而不见之意始好。』然文清意以不见此体,欲功夫有下手处,恐不可得,功夫既中正而天理
(缺页,据康熙三十年本补)
[见其参前倚衡,卓尔跃如,此是自然真见,都勿忘勿助之间有得。或不善体认,则多著想象,即是逐物。故释氏訾之为理障。公敬之言亦救此弊,似亦不可少。
昔尝与洪?子明论戒慎恐惧。渠云:「戒慎恐惧,心之动处,即喜怒哀乐之情,已发也,而又何以有未发之中?故戒慎恐惧者,天理也。」文清以为戒惧还是功夫,而不睹不闻是天理,功夫所以养此天理也。然功夫与天]理非判然二物,功夫停当处便是本体,便是天[理。无]此功夫,焉见天理?只谓迩来学者以戒慎恐惧[为天]理,故便以体认天理为逐外,以学者只做得致[和工]夫。一错百错,毫厘之差,千里之缪,然否?
[以戒慎]恐惧为动,为即是喜怒哀乐已发,为即是天理,皆未是。戒惧不过时时警觉不怠耳。吾子所说皆是切要,在察见不睹不闻之体,而戒惧以养之耳。
周有容论心要常照管。公敬曰:「无端私欲横生,盖由不照管故耳。今欲常常照管,则常常光明,私欲何自而生?」文清以为照管二字,诚今日为学之要务,然欲照管则便不能照管矣。君子之学惟在于立其主而已,主立则常知常觉,随动随静,常常照管,而天理流行。先生四勿总箴于学者极有力,曰:「如精中军,八面却敌。」精之云者,主立之谓也,而照管在其中矣。然立主又非可以作意为也,惟在调停于勿忘勿助之间,不致纤毫人力,则此主精精灵灵,通贯百体,遇未接物,此主之神明耿耿不昧,而私欲退听,以至处常处变,处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不为势屈、不为利疚、不为达变,皆此主之精灵一以贯之而不遗也。故曰:「精灵之至,是谓知几。」其此之谓乎?
此段看得好。「照管」字恐说得太重,此心时时常明,如悬明镜然,物无不照,不待临时纔去照管他,如此则又多一照管矣。
一友论戒惧以养天理,其义未安。盖戒惧者心,既云是心,即是好心,即是天理,而何以又云养天理?若此者,谓之非逐物者,诬我也。文清云:「浑然天理,这是道心,乃人之真心也;蔽于私欲,这是人心,非人之真心也。真心即所谓好心,心也者,虚灵知觉之神也,察见天理而戒惧以培养之焉,即功夫即见天理,而虚灵知觉之体浑全矣。不见天理,其得谓之真心乎?夫心之用广矣,循理而为圣为贤者,此也;徇欲而好货好色者,此也;陷于一偏而为杨、为墨者,此也;充一偏之极而至于弒父与君者,此也,其可得以谓之真心乎?其皆得以谓之天理乎?故以戒惧为天理者,由其以心为天理,一错百错,其流之弊,不至于为杨、为墨不止也。」
若如此言,则中庸止言「聪明睿知」足矣,何以谓「聪明睿知达天德?」天德者,天理也,若未察见天理,则戒惧所养何物?或者之言妄矣。道家诗犹能云:「鼎内若无真种子,如将水火煮空铛。」毫厘千里,不可不辩。
骆尧知问:「庄渠作白沙先生祭文,有黜聪明之说,盖本于白沙先生『去耳目支离之用』然乎?」
白沙先生说「去耳目支离之用」,不曰「去耳目之用」,犹书云「不役耳目」,非去耳目也,但恐今学者不善读书耳。
李尚理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此固孟子独得千古作圣功夫之程度,自程子论仁,已曾拈出教人矣,而又加以未尝致纤毫之力,吁!尽之矣。孟子以前,只说个敬,则勿忘勿助在其中;程子以前说勿忘勿助,则无纤毫在其中,所以各各痛彻迸口说出来者,不得已也。白沙先生立本自然之教,意正如此。昔理也初见之时,蒙问理字,答曰:『希孟,先君所命也。』先生语曰:『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尽此一言,可希孟矣。』于时心已豁然,至今日觉颇得力处,端端的的在此也。夫为学而必有事焉,则其学也实;勿正焉,则其心也虚。虚故无感不通,实故无行不利。然使或忘焉,或助焉,胥失之矣,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一以贯之者也。又尝推之,则所谓博约也,精一也,知行也,明诚也,慎独也,止至善也,是皆在勿忘勿助之间,随处察见天理,而存存为我有也。是故知行合德矣,心事合几矣,内外合原矣,先后合道矣,理所服膺者如此,若容有误而或不自觉者。」
希孟所说所见,皆合吾意,观自然堂铭序可见。如是用功,真可希孟矣。
易经一部,理尝欲以伏羲四图,不赘一字,自为一部,为伏羲之经。以文王乾坤三索图、八卦圆图列于前,次乾坤至未济六十四卦画列于后,每二卦一板,以便玩味,而写彖辞于各卦之下,又为一部,为文王之经。复就文王之经之内,于各卦后离开六行写各爻辞与彖平,又为一部,为周公之经。复就周公之经之内,冠伏羲之经于首,而每卦卦爻辞后略低一字,写孔子彖传、大小象传,而乾文言传照今写乾卦后,坤文言传照今写坤卦后,系辞以后皆如其旧,此又为一部,为孔子之经。此虽非古,易便观览,且亦不甚破折,未知可否?
古易只伏羲文王卦画彖爻辞为经,孔子十翼为传,以传解经,说了又说,许多广大悉备。后儒又纷纷添说,是以易道不明。
又问:「易未作之前,其理在天地,与天地间万有并形之物,固非屑屑求合于河图也;河图虽出于伏羲之时,但此已非作易之本。窃意河图图适与文王卦位合,而大衍策数又符之,疑是易道中兴之时,则之以易卦位制蓍策与?故伏羲之图之前,不敢先著河、洛二图也。抑圣人所为成天之能,固不待于河图、洛书,亦不违乎河图、洛书也?草率之见,唯就正焉。」
伏羲作易,只见天地间,惟阴阳奇偶耳,故始作一画,于上加之至六,而后尽天地人物变易之理。洛书之合者,[亦]合于此耳。后世有圣人作易,亦不过此,故伊川见卖兔者,亦云:「观此兔可以画卦。」亦以其一头一尾、二耳四足,一奇一偶之数耳。至宋而后,圆图方图出,其初画成只是横图耳,余皆后人添上。
心性图有谓:「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又中庸测有所谓「气之中者,即命即道,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即性。」近见史文有所谓:「五六中合,民所受以生。」窃以为得其旨。
五六天地之中,即刘子之说,彼时去古未远,故有此流传。
骆尧知问:「学不闻道,犹不学也,闻道则无过举。尧知非不学问以求放心也,非无小春秋以记过也,而于道未得,未能入寡过之地,何也?近幸得侍新泉,日玩先生身言之教,愈见此学只在自家调停此心,如调息然。何为调停?夫用而不用者,心也,觉得忘时,便著提醒,觉得助时,便要斩截,不使昏放矜持太过,此调停功夫也。这个功夫用得亲切,无有疏脱,则勿忘勿助之间,天理见矣。勿忘勿助,敬之节度也,故明道先生曰:『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可以驯至也。』然则戒慎恐惧贯动静而言之,如读书时敬,则本体不失而理益明,先生所谓『读书观山水不失己,书以明心,非以累心也』。应事时敬,则本体不失而理不差,先生所谓『几上用工,虽人事纷纭,不失吾心之本体也』。知乎此,则谓之随处体认天理可也,谓之戒惧慎独以养中可也,一贯无二,此千古圣贤中正心法。一息助忘,便是罪过,虽曰学道,而此心一忘一助,以之读书,依旧是埋头册子,不超于俗;以之应事,不觉失其所止而化于物,如此安得洞见道体,参前倚衡,壁立万仞,洒然平易,静而不息,动而不流?愚故曰:这个勿忘勿助中正的心法,须是劈初心上见得,虽颠沛造次、终食不违,而后能有受用处。夫谓先生之心法,即千古圣贤之心法,盖尝证之,如书之『精一以执中』也,如论语之『博约以为仁』也,如大学之『知止安虑以止至善』也,如中庸之『尊德性、道问学以修至德』也,如孟子之『学问以求放心』也,与夫戒惧慎独以养中者,一也。譬之镜焉,镜明而后能照物。不求磨镜而求照物者,众也;持镜照物与反鉴索照者,亦众也;物来则照,物去不留者,圣人也。圣人无事于镜,静为镜体、动为镜用者,缉熙敬止也。是故圣贤之学,先立乎其体而已,有体即有用。是故礼以存成性,则成性存存而道义出矣;戒惧慎独以养中,则中立而和生矣。朱子所谓『无过不及』,乃不偏不倚者之所为也,夫子所谓『修己以敬、以安百姓』者也,子思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也。虽然,普物无心之心,顺事无情之情,此皆本体之妙,学者当自得之于言外,不可以言传也。可以言传者,心法也。心法可以言而传,又不以易而能,若非打揲了习心两漏三漏子,而便能做勿忘勿助的功夫,不亦难乎!且如白沙先生与先生诗云:『千休千处得,一念一生持』,先生乃谓此言『非全放下,终难凑泊』,不知所谓全放下者,拆亦明道先生所谓『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焉』云乎?明道先生又谓:『鸢飞鱼跃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而勿正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不会得时二段,,只是摆弄精神。』又何谓也?」
先观吾君举十年前小春秋记过,后观吾君举此篇之问,乃知此吾君举觉后语也。以小春秋十年之功,乃能一旦弃去,以相信从,可谓舍己从人,自非明哲善择,何以及此?即君举所谓打叠了习心,乃能做勿忘勿助功夫也。世之贤者,一有意见便自以为是,固守而不知悟,其视君举之虚以受人远矣。君举所言多切要,如云:息忘助便为罪过,与磨镜之喻,静为镜体、动为镜用之喻,非实用功,何以及此?所谓调停此心,用而不用,即是勿忘勿助之间,合下下手便要如此,不必待于其忘助时乃提醒斩截之,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也。其白沙先生之所谓休,乃朱子全放下之说,乃孔子毋意必固我之说,而或者闻之便以为禅,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可叹可哀!吾子试于此心全放下时观之,乃知勿忘勿助之间,与鸢飞鱼跃同一本体自然,然后信明道与白沙二先生之言为不诬矣,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高简问:「虚灵知觉,心之本体,本体何尝不中正,盖天理即吾中正之性,性即吾心之生理,心之生理却虚灵知觉,能物来而顺应,本无不中不正者也。问辩录有曰:『以心为天理之患,以知觉为性之病。』简窃疑之,毋乃恐道通谓只是这些虚灵意思,其流弊至于不加体认,而或至认其私意以为虚灵矣乎?」
吾所答周道通之说,已明白痛切,不知吾公敬何以有此疑?无乃于释氏蠢动含虚无非佛性之说,犹未勘破乎?吾为吾子忧也。谓虚灵知觉本体无不中正,即天下无恶人矣;牛马含灵,亦皆如人之性矣。不可不仔细察识也。
简问:「事至物来,虽是方外功夫,然量度而后得宜,却不曾离了直内功夫。先生曰『心事合一』,尽之矣。详录中徐子所问,犹不免析内外为二的意思,先生乃曰『贤见得是』,如何?」
理无内外,就心而言谓之敬直,就事而言谓之义方,合内外之道也。吾故于徐勖之问,以方外也著力之说,不得而非之。
又问:「本体知觉即是良知,恻隐之类正是本体知觉,即良知也。今问辩录有非良知之说,窃有未喻。又云:『灵觉知识即非知之实理,若非所知之实理,即非灵觉知识,即非本体,即是意见。』盖实理即中正,中正之心乃为灵觉,乃为知识,若愚人之与物类,非无觉也,而不可以语灵;非无知也,而不可语良知;以其不中正而有蔽耳。今如录中云云,何如?」
吾所辩养知,不是只养他这灵觉,乃养其所知之理,程子意正如此,亦已明白,今人以知觉为良知,非也,吾子何疑!
辩录中有「知之在先,行之在后」二句,恐未免复启学者知先行后之惑,而昧通乎行而知之正旨矣;请裁之。
观易「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及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可知,但知行通贯耳。
简问:「讲学默识,固是合一功夫,然所默识,即其所讲者也;其所讲者,即其默识者也。今问者云:『讲学时即须存个默识意思,俾能得诸心;默识时又于所讲者旁通而曲畅之,俾能开其明。』恐一心之中,而未免有安排布置之病,虽曰一事,而实有以二之也。先生未见非之,敢疑?」
非有彼此往来二端,只是此心常勿忘勿助,何等自然,何有安排布置之病?有安排布置乃助矣。
辩录中有「精明不昧处是知」,即清明在躬之意,此间未似差,盖不昧处,即是私欲无所蒙蔽,惟无所蒙蔽而后谓之知觉,乃心之本体也。今曰「知觉是心」,而又曰「必有所知觉之理乃为真知」,愚谓心之知觉,本无有不中正者,即天理也,即真知也。若如近时以知觉为良知,而无知觉,即非真良知也。详先生语意,窃疑以所知之理为真知,则既指知觉是心矣,则所以知觉者非天理乎?若非天理,则亦不得为知觉矣,而复指所知之理为真知,岂惧夫人误认蠢然之知觉为真知乎?
佛氏有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知觉乃人心之灵明处,而便以此为性,则不可。如马牛皆有知觉,人之为恶,至如盗贼,皆有知觉,方能设巧计以劫人杀人,岂可便以知觉为天理?当彼时亦似精明不昧、清明在躬,而实非精明不昧、清明在躬也,故谓知之正当处为精明不昧、为天理,则可;谓知为精明不昧、为天理,则不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故学不可不仔细讲也。
简读阳明议论,其「致良知」正用学问思辩笃行功夫,如曰:「惟精者,惟一之功;博文者,约礼之功;道问学者,尊德性之功。」皆是致的意思。第其门人流传之差,故有谓不用学问思辩笃行之功者,非其本旨也。先生于问辩录中有为之指其弊,得非惧流传之差而使学术之偏乎?抑亦有见乎?立言者之果偏而故救之乎?
吾元年同方西樵、王改斋过江吊丧,阳明曾亲说:「我此学,途中小儿亦行得,不须读书。」想是一时之言乎?未可知也。亦是吾后来见其学者说此,吾云:「吾与尔说好了,只加学问思辩笃行,如此致之便是了。」
谢显问:「心体天地万物,元来只此心,得其中正时,虚明之本体既复,而生生之理自是不息,自是与天地万物相为流通,不成要把个躯壳之心安顿著天地万物而后为体也。向来落此想象,心中常若有物,恁地不洒脱,近纔觉得全放下为对症之方,然尚未能豁然于怀耳。」
此是吾子悟处。体认天理,正怕想象,亦恐人认作逐物去,都于全放下处有得。白沙先生诗:「千休千处得。」斯言岂欺我哉?勿忘勿助,便是全放下功夫。全放下非放倒也。
显问:「人之精神意气常令收摄近里,则聪明内蕴,运用有主,便时时见得参前倚衡底景象。顷刻不收摄,则顷刻便昏愦了也。故程子曰:『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石翁亦曰:『藏而后发,形而斯存。』其与先生毖斋之吟,皆天地人之一致欤?」
正是如此看,顷刻不收摄,即顷刻便昏愦;若顷刻收摄,即顷刻便精明,便参前倚衡之体见,便是合内外之道。非有表里,何有远近?近字与里字亦不消说矣。
又问:「即天地之四时行、百物生,其在我为率性以和乎情;即天地之寒暑灾祥、变动不居,其在我为约情以正其性。则是天地我之性情一也,天地之化即我之化,而万事万物莫不协于一,万事万物一,则无事矣。故曰:天道至教,圣人至德,至教至德,性情焉尽矣。是如此否?」
记曰:「人者,天地之心。」最是精微。若看得破,则人与天地只是隔一形骸皮肤耳,其气未尝不贯通。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人之性情即天地之性情;性情正而和,而万化生焉,故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是天地万化在我矣。孟子说「乐莫大焉」,大不足以言之也,特就人言耳矣。
显问:「圣人之道至卑而至崇,至虚而至实,其曰『智崇而礼卑』也,曰『文章、性与天道』也,曰『费而隐』也,曰『广大精微、高明中庸』也,则皆兼举、一原无间之实,欲人察识而会其全。故心性图只『包』、『贯』二字,便括尽宇宙内许大道理,言亦不过就人之本来体段画出以示人耳。人能常戒惧慎独以存养此体,则全体浑成、神妙不测,而于天地万物无不包;其发用不竭,而于天地万物无不贯。何等直截!何等洒落!而世之学者,顾有顽守空寂以为崇,徇生执有以为实者,是足以尽包贯之妙否乎?」
观此段,即吾子近来学问又进一格矣。此意不易见得,可善扩充,图在吾子之心矣。但合下便自有包贯,不分体用,随体随用,皆是本来如此。
又问:「心一也,用而未尝用者日益明,滞于用者日益晦。尝观周公制礼乐、系周易,孔子修定六经,下迨濂洛关闽诸君子之言论训释,概不为少,皆以是继往开来,而斯道至于今昭昭尔也。考亭勰勰著释,煞亦以阐明斯道为志,然而斯道反若未尽,人则以是病之者,亦其用心之有间欤?发愤刊落,其有以觉乎此耳!」
用而未尝用,即勿忘勿助之旨,此句最好。[诸]圣诸贤岂为事累?文公诸子必自有处置,则不可知。吾但见前辈未曾说破,及此理有缺,则生人之道未备处,有意即随笔而书,无意即止,亦必如明道作字时甚敬,功夫不离本体也。
洪梓问:「无在无不在,道体如是,功夫亦如是,此为圣学一贯不遗之旨。姑自饮食一端言之,人莫不曰:『当食而食、当饮而饮,便是道。』然观之程子曰:『别人吃饭从脊皮上过,某吃饭从肚里去。』中庸亦曰:『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盖以言乎心存也,心苟不存,则不知味而从脊皮上过矣;心存云者,非在于饮食,亦非不在于饮食,在而不在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亦不息此心而已。有在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而无所不在者,又非冥然荡然而无所止也。惟执事敬而忘助无,则庶可以恒见吾心之本体而存存不失。」
无在无不在,于饮食上调停亦切近,处处事事须如此用功。
先生尝云:「学须事上磨炼。」当时不知动上求静之旨,未免劳扰不安。近来幸闻初学还须静坐之教,与程子且省外事,白沙先生静中养出端倪之说,先后一致。梓乃今静坐之时多,而接应之时少,不觉此心略有澄然意思,及其接应处不甚周张忙错,方知坐有益。但静坐中有时昏明交战,有时脱然无事,若身居太古之上,其昏明交战,恐其终难有恒;其脱然处,又恐或流于空耳。
静坐固善,只恐又靠在一边,不若随静随动,内外两忘,更中正,便无事了。
梓问:「人子莫大乎顺亲,后世之为父兄者,莫不以科第责成于子弟。然由之有道,得之有命,为父兄者,或未深悉此义,一试未利,则曰:『吾子弟不能显亲扬名以成考志。』乃终日不乐,为之子弟者将若之何?愚意以为平日固宜早夜孜孜,勤勉举业,且曲尽子职,以喻之于道,俾之安于义命,则小小得失皆不足计。此亦为己为亲之要道,不可不明辩而豫立者。」
强勉进德修业、立身行道、显扬父母,乃孝之大者,备尽为子之道,未有不能孚乎亲,为己为亲,只是一事。
汪以仁问:「高简云:『静思时殆觉念头纷起,及至动而应事接物,似脱然无累。』愚验之亦若然者。后推其故,毕竟仍是静思之未得其真耳,使得其真,则浑然在中,自无偏倚,邪念何由而生?若应事接物而无累者,疑是此心直向事物上去做,而为事物牵引,自忘怀乎善恶之念,亦非动定者也。」
静时念头纷起,由于思之未真;动时似乎无累,由于心之随物。吾子以此反观内省,是矣。
孟子曰:「志至焉,气次焉。」程子曰:「志动气者什九。」是故人之所患者,志有不立尔,未有志立而气不为之辅者。愚尝自考,鄙志未尝不定,及至所为委靡退缩。推原其故,须仍是志未能真定。志气俱为一身之备,运用之间,疑若亦无轻重先后之甚别也。何如?
人只是一个志,志至气次。气一,气随也。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以仁又问:「天理人欲,不欲并立,当天理在时,不知人欲退于何处?人欲蔽时,天理又岂不系于心?其发见之微而交[胜]之机,必有所以然而然者。」
学者只是终日乾乾,体认自家本来天理,则人欲自消。又欲皆于心有懈怠时生,懈怠便是欲胜理之机也,又何必问其所以然乎?
施大任问:「当平旦时,自觉心地明莹、气象清虚,疑此即是天理萌动。及旦昼间遇一事来,此心不免为之昏扰,举动谬迷,去平旦时若远甚,正孟子所谓『梏亡之矣』。切虑人之一身,万事萃焉,安能一无所为?一日之间,安能常如平旦?今欲使遇事如无事时,一日常如平旦时,天理常存、本心常静,其必有至要之法也。」
当明莹清虚时,这一点大公之心便是天理;若明莹清虚而一无所见,恐又(尚)[向]别路去了。惟常存此心,勿忘勿助时,便常见此,更无别法,稍忘助即失之。
大任问:「心之本体,一友云:『在于勿助勿忘。』一友云:『觉者,心之本体。』及质之明论[云]:『知觉也者,心之本体也。』则以觉为本体者为的当,勿助勿忘似为存此本体之功夫。然有知非所当知,觉非所当觉者,谓之本体可乎?」
是如此看,不可便以知觉为中正、为本体、为天理,明论正谓中正的知觉。
又问:「二业合一训云:『读书以养吾心性,以体吾实事,而举业在其中。』诚为确论。言不应试则已,欲应试,恐于词章亦不可缺,盖有心性实事,而词章不足以发之,亦终于言之无文,第不可剽窃而为之耳。」
吾所谓二业合一者,就于读书作文写字中存习,则词章自高妙,非欲人缺词章也。
今之教人者,有谓先孝悌而后心性,以孝悌乃庸行之常,学者易于学,教者易于教,非若心性之有难于语人者。
孝悌即是心性真切处。谓先孝弟而后心性者,徒以服劳奉养、徐行后长之事为孝弟耳。此等学者,便不识心性,乃俗学也。
大任问:「后儒云:『自洒扫应对上可以到圣人事。』又曰:『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窃以道理一贯,初无其然、所以然之说,如洒扫时诚敬以趋事,即此充之,天德王道在此,便可到圣人事了,岂又有所以然之说哉?」
就事便立诚敬。
叶春芳问:「久侍教于夫子,不敢常有请,非不欲有请也,惧之行不于其言,有负夫子之教耳
!窃意体认天理,勿忘勿助,求之急促便是助长,又安见得天理?故只潜心体认天理,且于日用人事上验过,惟求『真实』二字,不敢少有假借,行得一分实处,方有一分受用,庶优游厌饫以渐而进耳。何如?」
吾子有行不逮之忧,即可生勇矣。真实则果确,果确则勇,然世儒认得真实者少,多以有执著必信必果为真实,非真实也。惟勿忘勿助,心自诚确,乃真实也,可于此自知识。
春芳问:「孔门不仕大夫之家者,闵子、曾子数人。曾、闵而下,由与求皆高弟也,一则臣季氏,一则食辄之食,二子得圣人为之依归,而大节如此!窃尝揣之,圣人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而由、求皆有用之才,使二子之出,救得一分,则人受一分之赐,此圣人仁天下之心也。乃若曾、闵之不仕,则又正当的道理,故不仕者,孔子未尝强之;其仕者,孔子亦未尝止之,皆有义存焉。是否?」
圣人心如化工之付物,因材而笃。天地岂待物物而雕之?圣人岂得人人而强之?出处之道亦多矣,或出或处,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孔子一身,仕止久速皆备,惟时焉而已。时也者,道也,今儒只以不做官便是道,末之难矣。
又问:「以静为学,非知道者不能,故大学曰『定静』,周子曰『主静』。然须于静时有个操存涵养功夫,如江门夫子所谓『静中养出端倪』,又曰:『藏而后发』,诚与圣贤之言千古一(辄)[辙],非如释家之所谓『静而寂』也。世之学者不知先生之详,乃有摘其序道学传所谓『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二语,似涉于禅。窃谓支离之用,亦当去之,非谓黜聪明也。心之神明不测,全其本体,如孟子之存心,亦何足以病夫先生!知道者自能识之。何如?」
谓以静为学则不可,谓静为非学亦不可。静中有见,则是静而无静也;动中有见,则是动而无动也。静中养出端倪,为初学者言之,此个端倪,天之所以与我者,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但其汩没之久,非静养之,则微而不可见,若彼濯濯耳。孟子夜气之所息、平旦之气,须有这般端倪呈露,此即四端之端,由此便可加涵养功夫,所谓知皆所以扩而充之也。若不见此所养者何物,如将水火煮空铛也,俗儒乃以为禅,然则孟子所言亦皆禅欤?
虞史称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盖以其处变而不失其常,尤人所难也。释之者曰:「虽其度量有过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是固然矣。」窃谓圣人之所以大过乎人者,夫岂无自?盖其耕于历山,力行孝弟,一出至诚,是以瞽亦允若,受尧之天下,若固有之处常应变,各适其宜,以其有此具也。如孟子加齐卿相,成霸王之业而不动心,亦自知言养气中来。今人自谓能辩大事、决大议,大率皆气质用事,虽一时建立似有可观,而终非纯王之治,无本故也。儒先有言:「孝弟通乎神明。」又云:「自洒扫应对可到圣人事。」愚亦谓舜处变不失其常,当自其力行孝弟,与夫洒扫应对时求之,而学圣人者亦不外是。请教。
此是知本之论。舜之不迷乃其度量,若以为天地神明之相,则末矣。如易之「震惊百里,不丧亡鬯」亦是如此,只到无我之至便能如此。且如雷炮声之击烈,虽壮夫悍人则反惊惧昏倒,未周婴孩则若不闻者,何也?真纯与不真纯之别也,有我与无我之分也,此自难强,皆涵养所至。
何大通问:「天理者,直指人心之本体而言。以言乎天者,万物皆备之矣,所以大一体之意也。在天曰理,理者,礼而已矣,本其于穆不已,流形万变,天地以是而覆载,日月以是照临,鬼神以是而幽明,人物以是而动静,山河以是而流峙,风云以是而变迁,以至霜露雨旸,无非此理也,圣人之糟粕煨烬,亦无非此教也。是以人曰心,心也者,天理而已矣。尊卑殊分,贵贱殊亲,民物殊爱,一以贯万,万以原一者,抑亦无非此理,无非此教也。曰体认者,只是天理本体上用功,所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千古圣贤只有此一些子不放过,所以立天下大本,重天下之急务。尧告舜曰『精一』、舜告禹曰『执中』,无非精此执此一念而已,是所谓『缉熙敬止』也、『顾諟明命』也、『安汝止』也。曰随处,无在无不在之意也,所以不可须臾离也,所以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颠沛必于是也。颜子三月不违,只是三月随处用功而已,其余则日月至焉,只是日月间随处用功而已。」
「天理」二字乾涉甚大,人不足以名之,无与之对者。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鬼神之吉凶,人物山河、风云雷雨之聚散消息,无非这一个形见,不必言以是也。随处体认说得是,这一个功夫乃自然功夫,与天地合德,与无终食违仁,自造次颠沛必于是,与三月不违,与顾諟明命,与缉熙敬止,与惟精惟一,皆同条共贯。此个条贯,千圣千贤一大头脑,正是作圣功夫。贤能看得破,便可下手,便可起脚向圣人路上行矣。
「必有事焉」,事字是一点真道理,自是勿忘勿助的道理。苟能扩充此一点,便是圣贤的真乐,便是配义与道,所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处,皆是中情达乎人,非为人者。由是观之,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非真无是心也,是自贼其情、自暴其气,为所不为、欲所不欲者也。苟能举此而措诸天下、达诸家国,则天下家国可得而平治,而况父母妻子乎!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先生指点出「天理」头脑,较于「事」字明白简易,通虽不敏,请事斯语。
切须认得所有事者何事?天理即是真道理,真道理即是真心。孟子言乍见孺子入井,怵惕恻隐之心,即是真心。此心是自然之心,勿忘勿助只是做必有事之功夫,此功夫亦是自然功夫,所以能体自然道理。孟子言「充之足保四海」者何谓?盖此本元于天地同体,故云保四海,亦复其本然者耳。其万变万化,亦只是同体中事耳。
有所著于怒便是迁,有所留于过便是贰。怒与过,颜子有所不免;怒不迁、过不贰,斯为几微之妙,谓之真好学。然否?
云「有所著于怒」,是也,著则以已与之。若云「有所留于过」,则非也。过萌于心又发于事,是贰也;若过发于事,即是祗悔,又何待留?
仲尼、颜子乐处,此「乐」字极有意味,本人人皆具此乐,溺于闻见之小,所以失之。此乐是乐于天理流行、充塞宇宙之大,苟能识得此一点意思,虽蔬食饮水、箪食瓢饮,此乐自如;吟风弄月、傍花随柳,此乐自如;鸢鱼活泼、舞雩风咏,皆是此乐之流行动静,天机一点真消息也。
云「此乐是乐于天理」,则不是。盖知天理可乐,即又为天理所累,得此天理则自乐,自不知其所以乐,此与箪瓢陋巷不相乾,与花柳鸢鱼亦不相乾,乐在中,触于外而发耳。
大通初然静坐体认时,觉此心茫然无措,提醒数番,尽将从前所有的声色货利、功名富贵、死生患难的念头全放下,每有意念发作,甚觉是非明白,好恶真诚,了然无滞,易为克治,虽有千头万绪,皆自一念无间、生生变易中来。如此用功,稍觉志气明□心□平顺,其灵昭不昧之体,随时感应虚寂矣,但未识此生还有透脱功夫否?
更无别透脱功夫,于灵昭不昧处便体认得天然自有之理,久则此理渐长,而病根渐消,消尽即是透脱,直达天德。今之灵昭不昧之体亦是一斑然,未为实得也。
王元德问:「欲学在敬,欲敬在一,欲一在审节度,曰『勿忘勿助』、曰『无在无不在』、曰『不离于物而不滞于物』,三句互相发明,所谓自然之度也。寻此一段,颇有凑泊,前此不免时有偏拗而未之定也,今犹未知是否?」
此问比前见得越亲切,紧要在「审节度」一句,此节度是自然之节度。是自然之功夫,便可合自然之本体,可合天然自有之理。人有欲强为之者,不足以合天,不足以合道矣。
程相问:「心外无道,日常真实体认求之,一处是则处处皆是。奈何此心此理仍未凑泊吻合,毋亦病根常在,以致胸中未能摆脱?兹欲先静坐磨炼本体,久之成熟,然后应物,庶功夫易进而有著力,又恐有累孔门之教。」
天理无间动静,理无二故也。动静合一,此是中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然此在学者自家审己量力,若于动时未得力,且先兼在静坐涵养,俟力渐大渐应接亦可,程门元有此教。
韩一芝问:「心事合一功夫,只是要见天理为主。见了天理是我自然的本体,然后可以率性,不然皆是躯壳上起念,虽说无意必固我,谁知纯是一块私意?见天理只是主一为要,不知要则终不得纯熟,而神化之妙不到,是否?」
此问稍亲切,云「见天理只是主一为要」最好。今且莫求天理,只求主一,便自见得。见得天理,便不分心事知行,一齐到了。
方珙问:「归来细玩明训,及答王元德问语,并思先生动静语默,然后知先生精神心思已在是,头脑功夫已在是,至博而约、至简而易,合人己天地万物而一之,日用之间,自不觉有生意流动。」
览子此书,知有开悟。如人行夜路,有一点明处,便急须接续进步,前头更有明处,若不接续,少间忽然迷了前所见路矣。
蔡继成问:「日习似见惺惺,但应物时忽有不知,或被所引,惟一觉便在。成用常觉打成一片,何如?」
常觉便知痛痒,岂可一息不觉?第要知所觉何事,乃精切耳。应物时被引,则恐不应时亦未停当。惟知止乃能有定,有定则动静皆定矣。
又问:「消习心,去成心,亦是要克私意。成谓勿助勿忘,常常中正,习心成心便消去,故为学须得头脑耳。」
勿忘勿助之间,即是的当处。顷刻在此,私意习心成心一切皆了。
或云:「天理何见也?只发生处,见善便存,见恶便去,临时下手,成试之甚不得力。只终日终时,无动无静,勿助勿忘,便自中正,遇事稳当。一有差池,还是功夫有亏,中正之体不存也。」
终日终身,勿忘勿助,一了百了,若临时下手,灭东生西,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辗转缠障,不惟不得力,而又害之。
有云:「学要到脱洒处。」亦是言美在其中,畅于四肢。见舍其中美而调习外形,久假不归,至于惯熟,自以为学。成谓只终日终时存存,本体自然廓清,廓清则富贵贫贱无所与,无与则无累而乐生。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本体存存,廓清洒脱者,由仁义行之学、集义所生之学也。调习外形,久假不归,因以为学,自是自安者,行仁义之学、义袭之学、必信必果之学而不自觉者也。间不容发。
精察本体,实见无在而无不在,虽泯然声臭,而炯然灵觉,终日乾乾乎!此何如?
止说炯然灵觉,亦尚未见真切。夫子所谓「参前倚衡」者何物?颜子所谓「如有所立卓尔」者何物?
圣人言士当志于道,所谓从其大体也;耻恶衣食,人不足与议,所谓从其小体也。一是一非,士与者对作两人,勿作一人看,何如?
恐不然,世间自有此等半上半下的人,一心志于道,一心又耻恶衣恶食,则志非其志,非不可夺之志矣。见道分明,则自与衣食不相乾,所性不存故也。
晦庵居家立朝皆可观,卒不见道,恐是合下手要做孔子,则述作久久,至于玩物丧志,遗其本而不知。故白沙师云:「先令我打叠得洁洁净净,便是要立本。」故曰:「学须见头脑始得。」
未可谓此公不见道。初见延平,即举程子「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语,岂不见得?被延平虑其过高一语转却,谓要见理一不难,须要见分殊。吾尝谓理一分殊本是一体,分殊即在理一之中,故示学诗有云:「万物宇宙间,混沦同一气;充塞与流行,其体实无二。就中有粲然,即一为万理。外此以索万,舍身别求臂。」
吾性原是完完全全天然自有之理,不假一毫人为。故夫子欲人用勿助勿忘自然之功,合自然本体,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岂是人为?皆自然如此。人为[则伪],无为则诚也。
正是如此看。此吾四十年来所得者,乃今信之深也。不做自然功夫,便不合自然道理,道理不自然,即非道矣。非自然道理,即不是圣人路脉,又别是一个路脉,夫子所谓异端也,可不[思哉!]可不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