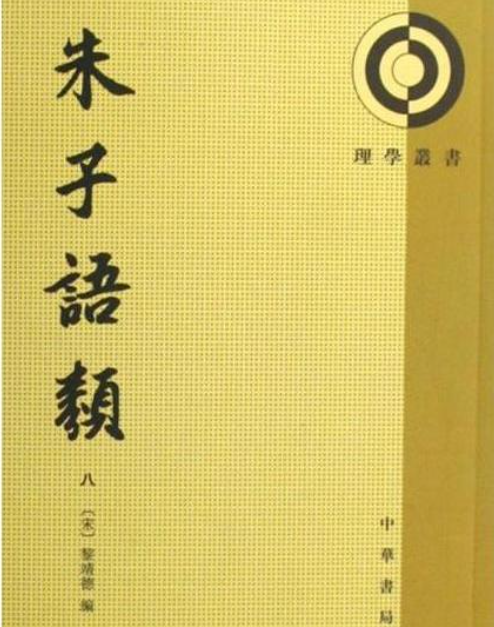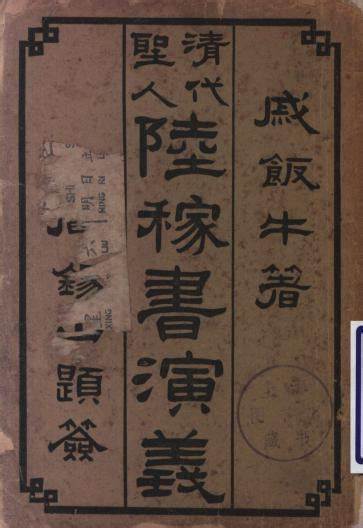论语二
学而篇上
学而时习之章
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余自然易晓。寿昌。
学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有朋自远方来」,在「时习」之后;「而亲仁」,在「入则孝,出则弟」之后;「就有道而正焉」,在「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之后;「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则不威」之后。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专靠师友说话。
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而今人道理在这里,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刘问「学而时习之」。曰:「今且理会个『学』,是学个甚底,然后理会『习』字、『时』字。盖人只有个心,天下之理皆聚于此,此是主张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里得理来!惟学之久,则心与理一,而周流泛应,无不曲当矣。且说为学有多少事,孟子只说『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盖为学之事虽多有头项,而为学之道,则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学习。
书也只是熟读,常记在心头,便得。虽孔子教人,也只是「学而时习之」。若不去时习,则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门弟子编集,把这个作第一件。若能时习,将次自晓得。十分难晓底,也解晓得。
或问:「『学而时习』,不是诗书礼乐。」「固不是诗书礼乐。然无诗书礼乐,亦不得。圣人之学与俗学不同,亦只争这些子。圣贤教人读书,只要知所以为学之道。俗学读书,便只是读书,更不理会为学之道是如何。」
问:注云:『学之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曰:「是如此。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皆学效之事也。」骧。容录云:「人凡有可效处,皆当效之。」
吴知先问『学习』二字。曰:「『学』,是未理会得时,便去学;『习』,是已学了,又去重学。非是学得了,顿放在一处,却又去习也。只是一件事。『如鸟数飞』,只是飞了又飞,所谓『鹰乃学习』是也。」先生因言:「此等处,添入集注中更好。」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
读书、讲论、修饬,皆要时习。
「学而时习之」,虽是讲学、力行平说,然看他文意,讲学意思终较多。观「则以学文」,「虽曰未学」,则可见。
或问「学而时习之」。曰:「学是学别人,行是自家行。习是行未熟,须在此习行之也。」履。
问:「时习,是温寻其义理,抑习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只是学做此一件事,便须习此一件事。且如学『克己复礼』,便须朝朝暮暮习这『克己复礼』。学,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巫、医亦然。」
学习,须是只管在心,常常习。若习得专一,定是脱然通解。
且如今日说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三番思之,便是时习。今学者才说了便休。学蒙。
问:「如何是时习?」曰:「如写一个『上』字,写了一个,又写一个,又写一个。」当时先生亦逐一书此「上」于掌中。
国秀问:「格物、致知是学,诚意、正心是习;学是知,习是行否?」曰:「伊川云:『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这未说到行。知,自有知底学,自有知底习;行,自有行底学,自有行底习。如小儿写字,知得字合恁地写,这是学;便须将心思量安排,这是习。待将笔去写成几个字,这是行底学;今日写一纸,明日写一纸,又明日写一纸,这是行底习。人于知上不习,便要去行,如何得!人于知上不习,非独是知得不分晓,终不能有诸已。」贺孙。
问:「程子二说:一云『时复思绎』,是就知上习;『所学在我』,是就行上习否?」曰:「是如此。」柄。
「浃洽」二字,宜子细看。凡于圣贤言语思量透彻,乃有所得。譬之浸物于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湿,里面依前干燥。必浸之久,则透内皆湿。程子言「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极有深意。先生令诸生同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须以近者譬得分晓乃可。如小子初授读书,是学也。令读百数十遍,是时习也。既熟,则不烦恼,覆背得,此便是说也。书字亦然。或问中云:「学是未知而求知底工夫,习是未能而求能底工夫。」以此推之,意可得矣。」杂说载魏帝「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锺」之令。答者云:「吴人没水自云工,屠儿割肉与称同,伎儿掷绳在虚空。」盖有类三句。陈思王见三人答后,却云:「臣解得是『习』字。」亦善谑矣。皆说习熟之意。先生然之。
「学而时习之」,若伊川之说,则专在思索而无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说,则专于力行而废讲究之义,似皆偏了。
问:「程云:『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看来只就义理处说。后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处说,然后尽时习之意。」曰:「某备两说,某意可见。两段者各只说得一边,寻绎义理与居处皆当习,可也。」后又问:『习,鸟数飞也』,如何是数飞之义?」曰:「此是说文『习』字从『羽』。月令:『鹰乃学习。』只是飞来飞去也。」
问:「『学而时习之』,伊川说『习』字,就思上说;范氏游氏说,都就行上说。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谢氏『坐如尸,立如齐』一段,为习于行。据贺孙看,不思而行,则未必中道;思得惯熟了,却行无不当者。」曰:「伊川意是说习于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会行得!说习于行者,亦不是外于思。思与行亦不可分说。」
「坐如尸,立如齐。」学时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齐」。及做时,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齐,此是习之事也。卓。
上蔡谓:「『坐如尸』,坐时习;『立如齐』,立时习。」只是儱侗说成一个物,恁地习。以见立言最难。某谓,须坐常常照管教如尸,方始是习;立常常照管教如齐,方始是习。逐件中各有一个习,若恁散说,便宽了。
「坐如尸,立如齐」,谢氏说得也疏率。这个须是说坐时常如尸,立时常如齐,便是。今谢氏却只将这两句来儱侗说了。不知这两句里面尚有多少事,逐件各有个习在。立言便也是难。
方叔弟问:「平居时习,而习中每觉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续也。要习,须常令工夫接续则得。」又问寻求古人意思。曰:「某尝谓学者须是信,又须不信。久之,却自寻得个可信底道理,则是真信也。」
「学而时习之」,须是自己时习,然后知心里说处。说。
或问「不亦说乎」。曰:「不但只是学道有说处。今人学写字,初间写不好,到后来一旦写得好时,岂不欢喜!又如人习射,初间都射不中,到后来射得中时,岂不欢喜!大抵学到说时,已是进一进了。只说后,便自住不得。且如人过险处,过不得,得人扶持将纔过得险处了,见一条平坦路,便自欢喜行将去矣。」
问:「集注谓『中心喜悦,其进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诸公将文字熟读,方始经心,方始谓之习。习是常常去习。今人所以或作或辍者,只缘是不曾到说处。若到说处,自住不得。看来夫子只用说『学而时习』一句,下面事自节节可见。」
问:「『有朋自远方来』,莫是为学之验否?」曰:「不必以验言。大抵朋友远来,能相信从,吾既与他共知得这个道理,自是乐也。」或问:「说与乐如何?」曰:「说是自家心里喜说,人却不知;乐则发散于外也。」朋自远方来。
郑齐卿问「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曰:「旧尝有『信从者众,足以验己之有得』。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从,始为可乐。须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从者但一二,亦未能惬吾之意。至于信之从之者众,则岂不可乐!」又曰:「此段工夫专在时习上做。时习而至于说,则自不能已,后面工夫节节自有来。」
问:「『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是乐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乐其信从者众乎?」曰:「乐其信从者众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见,则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广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之,以教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闷!今既信从者自远而至,其众如是,安得不乐!」又云:「紧要在『学而时习之』,到说处自不能已。今人学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说处。到学而不能自已,则久久自有此理。」
问「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曰:「须是自家有这善,方可及人;无这善,如何及得人。看圣人所言,多少宽大气象!常人褊迫,但闻得些善言,写得些文字,便自宝藏之,以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样!今不必说朋来远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写得片文只字而归,人有求者,须当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处。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门而告之。若登门而告之,是往教也,便不可如此。」
问:「『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语初学,将自谋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谓如传得师友些好说话好文字,归与朋友,亦唤做及人。如有好说话,得好文字,紧紧藏在笼箧中,如何得及人。」容。
或问:「『有朋自远方来』,程先生云:『推己之善以及人。』有舜善与人同底意。」曰:「不必如此思量推广添将去,且就此上看。此中学问,大率病根在此,不特近时为然。自彪德美来已如此,盖三十余年矣。向来记得与他说中庸鬼神之事,也须要说此非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羇缠说去,更无了期。只是向高乘虚接渺说了。此正如看屋,不向屋里看其间架如何,好恶如何,堂奥如何,只在外略一绰过,便说更有一个好屋在,又说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又如吃饭,不吃在肚里,却向上家讨一碗来比,下家讨一碗来比,济得甚事!且如读书,直是将一般书子细沈潜去理会。有一看而不晓者,有再看而不晓者,其中亦有再看而可晓者。看得来多,不可晓者自可晓。果是不晓致疑,方问人。今来所问,皆是不曾子细看书,又不曾从头至尾看,只是中间接起一句一字来备礼发问。此皆是应故事来问底,于己何益,将来何用。此最学者大病!」
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乐。」此说是。若杨氏云:「与共讲学」之类,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资人相共讲学,安得「有朋自远方来」!
吴仁父问「非乐不足以语君子」。曰:「惟乐后,方能进这一步。不乐,则何以为君子。」时举云:「说在己,乐有与众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学者在我,故说。人只争这一句。若果能悦,则乐与不愠,自可以次而进矣。」
「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说是中心自喜说,乐便是说之发于外者。说乐。
说是感于外而发于中,乐则充于中而溢于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为学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后真能不要人知尔。若锻炼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里固有时被它动。及到这里,方真个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人不知不愠。
「人不知而不愠」。为善乃是自己当然事,于人何与。譬如吃饭,乃是要得自家饱。我既在家中吃饭了,何必问外人知与不知。盖与人初不相干也。拱寿。
问「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则便有不乐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为之不平,况其不知己乎!此则不知不愠,所以为难。」
尹氏云:「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此等句极好。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
问:「学者稍知为己,则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知不愠者逆而难』?」曰:「人之待己,平平恁地过,亦不觉。若被人做个全不足比数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愠非忿怒之谓。」
或问「不亦乐乎」与「人不知而不愠」。曰:「乐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乐,无私己之怨。」乐、不愠。
有朋自远方来而乐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则乐;人不己知,则不愠。乐愠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
「或问谓朋来讲习之乐为乐。」曰:「不似伊川说得大。盖此个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独晓之,而人晓不得,也自闷人。若『有朋自远方来』,则信向者众,故可乐。若以讲习为乐,则此方有资于彼而后乐,则其为乐也小矣。这个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说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难。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里略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深,养之厚者,不能如此。」义刚录同,见训
圣贤言语平铺地说在那里。如夫子说「学而时习之」,自家是学何事,便须着时习。习之果能说否?「有朋自远方来」,果能乐不乐?今人之学,所以求人知之。不见知,果能不愠否?总论。
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到熟后,自然说否?」曰:「见得渐渐分晓,行得渐渐熟,便说。」又问:「『人不知而不愠』,此是所得深后,外物不足为轻重。学到此方始是成否?」曰:「此事极难。愠,非勃然而怒之谓,只有些小不快活处便是。」正叔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习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愠』处,方是成德。」
吴子常问「学而时习」一章。曰:「学只是要一个习,习到熟后,自然喜说不能自已。今人学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习熟,不见得好。此一句却系切己用功处,下句即因人矣。」又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善,不是自家独有,人皆有之。我习而自得,未能及人,虽说未乐。」
黄问:「学而首章是始、中、终之序否?」曰:「此章须看:如何是『学而时习之』,便『不亦说乎』!如何是『有朋自远方来』,便『不亦乐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愠』,便『不亦君子乎』?里面有许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将三字来包了!若然,则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许多话。向日君举在三山请某人学中讲说此,谓第一节是心与理一,第二节是己与人一,第三节是人与天一,以为奇论。可谓作怪!」黄录详,别出。
问:「学而首章,把作始、中、终之序看时,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说。而今且去看『学而时习之』是如何,『有朋自远方来』是如何。若把始、中、终三个字括了时便是了,更读个甚么!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适间说文子,只是他有这一长,故谥之以『文』,未见其它不好处。今公却恁地去看。这一个字,如何解包得许多意思?大概江西人好拗、人说臭,他须要说香。如告子不如孟子,若只恁地说时,便人与我一般。我须道,告子强似孟子。王介甫尝作一篇兵论,在书院中砚下,是时他已参政。刘贡父见之,值客直入书院,见其文。遂言庶官见执政,不应直入其书院,且出。少顷厅上相见,问刘近作,刘遂将适间之文意换了言语答它。王大不乐,退而碎其纸。盖有两个道此,则是我说不奇,故如此。」因言福州尝有姓林者,解「学而时习」是心与理为一,「有朋自远方来」是己与人为一,「人不知而不愠」是人与天为一。君举大奇之,这有甚好处!要是它们科举之习未除,故说得如此。
问:「横渠解『学而时习之』云:『潜心于学,忽忽为他虑引去者,此气也。』震看得为他虑所引,必是意不诚,心不定,便如此。横渠却以为气,如何?」曰:「人谁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时,也不奈何得。如人担一重担,尽力担到前面,忽担不去。缘何如此?只为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无工夫。」曰:「所以不曾下得工夫,病痛在何处?」曰:「须是有所养。」曰:「所谓养者,『以直养』否?」曰:「未到『以直养』处,且『持其志无暴其气』可也。若我不放纵此气,自然心定。」震又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时,未免难,不知用力久后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义理养之,久而自熟。」震。诸说。
「范说云:『习在己而有得于内,朋友在人而有得于外。』恐此语未稳。」先生问:「如何?」卓云:「得虽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安有内外之别!」曰:「此说大段不是,正与告子义外之说一般。」
再见,因呈所撰论语精义备说。观二章毕,即曰:「大抵看圣贤语言,不须作课程。但平心定气熟看,将来自有得处。今看老兄此书,只是拶成文字,元不求自得。且如『学而时习』一章,诸家说各有长处,亦有短处。如云『「鹰乃学习」之谓』,与『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矣』,此程说最是的当处。如云『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此程说,正得夫子意。如云『学在己,知不知在人』,尹子之言当矣。如游说『宜其令闻广誉施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此最是语病。果如此说,则是君子为人所不知,退而安之于命,付之无可奈何,却如何见得真不愠处出来。且圣人之意尽有高远处,转穷究,转有深义。今作就此书,则遂不复看精义矣。自此隔下了,见识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复见矣。大抵看圣贤语言,须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后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寻罅隙处,游刃以往,而众理自解,芒刃亦不钝。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谓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凿,凿开成痕,所以刃屡钝。如此,如何见得圣贤本意。且前辈讲求非不熟,初学须是自处于无能,遵禀他前辈说话,渐见实处。今一看未见意趣,便争手夺脚,近前争说一分。以某观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说耳,其意直是谓圣贤说有未至,他要说出圣贤一头地。曾不知于自己本无所益。乡令老兄虚心平气看圣人语言,不意今如此支离!大抵中年以后为学,且须爱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细务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来,则无以待之。」
问「学而」一章。曰:「看精义,须看诸先生说『学』字,谁说得好;『时习』字,谁说得好;『说』字,谁说得好。须恁地看。」林扩之问:「多把『习』字作『行』字说,如何?」曰:「看古人说『学』字、『习』字,大意只是讲习,亦不必须是行。」干问:「谢氏、游氏说『习』字,似分晓。」曰:「据正文意,只是讲习。游谢说乃推广『习』字,毕竟也在里面。游氏说得虽好,取正文便较迂曲些。」问:「伊川解『不亦说』作『说在心』,范氏作『说自外至』,似相反。」曰:「这在人自忖度。」干曰:「既是『思绎浃洽于中』,则说必是在内。」曰:「范氏这一句较疏。说自是在心,说便如暗欢喜相似。乐便是个发越通畅底气象。」问:「范氏下面『乐由中出』与伊川『发散在外』之说却同。」曰:「然。」问:「范氏以『不亦说乎』作『比于说,犹未正夫说』,如何?」曰:「不必如此说。」问:「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乎』。如何?」曰:「此也是小可事,也未说到命处。为学之意,本不欲人知。『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问:「谢氏『知我者希』之说如何?」曰:「此老子语也。亦不必如此说。」
萧定夫说:「胡致堂云:『学者何?仁也。』」曰:「『学』字本是无定底字,若止云仁,则渐入无形体去了。所谓『学』者,每事皆当学,便实。如上蔡所谓『「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以此推之,方是学。某到此,见学者都无南轩乡来所说一字,几乎断绝了!盖缘学者都好高,说空,说悟。」定夫又云:「南轩云:『致堂之说未的确。』」曰:「便是南轩主胡五峰而抑致堂。某以为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处。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辨得始得。」震。
「致堂谓『学所以求仁也』。仁是无头面底,若将『学』字来解求仁,则可;若以求仁解『学』字,又没理会了。」直卿云:「若如此说,一部论语,只将『求仁』二字说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轩只说五峰说底是,致堂说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说得好处,或有文定五峰说不到处。」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
问有子言孝悌处。先生谓:「有子言语似有些重复处,然是其诚实践履之言,细咀嚼之,益有味。」
因说陆先生每对人说,有子非后学急务,又云,以其说不合有节目,多不直截。某因谓,是比圣人言语较紧。且如孝弟之人岂尚解犯上,又更作乱!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乱者。圣贤言语宽平,不须如此急迫看。」
陆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说为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起头说得重,却得。『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却说得轻了。」先生曰:「上两句泛说,下两句却说行仁当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谓孝弟为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所谓『亲亲而仁民』也。圣贤言仁不同。此是说『为仁』,若『巧言令色,鲜矣仁』,却是近里说。」因言有子说数段话,都说得反复曲折,惟「盍彻」一段说得直截耳。想是一个重厚和易底人,当时弟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没后,「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
「其为人也孝弟」,此说资质好底人,其心和顺柔逊,必不好犯上,仁便从此生。鲜,是少,对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势如此。若「巧言令色,鲜矣仁」,鲜字则是绝无。「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此两句泛说凡事是如此,与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应上文也,故集注着个「大凡」也。
或说:「世间孝弟底人,发于他事,无不和顺。」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这道理中间断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来,所以说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间又有一种孝慈人,却无刚断。」曰:「人有几多般,此属气禀。如唐明皇为人,于父子夫妇君臣分上煞无状,却终始爱兄弟不衰,只缘宁王让他位,所以如此。这一节感动,终始友爱不衰。或谓明皇因宁王而后能如此,这也是他里面有这道理,方始感发得出来。若其中元无此理,如何会感发得!」
问:「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长者』之类?」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乱,到得『作乱』,则为争斗悖逆之事矣!」问:「人子之谏父母,或贻父母之怒,此不为干犯否?」曰:「此是孝里面事,安得为犯?然谏又自『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亦非凌犯也。」又问:「谏争于君,如『君事有犯无隐』,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说得轻。如君有不是,须直与他说,此之谓『犯』。但人臣之谏君,亦有个宛转底道理。若暴扬其恶,言语不逊,叫唤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当熟谏。』」
问:「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于『作乱』?可见其益远孝弟之所为。」曰:「只言其无此事。论来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处乃为犯也。若作乱,谓之『未之有也』,绝无可知。」
「犯上者鲜矣」,是对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浅深。若「鲜矣仁」,则是专言。这非只是少,直是无了!但圣人言得慢耳。
「犯上者鲜矣」之「鲜」,与「鲜矣仁」之「鲜」不同。「鲜矣仁」是绝无了。「好犯上者鲜」,则犹有在;下面「未之有也」,方是都无。
问:「『君子务本』,注云:『凡事专用力于根本。』如此,则『孝弟为仁之本』,乃是举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说孝弟,上面『务本』,是且引来。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来说。」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较亲切。『于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便是本。」
问:「合当说『本立而末生』,有子何故却说『本立而道生』?」曰:「本立则道随事而生,如『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
问「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渐渐和于一家,以至亲戚,以至故旧,渐渐通透。」
孝弟固具于仁。以其先发,故是行仁之本。以下孝弟仁之本。
子上说:「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须如此说,只平稳就事上观。有子言其为人孝弟,则必须柔恭;柔恭,则必无犯上作乱之事。是以君子专致力于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盖能孝弟了,便须从此推去,故能爱人利物也。」昔人有问:「孝弟为仁之本,不知义礼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义礼智之本皆在此:使其事亲从兄得宜者,行义之本也;事亲从兄有节文者,行礼之本也;知事亲从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舍孝弟则无以本之矣。」可学录别出。
问:「孝弟是良心之发见,因其良心之发见,为仁甚易。」曰:「此说固好,但无执着。观此文意,只是云其为人孝弟,则和逊温柔,必能齐家,则推之可以仁民。务者,朝夕为此,且把这一个作一把头处。」
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曰:「这个仁,是爱底意思。行爱自孝弟始。」又曰:「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亲亲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知得事亲不可不孝,事长不可不弟,是为义之本;知事亲事长之节文,为礼之本;知事亲事长,为智之本。」张仁叟问:「义亦可为心之德?」曰:「义不可为心之德。仁是专德,便是难说,某也只说到这里。」又曰:「行仁之事。」又曰:「此『仁』字是偏言底,不是专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
胡兄说:「尝见世间孝弟底人,少间发出来,于他事无不和顺,慈爱处自有次第道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这个道理中间跌断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来了,所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问:「『孝弟为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尽道,乃立得个根本,则推而仁民爱物,方行得有条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当底事,不是要仁民爱物方从孝弟做去。」可学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叶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则枝叶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叶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南升。
陈敬之说「孝弟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细看,全未与说。数日后,方作一图示之:中写「仁」字,外一重写「孝弟」字,又外一重写「仁民爱物」字。谓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亲亲长长,而后次第推去,非若兼爱之无分别也。
问「孝弟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发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己复礼为仁』之『仁』,故伊川谓之『行仁』。学者之为仁,只一念相应便是仁。然也只是这一个道理。『为仁之本』,就事上说;『克己复礼』,就心上说。」又论「本」字云:「此便只是大学『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虽贵乎一视同仁,然不自亲始,也不得。」
问:「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尽仁,何故?莫是志不立?」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谓『由之而不知,习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过,却昏了。」又问:「伊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谓用,莫是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发见于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仁,后有是孝弟。」
直卿说「孝弟为仁之本」,云:「孔门以求仁为先,学者须是先理会得一个『心』字。上古圣贤,自尧舜以来,便是说『人心道心』。集注所谓『心之德,爱之理』,须理会得是个甚底物,学问方始有安顿处。」先生曰:「仁义礼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炉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时,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昼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万叶,千条万绪,都是这四者做出来。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许多般样。且如仁主于爱,便有爱亲,爱故旧,爱朋友底许多般道理。义主于敬,如贵贵,则自敬君而下,以至『与上大夫、下大夫言』许多般;如尊贤,便有『师之者,友之者』许多般。礼智亦然。但是爱亲爱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无本。如水之流,必过第一池,然后过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过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为义礼智亦必以此为本也。」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爱物则三坎也。
问:「『孝弟为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之意?」曰:「然。」
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专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关。说着偏言底,专言底便在里面;说专言底,则偏言底便在里面。虽是相关,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从爱上说。如云『恻隐之心仁之端』,正是此类。至于说『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其言也讱』,『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说专言之仁,又自不同。然虽说专言之仁,所谓偏言之仁亦在里面。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此便是都相关说,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
问「孝弟为仁之本」。曰:「论仁,则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则当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以此观之,岂特孝弟为仁之本?四端皆本于孝弟而后见也。然四端又在学者子细省察。」
问:「有子以『孝弟为仁之本』,是孝弟皆由于仁矣。孟子却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却以弟属义,何也?」曰:「孝于父母,更无商量。」
「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爱是情,情则发于用。性者指其未发,故曰「仁者爱之理」。情即已发,故曰「爱者仁之用」。集注。爱之理。
「仁者爱之理」,理是根,爱是苗。仁之爱,如糖之甜,醋之酸,爱是那滋味。
仁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佐。
仁是未发,爱是已发。
仁父问「仁者爱之理」。曰:「这一句,只将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则是情。恻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用。」又曰:「『爱之理』,爱自仁出也。然亦不可离了爱去说仁。」问韩愈「博爱之谓仁」。曰:「是指情为性了。」问:「周子说『爱曰仁』,与博爱之说如何?」曰:「『爱曰仁』,犹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就爱处指出仁。若『博爱之谓仁』,之谓,便是把博爱做仁了,终不同。」问:「张无垢说:『仁者,觉也。』」曰:「觉是智,以觉为仁,则是以智为仁。觉也是仁里面物事,只是便把做仁不得。」
说「仁者,爱之理」,曰:「仁自是个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较和柔;及至夏间长茂,方始稍坚硬;秋则收结成实,冬则敛藏。然四时生气无不该贯。如程子说生意处,非是说以生意为仁,只是说生物皆能发动,死物则都不能。譬如谷种,蒸杀则不能生也。」又曰:「以谷种譬之,一粒谷,春则发生,夏则成苗,秋则结实,冬则收藏,生意依旧包在里面。每个谷子里,有一个生意藏在里面,种而后生也。仁义礼智亦然。」又曰:「仁与礼,自是有个发生底意思;义与智,自是有个收敛底意思。」
「爱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
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后,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未发而言仁,可以包义礼智;既发而言恻隐,可以包恭敬、辞逊、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恻隐方是从仁里面发出来底端。程子曰:「因其恻隐,知其有仁。」因其外面发出来底,便知是性在里面。
问:「先生前日以『为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爱之理。以节观之,似是仁之事,非爱之理。」曰:「亲亲、仁民、爱物,是做这爱之理。」又问:「节常以『专言则包四者』推之,于体上推不去,于用上则推得去。如无春,则无夏、秋、冬。至于体,则有时合下齐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难说。」又曰:「用是恁地时,体亦是恁地。」问:「直卿已前说:『仁义礼智皆是仁,仁是仁中之切要底。』此说如何?」曰:「全谓之仁亦可。只是偏言底是仁之本位。」
问:「『仁者心之德』,义礼智亦可为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专此心之德。」心之德。
知觉便是心之德。
仁只是爱底道理,此所以为「心之德」。爱之理,心之德。
问「心之德,爱之理」。曰:「爱是个动物事,理是个静物事。」
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根。
「心之德」是统言,「爱之理」是就仁义礼智上分说。如义便是宜之理,礼便是别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会得爱之理,便理会得心之德。又曰:「爱虽是情,爱之理是仁也。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爱之理」,只是就仁体段说。其发为爱,其理则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这些生意流行。
「其为人也孝弟」章,「心之德,爱之理」。戴云:「『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弟为主。仁义礼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某寻常与朋友说,仁为孝弟之本,义礼智亦然。义只是知事亲如此孝,事长如此弟,礼亦是有事亲事长之礼,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为心之德,则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专言则包四者』是也;『爱之理』,如所谓『偏言则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动处便见。有感而动时,皆自仁中发出来。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圆池,池虽不同,皆由水而为之也。」
「爱之理」,是「偏言则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则四者皆心之德,而仁为之主;分而言之,则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
以「心之德」而专言之,则未发是体,已发是用;以「爱之理」而偏言之,则仁便是体,恻隐是用。
问:「『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圣贤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圣贤言仁,有就『心之德』说者,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之类;有就『爱之理』说者,如『孝弟为仁之本』之类。」
杨问:「『仁者,爱之理。』看孔门答问仁多矣,如克己等类,『爱』字恐未足以尽之。」曰:「必着许多,所以全得那爱,所以能爱。如『克己复礼』,如『居处恭,执事敬』,这处岂便是仁?所以唤醒那仁。这里须醒觉,若私欲昏蔽,这里便死了,没这仁了。」又问:「『心之德』,义礼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专言『心之德』,所统又大。」安卿问:「『心之德』,以专言;『爱之理』,以偏言。」曰:「固是。『爱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别有个『爱之理』。偏言、专言,亦不是两个仁。小处也只在大里面。」淳录云:「仁只是一个仁,不是有一个大底仁,其中又有一个小底仁。尝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带福建路安抚使。以安抚使言之,则统一路州军;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较大耳。然太守即是这安抚使,随地施用而见。」
或问「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曰:「『爱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气上看。如春夏秋冬,须看他四时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时。四时之气,温叙寒热,叙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气之长,秋是生气之敛,冬是生气之藏。若春无生物之意,后面三时都无了。此仁所以包得义礼智也,明道所以言义礼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抚使,更无一个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抚也。今学者须是先自讲明得一个仁,若理会得后,在心术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见得此仁,则心术上言仁与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学者『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须常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
「『仁者爱之理』,是将仁来分作四段看。仁便是『爱之理』,至于爱人爱物,皆是此理。义便是宜之理,礼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别是非之理。理不可见,因其爱与宜,恭敬与是非,而知有仁义礼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谓『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处,所谓『保合太和』是也。仁是个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尝不仁,只是为私欲所昏,才『克己复礼』,仁依旧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别有个私欲,只心之偏处便是。」汪正甫问:「三仕三已不为仁,管仲又却称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独自底,管仲出来,毕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个人坐亡立化,有一个人仗节死义。毕竟还仗节死义底是。坐亡立化,济得甚事!」。●亚夫问「杀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毕竟是心不安。理当死,即得杀身,身虽死,而理即在。」亚夫云:「要将言仁处类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赶缚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会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会一段,觉见得意思转好。」南升。
或问「仁者心之德。」曰:「义礼智,皆心之所有,仁则浑然。分而言之,仁主乎爱;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问:「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辞逊;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恶;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乌能辞逊、羞恶、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于夏之长,则是生者长;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斩断其根,则生者丧矣,其谷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丧,须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种之,又复有生。诸子问仁不同,而今曰『爱之理』云者,『克己复礼』,亦只要存得此爱,非以『克己复礼』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贤者』,亦只是要见得此爱。其余皆然。」
问「爱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缘里面有这爱之理,所以发出来无不爱。程子曰:『心如谷种,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爱之理』也。尝譬如一个物有四面:一面青,一面红,一面白,一面黑。青属东方,则仁也;红属南方,礼也;白属西方,义也;黑属北方,智也。然这个物生时,却从东方左边生起。故寅卯辰属东方,便是这仁,万物得这生气方生。及至巳午未,南方,万物盛大,便是这生气已充满。及申酉戌,西方,则物又只有许多限量,生满了,更生不去,故生气到此自是收敛。若更生去,则无收杀了。又至亥子丑,北方,生气都收藏。然虽是收敛,早是又在里面发动了,故圣人说『复见天地之心』,可见生气之不息也。所以仁贯四端,只如此看便见。」
问:「浑然无私,便是『爱之理』;行仁而有得于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释文义亦可,但恐本领上未透彻尔。」少顷,问濂溪中正仁义之说。先生遽曰:「义理才觉有疑,便札定脚步,且与究竟到底。谓如说仁,便要见得仁是甚物。如义,如智,如礼,亦然。识得道理一一分晓,了然如在目中,则自然浃洽融会,形之言语自别。若只仿像测度,才说不通,便走作向别处去,是终不能贯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处,且子细玩索。」谟退而讲曰:「一性禀于天,而万善皆具,仁义礼智,所以分统万善而合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动』,此理完然,是为性之本体。及因事感发而见于中节之时,则一事所形,一理随着。一理之当,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见于事亲从兄之际,莫非仁之发也。有子谓孝弟行仁之本,说者于是以爱言仁,而爱不足以尽之;以心喻仁,而心实宰之。必曰『仁者爱之理』,然后仁之体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后仁之用显。学者识是『爱之理』,而后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说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续处,便是见得未亲切。」曰:「莫是不合分体、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个心,便自具了仁之体、用。喜怒哀乐未发处是体,发于恻隐处,便却是情。」因举天地万物同体之意极问其理。曰:「须是近里着身推究,未干天地万物事也。须知所谓『心之德』者,即程先生谷种之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只以此意推之,不须外边添入道理。若于此处认得『仁』字,即不妨与天地万物同体。若不会得,便将天地万物同体为仁,却转无交涉矣。孔门之教说许多仁,却未曾正定说出。盖此理直是难言,若立下一个定说,便该括不尽。且只于自家身分上体究,久之自然通达。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须是统看仁如何却包得数者;又却分看义礼智信如何亦谓之仁。大抵于仁上见得尽。须知发于刚果处亦是仁,发于辞逊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识尽全体。正犹观山所谓『横看成岭,直看成峰』,若自家见他不尽,初谓只是一岭,及少时又见一峰出来,便是未曾尽见全山,到底无定据也。此是学者紧切用功处,宜加意焉。」此一条,中间初未看得分明,后复以书请问,故发明紧切处兼载书中之语。
问:「『爱之理』实具于心,『心之德』发而为爱否?」曰:「解释文义则可,实下功夫当如何?」曰:「据其已发之爱,则知其为『心之德』;指其未发之仁,则知其为『爱之理』。」曰:「某记少时与人讲论此等道理,见得未真,又不敢断定,触处间又自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须是就自己实做工夫处,分明见得这个道理,意味自别。如『克己复礼』则如何为仁?『居处恭,执事敬』,与『出门如见大宾』之类,亦然。『克己复礼』本非仁,却须从『克己复礼』中寻究仁在何处,亲切贴身体验出来,不须向外处求。」谟曰:「平居持养,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发见,无非爱而已。」曰:「此语近之。正如疏导沟渠,初为物所壅蔽,才疏导得通,则水自流行。『克己复礼』,便是疏导意思;流行处,便是仁。」
先生尝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论孟中有专就『心之德』上说者,如『克己复礼』,『承祭、见宾』,与答樊迟『居处恭』,『仁人心也』之类。有就『爱之理』上说者,如『孝弟为仁之本』,与『爱人』,『恻隐之心』之类。」过续与朋友讲此,因曰:「就人心之德说者,有是『心之德』。」陈廉夫云:「如此转语方得。」先生尝说:「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蔡季通曰:「如『雍也可使南面』,是也。」先生极然之。杨至之尝疑先生「君子而时中」解处,恐不必说「而又」字,先生曰:「只是未理会此意。」过曰:「正如程子易传云『正不必中,中重于正』之意。」曰:「固是。既君子,又须时中;彼既小人矣,又无忌惮。」先生语辅汉卿曰:「所看文字,于理会得底更去看,又好。」
「孝弟为仁之本」注中,程子所说三段,须要看得分晓。仁就性上说,孝弟就事上说。」集注。程子说。
孝弟如何谓之顺德?且如义之羞恶,羞恶则有违逆处。惟孝弟则皆是顺。
伊川说:「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此言最切,须子细看,方知得是解经密察处。非若今人自看得不子细,只见于我意不合,便胡骂古人也。
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发出来底。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如亲亲,仁民,爱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须先从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所载「程子曰」两段,分晓可观。语录所载他说,却未须看。如语录所载,「尽得孝弟便是仁」,此一段最难晓,不知何故如此说。
「『为仁以孝弟为本』,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是皆发于心德之自然,故『论性以仁为孝弟之本』。『为仁以孝弟为本』,这个『仁』字,是指其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为孝弟之本』,这个『仁』字,是指其本体发动处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里发出,首先是发出为爱。爱莫切于爱亲,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于他,皆从这里出。如水相似,爱是个源头,渐渐流出。」
问:「孝根原是从仁来。仁者,爱也。爱莫大于爱亲,于是乎有孝之名。既曰孝,则又当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于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故孝不特是承顺养志为孝,又当保其所受之身体,全其所受之德性,无忝乎父母所生,始得。所以『为人子止于孝』。」曰:「凡论道理,须是论到极处。」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个仁,爱念动出来便是孝。程子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曷尝有孝弟来。』譬如一粒粟,生出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干,有枝叶,亲亲是根,仁民是干,爱物是枝叶,便是行仁以孝弟为本。」
「『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刘安节记,最全备。」问:「把孝弟唤做仁之本,却是把枝叶做本根。」曰:「然。」
「由孝弟可以至仁」,则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一事也。如仁之发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个全体,孝弟却是用。凡爱处皆属仁。爱之发,必先自亲亲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行仁之事也。
问:「『孝弟为仁之本。』或人之问:『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谓『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曰:「如何看此不子细!程先生所答,煞分晓。据或人之问,仁不在孝弟之中,乃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阳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说在孝弟之中,只一个物事。如公所说程子之意,孝弟与仁却是两个物事,岂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么做仁!前日戏与赵子钦说,须画一个圈子,就中更画大小次第作圈。中间圈子写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写『仁义礼智』四字。『仁』之下写『恻隐』,『恻隐』下写『事亲』,『事亲』下写『仁民』,『仁民』下写『爱物』。『义』下写『羞恶』,『羞恶』下写『从兄』,『从兄』下写『尊贤』,『尊贤』下写『贵贵』。于『礼』下写『辞逊』,『辞逊』下写『节文』。『智』下写『是非』,『是非』下写『辨别』。」直卿又谓:「但将仁作仁爱看,便可见。程子说『仁主于爱』,此语最切。」曰:「要从里面说出来。仁是性,发出来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爱物,只是这个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从里面行将去,这只是一个物事。今人看道理,多要说做里面去,不要说从外面来,不可晓。深处还他深,浅处还他浅。」
「行仁自孝弟始。」盖仁自事亲、从兄,以至亲亲、仁民,仁民、爱物,无非仁。然初自事亲、从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遍天下。只见孺子入井,这里便有恻隐欲救之心,只恁地做将去。故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只是就这里当爱者便爱。
问节:「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当爱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发得孝弟出来,无仁则何处得孝弟!」先生应。次日问曰:「先生以节言所以当爱底不是,未达。」曰:「『当』字不是。」又曰:「未说着爱在。他会爱,如目能视,虽瞑目不动,他却能视。仁非爱,他却能爱。」又曰:「爱非仁,爱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举程子说云:「『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何尝有孝弟来!』说得甚险。自未知者观之,其说亦异矣。然百行各有所属,孝弟是属于仁者也。」因问仁包四者之义。曰:「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遂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仁便有个动而善之意。如动而有礼,凡其辞逊皆礼也;然动而礼之善者,则仁也。曰义,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爱、恭敬、果毅、知觉之属,则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也。然王畿之内是王者所居,大而诸路,王畿之所辖也;小而州县市镇,又诸路之所辖也。若王者而居州镇,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见于事。「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曷尝有孝弟!」见于爱亲,便唤做孝;见于事兄,便唤做弟。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仁。性中何尝有许多般,只有个仁。自亲亲至于爱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行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则义为羞恶之本,礼为恭敬之本,智为是非之本。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都无许多般样,见于事,自有许多般样。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发见者。孝弟即仁之属,但方其未发,则此心所存只是有爱之理而已,未有所谓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来!」
问:「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既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理?」曰:「且如父有争子,一不中理,则不能承意,遂至于犯上。」问:「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为仁之本』,如何?」曰:「此是不忘其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来说。其它『爱』字,皆推向外去;此个『爱』字,便推向里来。玩味此语尽好。」问:「或人问伊川曰:『「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何。」曰:「仁不可言仁者,义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则可以言又不是孝弟在这里,仁在那里,便由孝弟以至仁,无此理。如所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圣,却是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说道:『尽得仁,斯尽得孝弟;尽得孝弟,便是仁。』又曰:『孝弟,仁之一事。』」问:「曰仁是义理之言,盖以仁是自家元本有底否?」曰:「固是。但行之亦有次序,所以莫先于孝弟。」问:「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如所谓『干卦』相似。卦自有乾坤之类,性与心便有仁义礼智,却不是把性与心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孝弟者,性之用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皆情也。」问:「伊川何以谓『仁是性』?孟子何以谓『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说得亲切,莫如就『心』字说。心者,兼体、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恻隐是情。』若孟子,便只说心。程子是分别体、用而言;孟子是兼体、用而言。」问:「伊川曰『仁主乎爱』,爱便是仁否?」曰:「『仁主乎爱』者,仁发出来便做那慈爱底事。某尝说『仁主乎爱』,仁须用『爱』字说,被诸友四面攻道不是。吕伯恭亦云:『说得来太易了。』爱与恻隐,本是仁底事。仁本不难见,缘诸儒说得来浅近了,故二先生便说道,仁不是如此说。后人又却说得来高远没理会了。」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阴阳刚柔,元亨利贞。以气言,则春夏秋冬;以德言,则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是个坯朴里便有这底。天下未尝有性外之物。仁则为慈爱之类;义则为刚断之类;礼则为谦逊;智则为明辨;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问:「如何不道『鲜矣义礼智』,只道『鲜矣仁』?」曰:「程先生易传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专言则包四者,偏言之则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义也在里面;『知觉谓之仁』,便智也在里面。如『孝弟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爱而言。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纔有私欲,则义礼智都是私,爱也是私爱。譬如一路数州,必有一帅,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帅;自一州而言,只是一州之事。然而帅府之属县,便较易治。若要治属郡之县,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爱而言。」又曰:「仁义礼智共把来看,便见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处住,看了三个,则那一个定是仁。不看那三个,只去求一个,如何讨得着!」又曰:「『仁主乎爱』,如灯有光。若把光做灯,又不得。谢氏说曰:『若不知仁,则只知「克己复礼」而已。』岂有知『克己复礼』而不知仁者!谢氏这话都不甚稳。」问:「知觉是仁否?」曰:「仁然后有知觉。」问:「知觉可以求仁否?」曰:「不可。」问:「谢氏曰『试察吾事亲从兄之时,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则知仁』,何也?」曰:「便是这些话心烦人,二先生却不如此说。」问:「谢氏曰:『人心之不伪者,莫如事亲、从兄。』如何?」曰:「人心本无伪,如何只道事亲从兄是不伪?」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诚心否?」曰:「也不然。人心那个是不诚底?皆是诚。如四端不言信,盖四端皆是诚实底。」问:「四肢痿痹为不仁,莫把四肢喻万物否?」曰:「不特喻万物,他有数处说,有喻万物底,有只是顷刻不相应,便是不仁。如病风人一肢不仁,两肢不仁,为其不省悟也。似此等语,被上蔡说,便似忒过了。他专把省察做事。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省,看这事合恁地,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诸公说道去那上面察探。要见这道理,道理自在那里,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如上蔡说仁,曰:『试察吾事亲、从兄时,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剩了。仁者便有所知觉,不仁者便无所知觉,恁地却说得。若曰『心有知觉之谓仁』,却不得。『仁』字最难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里,夫子却不曾说,只是教人非礼勿视听言动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便是说得仁前面话;『仁者其言也讱』,『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乐山』之类,便是说得仁后面话。只是这中间便着理会仁之体。仁义礼智,只把元亨利贞,春夏秋冬看,便见。知觉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贞』字。而智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循环处。若无这智,便起这仁不得。」问:「先生作克己斋铭有曰:『求之于机警危迫之际。』想正为此设。」曰:「后来也改却,不欲说到那里。然而他说仁,说知觉,分明是说禅。」又曰:「如湖南五峰多说『人要识心』。心自是个识底,却又把甚底去识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见物,却如何见得眼!故学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药以治眼,然后眼明。他而今便把孟子爱牛入井做主说。却不知孟子他此说,盖为有那一般极愚昧底人,便着恁地向他说道是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说。诸公于此,便要等候探知这心,却恐不如此。」集义。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满体是仁。内自一念之微,以至万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说孝弟非仁,不知何从得来。上蔡之意,盖谓别有一物是仁。如此,则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则知仁矣。』此语好。」曰:「圣门只说为仁,不说知仁。或录云「上蔡说仁,只从知觉上说,不就为仁处说。圣人分明说『克己复礼为仁』,不曾说知觉底意。上蔡一变」云云。盖卿录云「孔门只说为仁,上蔡却说知仁。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上蔡一转」云云。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张子韶出来,尽冲突了。盖卿录云:「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近年陆子静又冲突出张子韶之上。」盖卿录云:「子韶所不敢冲突者,子静尽冲突。」
问:「『孝弟是行仁之本』,则上面『生』字恐着不得否?」曰:「亦是仁民爱物,都从亲亲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爱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头事,从这里做起。」问:「『为仁』,只是推行仁爱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爱以及物,不是就这上求仁。如谢氏说『就良心生来』,便是求仁。程子说,初看未晓,似闷人;看熟了,真扑不破!」
问「孝弟为仁之本」。曰:「上蔡谓:『事亲、从兄时,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盖为仁,便是要做这一件事,从孝弟上做将去。曰『就事亲从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来,要知个仁而已,不是要为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觉为仁。但以觉为仁,只将针来刺股上,才觉得痛,亦可谓之仁矣。此大不然也!」
巧言令色鲜矣仁章
或问「巧言令色,鲜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录云:「他自使去了此心在外,如何得仁。」不是别更有仁。」
「巧言令色,鲜矣仁!」只争一个为己、为人。且如「动容貌,正颜色」,是合当如此,何害于事。若做这模样务以悦人,则不可。
或以巧言为言不诚。曰:「据某所见,巧言即所谓花言巧语。如今世举子弄笔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这般模样时,其心还在腔子里否?」
问:「『巧言令色,鲜矣仁!』记言『辞欲巧』,诗言『令仪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当如此。记言『辞欲巧』,非是要人机巧,盖欲其辞之委曲耳。如语言:『夫子为卫君乎?』答曰:『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之类是也。诗人所谓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仪令色。』此德之形于外者如此,与『鲜矣仁』者不干事。」
问:「巧言令色是诈伪否?」曰:「诸家之说,都无诈伪意思。但驰心于外,便是不仁。若至诚巧令,尤远于仁矣!」
「巧言令色,鲜矣仁!」圣人说得直截。专言鲜,则绝无可知,是辞不迫切,有含容之意。若云鲜矣仁者,犹有些在,则失圣人之意矣。
问:「『鲜矣仁』,集注以为绝无仁,恐未至绝无处否?」曰:「人多解作尚有些个仁,便粘滞,咬不断了。子细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于外,大体是无仁了。纵有些个仁,亦成甚么!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为非仁。『绝无』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
问:「『鲜矣仁』,先生云『绝无』,何也?」曰:「只是心在时,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则心便不在,安得谓之仁!『颜子三月不违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谓之非仁,则绝无可知。」南升。
问:「『鲜矣仁』,程子却说非仁,何也?」曰:「『鲜』字若对上面说,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鲜』,这便是少。若只单说,便是无了。巧言令色,又去那里讨仁!」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虽未是大段奸恶底人,然心已务外,只求人悦,便到恶处亦不难。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此说极尽。若能反观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务外,便自可。与前章「程子曰」两条若理会得,则论语一书,凡论仁处皆可通矣。论语首章载时习,便列两章说仁次之,其意深矣!
问:「『鲜矣仁』章,诸先生说都似迂曲,不知何说为正?」曰:「便是这一章都生受。惟杨氏后说近之,然不似程说好,更子细玩味。」问:「游氏说『诚』字,如何?」曰:「他却说成『巧言令色鲜矣诚』,不是『鲜矣仁』。说仁,须到那仁处,便安排一个『仁』字安顿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则三四字亦得。又须把前后说来相参,子细玩味,看道理贯通与不贯通,便见得。如洙泗言仁一书,却只总来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来相参,自然见得。」先生因问曰:「曾理会得伊川曰『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否?」干曰:「有这性,便有这仁。仁发出来,方做孝弟。」曰:「但把这底看『巧言令色鲜矣仁』,便见得。且如巧言令色人,尽是私欲,许多有底,便都不见了。私欲之害,岂特是仁,和义礼智都不见了。」问:「何以不曰『鲜矣义礼智』,而只曰『鲜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则主一事;专言之,则包四者。』」先生又曰:「仁与不仁,只就向外向里看,便见得。且如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于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问:「谢氏说如何?」曰:「谢氏此一段如乱丝,须逐一剔拨得言语异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须见得有个总会处。且如『辞欲巧』,便与『逊以出之』一般。『逞颜色』与仲山甫之『令仪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恶讦以为直』,也是个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厉而内荏』,又是令色之尤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