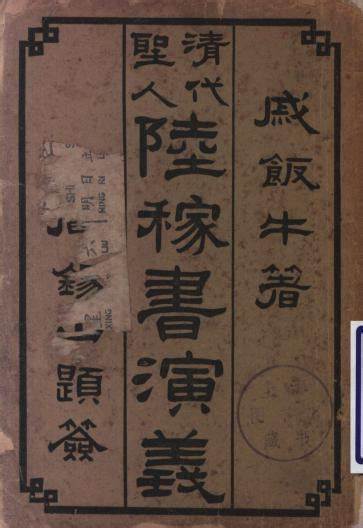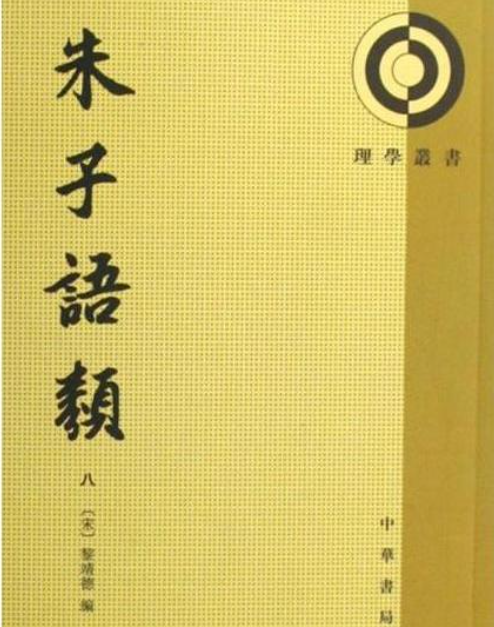朱子六
论取士
古人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猎,皆只是一项事,皆一理也。
召穆公始谏厉王不听,而退居于郊。及厉王出奔,国人欲杀其子,召公匿之。国人围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厉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叹曰:「便是这话难说!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意交结素深,与国家共休戚,故患难相为如此。后世相遇如涂人,及有患难,则涣然离散而已。然今之公卿子孙,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孙莫不骄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进之士,举而加之公卿之位,以为苟胜于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义理,故胜之耳。若更不知义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国子,其法至详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熏陶渐染,而不失为寡过之人,岂若今之骄騃淫奢也哉!陈同父课稾中有一段论此,稍佳。」
窦问:「人才须教养。明道章疏须先择学官,如何?」曰:「便是未有善择底人。某尝谓,天下事不是从中做起,须得结子头是当,然后从上梳理下来,方见次序。」德明问:「闻先生尝言,州县学且依旧课试,太学当专养行义之士。」曰:「却如此不得。士自四方远来太学,无缘尽知其来历,须是从乡举。」
「吕与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经,曰政事,曰文学。德行则待州县举荐,下三科却许人投牒自试。明经里面分许多项目:如春秋则兼通三传,礼则通三礼,乐则尽通诸经所说乐处。某看来,乐处说也未尽。政事则如试法律等及行移决判事。又定为试辟,未试则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则令所属长官举辟。」远器云:「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这却法意详尽。如今科举,直是法先不是了。今来欲教吏部与二三郎官尽识得天下官之贤否,定是了不得这事!」
因论学校,曰:「凡事须有规模。且如太学,亦当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绳墨,迟之十年,日与之磨炼,方可。今日学官只是计资考迁用,又学识短浅,学者亦不尊尚。」可学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学亦盛。」曰:「吕氏家塾记云,未立三舍前,太学只是一大书会,当时有孙明复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趋慕!」
林择之曰:「今士人所聚多处,风俗便不好。故太学不如州学,州学不如县学,县学不如乡学。」曰:「太学真个无益,于国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见陈魏公说,亦以为可罢。」
祖宗时,科举法疏阔。张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应举。乖崖去寻得李畋出来举送去。如士人要应举时,只是着布衫麻鞋,陈状称,百姓某人,今闻朝廷取士如何如何,来应举;连投所业。太守略看所业,方请就客位,换襕[巾璞-王]相见,方得请试。只一二人,试讫举送。旧亦不糊名,仁宗时方糊名。
「商鞅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废了耕战。此无道之言。然以今观之,士人千人万人,不知理会甚事,真所谓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真是可忧!」因云云云。「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是四五千人,今多一倍。」因论吕与叔论得取士好。因论其集上代人章表之类,文字多难看,此文集之弊。扬因谓:「去了此等好。」曰:「然。」因叹:「与叔甚高,可惜死早!使其得六十左右,直可观,可惜善人无福!兄弟都有立。一兄和叔,做乡仪者,更直截,死早。」
康节谓:「天下治,则人上行;天下乱,则人上文。」太祖时,人都不理会文;仁宗时,人会说。今又不会说,只是胡说。因见时文义,甚是使人伤心!
因说「子张学干禄」,曰:「如今时文,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皆是吏人做上去。学官只是备员考试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艺可为表率,仁义礼智,从头不识到尾!国家元初取人如此,为之柰何!」
三舍人做干元统天义,说干元处云「如目之有视,耳之有听,体之有气,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无这般时文。
今人作经义,正是醉人说话。只是许多说话改头换面,说了又说,不成文字!
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方试官命此题,已欲其立奇说矣。又,出题目定不肯依经文成片段,都是断章牵合,是甚么义理!三十年前人犹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试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三句,后遂成例。当时人甚骇之,今遂以为常矣。遂使后生辈违背经旨,争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长浮竞薄,终将若何,可虑!可虑!王介甫三经义固非圣人意,然犹使学者知所统一。不过专念本经,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说为文辞,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岂若今之违经背义,恣为奇说,而无所底止哉!当时神宗令介甫造三经义,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学不正,不足以发明圣意为可惜耳。今为经义者,又不若为词赋;词赋不过工于对偶,不敢如治经者之乱说也。闻虏中科举罢,即晓示云,后举于某经某史命题,仰士子各习此业。使人心有所定止,专心看一经一史,不过数举,则经史皆通。此法甚好。今为主司者,务出隐僻题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于检阅,茫然无所向方,是果何法也!
时有报行遣试官牵合破碎出题目者。或曰:「如此行遣一番,也好。」曰:「某常说,不当就题目上理会。这个都是道术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经字说,说是一道德,同风俗。是他真个使得天下学者尽只念这物事,更不敢别走作胡说,上下都有个据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这腔子里说得好,依旧是好文字。而今人却务出暗僻难晓底题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如何教他不杜撰,不胡说得!」或曰:「若不出难题,恐尽被人先牢笼做了。」曰:「莫管他。自家依旧是取得好文字,不误远方观听。而今却都是杜撰胡说,破坏后生心术,这个乖。某常说,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动不动便鼓噪作闹,以相迫胁,非盗贼而何?这个治之无他,只是严挟书传义之禁,不许继烛,少间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来。虽无沙汰之名,而有其实。既不许继烛,他自要奔,去声。无缘更代得人笔。」或曰:「恐难止遏。今只省试及太学补试,已自禁遏不住。」曰:「也只是无人理会。若捉得一两个,真个痛治,人谁敢犯!这个须从保伍中做起,却从保正社首中讨保明状,五家为保,互相保委。若不是秀才,定不得与保明。若捉出诡名纳两副三副卷底人来,定将保明人痛治,人谁敢犯!某尝说,天下无难理会底事,这般事,只是黑地里脚指缝也求得出来,不知如何得恁地无人理会!」又曰:「今日科举考试也无法不通看。」或曰:「解额当均否?」曰:「固是当均。」或曰:「看来不必立为定额,但以几名终场卷子取一名,足矣。」曰:「不得。少间便长诡名纳卷之弊。依旧与他立定额。只是从今起,照前三举内终场人数计之,就这数内立定额数。三举之后,又将来均一番。如此,则多少不至相悬绝矣。」因说混补,曰:「顷在朝时,赵丞相欲行三舍法。陈君举欲行混补,赵丞相不肯,曰:『今此天寒粟贵,若复混补,须添万余人,米价愈腾踊矣!』某曰:『为混补之说者固是谬,为三舍之说亦未为得也。未论其它,只州郡那里得许多钱榖养他?盖入学者既有舍法之利,又有科举之利,不入学者止有科举一涂,这里便是不均。利之所在,人谁不趋?看来只均太学解额于诸路,便无事。如今太学解额,七人取两人。便七人取一人也由我,十人取一人也由我,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取一人也只由我。而今自立个不平放这里,如何责得人趋』!」或问:「恩榜无益于国家,可去否?」曰:「此又去不得。去之则伤仁恩,人必怨。看来只好作文学助教阙,立定某州文学几员,助教几员,随其人士之多少以定员数,如宗室宫观例,令自指射占阙,相与受代,莫要教他出来做官。既不伤仁恩,又无老耄昏浊贪猥不事事之病矣。」杜佑通典中说释奠处有文学助教官。因说禄令,曰:「今日禄令更莫说,更是不均。且如宫观祠禄,少间又尽指占某州某州。盖州郡财赋各自不同,或元初立额有厚薄,或后来有增减,少间人尽占多处去。虽曰州郡富厚,被人炒多了,也供当不去。少间本州岛本郡底不曾给得,只得去应副他处人矣。」因又说经界。或曰:「初做,也须扰人。」曰:「若处之有法,何扰之有?而今只是人人不晓,所以被人瞒说难行。间有一两个晓得底,终不足以胜不晓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瞒不得矣。打量极多法,惟法算量极易,自绍兴间,秦丞相举行一番以至今。看来是苏绰以后,到绍兴方得行一番,今又多弊了。看来须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无弊。盖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少间病败便多,飞产匿名,无所不有。须是三十年再与打量一番,则乘其弊少而易为力,人习见之,亦无所容其奸矣。要之,既行,也安得尽无弊?只是得大纲好,其间宁无少弊处?只如秦丞相绍兴间行,也安得尽无弊?只是十分弊,也须革去得九分半,所余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愿受这十分重弊压在头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会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来瑕疵之,以为决不可行。如被人少却百贯千贯却不管,及被人少却百钱千钱,便反到要与理会。今人都是这般见识。而今分明是有个天下国家,无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说着。某常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样底说,我只认做三年官了去,谁能闲理会得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得好好做官去。次则豪家上户群起遮拦,恐法行则夺其利,尽用纳税。惟此二者为梗而已。」又曰:「事无有处置不得者。事事自有个恰好处,只是不会思量,不得其法。只如旧时科举无定日,少间人来这州试了,又过那州试;州里试了,又去漕司试;无理会处。不知谁恁聪明,会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积年之弊,一朝而革,这个方唤做处置事。圣人所以做事动中机会,便是如此。」又曰:「凡事须看透背后去。」因举掌云:「且如这一事,见得这一面是如此,便须看透那手背后去,方得。如国手下棋一着,便见得数十着以后之着。若只看这一面,如何见得那事几?更说甚治道!」
包显道言科举之弊。先生曰:「如他经尚是就文义上说,最是春秋不成说话,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说得不成模样。某说道,此皆是『侮圣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样,索性废了,较强。」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随时变通论,皆说要复古。至论科举要复乡举里选,却说须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种子尽了方行得。说得来也是。」
器远问:「今士人习为时文应举,如此须当有个转处否?」曰:「某旧时看,只见天下如何有许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来,只有一个道理,只有一个学。在下者也着如此学,在上者也着如此学。在上若好学,自见道理,许多弊政,亦自见得须要整顿。若上好学,便于学舍选举贤儒,如胡安定孙明复这般人为教导之官;又须将科目尽变了,全理会经学,这须会好。今未说士子,且看朝廷许多奏表,支离蔓衍,是说甚么!如诰宰相,只须说数语戒谕,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说:『表奏之文,下谀其上也;诰敕之文,上谀其下也。』」
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也废他不得。然亦须有个道理。」又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
「今时文赋却无害理,经义大不便,分明是『侮圣人之言』!如今年三知举所上札子,论举人使字,理会这个济得甚?今日亦未论变科举法。只是上之人主张分别善恶,擢用正人,使士子少知趋向,则人心自变,亦有可观。」可学问:「欧阳公当时变文体,亦是上之人主张?」曰:「渠是变其诡怪。但此等事,亦须平日先有服人,方可。」舜功问:「欧阳公本论亦好,但末结未尽。」曰:「本论精密却过于原道。原道言语皆自然,本论却生受。观其意思,乃是圣人许多忧虑做出,却无自然气象。下篇不可晓。」德粹云:「以拜佛,知人之性善。」先生曰:「亦有说话。佛亦教人为善,故渠以此观之也。」
今科举之弊极矣!乡举里选之法是第一义,今不能行。只是就科举法中与之区处,且变着如今经义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经大义。一举试春秋,一举试三礼,一举试易诗书,禁怀挟。出题目,便写出注疏与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策论则试以时务,如礼、乐、兵、刑之属,如此亦不为无益。欲革奔竞之弊,则均诸州解额,稍损太学之额。太学则罢月书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试,独取经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几矣。
因言今日所在解额太不均,先生曰:「只将诸州终场之数,与合发解人数定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设有定数,何故不敢改动?也是好笑!」
或言太学补试,动一二万人之冗。曰:「要得不冗,将太学解额减损,分布于诸州军解额少处。如此,则人皆只就本州岛军试,又何苦就补试也!」
临别,先生留饭。坐间出示理会科举文字,大要欲均诸州解额,仍乞罢诗赋,专经学论策,条目井井。云:「且得士人读些书,三十年后,恐有人出。」
乙卯年,先生作科举私议一通,付过看。大概欲于三年前晓示,下次科场,以某经、某子、某史试士人。如大义,每道只六百字,其余两场亦各不同。后次又预前以某年科场,别以某经、某子、某史试士人,盖欲其逐番精通也。过欲借录,不许。
先生言时文之谬,云:「如科举后便下诏,今番科举第一场出题目在甚经内;论题出在甚史内,如史记汉书等,广说二书;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几三年之间,专心去看得一书。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书子细。」
先生云:「礼书已定,中间无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举法。今之诗赋实为无用,经义则未离于说经。但变其虚浮之格,如近古义,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诗书为一类,三礼为一类,春秋三传为一类。如子年以易诗书取人,则以前三年举天下皆理会此三经;卯年以三礼取人,则以前三年举天下皆理会此三礼;午年以春秋三传取人,则以前三年举天下皆理会此春秋三传。如易诗书稍易理会,故先用此一类取人。如是周而复始,其每举所出策论,皆有定所。如某书出论,某书出策,如天文、地理、乐律之类,皆指定令学者习,而用以为题。」贺孙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须先令考官习之。」
李先生说:「今日习春秋者,皆令各习一传,并习谁解,只得依其说,不得臆说。」先生曰:「六经皆可如此,下家状时,皆令定了。」
今人都不曾读书,不会出题目。礼记有无数好处,好出题目。
科举种子不好。谓试官只是这般人。
张孟远以书来论省试策题目,言今日之弊,在任法而不任人。孟远谓今日凡事伤不能守法。曰:「此皆偏说。今日乃是要做好事,则以碍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即便越法不顾,只是不勇于为善。」
「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个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虽有良有司,亦无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两般法:一是排连法,今铨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举是也。」
问:「今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它未尝过而问焉。」曰:「怪它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曰:「上庠风化之原,所谓『季考行艺』者,行尤可笑,只每月占一日之食便是。」先生笑曰:「何其简易也!」曰:「天下之事,大正则难,如学校间小正须可。」曰:「大处正不得,小处越难。才动着,便有掣肘,如何正得!」琮。
因说科举所取文字,多是轻浮,不明白着实。因叹息云:「最可优者,不是说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
有少年试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须要去试教官?如今最没道理,是教人怀牒来试讨教官。某尝经历诸州,教官都是许多小儿子,未生髭须;入学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须是立个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须是罢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请本州岛乡先生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颖这般人做,士子也归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见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他教人也未是,如教人编抄甚长编文字。」又曰:「今教授之职,只教人做科举时文。若科举时文,他心心念念要争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设官置吏,费廪禄教他做?也须是当职底人怕道人不晓义理,须是要教人识些。如今全然无此意,如何恁地!」
坐中有说赴贤良科。曰:「向来作时文应举,虽是角虚无实,然犹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来最是唤做贤良者,其所作策论,更读不得。缘世上只有许多时事,已前一齐话了,自无可得说。如笮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许多糟粕里只管淋,有甚么得话!既无可得话,又只管要新。最切害处,是轻德行,毁名节,崇智术,尚变诈,读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变到这里,可畏!可畏!这都是不祥之兆,隆兴以来不恁地。自隆兴以后有恢复之说,都要来说功名,初不曾济得些事。今看来,反把许多元气都耗却。管子、孔门所不道,而其言犹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今将礼义廉耻一切埽除了,却来说事功!」
叶正则彭大老欲放混补,庙堂亦可之,但虑艰食,故不果行。二人之意,大率为其乡人地耳。庙堂云「今日太学文字不好」,却不知所以不好之因。便使时文做得十分好后,济得甚事!某有一策:诸州解额,取见三举终场最多人数,以宽处为准,皆与添上。省试取数却不增。其补试,却用科举年八月十五日引试。若要就补,须舍了解试始得。如此,庶几人有固志,免得如此奔竞喧哄。
说赵丞相欲放混补,叹息云:「方今大伦,恁地不成模样!身为宰相,合以何为急?却要急去理会这般事,如何恁地不识轻重!此皆是衰乱之态。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将至,宰相说甚事,只看实录头一版便见,且说太学秀才做时文不好,你道是识世界否!如今待补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人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乱说。待补之立,也恰如掷骰子一般,且试采,掷得便得试,掷不得便不得试,且以为节制。那里得底便是,不得底便不是?这般做事,都是枉费气力。某常说均解额,只将逐州三举终场人数,用其最多为额,每百人取几人,太学许多滥恩一齐省了。元在学者,听依旧恩例。诸路牒试皆罢了,士人如何也只安乡举。如何自家却立个物事,引诱人来奔趋!下面又恁地促窄,无入身处。如何又只就微末处理会!若均解额取人数多,或恐下梢恩科数多,则更将分数立一长限;以前得举人,却只依旧限,有甚不得处?他只说近日学中缘有待补,不得广取,以致学中无好文字。不知时文之弊已极,虽乡举又何尝有好文字脍炙人口?若是要取人才,那里将这几句冒头见得?只是胡说!今时文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秤斤注两,作两句破头,如此是多少衰气!」
或问:「赵子直建议行三舍法:补入县学;自县学比试,入于州学;自州学贡至行在补试,方入太学。如何?」曰:「这是显然不可行底事。某尝作书与说,他自谓行之有次第,这下梢须大乖。今只州县学里小小补试,动不动便只是请嘱之私。若便把这个为补试之地,下梢须至于兴大狱。子直这般所在,都不询访前辈。如向者三舍之弊,某尝及见老成人说,刘聘君云,县学尝得一番分肉,肉有内舍、外舍多寡之差。偶斋仆下错了一分,学生便以界方打斋仆,高声大怒云:『我是内舍生,如何却只得外舍生肉?』如此等无廉耻事无限,只是蔡京法度如此。尝见胡珵德辉有言曰:『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之人为忠为孝也。国家之学法,始于熙宁,成于崇观。熙宁之法,李定为之也;崇观之法,蔡京为之也。李定者,天下之至不孝者也;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岂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其所立之法可行于天下乎!』今欲行三舍之法,亦本无他说,只为所取待补多灭裂,真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太学就试,太学缘此多不得人。然初间所以立待补之意,只为四方士人都来就试,行在壅隘,故为此法。然又须思量,所以致得四方士人苦死都要来赴太学试,为甚么?这是个弊端,须从根本理会去。某与子直书曾云,若怕人都来赴太学试,须思量士人所以都要来做甚么。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养之实,而仕进之途如此其易。正试既优,又有舍选,恩数厚,较之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于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就这处医治,却只去理会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挥,自今太学并不许以恩例为免。若在学人援执旧例,则以自今新补入为始。他未入者幸得入而已,未暇计此。太学既无非望之恩,又于乡举额窄处增之,则人人自安乡里,何苦都要入太学!不就此整理,更说甚?高抑崇,秦相举之为司业,抑崇乃龟山门人。龟山于学校之弊,煞有说话,渠非不习闻讲论,到好做处,却略不施为。秦本恶程学,后见其用此人,人莫不相庆,以为庶几善类得相汲引。后乃大不然,一向苟合取媚而已!学校以前整顿固难。当那时兵兴之后,若从头依自家好规模整顿一番,岂不可为?他当时于秦相前,亦不敢说及此。」
因论黄几先言,曾于周丈处见虏中赋,气脉厚。先生曰:「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