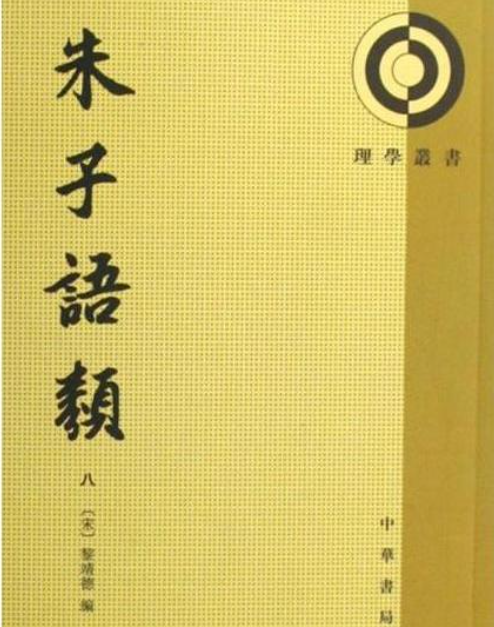孟子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为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须看因何理会个性善作甚底?赐。
性善,故人皆可为尧舜。「必称尧舜」者,所以验性善之实。
孔子罕言性。孟子见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称尧舜,恰似孟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个本原,则为善必力,去恶必勇。今于义理须是见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说我要做好事,所谓这些意,能得几时子!
刘栋问:「人未能便至尧舜,而孟子言必称之,何也?」曰:「『道性善』与『称尧舜』,二句正相表里。盖人之所以不至于尧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无可奈何。然人须当以尧舜为法,如射者之于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艺未精也。人到得尧舜地位,方做得一个人,无所欠阙,然也只是本分事,这便是『止于至善』。」
问:「孟子言性,何必于其已发处言之?」曰:「未发是性,已发是善。」
「孟子道性善」,其发于外也,必善无恶。恶,非性也;性,不恶矣。
问:「『孟子道性善』,不曾说气禀。」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这里,但说本性善,失却这一」问:「气禀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着,非是有安排等待。」问:「天生聪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来说主宰底一般。忽生得个人恁地,便是要他出来作君、作师。书中多说『聪明』,盖一个说白,一个说黑,若不是聪明底,如何遏伏得他众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且莫说圣贤,只如汉高祖光武唐宪宗武宗,他更自了得。某尝说,韩退之可怜。宪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宪宗死,亦便休了,盖只有宪宗会用得他。」池录作:「宪宗也会用人。」或曰:「用李绛亦如此。」曰:「宪宗初年许多伎俩,是李绛教他,绛本传说得详。然绛自有一书,名论事记,记得更详,如李德裕献替录之类。」
李仲实问:「注云:『惟尧舜为能无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盖有恬于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于彼,则蔽于此;不蔽于此,则蔽于彼,毕竟须有蔽处。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须是云遮,方不见;若无云,岂应不见耶!此等处,紧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为何物?反求吾心,有蔽无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论尧如何,舜又如何,如此方是读书。」
或问:「『孟子道性善』章,看来孟子言赤子将入井,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只就情上见,亦只说得时暂发见处。如言『孩提之童,无不亲其亲』,亦只是就情上说得他人事,初无预于己。若要看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谓:『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嘉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即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不善。』此语最为亲切。学者知此,当于喜怒哀乐未发,加持敬工夫;于喜怒哀乐已发,加省察工夫,方为切己。」曰:「不消分这个是亲切,那个是不亲切,如此则成两截了。盖是四者未发时,那怵惕恻隐与孩提爱亲之心,皆在里面了。少间发出来,即是未发底物事。静也只是这物事,动也只是这物事。如孟子所说,正要人于发动处见得是这物事。盖静中有动者存,动中有静者存。人但要动中见得静,静中见得动。若说动时见得是一般物事,静时又见得别是一般物事;静时见得是这般物事,动时又见得不是这般物事,没这说话。盖动时见得是这物事,即是静时所养底物事。静时若存守得这物事,则日用流行即是这物事。而今学者且要识得动静只是一个物事。」
性图。
恶。恶不可谓从善中直下来,只是不能善,则偏于一边,为恶。
性善。性无不善。善。发而中节,无往不善。
孟子初见滕世子,想是见其资质好,遂即其本原一切为他启迪了。世子若是负荷得时,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复见孟子,孟子见其领略未得,更不说了。只是发他志,但得于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说,便漏逗了。当时启迪之言想见甚好,惜其不全记,不得一观!」
问集注云云。曰:「大概是如此。孟子七篇论性处,只此一处,已说得尽。须是日日认一过,只是要熟。」又曰:「程子说才,与孟子说才自不同,然不相妨。须是子细看,始得。」
问:「三子之事,成[间见]则若参较彼己,颜子则知圣人学之必可至,公明仪则笃信好学者也。三者虽有浅深,要之皆是尚志。」曰:「也略有个浅深。恁地看文字,且须看他大意。」又曰:「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细分别出来,又却鹘突;到恁地细碎分别得出来,不曾看得大节目处,又只是在落草处寻。」道夫曰:「这般紧要节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终在『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曰:「然。」
符舜功问:「滕世子从孟子言,何故后来不济事?」曰:「亦是信不笃。如自楚反,复问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则是知性不的。他当时地步狭,本难做;又识见卑,未尝立定得志。且如许行之术至浅下,且延之,举此可见。」
或问:「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后来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国小,绝长补短,止五十里,不过如今一乡。然孟子与他说时,也只说『犹可以为善国』而已。终不成以所告齐梁之君者告之。兼又不多时,便为宋所灭。」因言:「程先生说:『孔子为乘田则为乘田,为委吏则为委吏,为司寇则为司寇,无不可者。至孟子,则必得宾师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处。惟圣人则无不遍,大小方圆,无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此亦是讲学之有阙。盖他心量不及圣人之大,故于天下事有包括不尽处。天下道理尽无穷,人要去做,又做不办;极力做得一两件,又困了。唯是圣人,便事事穷到彻底,包括净尽,无有或遗。」正淳曰:「如夏商之礼,孔子皆能言之,却是当时杞宋之国文献不足,不足取以证圣人之言耳。至孟子,则曰『吾未之学也』而已,『尝闻其略也』而已。」
滕定公薨章
今欲处世事于陵夷之后,乃一向讨论典故,亦果何益!孟子于滕文公乃云:「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便说与「齐疏之服,[食干]粥之食」,哭泣尽哀,大纲先正了。
滕文公问为国章
因说今日田赋利害,曰:「某尝疑孟子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许多畎沟浍洫之类,大段费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为七十,自七十而增为百亩,则田间许多疆理,都合更改,恐无是理。孟子当时未必亲见,只是传闻如此,恐亦难尽信也。」
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恐亦难如此移改。礼记正义引刘氏皇氏之说,正是呆人说话。盖田地一方,沟洫庐舍,成之亦难。自五十里而改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为百里,便都着那趱动,此扰乱之道。如此则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
孟子说贡、助、彻,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贡」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递相增补,岂不大扰!圣人举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国,割某地属某国,至于淮阳太守无民可治,来归京师,此尤可笑!正义引刘氏皇氏熊氏说,皆是臆度,迂僻之甚!
孟子说制度,皆举其纲而已。如田之十一,丧之「自天子达」之类。
「世禄,是食公田之人。」问:「邻长、比长之属有禄否?」曰:「恐未必有。」问:「士者之学如何?」曰:「亦农隙而学。」「孰与教之?」曰:「乡池录作「卿」。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
「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证周亦有公田,读书亦不须究尽细微。」因论「永嘉之学,于制度名物上致详。」
问:「滕文公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为后法?」曰:「他当时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来渠国亦不甚久便亡。」问:「所谓『小国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国,恐是燕韩之类。」曰:「然。」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如古注之说如何?」曰:「若将周礼一一求合其说,亦难。此二句,大率有周礼制度。野,谓甸、稍、县、都,行九一法。国中什一,以在王城,丰凶易察。」
或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曰:「国中行乡、遂之法,如『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又如『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皆是五五相连属,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赋。如乡、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为比』,比便有一个长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子说『夏五十而贡,殷七十而助,周百亩而彻』,此都是孟子拗处。先是五十,后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圣人处事必不如是劳扰。又如先儒说封建,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则斥大疆界,始大封侯国: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则是将那小底移动,添封为大国,岂有此理!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当时所谓国者,如今溪、洞之类。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个长,自为一处,都来朝王,想得礼数大段藞苴。后来到夏商衰时,皆相吞并,渐渐大了。至周时只有千八百国,便是万国吞并为千八百国,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见其又大了。周毕竟是因而封之,岂有移去许多小国,却封为大国!然圣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谓如封五百里国,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里。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别处讨一段子五十里来添,都不如此杀定。盖孟子时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时,既无人记得,又无载籍可考,所以难见得端的。又周封齐鲁之地,是『诛纣伐奄,灭国者五十』,所以封齐鲁之地极如鲁地方千里,如齐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是多少广阔!」
问:「圭田,余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当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亩』也。『余夫二十五亩』,乃十六岁以前所受,在一夫百亩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概耳,未必曾见周礼也。」
有为神农之言章
德修解君民并耕,以为「有体无用」。曰:「如何是有体无用?这个连体都不是。」德修曰:「食岂可无?但以君民并耕而食,则不可。不成因君民不可并耕却不耕,耕食自不可无,此是体。以君民并耕则无用。」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若是以君民并耕,毕竟体已不是。」
「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与江通,大纲如此说去。
问:「『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财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辅、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复从而教之。『放勋曰』,『曰』字不当音驿。」
墨者夷之章
「夷子以谓『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似知所先后者,其说如何?」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后,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错处。人之有爱,本由亲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级。今夷子先以为『爱无差等』,而施之则由亲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亲之言,而不知『爱无差等』之为二本也。」
亚夫问:「『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相类否?」曰:「既是『爱无差等』,何故又『施由亲始』?这便是有差等。又如『施由亲始』一句,乃是夷之临时譔出来凑孟子意,却不知『爱无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谓『施由亲始』,便是把『爱无差等』之心施之。然把爱人之心推来爱亲,是甚道理!」
问:「爱有差等,此所谓一本,盖亲亲、仁民、爱物具有本末也。所谓『二本』是如何?」曰:「『爱无差等』,何止二本?盖千万本也。」退与彦忠论此。彦忠云:「爱吾亲,又兼爱他人之亲,是二爱并立,故曰『二本』。」
或问「一本」。曰:「事他人之亲,如己之亲,则是两个一样重了,如一本有两根也。」
问:「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视他人之亲犹己之亲,如牵彼树根,强合此树根。」曰:「『爱无差等』,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虚字看,则不成句法。」曰:「是。」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无伪也。」既是一本,其中便自然有许多差等。二本,则二者并立,无差等矣。墨子是也。
滕文公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章
问「枉尺直寻」。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则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说甚事!自家身既已坏了,如何直人!」
「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刀锯在前而不避,非其气不馁,如何强得!
「诡遇」,是做人不当做底;「行险」,是做人不敢做底。
子路,则「范我驰驱」而不获者也。管仲之功,诡遇而获禽耳。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嬖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诡御就之,故良不贵之。御法而今尚可寻,但是今人寻得,亦无用处,故不肯。侯景反时,士大夫无人会骑,此时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一学时,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乱射将来,又学其法不得。某旧学琴,且乱弹,谓待会了,却依法。原来不然,其后遂学不得,知学问安可不谨厥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章
敬之问「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概只是无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无一毫私意,直与天地同量,这便是『居天下之广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无些子不当于理,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礼』。及推而见于事,更无些子不合于义,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义』。论上两句,则居广居是体,立正位是用;论下两句,则立正位是体,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广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居之问「广居、正位、大道」。曰:「广居,是廓然大公,无私欲之蔽;正位,是所立处都无差过;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说,择之云:「广居就存心上说。」先生曰:「是。」『立』字是就身上说,『行』字是就施为上说。
居之问「广居、正位、大道」。曰:「广居是不狭隘,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何广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僻曲。正位就处身上说,大道就处事上说。」
居者,心之所存;广居,无私意也。才有私意,则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只见分小着。立者,身之所处。正位者,当为此官,则为此官,当在此,则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径,荆棘之场。人生只是此三事。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义、养气,方到此地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气对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在彼者,皆我之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问:「『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气否?」曰:「然。浩然之气须是养,有下工夫处。『居广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气,方能如此。」
问:「『居天下之广居』云云,如欲『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孟子若去那里立,便不是正位。」林择之云:「如『不与驩言』之事,亦是正位。」曰:「然。」
公孙丑问不见诸侯章
问:「公孙丑言孟子不见诸侯,何故千里来见梁惠王?」曰:「以史记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其曰『千里而来』者,亦是劳慰之辞尔。孟子出处,必不错了。如平日在诸侯国内,虽不为臣,亦有时去见他。若诸侯来召。则便不去。盖孟子以宾师自处,诸侯有谋则就之。如孟子一日将见王,王不合使人来道:『我本就见,缘有疾,不可以风,不知可以来见否?』孟子才闻此语,便不肯去。」时坐间有杨方县丞者,云:「弟子称其师不见诸侯,必是其师寻常如此。其见梁惠王,亦须有说。但今人不肯便信他说话,只管信后人言语,所以疑得孟子如此。」
孟子之时,时君重士,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时君致敬尽礼而后见。自是当时做得个规模如此定了,如史记中列国之君拥篲先迎之类。却非是当世轻士,而孟子有意于矫之以自高也。因说孟子不见诸侯及此。
至云:「看得孟子于辞受取舍进退去就,莫非天理时中之妙,无一毫人欲之私,无一毫过不及之病。如谓『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辞曰『闻戒』,『馈赆』,可受则受之,皆无一毫过不及,无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这道理又却那里安顿?」
公都子问好辩章
居之问孟子「岂好辩」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见诸圣贤遭时之变,各行其道,是这般时节;其所以正救之者,是这般样子,这见得圣贤是甚么样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阙齾处,得圣贤出来补得教周全。补得周全后,过得稍久,又不免有阙,又得圣贤出来补,这见圣贤是甚力量!直有阖辟乾坤之功!」
尧晚年方遭水。尧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晓。胡安定说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盖尧甚以为儆,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是不曾见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治黄河费许多力。黄河今由梁山泊入清河楚州。
问:「孔子作春秋,空言无补,乱臣贼子何缘便惧?且何足为春秋之一治?」曰:「非说当时便一治,只是存得个治法,使这道理光明灿烂,有能举而行之,为治不难。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见,及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说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某字,有甚微词奥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褒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在目,观之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犯耳。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问:「孔子所书辞严义简,若非三传详着事迹,也晓得笔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书时,事迹皆在,门人弟子皆晓他圣人笔削之意。三家惧其久而泯没也,始皆笔之于书。流传既久,是以不无讹谬。然孔子已自直书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与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薨于齐』,『公之丧至自齐』,『夫人孙于齐』,此等显然在目,虽无传亦可晓。且如楚子侵中国,得齐桓公与之做头抵拦,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齐桓公死,又得晋文公拦遏住,如横流泛滥,硬做堤防。不然,中国为渰浸必矣。此等义,何难晓?」问读春秋之法。曰:「无它法,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准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如看史记,秦之所以失如何?汉之所以得如何?楚汉交争,楚何以亡?汉何以兴?其所以为是非得失成败盛衰者何故?只将自家平日讲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见。看春秋亦如此。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问:「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说得太深。苏子由教人看左传,不过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义理折衷去取之耳。」
孟子苦死要与杨墨辩,是如何?与他有甚冤恶,所以辟之如不共戴天之雠?「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才说道要距杨墨,便是圣人之徒。如人逐贼,有人见了自不与捉,这便唤做是贼之党。贼是人情之所当恶。若说道贼当捉,当诛,这便是主人边人。若说道贼也可捉,可恕,这只唤做贼边人!
问孟子「好辩」一曰:「当时如纵横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盖他只坏得个粗底。若杨墨则害了人心,须着与之辩。」时举谓:「当时人心不正,趋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辟之,则圣人之道无自而明。是时真个少孟子不得!」曰:「孟子于当时只在私下恁地说,所谓杨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后世却因其言而知圣人之道为是,知异端之学为非,乃是孟子有功于后世耳。」
因居之看「好辩」一章,曰:「墨氏『爱无差等』,故视其父如路人。杨氏只理会自己,所谓『修其身而外天下国家』者,故至于无君。要之,杨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顺生向上去,是顺理。今一枝乃逆下生来,是逆理也。如水本润下,今洪水乃横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顺水之性,使之润下而已。暴君『坏宫室以为污池,弃田以为园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种桑麻,今乃坏而弃之,是逆理也。汤武之举,乃是顺理。如杨墨逆理,无父无君,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便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极力辟之,亦只是顺理而已。」此一段多推本先生意,非全语。
敬之问杨墨。曰:「杨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于无父无君。盖杨氏见世间人营营于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独洁其身以自高,如荷蒉接舆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洁身而自为,则天下事教谁理会?此便是无君也。墨氏见世间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尽爱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难,在君亲则当先救,在他人则后救之。若君亲与他人不分先后,则是待君亲犹他人也,便是无父。此二者之所以为禽兽也。孟子之辩,只缘是放过不得。今人见佛老家之说者,或以为其说似胜吾儒之说;或又以为彼虽说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与之辩。若真个见得是害人心,乱吾道,岂容不与之辩!所谓孟子好辩者,非好辩也,自是住不得也。」南升。
问:「墨氏兼爱,何遽至于无父?」曰:「人也只孝得一个父母,那有七手八脚,爱得许多!能养其父无阙,则已难矣。想得他之所以养父母者,粗衣粝食,必不能堪。盖他既欲兼爱,则其爱父母也必疏,其孝也不周至,非无父而何。墨子尚俭恶乐,所以说『里号朝歌,墨子回车』。想得是个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见。」又问:「『率兽食人』,亦深其弊而极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杨氏自是个退步爱身,不理会事底人。墨氏兼爱,又弄得没合杀。使天下伥伥然,必至于大乱而后已,非『率兽食人』而何?如东晋之尚清谈,此便是杨氏之学。杨氏即老庄之道,少间百事废弛,遂启夷狄乱华,其祸岂不惨于洪水猛兽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于社稷丘墟,亦其验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学问高妙,出入于老佛之间,其政事欲与尧舜三代争衡。然所用者尽是小人,聚天下轻薄无赖小人作一处,以至遗祸至今。他初间也何尝有启狄乱华,『率兽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义理不明,其终必至于是耳。」或云:「若论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节好。其它狠厉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资质学问之差。亦安得以一节之好,而盖其大节之恶哉!吁,可畏!可畏!」
问:「墨氏兼爱,疑于仁,此易见。杨氏为我,何以疑于义?」曰:「杨朱看来不似义,他全是老子之学。只是个逍遥物外,仅足其身,不屑世务之人。只是他自要其身界限齐整,不相侵越,微似义耳,然终不似也。」论杨墨及异端类,余见尽心上。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盖人心正,然后可以有所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