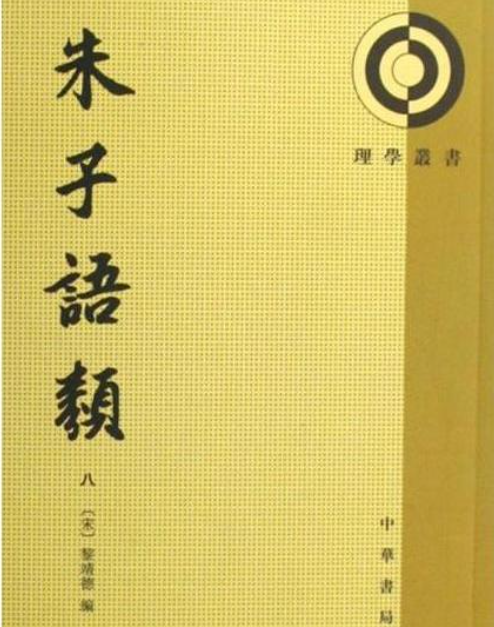中庸一
纲领
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齐整!
中庸,初学者未当理会。
中庸之书难看。中间说鬼说神,都无理会。学者须是见得个道理了,方可看此书,将来印证。赐。夔孙录云「中庸之书,如个卦影相似,中间」云云。
问中庸。曰:「而今都难恁理会。某说个读书之序,须是且着力去看大学,又着力去看论语,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书了,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问人,只略略恁看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难底。中庸多说无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参』等类,说得高;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若且理会文义,则可矣。」问:「中庸精粗本末无不兼备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无不备处。」
问中庸大学之别。曰:「如读中庸求义理,只是致知功夫;如慎独修省,亦只是诚意。」问:「只是中庸直说到『圣而不可知』处。」曰:「如大学里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笃恭而天下平』底事。」
读书先须看大纲,又看几多间架。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是大纲。夫妇所知所能,与圣人不知不能处,此类是间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纲,次看几多间,间内又有小间,然后方得贯通。」
问:「中庸名篇之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兼此二义,包括方尽。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发之中;就经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时中』之『中』。然所以能时中者,盖有那未发之中在。所以先开说未发之中,然后又说『君子之时中』。」以下论名篇之义。
至之问:「『中』含二义,有未发之中,有随时之中。」曰:「中庸一书,本只是说随时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随时之中,缘是有那未发之中,后面方说『时中』去。」至之又问:「『随时之中,犹日中之中』,何意?」曰:「本意只是说昨日看得是中,今日看得又不是中。然譬喻不相似,亦未稳在。」直卿云:「在中之中,与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体,彼是尾。」与上条盖同闻。
「『中庸』之『中』,本是无过无不及之中,大旨在时中上。若推其中,则自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为『时中』之『中』。未发之中是体,『时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直卿云:「如『仁义』二字,若兼义,则仁是体,义是用;若独说仁,则义、礼、智皆在其中,自兼体用言之。」
「『中庸』之『中』,是兼已发而中节、无过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若不识得此理,则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谓『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论语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皆此意也。」
「『中庸』之『中』,兼不倚之中?」曰:「便是那不倚之中流从里出来。」炎。
问:「明道以『不易』为庸,先生以『常』为庸,二说不同?」曰:「言常,则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则是事之已然者。自后观之,则见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则日用常行者便是。」
或问:「『中庸』二字,伊川以庸为定理,先生易以为平常。据『中』之一字大段精微,若以平常释『庸』字,则两字大不相粘。」曰:「若看得不相粘,便是相粘了。如今说这物白,这物黑,便是相粘了。」广因云:「若不相粘,则自不须相对言得。」曰:「便是此理难说。前日与季通说话终日,惜乎不来听。东之与西,上之与下,以至于寒暑昼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对也。天地间物未尝无相对者,故程先生尝曰:『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看得来真个好笑!」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则不得久矣。譬如饮食,如五谷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异味不常得之物,则暂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为定理,则却不见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则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广因举释子偈有云:「世间万事不如常,又不惊人又久长。」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极相似处,只是说得来别。故某于中庸章句序中着语云:『至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须是看得他那『弥近理而大乱真』处,始得。」广云:「程子『自私』二字恐得其要领,但人看得此二字浅近了。」曰:「便是向日王顺伯曾有书与陆子静辨此二字云:『佛氏割截身体,犹自不顾,如何却谓之自私得!』」味道因举明道答横渠书云:「大抵人患在自私而用智。」曰:「此却是说大凡人之任私意耳。」因举下文「豁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曰:「此亦是对说。『豁然而大公』,便是不自私;『物来而顺应』,便是不用智。后面说治怒处曰:『但于怒时遽忘其怒,反观理之是非,则于道思过半矣。』『忘其怒』,便是大公;『反观理之是非』,便是顺应,都是对说。盖其理自如此。」广因云:「太极一判,便有阴阳相对。」曰:「然。」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饮食之有五谷,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异味,锦绮组绣,不久便须厌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为定理,却不见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晦问:「『中庸』二字,旧说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语。今说得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说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语;而以平常说庸,恰似不相粘着。」曰:「此其所以粘着。盖缘处得极精极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异,便不是极精极密,便不是中庸。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东便与西对,南便与北对,无一事一物不然。明道所以云:『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终夜思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直是可观,事事如此。」与广录盖闻同。
问:「中庸不是截然为二,庸只是中底常然而不易否?」曰:「是。」
问:「明道曰:『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自已尽矣。」曰:「中亦要得常,此是一经一纬,不可阙。」
蜚卿问:「『中庸之为德。』程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曰:「中则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异。中如一物竖置之,常如一物横置之。唯中而后常,不中则不能常。」因问曰:「不惟不中则不能常,然不常亦不能为中。」曰:「亦是如此。中而后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后能有中,此以人而言。」问:「龟山言:『高明则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不知将体用对说如何?」曰:「只就『中庸』字上说,自分晓,不须如此说亦可。」又举荆公「高明处己,中庸处人」之语为非是。因言:「龟山有功于学者。然就他说,据他自有做工夫处。高明,释氏诚有之,只缘其无『道中庸』一截。又一般人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弟,故十项事其八九可称。若一向拘挛,又做得甚事!要知中庸、高明二者皆不可废。」
或问:「中与诚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样,诚是道理之实处,中即诚矣。」又问:「智仁勇于诚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诚是行此三者都要实。」又问「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头看是中,就这头看是庸。譬如山与岭,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谓之山;行着岭路,则谓之岭,非二物也。方子录云:「问:『中庸既曰「中」,又曰「诚」,何如?』曰:『此古诗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也。』」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尧授舜,舜授禹,都是当其时合如此做,做得来恰好,所谓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汤武之事亦然。又如当盛夏极暑时,须用饮冷,就叙处,衣葛,挥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当隆冬盛寒时,须用饮汤,就密室,重裘,拥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极暑时重裘拥火,盛寒时衣葛挥扇,便是差异,便是失其中矣。」
问:「『中庸』之『庸』,平常也。所谓平常者,事理当然而无诡异也。或问言:『既曰当然,则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以至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无适而非平常矣。』窃谓尧舜禅授,汤武放伐,皆圣人非常之变,而谓之平常,何也?」曰:「尧舜禅授,汤武放伐,虽事异常,然皆是合当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说『经、权』字,『合权处,即便是经』。」铢曰:「程易说大过,以为『大过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过于理也。圣人尽人道,非过于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此。」
问道之常变。举中庸或问说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不得处只着变,而硬守定则不得。至变得来合理,断然着如此做,依旧是常。」又问:「前日说经权云:『常自是着还他一个常,变自是着还他一个变。』如或问举『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其变无穷,无适而非常』,却又皆以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处,只得变。变得是,仍旧是平常,然依旧着存一个变。」
有中必有庸,有庸必有中,两个少不得。赐。
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后可以发诸运用。
中庸该得中和之义。庸是见于事,和是发于心,庸该得和。
问:「『中庸』二字孰重?」曰:「庸是定理,有中而后有庸。」问:「或问中言:『中立而无依,则必至于倚。』如何是无依?」曰:「中立最难。譬如一物植立于此,中间无所依着,久之必倒去。」问:「若要植立得住,须用强矫?」曰:「大故要强立。」
「向见刘致中说,今世传明道中庸义是与叔初本,后为博士演为讲义。」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着,后掇其要为解也。」诸家解。
吕中庸,文滂沛,意浃洽。
李先生说:「陈几叟辈皆以杨氏中庸不如吕氏。」先生曰:「吕氏饱满充实。」
龟山门人自言龟山中庸枯燥,不如与叔浃洽。先生曰:「与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远。」
游杨吕侯诸先生解中庸,只说他所见一面道理,却不将圣人言语折衷,所以多失。
游杨诸公解中庸,引书语皆失本意。
「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说得数句好,下面便有几句走作无道理了,不知是如何。旧尝看栾城集,见他文势甚好,近日看,全无道理。如与刘原父书说藏巧若拙处,前面说得尽好,后面却说怕人来磨我,且恁地鹘突去,要他不来,便不成说话。又如苏东坡忠厚之至论说『举而归之于仁』,便是不柰他何,只恁地做个鹘突了。二苏说话,多是如此。此题目全在『疑』字上。谓如有人似有功,又似无功,不分晓,只是从其功处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无罪,不分晓,只得从其罪处轻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赏罚不可毫发轻重。而今说『举而归之于仁』,更无理会。」或举老苏五经论,先生曰:「说得圣人都是用术了!」
游丈开问:「中庸编集得如何?」曰:「便是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
先生以中庸或问见授,云:「亦有未满意处,如评论程子、诸子说处,尚多觕。」
问:「赵书记欲以先生中庸解锓木,如何?」先生曰:「公归时,烦说与,切不可!某为人迟钝,旋见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个人如此著述!」
章句序
问:「先生说,人心是『形气之私』,形气则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属。」曰:「固是。」问:「如此,则未可便谓之私?」曰:「但此数件物事属自家体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个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个不好底根本。」士毅。
问「或生于形气之私」。曰:「如饥饱寒暖之类,皆生于吾身血气形体,而他人无与,所谓私也。亦未能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犬旬]之耳。」
问:「人心本无不善,发于思虑,方始有不善。今先生指人心对道心而言,谓人心『生于形气之私』,不知是有形气便有这个人心否?」曰:「有恁地分别说底,有不恁地说底。如单说人心,则都是好。对道心说着,便是劳攘物事,会生病痛底。」
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先生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气亦皆有善。』不知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船无柁,纵之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乃形气,则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万物过不及』,亦不是。万物岂无中?渠又云:『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也。』此乃伊川说,然皆为养气言。养得则为浩然之气,不养则为恶气,卒徒理不得。且如今日说夜气是甚大事,专靠夜气,济得甚事!」可学云:「以前看夜气,多略了『足以』两字,故然。」先生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养是养此,识得更无走作。」舜功问:「天理人欲,毕竟须为分别,勿令交关。」先生曰:「五峰云:『性犹水,善犹水之下也,情犹澜也,欲犹水之波浪也。』波浪与澜,只争大小,欲岂可带于情!」某问:「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却是。」先生曰:「是。同行者,谓二人同行于天理中,一人日从天理,一人专徇人欲,是异情。下云『同体而异用』,则大错!」因举知言多有不是处。「『性无善恶』,此乃欲尊性,不知却鹘突了它。胡氏论性,大抵如此,自文定以下皆然。如曰:『性,善恶也。性、情、才相接。』此乃说着气,非说着性。向吕伯恭初读知言,以为只有二段是,其后却云:『极妙,过于正蒙!』」
问:「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掐着痛,抓着痒,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饥寒痛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逊,此道心也。虽上智亦同。一则危殆而难安,一则微妙而难见。『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
「因郑子上书来问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窃寻中庸序,以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盖觉于理谓性命,觉于欲谓形气云云。可学近观中庸序所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来专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于形气,如何去得!然人于性命之理不明,而专为形气所使,则流于人欲矣。如其达性命之理,则虽人心之用,而无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为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践形之义,则与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异?『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学者。可学以为必有道心,而后可以用人心,而于人心之中,又当识道心。若专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则固流入于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则是判性命为二物,而所谓道心者,空虚无有,将流于释老之学,而非虞书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云:「前辈多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当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则须绝灭此身,而后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说道心,后说人心?」大雅云:「如此,则人心生于血气,道心生于天理;人心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而道心则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但为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故圣人以为此人心,有知觉嗜欲,然无所主宰,则流而忘反,不可据以为安,故曰危。道心则是义理之心,可以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据以为准者也。且以饮食言之,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于孔悝之类,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则子必狠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则不然,虽其父欲杀之,而舜之孝则未尝替,此道心也。故当使人心每听道心之区处,方可。然此道心却杂出于人心之间,微而难见,故必须精之一之,而后中可执。然此又非有两心也,只是义理、人欲之辨尔。陆子静亦自说得是,云:『舜若以人心为全不好,则须说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说危者,不可据以为安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为所杂也。』此言亦自是。今郑子上之言都是,但于道心下,却一向说是个空虚无有之物,将流为释老之学。然则彼释迦是空虚之魁,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者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
章句
问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云云。曰:「如何说晓得一理了,万事都在里面?天下万事万物都要你逐一理会过,方得。所谓『中散为万事』,便是中庸。近世如龟山之论,便是如此,以为『反身而诚』,则天下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如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之理便自然备于我?成个甚么?」又曰:「所谓『中散为万事』,便是中庸中所说许多事,如智仁勇,许多为学底道理,与『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与祭祀鬼神许多事。圣人经书所以好看,中间无些子罅隙,句句是实理,无些子空缺处。」
问:「中庸始合为一理,「天命之谓性。」末复合为一理。」「无声无臭。」「始合而开,其开也有渐;末后开而复合,其合也亦有渐。」赐。夔孙录同。
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是专言理,虽气亦包在其中,然说理意较多。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谓道」不去。如太极虽不离乎阴阳,而亦不杂乎阴阳。
用之问:「『天命之谓性。』以其流行而付与万物者谓之命,以人物禀受者谓之性。然人物禀受,以其具仁义礼智而谓之性,以贫贱寿夭而言谓之命,是人又兼有性命。」曰:「命虽是恁地说,然亦是兼付与而言。」
问:「『天命之谓性』,此只是从原头说否?」曰:「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则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尽得?」又问:「以健顺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顺』字亦恐有碍否?」曰:「如牛之性顺,马之性健,即健顺之性。虎狼之仁,蝼蚁之义,即五常之性。但只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耳。」
问:「『天命之谓性』,章句云『健顺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顺』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顺』乃『阴阳』二字。某旧解未尝有此,后来思量,既有阴阳,须添此二字始得。」枅。
问:「『木之神为仁,火之神为礼』,如何见得?」曰:「『神』字,犹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见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里见得是礼?却是他意思是礼。」古注。
「率性之谓道」,郑氏以金木水火土,从「天命之谓性」说来,要顺从气说来方可。
「率性之谓道」,「率」字轻。
「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谓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率性之谓道」,「率」是呼唤字,盖曰循万物自然之性之谓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谓「合而言之道也」,是此义。
安卿问「率性」。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训循。到吕与叔说『循性而行,则谓之道』,伊川却便以为非是。至其自言,则曰:『循牛之性,则不为马之性;循马之性,则不为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尔。」
「率,循也。不是人去循之,吕说未是。程子谓:『通人物而言,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做马底性。』物物各有个理,即此便是道。」曰:「总而言之,又只是一个理否?」曰:「是。」
「率性之谓道」,只是随性去,皆是道。吕氏说以人行道。若然,则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
问:「『「率性之谓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说,还是就行道人上说?」曰:「诸家多作行道人上说,以率性便作修为,非也。率性者,只是说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许多道理。性是个浑沦底物,道是个性中分派条理。循性之所有,其许多分派条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气禀有异,不可道物无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则为牛之性,又不做马底性;马则为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物物各有这理,只为气禀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随他性之所通,道亦无所不在也。」
问:「率性通人物而言,则此『性』字似『生之谓性』之『性』,兼气禀言之否?」曰:「『天命之谓性』,这性亦离气禀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说,不是就行道人说。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气禀有异,不可道物无此理。性是个浑沦物,道是性中分派条理,随分派条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络马首,皆是随他所通处。仁义礼智,物岂不有,但偏耳。随他性之所通处,道皆无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问:「鸢有鸢之性,鱼有鱼之性,其飞其跃,天机自完,便是天理流行发见之妙处,故子思姑举此一二以明道之无所不在否?」曰:「是。」
孟子说「性善」,全是说理。若中庸「天命之谓性」,已自是兼带人物而言。「率性之谓道」,性是一个浑沦底物,道是支脉。恁地物,便有恁地道。率人之性,则为人之道,率牛之性,则为牛之道,非谓以人循之。若谓以人循之而后谓之道,则人未循之前,谓之无道,可乎!砥。
「天命之谓性」,指迥然孤独而言。「率性之谓道」,指着于事物之间而言。又云:「天命之性,指理言;率性之道,指人物所行言。或以率性为顺性命之理,则谓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方始有也!」
万物禀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与道相对,则性是体,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里面做出底道。」
问:「『天命之为性,率性之谓道』,伊川谓通人物而言。如此,却与告子所谓人物之性同。」曰:「据伊川之意,人与物之本性同,及至禀赋则异。盖本性理也,而禀赋之性则气也。性本自然,及至生赋,无气则乘载不去,故必顿此性于气上,而后可以生。及至已生,则物自禀物之气,人自禀人之气最难看。而其可验者,如四时之间,寒暑得宜,此气之正。当寒而暑,当暑而寒,乃气不得正。气正则为善,气不正则为不善。又如同是此人,有至昏愚者,是其禀得此浊气太深。」又问:「明道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曰:「论性不论气,孟子也;不备,但少欠耳。论气不论性,荀扬也;不明,则大害事!」可学问:「孟子何不言气?」曰:「孟子只是教人勇于为善,前更无阻碍。自学者而言,则不可不去其窒碍。正如将百万之兵,前有数万兵,韩白为之,不过鼓勇而进;至他人,则须先去此碍后可。」吴宜之问:「学者治此气,正如人之治病。」曰:「亦不同。须是明天理,天理明,则去。通书『刚柔』一段,亦须着且先易其恶,既易其恶,则致其中在人。」问:「恶安得谓之刚?」曰:「此本是刚出来。」语毕,先生又曰:「『生之谓性』,伊川以为生质之性,然告子此语亦未是。」再三请益,曰:「且就伊川此意理会,亦自好。」
问「『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皆是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人受其全,则其心具乎仁义礼智之全体;物受其偏,则随其品类各有得焉,而不能通贯乎全体。『率性之谓道』,若自人而言之,则循其仁义礼智之性而言之,固莫非道;自物而言之,飞潜动植之类各正其性,则亦各循其性于天地之间,莫非道也。如中庸或问所说『马首之可络,牛鼻之可穿』等数句,恐说未尽。所举或问,非今本。盖物之自循其性,多有与人初无干涉。多有人所不识之物,无不各循其性于天地之间,此莫非道也。如或问中所说,恐包未尽。」曰:「说话难。若说得阔,则人将来又只认『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等做性;却不认『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智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底是性。」因言:「解经立言,须要得实。如前辈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是饥食渴饮,夏葛冬裘,为乐尧舜之道。若如此说,则全身已浸在尧舜之道中,何用更说『岂若吾身亲见之哉』?如前辈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以为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间,一似常有一物昭然在目前,不会下去一般,此皆是说得不实。所以『未坠于地』者,只言周衰之时,文武之典章,人尚传诵得在,未至沦没。」先生既而又曰:「某晓得公说底。盖马首可络,牛鼻可穿,皆是就人看物处说。圣人『修道之谓教』,皆就这样处。如适间所说,却也见得一个大体。」方子录云:「至之问:『「率性之谓道」,或问只言「马首之可络,牛鼻之可穿」,都是说以人看物底。若论飞潜动植,各正其性,与人不相干涉者,何莫非道?恐如此看方是。』先生曰:『物物固皆是道。如蝼蚁之微,甚时胎,甚时卵,亦是道。但立言甚难,须是说得实。如龟山说「尧舜之道」,只夏葛冬裘、饥食渴饮处便是。如此,则全身浸在尧舜之道里,又何必言「岂若吾身亲见之哉」?』黄丈云:『若如此说,则人心、道心皆是道去。』先生曰:『相似「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性也」底,却认做道;「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智之于贤者,有性焉」底,却认不得。如「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李光祖乃曰:「日用之间,昭然在是。」如此,则只是说古今公共底,何必指文武?孔子盖是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沦没,非是指十方常住者而言也。』久之,复曰:『至之却亦看得一个大体。』」盖卿同。
问:「伊川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亦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谓教」,此专言人事。』」曰:「是如此。人与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则为人道,循马牛之性则为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马耕牛驰,则失其性,而非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
问:「『率性之谓道』,通人物而言,则『修道之谓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马』,『不杀胎,不夭殀』,『斧斤以时入山林』,此是圣人教化不特在人伦上,品节防范而及于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谓之『尽物之性』。但于人较详,于物较略;人上较多,物上较少。」砥。
问:「集解中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谓教』,是专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谓教』,就物上亦有个品先生所以咸若草木鸟兽,使庶类蕃殖,如周礼掌兽、掌山泽各有官,如周公驱虎豹犀象龙蛇,如『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之类,各有个品节,使万物各得其所,亦所谓教也。」
问「修道之谓教」。曰:「游杨说好,谓修者只是品节之也。明道之说自各有意。」
问:「明道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扬雄言:『学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谓扬雄为不识性。中庸却言『修道之谓教』,如何?」曰:「性不容修,修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圣人于中为之品节以教人耳,谁能便于道上行!」
「修道之谓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后面「自明诚」谓之教却说作自修。盖「天命谓性」之「性」与「自诚明」之性,「修道谓教」之「教」与「自明诚」之教,各自不同。诚明之性,「尧舜性之」之「性」;明诚之教,由教而入者也。
问:「中庸旧本不曾解『可离非道』一句。今先生说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离与不可离,道与非道,各相对待而言。离了仁便不仁,离了义便不义。公私善利皆然。向来从龟山说,只谓道自不可离,而先生旧亦不曾为学者说破。」曰:「向来亦是看得太」今按:「可离非道」,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与章句、或问说不合,更详之。
黻问:「中庸曰『道不可须臾离』,伊川却云『存无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长』,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此言,是为辟释氏而发。盖释氏不理会常行之道,只要空守着这一个物事,便唤做道,与中庸自不同。」说毕又曰:「辟异端说话,未要理会,且理会取自家事。自家事既明,那个自然见得。」与立。
杨通老问:「中庸或问引杨氏所谓『无适非道』之云,则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尽。盖衣食作息,视听举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义理准则,乃道也。」曰:「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谓食饮作息者是道,则不可,与庞居士『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之颂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后长』与『疾行先长』,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后长方是道,若疾行先长便不是道,岂可说只认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运水搬柴』,须是运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运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谓『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会是和非,只认得那衣食作息,视听举履,便是道。说我这个会说话底,会作用底,叫着便应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问道理如何。儒家则须是就这上寻讨个道理方是道。禅老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在汝等诸人面门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认得这个,把来作弄。」或问:「告子之学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告子底死杀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学者就故纸上理会,也解说得去,只是都无那快活和乐底意思,便是和这佛家底也不曾见得。似他佛家者虽是无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这形而下者之中,理会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学者看来,须是先晓得这一层,却去理会那上面一层方好。而今都是和这下面一层也不曾见得,所以和那下面一层也理会不得。」又曰:「天地中间,物物上有这个道理,虽至没紧要底物事,也有这道理。盖『天命之谓性』,这道理却无形,无安顿处。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这两个元不相离,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贵『博学于文』。看来博学似个没紧要物事,然那许多道理便都在这上,都从那源头上来。所以无精粗小大,都一齐用理会过,盖非外物也。都一齐理会,方无所不尽,方周遍无疏缺处。」又曰:「『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所谓不可离者,谓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间举止动作便是道,则无所适而非道,无时而非道,然则君子何用恐惧戒慎?何用更学道为?为其不可离,所以须是依道而行。如人说话,不成便以说话者为道,须是有个仁义礼智始得。若便以举止动作为道,何用更说不可离得?」又曰:「大学所以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所以只说『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所谓道者是如此,何尝说物便是则!龟山便只指那物做则,只是就这物上分精粗为物则。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视乃则也;耳物也,耳之听乃则也。殊不知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龟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乐在是。』如此,则世间伊尹甚多矣!龟山说话,大概有此病。」
问:「『道不可离』,只言我不可离这道,亦还是有不能离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离底。纯说是不能离,不成错行也是道!」时举录云:「叔重问:『「道不可离」,自家固不可离,然他也有不能离底意。』曰:『当参之于心,可离、不能离之间。纯说不能离,也不得,不成错行了也是道!』」因问:「龟山言:『饥食渴饮,手持足行,便是道。』窃谓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视耳听未是道,视明听聪乃道也。或谓不然,其说云:『手之不可履,犹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职。「率性之谓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审如何?」曰:「不然。桀纣亦会手持足履,目视耳听,如何便唤做道!若便以为道,是认欲为理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饥食渴饮,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废天职。』须看『着些私吝心』字。」时举录云:「夜来与先之论此。先之云『手之不可履』云云,先生曰云云。」
此道无时无之,然体之则合,背之则离也。一有离之,则当此之时,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须臾离」。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则不敢以须臾离也。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即是道不可须臾离处。履孙。
问:「日用间如何是不闻不见处?人之耳目闻见常自若,莫只是念虑未起,未有意于闻见否?」曰:「所不闻,所不见,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乐未发时。凡万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惧,常要提起此心,常在这里,便是防于未然,不见是图底意思。」徐问:「讲求义理时,此心如何?」曰:「思虑是心之发了。伊川谓:『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可,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寓录云:「问:『讲求义理,便是此心在否?』曰:『讲求义理,属思虑,心自动了,是已发之心。』」
刘黻问:「不知无事时如何戒慎恐惧?若只管如此,又恐执持太过;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么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惧。」与立。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处难言。大段着意,又却生病,只恁地略约住。道着戒慎恐惧,已是剩语,然又不得不如此说。
「戒慎恐惧是未发,然只做未发也不得,便是所以养其未发。只是耸然提起在这里,这个未发底便常在,何曾发?」或问:「恐惧是已思否?」曰:「思又别。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惧,正是防闲其未发。」或问:「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无失即所以中。』『敬而无失』,便是常敬,这中底便常在。」
问:「戒慎恐惧,以此涵养,固善。然推之于事,所谓『开物成务之几』,又当如何?」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独脚做不得,须是读书穷理。」又曰:「只是源头正,发处自正。只是这路子上来往。」
问:「中庸所谓『戒慎恐惧』,大学所谓『格物致知』,皆是为学知、利行以下底说否?」曰:「固然。然圣人亦未尝不戒慎恐惧。『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但圣人所谓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则勉强之念耳。」
所谓「不睹不闻」者,乃是从那尽处说来,非谓于所睹所闻处不慎也。如曰「道在瓦砾」,便不成不在金玉!
问:「『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与『莫见乎隐』两段,分明极有条理,何为前辈都作一段滚说去?」曰:「此分明是两节事。前段有『是故』字,后段有『故』字。圣贤不是要作文,只是逐节次说出许多道理。若作一段说,亦成是何文字!所以前辈诸公解此段繁杂无伦,都不分明。」
用之问:「戒惧不睹不闻,是起头处,至『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又用紧一紧。」曰:「不可如此说。戒慎恐惧是普说,言道理偪塞都是,无时而不戒慎恐惧。到得隐微之间,人所易忽,又更用慎,这个却是唤起说。戒惧无个起头处,只是普遍都用。如卓子有四角头,一齐用着工夫,更无空缺处。若说是起头,又遗了尾头;说是尾头,又遗了起头;若说属中间,又遗了两头。不用如此说。只是无时而不戒慎恐惧,只自做工夫,便自见得。曾子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成到临死之时,方如此战战兢兢。他是一生战战兢兢,到死时方了!」
问:「旧看『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两句,只谓人有所愧歉于中,则必见于颜色之间,而不可揜。昨闻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处』,自然见得愈是分晓。如做得是时,别人未见得是,自家先见得是;做得不是时,别人未见得非,自家先见得非。如此说时,觉得又亲切。」曰:「事之是与非,众人皆未见得,自家自是先见得分明。」问:「『复小而辨于物。』善端虽是方萌,只是昭昭灵灵地别,此便是那不可揜处?」曰:「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续得这意思去,又暗了。」
问:「『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程子举弹琴杀心事,是就人知处言。吕游杨氏所说,是就己自知处言。章句只说己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动于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谓诚之不可揜也。」
问:「伊川以鬼神凭依语言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如何?」曰:「隐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说出来,岂非『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盖鬼神只是气,心中实有是事,则感于气者,自然发见昭著如此。」文蔚问:「今人隐微之中,有不善者甚多,岂能一一如此?」曰:「此亦非常之事,所谓事之变者。」文蔚曰:「且如人生积累愆咎,感召不祥,致有日月薄蚀,山崩川竭,水旱凶荒之变,便只是此类否?」曰:「固是如此。」
戒慎恐惧乎其所不睹不闻,是从见闻处戒慎恐惧到那不睹不闻处。这不睹不闻处是工夫尽头。所以慎独,则是专指独处而言。如「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慎独紧切处。
黄灏谓:「戒惧是统体做工夫,慎独是又于其中紧切处加工夫,犹一经一纬而成帛。」先生以为然。
问「慎独」。曰:「是从见闻处至不睹不闻处皆戒慎了,又就其中于独处更加慎也。是无所不慎,而慎上更加慎也。」
问:「『不睹不闻』者,己之所不睹不闻也;『独』者,人之所不睹不闻也。如此看,便见得此章分两节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闻』,『其』之一字,便见得是说己不睹不闻处,只是诸家看得自不仔细耳。」又问:「如此分两节工夫,则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万物育』亦各有归着。」曰:「是。」
「戒慎」一节,当分为两事,「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如言「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是防之于未然,以全其体;「慎独」,是察之于将然,以审其几。
问:「『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与『慎独』两段事,广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慎恐惧,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慎独,则于善恶之几,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论『道不可离』,则先其戒慎,而后其慎独;舜论人心、道心,则先其惟精,而后其惟一。」曰:「两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闻时固当持守,然不可不察;慎独时固当致察,然不可不持守。」人杰录云:「汉卿问云云。先生曰:『不必分「惟精惟一」于两段上。但凡事察之贵精,守之贵一。如戒慎恐惧,是事之未形处;慎独,几之将然处。不可不精察而慎守之也。』」
问:「『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与『慎独』虽不同,若下工夫皆是敬否?」曰:「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只是常惺惺在这里,静不是睡着了。」
问:「『不睹不闻』与『慎独』何别?」曰:「上一节说存天理之本然,下一节说遏人欲于将萌。」又问:「能存天理了,则下面慎独,似多了一截。」曰:「虽是存得天理,临发时也须点检,这便是他密处。若只说存天理了,更不慎独,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问:「致中是未动之前,然谓之戒惧,却是动了。」曰:「公莫看得戒慎恐惧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惊惶震惧,略是个敬模样如此。然道着『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来,便在这里。伊川所谓『道个「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则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这里。如人之气,才呼便出,吸便入。」赐。
问「中庸戒惧慎独,学问辨行,用工之终始」。曰:「只是一个道理,说着要贴出来,便有许多说话。」又问:「是敬否?」曰:「说着『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来,便在这里。」
问:「『不闻不睹』与『慎独』如何?」曰:「『独』字又有个形迹在这里可慎。不闻不见,全然无形迹,暗昧不可得知。只于此时便戒慎了,便不敢。」卓才。
问:「『慎独』是念虑初萌处否?」曰:「此是通说,不止念虑初萌,只自家自知处。如小可没紧要处,只胡乱去,便是不慎。慎独是己思虑,己有些小事,已接物了。『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未有事时;在『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之时,『慎独』,便已有形迹了。『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诗人言语,只是大纲说。子思又就里面剔出这话来教人,又较紧密。大抵前圣所说底,后人只管就里面发得精细。如程子横渠所说,多有孔孟所未说底。伏羲画卦,只就阴阳以下,孔子又就阴阳上发出太极,康节又道:『须信画前元有易。』濂溪太极图又有许多详备。」问:「气化形化,男女之生是气化否?」曰:「凝结成个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阴阳。无物不是阴阳。」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事物虽未有。其理则具。」可学录云:「慎独已见于用。孔子言语只是混合说。子思恐人不晓,又为之分别。大凡古人说话,一节开一如伏羲易只就阴阳以下,至孔子又推本于太极,然只曰『易有太极』而已。至濂溪乃画出一图,康节又论画前之易。」
问:「『慎独』,莫只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处,也与那闇室不欺时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这独也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椿。
问:「『慎独』章:『迹虽未形,几则已动。人虽不知,己独知之。』上两句是程子意,下两句是游氏意,先生则合而论之,是否?」曰:「然。两事只是一理。几既动,则己必知之;己既知,则人必知之。故程子论杨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个知。』」
问:「『迹虽未形,几则已动。』看『莫见、莫显』,则已是先形了,如何却说『迹未形,几先动』?」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是大纲说。」
「吕子约书来,争『「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只管滚作一段看』。某答它书,江西诸人将去看,颇以其说为然。彭子寿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须臾离,且是大体说。到慎独处,尤见于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吕家之学,重于守旧,更不论理。」德明问:「『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是言道之体段如此;『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慎恐惧,君子必慎其独,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发之,如何滚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须臾离』,言道之至广至大者;『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极者。」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非谓于睹闻之时不戒惧也。言虽不睹不闻之际,亦致其慎,则睹闻之际,其慎可知。此乃统同说,承上「道不可须臾离」,则是无时不戒惧也。然下文慎独既专就已发上说,则此段正是未发时工夫,只得说「不睹不闻」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上既统同说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动处,虽至隐微,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尤当致慎。如一片止水,中间忽有一点动处,此最紧要着工夫处!
问:「『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以下是存养工夫,『莫见乎隐』以下是检察工夫否?」曰:「说『道不可须臾离』,是说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惧戒慎,做存养工夫。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说不可不慎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慎独,察其私意起处防之。只看两个『故』字,便是方说入身上来做工夫也。圣人教人,只此两端。」
问:「『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或问中引『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如何?」曰:「不呼唤时不见,时常准备着。」德明指坐合问曰:「此处便是耳目所睹闻,隔窗便是不睹也。」曰:「不然。只谓照管所不到,念虑所不及处。正如防贼相似,须尽塞其来路。」次日再问:「『不睹不闻』,终未莹。」曰:「此须意会。如或问中引『不见是图』,既是不见,安得有图?只是要于未有兆朕、无可睹闻时而戒惧耳。」又曰:「『不睹不闻』是提其大纲说,『慎独』乃审其微细。方不闻不睹之时,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谓『独』,即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极是要戒惧。自来人说『不睹不闻』与『慎独』,只是一意,无分别,便不是。」
问:「林子武以慎独为后,以戒惧为先。慎独以发处言,觉得也是在后。」曰:「分得也好。」又问:「余国秀谓戒惧是保守天理,慎独是检防人欲。」曰:「也得。」又问:「觉得戒慎恐惧与慎独也难分动静。静时固戒慎恐惧,动时又岂可不戒慎恐惧?」曰:「上言『道不可须臾离』,此言『戒惧其所不睹不闻』与『慎独』,皆是不可离。」又问:「泳欲谓戒惧是其常,慎独是慎其所发。」曰:「如此说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须臾离』,故言『戒慎恐惧其所不睹不闻』;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言『慎独』。」又曰:「『戒慎恐惧』是由外言之以尽于内,『慎独』是由内言之以及于外。」问:「自所睹所闻以至于不睹不闻,自发于心以至见于事,如此方说得『不可须臾离』出。」曰:「然。」
问:「中庸工夫只在『戒慎恐惧』与『慎独』。但二者工夫,其头脑又在道不可离处。若能识得全体、大用皆具于心,则二者工夫不待勉强,自然进进不已矣。」曰:「便是有个头脑。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古人因甚冠之章首?盖头脑如此。若识得此理,则便是勉强,亦有个着落矣。」又问:「『费隐』一章云:『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能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尝云:『此处难看。』近思之,颇看得透。侯氏说夫子问礼,问官,与夫子不得位,尧舜病博施,为不知不能之事,说得亦粗。止是寻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说着『及其至也』之意。此是圣人看得彻底,故于此理亦有未肯自居处。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类,真是圣人有未能处。又如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是圣人不敢自以为知。『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此是圣人不敢以为能处。」曰:「夫妇之与知能行是万分中有一分,圣人不知不能是万分中欠得一分。」又问:「以实事言之,亦有可言者,但恐非立教之道。」先生问:「如何?」曰:「夫子谓『事君尽礼,人以为谄。』相定公时甚好,及其受女乐,则不免于行,是事君之道犹有未孚于人者。又如原壤登木而歌,『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则以杖叩胫,近于太」曰:「这里说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恶,若要理会,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于夷俟之时,不可教诲,故直责之,复叩其胫,自当如此。若如正淳说,则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
共父问「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曰:「『中』字是状性之体。性具于心,发而中节,则是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以下中和。
答徐彦章问「中和」,云:「喜怒哀乐未发,如处室中,东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谓中也。及其既发,如已出门,东者不复能西,南者不复能北。然各因其事,无所乖逆,所谓和也。」
问:「喜怒哀乐之未发,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体。及其酬酢万变,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则事得其宜,不相凌夺,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节,则为不知,便自有碍,不可谓之达道矣。」曰:「然。」又问:「于学者如何皆得中节?」曰:「学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须且逐件使之中节,方得。此所以贵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无一事之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各求其中节,此所以为难也。」
自「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怎生地?这个心纔有这事,便有这个事影见;纔有那事,便有那个事影见?这个本自虚灵,常在这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须恁地,方能中只恁地黑淬淬地在这里,如何要得发必中节!
中和亦是承上两节说。
中,性之德;和,情之德。
喜怒是阴阳。发各有中节,不中节,又是四象。
「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是论圣人,只是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或曰:「恐众人未发,与圣人异否?」曰:「未发只做得未发。不然,是无大本,道理绝了。」或曰:「恐众人于未发昏了否?」曰:「这里未有昏明,须是还他做未发。若论原头,未发都一般。只论圣人动静,则全别;动亦定,静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发之中;自其感物而动,全是中节之和。众人有未发时,只是他不曾主静看,不曾知得。」
问:「恻隐羞恶,喜怒哀乐,固是心之发,晓然易见处。如未恻隐羞恶,喜怒哀乐之前,便是寂然而静时,然岂得皆块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闻见,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举动,不审此时唤作如何?」寓录云:「不知此处是已发未发?」曰:「喜怒哀乐未发,只是这心未发耳。其手足运动,自是形体如此。」寓录云:「其形体之行动则自若。」
未发之前,万理备具。纔涉思,即是已发动;而应事接物,虽万变不同,能省察得皆合于理处。盖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面旋安排也。今说为臣必忠、为子必孝之类,皆是已发。然所以合做此事,实具此理,乃未发也。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只是思虑未萌,无纤毫私欲,自然无所偏倚。所谓『寂然不动』,此之谓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块然之谓。只是这个心自有那未发时节,自有那已发时谓如此事未萌于思虑要做时,须便是中是体;及发于思了,如此做而得其当时,便是和是用,只管夹杂相滚。若以为截然有一时是未发时,一时是已发时,亦不成道理。今学者或谓每日将半日来静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乐未发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气质昏浊,为私欲所胜,客来为主。其未发时,只是块然如顽石相似,劈斫不开;发来便只是那乖底。」曰:「如此,则昏时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吕氏求中,却是已发。如伊川云:『只平日涵养便是。』」又曰:「看来人逐日未发时少,已发时多。」曰:「然。」
已发未发,只是说心有已发时,有未发时。方其未有事时,便是未发;纔有所感,便是已发,却不要泥着。慎独是从戒慎恐惧处,无时无处不用力,到此处又须慎独。只是一体事,不是两炎。
大本用涵养,中节则须穷理之功。
问:「『发而皆中节』,是无时而不戒慎恐惧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发而中若信口说去,信脚行去,如何会中节!」
问:「中庸一篇,学者求其门而入,固在于『慎独』。至下文言中之已发未发者,此正根本处。未发之时,难以加毫末之功。当发之际,欲其中节,不知若何而用工?得非即其所谓『戒慎恐惧』,『莫见乎隐』之心而乃底于中节否?」曰:「慎独是结上文一节之意。下文又自是一节,发明中与常行之道。欲其中节,正当加慎于欲发之际。」
问:「『浑然在中』,恐是喜怒哀乐未发,此心至虚,都无偏倚,停停当当,恰在中间。章句所谓『独立而不近四傍,心之体,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动时恰好处;时中者,已动时恰好处。才发时,不偏于喜,则偏于怒,不得谓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处之得恰好,则无过、不及矣。盖无过、不及,乃无偏倚者之所为;而无偏倚者,是所以能无过、不及也。」
问「浑然不待勉强而自中乎当然之节」。曰:「事事有个恰好处。因言荥阳王哀乐过人,以其哀时直是哀,纔过而乐,亦直是乐。情性之变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问:「未发之中,寂然不动,如何见得是中?」曰:「已发之中,实时中也,中节之谓也,却易见。未发更如何分别?某旧有一说,谓已发之中,是已施去者;未发是方来不穷者,意思大故猛。要之,却是伊川说『未发是在中之义』,最好。」
问:「伊川言『未发之中是在中之义』,如何?」曰:「是言在里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释『中』字。」问:「伊川又云:『只喜怒哀乐不发,便是。』如何说『不发』?」曰:「是言不曾发时。」
伊川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喜怒哀乐未发,无所偏倚,此之谓中。中,性也;「寂然不动」,言其体则然也。大本,则以其无不该遍,而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由是出焉。「『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喜怒哀乐之发,无所乖戾,此之谓「和」。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事则然也。达道,则以其自然流行,而理之由是而出者,无不通焉。先生后来说达道,意不如此。
喜怒哀乐未发,程子「敬而无失」之说甚好。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谓之中,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未说到义理涵养处。」大抵未发已发,只是一项工夫,未发固要存养,已发亦要审察。遇事时时复提起,不可自怠,生放过底心。无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
因论吕与叔说「中」字,大本差了。曰:「他底固不是,自家亦要见得他不是处。」文蔚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乃在中之义。他引虞书『允执厥中』之『中』,是不知『无过、不及之中』,与『在中』之义本自不同。又以为『赤子之心』,又以为『心为甚』,不知中乃喜怒哀乐未发而赤子之心已发。『心为甚』,孟子盖谓心欲审轻重,度长短,甚于权度。他便谓凡言心者,便能度轻重长短,权度有所不及,尤非孟子之意,即此便是差了。」曰:「如今点检他过处都是,自家却自要识中。」文蔚曰:「伊川云:『涵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发自中节矣。』今学者能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之中,而慎独于隐微之际,则中可得矣。」曰:「固是如此,亦要识得。且如今在此坐,卓然端正,不侧东,不侧西,便是中底气象。然人说中,亦只是大纲如此说,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谓之中,非能极其中。如人射箭,期于中红心,射在贴上亦可谓中,终不若他射中红心者。至如和,亦有大纲唤做和者,比之大段乖戾者,谓之和则可,非能极其和。且如喜怒,合喜三分,自家喜了四分;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分,便非和矣。」
问:「吕氏言:『中则性也。』或谓此与『性即理也』语意似同。铢疑不然。」先生曰:「公意如何?」铢曰:「理者,万事万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无不具者也。故谓性即理则可。中者,又所以言此理之不偏倚、无过不及者,故伊川只说『状性之体段』。」曰:「『中』是虚字,『理』是实字,故中所以状性之体段。」铢曰:「然则谓性中可乎?」曰:「此处定有脱误,性中亦说得未尽。」铢因言:「或问中,此等处尚多,略为说破亦好。」先生曰:「如何解一一嚼饭与人吃!」
吕氏「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说得亦好。德明录云:「伊川不破此说。」
问:「吕与叔云:『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南轩辨昭昭为已发,恐太过否?」曰:「这辨得亦没意思。敬夫太聪明,看道理不子细。伊川所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吕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后来又救前说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此语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观其所见如何。』此语甚圆,无病。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不得其意,则从那处推得出来?」问:「心本是个动物,不审未发之前,全是寂然而静,还是静中有动意?」曰:「不是静中有动意。周子谓『静无而动有』。静不是无,以其未形而谓之无;非因动而后有,以其可见而谓之有耳。横渠『心统性情』之说甚善。性是静,情是动。心则兼动静而言,或指体,或指用,随人所看。方其静时,动之理只在。伊川谓:『当中时,耳无闻,目无见,然见闻之理在,始得。及动时,又只是这静底。』」淳举伊川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曰:「动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见天地之心。如十月岂得无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贞』,元是萌芽初出时,亨是长枝叶时,利是成遂时,贞是结实归宿处。下梢若无这归宿处,便也无这元了。惟有这归宿处,元又从此起。元了又贞,贞了又元,万古只如此,循环无穷,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说已尽了。十月万物收敛,寂无踪迹,到一阳动处,生物之心始可见。」曰:「一阳之复,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处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处;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复。如睡到忽然醒觉处,亦是复底气象。又如人之沉滞,道不得行,到极处,忽少亨达,虽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复。这道理千变万化,随所在无不浑沦。」
先生问铢曰:「伊川说:『善观者,却于已发之时观之。』寻常看得此语如何?」铢曰:「此语有病。若只于已发处观之,恐无未发时存养工夫。」先生曰:「杨吕诸公说求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伊川又说于已发处观,如此则是全无未发时放下底。今且四平着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无一毫思虑。及至事物来时,随宜应接,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哀乐则哀乐。喜怒哀乐过了,此心湛然者,还与未发时一般,方是两下工夫。若只于已发处观,则是已发了,又去已发,展转多了一层,却是反鉴。看来此语只说得圣人之止,如君止于仁,臣止于敬,是就事物上说理,却不曾说得未发时心,后来伊川亦自以为未当。」铢曰:「此须是动静两下用工,而主静为本。静而存养,方始动而精明。」曰:「只为诸公不曾说得静中未发工夫。如胡氏兄弟说得已发事大猛了。」铢曰:「先生中和旧说,已发其义。」先生因言当时所见次第云云。
龟山说「喜怒哀乐未发」,似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
[莹田-玉]以所论湖南问答呈先生。先生曰:「已发未发,不必大泥。只是既涵养,又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若戒惧不睹不闻,便是通贯动静,只此便是工夫。至于慎独,又是或恐私意有萌处,又加紧切。若谓已发了更不须省察,则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发后省察。今湖南诸说,却是未发时安排如何涵养,已发时旋安排如何省察。」必大录云:「存养省察,是通贯乎已发未发功夫。未发时固要存养,已发时亦要存养。未发时固要省察,已发时亦要省察。只是要无时不做功夫。若谓已发后不当省察,不成便都不照管他。胡季随谓譬如射者失傅弦上始欲求中,则其不中也必矣。某谓『内志正,外体直』,觑梁取亲所以可中,岂有便闭目放箭之理!」
再论湖南问答,曰:「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谓如水长长地流,到高处又略起伏则个。如恐惧戒慎,是长长地做;到慎独,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辍地做。又如骑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险处,便加些提控。不成谓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发时当以理义涵养。」曰:「未发时着理义不得,纔知有理有义,便是已发。当此时有理义之原,未有理义条件。只一个主宰严肃,便有涵养工夫。伊川曰:『敬而无失便是,然不可谓之中。但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无涵养者,临事必不能强勉省察。」曰:「有涵养者固要省察,不曾涵养者亦当省察。不可道我无涵养工夫后,于已发处更不管他。若于发处能点检,亦可知得是与不是。今言涵养,则曰不先知理义底涵养不得;言省察,则曰无涵养,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担阁。」又曰:「如涵养熟者,固是自然中便做圣贤,于发处亦须审其是非而行。涵养不熟底,虽未必能中节,亦须直要中节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论中:○五峰与曾书。○吕书。○朱中庸说。○易传说「感物而动」,不可无「动」字,自是有动有静。○据伊川言:「中者,寂然不动。」已分明。○未发意,亦与戒慎恐惧相连,然似更提起自言。此大本虽庸、圣皆同,但庸则愦愦,圣则湛然。某初言此者,亦未尝杂人欲而说庸也。○如说性之用是情,心即是贯动静,却不可言性之用。○「在中」,只言喜怒哀乐未发是在中。如言一个理之本,后方就时上事上说过与不及之中。吕当初便说「在中」为此「时中」,所以异也。
「在中」之义,大本在此,此言包得也。至如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亦有不偏倚气象。
问:「中庸或问曰:『若未发时,纯一无伪,又不足以名之。』此是无形影,不可见否?」曰:「未发时,伪不伪皆不可见。不特赤子如此,大人亦如此。」淳曰:「只是大人有主宰,赤子则未有主宰。」曰:「然。」
问:「中庸或问说,未发时耳目当亦精明而不可乱。如平常着衣吃饭,是已发,是未发?」曰:「只心有所主着,便是发。如着衣吃饭,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发。」
问:「或问中『坤卦纯阴不为无阳』之说,如何?」曰:「虽十月为坤,十一月为复,然自小雪后,其下面一画,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阳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尔。故十月谓之『阳月』,盖嫌于无阳也。自姤至坤亦然。」曰:「然则阳毕竟有尽时矣。」曰:「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其间不容息也。」
问「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曰:「喜怒哀乐如东西南北,不倚于一方,只是在中间。」又问「和」。曰:「只是合当喜,合当怒。如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过其节;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又问:「『达』字,旧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见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节,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为合当喜;怒,天下以为合当怒,只是这个道理,便是通达意。『大本、达道』,而今不必说得张皇,只将动静看。静时这个便在这里,动时便无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问「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唤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问:「看见工夫先须致中?」曰:「这个也大段着脚手不得。若大段着脚手,便是已发了。子思说『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说,要人会得。只是略略地约住在这里。」又问:「发须中节,亦是倚于一偏否?」曰:「固是。」因说:「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达道也。』别人也不敢恁地说。『君子而时中』,便是恁地看。」以下「致中和」。
「致中和」,须兼表里而言。致中,欲其无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则欲其无少差缪,而又能无适不然。
「致中和。」所谓致和者,谓凡事皆欲中若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须有偏过四旁时。但久久纯熟,自别。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收其放心」,「操则存」,此等处乃致中也。至于充广其仁义之心等处,乃致和也。
周朴纯仁问「致中和」字。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义。且如此暖合,人皆以火炉为中,亦是须要去火炉中寻个至中处,方是的当。又如射箭,纔上红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须是射中红心之中,方是。如『致和』之『致』,亦同此义。『致』字工夫极精密也。」自修。
问:「未发之中是浑沦底,发而中节是浑沦底散开。『致中和』,注云:『致者,推而至其极。』『致中和』,想也别无用工夫处,只是上戒慎恐惧乎不睹不闻,与慎其独,便是致中和底工夫否?」曰:「『致中和』,只是无些子偏倚,无些子乖戾。若大段用倚靠,大段有乖戾底,固不是;有些子倚靠,有些子乖戾,亦未为是。须无些子倚靠,无些子乖戾,方是『致中和』。」
存养是静工夫。静时是中,以其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也。省察是动工夫。动时是和。才有思为,便是动。发而中节无所乖戾,乃和也。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其动时,发皆中节,止于其则,乃艮之「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动中之静也。穷理读书,皆是动中工夫。
问:「中有二义:不偏不倚,在中之义也;无过不及,随时取中也。无所偏倚,则无所用力矣。如吕氏之所谓『执』,杨氏之所谓『验』、所谓『体』,是皆欲致力于不偏不倚之时,故先生于或问中辨之最详。然而经文所谓『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之一字,岂全无所用其力耶?」曰:「致者,推至其极之谓。凡言『致』字,皆此意。如大学之『致知』,论语『学以致其道』,是也。致其中,如射相似,有中贴者,有中垛者,有中红心之边晕者,皆是未致。须是到那中心,方始为致。致和亦然,更无毫厘丝忽不尽,如何便不用力得!」问:「先生云:『自戒慎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则天地可位。』所谓『约』者,固异于吕杨所谓『执』、所谓『验』、所谓『体』矣,莫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是要存得。」问:「孟子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是此意否?」曰:「然。伊川所谓『只平日涵养底便是也』。」枅。僩录云:「问『致』字之义。曰『致者,推至其极之谓』云云。问:『吕氏所谓「执」,杨氏所谓「验」、所谓「体」,或问辨之已详。延平却云:「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气象为如何。」「验」字莫亦有吕杨之失否?』曰:『它只是要于平日间知得这个,又不是昏昏地都不管也。』」
或问:「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与喜怒哀乐不相干,恐非实理流行处。」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间何事不系在喜怒哀乐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赏之,而千万人劝;怒一人而罚之,而千万人惧;以至哀矜鳏寡,乐育英才,这是万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长幼相处相接,无不是这个。即这喜怒中节处,便是实理流行,更去那处寻实理流行!」
问:「『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时。」问:「如此,则须专就人主身上说,方有此功用?」曰:「规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随一个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学之为王者事。问:「向见南轩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术。」曰:「也要在下人心术是当,方可扶持得。」问:「今日士风如此,何时是太平?」曰:「即这身心,亦未见有太平之时。」三公燮理阴阳,须是先有个胸中始得。
「天地位,万物育」,便是「裁成辅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则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万物安得而育!
元思问:「『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指在上者而言。孔子如何?」曰:「孔子已到此地位。」
问:「『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如何一日克己于家,便得天下以仁归之?为有此理故也。」赐。
「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便是形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今人不肯恁地说,须要说入高妙处。不知这个极高妙,如何做得到这处。汉儒这几句本未有病,只为说得迫切了,他便说做其事即有此应,这便致得人不信处。佐。
问:「『静时无一息之不中,则阴阳动静各止其所,而天地于此乎位矣。』言阴阳动静何也?」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各有定所,此未有物相感也,和则交感而万物育矣。」问:「未能致中和,则天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陨、地震山崩之类否?」曰:「天变见乎上,地变动乎下,便是天地不位。」
问:「『善恶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达而在上者既日有以病之,则夫梨异之变,又岂穷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如此,则前所谓『力』者,是力分之『力』也。」曰:「然。」又问:「『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且以孔子之事言之,如何是天地万物安泰处?」曰:「在圣人之身,则天地万物自然安泰。」曰:「此莫是以理言之否?」曰:「然。一家一国,莫不如是。」
问:「或问所谓『吾身之天地万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应变曲折之万端,即吾身之万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