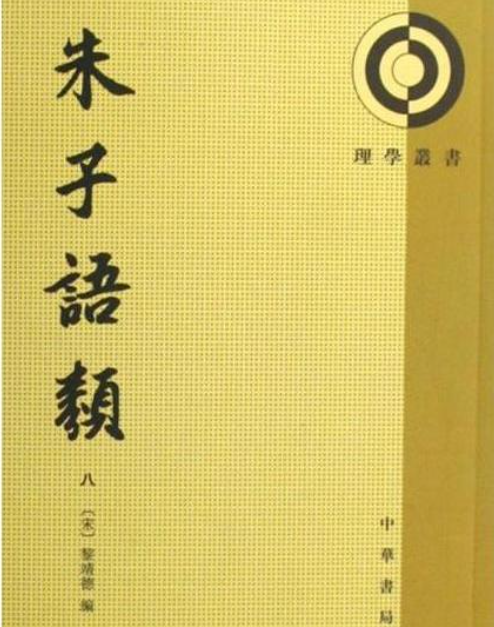论语十九
子罕篇下
法语之言章
「法语之言」,「巽与之言」,巽,谓巽顺。与他说,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逊于汝志」。重处在「不改、不绎」。圣人谓如此等人,与他说得也不济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植说:「此章集注云:『法语,人所敬惮,故必从。然不改,则面从而已。』如汉武帝见汲黯之直,深所敬惮,至帐中可其奏,可谓从矣。然黯论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岂非面从!集注云:『巽言无所乖忤,故必悦。然不绎,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论太王好色、好货,齐王岂不悦。若不知绎,则徒知古人所谓好色,不知其能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徒知古人所谓好货,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先生因曰:「集注中举杨氏说,亦好。」
三军可夺帅章
志若可夺,则如三军之帅被人夺了。做官夺人志。志执得定,故不可夺;执不牢,也被物欲夺去。志真个是不可夺!
衣敝缊袍章
「衣敝缊袍」,是里面夹衣,有绵作胎底。
「衣敝缊袍」,也有一等人资质自不爱者。然如此人亦难得。
先生曰:「李闳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己之无。』吕氏之说亦近此意。然此说又分晓。」
问「子路终身诵之」。曰:「是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这般当事。」[莹田-玉]问:「子路却是能克治。如『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犹要与众人共享了。上蔡论语中说管仲器小处一段,极好。」
问:「『子路终身诵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颜渊处。盖此便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底意思。然他将来自诵,便是『无那无伐善、施劳』意思。」曰:「所谓『终身诵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将这个做好底事,『终身诵之』,要常如此,便别无长进矣。」又问吕氏「贫与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语。曰:「世间人见富贵底,不是心里妒嫉他,便羡慕他,只是这般见识尔!」
谢教问:「『子路终身诵之』,夫子何以见得终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势恁地。这处好,只不合自担当了,便止于此,便是自画。大凡十分好底事,纔自担,便也坏了,所谓『有其善,丧厥善』。」
道怕担了。「何足以臧!」
知者不惑章
「知者不惑。」真见得分晓,故不惑。
道夫问「仁者不忧」。曰:「仁者通体是理,无一点私心。事之来者虽无穷,而此之应者各得其度。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何忧之有!」骧。
「仁者不忧。」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忧之有!
或问:「『仁者不忧』,但不忧,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学问百种,只是要『克己复礼』。若能克去私意,日间纯是天理,自无所忧,如何不是仁。」
陈仲亨说「仁者不忧」,云:「此非仁体,只是说夫子之事。」先生曰:「如何又生出这一项情节!恁地,则那两句也须恁地添一说,始得。这只是统说。仁者便是不忧。」
「勇者不惧。」气足以助道义,故不惧。故孟子说:「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今有见得道理分晓而反慑怯者,气不足也。
或问「勇者不惧」,举程子「明理可以治惧」之说。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惧』未得,盖争一节在,所以圣人曰:『勇者不惧。』」
李闳祖问:「论语所说『勇者不惧』处,作『有主则不惧』。恐『有主』字明『勇』字不出。」曰:「也觉见是如此。多是一时间下字未稳,又且恁地备员去。」因云:「前辈言,解经命字为难。近人解经,亦间有好处,但是下语亲切,说得分晓。若前辈所说,或有不大故分晓处,亦不好。如近来耿氏说易『女子贞不字』。伊川说作『字育』之『字』。耿氏说作『许嫁笄而字』之『字』,言『女子贞不字』者,谓其未许嫁也,却与昏媾之义相通,亦说得有理。」又云:「伊川易亦有不分晓处甚多。如『益之,用凶事』,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当时未见有刺史、郡守,岂可以此说。某谓『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是责难于君之时,必以危言鲠论恐动其君而益之,虽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而通,又非忠以益于君也。」
行夫说「仁者不忧」一章。曰:「『勇者不惧』,勇是一个果勇必行之意,说『不惧』也易见。『知者不惑』,知是一个分辨不乱之意,说『不惑』也易见。惟是仁如何会不忧?这须思之。」行夫云:「仁者顺理,故不忧。若只顺这道理做去,自是无忧。」曰:「意思也是如此,更须细思之。」久之,行夫复云云。曰:「毕竟也说得粗。仁者所以无忧者,止缘仁者之心便是一个道理。看是甚么事来,不问大小,改头换面来,自家此心各各是一个道理应副去。不待事来,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见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恪录别出。
蔡行夫问「仁者不忧」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惧,却易理会。『仁者不忧』,须思量仁者如何会不忧。」蔡云:「莫只是无私否?」方子录云:「或曰:『仁者无私心,故乐天而不忧。』」曰:「固是无私。然所以不忧者,须看得透,方得。」杨至之云:「是人欲净尽,自然乐否?」曰:「此亦只是貌说。」洪庆问:「先生说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来,便有道理应他,所以不忧。方子录云:「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来,便有一理以应之,所以无忧。」恪录一作:「仁者心与理一,心纯是这道理。看甚么事来,自有这道理在处置他,自不烦恼。」人所以忧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个道理应他,便不免有忧。」恪录一作:「今人有这事,却无道理,便处置不来,所以忧。」从周录云:「人所以有忧者,只是处未得。」
方毅父问:「『知者不惑』,明理便能无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无私欲,则不屈于物,故勇。惟圣人自诚而明,可以先言仁,后言知。至于教人,当以知为先。」时举少异。
先生说「知者不惑」章:「惟不惑不忧,便生得这勇来。」
问「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后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盖虽曰『仁能守之』,只有这勇方能守得到头,方能接得去。若无这勇,则虽有仁、知、少间亦恐会放倒了。所以中庸说『仁、知、勇三者』。勇,本是个没紧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则做不到头,半涂而废。」
或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何以与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此诚而明,明而诚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为学者言也。」问:「何以勇皆在后?」曰:「末后做工夫不退转,此方是勇。」
或问:「人之所以忧、惑、惧者,只是穷理不尽,故如此。若穷尽天下之理,则何忧何惧之有?因其无所忧,故名之曰仁;因其无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无所惧,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说孰是?」曰:「仁者随所寓而安,自是不忧;知者所见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惧。夫不忧、不惑、不惧,自有次第。」或曰:「勇于义,是义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人杰录云:「或曰:『勇是勇于义,或是武勇之勇?』曰:『大概统言之,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曰:「三者也须穷理克复,方得。只如此说,不济事。」
问:「『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终之。』看此三句,恐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养,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是持守坚固。」问:「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惧』意思。」曰:「交互说,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知都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行都是仁;『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都是勇。」宙。
可与共学章
「可与共学」,有志于此;「可与适道」,已看见路脉;「可与立」,能有所立;「可与权」,遭变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纲如此说。
问「可与适道」章。曰:「这个只说世人可与共学底,未必便可与适道;可与适道底,未必便可与立;可与立底,未必便可与权。学时,须便教可适道;适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须教权去。」
或问:「『可与立』,是如『嫂叔不通问』;『可与权』,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
问:「权,地位如何?」曰:「大贤已上。」
权,是称量教子细着。
问:「权便是义否?」曰:「权是用那义底。」问:「中便是时措之宜否?」曰:「以义权之,而后得中。义似称,权是将这称去称量,中是物得其平处。」
经自经,权自权。但经有不可行处,而至于用权,此权所以合经也,如汤、武事,伊、周事,嫂溺则援事。常如风和日暖,固好;变如迅雷烈风。若无迅雷烈风,则都旱了,不可以为常。
苏宜久问「可与权」。曰:「权与经,不可谓是一件物事。毕竟权自是权,经自是经。但非汉儒所谓权变、权术之说。圣人之权,虽异于经,其权亦是事体到那时,合恁地做,方好。」时举同。
「可与立,未可与权」,亦是甚不得已,方说此话。然须是圣人,方可与权。若以颜子之贤,恐也不敢议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缁,如何更说权变?所谓「未学行,先学走」也。
先生因说:「『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处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当用,小人固当去。然方当小人进用时,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当其深根固蒂时,便要去他,即为所害。这里须斟酌时宜,便知个缓急深浅,始得。」或言:「本朝人才过于汉唐,而治效不及者,缘汉唐不去攻小人,本朝专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说,所谓『内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乱恁地说,不知何等议论!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恐出此。」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叔重问:「程子云:『权者,言称锤之义也。何物以为权?义是也。然也只是说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刚者以为可诛,性之宽者以为可恕,概之以义,皆未是合宜。此则全在权量之精审,然后亲审不差。欲其权量精审,是他平日涵养本原,此心虚明纯一,自然权量精审。伊川常云:『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义以为质,则礼以行之。』」
问经、权之别。曰:「经与权,须还他中央有个界分。如程先生说,则无界分矣。程先生『权即经』之说,其意盖恐人离了经,然一滚来滚去,则经与权都鹘突没理会了。」又问:「权是称锤也。称衡是经否?」曰:「这个以物譬之,难得亲切。」久之,曰:「称得平,不可增加些子,是经;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权,依旧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经亦须合道也。」
问经、权。曰:「权者,乃是到这地头,道理合当恁地做,故虽异于经,而实亦经也。且如冬月便合着绵向火,此是经。忽然一日暖,则亦须使扇,当风坐,此便是权。伊川谓『权只是经』,意亦如此。但说『经』字太重,若偏了。汉儒『反经合道』之说,却说得『经、权』两字分晓。但他说权,遂谓反了经,一向流于变诈,则非矣。」
用之问:「『权也者,反经而合于道』,此语亦好。」曰:「若浅说,亦不妨。伊川以为权便是经。某以为反经而合于道,乃所以为经。如征伐视揖逊,放废视臣事,岂得是常事?但终是正也。」
或问:「伊川云:『权即是经。』汉儒云:『反经合道。』其说如何?」曰:「伊川所说权,是说这处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须是晓得他意。汉儒语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横说,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又曰:「『男女授受不亲』,是常经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也。忽然天气做热,便须衣夹挥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公羊就宋人执祭仲处,说得权又怪异了。」又曰:「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
吴伯英问:「伊川言『权即是经』,何也?」曰:「某常谓不必如此说。孟子分明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与经岂容无辨!但是伊川见汉儒只管言反经是权,恐后世无忌惮者皆得借权以自饰,因有此论耳。然经毕竟是常,权毕竟是变。」又问:「某欲以『义』字言权,如何?」曰:「义者,宜也。权固是宜,经独不宜乎?」
问:「经、权不同,而程子云:『权即经也。』」曰:「固是不同: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时多。」又曰:「权是时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赐。
或问:「『反经合道』之说,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说权,权即是经』,如何?」曰:「某常以为程先生不必如此说,是多说了。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如程先生之说,则鹘突了。所谓经,众人与学者皆能循之;至于权,则非圣贤不能行也。」
或有书来问经、权。先生曰:「程子固曰:『权即经也。』人须着子细看,此项大段要子细。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须是合义也。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此是权也。若日日时时用之,则成甚世界了!」或云:「权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时之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然舜禹之后六七百年方有汤;汤之后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权也是难说。故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到得可与权时节,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
或问经与权之义。曰:「公羊以『反经合道』为权,伊川以为非。若平看,反经亦未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经,不可易者。汤武之诛桀纣,却是以臣弒君;周公之诛管蔡,却是以弟杀兄,岂不是反经!但时节到这里,道理当恁地做,虽然反经,却自合道理。但反经而不合道理,则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于经乎!」又曰:「合于权,便是经在其中。」正甫谓:「『权、义举而皇极立』,权、义只相似。」曰:「义可以总括得经、权,不可将来对权。义当守经,则守经;义当用权,则用权,所以谓义可以总括得经、权。若可权、义并言,如以两字对一字,当云『经、权举』乃可。伊川曰:『惟义无对。』伊川所谓『权便是经』,亦少分别。须是分别经、权自是两物;到得合于权,便自与经无异,如此说乃可。」
问:「『可与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见得那正当底道理分明了,不为事物所迁惑。」又问:「程子谓『权只是经』,先生谓:『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莫是经是一定之理,权则是随事以取中;既是中,则与经不异否?」曰:「经,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通变底道理。权得其中,固是与经不异,毕竟权则可暂而不可常。如尧舜揖逊,汤武征诛,此是权也,岂可常行乎!观圣人此意,毕竟是未许人用『权』字。学者须当先理会这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别君子小人,君子则进之,小人则去之,此便是正当底道理。今人不去理会此,却说小人亦不可尽去,须放他一路,不尔,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济事者,但终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并进,则岂可也?」
亚夫问「可与立,未可与权」。曰:「汉儒谓『反经合道』为权;伊川说『权是经所不及者』。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盖权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热病者当服叙药,冷病者当服热药,此是常理。然有时有热病,却用热药去发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药去发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论者。然须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厘之差,便至于杀人,不是则剧。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这个物事。既是合用,此权也,所以为经也。大抵汉儒说权,是离了个经说;伊川说权,便道权只在经里面。且如周公诛管蔡,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其推刃于同气者虽同,而所以杀之者则异。盖管蔡与商之遗民谋危王室,此是得罪于天下,得罪于宗庙,盖不得不诛之也。若太宗,则分明是争天下。故周公可以谓之权,而太宗不可谓之权。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谓之权,而在他人则不可也。权是最难用底物事,故圣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贤以上,自见得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因论「经、权」二字,曰:「汉儒谓『权者,反经合道』,却是权与经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实未尝反经』,权与经又却是一个,略无分别。恐如此又不得。权固不离于经,看『可与立,未可与权』,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事』,毫厘之间,亦当有辨。」文蔚曰:「经是常行之理,权是适变处。」曰:「大纲说,固是如此。要就程子说中分别一个异同,须更精微。」文蔚曰:「权只是经之用。且如称衡有许多星两,一定而不可易。权往来称物,使轻重恰好,此便是经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纲都是,只争些子。伊川又云:『权是经所不及者。』此说方尽。经只是一个大纲,权是那精微曲折处。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经常之道,如何动得!其间有该不尽处,须是用权。权即细密,非见理大段精审,不能识此。『可与立』,便是可与经,却『未可与权』,此见经权毫厘之间分别处。庄子曰:『小变而不失其大常。』」或曰:「庄子意思又别。」曰:「他大概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将甚做大常。」僩录别出。
经与权之分,诸人说皆不合。曰:「若说权自权,经自经,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说事须用权,经须权而行,权只是经,则权与经又全无分别。观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则权与经须有异处。虽有异,而权实不离乎经也。这里所争只毫厘,只是诸公心粗,看不子细。伊川说:『权只是经』,恐也未尽。尝记龟山云:『权者,经之所不及。』这说却好。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底道理而已。盖精微曲折处,固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所以说『中之为贵者权』,权者即是经之要妙处也。如汉儒说『反经合道』,此语亦未甚病。盖事也有那反经底时节,只是不可说事事要反经,又不可说全不反经。如君令臣从,父慈子孝,此经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处,经所行不得处,也只得反经,依旧不离乎经耳,所以贵乎权也。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立便是经。『可与立』,则能守个经,有所执立矣,却说『未可与权』。以此观之,权乃经之要妙微密处。非见道理之精密、透彻、纯熟者,不足以语权也。」又曰:「庄子曰『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经权之别。」或曰:「恐庄子意思又别。」曰:「他大概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么做大常。」又云:「事有缓急,理有小大,这样处皆须以权称之。」们问:「『子莫执中。』程子之解经便是权,则权字又似海说。如云『时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则似事事皆用权。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则『权』字须有别。」曰:「『执中无权』,这『权』字稍轻,可以如此说。『嫂溺援之以手』之权,这『权』字却又重,亦有深浅也。」
问:「伊川谓『权只是经』,如何?」曰:「程子说得却不活络。如汉儒之说权,却自晓然。晓得程子说底,得知权也是常理;晓不得他说底,经权却鹘突了。某之说,非是异程子之说,只是须与他分别,经是经,权是权。且如『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是经也。有时天之气变,则冬日须着饮水,夏日须着饮汤,此是权也。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使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可数数用。如『舜不告而娶』,岂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观之,那时合如此处。然使人人不告而娶,岂不乱大伦?所以不可常用。」赐。夔孙录详,别出。
问经、权。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是经也。有时行不得处,冬日须饮水,夏日则饮汤,此是权也。此又依前是经。但经是可常之理,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始用权。然当那时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个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观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伦都乱了!因推说汤武事。伊川说『权却是经』,却说得死了,不活。如某说,非是异伊川说,即是须为他分别,经是经,权是权。如汉儒反经之说,却经、权晓然在眼前。伊川说,晓得底却知得权也是常理,晓不得底却鹘突了。如大过卦说:『道无不中,无不常。圣人有小过,无大』某谓不须恁地说,圣人既说有大过,直是有此事。但云『大过亦是常理』,则得。因举晋州蒲事,云:「某旧不晓文定之意。后以问其孙伯逢。他言此处有意思,但难说出。如左氏分明有称晋君无道之说。厉公信有罪,但废之可也。栾书中行偃直杀之则不是。然毕竟厉公有罪,故难说出。后必有晓此意者。」
问:「『可与立,未可与权』,看来『权』字亦有两样。伊川以权只是经,盖每日事事物物上称量个轻重处置,此权也,权而不离乎经也。若论尧舜禅逊,汤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权,是所谓『反经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异耳。如尧舜之禅逊是逊,与人逊一盆水也是逊;汤武放伐是争,争一个弹丸也是争。康节诗所谓『唐虞玉帛烟光紫,汤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尧夫非是爱吟诗』,正此意也。伊川说『经、权』字,将经做个大底物事,经却包得那个权,此说本好。只是据圣人说『可与立,未可与权』,须是还他是两个字,经自是经,权自是权。若如伊川说,便用废了那『权』字始得。只是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如冬日须向火,忽然一日大热,须着使扇,这便是反经。今须是晓得孔子说,又晓伊川之说,方得。若相把做一说,如两脚相并,便行不得。须还他是两只脚,虽是两只,依旧是脚。」又曰:「若不是大圣贤用权,少间出入,便易得走作。」
恭父问「可与立,未可与权」。曰:「『可与立』者,能处置得常事;『可与权』者,即能处置得变事。虽是处变事,而所谓处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此说义与权自不同。汉儒有反经之说,只缘将论语下文『偏其反而』误作一章解,故其说相承曼衍。且看集义中诸儒之说,莫不连下文。独是范纯夫不如此说,苏氏亦不如此说,自以『唐棣之华』为下截。程子所说汉儒之误,固是如此。要之,『反经合道』一句,细思之亦通。缘『权』字与『经』字对说。纔说权,便是变却那个,须谓之反可也。然虽是反那经,却不悖于道;虽与经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说,断然经自是经,权亦是经,汉儒反经之说不是。此说不可不知。然细与推考,其言亦无害,此说亦不可不知。『义』字大,自包得经与权,自在经与权过接处。如事合当如此区处,是常法如此,固是经;若合当如此,亦是义当守其常。事合当如此区处,却变了常法恁地区处,固是权;若合当恁地,亦是义当通其变。文中子云:『权义举而皇极立。』若云『经、权举』,则无害。今云『权、义举』,则『义』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将义来当权。不知经自是义,权亦是义,『义』字兼经、权而用之。若以义对经,恰似将一个包两物之物,对着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经便是权。」曰:「不是说经便是权。经自是经,权自是权。但是虽反经而能合道,却无背于经。如人两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时须一脚先,一脚后,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将左脚便唤做右脚,右脚便唤做左脚。系辞既说『井以辨义』,又说『井居其所而迁』。井是不可动底物事,水却可随所汲而往。如道之正体却一定于此,而随事制宜,自莫不当。所以说『井以辨义』,又云:『井居其所而迁。』」
唐棣之华章
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诗,与今常棣之诗别。常,音裳。尔雅:『棣,栘,似白杨,江东呼夫栘。常棣,棣,子如樱桃可食。』自是两般物。此逸诗,不知当时诗人思个甚底。东坡谓『思贤而不得之诗』,看来未必是思贤。但夫子大概止是取下面两句云:『人但不思,思则何远之有!』初不与上面说权处是一段。『唐棣之华』而下,自是一段。缘汉儒合上文为一章,故误认『偏其反而』为『反经合道』,所以错了。晋书于一处引『偏』字作『翩』,『反』作平声,言其花有翩反飞动之意。今无此诗,不可考据,故不可立为定说。」
或问「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一章。时举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尔。」